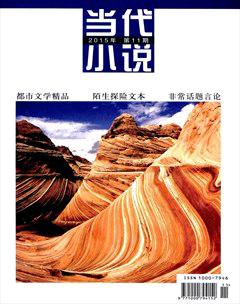车殇
叶雪松
一
我关了电脑,眯上眼皮正要睡觉。九点前,我的困劲儿就上来了,上下眼皮总想亲热地吻在一起。
手机响了起来。快十点了,谁还打电话。我懒洋洋地下地,拿起手机。
手机里传来柳月的声音,哥,鞋厂我干不了,皮肤过敏。
咋回事,你以前不是干过吗?我的困劲瞬间全无。
也不知为啥,刚去了几天,就起了满脸的小痘痘。你不是说给我找到在饭店的活儿吗?你打电话问问,他们还缺人不?
我说好,然后就给我的朋友老孟打电话。一个月前,我给老孟打电话说,让他帮柳月在市内寻一个在饭店打工之类的工作,老孟就留心了。我告诉柳月,老孟把事办妥了,老板娘是他的学生,她随时都可以过去。老板娘我也认识,老孟和我在她那儿吃过好几次饭,人长得漂亮不说,办事还泼辣,高声大嗓的。我交待老孟的事办好了,柳月却说,她想在附近的鞋厂干,我只好告诉老孟,柳月先不去了。没想到,刚去鞋厂没几天,就皮肤过敏。我再次给老孟打电话,问他的学生那儿还缺人不。老孟就和他的学生联系,电话很快回来了,说缺人,工资二千每月起,但没住的地方。我又给柳月回电话,让她和老孟直接联系,柳月说,她找不到地方,让周钢送去。我说,你们刚刚离婚,怎么还让人家给你送去?柳月说,他不把我送去,我找不到。我说,既然如此,何必当初,早干啥来的?孩子死了来奶了。这时,柳月就不说话了。
一个月前,柳月和周钢办理了离婚手续。可怜的柳月,似乎根本就不知道离婚这两个字的严重性。离婚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开弓没有回头箭。离婚的原因只有一个,周钢外头有了人。那女人寻死觅活非要和周钢在一起,柳月怕周钢吃官司,就答应了周钢,拿了周钢给的二十万,乖乖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可见,柳月是那么的爱着周钢。我当时劝她千万不要离婚,周钢的本质还是不错的,男人嘛,过了这个劲儿就好了。可柳月还是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回了娘家。我当时的理解是,柳月是想,过段时间,周钢和那个女人分手再来接她。可事情能顺着她的主观臆想发展吗?
这个天真的傻柳月呀,叽叽喳喳,一点主意也没有。她嘴上说,离婚不后悔,其实,肠子现在都可能悔青了。她想让周钢送她去那个饭店,是不是想和十几天前还是丈夫的前夫在一起重温一下曾经有过的亲情,我不得而知,可这世上,哪来的后悔药?
二
老实说,我并不怎么喜欢柳月,虽然,我只有她这一个妹妹。柳月小时候很刁,稍遇不顺就哇哇大哭,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她上初中。我父母就她这么一个女儿,对她的宠爱程度要在我和弟弟之上。因为她常对我奶奶出言不逊,因而,没少了我的拳打脚踢。直到她出嫁,我和她说话的次数屈指可数。
柳月相过一个对象,父亲没有相中,说小伙子家境不好,人长得瘦弱,不合适,这门亲事就没成。那个小伙子我看过。不久,有人介绍和周钢对象,父亲就同意了。原因很简单,小伙子虽然个子不高,不会说什么,但敦实,一看就钻致,是个过日子的好手,再加上是哥一个儿,柳月嫁过去一定不会受屈。庄稼院的姑娘找人家,就得找这样的。柳月比周钢大三岁,他们对象的时候,柳月二十三岁,周钢二十岁。
柳月毕业后在家做姑娘的时候,父母让她到六里外的小镇上学裁剪。父亲有他一套理论,庄稼院的姑娘,得有一双巧手,到婆家才会被看重。那时候,各式各样的培训班如雨后的蘑菇般出现在镇乡的大街小巷。我弟弟也参加过培训班,不过,学的是厨师。柳月在裁剪班学了两年,一般样式的衣服也都能做得很不错了。也在这时,小镇又出现了规模不一的鞋厂,街上到处是胶皮底子和汽车尾气的混合味道,小镇成了一潭沸腾的活水,柳月和那些渴望挣钱的姑娘们一道,加入了制鞋工人的行列。钱挣了点,父母说,家里不要你一分,留着做嫁妆吧。柳月当时除了学裁剪和进鞋厂做鞋外,几乎什么农活和家务活也没做过。这种情况下,柳月嫁给了周钢,嫁到了四里外的一个村子。
柳月嫁过去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包括我奶奶和姥姥,都为她捏把汗。几年过去,柳月的能干和贤惠在婆家的村子里是出了名的,婆媳关系情同母女,这时候,大家才松了口气。在家娇生惯养,到了婆家就能干了,用我奶奶和姥姥的话来说,这叫发婆家不发娘家。说来也怪,柳月嫁过来没几年,周家的日子就像添了干柴的灶膛,红火得不得了。她婆婆,我叫大姨的是个办事利索的女人,经常在人前夸柳月给他们家带来了福气。周家的活儿多,除了责任田外,又承包了几十亩地,还扣了大棚,一年四季,没有一刻消停的时候。在我的印象里,一年当中,柳月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就是偶尔回来,也是来也匆匆,回也匆匆。我对我妈说,还是儿子吧,闺女,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在家是女,在婆家就是媳。我妈说,过日子不就得干嘛。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我发现,柳月一年里,像一只急速旋转的陀螺,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变成了一个过早衰老的农妇。不过,就是这个与实际年龄不甚相符的柳月,却生养了两个水葱似的姑娘。每次孩子满月,周钢都笑着让我为新生女儿起名字。我给俩孩子起名芙美和婧美。这俩外甥女确实乖巧。老大内敛含蓄,老二恰恰相反,性情奔放。每次,我见了她们,都会逗她们说,要不是我给你俩起这么好的名字,你们俩哪有这么漂亮呢?
柳月说,闺女就是她的全部财富,这辈子,为她们受多大苦,挨多大累,也值当了。周钢是哥一个,他爸他妈也希望柳月给他们家生个儿子,及至看到两个水葱似的孙女,就改变了态度,他妈逢人便说,时代变了,男女都一样。没瞅瞅,现在的男孩,也没个男孩的腰杆,啥男孩女孩,聪明健康就好。看见我这两个孙女,我啥烦恼都没有了。这两孩子和爷爷奶奶的关系也好,过了一周岁,就都睡爷爷奶奶那屋了。我常常见到这样一个场景,逢年过节的,柳月和周钢带着孩子回娘家,有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两个孩子就吵吵着要回去,说想她爷爷奶奶了。这时候,我妈我爸还有柳月周钢就得哄,两个孩子方才作罢,不过,第二天,吃完早饭就得回去。柳月和周钢一家人,可谓其乐融融,让人羡煞。
我有一年多没见过周钢了。最后一次见到他,还是在前年大年初三,柳月和周钢带孩子回来过年的时候。让我惊讶的是,一家人是坐着新买的轿车回来的。我才知道,周钢买了一辆轿车,也是他们村里的第一辆轿车。柳月说,他稀罕一回,就让他买吧。你还不知道吗,你妹夫就喜欢车。我说,一个庄稼人,养轿车有什么用?别得瑟过了火。对于一些条件好的城里人来说,轿车算不上什么,可在农村,谁家要是有了轿车,南北二屯的人都会啧啧赞叹。我担心因车生变,吃团圆饭的时候,我对周钢说,有了车,也别整天招摇过市,要本本分分过日子,别老往卖店超市钻。周钢有个习惯,爱去卖店或超市玩小麻将。关于这个,柳月并不干涉他。我的话音刚落,周钢阴下脸,我是那样的人吗?说着,走了出去。柳月说,我们周钢可不是那样的人。我说,人都是会变的,好人坏人,谁脸上也没贴着标签。
这事儿就过去了,在这一年多时间,我没见到过周钢。我见到过柳月两次,问起周钢,柳月说他忙。我知道他们忙,听柳月说,他们家养了几亩地河蟹,还开着三轮车往邻市的建筑工地上送砖。我时常能想象柳月坐在三轮车上和周钢去邻市疾奔在公路上的情形,柳月扎着一个红色的围巾,脸儿被北风吹得粗糙而酡红。我劝柳月别那么拼,柳月却说,不干咋整,俩孩子,将来用钱的地儿多得是呢。是呀,这两个孩子一个月就得二千来块,不干咋行?虽然我有点心疼柳月,可我却无能为力,帮不上她什么,只能眼睁睁看着她风里来雨里去。柳月和周钢在我们村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大家都说柳月嫁了个好人家,找了个本分钻致的好男人,就连柳月也幸福满满地回忆起我那逝去的父亲独到的眼光。
每年大年初三,我们一家才吃团圆饭,柳月一家才从婆家回到娘家。今年的春节,我没见到周钢和柳月。原因是,他们在初三卖大棚里的韭菜。柳月家有几栋冷棚,说是冷棚,其实,也是要撂草苫子的,只是不生炉子。年前年后,是热卖韭菜的最忙的季节。周钢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是远近闻名的韭菜村。年前年后,韭菜到了收割的季节,收购韭菜的汽车就开到了大棚旁。我兄弟媳妇也常常天不亮就去给人家割韭菜挣点工钱,所以,柳月一家没在初三这天回来吃团圆饭也在情理之中。我和朋友们约定,第二天去邻市拜年,就没等柳月一家。
两个月后,一天晚上,我像往常那样眯着眼睛要睡觉,我的手机不依不饶地响了起来。我有点不耐烦地接通,居然是久不通话的妹妹。
是我。柳月说。
知道。我说。
哥,我要离婚。柳月说。
你要离婚?我以为我的耳朵出了问题,又重复了一遍。说别人离婚我信,说柳月要离婚,我还真有些接受不了。好好的日子,离的啥婚呢?
是的,哥,我要离婚。
为啥?
他和人跑了!
和谁跑了?
我也不知道,听说是市里的,唱歌的小姐。
你怎么就判断他有人了?
他拿了三万块钱,好几天不回家了。
你别捕风捉影。
没有,他承认了。真从你说的话儿上来了。我对他说,你大舅子早就看见你苗头不对,你还不愿意听,现在,让人家说着了吧。他说真让哥说着了,我也不是这样的人呀,也咋干这事儿了呢?
我劝柳月别轻易下定论,看看再说,离婚不是小孩儿过家家,是那么轻易的事吗?柳月撂下电话后,我不住地犯核计。这期间柳月又来过两次电话,我劝她冷静,别冲动,婚姻七年之痒,更何况你们都结婚二十多年了,三个七年之痒了。男人,有时候走点神儿,都可以理解。聪明的女人,是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柳月说,我受不了。我说,你有啥受不了的?你这样闹下去,只会适得其反。柳月沉吟了一会儿,说,哥,我听你的,再观察他一段时间。
几天后,柳月的电话又来了。
哥,和周钢在一起的女人你猜是谁?
我哪儿知道?
是后街陈明的媳妇张金玲。
我惊呆了。张金玲,不就是经常给他们家割韭菜的那个小媳妇吗?这个女人我认识。身材不高,挺白净。离过一次婚后才嫁给陈明的,给陈明生了个儿子。有一年,柳月家卖韭菜时,她去帮忙给大伙做饭,柳月把她介绍给我认识。这女人嘴儿甜,不笑不说话,冲我一口一个大哥地叫着。
柳月说,我早就觉察出他俩的眼神不对劲,可我没想到会是她。
我似乎听到了柳月的哭声。
这社会是怎么了,连周钢都出轨了。
三
天还没亮,寒夜的天幕上,星光在眨着眼。
柳月和周钢在大棚里看着雇来的割韭菜的人们。这是头茬韭菜,必须赶在初二这天装车卖出去。周钢已经联系好了买主,车就在大棚外边等着。头刀的黑韭菜,批发每斤三块。这一刀下来,就能割上万斤,卖三万多块钱。割韭菜的都是附近村屯的女人,也有前街后院的。人们的头上都戴着一盏灯,大棚里湿漉漉的,雾气很重,不时地从棚顶往下边掉着水滴。早上割的韭菜嫩,还压秤。人们帽子上的灯光一明一暗,像繁星点点,没有人说话,只听得韭菜刀割韭菜时的沙沙声。
第一棚的韭菜割完了,大家坐在地垄上歇着,柳月在发矿泉水,面前人影一闪,柳月抬头,是张金玲。
金玲,渴了吧!柳月将一瓶矿泉水递过去。
张金玲没接,说,嫂子,我想让我大哥送我回去,刚才,孩子打来电话,说肚子疼。
陈明没在家吗?
他在家,可孩子却哭着找我。你知道,陈明那个人,啥事儿上过阵呢?
柳月对他们家再了解不过了。他们两家只隔着一条街,柳月嫁过来的时候,坐的是手扶拖拉机,开拖拉机的就是陈明他爸。前几年,陈明他爸脑出血去世了,没事的时候,陈明就带媳妇到他们家来串门。周钢那时刚买了一辆大三轮子,去清河门拉煤。陈明也有一辆三轮,周钢和柳月就带着陈明两口子一块儿去。陈明老实,木讷,不擅交际,家里家外的事,都是媳妇一个人说了算。
柳月说,周钢,你就送金玲回去吧,孩子肚子疼,别再出啥事。
周钢就骑着摩托送张金玲回去了。大棚外正是冷得鬼呲牙的时候,柳月怕周钢冻着,拿起一件军大衣追了出去。柳月走出大棚,正遇到周钢在踩摩托车。柳月正要喊他,却发现张金玲坐了上去,搂住周钢的后腰,将脸贴在他的后背上。柳月揉了揉眼睛,周钢骑着摩托车驶出了大棚区。事后,柳月对周钢说,张金玲和你关系不一般呀!周钢说,胡说,我和她关系咋不一般了。周钢就把看到的一幕说了,周钢说,黑灯瞎火的,你是不是看花眼了?张金玲说冻手,在地里蹲了半天,腿脚麻,上不去摩托车,就扶了一下我的腰。周钢这样说,柳月也就无话可说。
日子不咸不淡地往前过,柳月也没觉察出什么。柳月是个很容易感到满足的人。丈夫虽然是哥一个,却有两个姑姐。姑姐多婆婆就多。柳月硬是用贤淑和勤快在婆家和整个村子赢得了较好的口碑。柳月初嫁来时,周钢家只是四间砖房,周钢的爷爷奶奶还在世。柳月提议,把新房安在西厢房。说是厢房,其实就是一间半低矮得伸手及檐光线阴暗的下屋。柳月就是在这个下屋里生了两个孩子,一住就是十三年。后来,周钢的爷爷奶奶相继过世,家境条件渐渐好起来了,把原来的四间砖房翻盖了,柳月这才住上了新居。周钢为人低调,不张扬,我们都为柳月感到欣慰。
我们家,包括我们屯认识柳月的人,柳月的同学什么的,也都无一例外地羡慕柳月。我们都觉得柳月的婚姻稳固传统长久。可是,谁也没想到,柳月的婚姻竟亮起了红灯,老实淳厚的周钢跟着有夫之妇的张金玲跑了。
这件事在我们家,在周钢家,无异于引爆了一枚炸弹。没有任何征兆,周钢在外面有人了。在农村,这种事,可能屯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只有当事人的配偶及其家人还蒙在鼓里。不过,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还是让柳月知道了。透露这件事的人是和柳月一起扣大棚的冯六儿媳妇。
那天,柳月和冯六儿媳妇去赶集。农村的集市上也多了些精品屋,冯六儿媳妇对柳月说,嫂子,咱俩也逛逛精品屋呗,遇到合适的就买一件。柳月说好哇,两人就逛了几家精品屋。最后,柳月在一件新款韩版的毛衫前停下了脚步。柳月问多少钱,年轻漂亮的店员说三百九十九,不打折。柳月嫌贵,摸着毛衫反复在身上比试,最后又让店员挂上。冯六儿媳妇说,嫂子,你家这刀韭菜刚卖了三万多,买件毛衫算什么?你为那个家出了多少力,别将来干来干去,自己啥也弄不着。柳月说,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讲究啥?能省一分是一分,咱们乡下人,一个汗珠掉地下摔八瓣,容易吗?一会儿,我给你钢哥挑双鞋。
嫂子,你就知道惦记我钢哥,咋就割不舍为自己花钱呢?你还不知道吧,我钢哥在别人身上一出手就上千。冯六儿媳妇说。
别人身上?谁身上?柳月看着冯六儿媳妇。
我是说,我钢哥有时请别人吃饭,一出手就上千。冯六儿媳妇说。
柳月笑了,说,往工地上送料,不请人吃顿饭咋行?哪顿饭都花个千八百的。
起初,柳月并未将冯六儿媳妇的话当回事,可回到家里躺在炕上越想越觉得冯六儿媳妇的话里有话。那天晚上,柳月将周钢推出了被窝。周钢也没反驳,很快发出了鼾声。在柳月的眼睛里,周钢淳厚老实,大字不识几个,平时,也不与谁开玩笑,她怎么也不能将老实巴交的周钢和拈花惹草的男人重叠起来。
是自己多疑了。就周钢这样,哪个女人会跟他?明天还得去大棚浇韭菜呢!
哗啦啦,对门屋,传来孩子去洗手间的声音。柳月支楞耳朵听了听,咧嘴儿笑了。她的心差不多让两个孩子占满了。这是她嫁给周钢后,结下的最丰硕的果实。这两个果实,圆润,水灵,像挂在树上的散发着清香的苹果,让她踏实,幸福,有成就感。会有哪个女人敢做一只被口水淹死的鸠抢占她固若铁桶般的鹊巢呢!
柳月睡着了。她做了个梦,梦见和周钢又办了一次婚礼。婚礼上,柳月穿着洁白的婚纱,周钢也穿着笔挺的西服,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踏上红色的地毯。有人发出一声锐利的口哨,把她从梦境中唤醒。
她翻了个身,发现,周钢躺的地方空荡荡的,而被窝里却冷冷的。柳月的第一反应就是,周钢没去洗手间。去哪儿了?柳月起身,周钢披着一身月光进来了。
大晚上的,干啥去了?柳月揉了一下眼睛,像一只觅食的鹰,目光犀利得似乎要将周钢穿透。
屋里闷,睡不着,出去抽根烟。周钢说着,上炕重新躺下。
柳月将头依在男人的肩膀上。闻着男人身上散发出的浓浓的烟味,柳月很快睡去。
天蒙蒙亮,两口子就去大棚浇韭菜去了。刚过了年,天还很冷,因为大棚面积大,加上浇水能保温,在一茬韭菜卖掉后,得早点浇水及时补充养分。周钢骑着摩托车,柳月将脸贴在周钢的背上。周钢说,抱紧点,小心!柳月抱紧男人,心里一暖。她从未听到男人这么关心她的话。于是她又说,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男人愣了愣,不耐烦地说,我让你抱紧点,别摔着,没听着呀。口气跟刚才迥然不同。柳月说,吃枪药了呀你!男人不再说话,摩托车怪叫着,箭一般驶向大棚。
柳月没想到,韭菜浇完后不久,男人接连两天没回家,打电话说在外边谈事。建筑工地欠了他们不少账,柳月以为男人在讨账,可没想到,有人告诉她,周钢和一个歌厅小姐在一起。那个人是二里地外姚家村开种子化肥商店的马驰,他说他去歌厅唱歌,看到周钢和一个歌厅小姐有说有笑进了包房。那天,柳月去马驰的商店给韭菜买速生肥,喝了半醉的马驰告诉她这件事。柳月想,如果马驰没喝酒,这件事根本就不会从他嘴里说出。柳月很伤心,周钢怎么和歌厅小姐在一起呢?市里开了不少歌厅,屯里的男人们经常呼朋唤友,成帮结伙地去哼两嗓子。越往回走,柳月越觉得不对劲。马驰话里有话,和歌厅的小姐有说有笑的,莫非,周钢除了唱歌外,做了啥下三滥的事了?柳月无论如何也想不出,周钢和小姐在一起有说有笑的样子。周钢不是那样的人呀,平时,换件新衣裳跟上刑似的,他怎么舍得花钱在歌厅找小姐唱歌?
晌午,柳月问回来的男人,问他离家这几天都做了些什么,男人说去讨账,柳月说就没做别的吗,男人说没有呀,怎么了?柳月犀利的目光似乎要把男人的肺腑穿透,真就没做别的?男人说没有。柳月说,可我怎么听说,你在市里和一个歌厅的小姐有说有笑在一起?男人说,你听谁说的?柳月说,别管我听谁说的,有没有这回事吧!男人说有,你听谁说的?柳月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有必要非得知道是谁说的吗?男人说,我是去歌厅了,也找了小姐陪唱,可那是为了揽新活。我找了几个工地上管事的人唱唱歌。
柳月瞪了男人一眼,忙别的去了。
四
二十多年的夫妻,男人啥样,在女人眼里心里熟悉得如同自己,可这次,柳月看走眼了。周钢这个人能干,可对自己却要求不高,浑身上下埋巴汰的,结婚到现在,衣裳由里及外,都是柳月洗。就在周钢回来的当天,吃完晌午饭,柳月给男人洗衣裳,意外地发现,男人的内衣里惊现一根女人的长发。这根长发,像根蔓草,缠绕在柳月的心里。柳月没声张,两个女儿也是长头发,会不会是女儿的长发粘在了上面?可一想,不对,这身衣服是男人刚刚脱下来的,女儿的长发怎么会粘到这上面?最后,柳月判断是,长发来源于歌厅的小姐。
柳月很纠结,胸口像堵了把茅草。和男人生活这么多年,处处谦让着他。当初,相对象的时候,因为年纪的原因,柳月多少有些犹豫。小女婿不好侍候,再加上哥一个,嫁过去,当媳妇当姐当妈,这日子不好过。除了上述观点外,就是,女人老得比男人快,更何况,她比周钢大三岁。现在看不出什么,再过二十年,就有差距了。父亲当时却极力推崇这门亲事,媒人也说,女大三,抱金砖。就这样,柳月嫁给了周家。过门后,果然是当媳妇当姐当妈,周钢脾气倔,遇事,十头牛拉不回,柳月向来顺着他。周钢发脾气,柳月一般不吱声,周钢在外头不顺心,柳月就劝他,想方设法让他高兴。我老说柳月,男人不是这样惯的,时间久了,会出毛病的。柳月却说,不让着他点咋行?家里家外,都靠他。柳月这样说,我这个当哥哥的自然不好说什么。
几天后,周钢拿着三万块钱再次不见了踪影。柳月给男人打电话,问他是不是和歌厅的小姐在一起,男人不置可否地摁了手机。柳月的心就慌了,男人怎么频繁出入歌厅,和陪唱小姐在一起呢?柳月不止一次听说,那种地方,男人去惯了有瘾。柳月疯了似的出入市里的歌厅,希望能看到男人,可接连几天,也没发现男人的身影。柳月知道,事情并不是仅仅限于男人和歌厅小姐在一起唱唱歌儿那么简单。
煎熬的等待中,周钢回来了。这期间,柳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要离婚,被我劝住了。男人回家,柳月发现,男人的脸上似乎罩上了一层迷雾,看起来有些陌生。柳月见男人脸生疲惫之色,什么也没问,只说了句饿了吧,就去厨房下面去了。
那天晚上,快睡觉的时候,柳月发现,周钢的肩胛处,有一圈红红的印记。柳月看得清清楚楚,是一圈牙印。因为当初咬得用力,印痕很清晰。
谁咬的?!柳月像头暴怒的母狮,咆哮着。
我们几个都喝大了,我也不知是谁咬的。男人狡辩着,脸涨得通红。
别以为我不知道。柳月推开了男人,脸沉得像一潭水。
我真不知是谁咬的。男人咬着厚厚的嘴唇。
哼!柳月躺下,给了男人一个后背。
早上,男人下地小便,柳月发现,男人的手机QQ有个小青蛙的头像一个劲在闪。小青蛙留言:亲爱的,还疼吗?对不起,我是想让你记住我。
这个头像和网名柳月再熟悉不过了,是陈明的媳妇张金玲。牙印,长发,无疑,都来源于她。柳月没声张,一个月后的一天黄昏,柳月终于在屯子外边的小树林里捉到了男人和张金玲在一起。柳月躲在草丛中,将他们拥抱的情形拍进了手机,然后,一个人回了家。
晚上,柳月将手机里的相片,通过QQ发给了男人。
男人说,你监视我?柳月说,周钢,别人说你跟歌厅小姐跑了,我不信,我的判断不错,你果然跟了她。男人说,我又不想离婚,你就别嚷嚷了。柳月说,你想家中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想得美!男人说,不会,不会。柳月说,那好,你现在就跟她断。男人说,咋断法?柳月说,当我面,给她打电话。男人说,这大晚上的,打什么电话?柳月说,你不打是吧,那好,我替你打!男人这才说,要不这样吧,我给她发个短信,我发誓,以后再也不找她。男人就发了个分手的短信。很快,女人的短信回来了,只有短短三个字:我恨你!
见男人的脸色很不好看,柳月说,你跟谁我都不笑话你,可我就不明白,你怎么就跟了她?你不知道,她咋离的婚嫁给陈明的吗?男人摇了摇头。柳月说,她以前嫁给廖屯老张家,因为跟屯里做干豆腐的于老二相好被男人给抓了个现形,男人暴打她一顿不要她了。她给前夫扔下一个闺女。男人说,你听谁说的?柳月说,听谁说的不要紧,要紧的是,你必须离这样的女人远一些。女人,能背叛自己的男人,将来,也能背叛你。男人说,啥逻辑?柳月说,别问我,你比谁都懂。明天,把车钥匙给我。
干啥呀这是?男人说。
你懂的。柳月说。
柳月想起了我跟她说过因车生变的话。如果没买轿车,不扎眼,男人一定和以前一样,踏踏实实跟她过日子。她还听姐妹们说,男人的口袋里没钱,就蹦不到哪儿去。拴住男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往他的口袋里揣钱。结婚多年来,家里的财权都由她控制着,周钢需要钱,都得提前跟她商量。上次的三万块钱,就是周钢说付给砖场的砖钱。柳月给砖场的姚场长打电话,才知道,男人根本没付砖钱。不过,男人回来,将二万八千块钱放到了她面前,对柳月说,他是想付砖场的工钱去了,可他去了砖场,姚场长没在。这几天,他花了两千块钱。柳月这才笑了。她知道男人的秉性,想把钱从他口袋里套出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别说柳月,连我这个舅哥,听到周钢出轨的事,都觉得不可思议。
周钢不具备风流男人的潜质,比如外貌,比如气质,比如文化水准。在我的印象里,周钢几乎没穿过几次干净利整的衣裳,脸也好像没洗,胡子拉碴的。并不是说周钢没有好衣服,而是,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几天闲下来的时光。他和柳月就像两只不停旋转的陀螺。
两只不停旋转的陀螺,怎么会有缝隙让别人有机可钻呢?好长时间,我沉浸在柳月和周钢的情感中不停地思考。
柳月本以为将车钥匙收了,把银行卡紧紧把住就万无一失了,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料。男人又有三天不着家了。柳月打电话,关机。她听说,张金玲也好几天不着家了。柳月知道,男人和她出去了。柳月求助于公公婆婆,公公婆婆才知道儿子外面有人。婆婆安慰她说,别怕,有妈在,谁也进不了这个家。他要不听劝,咱就把他赶出去,咱娘俩和你爸带孩子过。柳月被婆婆这番话感动得掉下泪来。虽然这样,柳月也什么也干不下去,有一次差点让开水烫伤了脚面。周钢回来了,柳月就说,既然你的心不在我身上,咱们还是离了吧,我成全你。柳月是在试探男人的态度,哪知男人却说,离就离吧,有什么条件,尽管提。柳月没想到男人这样说,就说,我什么也不要,只要你过得好就成。不过,我现在不能答应你,等老大高考完。男人说行。
大女儿高三,再有几个月就高考了。柳月不想女儿影响高考。我了解柳月,她的本意并不是想离婚。这么多年苦心经营,用血汗打拼出来的家,她怎么舍得散呢!这期间,她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对她说,婚姻好比手中的沙子,攥得越紧,流失得越快。与其这样痛苦,还不如给他一个空间。柳月说,我受不了。我说,如果你还想要这个家,就得学会忍耐。柳月想了想说,我听你的。
我让她别冲动,可柳月还是冲动了。其实,我是理解柳月的。会有哪个女人眼睁睁地看着男人和别的女人不清不白的呢?
那天,柳月去了陈明家。陈明在院子里修摩托车,见了柳月,脸上掠过不自然的神色,说,嫂子来了?
陈明和周钢以前的关系不错,可能,他也听说媳妇和周钢间的事了。要不然,表情不会不自然的。
我找金玲。
她在。
柳月直接推门进了屋。张金玲在洗头,白皙的脖颈,一头乌黑的长发正在往下滴着水珠。
嫂子来了。张金玲用毛巾将头发裹好。
柳月咬了咬嘴唇,知道我找你做什么来了吗?
我不知道,嫂子。
那好,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柳月冲上前,扇了张金玲一个耳光,随后,叉开五指,将她挠了个满脸开花。血,顺着张金玲的脖子和脸颊汇成小溪,流了下来。
奇怪的是,张金玲没还手,只是说,嫂子,有话好好说,凭什么打人?
打你是轻的,我还想杀了你。放着好日子不过,勾引别人家的男人,你说,你该不该打?
张金玲这才说,嫂子,这种事你找我有啥用?有本事,管住自己的男人。说着,照镜子,用面巾纸擦了擦脸。
柳月瞪了一眼张金玲,走到院子里,看了看仍在修摩托车的陈明,回到家扑到炕上嚎啕大哭起来。
男人走了进来,大白天的,哭什么?
柳月说,我把她挠了。
男人一惊,把谁挠了?
柳月抹了把泪,还能有谁,你的心肝宝贝呀!咋,心疼了?
男人说,你就作吧!
柳月说,就作,就作!
哭过后的第二天,柳月给我打电话,说挠了那女人满脸花,还要和周钢离婚。我知道柳月言不由衷,让她放弃她苦心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家,比杀了她还难。不过现在,她和周钢的关系已经到了非常时刻,我这个当哥哥的,还真就得尽当哥哥的义务。于是,我说你先回家去,过几天,我去你们家看看。
柳月说好吧。
一个星期后,我去了柳月家。
五
一年前,也是旱田里的高粱和玉米苗铺满了田野的时候,我来过柳月家。那年开春,柳月的婆婆病了一场,我知道的时候,正是我说周钢“有了车,也别整天招摇过市,要本本分分过日子,别老往卖店超市钻”的那一天。我为了缓和和周钢的矛盾,说过段时间去看看老太太。可我一直忙,就没腾出工夫来去履行我的承诺。五一放假,我才去了柳月家。
那天,周钢不在家,柳月见我到来分外高兴,公公婆婆非要留我在家吃饭不可。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走着回去看望六里外的母亲。此时,禾苗将大地铺了一层绿色,暖风习习,我的心境很好。没想到,一年后的同一时间,我又以另外一番心境走进柳月的家。到柳月家前,我和开“板的”的光头司机谈及我此行的目的。我说,我是大舅哥,如果是小舅子,非把他打得口鼻出血不可。光头司机说,别冲动,这种事劝和不劝离,打哪儿了,你妹妹还得怨你。你妹夫也是,这种事,怎么能让自己的老婆知道呢?我说,谁说不是呢,坏事人人有,不露是好手。光头司机说,一个上有老下有小、满脸高粱花的庄稼人,瞎折腾什么?以后,在屯子里还咋抬起头做人?我下车的时候,他又来了句,这世道变了,人心也变了,人心咋都让狗吃了呢?
我进去的时候,柳月在屋里给母亲打电话。公公婆婆见我来很意外。我说,柳月和周钢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这个当娘家哥的,怎么也得过来瞧瞧。她婆婆说,那是,那是。接着又是递烟,又是倒茶,然后说,她大舅,你不知道哇,周钢他这是犯了桃花了。我找人看过香了,过几天,就能好了。我笑了笑,将一口茶饮进肚子里。
这都啥社会了,还迷信这个?不过,我没说出口,只是说,大姨,我知道,你和柳月处得跟亲生母女似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谁进了你们家的门,谁都是您的儿媳妇。老太太的脸笑成了核桃,说除了柳月,我谁也不认。老太太的话让人感动,我知道,面对我这个娘家哥,她这个当婆婆的,也只能这样说。
饭菜摆好后,周钢浑身是泥胡子拉碴地回来了。一年多未见,似乎有些苍老。见到我,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我没指责他什么,只是说,你们的事,我听说了。男人,有个风吹草动,很正常,处理得当,就好。周钢听我这么一说,笑了。我说,都是男人,我理解。让你们现在就断,也难为你了,过段时间,冷却一下就好了。婆婆说,瞧你哥说的话多在理。周钢说,哥你放心,我也没打算娶她。没人的时候,柳月说,哥,你怎么还向着他说呢?我说,我不这样说怎样说?你们家有今天,容易吗?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动离婚的念头。女人出一家入一户的不易,更何况,两个孩子都这么大了。柳月说,就凭这俩孩子,那个女人也进不来。我说,啥事都无法预料,这世界,谁离开谁,都能活。
周钢开车送我回去,路上,谈及了他和那个女人的感情。尽管当着我的面表态和那个女人会分手,可我预感到,事情,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
不久,我再次接到了柳月的电话。柳月说,哥,我要离婚。我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别离婚吗?柳月说,我受不了。他心里没了我,我过的还有什么劲?他说了,给我二十万,孩子归他。我说,你认了?柳月说,成全他们。我说,还没到离的份上,忍忍。柳月说,女的寻死觅活的,我怕他摊官司。我说,那女人寻死觅活和他有啥关系?柳月说,我想通了。给他们倒地方。我很感叹,此时,柳月居然还怕男人摊官司。其实,我明白,那是男人设好的套儿,他深知柳月的脾气秉性,故意这么说。我说,既然你想好了,就做吧,不过,别后悔。
端午节放假,我回老家,看见了柳月。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柳月似乎老了十岁。
柳月说,我不想和他成仇,毕竟过了这么多年。我只是想不到,人心咋就变得这么快。母亲说,条件好了,人却坏了下水了。我听柳月的二女儿说,离婚的第二天,那个女人就跟着她爸下地干活去了。母亲说,人家是迫不及待把你妹妹往外赶呀!来串门的舅妈说,不安好心,他们过不长远的。她还没离婚,人家老陈家能容吗?等着吧,还会有好戏唱的。
我没说什么。我知道,评价一个人的好坏,和婚姻的长久似乎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我对柳月说,之所以造成离婚的局面,你也有责任。柳月没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儿看着她和两个女儿刚刚在照相馆照的相片。我为柳月感到悲哀,二十多年的婚姻,最后浓缩在一个镜框里。
柳月翻来覆去对两个女儿说,别对那个女人客气,那个女人走了,妈就回去了。刚刚高考完的大女儿躺在炕上闭着眼睛不吭声,小女儿听得不耐烦,说,能不能不说这个呀!
我叹了口气。
真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是怎样想的。
六
周钢还是开车来送柳月了。
离婚后,柳月住在了母亲那儿,通过二十年前的好朋友刘东旭介绍去六里外的鞋厂干活。做姑娘的时候,柳月和刘东旭一起学裁剪,关系一直挺好。柳月以前在鞋厂干过,按说驾轻就熟,干了没几天,脸上却起满了小疙瘩,看了几家医院,都说是粉尘导致的皮肤过敏。柳月这才又想起我托我的朋友老孟给她找的在饭店干杂活的事。柳月怕找不到,就打电话让成为前夫的周钢把她送过去。
坐在车上,柳月说,没想到,你能来送我。
周钢说,没仇没恨的,有啥不能来的?再怎么说,你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柳月说,算你还有点良心。
周钢笑笑,没说话。
柳月说,和她在一起开心吗?
周钢仍只是笑笑,开他的车。
只要你开心就好。柳月说。
柳月说,请我吃顿饭吧。
周钢说,好吧,你想吃什么?在哪儿吃?
柳月指了指路边的一家酒店,就在那儿吧。
周钢没说话,将车停在了店门口。
二楼的包间,柳月和周钢要了四个菜,边吃边聊。此时,一抹晚霞映在天际,正值夏季,远山近水,像在画中似的。
柳月说,谢谢你能来送我。从此后,我再不讨扰你了。这顿饭我请你,吃好,喝好。
周钢说,我请我请。
柳月说,谁请还不一样?
这顿饭吃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结婚二十多年,从未像今天这样客套过。没有人知道,这是一对离婚不久的夫妻。周钢不能喝酒,柳月从包里掏出一包茶来,要一壶开水,说,我亲手沏茶。咱们就以茶代酒吧。
泡了一会儿,给周钢倒上。
周钢呷了一口,什么茶,这么苦?
柳月说,茶是苦的好。不苦,还叫茶吗?咱们碰一杯。
柳月端起杯子,和周钢碰了一下。
吃完了饭,周钢继续开车送柳月。不远处,出现了一座桥。弯弯的,像彩虹。
柳月说,还记得这座桥吗?
周钢说,当然记得,二十二年前,我用手扶拖拉机,娶的你。
柳月说,你的记性还不错,我也记得,是陈明他爸开的车。当时你说,用手扶拖拉机娶我,委屈我了,将来,一定让我过上好日子。
那时候的条件就那样,用手扶娶你,就已经很不错了。
时过境迁。柳月居然用了一句成语,扭头看了看周钢,笑,娶我的时候开手扶,离婚后,用轿车送我去打工。
周钢笑了,笑得有些勉强。
车至桥头,柳月突然碰了一下周钢的胳臂,将方向盘往外一打。周钢觉得浑身松软,像抽去了筋骨,眼睁睁看着方向盘握在柳月手里。车子凌空,撞掉桥栏,飞驰而下,像条白色的海豚,隐入了碧波之中。
在轿车下坠的瞬间,周钢说,你给我喝的是啥?
柳月说,茶。
茶?
茶!
柳月笑了。
她看到一辆手扶载着一对新人,正缓缓开过桥面。
她的身体从未如此轻松过,像一片轻盈的羽毛,飘到了车窗外,看着载着她和他的车缓缓下落,直至不见。
责任编辑:王方晨
——记山东省特级教师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