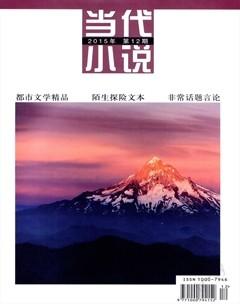人不是妖生的,却可以变成妖
王大鹏 张丽军
对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探索一直是文学作品表现出来的重要主题。文学曾编织着令人向往的爱情,讲述着感人泪下的亲情,探索着久藏心间的友情……这样的文学故事带给我们很多的向往。在如今日益物质化的社会里,文学开始一方面讲述被异化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一方面展现出对纯净感情的追忆。文学开始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这一期的文学期刊,依旧讲述着商业化冲击下的人们对爱情的追求、对友情的回忆、对亲情的思考、对文化知识的认知等,在展现着人性的丑陋与道德的沦丧同时,也包含着对于纯真本性的回归。
爱情本来是美好的,然而通往美好爱情的道路却是曲折的。一场难忘的相逢带给人们的可能是一段美好的爱情,也可能是一场不能自拔的灾难。物质化的时代,纯洁干净的爱情已经成为奢侈品。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是很难得到的。他们没有过多的祈求,只是想拥有一场美好的恋爱,收获爱情,然而他们终究得不到。他们的爱情观念在迷茫的追求中变得畸形,为了爱奋不顾身,挑战着自己的底线,践踏着自己的尊严。在金仁顺的《纪念我的朋友金枝》(《人民文学》2015年第9期)中讲述了金枝作为一个成功的药品推销员,生活豪放,体型较为丰满。她痴恋高中同学袁哲十年,对袁哲非常好,即使是面对袁哲的妻子聂盈盈也毫不避讳。她曾经大闹袁哲的婚礼,还因为不满聂盈盈对袁哲的责骂,与聂盈盈发生争执,被聂盈盈划伤了脸。袁哲带着感动和歉疚去金枝家安慰金枝,并与其发生了关系。像金枝这样的小人物很容易就会获得满足,一次安慰,一声问候都能让他们充满希望。金枝以为有了希望,便去了韩国,瘦身成功。袁哲在金枝去韩国期间对金枝表达了爱意。满怀激情的金枝回国后继续等袁哲,却从袁哲的嘴里听到了聂盈盈怀孕的消息,她的希望破灭了。就像金枝自己说的“爱情这东西,谁先动心,谁就满盘皆输。”金枝说“十年前我就输了”。最后金枝吞药自杀,爱死了袁哲。这长达十年无怨无悔的爱恋只换回了一个美丽的泡沫。对爱情的期待让她变得疯狂,对爱情的失望让她走向极端。同样,在光盘的《墨镜》(《清明》2015年第5期)中描写的那个经营着奶茶店的小芊也是追寻着畸形的爱恋。她因为身体肥胖一直未能结婚,后来爱上了一个常来奶茶店的戴墨镜的男子。这个男子自称是盲人,他带给了小芊爱情的希望。但是这个人是个骗子,不仅有家室,还骗走了小芊二十万。小芊对于爱情的追求使她充满希望地奉献,虽然在旁观者沈培佳眼里是一厢情愿。她拒绝了工程师管大鹏、成功人士毛元华的追求,一心只爱着墨镜男曹哲学。在小芊看来,爱就是爱,没有真假。为了让曹哲学少判刑,她放弃了自己的二十万;为了让曹哲学能够减刑,她贡献自己的身体,对狱警性贿赂。即使曹哲学出狱后仍然是和他的狐朋狗友混在一起,小芊忍受着折磨,践踏着自己的尊严,仍然坚持着自己虚无而真切的爱。这是一个女人的悲剧,是在绝望中仍然饱含希望的爱的悲剧。上演爱情悲剧还有田君的《李毅的V生活》(《清明》2015年第5期),陈再见的《浮世录》(《清明》2015年第5期),阿袁的《上耶》(《江南》2015年第5期),温亚军的《空巢》(《人民文学》2015年第9期),孙频的《色身》(《十月》2015年第5期)等,展现出人们在追寻变质的爱情时,畸形的爱恋与痛苦的自我折磨,在性和欲中轮回。
越来越物质化的世界,不仅侵蚀着爱情,也异化了人们对亲情、家乡的情感。乔叶在《玛丽嘉年华》(《清明》2015年第5期)刻画的肖玛丽是一个农村走出来的姑娘,在省城做着高管,生活很不错。她不经常回家,其实是不想回家。临近春节,她收到副总的邀请去参加嘉年华舞会,但是父亲母亲强烈地要求她回家。她没有理睬。相比较春节回家,她更喜欢珍惜城市的灯红酒绿;相比较回家与父母团圆,她更喜欢嘉年华舞会上的觥筹交错。她拖着回家的时间,给自己找理由:已经没有回家的车了。在嘉年华的舞会上,她接起了数次挂断的母亲的电话,才知道父亲不行了。她这才着急地冲出舞会,去坐那马上就开走的回家的车。不知道她最后有没有赶上车,不知道她有没有及时回到家,见到含辛茹苦养大她的父亲。我想如果见不到,她一辈子都会不安。大城市的生活迷乱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在大城市里其实是像水中的浮萍一样,物质化的快节奏生活裹挟着我们前行。我们在激烈地竞争,我们在奋力地争夺。这并不错,错的是忘了自己的根。我们忘了有根的树才能参天,无根的浮萍只能随波逐流。付秀莹《回家》(《十月》2015年第5期)中的小梨从北京回家待了几天,就觉得忍受不了琐碎的生活,深深地感受到了城市和农村的差异。她甚至开始讨厌这个她从小生活的地方,这个带给她亲切和关怀的地方。
商业化发展的社会不仅冲击着人们的情感世界,同时也已经侵蚀到传统的知识界、文化界。有的文化受到冲击后逐渐消亡,有的知识受到侵蚀后变了味道。像马拉在《送释之先生还走马》(《人民文学》2015年第9期)中的马释之一样,他是走马镇的书法家、画家。他的画和字儿都已经有了很高的价值。他的学生马一凡(一个爱好文学的商人)来请他出山,开始的目的很单纯,只是想请马释之先生去他专门找的清幽的书院教授国学。但是后来在朋友的怂恿下,一凡开始为马释之办画展、制画册、拍卖马释之先生的作品,为的是能够获得一定的利润。马释之开始的时候不高兴,后来也无可奈何地接受了。马释之先生最终不能习惯这处于嘈杂环境中的书院,回到了走马镇。当年马一凡结婚的时候,释之先生送的是并蒂莲,一方面是祝福,另一方面也希望马一凡能够继承他的治学品质。马一凡再一次回到释之先生家,释之先生画了一幅衰败的枯叶荷。昔日的并蒂莲变成了今日的枯叶荷,这不仅表现了释之先生的失望,更显现出国学在物质化社会的衰败。还有陈启文发表在《十月》(2015年第5期)的《短暂的远航》中讲的破烂王傅老板凭借着搜集的历史资料,吸引历史研究专家高先生的爱徒黄忠会和杨芝。表面上是帮助高先生查明历史,使高先生父亲的冤案得以昭雪,但是暗地里步步设局。他先是让自己的女儿成为了历史系的研究生,又娶得了杨芝这个研究生妻子,还设计气死了高先生。最后利用高先生的影响和重金建造的“大明宣德号”, 成功获得了寡妇矶的景区开发权利,获利丰厚。一切都做得滴水不漏,甚至连气死高先生的责任都推给了黄忠会。当知识、文化遇到了钱,便低下了自己的高傲的头颅。就算是高先生这样的历史大家,也没有钱建造一艘“大明宣德号”,真正的探索历史。前辈们留下的文化精粹已经不再是纯正的艺术,而是成了当下商业消费的热点。有人拿着艺术品去行贿,像梁晓声在《金原野》(《人民文学》2015年第9期)中刻画的汪君;有人借修建寺庙占地皮,像洪放的《菩萨蛮》(《清明》2015年第5期);编剧和演员之间进行着性交易,如邱华栋的《大叔》(《江南》2015年第5期)中的描写。商人们在文化精粹中发现商机,为的不是文化的继承,而是利用艺术圈钱。文化、艺术已经成了强者的工具,文化传承已经变成了消费文化。
真性情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挣扎生存。在这物质化的嘈杂生活中,当然也有对爱情的美好期待,像姜燕鸣的《千里之外》(《清明》2015年第5期);有对文化学术和本性的真情回归,像晓风的《回归》(《人民文学》2015年第9期);有对真情和家的回归,像陈洪金的《半朵雪花》(《清明》2015年第5期)。在追求欲望的道路上,真情的回归可能会更加有利于前行。人们开始通过追忆同窗之间逝去的青春,来填补现实内心情感的匮乏。李宏伟在《假时间聚会》(《人民文学》2015年第9期)中描写了王深参加高中同学举办的假面舞会。他回想起自己与方块、孙亦当年的美好生活与情感纠葛。无奈现在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他们扼腕叹息,感叹时光飞逝,旧情不再。幸运的是王深还有爱着他的妻子和女儿,这给了他些许的安慰。王咸在《相见欢》(《清明》2015年第5期)中的那句“要是钟离在这就好了”更是道出了内心的心酸。人们通过重游故地,感受曾经的美好,像何玉茹《回乡》(《人民文学》2015年第9期)。人们选择不再浮夸,通过平淡的小事儿表达最真实的爱恋,像匡瓢的《往昔之井》(《十月》2015年第5期)。通过细小却不平凡的生活来展现对于人性的思考,像马炜的《照镜子》(《人民文学》2015年第9期),“人是人生的,妖是妖生的”,人不能被社会异化成妖,做人就得有个人样。
“只想自己怎么活着,却没有想过自己死后。”这是陈仓的《墓园里的春天》(《江南》2015年第5期)的主人公说的。人们在嘈杂的社会中匆匆忙忙地活着,没有活出为什么,更别说想想自己死后。一个被胡主编辞退的资深记者,去了一个叫长寿园的地方卖墓地。开始他是愤怒的,直到他遇到了葬父的小姚,他感受到了生死的意义。听到胡主编为了报社跳楼自杀,没人管的情况下,他毅然地用自己的钱埋葬了无亲无故的胡主编。他也因此没了女朋友。然而他并没有后悔,在长寿园里他体悟了生死,安心地工作,用“把骨灰一分为二的方法”帮助小姚葬了她的丈夫。钟求是的《星子》(《人民文学》2015年第9期)中“韩先生”,也就是文中的“我”,在被确诊绝症后来到一个村子。名义上是来“买空气”,实则是想逃离在医院等待死亡的日子。身穿寿衣的老头,房东老妇以及她的孙子都对“我”的身份感到好奇。寿衣老头甚至都报了警。在得知真相后,寿衣老头对“我”充满了同情,主动约“我”谈他的经历,说起离开农村去往城市生活最终死在城市中的老哥。老孙头(寿衣老头)企图用一些生死观来帮“我”脱离痛苦,就像自己身穿寿衣最终摆脱了痛苦一样。最后“我”买下了老哥的棺材,并让老孙头张罗着帮“我”举行了一场葬礼。老孙头也尽心尽力地帮“我”,好像是举行了葬礼,“我”的病就会好了一样。按照葬礼的风俗一套下来,没有太多的悲伤,最后甚至是放了电影。“死了人,天上便容易有流星,村里人都说,一颗流星就是上天的一滴眼泪”。生的时候不去珍惜,一味的争夺又有什么意义。太多的东西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思考生死意义的还有王小王的《倒计时》(《人民文学》2015年第9期)。通过文学功能,作家向人们传达着对生死的叩问。
马克思曾对人的本质做出过论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既然生活在社会中,就必然会受到社会的影响,这是无可厚非的。体现在文学中也是这样的,文学也包含着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情感价值体验。表现在文学的场景里,常常设定在一个普通的家中,通过展现一个家,来阐明道理,像陈力娇的《家殇》(《清明》2015年第5期)。
战土改、乔米朵、战小易、战小莲是一家人。战土改经常打骂乔米朵,哥哥战小易以为是因为妹妹战小莲的出生。所以战小易就将妹妹骗到了一个荒野里,回家后谎称妹妹被姑姑接走了。战土改对乔米朵依然是打骂。在战小莲失踪半个多月后,这对打骂的夫妻才想起来自己的女儿。为了保住自己的儿子,乔米朵一口咬定是姑姑带走了战小莲,而不是去尽力地找。当时被哥哥遗弃的五岁的战小莲无意间走进了狼窝,然而狼并没有伤害她,却被猎人李大胆和冯化用猎枪打中,瞎了双眼。最后张刚找到了战小莲,母亲乔米朵却不承认这个已经瞎眼且变痴傻的孩子。如果父母在家里没有无休止的打骂,五岁的战小莲会有一个快乐的童年。然而没有如果,有的是后果和结果。父母是孩子的榜样,孩子才能成为父母的希望。张运涛的《梁柱》(《清明》2015年第5期)中的母亲白晓敏如果没有去找根本不存在的“儿子”,最后不至于家破人亡,女儿或许会有着幸福的生活。当然,这些作品中也传达出母亲的悲苦。毛家旺《村祭》(《十月》2015年第5期)中的母亲牛春粉因为儿子马春元杀人而受尽冷眼,在获得杀人者的父亲的原谅后,她终于能够在自己儿子的坟前大声地呼喊。 这也传达出了母爱的伟大和乡村农民的朴实与善良。人们除了家,更多就是待在工作的地方。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分支,工作的地方也反映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像梅驿的《班车》(《十月》2015年第5期),通过一个工人李冒和制药厂的“金子河”讲述了国企内部的混乱与腐朽。
人不是妖生的,却可以变成妖。物质化社会环境中诞生的文学作品,揭示着社会的黑暗杂乱,控诉着异化的生活、异化的人类。我们眼里满是诱惑,文学也不再那么纯粹。文学作品中充斥着财色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物质化社会带给人们的悲痛与绝望。在这种绝望中,爱情、友情、亲情等人类引以为豪的情感体验甚至不如低等动物之间美好。这是在批判着社会,但这何尝不是对这种物质化的一种变相宣传。人要回归本真,还是成为物质化生活的附庸;文学作为影响人类思想的精神旗帜,该如何飘扬,作家依然执着地提出问题。
本栏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