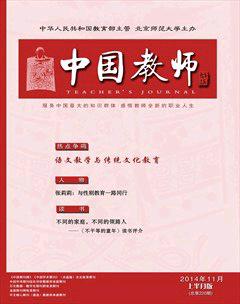与性别教育一路同行
张莉莉



年过半百之时,回首过去,不禁感慨我们这代人是非常幸运的。1977年,我上初一,适逢整个国家迎来科学的春天,对知识的渴望充盈在我的心灵深处。职业发展过程中,得益于国家的开放与变革,我有机会在香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学习,还曾两次在美国给研究生和本科生授课。过去的十几年间,我不仅从教学与研究中得到很多的锻炼,也在社会服务中找到了乐趣和价值。贯穿这些经历,性别视角始终带给我很多的激励和启发,使我成长为一位女性主义者。
一、大学:模糊的社会性别意识
中学阶段,我酷爱数学,初三时就自学了高中教材,并和高中生一起参加数学竞赛。数学让我体验到探究的乐趣,增加了我的成就感。1981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后,我更加被科学所折服,学到的每一个理论都使我感到奇妙而神秘。但是,理论研究的艰深也使我隐约地感觉到未来专业发展的困难,而且物理系的女教师也比较少,这让我隐隐地觉察到一种隐匿在学科之中的区隔。
大学时代,三点一线的生活之余,我和同学们都会被各种新的人文与社会思潮所吸引。我们除了会阅读一些对我们产生过深远影响的著作,如《大趋势》、《人啊人》等,还会听很多的讲座,如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的演讲,而且从她的讲述中我看到了一种女性的坚定和魅力。之后,我又开始读徐悲鸿前妻蒋碧薇女士的传记,在两位女性间形成的对比中,我对女性形象应是怎样的开始出现困惑。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对我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他坚定地认为女孩不应该因为打扮而分心。由于他在大学教书的同时兼任律师,工作很忙,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母亲应该承担更多的家务,但我母亲是个典型的职业女性,敬业并好学。这一方面让我认为知识女性不应该在家庭中丧失自我;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自己的母亲似乎太偏重工作了。对当时的我来说,这些想法存在着矛盾和模糊,没有建立起比较清晰的社会性别意识。
二、跨越:从物理系到教育系
考研究生时,为了寻觅某种职业梦想,我从物理系跨考到教育系。起初,我不太适应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感到物理学与教育学存在很大的差异,物理学重在发现规律,而教育学强调理论思辨。
留校任教后,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将我的理科优势运用到教育领域中,所以我开设的第一门课程是教育运筹学,尝试把系统思维融入教学,如怎样进行规划与博弈,在此基础上实现系统优化。此时,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把科学方法应用于教育学,让教育更有效率,但我又感觉自己能做的东西并不多,因为教育系统是非常复杂而行政化的一个体系。
工作几年之后,感觉自己亟须提升,于是我报考托福,申请到香港大学读书。尽管这一申请过程非常的不容易,但在撰写和完善研究计划中,我初步了解了什么是实证研究方法。在博士学习期间,我开始关注女学者的工作压力问题。当时我校教育系有很多特别优秀的女性教师,如裴娣娜老师、史静寰老师、郑新蓉老师等,而我的成长也离不开她们的激励和引领,但与她们存在的差距也让我有很强的压力感。随着时代的快速变化,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会面对越来越多的压力。结合自身的情况,我发现女性在平衡职业和生活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因此,我开始关注国内的一些女性学研究者,并跟其中的一部分人逐渐有了交往。研究过程中,我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上都接受了比较好的训练。同时,我也参加了香港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的活动,这是一个自主搭建的交流平台,尤其是其中几位负责人在推动社会性别研究方面的热诚令我感动。在香港大学,我的自信心得到提升,虽说用英文撰写博士论文是一个挑战,但让我找回了学生时代的刻苦与专注,培养了吃苦精神,克服了很多困难。
三、密西根大学访学:女性主义思想的启蒙
在郑新蓉老师的推荐下,我从香港大学毕业后就到密西根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学习了4个月,比较系统地接受女性主义理论的洗礼。在密西根大学学习期间,正好赶上“9·11事件”,见证多种思潮的对抗,我开始学会用多种批判的视角看待美国社会。当时我选修了三门课程,即女性主义理论、批判教育学、性别心理学,而且每门课程都需要进行大量的阅读,在上课时进行围圈讨论。
女性主义理论课程要求我们每周写一篇读书笔记,教师也会认真批阅。性别心理学课的教师会让我们自己准备并组织讨论,看似处在支持者位置上的她却在引领讨论走向深入方面发挥着神奇的作用。批判教育学课程的教师似乎很有行动力,寒暑假时经常带着学生去拉丁美洲的国家进行艾滋病防治教育。她认为,一个人能够传播所学过的知识时,才算是学会了知识。这位教师是弗莱雷的忠实信徒,认为教育就是要对弱势群体赋权。她告诫学生说:“将来无论你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干什么,都应该有理想,要能够为消除不平等做些什么。”记得有位同学是学医学的,想当个医生,说:“我除了能对不同阶层的人平等对待,其他的自己也做不了什么。”她却说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引导这位同学思考每个人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上的主体性。她确实把我们身上的这种行动力给激发出来了,这是一种追问,即我们能做什么?她认为每个人都能做很多,而且必须去做。批判教育学让我深切感受到,公正的社会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
学习女性主义理论时,一些流派和观点晦涩难懂,以至于我晚上经常做噩梦。但密西根大学的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开阔了我的视野,如有关黑人生活状态的电影周和研讨活动让我对多元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再如关于底特律城市变迁与重建计划等也让我对族群这个概念有了更深的理解。
密西根大学的学习生涯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像一块海绵,吸收到很多东西,有些未必能有很深的理解,但却播下了种子。比如关于女性主义,我不再会简单地认同某一种理论,而是会有一个自己思考的位置。回国后,我不再盲目,因为我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西方的女性主义者几乎是白人,大多家庭背景良好,而黑人的女性主义者却会质疑她们不接地气。
四、走进性别与教育领域:成为一名践行者
在教育系工作时,我发现已有一些教师在关注教育中的性别问题,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史静寰老师和郑新蓉老师。史老师特别干练,经常指点我。每次她有意无意的提点都会让我不断地反思自己。在参与北京市女大学生素质调查时,我发现史老师通过性别与阶层交互作用的视角进行解释与研究,这让我深受启发。与史老师和郑老师一起进行教材和教辅材料中的性别问题研究时,我真切地感受到女性团队的动能,带领子课题组开展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研究。
而且,我曾到日本和韩国参加过一些女性主义学者间的交流活动,接触了在亚洲有影响力的一批女性主义研究者,如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的几位学者。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中,我看到自己跟她们的不同点,她们在批判全球化、反殖民、表达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的诉求方面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且走得深远,很有批判性。但在中国的社会情境下,我主要关注的是如何为弱势女性,尤其是失、辍学女童提供培训和支持。
2004年起,郑老师推举我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中心代理主任,接手筹办首届海峡两岸行动研究大会。在领导的支持下,我和郑老师的博士生林玲等人把活动办得很有新意。会议中,不仅有对行动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探讨,而且还举办了工作坊。听着大家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现实困扰,我逐渐地认识到:每个人都是情境中的个体,尽管有些东西会束缚我们,但永远会有突破的空间。从那时起,我对行动研究有了新的认识,并将行动研究的方法应用到我的工作中。
2008年,我曾去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教书,看到该校课程与教学系的教师会将每次行政会议和教师网络建设结合起来,他们还会志愿承担一些行政和服务职责。回国后,在领导的支持下,我参与启动教育基础理论研究院的学术沙龙,不断有教师自愿承接并使其发展出自己的特色。
2011年,我以富布莱特学者的身份到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伊利分校授课,开设的课程有性别社会学和家庭视角下的中国文化。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每周准备六节课程,且要深入了解美国教育体系的要求,但我却从中得到很好的历练。美国的一年工作与生活中,我积极地和周围的教师、同学交流,进一步思考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发展。
近10年来,与郑新蓉老师共同参与中英西南基础教育项目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项目,让我看到进行性别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利用多元机会带动环境的改变。性别平等是一个行动的过程,因此,我对自己的定位是成为实践取向的女性主义研究者。
五、性别与教育课程:播撒性别意识的种子
在史静寰老师和郑新蓉老师的影响和带动下,从密西根大学回来后,我开设了全校公选课,即教育、心理和社会性别。我会从《参考消息》等报刊中剪辑资料,也会让学生写他们生活中的性别故事,这些作业至今都令我感动。近年来,我也开始在教育学部给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性别与教育方面的课程。我一直都在思考,女性主义课程到我们这一代时,应该传承什么,怎样传承。首先,要给学生自我表达的机会,培养他们的好奇心。我们要有足够的交流,不是给学生“灌输”系统的知识,而是启发他们对社会性别问题的关注与认识。其次,上课形式要多元化,注重丰富性和生动性,比如可以搞一些活动,请一些女性做讲座等。再次,我们可以组建“网络平台”,作为课堂外一种思想的联结。我会经常发一些信息,虽然有些信息可能让学生感到困惑,但我认为性别问题本身就非常复杂,一些故事和境遇总会不断发生,总会不断地循环,如爱恨情仇、家国情怀、生命叵测等,这些都会发生,但性别视角会给我们审视问题开启一种不同的视角。
面对当下如此丰富的大众媒体资源,性别教育这门课程该如何上?我认为放手让学生自主选择讨论题目并组织论坛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要走近人、走到实践中去。为此,我会让选修这门课的研究生自愿组织有关女汉子的讨论。另外,中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性别问题还是比较边缘化的,对中国未来女性学课程的发展,我充满好奇和期待。什么是中国特色?怎么才能帮助一些女生更加智慧、通达地面对生活?作为教师,我们自身的女性主义者身份怎样才能进一步确立?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回顾这些年的经历,感觉妇女学课程还没有在高校中受到广泛的重视,而在美国,妇女学是通识课程,基本上全体学生都要选修。而且,很多学校都有妇女学研究中心,可以授予妇女学学位。我们在这方面的路还很长。
六、社会发展项目专家:将行动研究与性别视角相结合
性别议题不是孤立的,它是与阶层、民族等因素相互作用的。我们尝试在社会发展项目中抓住多种机遇,采用多种形式让性别平等生根发芽。在参与开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爱生学校标准,以及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管理标准时,我们一直都在关注性别敏感指标。在参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合作项目——校外青少年弹性课程开发的过程中,通过不懈努力,女孩的生活技能课程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现在已经在10多个省份推广。对此,我们的态度是弹性的介入,而良好的合作是将性别视角融入项目实践的基础。
从2008年起,我做了4年有关大龄女童的项目,奔走在西南地区的项目县,有时候一走就是一天,到那儿后会想尽一切方法,琢磨女童该怎样增强技能,但内心中又有一种悲凉感,因为虽然我们成功地激励了她,但她甚至连抽水马桶都没用过,该如何面对全新的生活。她跟我们聊天说,她的父亲去世了,但其实是她的父亲因为偷了一头牛而入狱。纵使我们把她调动起来,有了学习的意愿,她也渴望改变,但又能怎样?我的心和这些弱势女孩儿捆绑在一起,始终带着一种痛,虽然曾帮助过她们,但却无力真正拉她们一把,而且有个女孩在给我的信上就印着她的泪痕。
然而,对北京农家女学校的项目评估改变了我的这一看法。我原以为启蒙过一个人,影响过一个人后,她会陷入一种觉醒后的尴尬与痛苦,因为她走不出那个大山。在评估中我发现,被培训过的女孩即使回到家乡,她也可以很有尊严地对待自己的生活。比如,在甘肃漳县,一位从农家女学校毕业的女孩开始建立爱心协会,在几个贫困乡镇收集一些家庭特别贫困、学习成绩却很好的孩子的资料,并把信息发给农家女学校创始人谢丽华女士,让她帮助寻求爱心人士的支持。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间断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开展女孩生活技能培训。我们会关注女孩的安全保护问题,也会着力提升她们的自我发展和职业规划意识。
此外,中英西南基础教育项目也使我得到很多的锻炼,郑新蓉老师和我都是这个项目的社会发展专家。我们开发了一套有关教育公平的培训教材。当时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师认为,他们是教育不公平的受害者,政策应该向他们倾斜,而不是让他们去促进教育公平。所以我们开始从公平和教师的相关性等入手进行教育公平培训,让教师意识到一个高质量的教育教学要基于教师的公平教育理念,要尊重学生的差异性。
随后,我们开始深入开展女性领导力项目。基线调研时发现,27个项目县中很少会有女校长,或一个县中会有一两个。云南省福贡县地处怒江两侧,交通不方便,当地市场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是傈僳族聚居的地方。在对福贡县进行调研时,发现那里的女性很有能力,但学校却很少有女校长,而且女教师的生活也很艰难,居住在山村,连找对象都有困难。看到郑老师和其他项目组成员来到这里,这里的教育局局长就想为女教师做些实事,让她们能安心地在山里学校教书。于是,郑老师顺势而为,思考着要通过一些项目帮助女性成长,把一些女教师培养成为女校长,启动女性领导力行动研究项目。什么叫领导力,我们认为,人的领导力不能被压抑,一旦被压抑,会表现出不够支持、不够合作,让人感到别扭。因此,领导力作为一种潜能,需要开发。同时,女性在表达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要提高自主表达和有效沟通的能力。我们会在培训中设计问题树分析活动,其中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城市学校会有很多女校长,而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却很少会出现女校长?”这个活动开始让参与者思考社会文化对女性参政的影响,开始解构女性不愿当领导的迷思。
女性领导力行动研究项目让我们看到成长起来的一批女校长和女教师,她们面临很多挑战,但也突破了一些固有的局限,让我们开始认识到,女性的领导力并不仅仅体现在权威和权力方面,她们也可以在一些重要位置上有担当,因为她有这个能力,还体现在若她们不在领导位置上,也应勇于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七、男女协同促进性别平等
性别平等就是消除一切对女性的歧视、偏见,为男女提供平等的机会,使女性最终在社会上得到更好的发展。在追求性别平等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自身反思,不是说遇到任何事情时马上说“不平等,怎么办?”性别平等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其遇到的障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因此我们心中要有追求这种平等的耐心和力量,并为此不懈努力。此外,我们要看到每个人在实现性别平等过程中的力量。当我们在研究论文中运用性别视角进行分析时,虽然她的工作可能与此关系不大,但已形成的这种意识,会在无形中影响她的实践。性别平等,最重要的是女性自身要有自信,这是实现性别平等的基础。而且,男性与女性间的理解和合作也非常重要,倘若男、女性之间不能促进彼此的对话、理解,永远也没有出路。我们也要有一种权利意识和行动力。换言之,我认为性别平等和其他的平等一样,要在行动中逐步实现,这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指标。
(责任编辑:孙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