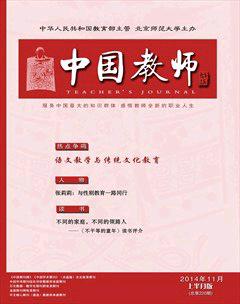《礼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当代价值
邵曼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直到现在,领略那些古人的智慧精髓依然让我们有醍醐灌顶之感,那些渗透在经典字句中的高尚品质依然规范着现代人的一言一行。随着中国经济的日新月异,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我们对自身的文化愈加引以为傲,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考察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从全国各地对儒学的日渐重视中便可窥见一斑。
2014年10月11日,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丁鼎教授应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之邀出席“京师人文宗教讲堂”,主讲儒学系列讲座第15场——《<礼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当代价值》。丁鼎教授在开场时对该讲座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朱小健教授表示了感谢,称自己到京师这藏龙卧虎之地举办讲座,感到诚惶诚恐,并简要介绍了讲座的主题:《礼记》在整个儒家经典体系中最集中、最全面、最系统地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和核心价值观,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广泛、持久而深刻的影响,直至今日,《礼记》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一、《礼记》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在儒家经典文献体系中,《礼记》一书虽然成书较晚,但却占有无与伦比、举足轻重的地位。考虑到大家的疑虑,丁鼎教授指出,经孔子整理并传承下来的“六经”(或“五经”)的确被普遍认为是儒家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元典,而且“六经”中的《礼》也的确是对《仪礼》十七篇而言的,而并非指《礼记》四十九篇。既然如此,那么为何又说《礼记》才是儒家经典的代表作呢?在丁鼎教授看来,之所以说《礼记》在思想意义的重要性上超越“五经”,甚至是“十三经”的其他经典,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其一,“礼”是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他指出,儒家礼学历来讲究“陈其数”、“知其义”,儒家“六经”无不渗透着浓重的“礼学”内容。对此,丁鼎教授解释道,“数”即是各种礼节和仪式的具体规定,“义”则是各种礼节和仪式所体现的思想内容。与《仪礼》十七篇和《周礼》单纯侧重于“数”不同,《礼记》四十九篇涵盖儒家“礼学”的“数”和“义”,因而更能代表儒家的礼学思想。他又进一步阐释道,《仪礼》十七篇所讲述的冠、婚、乡、射、朝、聘、丧、祭等八类礼节,基本上都属于“数”的范畴,主要讲述各类礼节的具体的行为规范;《周礼》(原名《周官》)是一部记述王室职官制度的著作,按照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个序列,记述了三百多种官职的设置及其职掌,基本上属于“陈其数”的范畴;《礼记》一书不仅陈述各种礼的“数”,而且揭示各种礼的“义”。
不仅如此,丁鼎教授还介绍说,《礼记》四十九篇,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上至治国方略、社会发展规律,下至家庭伦理规则,在《礼记》中都有专章论述。由此可知,《礼记》集中阐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在《三礼》之中最能代表儒家思想精髓。另外,丁教授以清代著名学者焦循之语进行佐证。焦循曾说,“《周官》、《礼仪》,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礼仪》。《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礼记补疏·序》)。这无疑肯定了《礼记》在三《礼》中的首要地位。
其二,《礼记》早在唐代就已取代了《仪礼》的地位。丁教授详细地将《礼记》和《仪礼》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指出《仪礼》十七篇相传是由孔子整理和传承下来的,汉代所谓“五经”之一的“《礼》”就是指《仪礼》。与此不同,《礼记》四十九篇则是西汉中期礼学博士戴圣搜集编纂的一部礼学资料汇编;到东汉末期,著名经学大师郑玄为其作注,《礼记》的思想学术价值越来越被学术界所重视;到三国曹魏时,《礼记》便升格为“经”,并设立了博士,取得与《礼仪》、《周礼》并列的地位;北朝时,“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礼》、《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北史·儒林传》)。可见,当时的学者重视并热衷于《礼记》之学,而对《仪礼》、《周礼》已相当冷淡;唐王朝统一天下后,唐太宗有鉴于由于南北朝时政治的分裂而形成的经学混乱的局面,便诏令当时的国子监祭酒孔颖达组织学者撰写《五经正义》,用以统一全国经学。由于当时人民普遍重视《礼记》一书,“人皆竞读”(《唐会要》卷十五),而《礼仪》一书,“殆将废绝”(《旧唐书·杨瑒传》),于是孔颖达等人便将《礼记》升格为“五经”之一,并为其作“正义”(疏),从此以后,《礼记》便取代《仪礼》,正式进入“五经”之列。根据《礼记》的发展过程及最终取代《仪礼》的事实来看,《礼记》在《三礼》乃至儒家经典中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
其三,《礼记》思想价值的重要性不仅在三《礼》中居于首位,而且其地位甚至盖过“五经”。丁鼎教授以朱熹创立的“四书学”作为导引,指出朱熹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与《论语》、《孟子》两书并列,合称“四书”,并为这四部经书分别作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朱熹的“四书学”思想不仅阐发了儒家义理(包括儒家的天理论、心性论、认识论等),而且着重强调“四书”重于“五经”。朱熹曾说“《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朱子语类》卷十九),以“熟饭”与“禾”来比喻“四书”与其他经典。丁教授解读道,朱熹此言是认为“四书”能够直接体现孔孟之道,相当于“熟饭”,而“四书”之外的其他经典则与孔孟之道有所间隔,相当于“禾”。既然阅读“四书”之外的其他经典相当于“打禾为饭”,也就是说,“四书”比“五经”及其他经典更重要,丁鼎教授如是总结道。
对于历史上及当今许多人把《周易》看作是“六经之首”的说法,丁鼎教授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坦言,诚然诸如《四库全书》、《十三经注疏》等许多重要丛书的确将《周易》排于首位,现代学术界也几乎将“六经之首”当成《周易》的同义语,但考诸相关文献便知,这种说法虽然渊源有自,持之有故,但并不确切,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丁鼎教授指出,先秦至西汉前期,儒家六经排列顺序一直是以《诗经》作为“六经之首”,而并非以《易经》居首。自西汉晚期刘歆《七略》开始,《易经》才被列于儒家“六经”的首位。至宋代虽有人明言《周易》为“六经之首”、“群经之首”,但也有人明言《诗经》为“六经之首”。而且南朝齐王俭的《七志》还曾将《孝经》列为众经的首位,宋范祖禹也明言《孝经》“乃群经之首”。综上所述,可知将《周易》列为“六经之首”或“群经之首”只是经学史上的一家之言。尽管西汉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采用了刘歆把《易经》列于群经之首的排列方法,但丁教授认为,这种排列顺序正如现代学者周予同先生所说:是以六经的撰作时代为序,而不宜从思想意义的重要性这一角度来解读这一排列方法。谈论至此,他不无遗憾地表示,由于《礼记》成书较晚,因而从未被列于群经之首。他随即又表示,《诗经》只是一部古代诗歌总集,虽然其基本精神符合儒家的思想格调,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阐释儒家的思想学说;《易经》本是一部卜筮之书,其“易传”(十翼)主要阐释阴阳变化的哲学思想,并未对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因此,丁鼎教授认为,无论是《易经》还是《诗经》,虽然它们在排列顺序上都曾居于首位,但从思想意义的重要性上来说,都不具备担当儒家“群经之首”的资格。
二、《礼记》的思想内容及其当代价值
在探讨《礼记》的当代价值之前,大家不妨考虑一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礼”,作为我国古代封建帝制社会纲纪的“礼”,有没有“当代价值”?丁鼎教授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两千余年,儒家所倡导的“礼”基本上一直被作为“修身”与“治国”的规范,但自从20世纪初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社会形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后,数千年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礼”不仅失去其作为社会纲纪、社会规范的地位,而且往往被看作是散发着“毒气”的垃圾而遭到全盘否定,人们甚至将中国近代以来经济、文化、科技的落后,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腐败,民众的愚昧落后等问题,统统归罪于儒家所倡导的“礼”。丁鼎教授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儒家倡导的“礼”固然有其陈旧、过时的内容,但仍存在许多具有普世价值的内容,这些思想内容对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他不赞成对礼学的全盘否定,认为应对其理性地、批判地继承和弘扬。
丁鼎教授以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理念及邓小平的“小康社会”理论为着眼点,从近代到现代的历史隧道中感知不同时代的踏浪扬帆者对礼学思想的不同运用。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深受西方进化论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但从总体来看,还是植根于《礼记·礼运》提出的“大同”思想。康有为依据《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表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由“据乱”进为“升平”(小康),由“升平”进为“太平”(大同),进入大同社会后,人们都会成为快活无比的“神圣”。据此,丁鼎教授强调说,显然康氏在《大同书》中追寻的理想社会,既有儒家传统社会理想的特色,又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世界。并且《礼记》在近代中国的时代价值不止于此,孙中山就曾极力推崇《礼记·礼运》所倡导的“天下为公”理念,主张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共和社会,这便是将《礼记》思想充分运用于时代的产物。他感叹道,在现代中国,《礼记》所蕴含的思想精华依然是国家领导人和思想家运筹帷幄的重要法宝。20世纪后半期,邓小平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提出的“小康社会”中的“小康”二字,实际上源于《礼记·礼运》,蕴含富足、礼义和公正的社会理想。在中国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手中,“小康”二字化用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目标,并对小康社会的标准、内涵、实现途径和时间都作了明确的阐释,将“小康社会”定义为“中国式的现代化”,使得“小康”一词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随后,丁鼎教授从“和谐社会”的角度切入,进一步揭示《礼记》在现当代散发的时代光辉。像《礼记·儒行》提出的“礼之以和为贵”,《礼记·中庸》所言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说法表明,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的主导精神是“和”。正是这一基本精神,决定了“礼”的社会功用,即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丁鼎教授认为进入21世纪后,我们党和国家断然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全党全国的历史任务,是对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批判地继承和超越,体现出向崇尚和平共处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回归,也是《礼记》一书现代价值的体现。
丁鼎教授开心地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很重视弘扬传统文化,曾于2013年专程到山东曲阜考察中国孔子研究院,并在座谈会中发表重要讲话,这被看作是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宣示。习总书记近几年来多次在讲话与文章中引用《礼记》的文字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认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礼记》的当代价值。丁教授在现场还详细为大家解读了这些事例,比如习总书记在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同学的回信中曾化用《礼记·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来勉励广大青年要勇于创新创造;又比如,在2014年6月28日举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总书记发表的题为《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的主旨讲话中,两次引用《礼记》的文字表述自己的思想认识。他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他又说:“坚公平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平正义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国际关系领域追求的崇高目标。”丁鼎对此解释道,其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典出于《礼记·中庸》,原文为“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典出《礼记·礼运》。习总书记在讲话中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作为当下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之道,而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看作是人类社会的远景目标。对《礼记》的引用等证明了《礼记》在治国安邦领域的价值,丁鼎教授如是总结道。
另外,丁鼎教授也肯定了《礼记》中的“大学之道”和“中庸之道”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当代价值。他认为《大学》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和《中庸》提出的“不偏”、“不易”、中正、平和的为人处世之道,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努力弘扬光明品德,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并积极入世,兼济天下,造福社会。《礼记》的诸多思想理念不仅成为鞭策知识分子修身养性、完善自我的思想圭臬,而且也被我国许多高等学校作为办学目标的校训。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河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诸多高校都从《礼记》中选取相关文字作为校训,如中山大学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河南大学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等。这绝非偶然,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些学校认识到了《礼记》的现代价值。不论在学校教育范围内,还是扩展到社会中,《礼记》中的相关思想已内化为人们的言行规范,无形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
丁鼎教授的这场讲座让大家体会到了礼学学者儒雅、博学的风范,认识到《礼记》在儒家经典体系的重要地位及其当代价值。他在现场笑言自己总是忍不住将《礼记》排在儒家经典体系之首,朱小健院长则戏称其为“学者对自身研究领域的热忱”。不论如何,我们都希望这场“礼学之风”兼容并包,古今贯通,扬起鲜明的时代特色,唤醒国人心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那份“热忱”。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孙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