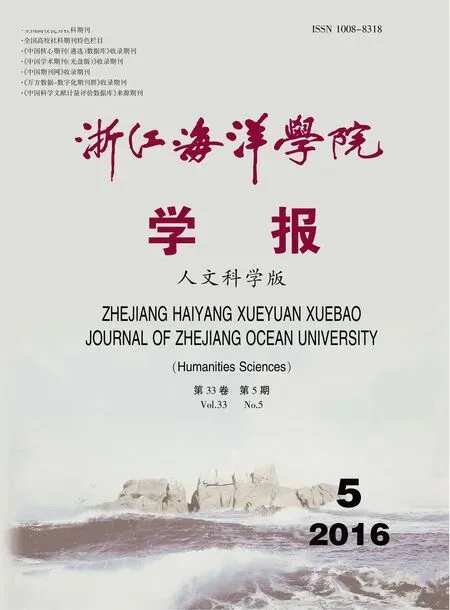从《佳人奇遇》看梁启超的小说翻译观
陆贝旎
(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技学院,浙江舟山316004)
从《佳人奇遇》看梁启超的小说翻译观
陆贝旎
(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技学院,浙江舟山316004)
作为政治家,梁启超小说翻译观的意识形态特征明显。他选取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进行翻译,其目的是要借助政治小说之力来提高国民的政治觉悟,开启民智,救亡图存,将外国政治小说中所宣扬的革命精神和政治主张引入中国,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本文试图通过论述梁启超翻译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的目的和动机,阐释其小说翻译观,并揭示这种翻译观的启蒙现代性意义。
《佳人奇遇》;梁启超;翻译观;启蒙;现代性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学术家,革命家和翻译家,其学术领域涉及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法学、社会学、图书馆文献学、宗教学、金融学、科技史、国际关系中外文化交流等,可谓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虽英年早逝,但其学术论著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今中国的学术界和思想界。他前半生投身政治,后半生倾心学术,游走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彰显了鲜明的个性。学界对其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概而言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梁启超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晚年社会活动;2.梁启超的文化思想;3.梁启超的佛学研究;4.梁启超的哲学思想研究;5.梁启超的文学研究;6.梁启超的图书馆学、文献学和目录学研究;7.梁启超的报刊与编辑思想研究;8.梁启超的美育教学研究;9.梁启超的翻译思想研究等。上述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从宏观角度来考察梁启超研究领域的,而从微观个案入手,论述梁启超的翻译思想的著述并不多见。本文试图以分析梁启超翻译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的目的与动机为切入点,剖析其小说翻译观及其启蒙现代性意义。
一、《佳人奇遇》其书
就小说类型看,《佳人奇遇》属于政治小说。该小说为日本作家柴四郎所作,全书共16回。描写的是主人公东海散士(作者柴四郎本人)游历欧美的过程。故事开篇,东海散士驻足美国费城自由钟前,瞻仰独立战争历史遗迹,偶遇一位爱尔兰独立运动斗士红莲,又遇西班牙卡尔洛斯党员幽兰。故事凭借东海散士与这两位佳人的交谈,抨击英国政府的暴政。接着描写东海散士与这两位佳人以及中国明代遗臣的交往和欧洲游历的所见所闻。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叙述东海散士与欧洲各国仁人志士的会面,各自慷慨陈词,议论日本与世界政事,作者的政治见解清晰可辨。小说特别反映出弱小民族向往国家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愿景,尤其提及爱尔兰、埃及、波兰、西班牙、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家争取自由独立的情况。这些弱小国家的奋斗精神无非透着这样一个信息: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共同意愿。小说还有不少篇幅借一位“支那志士”范卿之口讲述晚清中国的情况,尤其论及英国通过鸦片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小说第一回有一段如是说:“然其当道,不厌武事,蚕食诸邦之余,又犯日本,再攻清国,扬兵威,劫清人,输入鸦片,清人毙于此毒者以千万数”。小说最后,东海散士回到日本,投身于“新兴日本”的独立斗争。总之,该小说表达了作者对弱小国家的同情与对日本现状的强烈不满,充满了爱国的热情及独立的愿望。柴四郎试图透过叙述被统治民族的悲哀,说明自由与独立的重要。由此可见,《佳人奇遇》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小说,体现了强烈的自由民权思想和作者的政见。
二、梁启超翻译《佳人奇遇》的缘起和动机
梁启超邂逅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纯属偶然。“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在逃亡日本所乘坐的日本大岛号军舰上,舰长见他无聊郁闷,送《佳人奇遇》为其解闷。由于当时日本语的书写以日语汉字为主,假名用得较少,了解书中的大意对梁启超并无多大困难。他触景生情,将书中内容与当时中国国情发生联想,唤起了心中的悲愤,引发了强烈共鸣,因受到该小说内容刺激,梁启超试图通过译介政治小说来“浸润于国民脑质”。[1]23
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2]梁启超翻译《佳人奇遇》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自然也不是出于文学欣赏,其翻译行为带有鲜明的政治目的。众所周知,梁启超在众多的头衔中,首先是一位政治家。他译介《佳人奇遇》同样也呈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同样也要为其“政治活动服务”。1898年11月梁启超于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在其“规例”中,他明确提出了“政治小说”概念,并声明“政治小说”栏目为该报的重要内容之一。《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随之发表在该报上,阐述了翻译小说的重要意义,大力鼓吹政治小说的社会作用,明确指出政治小说用以启迪民智、振奋民众的爱国精神。该文声称“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在昔欧洲各国变更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3]
如前所述,《佳人奇遇》当属政治小说。“政治小说”这一说最初缘自英国,由梁启超从日本首次引入中国。学界一般认为开创政治小说这种文类的典型代表为英国著名政治家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年),在其还未涉足政坛时,曾出版过第一部政治讽刺小说《维维安·格雷》;曾担任过英国国会议员的布韦尔·李顿(Bulwer Lytton,1803—1873)也出版过政治小说。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极受欢迎,日本政治小说创作的崛起完全得益于他们近20部政治小说的译介。日本人格外推崇政治小说,称其为“以启发人民政治觉悟和宣传政党理想为目的”而创作的小说。[4]因此,日本人不但译介西方政治小说,还自创了许多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就是其代表作品之一。
实际上,梁启超译介《佳人奇遇》时,政治小说因其较强的政治性,大段的议论,单调的情节,可读性差等原因,在西方和日本已不再风光,但对于正挣扎在亡国边缘的中国来说却是适合的小说文类。梁启超这一选择的动机,顺应了当时中国国民启蒙教育的需要,其翻译实践可谓因时因势而作。梁启超一面鼓吹政治小说,一面躬亲《佳人奇遇》翻译。梁启超之所以选择翻译《佳人奇遇》,是因为其故事情节与自己境遇相类似,小说所体现的重建祖国的政治抱负又与自己的政治主张契合。他认为写政治小说的人往往均为大政治家,“寄托书中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固不得专以小说目之。而其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则《经国美谈》、《佳人奇遇》两书为最云”。[5]
正是在梁启超等人的竭力鼓吹下,众多的西方、日本政治小说相继译成中文,流行在近代中国的大地上。政治小说翻译成为20世纪初年中国翻译界一道靓丽的风景,除《佳人奇遇》外,著名的还有柴四郎的《东洋佳人》、大桥乙羽的《累卵东洋》、长田偶得的《日本维新英雄儿女奇遇记》、矢野文雄的《经国美谈》和《极乐世界》、东洋奇人的《未来战国志》、佐佐木龙的《政海波澜》、末广铁肠的《雪中梅》、《花间莺》和《哑旅行》、押川春浪的《千年后之世界》、《新舞台》和《旅顺双杰传》,还有未署名的《游侠风云录》等[6]。由此可见,政治小说在当时得到了国人的认可。
梁启超以政治家的身份从事翻译实践,其动机不言而喻,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是“专欲发表区区政见”。[7]通过有目的地译介西方政治思想和宣传他本人的政治主张,实现其“翻译救国”的思想。
三、梁启超的小说翻译观
梁启超可以说是提倡翻译西洋文学的第一人,在“救亡图存”和“翻译救国”功利主义思想引导下,梁启超的小说翻译兴趣落在了政治小说。虽然梁氏的小说创作成就并不突出,但其仅有的几部译作却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佳人奇遇》就是其中之一。梁启超通过译介《佳人奇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政治小说”这个概念,开创了近代中国政治小说翻译的先河。
晚清时期,翻译从非主流的“杂学”走向具有政治目的的行为,其始作俑者当推梁启超。早在1896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论译书》中就提倡翻译“西方致用”之书,并强调翻译之重要。他指出,“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8]他以“强国”为翻译宗旨,提出了远见卓识的翻译主张。虽说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间,小说被视为不入流的“小道”,是雕虫小技,为“壮夫所不为”,不过梁启超清楚:既然小说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它必须具备教诲功能,正所谓“文以载道”。他翻译《佳人奇遇》的动机和《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发表足以表明:在梁启超思想意识里,小说是可以用来作为改造国民性的工具。该文开篇就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9]
1898年,梁启超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从理论高度奠定了政治小说的社会地位和开民智功能。但是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小说却持否定态度,认为其不是“诲淫”便是“诲盗”,除此两端,别无他物。这说明在梁氏的眼里,中国传统小说内容是腐朽的,不可能用来改造国民的思想,只有通过大量译介外国小说,尤其是政治小说,才能启蒙国民的思想。因此,梁启超欲借西方小说来推行其“小说界革命”,竭力鼓吹西方小说的社会意义,并通过抨击中国传统小说的种种弊端,大肆宣扬西方小说的进步元素,从而变革中国的传统小说,以期提高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他曾大声疾呼“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把历来受轻视的小说正式纳入文学范畴。他明白小说可以“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也可以“劝善惩恶,幼存鉴戒,不可谓无补于世”。[10]梁启超如此极力主张译介外国政治小说,就想借“他山之石”去攻中国传统小说之“顽玉”。他首先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基础出发,确立理论的合理性,进而针对中国传统小说的不足,输进外国小说中的政治议论这一新鲜血液,以便浇灌国民的头脑。梁启超这种小说翻译观与中国传统“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的文学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梁启超慧眼识小说,识的是小说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他发起“小说界革命”,提倡翻译政治小说,定义翻译主张,这一切都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梁启超的这种政治情结同时也决定了其翻译观的功利性质。
维新派小说评论家丘炜爰的《论小说与民智关系》与梁氏抱有类似的观点,十分推崇政治小说的译介。他说:“故谋开凡民智慧,比转移士夫观听,须加什佰力量。其要领一在多译浅白读本,以资各州县城乡小馆塾,一在多译政治小说,以引彼农工商贩新思想,如东瀛柴四郎氏、矢野文雄氏近著《佳人奇遇》、《经国美谈》两小说之类,皆于政治界上新思想极有关涉,而词意尤浅白易晓。吾华旅东文土,已有译出,余尚恨其已译者之只此而足,未能大集同志,广译多类,以速吾国人求新之程度耳。”[11]《佳人奇遇》确实适应了当时国人的需要,该书在《清议报》连载时即引起极大反响。1901年,广智书局为其出单行本,次年,又编入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自1902年初版到1906年11月,曾重印过6版。[12]
四、梁启超小说翻译观的启蒙现代性意义
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催生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西学热,他们希望通过译介西方而不懈追求现代化。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严复的《天演论》和梁启超的《佳人奇遇》等译作都是有力的明证。这些外来文本被译介者灌注了新的思想内涵,再经过中国本土语境滋润,无疑成为了中国现代启蒙思想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启蒙现代性肇始于翻译活动。18世纪西方的启蒙主义者为了让人们解脱封建统治和宗教束缚,以理性为工具,强调人的主体性,构建了“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运动就是现代性的真正出发点。[13]从时空维度上看,晚清时期的中国也发生了一场启蒙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前后,以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发起了旨在“开民智、兴民德、鼓民力”的“新民”运动,其目的就是要摆脱旧文化的束缚,用西方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提倡自由和民主。因此,“现代性”(modernity)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进步意识形态相联系的。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认识到思想启蒙的意义,若要救国图强,必先救民思想,于是民众的政治启蒙被其列入了议事日程。蒋林认为,梁启超翻译《佳人奇遇》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小说中所反映的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向往自由和抵制封建专制的主题与梁启超“新民”和“民智启迪”思想相吻合;二是小说中所宣传的立宪公议主张更与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14]167翻译除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操控外,还受控于译者主体性发挥。梁启超的小说翻译观很显然具有现代性取向,其现代性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拟译文本的现代性取向和翻译话语的现代性”。[14]156从原作的文本选择来看,梁启超初涉翻译就选择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完全出于其政治思想的启蒙需要,而该小说的前半部分正是表现了强烈的自由民权思想。从翻译操作而论,梁启超充分发挥其作为译者的主体性作用,采用“译述”的方法,操控着翻译的整个过程,使翻译文本“译中有述”,“译中有改”、“译中有增”、“译中有删”、“译中有评”,体现了梁启超翻译行为和翻译话语的现代性取向。
梁启超不光自己翻译政治小说,还自作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他用“新”和“未来”这个“现代性”来挑战传统小说的“过去性”。可以这么说,这本自创小说就是梁启超对自己政治小说理论的献身说法。在一篇名为《中国之唯一文学报〈新小说〉》的文章中,梁启超评论了政治小说的形式设计:“政治小说者,著者欲藉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起立论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15]在梁启超的小说中,“未来”是一种动力目的,随着情节显示的时间流程,展示出其隐藏的终极目标。
梁启超不但从理论上倡导翻译政治小说的社会功用,而且还身体力行亲自翻译。从梁启超翻译《佳人奇遇》这部政治小说目的和动机看,其翻译观是功利的。他译介政治小说,其目的是为了配合维新改良运动,借“说部”“发表政见,商榷国计”。[1]37“政治小说”这种文类,虽然缺少文学的艺术性,没有小说应有的趣味性,但对于启发民众觉悟,提高民族意识,激发爱国主义精神无疑会产生积极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政治小说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启蒙现代性意义。
[1]陈平原,夏晓红.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Nord,Christiane.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1.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9:1.
[4](日)吉田精一.现代日本文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14.
[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八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9:41-42.
[6]陈应年.梁启超与日本政治小说在中国传播与评价[M]//杨正光.中日文化与交流(第一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117-118.
[7]王宏志.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72.
[8]梁启超.论译书[C].//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翻译研究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10.
[9]易鑫鼎.梁启超选集(上卷)[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12.
[10]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
[11]阿英.晚清文学丛抄·小说戏曲研究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0:411.
[12]李伟.中国近代翻译史[M].济南:齐鲁书社出版社,2005:265.
[13]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1.
[14]蒋林.梁启超“豪杰译”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15]梁启超.中国之唯一文学报《新小说》[M]//夏晓虹.觉世与传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65
On Liang Qichao’s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 from His Translated Novel Fortuitous Meeting
LU Beini
(Donghai Science&Technology College,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Zhoushan 316004,China)
As a politician,Liang Qichao’s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 is obviously characterized by social ideology.He selected the Japanese political novel Fortuitous Meeting to translate in order to raise the national political consciousness,enlighten the people and save his country from subjugation and ensure its survival with the help of political novels.He did his best to introduce into China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political views advocated in the novel,motivating the patriotism of his fellow countrymen.This paper attempts to elucidate that Liang Qichao’s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 reveals the significance of enlightenment of modernity by discussing both the purpose and motive of Liang Qichao’s translation of the political novel Fortuitous Meeting.
Fortuitous Meeting;Liang Qichao;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enlightenment;modernity
I207.41
A
1008-8318(2016)05-0054-05
2016-08-11
陆贝旎(1986-),女,浙江岱山人,助教,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