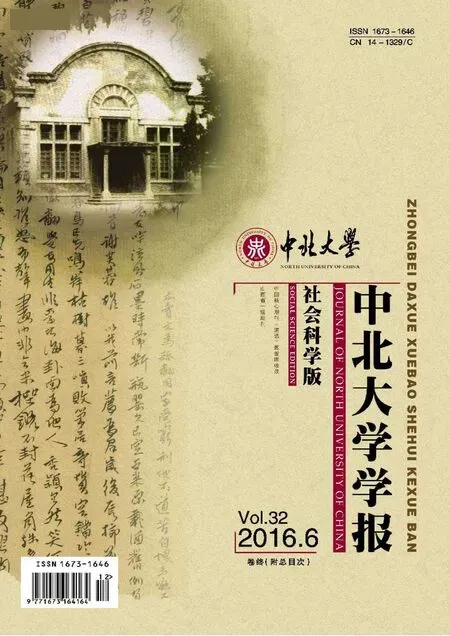清末民初新小说对诗性传统的中断与续接
廖高会
(中北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51)
清末民初新小说对诗性传统的中断与续接
廖高会
(中北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51)
晚清白话文运动和“小说界革命”的展开, 小说成为“文学之最上乘”者; 随着新小说的大量创作, 诗歌为主体的抒情文学受到冷落; 加上新小说对写实主义的过度推崇, 直接导致了民族文学诗性传统的中断; 西方启蒙思潮对国人时间观念的改变, 成为新小说诗性传统中断的深层文化根源。 而清末民初文人骨子里对诗性传统的眷恋、 新小说对诗性形式的审美追求及其以“文字为中心”的叙事模式的转变, 又在一定程度上对诗性传统进行了续接。 新小说对诗性传统的中断与续接呈现出承前启后的过度特色, 这既为五四现代汉语小说的诗性生成提供了新的契机, 也为中国诗性传统与现代汉语小说的融合揭开了序幕。
清末民初; 新小说; 诗性传统; 中断; 续接
中国文学具有悠久的诗性传统, 是中国文学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 诗性传统包括诗性精神和诗性形式, 二者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 诗性精神是主体具有的诗素质、 艺术创造素质, 也是一种处于原始冲动的、 自发的抒情精神, 是自由心灵与独立人格的体现, 是客体和主体在更高意义上的交融, 是神性与人性的沟通, 是一种天人合一、 物我两忘的境界, 是从另一个更理想的、 更高的、 超验的世界对现实世界重新设定的诗意冲动。[1]15诗性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将与相应的时代潮流结合并呈现出不同的精神诉求。 就清末民初而言, 其诗性精神主要表现为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 改良群治的启蒙精神、 去旧图新的革新精神和匡时济世的博爱情怀等。 诗性形式指文学作品呈现出抒情浓郁、 语言优美、 想象丰富、 意象丰满、 节奏突显、 意境幽深以及意蕴隽永等美学特征。 诗性传统主要体现在诗词曲赋等抒情文学中, 而诗歌一直是古代抒情文学的主体, 但到了近代, 在救亡图存的历史浪潮中, 以梁启超、 谭嗣同等为代表的晚清维新派, 把曾为小道的小说推向了文学的主体地位。 虽然梁启超等人也发起过“诗界革命”, 但终因其无法更好更快地传递新思想而宣告失败。 “改良群治”的启蒙使命最终落到了小说头上, 致使吟咏情志的诗歌从以往的主流地位退居边缘。 因诗歌地位的下降, 千百年来沿着诗歌河床潺缓流动的诗性传统此时突遇阻碍, 从而致使这条诗性主流暂时中断。 但诗性传统的中断不可能是彻底的, 其强大的惯性必然冲击并渗透到当时的主流文学——新小说之中。 正是清末民初的新小说揭开了现代汉语小说诗化的序幕, 并使中国古代文学与近现代文学在诗性传统方面得以贯通。
1 晚清白话文运动和新小说的兴起对诗性传统的中断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 国势日渐衰颓, 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特别是甲午中日海战的失败, 令朝野震动, 革新民智、 救亡图存迫在眉睫。 晚清维新派先进知识分子发起了以开启民智为目的的白话文运动。 黄遵宪在1895年刊行的《日本国志》中, 参照日本国语改良经验, 率先提出言、 文合一的主张: “盖语言与文字离, 则通文者少; 语言与文字合, 则通文者多: 其势然也。”[2]810他提倡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 梁启超也从宣传改良思想出发, 在《论进步》中指出“言文合一”不仅能使文字跟进新事物, 而且便于普及智识。 “言文合, 则言增而文与之俱增, 一新名物、 新意境出, 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 新新相引, 而日进焉。 ……言文合, 则但能通今文者, 已可得普通之智识, ……故能操语者即能读书, 而人生必需之常识, 可以普及。”[3]2061897年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中指出中国贫弱落后的原因在于“文言之为害矣”, 因而进一步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4]26-271900年, 康有为的弟子陈荣衮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中更加明确地提出改革文言的主张: “大抵今日变法, 以开民智为先; 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5]142由此可见, 无论是倡导“言文合一”还是“崇白话而废文言”, 晚晴白话文运动始终具有很强的政治功利目的。
在理论上倡导白话文的同时, 为了适应“言文合一” “维新”与“新民”的需要, 维新派还大量创办白话报刊以推动白话文运动。 从1901年到1911年, 白话报刊有一百多种, 如《苏州白话报》 《中国白话报》和《安徽俗话报》等。 阿英说: “这些‘白话报’的主要内容, 不外是‘觉民’和‘革命’”, 宗旨是“将文字交给大众”[6]106。 清末民初的白话报刊为晚清白话小说提供了发表阵地, 推进了白话小说的创作。
为了更好地宣传维新派的政治思想, 梁启超等人在文学领域里先后发动了“诗界革命” “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而“小说界革命”影响最大。 “百日维新”失败后, 在域外小说的影响下, 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小说》杂志, 阐明了创办《新小说》的宗旨为“专在借小说家言, 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 激励其爱国精神”[4]340同时提出 “小说界革命”的口号。 梁启超认为维新失败在于没有“新民”, 而“欲新一国之民, 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因为小说对社会道德、 宗教、 政治、 风俗、 学艺、 人心、 人格等方面皆有“不可思议之力”, 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7]1。 新小说的“革命”对象是诲淫诲盗的古代白话小说, 因为古代白话小说是“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7]4。 在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影响下, 晚清还出现了和《新小说》一同被称为 “四大小说杂志”的《绣像小说》 《月月小说》等著名小说杂志。 在它们的推动下, 我国掀起了新小说创作的热潮。
清末民初的新小说既有白话新小说(以下皆称白话小说), 也有文言新小说(以下皆称文言小说)。 但在晚清白话文倡导者看来, 白话小说才是小说之正宗。 梦生认为:“小说最好用白话体, 以用白话方能描写得尽情尽致, ‘之乎也哉’一概也用不着。”[8]3351912年, 管达如在《论小说》中, 将小说从语言上分为文言体、 白话体、 韵文体三类, 他独推白话体为正宗。 他说:“此体可谓小说之正宗。 盖小说固以通俗逯下为功, 而欲通俗逯下, 则非白话不能也。 且小说之妙, 在于描写入微, 形容尽意。 而欲描写入微, 形容尽致, 则有韵之文, 恒不如无韵之文为便。 故虽如传奇之优美; 弹词之浅显, 亦不能居小说文体正宗之名, 而不得不让之白话体矣。”[4]786另外, 1914年, 成之在《小说丛话》中说: “近世之事物, 惟近世之言语, 乃能逮之, 古代之言语, 必不足以用矣(文字之所以历世渐变, 今必不能与古者同, 理亦同此)。 故以文言、 俗语二体比较之, 又无宁以俗语为正格。 吾国小说之势力, 所以弥漫于社会者, 皆此种小说之为之也。 若去此体, 则小说殆无势力可言矣。”[9]442在成之看来, 俗语白话适合对“近世事物”的表达, 白话小说顺应了时代需求, 理所当然为小说之正宗。
从语言角度来看, 文言精炼含蓄, 更适合诗性表达, 白话更适合小说的情节叙事和人物塑造。 张卫中指出:“如果说文言和白话分别是诗歌和小说的庇护神, 那么, 语言的转型也就为二者位次的转换提供了一个必然的基础。”[10]正是晚清白话文运动带来了语言观的转型, 直接地导致了小说与诗歌的移位。 正如陈平原所说:“白话小说之所以在理论上占优势, 更得力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推波助澜。”[11]758也正因为白话小说的繁荣和中心化, 曾经承载诗性传统的以诗歌为主体的抒情文学因承担不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而遭到排斥。 康有为认为“士知诗文而不通中外”[12]151为当时社会大弊; 梁启超认为“词章乃娱魂调性之具, 偶一为之可也; 若以为业, 则玩物丧志, 与声色之累无异”[13]155; 谭嗣同则表示要尽弃全部“旧学之诗”, 因“天发杀机, 龙蛇起陆, 犹不自惩, 而为此无用之呻吟, 抑何靡与”[14]。 在维新派人士的眼中, 抒情表意的诗文词章于救亡图存无补, 于是他们把更具有宣传功能的白话小说推为小说之正宗并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被推为正宗的白话小说所体现出来的救亡图存和启蒙民众的时代精神与民族诗性传统中的诗性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明确指出小说的功能在于“激发国耻”, 揭露“官途丑态, 试场恶趣, 鸦片顽癖, 缠足虐刑”等[15]383, 其中既有对旧秩序的反抗, 也有对现实的超越, 这种对未来世界重新设定的诗意冲动, 正是传统诗性精神的体现。 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新小说中并不乏这种精神, 但因为维新派重小说的政治功利性而轻其艺术形式, 在风起云涌改良浪潮的推动下, 他们无暇顾及作品的推敲锤炼, 艺术上的粗疏不可避免, 加之白话在诗性传达方面天生不如文言具有优势, 这些因素导致了白话小说缺少诗性形式之美, 所以白话小说不但没能承担其续接民族诗性传统的历史使命, 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诗性传统的中断。
2 写实主义原则对诗性传统的中断
无论是晚清白话文运动还是新小说, 都承担着开启民智和救亡图存的政治功能, 出于这种政治功利目的, 晚清维新派进步人士非常重视新小说的写实能力。 梁启超于1902年就谈到了小说的写实, 认为小说应该将众人的生活境界“合盘托出, 彻底而发露之”[9]34。 以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和陈天华的《狮子吼》为代表的政治小说, 多采取政论演说的语体形式, “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9]44, 这种对创作意图“彻底发露”的写实方法, 显得说教味过浓而艺术性欠缺。 狄葆贤评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时指出其“字字根于学理, 据于时局”[16], 这“据于时局”的写实方法, 削弱了小说的审美价值。
晚清的谴责小说, 仍然走了“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的路子, 较多的议论穿插, 总是在小说中急不可耐地把创作意图和盘托出, 直露夸张, 毫无曲笔, 也无意趣。 此后黄人、 夏曾佑和王钟麒等维新派小说理论家对好空发议论的现象进行了针对性批评。 黄人在《小说小话》中指出: “小说之描写人物, 当如镜中取影, 研媸好丑, 令观者自知, 最忌搀入作者论断。”[4]179这实际上是强调写实以克服空发议论之弊端。 但由于晚清维新派对小说的宣传功能的过度偏重, 以至在新小说创作中把写实推向了另一个极端, 最后落入机械写实主义的窠臼, 把写实变成了“实写”。 吴硏人谈到自己小说创作经验时指出: 把报纸上抄来的或自己听来的材料“用一个贯穿之法”串起来, 写社会小说几乎都是这个套路。[17]按照这种纪实的方法创作的社会小说在整体上缺乏锤炼, 显得意浅神散, 缺乏形象与意蕴。
随着报章的出现和逐步发展, 新小说中如社会小说、 历史小说和黑幕小说都带上了时政新闻的特点, 具有了实录的性质。 就连当时的写情小说也要求: “惟必须写儿女之情而寓爱国之意者乃为有益时局。”[18]这种具有浓厚的理性意识和功利目的的写实主义方法, 导致了小说概念化、 类型化, 粗疏草率且缺少个性, 因而鲁迅批判这类小说“辞气浮露, 笔无藏锋”[19]258。 过度的写实所导致的艺术形式的粗糙, 无疑阻断了新小说通往诗性传统的路途。
3 时间观念的演变对诗性传统的中断
新小说对诗性传统的中断还存在更深层的思想根源, 即西方启蒙思想对晚清知识分子思想观念造成了巨大冲击和深刻影响。 李欧梵在《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中指出, 西方启蒙思想给中国带来了时间观念的改变, 即由古代循环的时间观逐渐演变成为西方线性(从过去经由现在而走向未来)的时间观, 新的时间观念导致了进步的历史观(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产生, 人们的着眼点不再是过去而是未来, 从而对未来产生乌托邦想象。[20]63时间不再是循环往复的, 而是线性发展的, 于是过去的一切都待重新估价, 时间是向着未来前进的, 未来意味着与进步相连, 于是对历史的批判变成为一种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逻辑诉求。 这种新的时间意识形态, 和当时传入中国的进化论观念一起, 对诗性传统在小说中的呈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进化论’在新旧时间观的转换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它不仅是摧毁传统文化时间观的利器, 也是新时间观形成的内在依据。”[21]中国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 人们的时空观念相对稳定, 传统农业社会中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 春夏秋冬四季循环的时间观念, 世代血脉相传、 生生不息的循环式的乡土时空模式, 在现代线性的时间观和进化论的冲击下, 都纷纷遭到了瓦解。 进化论把时间切割成过去、 现在与未来, 于是, 传统农业社会中田园牧歌般的封闭的时空遭到了现代工业文明坚硬而冰冷的机器利刃的切割而显得支离破碎, 过去意味着落后与陈腐, 于是改良和革命成为晚清至五四时期的时代洪流。 内忧外患的现实, 致使民族危机意识日益增强, 晚清进步的知识分子已经无法作悠闲的审美式的抒情了, 文学成为与社会改良或革命密切相关的事件, 个体的诗意抒写在峻急的变革潮流中显得不合时宜。 因而, 晚清时期的白话文运动, 新小说对传统诗文的地位的取代及其对诗性传统的中断, 无不与这种新的时间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新的时间观使晚清先进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 救亡图存, 时间是关键; 追赶西方, 时间是关键; 于是时间带来了压力, 紧迫感与紧张感成为这个特定时代的民族集体心理。 晚清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危机重重的现实面前, 再也无法关起门来从容锻打精致的形式。 正如梁启超所说: “吾辈之为文, 岂其欲藏之名山, 俟诸百世之后也, 应于时势, 发其胸中所欲言。”[15]386这种峻急的心态直接心理影响到小说创作。 为了快速传递思想, 新小说来不及被润色加工和从容修改便发表出来, 其艺术形式的粗疏与草率难以避免。
实际上, 这种峻急的时间意识, 与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的心理特征是一致的。 黄子平等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指出, 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正义、 浪漫激情和雍容华贵等美感特征不同,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充满了焦灼感与危机感, 这种焦灼感与危机感强烈地冲击并遮掩了古典文学中的“中和”之美。[20]14创作主体的峻急或焦灼心理, 使得古典诗意所赖以存在的悠闲从容的抒情时空逐渐丧失。 当开启民智、 救亡图存的启蒙呼声响彻神州大地时, 当放眼域外革故鼎新的现代化浪潮奔涌而来时, 老大帝国的美梦被峻急的时代铁蹄踏破惊醒, 从容悠闲的诗意再也难以为继。 古典文言优雅闲适的韵味变得如此的不合时宜, 而白话文通俗化、 大众化、 快速便捷的特点, 便“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传递新思想的历史使命。 在如此的文化背景下, 以思想启蒙为己任的晚清先进知识分子, 借助小说、 诗文等文学形式急切地表达自己的新观念、 新思想, 形成流行一时的“宣讲”之风。 这种“宣讲”式的文风与政论文章接近, 理胜于情, 功利实用价值大于审美价值。 这种文学观念的转变, 使得清末民初的新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缺乏艺术形式之美, 诗性传统之流也因此中断。
清末民初白话文运动和新小说的大量创作对中国文学的诗性传统造成了一次短暂的中断, 其意义在于它带来了诗歌与小说的移位, 并迫使诗性传统重新寻找栖居之所, 这既为五四现代汉语小说的诗性生成提供了新的契机, 也为中国诗性传统与现代汉语小说的亲密融合迈出了至关重要的步伐。
4 清末民初新小说对诗性传统的续接
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倡导以及新小说的创作实践, 都体现出对民族诗性传统的某种中断, 但是, 诗性传统作为民族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学传统的一种文化基因, 仍然显示出强大的遗传与再生能力。 就清末明初的新小说创作而言, 其对诗性传统的中断与续接是同步的。 新小说对诗性传统续接的动力, 一方面来自其自身所具有的强大惯性, 一方面来自现代社会思想文化变革所带来的历史必然。
首先从语言观来看, 晚清知识分子站在现实功利的角度提倡用白话文创作, 但从文人自身修养和审美情趣来看, 又倾向于使用文言文, 因而在推进白话文运动时产生了矛盾心理。 胡适曾对晚清知识分子把社会分作了两部分而采用不同的语言进行过批评: “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 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22]252这恰好抓住了晚清知识分子语言观的软肋。 为了弥合这种矛盾的语言观所带来的文化心理裂痕, 晚清知识分子在创作新小说时采取了“外俗内雅”的策略。 陈平原指出, 新小说家追求新小说的通俗化只是表面的, 其“俗”只是在文体上而不在审美情趣上, 目的是要灌输新思想, 目的是“启蒙”, 因而不可能是真正的通俗文学。 作家们的眼光和趣味仍是用雅文学的, 通俗只是形式上的。[23]100晚清进步知识分子在文学中体现出来的“雅”的审美趣味正是诗性传统的表现。 他们主张用白话文创作小说以求通俗, 但是其心灵深处始终存在着有关“社稷江山”的豪情壮志, 有关“风雅情怀”的文人品格, 他们潜意识中存在的这种诗骚传统决定了其精神境界的不俗, 晚清新小说开启民智、 救亡启蒙的崇高立意, 正是民族诗性精神的体现。 维新派的政治小说不乏浓郁的诗性精神, 但由于形式上缺乏诗性之美, 反而中断了诗性传统。 政治小说的“宣讲”式叙事, 打破了古代白话小说倚重情节的传统, 这种淡化情节的倾向为小说的主观抒情提供了可能, 为五四现代小说的诗化与散文化打开了通道。
政治小说的潮流过去后, 晚清知识者开始了对政治小说审美乏力之弊端的反思, 开始重视小说的审美价值。 当年黄人在《小说林》的发刊词上指出:“小说者, 文学之倾於美的方面之一种也。”[4]172陆绍明提出:“点缀写情, 则为美术家之小说。”[4]180而鲁迅则指出: “由纯文学上言之, 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 皆在使观听之人, 为之兴感怡悦。”[24]57-58他强调小说的审美价值和“兴感怡悦”的情感价值, 反对小说的过分功利化, 主张小说通过“不用之用”非直接功利之手段达到“涵养人之神思”, 这神思为“刚健抗拒破坏挑战”的精神[15]494-495, 即勇猛奋进、 昂扬向上的反抗精神, 这正是鲁迅欲在小说中灌注的诗性精神。 周作人在强调文章的审美性时指出: “文章中有不可缺者三状, 具神思(Ideal)、 能感兴(Impassioned)、 有美致(Artistic)也。 ……故文章者, 意象之作也。”[4]699周作人将叙事文体与抒情文体同等看待, 可见其对小说诗性的重视。 而周氏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正是他们对小说诗性美学追求的体现。 周氏兄弟对小说的美学价值和诗性精神的重视, 是对民族诗性传统的续接, 这种主张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小说创作的诗化倾向遥相呼应。
在资产阶级维新派中, 蒋智由的创作理论在回归与续接诗性传统方面也具有代表性。 蒋智由提倡创作自由, 但同时要求遵循艺术规律, 创造“理想美”, 强调通过艺术手段创造艺术形式之美, 并把“理想美”与时代精神相联系, 指出要成为艺术“大家”必须顺乎时代潮流且超越时代。[15]422-423文学创作者应站在时代的前列做思想的引领者, 这正是从“更高的、 理想的、 超验的世界来重新设定现实世界的诗意冲动”, 是诗性精神的体现, 而“理想美”则是对诗性形式的追求, 因而, 蒋智由的创作理论恰好体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对诗性传统的追求。
在实际创作中, 晚清文人自觉不自觉地将其诗性美学追求投射于小说创作之中。 刘鹗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他提出了“哭泣”说。 “盖哭泣者, 灵性之现象也, 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灵性生感情, 感情生哭泣。”而感情“有身世之感情, 有家国之感情, 有社会之感情, 有种教之感情。”[15]574-575其“哭泣”说是对抒情传统的回归, 其对家国之痛、 社会之悲、 民族之恨、 身世之忧的发愤抒情, 正是民族诗性精神的体现。 在《老残游记》中, 除了“哭泣”似的发愤抒情外, 在景物的抒写方面, 也体现出其潜意识的诗性冲动, 如对大明湖的秋景、 黄河冰冻的景象以及桃花山世界的描写, 便是自觉地把风景描写引入到小说中, 这种方式无不体现出对古代田园诗性传统的续接。 另外, 在晚清新小说中, 有的采用了象征与寓言的艺术形式来对现实社会进行映射式批评。 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回用蛇虫鼠蚁、 豺狼虎豹、 鬼魅魍魉来象征黑暗污秽的现实; 《黄绣球》第一回用东倒西歪的房屋、 污秽的饭和爬上了蚂蚁的花象征中国的贫困嬴弱; 《老残游记》中老残梦到的那即将沉没的危船是中国处于危急存亡之际的寓言性抒写。 这些艺术技巧正是对传统诗性形式的继承。
其次, 值得重视的是, 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对象是“诲淫诲盗”的白话章回体旧小说, 并非以文言写出的笔记体小说, 因而新小说中的文言小说并无间断, 而且在数量上有压倒白话小说的优势。 文言小说长期受到文学之主流——诗歌的影响, 具有浓郁的诗性特质, 其语言具有精练雅驯、 含蓄隽永之美。 文言小说在创作时自觉地追求“诗意” “诗趣” “情调”和“意境”, 这与当时深受文言诗性传统影响的文人情趣相一致。 晚清民初文人把小说当成“大道”, 采用文言非常严肃认真地描写, 于是清末民初形成了文言小说创作的热潮, 从而“揭开了文言小说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23]157。 清末民初的文言小说在传统文言小说的基础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特别是从传统小说零聚焦叙事转向现代小说心理意识流的呈现, 从而具有了现代小说的特质。 更为重要的是, 清末民初文言小说采用 “主观诗化语体”进行叙事, 使小说具有“内面”(即内在心灵)书写倾向[25], 如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 何诹的《醉琴楼》和鲁迅的《怀旧》等, 特别是《断鸿零雁记》“颇得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神韵, 开创造社第一人称抒情小说的先河”[23]114。 这种“主观诗化语体”的审美诉求和精神特质一直延伸到五四新文学, 并影响了五四现代汉语小说的诗性生成。 因而在清末民初, 恰好是文言小说更多地承担起续接诗性传统的历史使命, 从而与五四现代小说的诗性精神相沟通。
再次, 文言小说之所以能续接诗性传统更深层的原因是“以文字为中心”的“写—读”模式的形成。 而促成这种叙事模式形成的关键原因之一正是晚清到五四时期兴起并繁荣的报章杂志。 陈平原指出, 晚清至五四时期, 各报章杂志为了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 按读者要求刊载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 在每期杂志上都刊登相对完整的“故事”, 这就逼得作家在构思上作出调整, 一方面重视每次刊载内容的相对完整, 一方面忽略了小说的整体连贯性, 使得长篇小说很容易变成近乎短篇的连缀与集锦, 这一方面促进了短篇小说的发展; 一方面打破了古代白话小说“说—听”为主的传播方式所带来的连贯叙述, 从而逐渐摆脱了古代白话小说中的说书人腔调, 逐渐重视小说的“意旨”, 强调艺术个性与日常生活的抒写, 重视人物内心感受、 联想、 梦境、 幻觉与潜意识, 追求小说的“情调” “诗趣”与“意境”等, 使晚清文言小说具有了“非情节化” “心理化”与“诗化”的倾向。[20]238-247由此可见, 时代的潮流推动着小说文体向前发展, 以报章杂志等媒介为代表的文化潮流, 带来了清末民初小说诗性传统的回归, 这是一种客观的必然。 但由于维新派改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失败, 文人们精神较为萎靡甚至颓废, 革命的激情不复存在, 致使文言小说诗性精神相对欠缺, 它们更多走向了通俗小说的道路, 偏重于娱乐或重回说教传统。 因而清末民初文言小说对诗性传统的续接更多体现在诗性形式方面。
总而言之, 清末民初新小说的诗性精神与诗性形式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融合: 白话小说诗性精神显著但其艺术形式缺少诗性特色; 文言小说在形式上呈现出较明显的诗性倾向, 但诗性精神却显不足。 因而, 清末民初新小说中的诗性还只是一股潜流, 呈现出一种承前启后的过度特色。 只有到了五四时期, 现代汉语小说才真正实现了诗性精神与诗性形式的合流, 从而在小说领域里完成了对民族文学诗性传统的续接与重建, 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20世纪文学的精神走向。
[1]廖高会. 诗意的招魂: 中国当代诗化小说研究[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1.
[2]黄遵宪. 日本国志(下卷)[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3]王蘧常. 梁启超诗文选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4]邬国平, 黄霖. 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
[5]张向东. 语言变革与现代文学的发生[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6]阿英. 白话报——辛亥革命文谈(三)[N]. 人民日报. 1961-10-06.
[7]雷达, 李建军. 百年经典文学评论1901-2000[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4.
[8]梦生. 小说丛话[G]∥黄霖, 主编. 金瓶梅资料汇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9]陈平原, 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10]张卫中. “五四”语言转型与文学的变革[J]. 天津社会科学, 2004(4): .
[11]陈平原. 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中册)[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7.
[12]康有为. 上清帝第四书(1895年)[G]∥康有为政论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13]梁启超. 戊戌政变记[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14]谭嗣同. 莽苍苍斋诗补遗[G]∥谭嗣同全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15]王运熙, 顾易生.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16]平等阁主人. 《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总批[J]. 新小说, 1902(2).
[17]包天笑. 钏影楼笔记[J]. 小说月报, 1942(19).
[18]新小说社会征文启[J]. 新民丛报, 1902(19).
[19]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插图本)[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20]王晓明.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7.
[21]唐晓渡. 时间神话的终结[J]. 文艺争鸣, 1995(2): 9-17.
[22]胡适.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G]∥欧阳哲, 主编. 胡适文集(第3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3]陈平原.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 清末民初小说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24]赵瑞蕻. 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25]黄梅. 中国现代汉语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新小说语言与文体研究[D].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09.
The New Fiction’s Interruption and Restoration of Poetic Tradition Towards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LIAO Gaohui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stinute,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 Taiyuan 030051, China)
Towards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long with the campaign of modern vernacular Chinese and “Revolution in the field of Fiction”, fiction came to be the “the supreme literary genre”, and the fictional works mushroomed. This led to the confrontation of the lyrical literature with its period of depression, which coupled with new fiction’s over-emphasis on realism, resulted in the interruption of the poetical tradition in the national literature. Moreover, this interruption can find its cultural origin in the fact that the Western enlightenment had changed the temporal concept of the citizens. However, the sentimental attachment of men of letters then to the poetical tradition, the new fiction’s aesthetical pursuit of poetical form, and its narrative transformation against “words as the centre”, had managed to produce a restoration of the poetical tradition. This interruption and then restoration produced by the new fiction, which possessed a transitional feature, had provided a new opportunity for the poetical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and ushered in a new integration of the poetical tradition and modern Chinese fiction.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new fiction; poetical tradition; interruption; restoration
1673-1646(2016)06-0001-06
2016-06-12
山西省社科联2015至2016年度重点课题: 当代小说五四诗性传统的重建及其时代价值研究(SSKLZDKT2015066)
廖高会(1973-), 男, 副教授, 博士, 从事专业: 中国现当代文学。
I207.42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6.06.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