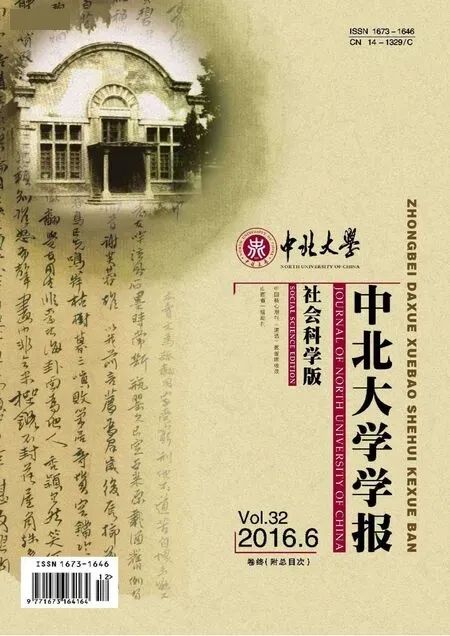从和魂汉才、和魂洋才角度论日本社区管理模式
米彦军, 胡 蓉
(山西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从和魂汉才、和魂洋才角度论日本社区管理模式
米彦军, 胡 蓉
(山西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本文根据日文第一手资料, 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 采取对比方法进行剖析; 结论如下: 世界各国的社区管理模式大致可以分为欧美模式、 日本模式、 华人模式三类, 日本政府在对欧美和华人社区管理模式进行扬弃的基础上, 探索出了半官半民的社区管理模式。 本文与其他相关论著的不同之处在于从和魂汉才与和魂洋才两个角度指出了日本社区管理模式的优缺点以及对中国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启示。
日本; 社区管理模式; 和魂汉才; 和魂洋才
1 日本社区管理模式的主要内容
日本采取半官半民方式管理社区, 即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分别设立专门机构管理社区事务, 与此同时, 又重视发挥社区居民的自主性, 实行社区自治, 为社区居民提供贴心服务。
1.1 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重视社区工作
在行政层面, 日本由东京都、 北海道、 大阪府、 京都府、 43个县(相当于省)及其下辖的市町村构成。 其中, 村属于农村社区, 由于日本城市化程度很高, 农村社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町含义有二: ①城市街区基本单位, 意为街、 巷; ②相当于我国的镇。 本文中提到的“町”采用的是第一层含义, 也就是指日本的城市社区。 由于社区建设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稳定, 因此日本政府历来重视社区工作, 从中央到地方, 各级政府都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社区事务, 具体来讲, 中央由自治省负责, 各都道府县由“社区建设委员会”和“自治活动课”负责, 在市(区)一级设立地域中心(属于政府的下派机构)负责。 管辖社区的政府机构只抓社区工作的大体方向, 负责做出规划、 指导, 提供部分经费, 征集民众意见, 干预社区具体事务的情况极少, 这给社区自治留出了很大余地。
1.2 社区居民发挥自主性, 实行社区自治
1.2.1 日本社区的居民构成和社区自治组织的结构
日本的公司绝大多数是私企, 人员流动性很强; 很多女性结婚后会选择辞职做家庭主妇, 过相夫教子的生活; 近年来, 日本的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老年人口不断增多, 等等。 基于这些原因, 负责管理日本社区的人数要比欧美和中国的多得多, 包括除了工人、 公务员、 职员、 教员、 学生以外的诸如家庭主妇、 商贩、 个体户、 失业者、 老年人等人员, 大约占到了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 而政府机构方面, 由于地域中心等民政部门没有足够的人手来直接管理社区居民, 因此他们不可能很好地表达社区居民的心声。 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社区实行自治式管理模式, 社区工作由社区居民参加的住区自治会、 住区协议会、 町内会等组织来实施, 虽然这些社区自治组织的名称不同, 但职责内容大同小异, 在日语中, 尤其以“町内会”一词用得最多。 日本社区自治组织是在自愿、 自主的基础上成立的, 以家庭为单位加入, 结构并不复杂, 主要包括会长、 副会长、 总务、 会计、 干事等。 社区的核心住户往往是一些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的旧中产阶级, 他们多数拥有房产、 靠房租过活, 或者从事个体经营, 自由时间充沛, 有条件管理社区事务, 因此会长多由这些居民中的德高望重之人担任, 副会长、 总务、 会计、 干事等均由社区居民直接选出, 利用业余时间义务兼职。 通过各种各样的社区自治组织, 社区居民能够直接参与社区事务管理, 经过民主表决可以罢免不称职的管理人员, 从而保障社区工作公平、 公正、 顺利地进行。
1.2.2 日本社区自治组织的主要职责
町内会等社区自治组织主要负责以下几类工作: ①协助市政府进行垃圾收集、 清运等环卫工作。 为了回收利用资源、 无害处理垃圾, 必须先对垃圾进行分类, 这项工作只有在社区工作人员的监督下才能圆满完成; ②与警察和政府组成联防协会搞好社区治安, 对青少年进行爱国、 爱乡、 爱社区教育, 对保释人员进行跟踪教育, 对刑释人员进行就业安置, 以防他们再次危害社区; ③办理国民健康保险、 社会福利、 代收税款等, 这类工作繁杂琐碎, 由于很多社区居民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 所以只能由社区工作人员来负责; ④组织抬神轿、 七五三、 新年参拜神社等与神道密切相关的节日庆典和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来加强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1]125-129; ⑤维持公民馆的运营, 社区居民在公民馆里进行茶道、 花道等活动, 弘扬日本传统文化, 观看国内外巡回演出, 增长见识, 等等。 由此可见, 町内会的工作内容是比较繁多的, 所以其资金来源不能仅靠微薄的政府拨款, 还要自筹资金, 筹集资金的具体方式主要包括以下两种: 一是每家每户缴纳会费, 社区工作群策群力, 不出力者出钱, 调动起了居民的积极性; 二是企业赞助或个人捐助, 通常情况下, 大多数社区内有企业的办公场所或者厂房, 企业为了搞好与社区居民的关系, 改善企业形象, 除了给社区自治组织捐款外, 还鼓励员工为社区作义工, 让社区工作进行得更加圆满顺利。
2 “汉才”与“洋才”——日本社区管理模式对中国和欧美的借鉴
2.1 从古代至二战结束日本对中国社区制度的借鉴
日本社会学者仓泽进曾指出, 中国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对基层社会的统治, 在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的制度。 从商鞅变法开始, 就尝试把军事制度活用到民间, 实行连坐制。 到了宋代王安石变法时, 以连坐制为基础制定了保甲制来管理乡村、 城镇。 此后, 虽然因朝代不同、 辖户各异, 产生了乡里制度、 村社制度、 里甲制度等称法, 但都以“户(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 以宗法社会作为管辖的社会基础。 城镇地区除了保甲制度外还有商会等自治性组织来加强管理。 与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管理的西方社会迥异, 这一制度有利于维护多民族、 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2]65-78因此, 直至20世纪初, 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 还继续沿袭了保甲制度, 形成了近代中国社区的管理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 人民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社会基层组织开始归于民政部管辖, 民政部在街道办事处之下, 设立了居委会, 负责管理辖区内没有正式单位的社会闲散人员, 后来为了与国际接轨, 采用了社区的称法。 总而言之, 我国从古至今的社区制度在促进民族团结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而日本对中国社区制度的借鉴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 公元646年, 日本在学习唐朝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化改新, 建立了天皇制中央集权制度, 加强了对基层社会的统治。 1192年以后, 日本进入武家社会, 镰仓幕府专门设置了寺社奉行一职来管理佛寺、 神社, 规定所有居民的户籍归一个个佛寺管理, 对基层社会的统治进一步加强。 江户时期, 德川幕府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这一制度更加成熟。[3]317到了20世纪30年代, 日本政府发现中国自古以来的保甲制度对加强基层社会统治、 实现举国一致大有裨益, 于是决定效仿, 建立了町内会、 邻组等制度, 形成了日本近代社区。
2.2 明治维新后日本对欧美社区制度的借鉴
2.2.1 加强中央政府对社区的管理
19世纪60年代,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结束了长达七百年的幕藩体制, 恢复了天皇制中央集权统治。 为了学习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 明治政府派出使节团对欧美国家进行了考察, 发现在社区治理方面, 英法美等国实行与议会民主制度相对应的自治式社区管理模式, 德国实行与君主专制相对应的政府主导式的社区管理模式。 由于日本与德国的国情更为相近, 明治政府遂以“和魂洋才”为理念, 采用德国的国家至上主义意识形态, 建立了都道府县行政制度, 在社区层面实行政府主导式的管理模式。 直到二战后, 日本也未放松对社区层面的管理。
2.2.2 实行社区自治
在日本社区治理中, 除了政府设立专门机构管理社区事务外, 社区居民也发挥自主性, 实行社区自治。 日本实行社区自治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内因方面来看, 自1192年源赖朝开设镰仓幕府, 到1868年明治维新, 六百多年间, 日本一直由武士阶层掌权, 在政治上实行幕藩体制, 也就是分封制, 各个诸侯的领地拥有高度的自治权, 俨然成为一个个独立王国。 再加上日本地形复杂, 交通不便, 每个村落便以神社为依托, 实行自治。 城镇化之后, 这些村落就成为城市社区的原型。 二战结束后, 日本的都道府县各自成为一个个自治体, 拥有自己的议会, 推选自己的行政首脑, 并不依靠中央任命[4]76-82, 这为社区自治提供了参考。 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 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极强, 自治不会影响国家统一, 这成为日本社区能够实行自治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上述内因, 外因对日本实行社区自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方面, 明治维新前后, 日本在积极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发现, 欧美国家普遍采用的是自治式社区管理模式, 即社区居民通过民主选举, 选出负责人来管理社区事务, 虽然日本政府在一定时期内采取了德国的政府主导式社区管理模式, 但自治式社区管理模式对日本社区管理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 从江户时期, 日本向荷兰学习, 到明治维新时期全盘欧化, 再到二战后, 在美国驻军当局的主导下, 进行民主化改革, 日本经过长期与西方国家接触, 西方的自由、 平等、 民主思想在日本社会根深蒂固, 成为了日本社区自治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
3 “和魂”——日本社区管理模式对中国、 欧美社区管理模式的扬弃
3.1 坚持“和魂汉才”理念, 革除中国社区管理模式中不适合日本国情之处
新中国成立前, 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很低, 因此, 近代中国的社区管理主要是指农村社区管理。 在近代中国的社区管理中, 存在着社区内的邻里关系远远不及家族内部的凝聚力、 有权有势的大家族常常干预社区事务的情况, 这些现象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国情是分不开的。 中国属于父系血缘社会, 并以血缘为纽带形成宗法社会, 历史上, 各个朝代都重视孝道, 以孝治国, 在中央层面实行家天下式的中央集权制, 在地方层面实行保甲制, 构成了中国近代社区的雏形。 在近代中国的宗法社会中, 宗祠只有直系男性才能祭拜, 父权凌驾于家族, 领导者凌驾于集体之上。[5]虽然儒家讲究入则孝出则悌[6]56-65, 即要向对待父母一样对待外人, 类似于“博爱”, 但是“爱”因血缘关系的疏远而递减, 因此产生了邻里关系淡薄、 大的家族有时欺压良善, 威胁到地方政府的权威等现象。 而日本虽然自古以来也受儒家思想影响, 但是母系氏族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 所以日本人更重视地缘关系, 忠大于孝, 家长服从家族, 家庭利益服从社区整体利益, 远亲不如近邻, 社区居民都有资格祭拜神社, 如此一来, 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得到了加强。
3.2 坚持“和魂洋才”理念, 革除欧美社区管理模式中不适合日本国情之处
欧美社会属于横向社会, 崇尚个性解放、 自由、 法和契约精神, 而长幼尊卑、 孝顺父母意识相对淡薄, 在社区管理中, 多采取自治为主的模式, 以个人为单位加入社区, 以基督教作为维系社区居民的精神纽带。 而日本社会属于纵向社会[7],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老幼、 尊卑观念根深蒂固, 社区、 家族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 居民以家庭为单位加入社区, 同时, 日本社区居民都是社区内神社的氏子, 即便有信仰基督教的, 也要优先参拜神社, 以神道作为凝聚居民的精神纽带, 这一点与欧美国家有很大不同。
3.3 日本社区管理模式半官半民, 相互补充, 相得益彰
日本政府本着“和魂汉才”理念, 学习中国近代社区管理制度, 对其中不符合日本国情之处进行了改造。 在此基础上, 日本政府又根据“和魂洋才”理念, 引进了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 探索出了半官半民的自治式社区管理模式。 在日本的社区管理中, 町内会等社区自治组织因其功能多样, 综合性强, 对市、 区、 街道办事处等基层政权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 社区自治组织作为沟通社区居民和政府的桥梁, 弥补了管辖日本社区的社区建设委员会、 自治活动课[8]、 地域中心等政府机构由于工作人员数量有限而无法直接与广大社区居民接触, 导致工作上出现偏差的缺陷, 使政府能够听到居民的诉求, 使政府的计划更加符合实际, 更加行之有效。 同时, 政府机构和社区自治组织的职权互不交叉, 都为社区居民服务, 在共同保障社会和谐与稳定, 促进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9]97-101日本各级政府还积极呼吁各类社会公益团体和企业为社区提供教育、 看护等免费服务, 并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借以弥补政府对社区拨款的不足。[10]这些措施既为政府节省了税金, 减轻了税负, 使政府可以将有限的税金用在民生福祉、 工农业等领域, 同时也使社区居民享受到了贴心的服务。
4 结 语
综上所述, 日本秉着“和魂汉才” “和魂洋才”的理念吸收了中国政府主导式和欧美自治式社区管理模式的长处, 创造出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社区管理模式, 促进了社区和谐、 安定和健康发展, 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然而这种管理模式也存在明显的缺点, 如出头的椽子先烂等负面习俗依然根深蒂固; 不愿加入社区的居民与社区自治组织矛盾重重; 社区居民中有信仰其他宗教的, 町内会管理人员有时强制居民参拜神社, 违反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等。
与日本相比, 我国城市化程度还比较低, 在社区建设方面还有诸多地方有待提高。 因为自古以来日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 所以日本社区管理模式对我国有诸多借鉴之处。 然而, 由于国情不同, 我国不能生搬硬套日本社区管理模式, 应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对日本社区管理模式进行扬弃,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解放前, 中国近代社区宗法社会色彩浓厚, 导致了一盘散沙的弊病。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为了提高民族凝聚力, 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 革除了儒家思想中的弊端, 建立了居委会, 后来为与国际接轨, 改称社区, 在社区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因此, 我们应该在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学习日本人的团队精神、 集体意识、 有序的社区自治和日本企业为社区服务等做法, 同时也应看到神道在侵犯日本社区居民的信仰自由方面的弊端, 将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 爱国主义、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维系中国社区居民的精神纽带, 使我国的社区建设更加完善。
[1][日]吉原直树. 亚洲社区居民组织[M]. 东京:灯塔社, 2012.
[2][日]仓泽进. 社区和居民活动[M]. 东京: NHK广播大学教育振兴会, 1998.
[3]日本史编委会. 详解日本史[M]. 东京: 山川出版社, 1981.
[4][日]中田次郎. 日本邻保组织研究[M]. 第5版. 东京: 秀英出版社, 2012.
[5]王敏敏. 日本社区管理特点分析及比较[J]. 领导之友, 2012(1): 54-55.
[6][日]越智升. 社区义工论[M]. 第5版. 东京: 幻冬舍, 2013.
[7]薛亮. 日本“家”文化刍议[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5(2): 71-72.
[8]高祥冠, 杨刚俊, 卢春莉. 城市标识系统的文化传承功能探讨[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5(1): 73-77.
[9][日]中田实. 生活自治体论[M]. 东京: 灯塔社, 2012.
[10][日]山田五郎. 出前村政朝日村役场[J]. 同志社大学纪要, 2014(1): 39-40.
On the Japanese Community Management Mode from the View of Wakonkansai and Wakonyousai
MI Yanjun, HU Rong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ain the historical, cultural, social origin and essence of Japanese community management mode; The method used in this paper is adopting the comparative method to analyze, based on the first hand data in Japanese, standing in the position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as follows: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community management mode in the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Europe and America mode, Japan mode, and China mod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discovered the official civilian community management mode by learning from Europe and America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management mode. What differs this paper from other works is that it analyz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ommunity management mode in Japan from the view of wakonkansai and wakonyousai, and it pointed out how China should draw lessons from Japan.
Japan; community management mode; wakonkansai; wakonyousai
1673-1646(2016)06-0045-04
2016-06-27
2013年度山西省留学人员科技择优项目: 日本社区管理模式研究(20130613)
米彦军(1970-), 男, 副教授, 博士, 从事专业: 日本社会史、 思想史。
F299.3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6.06.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