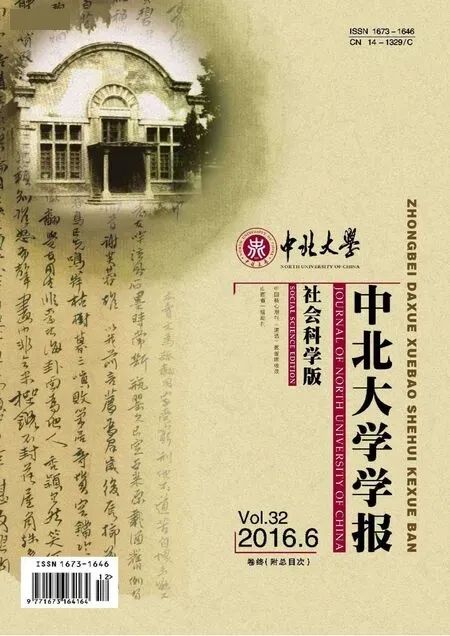浅析日本的旅行文化
徐小淑, 孟红淼
(山西大同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西 大同 037009)
浅析日本的旅行文化
徐小淑, 孟红淼
(山西大同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西 大同 037009)
本文从民俗宗教的角度分三部分梳理了从古代到现代日本旅行文化的发展变迁, 并以江户时代为重点, 分析其得以发展传承的内因与外因以及所体现的日本人内心深处的宗教情结。 江户时代是日本的大众旅行文化形成发展的时期, 沿袭了中世时代以来以寺社参拜、 巡礼等宗教信仰为目的的旅行方式, 但是已经兼有了观光游览的要素, 近代明治维新带来的制度变化和铁路交通的发展, 以巡礼为原型的新型周游观光体系应运而生, 宗教色彩逐渐淡化。 现代旅行方式和目的虽然多样化, 但是传承了几个世纪的修行之旅却以另一种形式融入到了日本人的旅行之中。
日本; 旅行文化; 寺社参拜; 巡礼; 信仰
现代社会的人们可以为休闲娱乐或兴趣爱好而自由旅行, 而近代以前的日本人大多是以灵山灵地、 神社佛寺的参拜、 巡礼, 即以信仰为名才可以外出旅行。 这一传统经过近世的庶民化得以普及。 江户时代(1603年~1868年)是日本的大众旅行文化的形成发展期, 虽然仍是以寺社参拜为主要目的, 但是已经有了观光娱乐的要素, 近代进一步发展为以参拜、 巡礼为原型的大型团体旅行。 现在的旅行方式和目的虽然多样化, 但是最初以信仰、 修行为目的的旅行仍然以另一种形式存续在现代日本人的旅行生活中。 本文从民俗宗教的角度分三部分梳理了从古代到现代日本旅行文化的发展变迁, 并以江户时代为重点, 分析其得以发展传承的内因与外因以及所体现的日本人内心深处的宗教情结。
1 宗教者的修行之旅
从奈良时代(710年~794年)开始, 日本就有山岳修行者前往包括吉野山和熊野山在内的大峰山脉修行, 他们相信吉野山上的灵石、 熊野的山川及那智瀑布是神灵居住的地方, 吉野山的金峰山寺、 熊野三社(即位于熊野川和音无川交汇的绿洲上的熊野本宫大社、 熊野川边权现山山麓的新宫熊野速玉大社、 那智大瀑布附近的熊野那智大社)就是修行者祭奉神佛的寺社。 平安时代(794年~1185年)入唐求法后回到日本的最澄(767年~822年)在京都比叡山建立了天台宗; 空海(774年~835年)以高野山为修行道场建立了真言宗, 这两个宗派成为日本佛教的主流, 真言宗的东密和天台宗的台密在重视现世利益的日本广为流传, 密教的修行者从事笼山修行。*所谓笼山修行, 即一定时期内在山中进行修行, 不能下山。 最澄在比叡山设立了十二年的山中修行制度, 称为 “笼山制度”。同时, 山岳修行者们集中在金峰山以及熊野山上创立了修验道*修验道为日本佛教的一个宗派, 以日本古来的山岳信仰为基础, 吸收了佛教尤其是密教的内容, 主张与自然合为一体的即身成佛。 也称为修验宗, 修验道的实践者称为修验者或山伏。, 开辟了从吉野至熊野的大峰山系的诸峰修行之路, 修验者视沿途的岩石、 洞窟、 树木、 瀑布、 河川等自然物为神灵, 赋予神或佛的名称并修建祠堂祭祀, 后世称为大峰七十五灵地。 大峰山系的吉野山和熊野山分别被描绘成金刚界曼陀罗和胎藏界曼陀罗, 修验者进入大峰山闭关修行之际, 要举行象征死亡的仪礼, 十界修行结束出大峰山之际也要举行象征再生的仪礼。 吉野山之后是熊野山, 站在熊野三社上, 修验者可以望见点缀着许多美丽小岛的熊野的大海, 这片海域被认为是通往观音的普陀洛伽山净土的入口。 此外, 还有以二上山为首的修验灵山葛城山系, 山中有根据《法华经》二十八品设置的岩石、 树木、 洞窟等二十八灵地, 峰顶有十界修行场。 平安中期, “森罗万象皆有佛性、 如得开悟即身成佛”的本觉思想在比叡山上非常盛行, 并由此诞生了净土、 日莲、 禅宗等镰仓新佛教。 本觉思想所倡导的“山川草木悉有仏性”思想与民俗宗教的万物皆有灵魂存在的泛灵论有着相通之处。[1]47比叡山的回峰行*回峰行是始于平安中期的佛教修行方式, 在深夜绕京都的比叡山一周, 七年内绕山千日。就是基于这一思想的修行方式, 将比叡山神圣化, 山中的堂舍、 木石皆视为佛身, 通过深夜巡拜山中灵地的苦行实践来领会天台本觉论, 即使现代仍然有出于忏悔或是寻求长生意义的回峰行者。 无论是回峰行者还是修验者、 修行僧, 其目的都是通过在与世隔绝的自然中修行, 用身体感知自然的灵力并与之同化, 从而获得新生。[2]151-152进入中世时代(1185年~1573年)以后, 日本不仅诞生了高野山、 信浓的善光寺等被视为死者他界的圣地, 全国各地也相继形成了羽黑山、 立山、 白山、 英彦山等修验道的灵山。
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镰仓新佛教的各种流派在民间普及, 成为直至今日的大多数日本人宗教生活的源泉。[3]52修验者、 修行者云游各地, 利用咒术或法力满足世人对现世利益的希求, 并利用宗教故事、 画卷来进行传教活动, 劝导平民百姓参拜圣地。 堀一郎根据众多史料将日本中世时代的这种云游四方的宗教者分为三类, 即从事山野修行、 带妻修验等在俗山伏类、 专事巫术的阴阳师类、 念佛类, 并指出他们对日本民俗宗教的形成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4]这也为近世以后庶民多样化的宗教生活奠定了基础。
2 大众的修行之旅
日本的寺社参拜、 巡礼历史比较悠久。 通过游走于民间的各类宗教者的努力, 室町时代(1333年~1573年)末期, 平民开始登拜灵山、 巡礼, 江户时代基本普及, 盛行着伊势神宫、 善光寺、 高野山、 成田山等神社, 寺院参拜活动以及各类巡礼, 这些活动大都是以“讲”的形式进行的团体活动, 即持有共同信仰的人组成的朝圣团体。 江户时代社会稳定, 成立初期, 幕府为贯彻参勤交替制度*参勤交替制度是江户幕府的大名统治政策之一, 原则上一年一轮换, 让各大名轮流在江户和领地居住的制度。 大名是江户时代将军的直属家臣中俸禄在一万石以上的武士, 约有260家~270家。, 优先整备了各地通往江户的道路和宿驿(驿站), 这些为各类参拜提供了安全方便的旅行环境; 十七世纪后半期开始, 都市工商业阶层的经济实力得到增强, 地方村落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 从经济上为广大民众的巡礼朝圣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也保证了参拜的顺利实施和良性循环。 以下笔者就以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寺社参拜和巡礼活动为例, 分析日本以信仰为名的旅行实态。
2.1 寺社参拜——以伊势讲为例
江户时代最负盛名、 参拜者最多的是伊势神宫, 神宫分为内宫和外宫, 内宫祭祀皇室的祖神天照大神, 外宫祭祀衣食住和产业的守护神丰受大神。 伊势讲在日本中世时代末期的近畿地区已经出现, 江户时期发展为遍布全国的宗教团体。 讲的组织者被称为“御师”的下级神官, 他们到各地传教, 主要是面向新兴的城镇工商业者、 农民, 将信者集中组成伊势讲, 讲员定期聚会并缴纳一定金额作为讲的参宫基金, 每年选出几个“代参者”用这笔基金到伊势参拜, 这样每人都会有一次机会。 江户时代严格限制人口, 特别是限制农民的自由流动, 但是以寺社参拜或汤治(到温泉治病)为目的可以得到外出的许可, 因此参加各种讲是庶民尤其是农民出去旅行的好机会。 他们在出发之前的一定时期就要开始斋戒直至参拜结束, 代参者要为全体讲员向神祈愿、 给神上供品和布施, 并给大家带回神社的神符或护身符。 旅途中的食宿都在御师签约的旅馆、 茶屋, 他们到达伊势之后住在御师经营的御师馆, 参宫及供品、 布施以及伊势名所的游览等全部事宜都由御师安排。 御师名义上是属于伊势神宫外宫的神职人员, 实际上在经济上是完全独立于神社的, 讲员的参宫基金以及给神宫的供奉金中有一部分会成为他们的收入, 他们与讲员之间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商人与顾客的关系。 江户中后期, 伊势神宫有两千多名御师活跃在全国各地, 光是外宫就有六百多家御师馆给讲员提供食宿[5], 随着参宫者的增多, 还出现了雇佣代理、 导游等雇员的御师。[6]11伊势讲的这种组织和运营机制, 既扩大了伊势神宫的影响, 也增加了御师的收入, 同时满足了民众的信仰心及安全旅行的需求。 享和二年(1802年)出版的十返舍一九的滑稽本《东海道徒步旅行记》*滑稽本即幽默小说, 江户后期小说体裁的一种, 多以町人的生活为题材, 采用对话形式。 读者多为平民。描写了两位主人公从江户(东京)出发参拜伊势神宫, 沿途经历的各种趣事, 引发了大众的话题, 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还有浮世绘(又称风俗画)名作、 歌川广重的《东海道五十三驿站》中描绘的东海道沿途的明媚风光及参拜者的旅途生活, 唤起了人们对旅行的憧憬, 去伊势成为许多人一生的愿望, 江户后期掀起了伊势参拜的热潮。 与现代不同, 当时没有什么娱乐休闲方式, 因此, 对生活单调的普通人来说, 旅行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团体参拜的盛行带动了和旅行相关的服务、 设施等的进一步发展,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兼具观光旅行性质的参拜日程。 参拜者忍受旅途的艰辛和各种禁忌, 净身心慎言行, 参拜结束后开荤畅饮、 游览名所、 购买土特产等尽情享受日常难以享受的乐趣, 因此大的寺社周边都有商业街, 商业街的发展也是参拜观光化的主要原因。 而且, 因为是以宗教信仰为名, 所以他们的日程及路线不受限制。 塚本明分析现存的江户时代庶民的道中日记后指出, 大半以上是以伊势参宫为中心, 且参宫之后直接返回即往返型的极少, 多数是前往京都、 大阪游览, 或是经熊野赴关西三十三观音灵场巡礼, 顺便参观沿途的名胜古迹、 享受美食、 温泉。[7]可以说, 他们是三分信仰七分游玩。 这样的周游型参拜日程得以被大众接受, 甚至有“顺便参拜伊势神宫”的落语*落语, 即日本大众曲艺之一, 类似单口相声, 以诙谐的语句加上动作, 再以有趣的结尾引人发笑。, 即实际目的是旅游观光。 这种吃喝游购的周游模式一直传承到现在。 不过即使是名义上的信仰, 参拜者到达伊势后还是会诚心诚意参拜, 除了敬畏神灵的传统思想, 也许还包含了克服漫长旅途中种种困难、 平安无事到达目的地的感激之情吧; 二是旅行指南类书籍的问世。 在旅行制度不够完善、 旅行设施不充分的时代, 参拜者到未知地域参拜时途中的指南是不可缺少的。 十七世纪中期开始有了提供旅行信息的出版物, 《东海道名所图绘》等被称为“名所图绘”的出版物图文并茂地记录了各地名胜古迹的来历, 也有记录旅行见闻的各种旅行记, 书中附有很多插画, 还有被称为“道中记”的各种旅行指南, 既有面向公用、 商用的, 也有面向寺社参拜、 巡礼的, 前者比较简略, 后者则因兼有观光性质而颇为详细。 这些图绘按照参拜目的地分类编纂, 详实地记录了途中的地名、 距离、 名胜古迹、 河川以及山道等要注意的艰险地点等。[7]1810年出版的八隅庐庵的《旅行用心集》, 其中很多内容直至现在仍然适用。 作者从旅行心得开始, 详细介绍了各地温泉所在地、 相当于现在的交通地图的街道图, 尤其是标注了61条注意事项以及旅行必备品等现在日本的旅行指南也沿用的内容,初次出行的平民通过这本书了解了旅行中的危机管理、 应有的礼貌、 享受旅行的方式等。[8]这些旅行出版物反过来也促进了庶民旅行的发展, 即现在日本的书店也摆放着各种应季的旅行指南杂志或书籍; 三是宿驿町的形成和发展。 宿驿町即以宿驿为中心形成的城镇, 包括旅馆、 商店、 茶屋等面向旅行者的设施, 当时是以徒步旅行为主, 加之是周游型, 所需时日长, 根据出发地和周游路线的不同, 一般需要一到三个月不等, 因此对于旅行者来说, 在宿驿町住宿或小憩、 品尝当地名吃也不失为漫长旅途中的一种乐趣和期待。 其次, 对温泉的利用方式也产生了影响, 不仅可以治病疗养, 还可以作为观光旅游的据点。
综上所述, 全国各地“××讲”的寺社参拜方式与伊势讲大同小异, 此外, 大峰山、 富士山、 出羽三山等灵山登拜也是以讲的形式进行。 如伊势讲那样, 参拜不是直线往返, 伊势参宫结束后大多是经大和地区前往京都大阪巡游寺社名所、 或是经熊野那智再绕道近畿巡礼三十三所观音灵场, 这种周游型的日程可以说是江户时代以信仰为名的旅行的共通点。 各种讲的盛行, 一方面促进了民间信仰的传播, 另一方面也带动了旅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而旅行文化反过来又推动了信仰之旅的观光化, 其中, 御师发挥了组织游客、 安排食宿、 制定日程、 导游等旅行社的功能, 参拜团体的吃、 喝、 游、 购则带动了旅行出版物、 观光地和交通等旅行相关产业的整备和发展。
2.2 巡礼朝圣
僧侣、 贵族的巡礼在平安时代就已经出现。 众所周知, 佛教作为中国的先进文化在唐代传入日本后, 首先是作为国家佛教, 即以镇护国家为主要目的, 平安时代以前的信奉者都是贵族, 中世时代才逐渐在民间广为传播。 庶民的巡礼最早见于室町时代末期, 其中关西三十三所和四国八十八所巡礼影响范围广泛、 且传承至今, 以下就这两种巡礼的方式和目的做一简单梳理。
关西三十三所巡礼是顺次巡拜关西地区的三十三处观音灵地, 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巡礼。 十一世纪末三井寺僧人行尊首次巡礼关西的观音灵场, 之后随着观音信仰的广泛传播, 确定了三十三所观音灵场, 巡礼者主要是修验者、 修行僧、 贵族等, 十五世纪后半期由这些宗教者引导民众加入其中, 十七世纪初期开始庶民化, 日本各地组织了很多“巡礼讲”, 刊行了《西国巡礼详图大全》等旅行指南。 中世时代一直到近代, 是关东以及东北等边远地区的人们赴中央圣地巡礼的时期, 巡礼者一般在伊势参宫之后越过大和地区或是穿过熊野街道, 前往关西三十三所, 而且将沿途的寺社也作为信仰对象参拜。 巡礼的灵场都位于海岸附近或是山脚、 丘陵等风景优美的地方, 旅途中又有京都、 大阪、 奈良等大都市, 具有得天独厚的观光资源, 因此巡礼者在向观音菩萨祈求现世利益的同时, 还可以增长见识、 享受旅行带来的愉悦。 现在仍有不少关西三十三所巡礼者, 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吧。
四国八十八所巡礼指巡拜弘法大师(弘法大师为空海的谥号)在四国地区的八十八处修行遗迹, 又被称为“四国遍路”, 是环绕四国的山与海进行的朝拜活动。 连接八十八所灵场寺院的道路则称为“遍路道”, 是最具日本特色的回游型巡礼文化, 2015年入选日本文部省指定的日本遗产名录。[9]24弘法大师入定后, 修行僧、 修验者开始了沿着大师足迹的遍历之旅, 室町时代盛行宗教者的遍路, 江户初期民众也开始参与其中。 十七世纪发行了诸如僧人真念所著《四国遍路指南》那样的面向民众的遍路指南, 并增设了路标。 除了以讲的形式的团体遍路, 还有个人遍路, 患有麻风病等被认为是恶业报应而难以治愈的病人、 因某种原因受到排斥或被逐出故乡的人等, 他们抱着对大师的信仰和各种各样的祈愿, 踏上四国遍路的心灵修行之旅, 因此与其他以祈求现世利益为目的的巡礼团体相比, 四国遍路的巡礼者的目的多为健康祈愿、 寻找自我等, 他们相信追寻大师的修行之旅可以消除业障、 求得来世的幸福。 巡礼者带的斗笠上面有“同行二人”的字样, 即自己与弘法大师二人一起巡礼之意。 而且, 四国地区的人们相信招待遍路者可以得到好报, 因此会伸出温暖之手接待他们或赠其钱物, 这个习俗一直传承到现在。
另外, 模仿三十三所或八十八所, 日本还开创了坂東三十三所、 秩父三十三所、 小豆岛八十八所、 御府内八十八所等各种小规模的巡礼, 满足那些因没有经济能力或身体原因而不方便巡礼的人, 足以说明当时巡礼的盛行。 即便是现在, 日本人依旧认为如果能把关西或四国的几十处全部巡礼的话, 就相当于经历了圣人的体验, 可以获得周围的高度评价, 可见巡礼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不仅如此, 日本人还喜欢游览和某个历史人物有关系的名胜古迹, 即步名人后尘的旅行。[10]82
综上所述, 日本人的修行之旅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从参拜的运营机制来看, 这是以信仰为名、 以讲的形式进行的团体活动。 讲的组织者发挥了现代旅行社的作用, 可以说是日本人乐此不疲的团体旅游的原型; ②从参拜的内容来看, 这不仅只是一个目的或信仰, 既有佛教的净土、 也有祖灵镇守的神社, 体现了日本人以现世利益为中心、 神佛兼信的思想, 即希望他们在现世生活中得到神的庇护, 死后往生佛的净土; ③从参拜的具体流程来看, 他们在去程中不沾酒肉、 不近女色、 言行谨慎, 一旦参拜完毕, 他们就举行开斋的宴会、 吃喝游玩泡温泉, 即修行——参拜——游乐三部曲; ④从圣地的风景来看, 寺社一般位于山中、 海边、 河川边, 因此都是围绕山川河海的巡礼, 这些远离现实的神圣之地能够抚慰、 唤醒日本人的心灵并赋予他们力量和信念, 具有特殊的意义。 作为成人仪式的伊势参拜、 巡礼和遍路就具有这种特殊意义, 年轻人经历了这样的洗礼才能作为成人被社会承认。
明治维新以后, 日本政府废除了各地的关卡, 个人自由出行成为可能, 而铁路的开通方便了人们的出行; 政府废除了御师制度, 御师大多转行从事旅馆业或商业, 但是以寺社巡礼为原型的周游观光体系却保留了下来。 明治二十年(1887年)开始实施并延续到现代的修学旅行就是其中之一, 曾经的成人仪式的一环是参拜巡礼, 因近代学校教育制度, 这个年龄还属于在学期间, 因此以修学旅行的方式代替, 一般是伊势、 京都、 奈良, 或是东京(皇居)、 箱根、 日光等地的参观学习, 政府以这样的方式让年轻人接触了解日本文化的核心。[11]148不仅如此, 从大都市近郊的民营铁路的成立看, 为成田山参拜而建的京成铁路(1897年)、 通往川崎大师的京浜线(1899年)、 高野山的南海线(1895年)、 伊势和吉野的近铁线(1927)等铁路线, 都是以社寺参拜者为主要客源而兴建的。 日本第一家旅行社(现在的日本旅行株式会社)就是利用铁路的便利和对团体旅客的优惠价格, 以组织神社参拜、 观光为目的而创立的, 并于1905年成功策划了高野山和伊势神宫的团体参拜。[12]铁路交通代替了徒步, 大大缩短了参拜时日, 参拜者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饱览沿线的名胜古迹, 享受温泉, 因此宗教要素逐渐淡化, 观光色彩更加浓厚。
3 现代日本人的旅行
日本人经过漫长历史而形成的参拜与观光兼具的各种修行之旅一直存续到现代: 战后日本观光旅游业的重振; 修学旅行和宗教团体的参拜之旅发挥了重要作用; 基于古来的信仰或是期待现世及来世利益的寺社参拜、 山岳登拜、 巡礼和遍路等旅行依然在继续。 随着压力社会的到来,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 以寻找自我、 寻求心灵净化和治愈为目的的巡礼者增加, 电视等媒体也制作了比叡山的回峰行、 四国遍路等传统修行的系列专题节目以及沿途观光地的风景、 传说、 料理、 特产等节目, 引起了大众的关注。 2004年, 纪伊山地的灵场和参拜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这些有效地推动了通过寺社巡礼了解日本传统文化、 接触自然之旅的发展。 由于便利快捷的交通手段等因素, 日本人的修行色彩淡薄, 温泉旅行、 名胜古迹的游览等观光因素增加。 现在既有徒步、 骑行、 自驾等个人或家庭、 亲朋好友的小规模巡礼、 也有乘坐观光大巴的团体巡礼。 JTB、 阪急交通社等各大旅行社都有面向个人和团体的主题巡礼或灵山参拜线路, 比如阪急交通社的“治愈心灵的巡礼之旅”[13]。 铁道公司、 巴士公司也组织各种参拜团体, 如京都京阪巴士公司的“关西三十三所巡游”[14]等, 照顾到各个年龄层和健康状况的客人, 尤其深受中老年人的欢迎。 四国地区的德岛大学等甚至将巡礼作为重新审视和发现自己的机会而编入教育课程。
当然, 现在日本人的旅行内容和方式丰富多彩, 除了上述传统的修行旅行, 还有与宗教信仰没有直接关系的旅行。 有公司的团体旅行、 家庭或友人的观光旅行等; 也有中小学生的修学旅行、 大学生的毕业旅行、 新婚旅行、 迎来花甲、 古稀之年的夫妇旅行等人生不同阶段的旅行; 还有盂兰盆节、 正月的归乡之旅, 这些基本上已经定型化成为习惯。 这些旅行中, 多多少少包含有参观学习寺社及地方传统文化、 游览山川河海体验自然、 到自己信仰的寺社所在的圣地或回到故乡寻找心中的原风景等内容, 这是与现实生活空间不同的世界, 无论是哪种旅行, 人们首先体味的是远离日常繁杂事务的解放感, 并且可以学到日常生活中体验不到的事情, 通过旅途中的同甘共苦加深与家人朋友、 同事同学之间的情谊。 与此相对, 因失恋、 工作停滞不前、 人际关系的矛盾等困扰, 独自漫无目的外出旅行的人也不少, 他们到远离尘埃的山岳寺社、 投入自然的怀抱, 或是漫步于大都市熙熙攘攘的人群。 他们从这些新的世界中得到些许慰藉或遇到人生的新契机, 从而开始新的生活。 总之, 旅行就是通过圣地、 自然、 异地等非日常性的体验, 缓减压力、 消除烦恼、 获得新的活力, 再次精神饱满地回归日常性生活。
4 结 语
综上所述, 古代的山林修行者视大自然的一草一木皆为神佛, 创立了多种修行方式和遍布日本各地的修验名山, 中世通过各类宗教者的努力, 逐渐出现了民众的修行之旅, 近世得以普及发展, 掀起了灵山圣地的参拜、 巡礼高潮。 这些以信仰为名的旅行以讲的形式运行, 讲的组织者御师充当了现代综合旅游业的经营管理者的角色, 而各种参拜巡礼讲的盛行则带动了与旅行相关产业的发展, 制度(讲的组织运营)与设施(道路交通、 食宿等)、 以徒步为主的周游旅行所需的软件与硬件系统得到了完善, 大众的修行之旅兼具了观光性质。 当然, 与现代作为个人休闲娱乐的观光旅游不同, 参拜巡礼是代表全体讲员完成参拜重任之后的放松。 近代明治维新带来的制度变化和铁路交通的发展, 使参拜巡礼成为个人行为, 铁路代替了徒步, 以巡礼为原型带有宗教色彩的新型周游观光体系应运而生, 出现了组织大型参拜观光团体的现代意义上的旅行公司, 便利快捷的交通可以使人们在参拜之余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享受旅行的乐趣, 宗教色彩逐渐淡化。 现在日本, 与宗教相关或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旅行丰富多彩, 不管何种旅行, 或多或少都有名胜古迹或自然风光的游览, 这与古代通过巡礼体验圣人、 名人的足迹、 从大自然的山川草木获得灵感和活力的修行之旅不无相通之处, 尤其是九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各种参拜、 巡礼热, 说明现代压力社会的人们仍在寻求治愈身心的回归自然之旅, 也体现了他们正向以自然为中心的世界观回归。 可以这样说, 传承了几个世纪的以信仰为名的修行之旅, 以另一种形式融入到了现代日本人的旅行之中。
[1][日]宫家准. 日本的民俗宗教[M]. 赵仲明,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日]宫家準. 生活の中の宗教[M]. 東京: 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1990.
[3][日]尾藤正英. 日本文化的历史[M]. 彭曦,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4][日]堀一郎. 我が国民間信仰史の研究: 宗教史編[M].東京: 創元社, 1953.
[5][日]神崎宣武. 大山詣りと講社[G]∥旅の文化研究所.落語に見る日本の旅文化. 東京: 和泉書院, 1995.
[6][日]神崎宣武. 江戸の旅文化[DB/OL]. 2016-05-18[2016-06-20]. www.nihon-kankou.or.jp/home/committees/
[7][日]塚本明. 道中記研究の可能性[J]. 三重大史学, 2008(8): 31-51.
[8][日]八隅蘆菴. 旅行用心集[M]. 桜井正信, 訳. 東京: 八坂書房, 2009.
[9]日本文化庁. 日本遺産[EB/OL]. 2016-05-20[2016-06-20]. www.bunka.go.jp/
[10][日]多田道太郎. 身边的日本文化[M]. 汪丽影,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1][日]宫家準. 宗教民俗学への招待[M]. 東京: 丸善株式会社, 1992.
[12]日本旅行株式会社. 会社情報[EB/OL]. 2016-05-26[2016-06-20]. www.nta.co.jp.
[13]阪急交通社.国内フリープラン[EB/OL]. 2016-05-26[2016-06-20]. www.hankyu-travel.com/
[14]京都京阪バス.バスツァー[EB/OL]. 2016-05-26[2016-06-20]. http:∥kyotokeihanbus.jp/
An Analysis of Japanese Travel Culture
XU Xiaoshu, MENG Hongmi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 Datong 037009,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ligion and folk customs,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travel culture, among which the Edo period is considered as the key to the analysi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reflected inner depths of Japanese religious complex. Japanese mass travel culture came into being and developed during the Edo period,following the trend of temple shrine, tour and other ways for the purpose of religious beliefs, but already included sightseeing, the elements of modern institutional changes resulting from the Meiji Resto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ailway.A new travel sightseeing systemfollowing the prototype of tour arose at the historic moment with religious tone gradually fading. Spiritual journeys which lasted for several centuries integrated into the Japanese trips in another form despite modern diverse ways and purposes of travel.
Japan; travel culture; temple club shrine; the tour; faith
1673-1646(2016)06-0049-06
2016-06-30
2014年度山西大同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 日本温泉文化研究(2013-B-22)
徐小淑(1970-), 女, 讲师, 博士, 从事专业: 日本文化研究。
F593.13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6.06.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