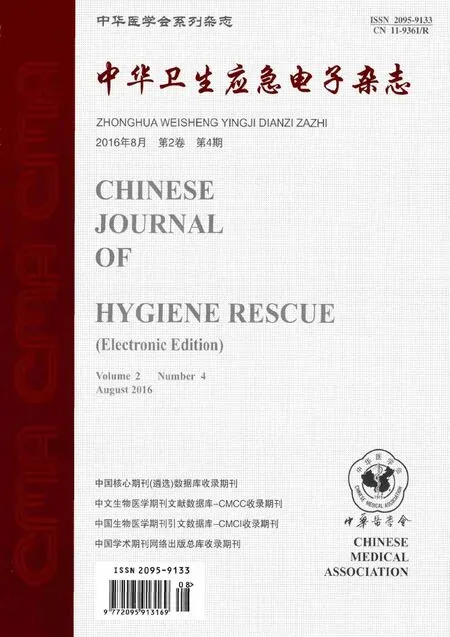脓毒症的精准诊治
——未来的发展方向
梁华平 马晓媛 孙宇
自2015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精准医学计划”以来,“精准医学”得到国内外医药学界的广泛关注。其本质是通过基因组、蛋白质组等组学技术和医学前沿技术,对于大样本人群与特定疾病类型进行生物标记物分析、鉴定、验证和应用,从而精确寻找到疾病的病因和治疗靶点,并对某种疾病的不同病程阶段进行精确分类,最终达到对疾病和特定患者行个体化精准治疗的目的,提高疾病诊治与预防的效益。国家科技部将“精准医学研究”列入2016年优先启动的重点专项之一,并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该专项的总体目标是以我国常见、高发和危害重大的疾病及若干流行率相对较高的罕见病为切入点,实行精准医学研究的全创新链协同攻关。尽管脓毒症尚未被列入其中,但针对其精准救治的时代即将到来。
一、脓毒症的诊治需要精准医学
以创伤后并发感染而进展为脓毒症者为例,笔者所在团队调查发现[1],2012年至2015年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收治的伤后24 h内入住的严重创伤患者,其感染发生率为66.96%,且感染患者中绝大部分(74.01%)发展成为脓毒症。这说明目前临床上推行的创伤感染治疗指南并不能有效遏制感染的进一步恶化。而脓毒症发生与否可明显影响其治疗结局,本团队的统计结果显示[2],ICU无脓毒症的创伤患者死亡率为3.51%,但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患者死亡率分别为16.22%、20.00%。可见脓毒症已经成为制约严重创伤患者救治水平提升的瓶颈。严重创伤患者脓毒症发生率和病死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可归咎为目前临床上根据创伤救治、脓毒症诊治指南要求采取“一种药物适用于所有患者”的治疗模式[3-4]。脓毒症患者在其遗传倾向性、既往健康史、机体免疫状态、病原体的类型、感染部位和程度均存在差异,且同一患者在脓毒症的不同进程也会呈现不同的表现及特征[5];而对于因创伤所致的脓毒症患者,影响脓毒症发生与否及治疗效果的因素更加复杂:既受到原发打击的影响,还会受到施治医院救治水平的制约。因此对脓毒症患者只有实施“精准预防”、“精准诊断”与“精准治疗”,才有可能切实降低其发生率和病死率[6]。
二、脓毒症的精准诊断
(一)快速准确鉴定感染的病原微生物
业届已证实,脓毒症诊断后1 h内应用抗生素治疗可改善患者预后,但是传统诊断方法(如血培养)耗时较长,导致后续抗生素用药延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不必要广谱抗生素的应用率。新型诊断工具相较于传统血培养更精确、快速:核酸诊断可检测细菌或真菌,较常规血培养获得检测结果更快速、病原体检测范围更广;基于微阵列的病原体检测平台也进入实用阶段。
然而上述方法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是血培养阴性但PCR阳性结果需再次验证;二是近乎1/3的血培养阳性样本不能经核酸扩增试验重复出来;三是这些方法并不能常规检测出细菌(特别是革兰阴性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6]。
有研究报道,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法(MALDI-TOF)是近年发展迅速的一种新型生物质谱技术,可快速稳定地进行细菌鉴定与分型。MALDI-TOF联合多重PCR可快速诊断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7]。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已设计制造出一种用来快速探测并识别病原生物体的小型化便携式诊断系统。该系统利用微循环和微工程技术,在一个便携的仪器中完成样品处理、纯化并检测多种病原体。目前正在进行一项能在最短时间内检测出病原微生物激光技术的试验,该技术可在野外或机场方便地检测空气或其它标本中是否含有病原微生物。用激光对微量的可疑物质加热至43 000℃,在传感器的帮助下,可识别任何可疑物的化学组成本质,检测可达皮克(pg)级。该技术的应用对于病原微生物以及可能存在的生物战剂(如“超级细菌”)的快速侦检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二)检测特异的生物标志物
对于脓毒症患者而言,约一半的血培养为阴性,该类患者与非感染性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患者的临床症状难以区分,因此发现特异性的生物标志物用于脓毒症的诊断及预后评估至关重要。目前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6]:(1)在急性期蛋白、细胞因子及凝血功能检测指标中,只有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可用于鉴别脓毒症与非感染性SIRS患者,指导抗生素的使用;脓毒症标记物Presepsin是往往在细菌感染时产生的CD14 的 N 端片段,一项研究[3]发现,Presepsin 可在脓毒症严重程度及预后风险评估中发挥积极作用,其预测准确性优于PCT,但尚需大规模临床验证[8]。(2)细胞表面分子、血管活性激素、可溶性受体(suPAR,sTREM-1)、内皮细胞标志物以及上述生物标志物的组合,虽被报道可用于协助诊断脓毒症,但尚需要进行大规模的临床验证。(3)单核细胞人类白细胞DR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 DR,HLA-DR)表达降低被认为是脓毒症的免疫麻痹状态,已被用于指导增强免疫功能的治疗。(4)通过微阵列平台进行全血样本的基因组、转录组及蛋白组学检测已被用于发现用于诊断脓毒症的特异性基因表达谱和生物标志物谱,但同样需要进一步的临床验证。
毋庸置疑,在脓毒症患者病情发展的各个阶段检测生物标志物有利于人群分层,对后续采取最佳治疗方法以及精确评估预后具有重要作用。PCT 作为研究最多且最全面的生物标志物显示出了很好的预警诊断价值,其与多种标志物联合使用可提升对脓毒症的诊断能力。越来越多的临床试验已探究采取组合的生物标志物谱对脓毒症进行诊断及预后评估[9]。有学者提议将生物标志物与临床体征相结合,如组合分析淋巴细胞表面标志[如HLA-DR、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1,PD-1)]、细胞因子[如γ-干扰素(interferon-γ,IFN-γ)]分泌功能、是否伴随院内感染及潜伏病毒的激活,将有助于指导患者的免疫治疗[10]。
(三)筛查遗传背景
众所周知,遗传变异影响了个体患病风险以及后续临床进展,深入研究个体遗传多样性有助于人们在分子水平更好地了解脓毒症。利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可对脓毒症患者与非脓毒症患者的差异位点所在DNA区段以及周边区段做进一步的遗传分析,找出与脓毒症直接相关的基因;也可将那些与脓毒症表型最相关的差异位点群作为其诊断或预测的代理标记。然而目前这种方法还并不完善,主要是较大程度上依赖于统计分析,导致假阳性和假阴性结果较多。基因组罕见变异与拷贝数变异分析对感染性疾病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脓毒症患者罕见变异与基因组拷贝数变异目前尚未完全被GWAS分析[11-13]。目前报道较多的是宿主的基因多态性,特别是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s)与脓毒症发生发展及预后的关联研究。研究最广泛的SNPs是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巨噬细胞迁移抑制因子、Ⅰ型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因子以及编码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基因的SNP。其中,TNF基因308位点的SNP研究较多。以上所有的SNPs均涉及鸟嘌呤(G)被腺嘌呤(A)替代。一项1 498例严重创伤患者队列研究显示,编码TLR1的基因-7202(rs5743551)区低频G等位基因与+1 804(rs5743612)区低频胸腺嘧啶(T)等位基因的纯合子患者具有较高的脓毒症致死风险。有研究指出,脓毒症患者SNPs与预后相关。脓毒症患者早期基因分型有助于临床医生对高危患者进行分类救治,还可识别能够受益于免疫调节治疗的患者。研究显示,当脓毒症发生时,单核细胞的TNF基因腺嘌呤(A)SNP等位基因可调控大量促炎因子的产生,然而采用抗TNF疗法治疗炎症疾病并不理想[9]。可见SNPs的检测结果如何指导脓毒症的治疗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三、脓毒症的精准治疗
如要实现脓毒症的个体化精准治疗,则需要将每位脓毒症患者的宿主—病原体相互作用的特点清晰描述出来[9],即需要关注个体异质性。但目前缺少针对于脓毒症患者的有效临床分层系统[7]。有关其精准治疗的策略尚处于尝试状态。
(一)靶向抗感染治疗
相比于传统的经验性抗生素预防以及基于病原体精准诊断的窄谱抗生素应用,靶向抗感染治疗策略更具优势和应用前景。目前,纳米颗粒已经成为抗生素载药系统及调控局部免疫炎症反应的理想工具,有效规避了传统药物出现的细菌耐药性、毒性等。如可释放一氧化氮、包含壳聚糖及金属的纳米颗粒可靶向到达感染部位,提高药物的局部浓度并通过多种机制杀菌且减少相关副作用。另外包含小干扰核糖核酸(ribonucleic acid,RNA)的纳米微粒也可将治疗性分子物质输送至感染的细胞[13]。
(二)动态调节免疫功能
脓毒症患者的免疫应答存在个体差异,且同一脓毒症患者在不同病程阶段可表现为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的免疫应答状态,因此精准评估脓毒症免疫功能,有助于实现免疫调节用药个体化。
脓毒症患者免疫功能紊乱具有以下十大特点[14-15]:(1)抗原呈递功能缺陷:单核细胞与树突状细胞表面HLA-DR表达受抑,与感染及死亡高风险相关;调节抗原呈递的某些基因表达受抑。(2)T细胞与B细胞免疫调节功能缺陷:因脓毒症死亡的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急剧消耗;CD4+T细胞、CD8+T细胞与CD19+B细胞群凋亡显著增加;IL-7/γδ T细胞轴受抑,影响其存活率。(3)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NK)免疫调节功能缺陷:NK细胞总数以及相关基因表达量减少;由NK细胞产生的IFN-γ减少,提示机体内潜伏病毒可能再度活化。(4)调节性T细胞相对增加:血中CD4+、 CD25+调节性T细胞数量相对增加;调节性T细胞CD39+表达量增加,提示患者预后较差。(5)PD-1活化:免疫抑制分子PD-1及其配体PD-L1、PD-L2在单核细胞与T淋巴细胞的表达量增加。(6)抗体水平较低:脓毒症诊断中常发现患者血丙种球蛋白过少,这会影响三种免疫球蛋白(immunoglobulin,Ig)亚型(IgG,IgA,IgM);白细胞内编码Ig的基因过表达;存活者体内IgM显著升高。(7)中性粒细胞数量及功能的改变:死亡患者外周血中性粒细胞减少;中性粒细胞迁移功能受抑,杀菌能力减弱;中性粒细胞C5a受体表达降低,与脓毒症严重度相关;不成熟中性粒细胞数量增加,与高死亡率相关;不成熟中性粒细胞标记物(弹性蛋白酶,组织蛋白酶)与器官衰竭和死亡率相关;外周血出现大量不成熟的中性粒细胞预示着早期脓毒症的恶化。(8)高细胞因子血症:脓毒症早期出现大量促炎与抗炎细胞因子;信使核糖核酸(messenger ribonucleic acid,mRNA)水平检测显示,在脓毒症早期促炎症反应与免疫抑制共存;死亡患者血清抗炎细胞因子持续高水平;脓毒症病情发展的最后阶段,脾细胞的细胞因子分泌受到抑制。(9)补体消耗:补体活化的经典途径与旁路途经均减弱;死亡患者补体C3、C4与B因子水平较低,与C3消耗增多、凝血病以及感染加重有关。(10)杀菌能力缺陷: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NETs)参与过度炎症反应与组织损伤;NETs杀菌能力减弱。
针对脓毒症患者免疫功能障碍的临床试验疗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4]:(1)胸腺素α1:介导T细胞与树突状细胞成熟,有效降低脓毒症患者死亡率。(2)重组人白细胞介素-7(interleukin-7,IL-7):促进淋巴细胞功能,如CD4+与CD8+T细胞增殖、IFN-γ产生、信号传导及转录激活因子磷酸化和凋亡相关蛋白Bcl-2表达。(3)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与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增加中性粒细胞数量。(4)IFN-γ:恢复脓毒症患者单核细胞表面HLA-DR表达。(5)阿那白滞素:通过阻断IL-1改善脓毒症患者肝胆功能紊乱、弥漫性血管内凝血以及生存率。(6)外源性免疫球蛋白:清除毒素,能有效抗菌、调节免疫,但尚未显示出可观疗效。
通过动态检测脓毒症患者免疫学指标的改善可用于判断临床治疗方法的疗效。由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所致脓毒症患者IL-10/TNFα比例显著增加,IL-6生成减少,外周血单核细胞表面白细胞分化抗原-86表达降低,这些可作为克拉霉素辅助应用的指标;单核细胞表面HLA-DR表达低于30%的脓毒症患者,经接受IFN-γ(100 μg/d)能逆转单核细胞免疫麻痹;连续注射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8 d可恢复单个核细胞的免疫活性,并能减少患者机械通气时间与住院时间。但由于缺乏应用指南与大规模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的研究证据,导致依据免疫分子表达或蛋白指标指导脓毒症患者的个体化治疗尚不可行[9]。
通过以下研究策略将有助于精准诊断患者的免疫功能紊乱状态,进而实施针对性的免疫治疗:(1)通过整合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数据,应用系统生物学综合分析机体感染期间的宿主—病原体之间的细胞与分子网络反应。(2)应用基于计算机仿真技术的系统免疫学技术检测宿主与病原体之间的配体—受体动态反应。(3)应用人类微生物组学技术发现感染的生物标志物和新的抗感染靶点[6]。上述研究策略可识别脓毒症患者抵御病原体的促炎通路或抗炎通路是上调还是下调,根据患者所处的免疫应答阶段,合理选择免疫调节药物[9]。
(三)个体化营养
大规模的临床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应用益生菌可降低脓毒症的发生率。个体化营养旨在筛选出能从服用益生菌、益生元或服用可避免或阻止病原体入侵的饮食中获益的人群,进而针对性应用以进一步降低脓毒症的发生率。服用基因修饰的微生物菌群或实施粪便移植是可选择的替代疗法[13]。
四、脓毒症精准诊治的发展方向
脓毒症的临床治疗迄今未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这是因为脓毒症患者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同质的个体,忽视了患者间的个体差异性。“一种药物适用于所有患者”的治疗模式极有可能是无效、危险和昂贵的,而“治疗诊断学”模式是通过对脓毒症患者进行诊断并确定其最有可能从该药物中获益的人群进行靶向治疗[6]。后者无疑与脓毒症精准诊治的发展方向相契合。
高通量技术与计算生物学发展的限制致使实现脓毒症个体化医疗还面临较多的难题。例如,基因组数据与临床医学信息之间的整合,基因组数据无法被临床医生搜索、共享和理解;由于基因与基因组、疾病发生因素等数据之间的高度非线性,大数据智能分析方法有待改进;新型智能统计分析系统研究尚未成熟等。如何解析上述研究进展产生的海量数据,并转化为脓毒症的临床实践诊治仍然是一项前景可观巨大挑战。
1 肖雅.解剖学评分及生理学评分联用预测严重创伤后不良结局[D].重庆:第三军医大学, 2015.
2 马晓媛,肖雅,陈涛,等. 解剖学评分联合生理学评分对严重创伤患者并发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预测价值[C].深圳,2016.广东:第十二届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灾害医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暨2016灾害医学与急危 重症高端论坛,2016.
3 马晓媛,田李星,梁华平.中西医结合诊治脓毒症的现状及思考[J/CD].中华卫生应急电子杂志,2015,1(6):389-393.
4 王正国,梁华平.战伤感染与脓毒症防治新策略[J/CD].中华卫生应急电子杂志,2015,1(1):1-3.
5 Head LW,Coopersmith CM. Evolution of Sepsis Management:From Early Goal-Directed Therapy to Personalized Care[J].Adv Surg,2016,50(1):221-234.
6 Christaki E. Personalized medicine in sepsis:the coming of age[J].Expert Rev Anti Infect Ther,2013,11(7):645-647.
7 Cohen J,Vincent JL,Adhikari NK,et al.Sepsis:a roadmap for future research[J].Lancet Infect Dis,2015,15(5):581-614.
8 Schuetz P. “Personalized” sepsis care with the help of specific biomarker levels on admission and during follow up:are we there yet? [J].Clin Chem Lab Med,2015,53(4):515-517.
9 Christaki E,Giamarellos-Bourboulis EJ.The beginning of personalized medicine in sepsis: small steps to a bright future[J].Clin Genet,2014,86(1):56-61.
10 Boomer JS,Green JM,Hotchkiss RS.The changing immune system in sepsis:is individualized immuno-modulatory therapy the answer? [J].Virulence,2014,5(1):45-56.
11 Long E,Oakley E,Babl FE,et al.An observational study using ultrasound to assess physiological changes following fluid bolus administration in paediatric sepsis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J].BMC Pediatr,2016,16(1):1-7.
12 Wheeler DS. Is the “golden age” of the “golden hour” in sepsis over?[J]. Crit Care.2015; 19:447.
13 Pinheiro DSF,Cesar MM. Personalized Medicine for Sepsis[J]. Am J Med Sci,2015,350(5):409-13.
14 Bermejo-Martin JF,Andaluz-Ojeda D,Almansa R,et al.Defining immunological dysfunction in sepsis:A requisite tool for precision medicine[J].J Infect,2016,72(5):525-36.
15 Duarte TT,Spencer CT.Personalized Proteomics:The Future of Precision Medicine[J].Proteomes,2016,4(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