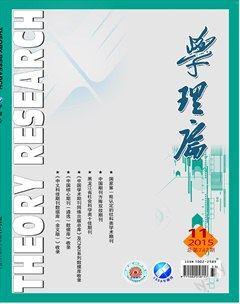从《菊与刀》看日本国民性的“矛盾性”
徐珺玉
摘 要:《菊与刀》是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论的指导下运用文化遥距法研究日本国民性的经典之作,本尼迪克特开门见山地指出:“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但是之类的词语被用于描述日本人”[1]2,关于日本国民性的“矛盾性”的描写更是贯穿全书。本文通过对本尼迪克特所写内容的简要梳理,重新审视日本国民性的“矛盾性”特征,认为日本国民性的“矛盾性”只是其行为的外在表现,这种“矛盾性”最终统一于预设的最高伦理价值。
关键词:《菊与刀》;等级制;“情理”;耻感文化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3-0095-02
本尼迪克特认为,人类行为的本质要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探究,因此对于日本国民性的研究就要求研究者“研究出这些公认的行为和判断是如何形成日本人观察现存事物的角度”[1]121。通观全书,日本的国民性是等级制、“恩情”和“情理”、耻感文化三个因素共同塑造的产物。
一、《菊与刀》内容简析
(一)深受等级制浸淫的国民性
1.战争源于对等级制的绝对信仰衍生而出的荒谬责任感。美国人认为二战的根源在于轴心国的侵略,本尼迪克特的分析则让我们洞察二战源于日本人对等级制的绝对信仰。天皇的神圣性在等级制中居于最高地位,虽然事实上对皇室的忠诚与军国主义侵略完全是两码事,但军国主义者的鼓吹使日本士兵将这两件事情合二為一。等级制观念被日本人荒谬地由自我文化移植到了他者文化之中。日本人开始认为各国的绝对主权使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他们有为世界秩序奋起而战的神圣责任,战争随即爆发。
2.基于等级制的各得其所的生活常态。“各得其所”是了解日本人的出发点,由等级制而生的不平等是日本人组织生活的准则,“各得其所”是对这种生活常态的精确概括,体现在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日本的长子从小就习得负有责任的气派;鞠躬意味着承认施礼者愿意被受礼者干预以及受礼者要承担其帮助施礼者的责任;辈分、性别、年龄本身就意味着特权;规矩、特权以及特权间的界限不可亵渎。万事万物“各归其位”“各得其所”是日本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3.由信仰等级制的明治政治家们推行的明治维新。以“尊王攘夷”为号角声的明治维新标志着近代日本的到来。等级制植根于日本的传统文化中,明治政治家们必须维护并强化日本国民对此全盘接受。“凡事关等级特权,日本人就会接受由此产生的所有后果,这并非因为他们同意这项政策,而是他们不赞成逾越特权之间的界限”[1]64。日本政府在推行新政时也不会采取硬性推广方式,因为顺应国民意愿也是“各得其所”的体现。
日本人将等级制奉为圭臬并将井然有序的等级社会视为理想社会。然而,日本人把深受等级制浸淫的文化向外输出时却遭到了惨败,日本人并未意识到,“各得其所”只是日本本土文化的产物,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
(二)被“恩情”和“情理”包裹的国民性
1.“恩情”重负下的历史欠债者。“在日本,所谓‘义就是确认自己在各人相互欠债的巨大网络中所处的地位,既包括对祖先,也包括对同时代的人”[1]68。日本人认为自己从呱呱坠地时就蒙受重恩,所以日本人不是历史的继承者而是历史的欠债者,尽孝是报父母之恩,忠诚是报天皇之恩。虽然积极报恩是日本人公认的美德,然而恩却是日本人的颈上重负,扔不得,只好扛起来。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提到一个例子,日本人表示感谢不是明言“谢谢”,而是以“这如何得了”取而代之,这种诚惶诚恐受恩的态度是对“恩”之重负的准确揭示,因为在日本人看来,“万难报恩于万一”[1]71。负有恩情债,早晚总要归还,否则便会心存不快。
2.作为动机、名誉和困境之源的“情理”。“情理”包括对社会的情理和对名誉的情理,前者是对契约关系的履行,后者代表对名声的珍视。“情理”无异于日本人的行为动机,若行为发自内心便可被认为是合乎“情理”。而对名誉的情理就是要力保不受污名,这使得日本人拥有近乎神经敏感般的自我防御态度,日本人讳言别人的失误,也避免直接竞争,甚至推崇为恢复名誉的自杀行为,只因名誉是他们的最高追求目标。“情理”在某些时候也会成为日本人的困境,当日本人面对失败、挫折时,对“名誉”的情理使得日本人倾向于自我折磨。
(三)追求适度感官享受和注重自我修养的国民性
1.不妨碍人生大事的感官享受。日本人享乐的准则是不能耽于享乐。同时,日本人认为牺牲感官享受是培养意志的有效途径,比如采用冲凉水的途径强身,不预防感冒以提高儿童身体的免疫力,甚至把绝食当作是检测一个人坚强意志的试金石。
2.以培养能力和圆熟为目标的自我修养。日本人将自我牺牲和为他人牺牲而做的事视为互惠,自我牺牲比如孩子从小就受到严格的训练会使其人生变得开阔,为他人牺牲则会得到回报。因此,日本人对能力的培养一以贯穿着自律精神,他们力求完善自己驾驭生活的能力,而且不擅长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托词。“圆熟”则意味着“意志与行动之间‘丝毫无间的经验”[1]163,以无我为基础的像死人一样地活着是“圆熟”的最高境界,也标志着自我修养的最高境界。
3.“旁观自我”视角下的儿童学习。作为对成年期严格约束自我的补偿,日本人允许幼儿和老人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不过,日本父母会坚持训练孩子的便溺习惯和纠正孩子的姿势,并且会常常嘲笑孩子,这两件事会使日本儿童树立“旁观自我”的观念,为追求他人的赞扬,儿童成人之后便会严格要求自己,力争成为受到外界肯定的人。
二、日本国民性的“矛盾性”统一于预设的最高伦理价值
日本国民性的“矛盾性”无处不在:“(1)爱美又黩武;(2)尚礼又好斗;(3)喜新又顽固;(4)服从又不驯”[2]。菊与刀是对日本国民性的“矛盾性”的点睛概括:菊是恬适静美的皇室家徽,刀是坚韧黩武的武士文化,看似处于两个极端的事物特性却在日本人身上兼而有之。同时,充满“矛盾性”的日本人却能毫无精神负担地转变自己的行为,这着实让人费解。本尼迪克特指出,西方人的生活世界是善恶转换的世界,而日本人的生活世界不包括“恶的世界”,人生是一出随时根据幕景变更行为与态度的戏,西方人眼中的“矛盾性”在日本人看来一点都不矛盾,日本人只要遵守这出戏预设的最高伦理价值即可。
(一)等级制的预设最高伦理价值是天皇至上
1.投降源于对天皇的绝对忠诚。二战中的日本战俘这样说:“只要天皇一声令下,日本人即使手中只有竹竿也会毫不犹豫马上投入战斗。同样地,只要天皇下令,也会迅速停止战斗”[1]24。1945年8月15日,素来认为投降可耻的日本人坦然接受了这一行为,因为此乃天皇敕诏。日本投降以后,日本舆论对天皇无条件的忠诚与对其他人的指责形成鲜明对照,天皇至上作为预设的最高伦理价值自始至终都没有对错之分,天皇要为重建世界秩序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人就会奋不顾身;天皇要选择投降,日本人便自然地改弦更张不再战斗。
2.各得其所的生活常态皈依于天皇生而神圣。单从精神层面上看,把日本人对于天皇的信仰比拟成宗教皈依,并不为过。日本人以社会地位中的各得其所为信条,但这并不能使封建领主们安于其位。领主们互相嫉妒彼此的权力和封地,各自混战,武士们威风凛凛,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大名或将军向敌对势力拔剑。权力虽然在不同的封建领主之间发生更替,朝代却从未更替。在“云上所”里居住的天皇必须是这个家族内部的人,领主和家臣冲突不断,天皇始终神圣。
3.对天皇的义务是明治维新的大好时机。明治维新不是观念上的革新,而是一项把日本变为强国的实际工作。明治政治家们“尊王复古”,把天皇推上权力之巅。在对天皇的绝对义务之下,仍旧是各得其所的等级常态,这使得日本政府不必像西方政府一样考虑选民的意见,从而强有力地促进了新政的实施并且成效显著。经由明治维新,日本国力一跃而增。
(二)“恩情”与“情理”的预设最高伦理价值是报恩与尽忠
1.为偿还恩情债而报恩。日本人认为自己身受天皇、父母、老师、主人之恩,对天皇的忠诚、对父母的孝道、对老师和主人在困境时的帮助都是报恩之举。“恩情”的力量推动人们全力以赴地报恩。然而,当“恩情”过重时,就会变成使受恩者难以接受的痛苦。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描述了一个失去妻子的男人,他为了孩子不再续弦,子女反而因为意识到父亲如此巨大的“恩情”之后反感父亲。不过,日本人虽然对“恩情”的反应矛盾而复杂,但报恩仍是预设的最高伦理价值,倘若暂时无法报恩,社会道德要求日本人至少要心怀愧疚。
2.“情理”不可违,“忠”更胜一筹。日本人认为对名分的“情理”不属于“恩情”的范畴,而只是保护自己荣誉的问题,必要时可以以牙还牙,采取报复或者自杀维护自身名声都未尝不可。不过,在“情理”与“忠”出现矛盾时,尽忠成为最高伦理价值。日本的民族史诗《四十七士》讲述的故事如下:四十七士为完成其主人浅野侯对“名分的情理”的义务,决定向主人的敌人吉良侯复仇。为达到使吉良侯放松警惕的目的,他们矢口否认复仇计划,有的纵情声色被人们看不起,有的为筹资金而把妻子卖为娼妓,有的采用美人计把自己的妹妹送给吉良侯以获取信息。终于,他们大仇得报,杀了吉良侯,报答了主人浅野侯的“恩情”,然而由于他们曾为报仇而“变节”,唯有一死方能两全。
(三)感官享受与自我修养的预设最高伦理价值是耻感文化统治下的他人评价
1.适度享受源于肉体与灵魂的共存。强调自我约束的日本人并不像清教徒那样约束自我欲望的满足,乍看令人不解。日本人并不承认西方哲学中肉体与灵魂是生命中此消彼长的两个力量的观点,他们认为肉体并不邪恶,因此享受无可厚非。耻感文化下的日本人又注重他人及社会的评价,故而享受又要适度,不能妨碍人生大事。
2.自我修养同样源于耻感文化。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界舆论评判自身价值,日本即是如此。日本人要想成为众口传颂之人,必须加强自我修养,既要完善自己驾驭生活的能力,又要使人生境界力臻圆熟。日本小孩从小就对镜子有特殊感情,因为镜子是“旁观自我”的象征,自律精神是日本人追求旁观者的高度评价的产物。
綜上所述,日本国民性的“矛盾性”统一于预设的最高伦理价值。真正了解日本国民性的“矛盾性”,才能真正把握日本人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及其根源所在,对于研究中日文化的差异性,正确处理中日关系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
[2]赵小平.从《菊与刀》来看日本社会国民性——矛盾性[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