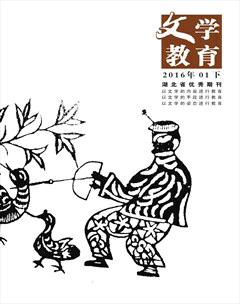例谈《汉书》个性化的写人叙事艺术
王园园
内容摘要:自甲骨卜辞对历史事件零星而不乏生动的记载,到《尚书》、《春秋》初步系统化的历史叙事出现,至《左传》、《国语》、《战国策》更是将先秦写人叙事文学推向了辉煌。司马迁吸纳众长,长于叙事,布局细节铺排有致,妙手写人,形神兼具,代表着古代历史散文叙事写人艺术的高峰。锺此,《汉书》写人叙事成就也比较高,行文从容得体,有条不紊,给人直面历史之感,呈现出独有的艺术手法,依次述之为:虚实相间与增删史事;概叙与详叙相互穿插;以叙为议与细笔妙补。还有层层推进等手法也一并加以阐述。
关键词:《汉书》写人 叙事 艺术手法
就史籍记载而言,自古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章学诚论叙事与记言的区别时称:“叙事之文,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期于适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追求实录,尽量接近历史真实,是史家的职责。然而,历史是不可能还原的,而史官又总是带着批判的眼光来对待历史人事,所以叙事之文为作者之创造自不待言。杰出的作家更能够在总体统一的风格中追求多样的变化,《史记》导其先路,写人叙事篇篇具有个性,《汉书》紧随其后,也能于篇章中运用多种手法凸显个性,令人物风神毕见,事迹详赡清晰。
一、虚实相间与增删史事
历史的纪实是相对而言的,在必要之时也需要艺术创造,当然一切的创造必须要符合历史事件的基本发展过程,并且要合乎人物的性格特征。钱钟书曾言:“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史传文学不同于小说,但是《左传》、《国语》、《战国策》在叙事写人方面均有虚构的内容,多言鬼神而传奇色彩非常浓厚,与绝对的史实相区别,但是却增强了作品的合理性,生动性和文学性,如《左传·宣公十五年》讲述的“结草衔环”的故事,就涉及到记梦与因果报应的思想。虚实相生,增强了写人叙事的可信度和感染力。《史记》中的以文运事、以情驭史的成分随处可见,如《刺客列传》中聂政之姐死烈那样富于传奇色彩的描写,入骨三分,不仅对真实的历史事件有所补充,而且本身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汉书》的作者班固虽然是一副经学家的古板面孔,但是从他的写人叙事中,我们也能够看出作者合理的想象和虚构使得篇章文采奕奕,情感表达更为充沛的一面。
如《汉书·王章传》在如实地叙述历史的同时,虚构或者想象的情节,尤为引人入胜:
初,章为诸生学长安,独与妻居。章疾病,无被,卧牛衣中,与妻决,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师尊贵在朝廷人谁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
后章任官,历位及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当知足,独不念牛衣中涕泣时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
这两个情节叙写了很小的生活故事,“牛衣涕泣”旁人难以得见,夫妻之间的对话也不是外人能够听见的,可见这些都是出于作者合乎生活实际的想象。从一“呵怒”,一“止之”可以看出王章妻是一个有见识的女子,而王章的个性形象也由此得以多方面的展现。
虽然史传作品不允许虚构或者任意改动历史人物的行事和风格,但是作为精神生产物,作家一定会带着自己的个性、局限以及时代特征去完成创作。因此,经过创作主体再现的历史人物形象必然受到了主体的“审美观照”。那么由一些创作者“观照”下描述的细节更是妙笔生花了,比如《汉书·陈万年传》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节“陈万年病榻教子”:
万年尝病,召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仗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
陈万年作为汉朝的高官,处世秘诀居然是左右逢源,谄媚事人。几句对话,先“欲仗之”后“乃不复言”,如此传神的刻画,对于陈万年父子的个性形象都有典型意义。试想,这种半夜教育儿子的事,外人几乎不可能亲眼所见、亲耳听见,而班固描写的如此细致,真实,令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才思与妙想了。
还有《外戚传》中出身倡优而以“妙丽善舞”得幸君王的李夫人,于病笃之时冒着极大的风险,再三拒绝来探望的武帝提出见面的要求。在当时李夫人的行为令人惊诧,但其深刻用心为作者通过李夫人姊妹间的对话巧妙传出:“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受宠美人与君王之爱仅止于此,读之令人嘘唏,但读者一望而知,这等姊妹间的私语不可能为外人所知,相信应是作者揣摩情境的合理想象,既符合人物的个性特征,又显得真实感人。
后世有学者批评班固为司马迁立传,几乎全部照搬《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内容,但《汉书》对《报任安书》的增收,对后世研究司马迁的生平事迹与思想显然是极为重要,由此也能够看出班固作为史官的素质和非凡的眼光。还有《汉书·贾谊传》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增补也显示出班固的卓识。司马迁从个人遭遇的角度,将屈原与贾谊二人合传,写怀才不遇的感慨与抑郁难遏之气,其中浸透了作者个人的情韵,凸现了传主的风神,因此是大家公认的成功之作。但从史学的角度来说,班固在《贾谊传》中既保存了其辞赋的代表作《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又极具眼光地收录了《治安策》、《处置淮阳各国疏》和《谏封淮南厉王诸子疏》,这样就更全面地展示了传主不仅有文学才华,也有政治才能,人物事迹始末具全,由此更深刻地写出了贾谊怀才不遇的境地,读之不禁令人扼腕叹息。就这篇传来说,于增删裁剪间,班固写人叙事显得更加详细严谨,不愧为“良史之才”。
司马迁文采卓然,纵横恣肆,而《汉书》素以严谨著称,严肃的史实经过作者的反复斟酌,裁择,显示出详略相宜,整饬谨严的风格。因此《汉书》对《史记》的删减修正之处也比较多。如《史记·张耳陈馀列传》所载“贯高事”比较详细,而《汉书》则有所删减:
汉七年, 汉高祖从平城过赵,对赵王傲慢无礼,赵相贯高等人欲杀高祖,赵王不允。···汉九年,贯高怨家知其谋,乃上变告之。于是上皆并逮捕赵王、贯高等。十余人皆争自刭,贯高独怒骂曰:“谁令公为之?今王实无谋,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谁白王不反者!”乃车胶致, 与王诣长安。治张敖之罪。上乃诏赵群臣宾客有敢从王皆族。贯高与客孟舒等十余人,皆自髡钳,为王家奴,从来。
《汉书·张耳陈馀传》记述此事,删“治张敖之罪。上乃诏赵群臣宾客有敢从王皆族。贯高与客孟舒等十余人,皆自髡钳,为王家奴,从来”一句。因为《史记》前文已经交代“上皆并逮捕赵王、贯高等。……( 贯高) 乃车胶致, 与王诣长安”,所以《汉书》在此删去前后相抵触的句子,从语意等方面来说甚为得当。
二、概叙与详叙相互穿插
历史叙事要求史家以实录的笔法,在有限的篇幅内容纳入大量丰富复杂的历史信息,这样,史家不但要在人、事材料方面精心选择,更要选用大量简单的白描,将最大的信息量浓缩于最少的文字中。如果史官仅仅是概括性的勾勒,而无铺陈与渲染之处,则会显得呆板无味,失去了历史本身的生动色彩。因此,在历史著作里如何将“史笔”与“文笔”处理好,无疑是非常重要。用现代叙事理论来说,就是把讲述性叙事、纯叙事与对话叙事、模仿叙事相结合,才能完成一篇写人叙事的佳作。司马迁首创了以人物形象解释演绎历史的纪传体,班固完全继承了这种以人写史的传统,在《史记》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史传文学的艺术技巧和叙事手法,着力塑造了有汉一代的众生相。
大凡历史著作所应有的本体意识,如史鉴与劝惩职能,讲求实录的原则,以至史家所必须的德、才、学、识,在史传文学作品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里转引了这样一段话:“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事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字里行间都充满着他对司马迁的真诚称赞与欣赏,在编写《汉书》时也处处以其为楷模。郭预衡先生认为:“(汉代)保有‘白描特点的是司马迁。司马迁的文章长处很多,其中主要的一点是不‘太做。这是扬雄、班固望尘不及的。”实际上,《汉书》虽说写人叙事较为详细,特别注重细节描写,语辞也比较典雅,但是总体风格并不是矫揉造作的,而是相对简朴凝练,特别是在概叙与详叙相结合这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方面,继踵《史记》,而更纯熟。
如《汉书》对霍光早期经历表现和外貌为人有两段简洁的描述,可窥一斑:
去病死后,光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
光为人沉静详审,长财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须髯。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
这两节交待了霍光的外貌和为人,为后面叙写其它事迹打下了基础。文中写霍光从外貌行事来看其人谨慎文弱,未尝有过,仅是守礼之人罢了。但与后面武帝临危托孤,其处事刚毅果断相对比,前后照应,以小见大,于细微处见真章。后来班固又以时间为序,详细地叙述了霍光匡国安民之举:处置上官桀父子阴谋叛乱之事,稳定政局;昭帝崩后立昌邑王贺,后又废贺立宣帝;辅佐宣帝谨慎忠勤,沉稳执政。作者集中精力刻画了一代政治家的形象,不是单一的塑造历史人物典型,而是注意多方面多手法来描写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叙事严谨详实,目的在于警醒后人,以史为鉴。
然而不得不提到的是《汉书·蔡义传》中对霍光言行的补充叙写,虽然寥寥几笔,但很能反映霍光弄权谋政的一面:
义为丞相时年八十余,短小无须眉,貌似老妪,行步俯偻,常两吏扶夹乃能行。时大将军光秉政,议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选贤,苟用可专制者。光闻之,谓侍中左右及官属曰:“以为人主师当为宰相,何谓云云?此语不可使天下闻也。”
另如《萧望之传》、《杨敞传》等均有影射霍光弄权的记载,作者将其一一叙述出来,体现了“实录无隐”的史学精神。而霍光对于昭、宣中兴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所以班固以尽量客观的态度来刻画这位人物,本传与他传相呼应,概叙与详叙相结合,起伏有致,不至于平淡无奇,罗列账单。
其中《汉书·赵广汉传》是班固撰写的较为精彩的一篇传记,叙述了赵广汉作为一个极具个性、政绩累累而又缺点突出的能干官吏,一生行事练达果敢,却最终身败名裂的事迹。全传以时间先后为序,细致地描写了赵广汉在为官期间多获政绩,打击豪强为民伸张,因“治行尤异”迁至京兆尹,然后再次曲尽细笔数列种种事例,描摹其严格执法,吏能优异。但是在全传中处于关键地位的是这样一节:
所居好用世吏子孙新进年少者,专厉强壮锋气,见事风生,无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计,莫为持难。广汉终以此败。
此段写得可谓文如其人,将赵广汉敏捷强悍的个性以及后来身陷刑戮的原因,都概叙其中。赵广汉有过人才干,使得威名远播,“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闻广汉”,作者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后来又完整地论述了赵广汉的钩距之法,与丞相魏相的较量等事情,传末专门提及因为赵广汉的廉明,百姓追思他,歌颂他。可见作者对这样一位能吏是倾向于同情和部分肯定的。作者有详有略地叙述,不紧不慢地概括出了传主的一生行迹,手法多样,主旨鲜明,章法严谨。
还有《汉书·李广苏建传》(附《苏武传》)篇末特别记载麒麟阁图画功臣的事迹,罗列十分详细,也更能突出人物形象和作者的言外之意:
甘露三年,单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次曰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次曰车骑将军龙额侯韩增,次曰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阳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阳城侯刘德,次曰少府梁丘贺,次曰太子太傅萧望之,次曰典属国苏武。皆有功德,知名当世,是以表而扬之,明著中兴辅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传。自丞相黄霸、廷尉于定国、大司农朱邑、京兆尹张敞、右扶风尹翁归及儒者夏侯胜等,皆以善终,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于名臣之图,以此知其选矣。
麒麟阁内画像有十一个人,班固不惜一一列举众人的职位名字,而且还以黄霸等人相对比,更加突出了苏武在班固心中的地位。归汉后的苏武仅为典属国,职位比较低,却和大将军霍光等同列功臣之属,可见作者对苏武的敬佩和颂扬之情溢于言表。另外,在《苏武传》中对苏武在绝地牧羊,受尽折磨的情状给予了细致的描写,读来令人动容,而对其归国后的几句白描式的叙写更是让人感动至深:“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十九年的生活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短短的一段,但是对于苏武来说却需要钢铁般的意志才能克服煎熬生存下来。作者用苏武出使前后的形貌对比,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而班固作为秉笔直书的史官,于写人叙事之间,冷静之余,也不禁倾注了浓浓的赞誉之情。而因为班固不遗余力地生动描写,苏武这个人物的形象已经具有了典型的意义,成为了坚守民族大义、不辱使命的代表,受到人们世代敬仰。
三、以叙为议与细笔妙补
《汉书》总体风格是内敛严谨的,在行文中更是较少直接议论的语句,与司马迁的鲜明褒贬相比,作者这种客观冷静的态度让后人非议颇多。唯《王莽传》中,作者在洋洋洒洒四万多字的叙事中,多有议论之语,以求多方面展示王莽的形象,这也是出于详述事迹,条分缕析内外因以告诫后世的需要。至于大部分的篇章,除赞语外,多是将感情蕴含于具体生动的叙述中,即以叙为议,真是“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总能让人“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然而,汉书的“论赞”部分有的夹叙夹议,或者稍作批判,也是对以叙为议这种艺术手法的补充。有的篇章于细笔巧妙地补出作者写人叙事的真实意图,于冷静地思索外顿感意味深远。
劝惩的精神和实录的原则,使得史传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作者要忠于史实,坚持原则,明辨是非,善善恶恶,黑白分明。歌颂光明并不难,难的是敢于揭露黑暗,鞭挞丑恶。其实从先秦时代董狐与齐太史身上,我们已经看到正直的史官在记载历史时的批评精神。其后有历史责任感的史官,无不自觉地继承了这种精神。《汉书》揭露汉文帝后期的荒于政事耽于逸乐,武帝的好大喜功连年用兵,诸侯王多凶狠残忍、恣意妄为,外戚之骄纵放恣、残暴不仁等等,都显示出强烈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不但针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体现在作者所生活的当代统治者身上。出于尊汉护国、以史为鉴的需要,历数王莽之乱始末的史官班固,对西汉末期君臣事迹记录的尤其详细。如《汉书·元后传》表现外戚王凤擅权欺主的行径令人震惊:
左右常荐光禄大夫刘向少子歆通达有异材。上召见歆,诵读诗赋,甚说之,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其见惮如此。
作者只是描述了一件寻常小事,但从皇帝与大臣的对话行事,足以看出当时百官唯王凤之命是从的状态。一句“其见惮如此”,是作者插入的评论之语,饱含着气愤与无奈。被欺压的成帝如此昏庸无能,外戚专权盖主之气焰何等嚣张。作者虽然是在简洁地叙述本事,鲜少大段的评论,但我们仍然能感觉到他难以忍耐的愤怒充斥在字里行间。
又如《汉书·元后传》记载大将军王凤临终之时,向成帝荐王音以代己:
及凤且死,上疏谢上,复固荐音自代,言谭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谭倨,不肯事凤,而音敬凤,卑恭如子,故荐之。
仅仅几句话就将王音的谄媚无耻,王凤的自私弄权,成帝的昏弱无用,一一展现了出来。作者虽没有评论,但鲜明的批判含义呼之欲出。而这些关于外戚的事迹记录在《元后传》中更显得作者匠心独运。因为元后一生见证了西汉的衰亡,作者遂将其与汉朝的国祚之变紧密相连,对元后的为人写的十分详细。哀帝驾崩之后,平帝初立,王莽辅政,才一步步将西汉王朝推向了覆灭之路。虽说王莽篡汉,处心积虑,非元后一女子所能阻挡,但在元帝、成帝之时,外戚势力已经不容小觑,而元后本欲王氏专擅天下,对王凤、王莽等人的纵宠,实际上对刘氏之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是作者专设单传以写人叙事的本意:防微杜渐,以警当朝统治者。
而作者的细笔妙补,也能篇末见真章,如《汉书·公孙弘传》末曰:
凡为丞相御史六岁,年八十,终丞相位。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继踵为丞相。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氂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唯庆以惇谨,复终相位,其馀尽伏诛云。
此段文字,《史记》没有记录,班固特意补叙,以李蔡等人相继被杀与公孙弘的逢迎安世相对比,更突出了其人的狡猾世故,身处相位却只顾迎合主上的丑陋、虚伪行为。
又如《汉书·元后传》起始曰:“孝元皇后,王莽姑也。”而结语提到:“太后崩后十年,汉兵诛莽。”不但使得传记叙事写人,有首有尾,而且两次提到王莽,更发人深省。这些小细节对王莽乱汉的事迹有所补充,更显示出作者对元后的微词,令人物事迹更加清晰,有助于对人物多方面的评价。又如《汉书·东方朔传》写东方朔直斥董偃之罪,间接地揭露了窦太主、武帝之过,作者对他们的批判之意明显。但结尾称“是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自董偃始”,看似闲笔,实际上批判之意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董偃之事了。
《汉书》还善于用层层推进法来叙写人物事迹,于极为纷繁的人情关系中将历史事描写的有条有理,刻画人物也有声有色,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创造力,如《汉书·王嘉传》笔笔聚焦于王嘉的刚直忧国,堪作柱石之臣却终被害致死,《汉书·金日磾传》不过千余字,逐层推进式叙写武帝与金日磾之君臣遇合,都是颇为成功之例。如写武帝宠爱金日磾的长子,但金日磾却因为儿子恃宠而骄,淫乱无状而杀掉他。武帝虽怒却心敬之。另一方面又将金日磾自身严于律己的作为写出,突出武帝对他非同一般的态度。双线交错,将一位谨慎持重的大臣形象刻画的栩栩如生。同时又将霍光与金日磾相互对比而写,起到了互相映衬的效果。印证了传末的赞语,同时也显示了作者的贬褒态度。
当然,《汉书》叙事写人方面有时不免因为过于详细而有繁复之嫌,有些甚至是重复出现的段落,但是就总体而言,班固善于将平叙与逆叙、插叙等多种手法交错运用,使文章的主旨更加鲜明,人物形象更加突出,其严密与详赡,实有胜于《史记》,无愧于范晔“赡而不秽,详而有体”的赞誉。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撰.史记 [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 余英时.史家、史学与时代 [M].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
[4] 杨树达.汉书窥管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郭丹.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 [M].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1999.
[6]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 [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
[7]王洲明.中国文学精神(汉代卷) [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8]崔军伟.《汉书》矫正《史记》举隅 [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作者单位:四川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