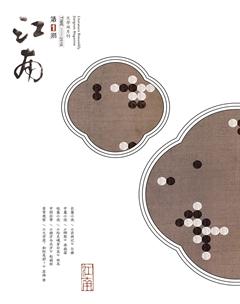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文学的财富
对话时间:2015年5月
对话人及对话整理:董晓明
一、我把诚实作为写作第一道德
董晓明:乔叶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抽空接受我们的访谈。很多读者对您的作品很熟悉,对于您的人生经历,读者也很好奇,首先请您谈谈您的成长经历好吗?
乔 叶:我1972年底出生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李万乡杨庄村,后来李万乡划到了焦作市高新区。1987年父亲去世,患癌症。1996年母亲去世,患脑溢血。父亲是焦作市矿务局干部,是村里的第一个大专生,学的是地质专业。母亲是村小的民办教师,快退休时才转正,退休没多久就去世了。弟兄姊妹五个,三男两女,我是老四,上面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在村里我们家算是书香门第吧,大哥上的中专,二哥上的师范,我也是师范。
董晓明:您的文学启蒙起于何时?是什么机缘使您走上了文学之路?
乔 叶:我的文学启蒙是上师范以后才逐渐开始的,师范生活因为没有学业和就业压力,总体来说很放松,学生们自办的社团很多,我参加的是文学社,算是一个文学小青年。当时就是觉得好玩,也没怎么上心,那时文学社的朋友也基本都是这种状况,所以当时大家在一起就是玩伴。这么多年过去再看看,好像一直还在文学路上的只有我一个了。后来一年暑假打工的时候我以打工生活为素材写了一篇小文章,参加了一个全国作文大赛,获了三等奖,主办方奖了我一百块钱,还有很多书,校长为我贴了一张大红喜报,我很惊喜,对文学的兴致就慢慢扎下根来。1990年师范毕业之后,我在乡下教书,工作之余闲极无聊,也没有合适的男人可以谈恋爱,就开始想要写作。
董晓明:您还记得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刊物吗?当时的感觉如何?
乔 叶: 1993年在《中国青年报》的副刊上发表了散文《别同情我》,我视为我的散文处女作,记得当时的稿费还蛮高的,比当月的工资还要高。上了这样的大报当然喜不自禁,好像喝了点儿啤酒吧,觉得啤酒真难喝啊。同年我也开始在《诗刊》发表诗歌,真是个标准的文学青年。1994年调到县委宣传部做干事,1998年当选县文联副主席,2001年调到省文学院当专业作家,直到今天。
董晓明: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特别影响您创作的作家或书籍?
乔 叶:我觉得这是蛮复杂的一种化学反应,很难说哪个作家谁的作品就直接影响了我。你真正写东西的时候,你不会考虑谁影响你了你才去写。不过写出来之后再去仔细分析,可能会看到或轻或重或深或浅的某些文脉。我有几个很好的作家朋友,我们互相会推荐给彼此一些书目。每个人的阅读领域不一样,这样的交叉很有益。我们读书也不只读文学类的书,社会学、哲学的也读,这也都算是知识积累吧。从个人口味而言,我比较喜欢久经考验的经典。比如前段时间我把王安忆的《长恨歌》和阿来的《尘埃落定》又拿出来看了一遍。不同的年龄去读这些作品,会有不同的感知,而且你的兴趣点可能也不同。刚开始,你可能专注于故事情节或者语言,然后慢慢地你会分析它的结构、它叙述的节奏等等。所以我会反复地读经典,从不同角度吸收营养。
董晓明:作为女性,我对您在小说中塑造的不同身份和性格的女性形象很感兴趣。您笔下的女性类型多种多样,有生活境遇窘迫的边缘女性,有挣扎在婚外情感牵绊中的职业女性等等。在您的小说中,女性总会成为小说的叙述者,敏感、细腻,注重细节和情感认知,让作为读者的我更容易接触到作品最核心的部分,采用这种女性叙述是您有意选择的吗?
乔 叶:女性人物在我的小说中出现得确实比较多,因为同为女人,写起来可能比较容易抵达。所以从女性角度叙述是很自然的选择。但写作如果仅限于个人经验或者和自己很贴近的某类人的经验,那正如张爱玲说过的那样:“通篇我我我的身边文学是要挨骂的。最近我在一本英文书上看到两句话,借来骂那种对于自己过分感兴趣的作家,倒是非常恰当:他们花费一辈子的时间瞪眼看自己的肚脐,并且想法子寻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兴趣的,叫人家也来瞪眼看。”再怎么说,肚脐眼还是小,看够了就得把目光投向其他地方。所以除了女性角度,我还是尽力让自己的角度更多维一些。无论是什么人的角度,只要是以人为本的角度就好。
董晓明:我喜欢《最慢的是活着》,它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受到广泛赞扬。我想知道这部作品写作初衷是什么。在这部作品里,奶奶不仅仅是一个人,也是一代人,许多人认为您通过奶奶和我,写了一种女性史,您认同这个说法吗?您是有意识地写作两代女性之间的命运和关系吗?
乔 叶:我的创作初衷,没有什么女性史的概念。当年写的时候没有这么宏大的文学志向。我只是怀念祖母。我和祖母的感情非常深,就特别想写一个祖孙关系的小说,觉得很有意思。怎么写呢?两人反差性非常强,精神的沿承性又非常深情,我就想写生命绵延传承的密码在哪里,对于我们何以为生、何以为活做一种思考。我大概这样想,就写了。我希望写出跟别人写的祖母不一样的、独特的祖母形象。这种写作是带有我私人温度的和个人情感认识的,某种程度上很个人化的,但也有共通的意义。小说里的叙述和我本人对照而言,在精神脉络上是一致的,但是,很多写实的东西,其实是别人的奶奶。我在阅读别人的散文时,觉得中国的祖母形象非常多,我写小说时,也在豫北乡下走了走,听朋友讲他和祖母的故事。听得非常多,特别有感触。所以这个小说里很多细节都是别人祖母的,我拿来用而已。
董晓明:我觉得,作为女性的发声者和叙述人,您的作品与传统女性书写的“私密写作”和“窃窃私语”不同,您着力展现不同女性在情感中的相同境遇,在伦理和人性面前,你给予了女性最大限度的宽容和自由,把束缚于伦理中的女性解放出来。把女人回归于人来写,我觉得这是您塑造女性人物形象很大的一个特点,您如何理解女性身体及身体书写?
乔 叶:我在中篇小说《轮椅》里有一段话,算作是自己的身体观吧:“……多么不堪。人的身体。不仅要吃喝拉撒,还要病残老死。所有的丑态和洋相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还有欲望。……是的,没有什么比身体,比我们的身体更诚实的了。”诚实的身体决定了我诚实的写作。我把诚实作为写作的第一道德。而这种诚实,无论是写男人还是写女人,我都要面对。比如说一男一女在房间里,情节发展到需要男的要有所动作的时候,我觉得硬要他去规矩,首先对我自己就交代不过去。我问自己:这符合生活的逻辑吗?不符合,那就不矫情。你就是矫情了智慧的读者也不会相信。
董晓明:在您的作品中,男性没有那种站在性别对立角度去审视的偏见色彩。在写作男女关系时,您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吗?很多评论家都提到您作品中的“耻感”问题,就是女性常常有耻辱感,这是您创作的一个独特存在,您怎样理解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这种心理?
乔 叶:坦率地说,虽然我是女作家,在小说中也常以女性视角来写作,但我不觉得自己有强烈的女性意识。无论是男性和女性,大家都是人,大家都有性嘛。我写的男性人物,他们也不一定就比我的女性人物更不可信。就比如说《打火机》里的胡厅长。那天遇到一个读者对我说,他看过《打火机》后,觉得我对男人的事、男人的心理还挺了解的。我觉得这是一种表扬。我常常觉得男性也很不容易。比如《他一定很爱你》中的陈歌,虽然是感情骗子,但他也很可怜,他也希望自己的感情有一个落脚点。每个人都有多重的角色,想让自己的写作宽广,就需要用多重视角来看问题。我举个例子: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县城工作,那里有驻地的士兵,他们大概定期才能上街,所以看到女孩就会比较兴奋。当时碰到他们吹口哨什么的,我就会特别讨厌他们,认为他们非常没有素质。后来我弟弟当兵了,我去他的驻地看他,感觉非常亲切。后来再遇到大兵吹口哨,我就觉得没什么,因为我已经开始想:我弟弟在异乡也这样啊,他也不是那么没素质嘛。设身处地这么一想,我就会很理解。所以说人的视角是会发生变化的。如果以非常苛刻的态度去看待男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他也是父亲、他也是儿子,他有他非常正常的人性上的很多东西?他对你所展示的,可能只是他恶毒和狭窄的一面。如果你这样去理解,可能你表现的东西就不会那么狭隘和尖刻。所以我觉得不论男人女人,首先他是人,所以我不去强调男性女性,而是强调人性,这是第一位的。我比较讨厌说男性很花心那种论调,女性不花心吗?当你遇到合适的机遇的时候,可能也会很花心。至于耻辱感,是评论界的一种发现或者命名,我觉得不仅是对女人适用,对男人也一样的。只要是人,耻辱感都是精神内在的一部分。
二、小说的本质就是冒犯
董晓明:2013年,您的《认罪书》的出版引起了很大轰动,这部作品给人的感觉是一气呵成的,我是用了两天的时间一口气把它读完的,随着情节的步步逼近思考也越来越深入,虽然有压抑的阅读心理,但更多的是震撼。您把目光投向那段曾被尘封的历史,用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完成了对历史的重新指认。是什么使您决定写这部小说的?
乔 叶:创作这部小说的第一动力自然是因为我对“文革”产生了兴趣。而我之所以对“文革”产生了兴趣,追根求源,也许是因为我对我们的当下生活更感兴趣,对我们当下的很多人性问题和社会问题更感兴趣。比如,现在的雾霾天,老人摔倒了没人扶等等社会问题,我会思考为什么人变成这样的,当下的国民精神状态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于是就去探究,由此上溯,找到了“文革”这一支比较近的历史源头。曾有朋友问过我:你写“文革”到底是动了哪根筋?我说不是我动了哪根筋,而是那根筋原本就一直在动,在我的身体和心里动着,而且已经动了很久,只是近几年我才发现了它的动,等到它动得我再也不能忍受的时候,我就开始动手写了。
董晓明:我很感兴趣的是《认罪书》的框架结构。小说开头以金金的死亡和她转交书稿把故事带出来,接收书稿的“我”作为编辑看似和故事没什么关系,但却成了另一个视角的叙述者,而穿插在书中的“编者注”和“碎片”,让人读起来颇有“非虚构”的感觉。能谈谈您为何选取这种独特的切入视角吗?
乔 叶: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是因为第一人称读者读起来会有真切感,容易进入。我作为写作者来说也容易进入。我个人在写作时非常不喜欢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我觉得作为人都是有局限性的,我作为写作者也是有局限性的,所以我喜欢有局限性的叙述,写起来会比较踏实。因此,文中的金金的叙述也是有局限性的,为了在这种有局限性的叙述中找到一个相对稳定、客观冷静的叙述角度,我就采用了编辑发稿的形式。因此,小说开头是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参与,而且书的封面就是审稿签,文本从封面就开始了。文中的编者按和编者注都是和发稿签是一套程序的。因为《认罪书》里很多人的叙述都是第一人称的叙述,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会让读者在读的时候有强烈的同质性,为了把这种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东西中和一下,我就采用了冷静客观的编者注形式。这样,不论是对我的叙述节奏还是读者的阅读节奏都会好一些。我设计金金这个角色是想要她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罪的发现者、认证者、认领者来对整个故事的主线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小说中的金金是80后,我自己是70后,在写作之初我想过把金金定位为70后,但最终还是将其设定为80后。我觉得这个设定更有意义。80后对文革、对历史,对历史深藏的国民性的东西可能认识更浅,更不够,那么,从80后的角度去写,因为他们对历史的认识几乎空白,反差就会更大。所以我特别希望80后、90后读者或者更年轻的读者在我的小说中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会有所思考,这样我会很欣慰的。因此当张莉老师说:“事实上我认为这个小说有一个潜在的读者群,它其实是给更年轻的一代看,这个作品非常成功完成了一点,是青年一代认同和情感交流的一部小说,因为反向的挖掘适合青年一代读者去重新观察、感应和面对我们历史中不愿意去正视的东西。她做到了,我认为乔叶作为青年作家承担了这一代人的历史抒写,而且找到了她的一个路径,我一直认为作家是独特民族精神的记忆者,70后作家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找到他的历史担承,这个小说做到了。”我觉得她特别懂我。
董晓明:在《认罪书》的封面上有这样一行字:“要认罪,先知罪。也许,只有先去真正的理解,才有可能抵达真正的谴责。”我认为比起“文革”那段荒唐的岁月,《认罪书》里展示更多的是来自人性中原始的“恶”。 这种“恶”它不是罪,但却是罪的根源,追问历史,更拷问人性。这是您写作本书的终极意义吗?您定义的罪感又是什么呢?
乔 叶:论到初衷,《认罪书》的本质和道歉有关,和忏悔有关,和反思有关,也因为道歉、忏悔和反思的人是如此之少,所以更和追究有关,和认罪有关。所以《认罪书》题记中我写下了“要认知,认证,认定,认领,认罚这些罪”,这“罪”到底是什么罪?当然这样的问题可以有更周详的回答,但我还是愿意去做一个哪怕不周详但却有重点的一个回答:我最想让小说里的人和小说外的人认的“罪”,也许就是他们面对自己身上的罪时所表现出来的否认、忘掉和推脱。至于导致所有人悲剧的“罪”,肯定不止一种。时代的,政治的,民族的,文化的……都有其根源。而我在《认罪书》里想探讨的,只是平常人的罪。正因为平常人这些罪都很难说是上条上款的实际罪状,所以这也正是我想探究和表达的。写这个小说前,我在网上看过一个人物纪录片,叫《我是杀人犯》,主角是在16岁那年杀人的,那一年是1967年。我写的时候想起了这个人,我想:是从那些人直接杀人的角度写呢?还是从谁都没有亲自动手杀人所以谁都可以觉得自己无辜这个角度写呢?最终,我决定,就从后一种角度写。我坚信,“文革”中尽管很多人都杀了人,但是和自认为没有杀人实际上也在杀人的人相比,杀人的人还是少的。自认为没有罪的人一定是绝大多数。这绝大多数是最容易被人原谅和自我原谅的绝大多数,当然也是最爱遗忘的对“文革”最保持沉默的绝大多数。从这个角度写,更微妙,更繁复,也更有我自己认为的意义。这种对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去回避、推脱、否定和遗忘的习惯作为我们国民性的一种病毒,一直运行在无数人的血液里,从过去流到今天,还会流向明天。如果不去反思和警惕它的存在,那么,真的,我们一步就可以回到从前。也因此,每当看到“80后”“90后”对《认罪书》进行阅读和评判的时候,我会尤其感觉欣慰和惊喜。
董晓明:您并非文革的亲历者,这种身份会给您创作《认罪书》带来限制吗?您认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历史观呢?
乔 叶:任何身份都会带来限制,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没有完美的身份。而写作的张力也恰恰来自于限制。至于历史观,我不觉得一个作家应该有一个历史观,那是政治学家或者历史学家的事。作家关心和体现的应该是人,历史中的人,和历史中的人性。
董晓明:《拆楼记》在您的创作里,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是非虚构,发表后有许多争议,我觉得它很真实,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事件立了传。请问,您这部作品的写作动机是什么?您觉得达到您的创作初衷了吗?
乔 叶:写作动机是因为看见。其实一直都在看见,但这之前没想到要去写,觉得自己写不了。有次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还说自己没能力写这个。朋友当即就说:“很多时候,勇气就是能力。”我顿悟,明白自己是本能地知道这种事件写起来有多么难,潜意识深处原来就在知难而退。直到2010年受到《人民文学》“非虚构写作”风潮的引领,恰巧又近距离地遭遇了姐姐村庄的拆迁事件,于是我近乎强迫地让自己把目光集中在这个事件之上,在克服了心理障碍和写作障碍之后,就有了它。有媒体说我是为了表达农民个体和国家体制的利益博弈,当然也含有这方面的意思。但我的初衷就是想写一个个个体。拆迁的人,抗拆的人,违建的人,包括代表国家意志的官员,其实每个人都是个体,他们都是蛮可怜的个体,他们都有自己的声音,其实都很不容易,都在煎熬,都是一群受苦的人,大家都像在泥塘里打滚一样。在这个事件里,我要很诚实地表达我的所见所思。这是我坚定的想法。我要把听到的各种声音处理好,表达好,这就是我做的努力。可能做得并不很好,但我尽力了。
董晓明:张莉老师在评价《拆楼记》时也提出了您创作中的这种“冒犯”精神:“这个在《读者》杂志拥有诸多大众读者的作家有可能因《拆楼记》而冒犯她的许多‘粉丝,但她的写作也会因这种冒犯而发生重要的、具有转折意义的蜕变。”无论是您创作中“去道德”化的对人伦禁区的僭越,还是尖锐深刻地对社会人性阴暗的指认,都让我在阅读中陷入深思。您认为“冒犯”精神给您的文学创作带来了什么?在“去道德化”的写作中,您认为什么是属于小说的伦理和道德呢?
乔 叶:在创作中,我一直是尽力“去道德”的。对大家墨守成规、约定俗成的这些道德,我尽力去无视它们。就像赫尔曼·布洛赫说的,小说家只需要遵循小说的道德。我觉得这是一条金律。在创作中,我要的不是常规道德的正直、高尚,我要的是文学意义的丰富。我觉得这就是文学或者说是小说的伦理和道德。比如说安娜卡列尼娜,她是红杏出墙,那是不是要从社会道德来评价她呢?按照一些人的习惯来追问:托尔斯泰写这个东西是什么立场?他到底要歌颂什么赞美什么?这么去看就没法说了。但是你看他把安娜写的,让大家那么喜爱,对她充满了同情,知道她的痛苦,尽管她的老公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也没多大的问题。可以说看着安娜的故事,一个正常情商和智商的人都能理解她、她的痛苦和她的选择。让人理解她、悲悯她,我觉得这就是小说家做到的道德。我认为小说家的社会责任就是把人物以最真诚的理解表现出来。通常意义上的道德并不是小说家的道德。小说甚至要拓宽通常所说的这些“道德”。所以我们才会说,小说的本质就是冒犯,真正优秀的小说就是冒犯,他在拓展那些很庸常的对社会伦理的认识。就小说家本身的主观行为来说,他就是在冒犯,因为原有的边界已经划得很清楚了,而小说家却要突破它。你看,包括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那也是冒犯。这种冒犯也正是小说家的道德。其实我们五四时期的文学,哪个不是冒犯?全都是冒犯。像《莎菲女士的日记》,莎菲绝对是史无前例的冒犯型的问题少女。平常我们说“文学艺术”时把“文学”放到前面,说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体,我觉得就是因为它走在前沿,走在前沿就必然含有冒犯。不过冒犯是需要思想深度的,对作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就是说,你不是想冒犯就能冒犯的,没有能力的话,根本不可能去挑战道德的边界,或者是拓宽这个边界。
三、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文学的财富
董晓明:原本您是写散文的,是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的散文家,是什么样的契机使您开始写小说的?
乔 叶:对于我的转型,很多人都表示过不解。李洱曾在文章里调侃我说:我的散文能使人想到早年的冰心,能让人感到自己的世故,就像吃了鲜鱼能让人感到自己嘴巴的不洁。他对我转型写小说很惊讶。我想,不仅是他,很多人都有理由惊讶。但我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多么必然。如果说我的散文创作是鲜鱼的话,那么作为厨师,我怎么会不知道厨房里还有什么呢:破碎的鱼鳞,鲜红的内脏,暧昧黏缠的腥气,以及尖锐狼藉的骨和刺……这些都是意味丰富的小说原料,早就在我的内心潜藏。2001年,我调到河南文学院当专业作家,我们的业务研讨会是以小说为主的,我从中听到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专业作家不用坐班,时间也很宽裕,让我有充分的时间去领会小说。各种条件都比较成熟,小说的种子也经过了漫长的埋伏,已然到了最合适的时候,于是就破土而出了。
董晓明:您怎样评价自己以前的散文写作?
乔 叶:以小说创作为分水岭,我写小说前的散文和写小说后的散文已经有所不同。之前的散文是属于外焦里嫩的青春矫情,之后的散文则可归为滋味渐浓的成人心意。为什么说之前的散文矫情呢?比如说我那时候经常在小散文里讲故事。那时候听别人的故事的时候,觉得已经很生动、深刻了,但这个生动、深刻其实也是想象中的,这个道理是我多年后才领悟到的。当时觉得很生动很深刻呀,然后总结一个哲理出来,而实际上这种总结只是对别人人生的一个简单的想象和总结。所以,我那时候最多可能也只能是审美主义者。
董晓明:我喜欢您小说的语言,自由,没有程式化的约束。比如《指甲花开》《最慢的是活着》是清新流畅的散文式语言,《拆楼记》是非虚构的纪实语言,《旦角》中对戏台上下演员观众的细致刻画,又展现了您深厚的白描功力。郜元宝老师对您的小说语言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在你的语言面前,我感到充沛、胜任、丰满、流畅、机智乃至急智。许多地方触类旁通,联翩而下,以致用墨如泼,酣畅淋漓。”我感觉您的小说语言并非严格意义上标准的小说语言,以去程式化的生活语言为主调,时而亲切美好,时而犀利尖锐,这是属于您独有的一种叙述自由。您这种自由的叙述语言,是受到散文的影响吗?
乔 叶:毕竟写了那么多的散文,应该有散文创作的影响。我没有对自己的小说语言进行过总结,不过我希望它表现出来的面貌是干净的,简洁的,有节奏感的,有弹性和有力度的,也是有想象力的。我当然远远没有达到这个要求,这只能说是一个目标,甚至是需要毕生努力也不一定能抵达的目标。我很喜欢毕飞宇的语言,也一直很喜欢他的作品,他的作品语言就是干净的,简洁的,有节奏感的,有弹性和有力度的,也是有想象力的,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董晓明:70后作家,是评论界为您贴上的一个标签。现在70后创作渐成气候,已然是当下文坛创作的中坚力量,而您也用充满说服力的作品成为了70后写作大军中的佼佼者, 但许多人都说70后一代是腹背受敌的一代人,您认为70后作家该如何在这个时代确认自己。
乔 叶:所谓70后,不过是大众媒体对这些人比较省事的称呼而已,我觉得不是什么很有质量的标签。写作说到底是个人的事,也都是拿作品说话的事,读者不会因为你是70后就会格外厚待你,也不会因为你是90后就特别纵容你。而且,从大时间的概念来看,70、80、90难道不是同一代人吗?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我觉得最根本的敌人永远是在自己内部,有个词叫祸起萧墙,我认为最根本的挑战就是“战起萧墙”,是自己对自己的挑战。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清楚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最想要的是什么?清楚了这个,所有的冲击都不足为惧。如我,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写出忠实于内心忠实于文学道德的并在艺术上有不断可能性的小说,这就够了。
董晓明:创作中您是否遇到过想写却写不出来的情况?如果有的话,您是怎么解决的?
乔 叶: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最初写作时会很焦虑,后来就好多了。毕飞宇老师说过一个观点,大意是,当写作遇到困难时,你要知道,障碍就是宝藏。等你克服了这个障碍,往往宝藏也就出现了。所以,我在遇到障碍时,经常会贪婪地想着宝藏,然后慢慢地把它克服掉。
董晓明:您通常是在什么时候写作?您是如何处理创作和生活的关系?
乔 叶:我白天写作。三十五岁之后,我就不再熬夜过十二点了。生活和创作的关系,在我来说是非常友爱非常亲密的关系,一点儿都不矛盾。我创作中最重要的营养源,一是读书,二是生活。有老师告诉我: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文学的财富。这是真理。
董晓明:看您的介绍,现在您是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官方职务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乔 叶:作协副主席就是一个荣誉性的虚职而已,对我的创作没什么影响。当然如果把它当成个事,那就会造成影响。但在我这里,它确实不是个什么事。最重要的意义也许是让我在写作者简介的时候可以提上一句,让简介变得长一点儿。
董晓明:您现在还担任《散文选刊》副主编吗?编刊事务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乔 叶:我自2010年4月起担任《散文选刊》副主编,迄今已经五年了,最近工作做了调整,离开了《散文选刊》。在《散文选刊》这五年,我收获非常多。之前是一个单纯的写作者,在杂志社的经历让我彻底了解了编辑工作的辛苦付出,对编辑工作充满了理解和尊重。另外,作为一个年轻的专业作家,《散文选刊》的平台也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让我有了一个正常的渠道和社会接触,对很多事情的认识不那么狭窄和单薄,这对我的创作应该有很重要的间接影响。
董晓明:能回忆下鲁迅文学院的生活吗?
乔 叶:我上的是第三届高研班,那是2004年吧。还真的没有专门回忆过,现在想起来的只是一些片段。那时还没写过什么中短篇小说,进小说组是因为准备写小说,但学习态度一点儿也不谦虚,还无知无畏地觉得小说没什么大不了,现在想想就脸红得发紫。我和胡学文同属一个小说组,第一次小组课,某老师让大家发言,大家都矜持着,我说我先来。某老师揶揄着赞许:“看看人家女生。”等我慷慨激昂地说完,大家静默,然后一起看着老师,我也巴巴地看着他,等着他评价。老师却不看我,只是看着胡学文说:“学文,你说。”很久之后,我才回悟出大家对我的忍耐:这大妞该是有多么不靠谱!我和《江南》杂志的主编钟求是也是相识于那时,在一起同学了四个半月。理论上是四个半月,除去节假日、课休和私人时间,我估计同学们实际上在一起也就两个月左右的净时,尤其是男女生不在一个楼层,相处也就更少。不过我窃以为钟求是应是和我相处时间最长的几个男生之一,这么说的根据只有一个:我和他都常常呆在电脑房里。那时很多同学都有笔记本电脑,去电脑房的没有多少,寂静得很。我和钟求是常常一前一后坐着,啪啪啪地打着键盘,偶尔休息的时候,就说一会儿话。多半是我找他说话,他一直都很安静,话不多,和女同学的话就更少,我若不主动,他恐怕连一句话都没有。我那时候刚开始学写中短篇小说,特别喜欢兴致勃勃地和人讨论分析小说问题,逮住一个人就问啊说啊,很多同学都受过我的折磨,钟求是就是其中之一。我得承认,在鲁院那四个半月让我刚刚有点儿知道了什么是小说。
董晓明:除了创作,您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乔 叶:美食和旅行。
董晓明:如果时光倒流,您还会选择写作这条路吗?
乔 叶:假设没有意义,时光不会倒流,所以我只能选择写作。有意思的是,在写作的时候,时光往往反而可以真正倒流,想怎么倒流就怎么倒流,这也是写作最重要的魅力之一。
董晓明:我们常说男女平等,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有些不平等之处,譬如大部分的女性对家庭琐事付出的时间要比男性多。就创作而言,您觉得女性具有先天优势吗?
乔 叶:世间万事都不可能有绝对的平等,我一想到祖母那一代女人,就觉得现在我们这一代女人的生活就表象而言和她已经有天壤之别了。能读书,能写作,有话语权……我常常觉得很满足。至于家庭琐事,没必要那么计较吧。男人有男人的辛苦,男人女人都不容易。在创作上,女性的优势也许就是更感性更细腻,但男人往往更厚重更辽阔,各有优势吧。一定要这么比一下么?无论男人女人,能写出好作品的就是好作家。
董晓明:您目前正在写作的是什么?您对自己的创作有长期规划吗?
乔 叶:正在写的,无非是小说而已,偶尔也有散文。没有什么长期规划,就是尽己所能写出好的作品。作品是作家生命的另一种形式,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我离开了世界,我的作品还能替我活着。如果说长期规划的话,这算是我的长期规划了吧。
(黄文婧女士对本访谈亦有贡献)
董晓明:天津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