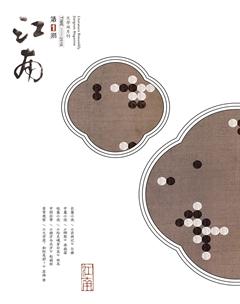给灵魂穿白衣
田耳
一路颠簸,小丁不免对小赵心怀歉疚。小赵一直将摄像机抱紧,担心机子被山路抖坏。山路颠簸,小丁常走,开车依然小心。车程一个半小时的鹭庄,显得格外遥远。手机断了信号。前方那一带山壁呈现大片青灰色调,将整个视野修饰成傍晚来临的样子。
昨晚接小叔的电话。“小丁啊,你爹在吗?”
“不在,开会去了。”
“你爷爷又差不多了,就这一两天。你们都过来一趟。”小叔又补充说,“这回真差不多了。”
去年五月直到现在,报病危的电话,小叔打来四五次,都说老人家看样子快不行了,叫他们回鹭庄接气。小丁父亲丁正钊头两次去,结果小丁爷爷挣扎一番又活过来。那以后再有报病危电话,丁正钊就不肯轻易耽误时间,支使小丁先回鹭庄探看情况。丁正钊交代,真差不多了,赶紧打我电话!
父亲眼里有内疚,同时又摆出毋庸置疑的神色。父亲每天要赶赴多场会议,办许多事,见许多人。某些场合,他喜欢在洒金宣上写下相同的两句诗: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
这次小叔又将电话打来。小丁已经没法和父亲联系,但父亲提前交代过,若去鹭庄,带上电视台小赵同去。
鹭庄是个长满古树的村庄。鹭鸶是一种呆鸟,十年以前,它们一堆一堆盘踞在枝头。如果树上有七只鹭鸶,一枪打去,如果这枪打虚,树上还有七只;如果打死一只,树上还剩六只。现在鹭鸶已经没了,古树也所剩不多,鹭庄还叫鹭庄。
进门就看见爷爷,躺在老床上,呈弥留状。小丁走近叫唤几声,老人的眼睛就亮了,眼仁子从堆堆叠叠的眼皱以及白翳底下翻出来。
爷爷问:“是丁小唐?你爸怎么没来?”
小丁说:“他忙。”
“他总是很忙。”稍后,爷爷又说,“总是让你空跑。”
“累了就睡!”小丁不难看出来,爷爷为自己几番眼看就要死了、最后又活过来而内疚不已。
“小丁你来了,我看见你,又做完一件事。你爸不来,丁正钊他不来,我也不怪他。我不能因为他老不来,就老是赖着不走。村里人已经在看我笑话。他们背后笑话我怕死,我的脖颈就会一阵阵发冷,像是有小鬼在吹阴风……”
耳畔,又是一阵大声的咳嗽。
小丁岔了神,忽又记起奶奶临走的样子。奶奶转眼走了十来年。这里有个习惯,人死之前要为他(她)接气——所有的亲人都围在临死的人身边,讲许多告别的话,再讲许多鼓励的话。
奶奶走的那天,小丁听见亲人们口舌混杂地跟奶奶说话。
爷爷说:你先去,过几年我就来陪你。
林贵叔公说:今天选对日子了,今天日朗风清,适合出远门的。
孤老福久摆出羡慕模样说:你是有福气的人,你的崽女都来齐了,都百般孝顺,都来为你接气哩。我走的时候哪有人送我?知足吧!
接气那天,通常要有一名老道士。道士也凑过来搭腔:走就走吧,就那回事,要不然你崽女又会哭,让你挂牵。走咯,走咯…………他的口气和每个人都不同。别人在送别,道士像要带着奶奶往前走,催促她别耽搁。
道士站在奶奶和那些亲戚背后,细致观察着奶奶的脸色。看看时间差不多了,道士就开口说话。他只说一句话,可以了。亲戚们的啜泣和轻声呼喊,像从一个个水嘴里流出来的一样。道士再一发话,马上又能停住,人闪到一旁,看道士手中多了一个方木枕。奶奶头朝向的那一边被抬高,方木枕枕在床脚下面,床的一侧垫高有二十厘米。小丁很怀疑那块木枕头的效用。他想,那一块木头就能把人平静地打发走?
那一年父亲同样没赶到鹭庄为奶奶接气送行。他嘱咐小丁多拍几张照片。 “我对不起你奶奶,你多照几张照片拿给我看。”电话那头,父亲忽然哽噎。当时倒也情有可原,奶奶死得痛快,头一次报病危就走了,而父亲正带团在新马泰考察,想赶也赶不及。
那一年,老家的房子还没有翻修,屋子被经年柴烟熏得漆黑一片。屋内暗淡的光,加重了奶奶对死亡的恐惧,她用力吸着浑浊的空气,喉咙里堵满黏液。她上半截身体随着喘气的频率抽搐着,下半截又纹丝不动。从那天清早到中午时分,奶奶一直保持这状态,眼里不停流泪,需要人不时地擦一擦。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道士眼睛盯着奶奶,手在挪动木枕位置,像是调频找电台一样。奶奶的脸纹忽然舒展了些,道士赶快停手,让木枕定在那里。小丁看出来,那是木枕起了作用,惊讶不已。所谓安乐死,在乡间只需一块木枕就能完成?他怀疑道士确有几手法术。他这才仔细看看那个乡村道士,道士当天穿一件脏兮兮的中山装,正吸着自卷的大炮筒。他告诉别人,道袍洗了,还没晾干。
小丁坐柴堆上,斜眼看着道士。他知道,道士手一挥,就将宣告奶奶的离去。他有一种怕感,不想看见道士那只手,但余光又牢牢粘在上面。
过一刻钟,奶奶就彻底死了。
所有亲戚涌进房里。小丁记忆异常清晰:那一刹,奶奶的嘴唇突地变色,从赭红变成了灰白。当然,他没搞明白那是光线的作用,还是自己内心某种情绪的映射。
道士扔下烟头过去查看,然后手有力地一挥,跟所有人说:“行了,哭吧。”大家放声哭泣的时候,外面有人放响了爆竹。小丁走上前去,揣着几分担心看向奶奶的遗容。他担心奶奶会被爆竹的声音再度弄醒。但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小丁给奶奶的遗容照相,闪光灯把暗屋子强烈地晃了一下,把大伙的哭声中断了数秒。间歇过后,哭声愈发恣肆。
当天,小丁也哭,别人很快停下,他也跟着停下,哭声成了一种合奏,小丁将哭声融进合奏,当别人停歇,他也不由自主地闭了嘴。小丁一扭头,见爷爷站在床头,口中念念有词,正对奶奶的遗体说些什么——也许,是唱些什么。作为一个山歌手,老人拙于言说,喜欢把心事唱成山歌,歌词可以即兴编排。随着嘴唇的蠕动,爷爷脸上很快变得平静,没有哀怨,没有悲伤,有的仅仅是一些怅惘。
小丁此前没有为将亡者接气的经验。那年他二十岁,二十年里直系亲戚里头没有死去一个,外公外婆都还咬得动牛板筋,离死去还很遥远。他以为任何一个亲人的离去,都会带来摧肝裂胆般的痛苦,都会让自己长哭不起。奶奶是头一个死去的至亲。当天的情况,让小丁感受到一种意外——一切都不同于他先前的想象,哭几声就停止了,像交了差事。有些人在哭,更多的亲人已经在把堂屋打理成灵堂,贴上“当大事”的字幅。一切有条不紊,仿佛奶奶的死只是整个活动中的一环。
小丁过去捏了一下奶奶的手,还有些虚热。
半夜的时候小丁忽然哭了。当时他躺在一张椅子上准备守夜,但不小心睡着了。他梦见奶奶躺在床上又一次重复着死亡的过程。当奶奶在梦中第二次死去时,他哭了,也就醒了。
爷爷说,他并不是怕死,只是舍不下每一个亲人。又说:“小丁,你都还没结婚呢,真让人着急。我爷爷死那年我都有三个崽了。”小丁知道,爷爷羞于承认怕死,而对死的恐惧又这样直白地写在脸上。年轻人可以怕死,可以流露出来,但上了年纪,似乎应该摆出一种顺其自然安于天命的态度。
小叔虚报几次病危,也有怨言。进城跟小丁父亲喝酒时说:“爹胆子就是小,怕死得很,几次差不多了,到最后又不肯死,不像娘那样胆气足。”
丁正钊皱皱眉头说:“话不能这么讲。”
“本来就这样。一个乡里人,又没有医保,赖在床上不死,自己也受罪不是?”
丁正钊也不好多加指责,毕竟,守在父亲身边的是这小弟。在鹭庄,一个老人到了年纪老是不肯死,乡亲们就拿这当笑话讲。丁正钊又说:“毕竟娘管了爹一辈子,家里女人顶梁,轮不着爹胆子大。在我们看来他是爹,在娘看来他就是大儿子。”
两兄弟都说得笑起来,接着喝。
以前奶奶也老跟人说,爷爷从来都是胆小鬼。奶奶比爷爷还大几岁,两人成亲那年,爷爷才十七,是家里满崽。新房离茅厕很远。夜晚,豺狗子的嚎叫随风一阵一阵钻进耳朵眼,爷爷尿憋了想去茅厕,却不敢,脸憋通红。奶奶看出来了,带他走过那段黑路。当时,奶奶还跟爷爷说:“呃,夜路你都不敢走,以后有什么用咯。”
爷爷丁先存嗓门奇高,是块唱山歌的好料,二十啷当岁,就唱得远近出名。到他晚年,常有地方上的演出邀他露脸,也有文联干事搜集他编的山歌。一本《土家歌王丁先存山歌集》作为县里文史资料的一辑早已编好,但因资金紧张一直压着。领导们的回忆录总是插队,赶前面印。
看看泛黄的照片,小丁不难想象,爷爷年轻时是个风流俊俏的家伙。他编的歌词记载了当时的生活场景,就像有文化的人记日记。其中一首歌这样唱:“砍柴要砍竹子柴,砍了竹竿笋又来。相亲要相两姐妹,姐姐不肯有妹妹。砍柴莫砍倒钩藤,相亲莫相寨子人。下午才得吵一架,晚上舅佬打上门。”奶奶和爷爷是同村人,据说奶奶还有一对五大三粗的双胞胎弟弟,解放前失踪一个,紧跟着又死一个。小丁听着爷爷唱起这样的歌,就想笑。他想象遥远的某天,爷爷对别家妹子唱了几句稍带撩拨意味的山歌,妹子忍俊不禁笑起来。当天下午奶奶拿爷爷的错,爷爷竟然顶嘴,结果,晚上奶奶那两个弟弟就找上门来。
爷爷唱的山歌总这样信手拈来。
在山歌里,爷爷仿佛对死有种超脱的态度。比如说另一首,他拿死亡任意编排:“看见什么唱什么,看见灵魂换穿着。看见尸首洗尸脚,尸脚试鞋大小合。看见鬼爹笑呵呵,看见鬼妹害娇羞。从此鬼府添一口,耕种鬼田多双手。”他毕竟一辈子土里刨食,在他想来,死也就是去另一个地方娶妻生子,照样耕田种稻。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怀惴的是一种对新生活的喜悦。但是,真要去另一处地方,又不是他歌里唱的那样超脱。亲人给他接几回气了,甚至有次,道士已给床脚垫上木枕,老人还是把牙一咬,活了过来。
那次道士觉着丢了大脸,因为他蛮有把握地说出“差不多了”。每个行当都自有一套行规和操守,下次再请那道士,他不来。爷爷活过来后,不敢看别人失望的表情,像是平白无故地耍了别人一道。这次只好请另一个,还是原先那个道士带出的徒弟。
晚饭时,爷爷竟能垫着枕头在床头稍稍坐直。小叔给他煮了一碗糯米粥,爷爷说,加点辣椒。小叔就往粥里加了辣椒末。他把粥喝得一点不剩。吃那么多东西,不但饱了肚肠,对老人内心也是安慰。爷爷脸纹敛开了,喘着粗重的气,告诉小丁:“晓得吗,我二十来岁的时候,已经死过一次。”小丁赶快点点头。他希望爷爷最好是节省点力气,少说话。多说两句,他又会急喘。
那故事小丁听了不下十遍。爷爷能唱上千首山歌,但能讲出来的故事,翻来覆去只那几个。爷爷口拙,从不讲别人的故事,只讲自己。
“其实走夜路,我一惯都很小心,出门前要念一通‘三收诀。没想到,三收诀能收老虎、蛇和鬼,却不能收狐狸。结果那一晚赶巧就碰上了狐狸哭坟。你晓得么,有时候狐狸往凶死的人的坟前走过,灵魂会把狐狸抓住,让狐狸哭坟。人死了,自己儿女经常是在假哭,心里面喜悦,这样哪能哭出悲调调?只有狐狸哭坟,哭得伤透了心,哭得真是好。”爷爷的故事总是这样开头,然后满怀悔意地说,我年轻时候干过不少蠢事,尤其不该打那只哭坟的狐狸呵。
他说自己二十二岁那年,秋天的某个夜晚他从奶奶娘家帮工回自己家,路过丝瓜冲下面一片坟地。正走,听见哭声从坟地传来。有两股哭声纠合在一起,此起彼伏,非常凄凉,让人毛骨悚然。他想,谁在这时候哭坟呢?天上正好有月亮,借着月光,他壮起胆子绕到一块碑石后,循哭声看去。月光下,两只狐狸蹲在另一块碑前哭泣。狐狸半蹲,前爪作揖,长长的尾巴轻轻抖动,光亮的皮毛反射着暗淡月光,显现出缎子般的质地。他听道士说过,见狐狸哭坟,必须把它们打死,要不然,家中必遭灾难。他逼不得已摸起一块石头,冲上前朝其中一只狐狸砸去。另一只被吓醒了,一头扎进坟茔深处。
那只狐狸还在地上,盘虬着身子,拼命挣扎。他狠了狠心又砸下一石头。
“吃了狐狸肉,就病了,怪病,躺在床上不能动。我这人被病劈成了两半,右半边已经死了,左半边还有气。我和别人讲话,动的都是左边半个嘴巴。去问道士,道士说,要把那两只狐狸都打死,病才消解。丁家的堂兄弟邀来一帮猎户,牵着十几条赶山狗,把鹭庄周围所有的山都清了一遍,打下一大堆狐狸。另一只哭坟的狐狸也没躲过,不晓得是哪只,反正,它肯定被打死了,这样,我又活了过来。”
爷爷还说:“造孽呵,那以后我们鹭庄很少看见狐狸了。后来想想,狐狸能给人哭坟,有情有义的活物,不是孽障,我凭什么砸死它?”
说这一阵话,爷爷累了,很快睡去。他睡去的样子很安详,安详得不可能是去了梦境。看着爷爷酣睡,小丁心中一凛。他再次提醒自己,爷爷就要走了!他想起过往的事情,和爷爷在一起的情景,时间没了先后,一齐浮现脑海,又瞬间消失,眼角忽已濡湿,就像蠕虫爬过。
小丁偏过头去,见衣柜的穿衣大镜被线毯罩住了。他拢过去想扯开线毯,才看见线毯被小号铁钉密集地钉了一圈,钉死在衣柜的木门上。
“是你爷爷要我钉上的。”小叔告诉小丁,“去年就钉上了。你爷爷总是跟我说,天要黑的时候,他就不敢看镜子。他讲,老是觉得有个人从镜子里面很远的地方朝他走来。我问,看见那个人是谁。你爷爷说看不清楚,反正不像是他自己。”小叔说到这里就笑了,说老小老小,人老了也就像小孩一样,会怕一些讲不出所以然的东西。
若要爷爷不照镜子,就和奶奶戒除酒瘾一样,着实不易。既是小有名气的山歌手,爷爷比一般庄稼人注重仪表。他爱穿白衣,喜欢人家称他为“白衣丁先存”;还喜欢照镜子,甚至不避讳在别人面前照来照去,和镜中成像挤眉弄眼。
奶奶娘家是酿米酒做醪糟的营生,所以奶奶酒瘾很大。奶奶在世的时候,爱取笑爷爷照镜子的毛病。那时爷爷也已七十多岁,每天起早,仍对着镜子摆弄穿着。整个鹭庄,男人们都不屑于用镜子来映照自己的灰头土脸,爷爷是唯一的例外。村里人拿爷爷照镜子的事当笑料,从解放前直到前不久,这笑料抖了几十年。现在讲出来,还是会有人发笑。一个爱照镜子的老头,天天老来扮俏!一说照镜子,又会理出爷爷的身世,他本是流浪儿,被小丁的太爷抱回家里,取名“先存”,意思是先存在这里,亲生父母找来了,就还给他们。但没人认领,就一直先存着,一天天长成人,为人夫,为人父,后来成了小丁的爷爷。
村里老辈人一直认为,丁先存定是周遭哪家富户走丢的小少爷。
爷爷一直嫉羡奶奶的酒量。他也时常想喝一点,干了活以后,逢年过节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还有心情一团糟的时候,他都想陪老妻喝几蛊。他身体对酒精的过敏反应过大,稍微来些酒,脑袋就天旋地转,过后皮肤还会出现油芝麻大小的红疹。爷爷没法去碰酒这东西。
现在,爷爷也不敢照镜子了。小丁很想知道爷爷去年在镜子深处,看到了谁。他有些怀疑,爷爷是看见了奶奶,而且奶奶仍想和爷爷唠叨一番。但爷爷如果看见奶奶,又有什么好怕的?
爷爷再次醒来,气息浊重地喘了一通。他深陷的眼窝里储满了液体,小丁拿干毛巾搌去眼窝里的积液。
“我梦见她了,她喊了我几声,把我喊醒。”爷爷虚弱地说,“可能,也就这几天……你奶奶已经给我报得冥信了。”
小婶娘说:“爷(音Ya,阳平)哎,不要乱想。你脑子还蛮清楚哩。”
“不清楚,老糊涂了。”说着,他眼窝子重又湿润起来。小丁递去了湿帕子。爷爷抹抹眼窝,又抹了抹整张脸。他换了一种斜躺的姿势,眼睛睁开,看向屋顶。现在住的屋,是丁正钊从城里请来建筑队修建的。村里同姓的人对这事有意见,说乡里乡亲的,其他的事帮不上,建幢房屋还要去请城里人,这是打血亲族友的脸。房屋建好,他们便不作声了。那是一幢欧式风格的房子,有穹顶,又结合了中式的琉璃瓦。爷爷说,要贴大块的洋瓷砖。于是墙体贴了大块瓷砖。爷爷说,瓦檐下面最好是画些画,这样显得热闹。于是丁正钊请了庙里的画匠,在爷爷指定位置画了福禄寿喜梅兰竹菊,还有戏文画。
房子落成,爷爷便对邻居说:“我以前根本不敢想,自己能死在这么好的房子里。”别人也承认,鹭庄的泥瓦匠可造不出这样的房子。他们都恭维地说,你是有福气的了。
爷爷看着屋顶,屋顶是简易的石膏吊顶。屋里是雪白的颜色,爷爷说:“这让我安神一些。”搬进新屋,他不再烧柴,怕柴烟熏黑了墙壁和屋顶,改用煤炉,用白铁的转角烟囱把煤烟送到屋外。
新屋建成,爷爷用不着去别家打牌。入了冬,备好炉火,每天都有人来家里找座。都是老人,搓麻将嫌累,只打纸牌,输赢几角小票,一月下来进出不过一两百。丁正钊晓得这情况,欣慰,电话里指示小叔:“爹打牌的钱都算到我头上……你想想,就算每月都输两百,但总有三四个人成天守着爹,你我出外也放心不是?”此后,小叔每每提起这事,都要撅起手指说:“三哥厉害,坏事经他一说马上变了好事,所以人家活该当官。”
其实爷爷牌把式稳当,年纪是大点,脑子不糊涂,经常能小赢几块。老光棍福久输得多,常为赖几块钱抬屁股走人。爷爷好脾性,无所谓。林贵叔公有次急了,说:“你光人一个,到死的那天帮你接气的人都没有,还把钱看得比命大,有什么意思?”福久屁股离了板凳,边走边说:“没人接气,也就没人逼我上路,清静是福晓得啵?”
福久的老宅地卖掉了,也输光了,在鹭庄没了家,后来住进镇上养老院。见不着福久,爷爷时常想起他。那个老光棍,无牵无挂,扛着脑袋来,抬起屁股走,脸上随时开着笑颜。谁挨近他,谁就得来无尽乐趣。
“……不要给我接气,让我清静死一回!”爷爷冲着婶娘,语气有些铿锵。为讲这句话,他肯定攒了一把力气。小婶娘赶紧往地上吐了口唾沫,并用鞋底一擦,说:“爹你又说胡话,把病养好,你照样唱你的歌。”
小婶娘出去淘米做饭。爷爷长久地盯着吊顶,又瞥小丁一眼,喃喃地说:“你奶奶大我三岁,要是不去,再过几天,就满了七轮。”
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了五十九年。奶奶死的那年,爷爷非常惋惜地说,挨到明年多好啊,走得这么急。他非常想把两人共同生活的年限凑个整,一甲子。小丁估计爷爷和奶奶属于那种互补型的夫妻。奶奶年轻时脾气很不好,这也难怪,婚后二十年里她拉拉杂杂生下十几个孩子,成天老大哭嚎老二闹,老三撒尿老四泡,这状况,没法让奶奶脾气好起来。爷爷恰巧是没脾气的人,除了唱歌,脸上成天弥勒佛似地堆着笑。
爷爷以前常跟人说,这叫一个榫头一个眼,一把钥匙一把锁。我跟我家老婆子,活上千年难撞到,就该是一对人。她要是嫁一个脾气大的男人,两人肯定见天打架。她脾气纵是大,终归是女人,真动起手来哪能不吃亏?说到这里,爷爷脸皮一搐,仿佛老婆子已被想象中的那男人暴打了一顿。
爷爷忽然说,热!又说:贴身的衣服像被汗水濡湿了。小丁扶他坐直,用手探向后背,还好,老人枯树皮般的身体生不出水分。既想换衣,小丁就帮他找衣服。拉开柜门,一堆衣服尽是白色。老人喜欢穿得自己一身白,多少年来没变过。当全国人民一片绿的时候,一片灰的时候,直至全国人民五颜六色的时候,老人都一成不变地穿白衣。他老说,穿上白衣,唱歌才好扯开喉咙。
小丁没看过爷爷穿白衣上台对歌,但每年祭祀或是向傩神还愿,爷爷在神像前做祭礼或者是祷告,口中念念有词,一脸的虔敬。他想,当年爷爷上台对歌应该也这样,两眼微合,很快进入心无旁骛的境地中。
小丁找了一件对襟布钮的,刚要给爷爷换上,小叔拦住。他说:“爹,你哪有汗水?你哪还出得出汗?自己想多了。”
爷爷眼睛盯着那件白衫。小叔示意小丁将衣服塞进衣柜。爷爷也不吭声,现在小叔照顾他起居,小叔说话算数。
稍过一会爷爷睡去,小叔将小丁拉到屋外。“他这几天情况很不好,换衣这些事你不熟,不要乱弄,要等我来。现在就算换身衣服,也可能耗掉他身上最后那一把力气。”小叔这么解释,小丁倒吸一口凉气,暗怪自己年轻不晓得。若真的像小叔所说,换衣服时爷爷突然一口气提不上来,死在自己肩头,如何是好?他还没准备好应对这种事。按说,爷爷应该死在父亲、小叔的肩头。依此类推,等父亲成了爷爷,自己成了父亲……
其实小叔真正的想法,不便讲出口。前几次,他眼见老爹快要蹬腿走人了,忽然挣扎着说要换白衣。小叔慢慢摸索出经验:老爹前几次都是穿着深色衣服时进入弥留状态,一换白衣服,脸上立现生机,浑身又多了几把活下去的力气。
傍晚爷爷醒来,把小丁叫到床前,艰难地说:“明天能不能把你爹叫来?我自己知道,明天后天,我肯定是要走。我好久没见着他了。”
小丁敷衍似地应和着。他知道父亲不可能来,父亲现在正被要求交代问题,没把所有问题交代清楚,就出不来。小丁知道,交代清楚了,一般也出不来。
来鹭庄之前,小丁想去学习班看看父亲,但没得到许可。前不久,丁正钊忽然很怀念自己的老家,掐指一算,竟是有四年没回到家了。丁正钊那天表情依然严肃:“鹭庄坐车也就一个多小时,早该……”他发着感慨,在屋子里踱步。他忽然跟小丁说:“小叔再打电话来,如果我去不了,你就把电视台小赵叫上。”
“怎么了?”
“让他……全都拍下来。”父亲的手一抽,就势比划了一下。
现在面对爷爷,小丁才意识到,当父亲想起爷爷,其实是预感到某些无可逃避的事情即将来临。
来鹭庄之前,小丁打电话给小赵,他当然一口答应。小赵能进到电视台工作,丁正钊替他攒了一把劲的,这是他投桃报李的机会。
乡村的夜晚比城里黑,看样子,爷爷又挨过了这一天。小丁带小赵去溪口镇吃宵夜。镇上只有一两家夜宵摊子,生意清淡,啤酒也是越喝越冷。远远飘来卡拉OK的声音,听得出音响有多么山寨,话筒说不定布满锈迹。喝了酒,小丁想拽小赵去OK一把。这次来,还不知道要耽搁小赵多少时间。
“不去了,早点休息。”小赵把啤酒瓶喝空,咂咂嘴,终于说,“丁哥,我们台里最近忙……我是说,机子我可以留一台给你,但我恐怕不能一天天守在这里。你家老寿星,我看气色不错。要不,我明天教你怎么用,你自己随时可以拍。现在,这些机器都是傻瓜机,比唱卡拉OK还容易。”
小丁只好点点头。
爷爷一夜好睡,次日九点多睁开眼,阳光照进房内,大块大块光斑铺在地上、墙上,也有几块爬上床头。这是令人愉悦的天色,阳光让人产生许多明朗的念头。
小叔又把道士叫来。这天道士一身道袍有模有样,不至于让人把他和和尚混淆。道士进屋转了一圈,看看爷爷的气色,就跟孝子贤孙们说:“他这口气顺过来了,你们不要守,该干活干活。”
众人散去,小叔看小丁守着。就说:“那我去给秧田放水,我都好多天没去田里伺弄了。”小丁点点头。
小赵架起三角架,把摄像机安上去,准备给小丁上一堂速成课。一开机,电源灯就亮了,虽然灯光微弱得有如秋夜萤火,爷爷却像是被闪了一下,慢慢睁开眼看着不远处摆着的机器。
“是摄像机?”他问。
小丁点点头。爷爷认得。他是个农民,也是远近有名的山歌王,曾经接受过采访,采访时,也有摄像机对准他。面对镜头,爷爷得来从未曾有过的体面,他知道,能上电视的都是人物,每天上县台新闻的大都是县领导,省台的新闻,也差不多是省领导的工作日志。儿子丁正钊虽难得见上一面,但老人经常在电视上看见他晃来晃去。
“是拍我?拍我怎么死么?”
小丁摇摇头,坐到床头想跟爷爷解释,一时语塞。小丁心底涌过一阵内疚。当一个人发现自己的死亡正在被别人记录,那会是怎样的心情?
这时候,爷爷却又变得异常清醒。“正钊有什么事来不了,叫你拍下我怎么死的,对么?有什么事?”
“……出国了。”小丁喃喃地说。此时,他觉得什么都瞒不住爷爷,爷爷的眼光洞察世事,没有丝毫浑浊。
“出国了?”爷爷想侧过身子面对摄像机,小丁帮了他一把。他身子忽然抖不停,小丁赶紧将他放平。爷爷眼睛盯着天花板,慢慢想起什么来。他又说:“是的了,老婆子死的时候,正钊也在出国。”
小丁示意小赵将摄像机拿到屋外去,爷爷再次发话:“就放在那里,就这样……我差不多了。”
“爷爷!”
爷爷呼吸变得粗重,稍过不久,突然陷入谵妄状态。小丁感觉到不对劲,凑近他的耳际大声地喊了两声,没见反应。这一刹,小丁分明感到爷爷正在离自己而去。虽然他身体还横在眼前,但他体内的某些东西正往某个不确定的地方飘逸,像是蒸气或者光柱里悬浮着的尘埃。他分明触碰到了这种流逝。小丁再喊一声,喊出来全是颤音。爷爷脸纹也开始抽搐,嘴角流涎,像皮筋一样弹几弹。
小丁赶紧去找小叔,小叔进屋看了一眼,就跑到屋外,手作扩音筒状召唤道士。道士进来时紧了紧眉头,再打量床上老人。他问:“怪事,怎么突然就这个样子了?”小叔解释:“没有原因。”道士有些气馁,刚才遣散众人,他还把话说得相当肯定,简直就是打自己的脸。
“应该……快了,就是今天,就是……马上。”道士说话时犹豫,但仰起头,脸上又是不容置疑的表情。小叔赶紧去叫人,道士看了看小丁和小赵,随后看看那台摄像机,眼角闪过一刹那的疑惑。小丁头皮倏地一麻,突然省悟:前面几回,爷爷也不是怕死,而是不想死得如此无声无息。而现在,在镜头面前,他找到某种庄严之感,有了这种庄严,死起来就变得从容了。
是这样吗?爷爷已无法回话。
小叔很快叫来二伯、五叔、六叔,还打电话给嫁到洞井村的三姑。洞井村在坳上,鹭庄在坳下,两袋烟的路程。
小叔给道士递去一支烟,并问:“那么,可以接气了?”
“说不准。”道士挟烟的手势独特,用的是无名指和拇指。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其实那钟早两年就不能动弹了。
逐渐到来的亲戚们都被安排在堂屋歇息。堂屋的火塘里有块子柴,正慢慢燃起势。二伯趁这工夫讲起了新趸来的笑话。二伯是木匠,游走了不少地方,会讲每个地方的笑话。
小丁和道士、小叔、小赵四人留在房内。小赵已开始拍摄,他往透进光的那窗口上掐了约八秒钟的起幅,然后将镜头缓缓移至老人的脸上。老人那张脸上,两处深深的眼窝在镜头中显得很有层次感,眼眶上的褶皱犹如经过长时间摆放的纸花,质地焦燥、易碎。他的嘴唇还没有瘪下去,牙床上保留有十几粒牙齿,这些牙齿把那嘴唇勉强撑了起来。
道士又看一眼那摄像机,附耳跟小叔嘀咕起来,小叔又耳语着向道士作解释。这时,小赵有意把镜头移偏,朝道士罩去。那道士镜头感很不好,浑不自在。那副拘谨模样,使得小丁怀疑他的功力。镜头很快移回原处。小丁这时觉得,爷爷那张脸像是出土的陶器,尘埃感十足。
窗外的天空有了云翳,光线陡暗。老人这时忽然睁开眼,看着摄像机,表情竟似有些惊惧。小叔也看出情况来,冲小丁说,把机子关一下。他还做了个手势,提醒小赵。小赵把机子移开。稍后,爷爷又恢复了睡态,面部肌群虽然时有抽搐,但比刚才已经平静许多。那眼窝幽邃的样子,让小丁怀疑,刚才他并没有把眼睛睁开过。
道士这时候说:“可以换衣了。”
换衣是个信号,兆示着接气仪式将接踵而来。小婶娘从衣柜底脚处的抽屉里拿出老早就缝好的寿衣。那又叫棺材衣——面料是黢黑色的,里衬是洋红色,用色和棺材漆别无二致。据说,临死前给人换一身寿衣,会起到静心安神的效用,使得人这一路上走得平稳一些。小丁却觉得,那两色反差过大,搭在一起,让人产生难以扼抑的紧张和厌恶。
二伯和小叔翻动着爷爷的肢体,换衣服换得并不利索。爷爷对此有了反应,他蹙了蹙眉头,还好,最终没有睁开眼。道士切了切脉象,然后说:“可以把亲戚叫进来了。”说着,他往床底下一摸。那木枕赫然滚了出来,不知哪时已备在床底下。
堂屋里那些亲戚鱼贯而入。二伯给每一个人安排位置,有些亲戚按辈分必须站在床头这侧,有些只好站在床尾。
小赵继续操起摄像机,抓拍整个场面。爷爷穿着寿衣,脸色也变得黯淡。谁都能看得出来,老人在阳世的时间只能以分秒计算。
这时小丁手机在响,他看了外屏上显示的号码,是他母亲打来的。
小丁出去接了一通电话。他知道父亲坐那个位置,肯定犯下事体。这些年,他能从一些细致入微的地方感受着父亲的变化。没想,事情比预想的严重许多。
“你爷爷怎么样了?”母亲抽泣着说完父亲的事,忽然想到这个。
“还是那样!”
小丁关掉手机,吐了口气回到房内,见爷爷竟然睁开了眼,还盯着自己。这时,老人的眼神,不像一个垂死的人,他还奋力要坐起,终于,问出一句话:“正钊怎么了?”
爷爷不可能听见电话里讲了什么。小丁想,也许,这就叫心灵感应吧。就像童谣里唱的,父亲的父亲叫爷爷。父亲永远都是爷爷的儿子。
众人安抚着老人。爷爷这才发现,身上已换了寿衣,情绪有些激动。那种很虚弱又很激动的样子,让人难以面对。
“……给我换衣服。”爷爷讲得很吃力,但把字音咬得奇怪而清晰。他断断续续地说:“我死后,再换上寿衣。现在我要穿那套白衣。穿这黑衣服,灵魂怕是消散不掉,我也实在落不下这口气。”
小丁叫小赵把机子摆到稍为隐蔽的地方,继续拍摄。
“灵魂”这词,让小丁觉着有些刺耳。这词本身没什么问题,但从爷爷嘴里吐出来,却让人感觉不伦不类。这地方的语言习惯,灵和魂从来都是分开着讲的,要么灵,要么魂,没人会把这两字凑成一个词。偏偏爷爷爱这样用,多年来,他让“灵魂”频率极高地出现在他的那些山歌里,这个词对于他来说,仿佛是盐,可以往哪盘菜里都搁一点。小丁老早注意到爷爷的措词,为此还查了一些书,大概能将两个字稍加区分:灵,是居于躯体内并主宰躯体的精神体;而魂,是精神体脱离躯体以后的独立存在。小丁想,在爷爷的见识里面,灵魂到底是怎样一种东西,又有什么样的面目?
爷爷这时现出愤怒的样子,冲二伯和小叔说:“给我换白衣,我保证今天死,保证马上就死!”
二伯和小叔商量着,找出一件白色衣服给老爹换上。这是他老人家以前上台唱歌时穿的,一换好,他气色果然好些了。他攒了一把气力,往柜头上指了指。那里有一台卡式收录机。
小丁率先弄明白爷爷的意思,他想听听自己曾经唱出的那些山歌。柜子里一盘盘磁带全是爷爷自编的山歌,自然也由他本人唱。此前,有小贩找来废旧磁带,消了磁,录上爷爷清唱的山歌。赶集的时候,小贩把这种磁带摆着卖,一摞一摞,像卖水果一样摆在地摊上卖,两三块钱一盘,盒内附有白纸片,上面通常写着:白衣丁先存山歌集,甚至还夹上一张照片当封套。
附近几个县的山歌手,都被录了这样的磁带,在地摊上排开了卖。录有爷爷山歌的磁带,据说卖得最好。
山歌总是一个调子,只有唱词换来换去,多听几支难免枯燥。
爷爷听着自己的歌声,人就舒展了。他听得一阵,又用眼睛瞪着小丁。小丁看出来,爷爷还有话说。小丁俯下身去,老人咽了一阵唾沫,发出微弱的声音:“能不能在电视上放?让我看着自己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小丁把视频接上,找来个茶几,把摄像机固定好一个位置。电视里面光斑一阵闪动,终于跳定,然后,爷爷的图像就出现在荧光屏上。爷爷侧过了身体,竟然能看清楚。他说:“反了。”电视机里,爷爷是反向睡着。小丁摇了摇头,他告诉爷爷,那不是镜子。他说了几遍,爷爷终于听明白,眼神古怪地盯着电视。
他最后说:“好了,你们都出去,我一个人走。”他说完了所有的话,显得精疲力竭,但另有一种轻松。他确实没什么可交代的了。
叔伯们有些犯难,不知道是不是该听父亲的话,老老实实走出去。他们把眼光都投到那个道士身上。道士轻轻地说:“死者为大,按他讲的办。”
按道士说来,老人已经是个死人了。
道士安排着把床脚垫高,然后才出去。出去时轻轻地带上了房门。
亲戚们都在堂屋或者院子里等着那一刻到来。道士独自站在窗外,朝里间窥望。他负责通报老人的情况。他似乎是很负责的一个人,卖力地干着这事,眼珠子几乎不转。时间稍微长一点,道士也显得紧张,他的一只手无意识地举了起来。当他不小心把那只手放下来的时候,三姑就哭了。三姑以为道士的意思是,老人家走了。
道士回过头看看三姑,告诉她说:“还没呢,慢点哭。”
道士意识到那只手可能传达错误的信号,干脆把手揣进裤兜里面。
爷爷的底气比一般的濒死者要长。亲戚们过久的等待,开始说起话来。他们认为,这可能是老人唱了一辈子歌,拓展了肺量。
屋外陷入奇怪的静寂,远处几声狗叫也沉闷无力。有一刹,小丁清晰意识到,现在进去,马上进去,还可以守候爷爷最后一息。时间稍纵即逝,再慢几拍,将永无机会!他想站起来,身体异常地软,他的脚被现场那气氛定住。往往这种时候,一个人会猛然发觉,好多事情——好多看似极简单的事情,也完全不由自主。
近处,二伯和小叔聚在一起抽烟。小叔讲起刚才的事,他也看出来,老爹的死和那台摄像机关系甚微妙。“……我们去接气,爹不想死又活过来,但摄像机给他接气,他不敢不死。爹以前就喜欢摄像机拍他,一拍,他就来劲,今天他被摄像机一拍,死也不怕了。道士那一套有点过时,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小叔这么解释。二伯点点头,又想到自己岳父也差不多了。二伯冲小丁说:“哪天我岳老子到时候了,你也带摄像机过来帮帮忙。”
小丁没吭声。
道士迟迟没有报丧,这种等待让人心力交瘁。小丁找一把椅子坐下,合上眼皮养神。他知道,不定哪一分哪一秒钟,道士就把一只手举起,短促有力地往下一挥,并用他洪亮的嗓音宣告:
“行了。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