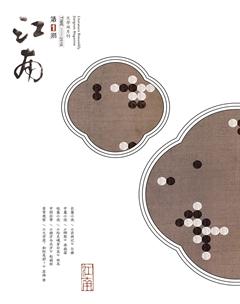断七
吴文君
一
早上,乐云五点不到起来,轻手轻脚梳洗好,换了衣服,到佛像前拜了拜,供上三炷香,盘腿坐到蒲团上。念完一部《地藏经》,天已经大亮。今天父亲断七,旧时的说法,死去的人经过七七四十九天,到了这天,要么投胎转世,要么灭失,总是和前一生彻底了断了。现在做七流行只做到五七,昨天乐云问母亲,母亲说,烧几个菜,再请一请他吧。她松了口气,说好菜她带过去,念《地藏经》的事,没跟母亲讲,七天一部念下来到今天正好念满七部。说她相信父亲会因此得到超度,不如说她再也没有别的办法把自己的心意寄托出去,虽然父亲还在的时候根本也不要她的什么心意的。
朝着装有父亲遗物的小盒子也拜了拜,拿出昨晚没看完的清样,打算出门前把这一期的杂志校完。
最好的世界还是在书里,她现在越来越有这种感觉。之前的几个工作虽跟书无关,六年前还当着主编的老师把她调到现在这家单位,虽说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刊物,这编辑也做了六年了,前些年只坐半天班,多出来的半天,她都用来读书了。
在母亲眼里读这些书有没有用,真不好说。工资还是那点,难得投个稿,稿费实在少到不值一提。母亲说起表哥过年给舅妈一给就是五千一万,她只有羞赧的份儿。
征文得的两次奖,一次二等奖,奖金五千,回来母亲问一等奖多少钱?她说八千,母亲说,噢,八千啊!拿三等奖那次,母亲问她二等奖多少钱?她说五千,母亲说,五千啊!那么多!
再快乐的事到了母亲这儿就没有了——破得四分五裂——她连想都不愿再想。五千块拿到,分成一样的两份,一份父亲,一份母亲,算弥补自己的不孝。到过年,钱装在压岁包里又回到儿子这儿。
母亲其实也不要她的钱的。和母亲之间的鸿沟,还是不知不觉在宽起来。难得一起买衣服,母亲挑出来叫她试的,总吓得她跳起来;她说好的,母亲也是不要。“难看死了”就是母亲对她的审美的评价。
姐姐礼云买的,母亲就觉得样样好。
礼云是舅舅的女儿,大乐云三岁。舅舅有段时间去北方了,乐云还没出生,礼云就跟在母亲身边。时间也不算长,舅舅据说被舅妈砍断情缘从北方回来,礼云也回自己家住了。礼云和母亲更像亲母女却是一个事实。礼云来家里,晚上亲亲热热和母亲睡一头,乐云睡脚边,听她们嘀嘀咕咕讲话,一句也插不进。三个人上街,也是礼云挽着母亲,不太熟的人都指着礼云问母亲这是不是你女儿。
就是没有办法让母亲喜欢,她才宁肯一个人读书的吧。读书让她心里安定。即使这两年编辑的位子坐得并不稳,有人想把她从编辑室掘出去,说了她很多坏话。
她专心校着稿,暗沉沉的书柜上慢慢移过来一个光团,鸟在阳台上叫着跳来跳去,浴室也传来抽水声和细细碎碎的声响。
是大象起来了。
乐云把粥盛出来。
中午去你妈那儿吗?大象问她。
去。
那我提早一点下班过去?
乐云关照大象不用去太早,其实这最后一个七跟之前几个七也不会有差别,是自己要把今天想成特殊的一天,想成父亲肉体消失后和她的又一次离别,她要送好父亲这最后一程。这点心思她不想提,只跟大象抱怨,我其实真怕跟我妈她们呆在一起,又没有话说。
反正吃了饭你就回来。大象安慰她,急着拿起包上班去了。
二
拎着打包的菜赶到母亲这儿,两个阿姨都来了,母亲在厨房炒洋葱肉丝,要给父亲做洋葱肉丝盖浇饭,房间里全是洋葱味道。乐云拿起桌上的酒瓶,在上面找生产日期。母亲一转身正好看到,头探出来,这我早上才买的。以前母亲拿过期的酒敬祖宗,乐云发现了,问她骗祖宗吗?这时也不多说,拿出桌布,铺好,把酒放回到桌上。
门铃响,是母亲的干女儿丽玲,手里抱着一束花。五七那天她就说要买花。两个阿姨招呼她坐,房间里一时都是说话声,好像坐了十七八个人似的。父亲爱清静,这一点乐云像父亲。她跟大象说过两次,说你别看我好像跟谁都很好,其实藏在这底下的是冷漠,我是很冷漠的,我知道自己。大象点点头,说你是这样的。可这个时候,乐云真心感谢丽玲,把那束鲜黄的小雏菊在供桌上端端正正地摆好。那边,两个阿姨也赞起丽玲,从丽玲就是好,说到这么好的人为什么偏偏找不到对象结婚呢。
没人配得上丽玲吧。以前说到丽玲五十了还不结婚,乐云从不说什么,今天这句话脱口而出。往桌上摆供品的手也别扭起来,倒好像正是这会的热闹提醒她父亲真的不在了,突然想起来,拉开厨房的玻璃门问,照片呢?
别拿出来了,看见难过。母亲熄了煤气的火,看她还站着,又说,早上我跟你爸说过了,他不会怪我的。
反正她的事母亲都要泼冷水,本来她今天特别想再看看父亲。父亲也没有像样的照片,丧葬一条龙的人只好拿了身份证去翻拍,没想到那么好,那么像他平常的样子。
硬把照片从抽屉里拿出来母亲也没办法,乐云几乎想这么做了,一阵冲动,又把心里冒出的尖压回去。
她早就习惯了把这个尖压回去,尽管这个反抗的尖无时无刻不想着从肉里钻出来,十岁以来?二十岁以来?一直以来?
算了吧,今天父亲断七。没有照片,眼前也恍惚显出父亲的样子,坐在藤椅上抽烟,看着窗外,想着什么。
母亲端着铺了厚厚一层洋葱肉丝的盖浇饭出来,问她买了什么。
乐云说去得太早,饭店刚开门,乱得一团糟,还好白斩鸡和盐水毛豆做出来了。
你买白斩鸡了?你大阿姨也买了呀!
我又不知道,你不说。乐云没想到是这样,刚压下去的尖又要冒出来。
我怎么知道你也去买了,母亲瞪了她买的鸡半晌,说,先放冰箱里。又去厨房,端出一整只焐好的鸡。
一百块钱呢,母亲把鸡搁到供桌上。鸡皮凝着油光,屈膝低头歪着脖子的样子让乐云不忍心多看,不甘心地说,说好菜我买,不能打个电话给我,我买别的?
就这几个人,还要买,吃得了那么多?
大阿姨拍拍僵硬的膝关节,我是想就这一次了,贵点就贵点,只要鸡好,大家吃个开心。
小阿姨刚说,要我说也没什么好吃,母亲抢上去说,你又来了,比一新饭店的总好多了!
提到一新饭店,乐云不说话了,思绪又回到刚才。刚才,她一脚踏进饭店,里面,老板娘抓着拖把一边麻利地拖地,一边问她,最近旅游去了?好久没见你了。
呃,她说,差点流下眼泪。
上一次来这里吃饭还是她过生日。四十多岁了,还有父母给自己过生日,收到丈夫送的花,在理智上她承认自己也算幸福了,心里仍然为自己活在父母常年争执的阴影下摆脱不了而不痛快。那天的菜就有白斩鸡、盐水毛豆和带鱼。吃好大象要付钱,父亲拉开他,硬要自己来付。任凭大象一米七八的个子,抢不过不到一米七病了一年多的父亲。店里的几个湖南妹子活也不干了,笑嘻嘻地看着他们。她也不懂父亲干什么嘛,又没有多少钱。
回去的路上父亲突然说,其实是我没跟你们说,我现在吃什么都没一点味道。父亲难得泄露自己的病情,乐云看看母亲,又看看大象,都没敢往下说。这段路没有灯,四周暗得很,她就像眼前发懵走得一脚高一脚低,跟在父亲后面看他在拉皮带,拉了一下又拉一下。期期艾艾劝父亲去医院看看,也知道父亲不会听。他一向恨医院,恨医生只要钱,没有医德。果然,父亲说,看什么!他那时已经预感那是最后一次在外面吃饭庆贺了吧。之后,只过了三个多月,父亲不得不被他们送进医院,再之后,一天没有要她服侍就走了。
饭店的大厨煎好带鱼,也问她旅游去了?她还是说,呃,不太友好地垂下眼睛。
其实头上戴了白发圈的,也许他们没看到。可是,无论如何,还是不说好。
现在坐在母亲边上,也一样说不出,不想说。她是母亲生的,却和母亲越来越不像了。
她没去想母亲做洋葱肉丝盖浇饭是和她一样的意思。她只是抚着脚踝,好像这样能安抚自己,不让心里的尖再冒出来似的沉默地坐着。
三
不至于这么走不出。
根本是她不想走出来。
即使同事抱怨办公室装修,灰这么大,还叫他们坐班,她听了也像没听到,就像人不在那里。
在死面前,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母亲上了香。
青蓝的烟一缕缕飘浮着,飘向窗外。
香真的能把这个世界的信息传到另外的那个世界里去?那样,父亲就能听到她在问他还有什么心愿。
她一边断定这是不可能的,一边捕捉着心里的感受——可以称得上感应的感受。突然,有人敲门。是礼云。
母亲接过她手里的水果,埋怨她怎么来了,说了不用来的,家里事这么多。
今天姑夫断七,总要到一到,坐五分钟就走。礼云麻利地跪下磕了头。
你婆婆呢?一个人在家?母亲不放心地跟过去,坐到丽玲和礼云的中间。
没事,菜我弄好了,回去热一下,用不了几分钟!礼云把包往茶几上一摔,只静了一静,就暴发了。
不是我背后说她,你们说有这样的人吗?出个门,叫她在家里别做什么等我回来要说七八遍。
哎呀,大家一齐上阵,劝她人老了都这样,只要让她吃好穿好,别的都随她去。
真是没见过,就说出去吃个饭,我问她,妈,一块去吧?她说,你们去,我就不去了。我们要走了,她又眼巴巴看着,好像在等我们求她。我再说,妈,一块去吧?她说,那我穿件衣服。衣服穿好了,看着我又说不去了。要吃饭了,她就开始哭了,这个菜你爸爱吃的,那个菜你爸爱吃的,这饭我真没法吃了……
礼云只要讲起婆婆,就崩溃了一样停不下来。实在也是想不到的事,公公只动了个腿部的小手术,却因为并发症,手术的第二天就去世了。礼云只好和丈夫一起把婆婆接到家里住。这样有一年了,这些话,礼云也讲了一年了。
真的,乐云,礼云指着她,这种日子只有我过得下去,换成你,早拍拍屁股走了。
她想说,你怎么知道我会这样,却忍了下去。跟礼云没什么好争的,她只说她的,根本不听你的。看着礼云转过身,又去跟丽玲说。
丽玲,你受得了吗?一块肉一根葱,什么都要拿到你鼻子底下叫你闻,天天这样受得了吗?
丽玲往后缩了缩,想让开礼云伸过来的手,脸差点被礼云碰到。
母亲说,你忍忍吧,不是两边轮着住吗?反正一个月到了就去小宝那边了。
小宝那边!还不是跟小宝闹得更厉害。上次在医院里小宝当着医生的面说她作,气得她哭了半天。我好心叫她住我这里,她怎么说?要先问问小宝!就怕得罪小宝。我是看透了,再怎么小宝是女儿,我是媳妇,对她再好也没用!乐云,换成你早走了。
乐云看着礼云的脸,即使厚厚的粉底,也掩不掉脸上那团青气。母亲提起礼云发青的脸,总要叹气,说礼云的体质不能劳累。乐云想的却是礼云只在她们面前发泄,回到家里就把心里的恶气收起来,跑前跑后做着最孝顺、最有耐心、最好的人。
那边,小阿姨问礼云,你还不走?都一刻钟了。
有那么快吗?礼云伸了伸懒腰,笑着嘟哝,不回去了,真不想回那个家!
母亲说,你再等几分钟,请了宽,带点白斩鸡过去。
算了,昨天刚吃过。礼云抓起包,站到一半,又坐下去说,这样做人也真是太累了!反正我就在这里说说——昨天,我想好久没有吃鸡了,买了半只。晚上小宝来电话,我就去接,谁知道接了回来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问了半天才说小宝问她饭吃了,她说吃了,小宝又问她吃得好不好,她说吃白斩鸡。小宝一听白斩鸡就发火了,不知道说了她什么。还问我小宝发什么神经?我说,小宝才不神经,还不是你说错了,不该说吃白斩鸡。
这也错了?丽玲摇头。
礼云说,我没有读过书,话里的意思还明白,小宝问她胃口好不好,吃得多不多,不是问她吃什么东西。她说吃白斩鸡,小宝怕我知道了,误会她在查我们吃什么,当然生气。还是子杰,这小东西真聪明,马上偷偷打电话给他姑姑,说奶奶在生气,妈妈劝不住了,姑姑你快打电话给奶奶。
乐云努力不去听礼云说什么,手指下意识地在手机上抹来抹去,竟然抹开一段视频,闪过一个美国女孩跟刚认识的士官疯狂做爱的画面,伴随着露骨的呻吟。她早过了看这种东西的兴奋期,只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这段视频怎么会在手机里的,慌忙关了。
那边礼云不知道说到哪里,忽然站起来忿忿地说,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话越讲越错,一句不讲最好,以后随她们说什么,我只当没听见!
母亲跟着站起来,我这就请好了呀,你再等几分钟。
真不要了,说了这么多,姑夫要烦死了!是不是?姑夫?
礼云麻利地磕了头,指着带来的水果对乐云说,里面有你喜欢的莲雾。又对母亲说,你上次说的鞋子过两天再去看看有没有。母亲忙说鞋子啊,不要买了,我随口说说的,站在门口,礼云的脚步声听不见了,才关上门。
乐云剥开一个白纸团,露出嫣红的玛瑙一样的莲雾,克制着没有说它们是这么的可爱。
四
大象进来,房间里仍留着礼云的戾气。
最近收到的杂志一翻开也是扑上来的戾气:精神病,乱伦,奔丧……
书上是怎么说的?她们这些女人表面上为别的事烦恼,说到底还是为了男人,为了没从男人那儿得到想要的东西。礼云的丈夫这两年不停地被单位派出去出差,这才是礼云说不出的苦衷吧。
可是只要礼云来过,她都要沉重一会,好像吞下不止一个铅锭,要花些时间才能把这些铅锭消化了,想起礼云对她好的地方。
母亲拿出纸钱,乐云说,我去。她早想出去透一下气了。和大象、丽玲到楼下,还在上次化过纸钱的地方,把纸钱倒出来。
她蹲下,看着银灰色的闪闪发光的锡箔焚得比最细的棉纱还要薄,还要脆,在微风里颤颤地动着,边缘的火光像蚕食一样一圈圈缩小下去。
礼云好像过得也不好。丽玲说。
呃。乐云垂着头。
听说她现在很有钱……丽玲的喉间发出叹息一样的声音。
呃,以前没钱她也这样。乐云还是垂着头,眼前只剩一堆冷下去的微黄的碎片。
大概只除了她——大家都相信父亲已经走了。
父亲在的时候,礼云哪敢说这些。
她已经忘了礼云那天为什么来家里,找母亲干什么。那时她们刚读初中,她的兴趣全在书上,根本没注意礼云,只恍惚觉得礼云和往常一样做起了家务。一起说话做家务本来就是她们俩的乐事,等她意识到有什么不对朝他们看过去,只看见礼云飞快地缩回来的手,那只瘦得像鸟爪一样的手正从父亲坐着的地方缩回来。礼云胆子太大,热心得过了头,以为父亲也像母亲,样样听她的,就像从母亲手里拿过什么那么自然那么快。听见父亲吼着叫礼云滚,她吓得说不出话。父亲还没有这么骂过亲戚中的哪个小孩。礼云站了一会儿,没说什么就走了。她紧张地偷觑着父亲把桌上的钱推到角上,捋到手心里,塞进口袋,把一颗蓬乱发灰的头扭到她的背面。看上去他已经平息了,至少不会连累她也挨一顿骂。可她并没有因此觉得高兴,她更感到难为情,为自己有这样一个脾气暴躁不近人情的父亲难为情。那时她其实比礼云更恨父亲。
她背上有条挺长的疤,父母都说是自行车轧的,在不同的场合,他们都说过,你从地上爬起来,轮胎印子都还在背上呢。可她模模糊糊始终觉得那是父亲打的。比礼云挨骂要早几年,她在读二年级还是三年级,父亲好不了三天就要在家里砸碎点什么,热水瓶,碗,茶杯。白天总让他烦燥、易怒,晚上好一点,很晚了,还在厨房里听收音机,收音机里也永远有一个柔顺的女声会像医生那样治好他的烦燥、易怒。天一亮,他又变回了老样子。他有时根本忘了她只是个小孩,把她也当成热水瓶,碗,茶杯,为一点点小事,比如忘了做作业,忘了把看完的书放好,都能打一顿。那天肯定是他打得最厉害的一次。那天也肯定是她反抗得最厉害的一次。从家里冲出来,不顾一切地跑着,跑过宿舍区,跑过菜场学校,就像跑在操场上,什么也不看,什么也看不见,她要跑,能跑多远跑多远。后来她躲进理发店烧水的小屋,晚上父亲把她找了回来,母亲像只蚂蚁在门口转来转去。她咬着嘴,谁也撬不开她的嘴让她说话,一直到睡觉,她才说,我不是你们生的。瞎说,母亲说,你当然是我们生的。她紧紧闭上眼睛,眼睛合上前的一刹那,她看到父亲的脸像核桃一样皱了起来。她有点高兴,觉得打中了父亲的一个地方。可是那天整晚她做着梦,梦见一根皮带像鞭子一样抽着她。
一个小孩被大人打几下有什么,一个国家还要拨乱反正呢,不久之后,收音机每天都在播报哪些人平反了。她慢慢弄懂了平反的意思。可是平反对她并没有特别的意义,除了祖母的一个弟弟——已经在狱中死去多年——家里没有人平反。再后来,大概该平反的都轮到了平反,人们开始忙着挣钱出国。店里的书也突然多起来,父亲一本本买来高高地堆在桌上。他最爱谈那些书,谈到愤怒的时候总像精神病,大家一致认为他讲的都是大道理,没什么意思,听众越来越少。母亲要洗衣服做饭,和邻居闲聊,最后只有她坐下来,听父亲讲政治就是把彼得的东西拿给保罗,讲欺骗就是一边朝你微笑一边掏你的腰包,讲死去的人哪怕恶鬼远没有活人可怕。知道这些话大部分出自书里,她也开始看书了。
她以为礼云不会再来了,母亲只能喜欢自己了。然而过了一年礼云就像没事一样又来了,见了父亲还是叫他姑夫,父亲也没事一样招呼她,大家从来不提那天的事。
上去吧,大象说。
屋里,母亲吹熄蜡烛,把椅子从桌前拖开——这就是请宽,也就是叫父亲走了,去他应该去的地方,直到某些日子,再请他回来。
大家也随之轻松起来,瓜分着一整只鸡,热热闹闹吃完了饭。
大象走之前问她,你也走吗?我再坐一会,她没去接那两道目光。两个阿姨也一起走了。丽玲坐了坐,说还得回去开张发票,也走了。
母亲叫她回去,她说再坐一会。
母亲还是说,回去吧,回去睡会儿。
坐着,也没有话。母亲从来不问她和大象怎么样,那个编辑的位子是不是坐得下去,她说过一次,满含郁气,母亲说,是你自己要去,那时倒没想到今天!
又挨了一会儿,她没有再让母亲催,站起来走了。
下午的太阳淡了一些,风吹动树枝,凉爽的感觉包裹住她的全身。可是上午出门前的安定没有了,念《地藏经》的安定也没有了。思路从吃晚饭前校完清样跳到晚上,大象忍耐好多天了,要是她坚持今天晚上还是不行,他也会听,可明天他会做出同样的暗示。怎么说服他再等等呢?他会说这么多天也差不多了。还是干脆什么都不要想了,被他拖到深水里似的好好放纵一次。她遐想着,有一种感觉几乎涌上来,一种陌生的、只有活着的肉体久久的轻柔的摩擦才有的快感。为什么不能像刚才视频里放纵的美国女孩呢?她和礼云一样需要发泄,可是,她知道自己是不可能的——刹那间,她又下意识地感到两腿僵硬,内心沉重。
这里,是往常父亲从家里出来必定要经过的地方。还是一样的小巷,一样的香樟树枇杷树,跨过马路就是公园,门口还是那个水果摊,冬天卖甘蔗,夏天卖西瓜,一只烂熟的西瓜被摊主扔出去,远远露出腐败发黄的瓜瓤。
路上有一点冷清。不管乐云怎么看,都看不出有什么消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