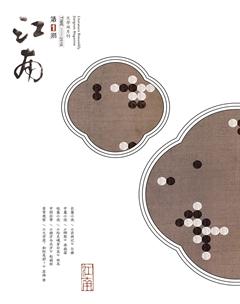猫在钢琴上昏倒了
小昌
小文先出门了,高跟鞋啄着楼道里的地板砖。咄咄咄,声势渐小,后来就听不到了。窗外猝然几声鸟叫,阿信立在窗前,剃须刀响起来,那只叫贝蒂的猫睁开了眼,瞄了一眼,又闭上了,把脑袋塞进自己的怀抱。阿信看见小文从楼里走出来,阳光落在她身上。整个人也光彩起来,袅袅婷婷,消失在阿信的视线里。
他也该出门了。贝蒂最终醒来了,从钢琴上一跃而下。他抱起贝蒂,小心地爱抚。后来亲了一口,就放下了。贝蒂伸了伸懒腰,张了下嘴,锋利的尖牙迅速缩进嘴里。阿信说:“再见,宝贝儿。”贝蒂没理他,闲走了几步,跳了一下,又跳了一下,最终落在钢琴上,蜷缩起来,眯上了眼。阿信不甘心,又跑过来,把贝蒂抱进怀里,挠它的小肚子。
他很快坐上了公交车。上班高峰期已过,人少了许多。他在靠窗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侧面写着“老弱病残孕专座”一行字。他盯了一阵,发现“孕”这个字是个象形字。公交车的门开开合合,上了一些人,又下了一些人。门一开,热风扑进来。有个不算老的男人挨过来,拽着扶手,一眼眼看阿信。他看着窗外,动物园到了。突然很想去动物园看看小动物。身边男人伸出手碰了碰他,阿信抬头看,瞧那意思,逼他让座。阿信说:“那边不是有空座吗?”老男人急了,唾沫星子飞出来,指着那行字说:“老弱病残孕专座,不认识字吗?”阿信说了句操,还是闪身离开了。老男人瞪着眼,说了句什么东西。阿信没跟他计较,把头转了过去。
到站了,他像只猫似的跳下来,落进了一大团阳光里。
阳光有了重量似的,压在他的颈背上,落在地上也有声音。他走进一栋高楼,保安不怀好意地看他。他在等电梯的时候,在一面玻璃前,好好看了看自己。西装还算合身,领带和衬衫的颜色没什么冲突。理了理头发,进电梯,摁了22。只有他一个人。电梯很干净,很像个棺材。他怎么会想起棺材来。
从电梯里走出来,就看到了那家公司。他怯生生地进去了。
“来面试的吧?”有人问他。阿信小心地回答说是。
“跟我走吧。”说话的口气有点像警察。
他被带进一个房间里。“坐下吧。”他就坐下了。眼前三个人坐在一张长条桌背后。阳光透过玻璃变轻了,斜斜照过来,把他影在地板上。中间的男人开始问话,一直在抖腿。左右抖一阵,上下又抖。
“司迪麦知道吧?”
阿信点了点头,不知道他在问什么。
“《听说篇》中,从第一个人嘴里说出的一句话‘新建筑正在倒塌中,经过许多人的转述,最后变成了哪句话呀?”
他摇了摇头。男人旁边是两个女孩,刚才还一直在转笔,等待机会做记录。见他摇头,都笑了。
他又坚决地摇了摇头。中间的男人也笑了,说:“告诉你吧,那句话是猫在钢琴上昏倒了。”都在笑,他也笑了,问:“为什么?”这句话一说,三个人笑得更急了,也许笑下去有伤大雅,中间的男人火速严肃下来,旁边的两个女孩住了嘴,又转起笔来。
“不为什么,猫就在钢琴上昏倒了,你喜欢猫吗?”
阿信说:“很喜欢,我就养了一只猫,是我在街上捡的,它叫贝蒂。”
“其实跟猫没关系,一点关系也没有。不过你很有爱心呀,收养流浪猫的人,应该是个有爱心的人。”说完左右看了看,女孩们都冲他点头。
阿信说:“谈不上吧,跟它挺有缘的,老跟着我。”
“说说你写过的广告语。当然是你认为最满意的,有吗?”
阿信想了想说:“爱我就来看我吧!”
“这是你写的。”
阿信点点头。后来又问了几个问题,他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有没有道理。
面试很快结束了,他们说让他等电话。阿信只好离开了,坐电梯,从电梯里走出来,离开那栋楼,把自己扔在飘满阳光的大街上。
小文没去上班,急匆匆钻进的士,逃也似的走了。也许早就知道阿信立在窗前俯看她。她去了那所大学,竟去了那里,连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从那所大学毕业好几年了,一直没回去过,没有无缘无故就去的道理。本来要去上班的,从那栋楼里走出来,闻到一抹抹的桂花香掠过来,突然就改了主意。一个念头袭来,让她越走越快,路边叫了的士,说了地址,出租车就一往无前了。坐进车里才打电话回公司,请了假。
托着腮看窗外的高楼和车来车往。公司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听上去头儿有些不高兴,没说再见就把电话挂了。小文很少这样,一点也不像她,连头儿也觉得有些意外,不知说什么好。她看了看自己,还穿着上班时该穿的衣服。过桥,又过桥,总算到了。
进校门的时候,新发现一对石狮子,比她还高。它们蹲在校门两旁抖威风。她踮着脚摸一只狮子的眼睛,眼珠子凸出来了,这样才算凶神恶煞。只好摸摸它的尾巴,一折身进了校园,四处乱晃,不知道要干什么。后来一个人爬上了最高的教学楼,一直爬到楼顶。找了个原来呆过的地方,两条腿自然耷拉下来,低头就能面对瘆人的虚空。腿在虚空里晃。看样子跳下去轻而易举。
一下子想起阿信拿头撞墙的事儿来了。小文一个人呵呵笑起来。阿信说:“信不信,我一头撞死,你信不信?”说完,就一头撞了上去,鲜血直流,顷刻间染红了额头。这么些年过去了,想来他们之间没什么可说的了,难道就这样继续下去了?一点点老下去。低眼向下望,楼下那么多人,突然多出那么多人,正仰头看她。越来越多,有人开始大声喊叫,隐约能听到。他们以为她要跳下去。
有人上来了。更多人上来了。在她背后,不敢向前,轻声劝她生活多美好,人还很年轻,不要一时冲动,让爱你的人伤心。有个老男人,看样子像个教导处主任,向前伸着手,五指分开,做千万别这样的手势。小文回头看他们,一脸楚楚,像个可怜的该跳下去的女人。
教导处主任模样的人一点点抹过来。一寸寸向前进,近了,更近了。最终抱住了她。把她拖下楼,走到楼梯间,她就笑了起来,实在绷不住了。别人以为她过于激动或者紧张,有些失常。后来,她就被硬生生拉进大学生心理咨询室了。一屁股坐下来,松了口气。她说什么,也没人相信了,百口莫辩。只好认真整理自己乱开来的头发。
他们几个争相说着,很快讲完了她的故事。所有人鱼贯而出,仍有人朝心理咨询师探头。心理医生从她身边走过去,关上了门。又回头笑脸盈盈地看她,就像突然变了张脸。医生是个女的,却长得很雄壮,肩宽背阔丰乳肥臀像个球,脸蛋也圆圆的,小眼睛炯炯放光。她开始说话了,像个好朋友。一切没什么大不了,阳光照进来了。小文也许要暗自发笑了,没去上班,却被拖进心理咨询室来了。
小文说:“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我早就毕业了,不是这里的学生,只是回来看看,回忆一下美好时光。”
“别急呀,同学,慢慢说。”
小文说:“早跟你说了,不是同学,放了我吧。”
“你是自由的,从来都是自由的,想走就走。但我希望你还是留下来,也许你有很多话想对我说,对一个好朋友说。把我当一个好朋友好吗?难道不是吗?”
小文想起那个留校的男同学来,掏出手机来,打了出去。
“快救救我吧,我在心理咨询室呢。”挂断电话,才想起已经很久没联系过他了,早忘了还有这么个人存在。也许上学的时候,那人喜欢过她,她才这么放肆,第一句就直奔主题,让他来救她。这么一来,她还是那时候的她了。
很快有人敲门,门一开,有个男的立在门外,一眼瞧住了小文,笑起来。“误会,误会,王老师,绝对是误会,这是我的大学同学小文。”小文也站起来了,说:“王老师把我当成臆想症了,我说的她全不信。”幸亏有这个故事和王老师这个人,突然见了这个男同学,真不知道从何说起。
小文瞧了他一眼。额前的头发更加稀疏了,寥寥几根,脖子也粗了些,像个陌生人。他一直在笑,看上去好开心。
“一点没变,你一点没变,还是那么漂亮。”
小文说:“哪有,取笑我,取笑我对吧。”
一前一后,他们在校园里走。有叶子慢慢落下来,小文恍惚了一下。想起了很多事来。
“带你转转吧,好久没来了吧,好几个地方都拆了,正在建高楼。瞧那边,正在建实验大楼,据说有二三十层呢,建成了就是我们大学的标志性建筑。”
小文说:“了不起,真了不起。”
她还在想那些事吧。
阿信沿着盲人道走下去。他总是喜欢走在盲人道上。有时甚至闭上眼,找根棍子支着走,跟盲人没什么两样。这样走下去,看自己能走多远。这次他又闭上了眼,走着走着一睁眼,就到了动物园。买了张成人票,想也没想就进去了。像是故意来的。
动物园高树成行绿草如茵。动物们都很沉静,甚至懒得看人。阿信信步走着,上了鳄鱼岛,猴山近在眼前。鳄鱼像死了似的,横七竖八,趴在池子里一动不动。他扔了块石头,又扔了块石头,石头都砸在它们身上,就像砸中了另外一块石头。有人走过来,说要罚款,向池中扔一块石头,罚款五十元。像他这样连扔两块,共计一百元。单据也开好了,递给阿信,那人站在面前,等他付钱。
阿信伸手从外套内兜里掏去。面前的人儿把微笑荡漾在唇角,该来的总会来的,一直伸着手。没想到阿信竟掏出一把枪来。黑森森的,似乎也沉甸甸的。瞬间拿枪顶住了那人的肚子,阿信说:“敢跟老子要钱,不想活了。信不信,我崩了你,信不信?”对面的人吓坏了,唇角抖掉了刚才的微笑,松软下来,下巴干垂着。“信,我信。求你别开枪,大哥,求你别开枪,大爷。”看样子他吓坏了,腿发软,不及时制止很快就会跪下去。阿信搀住了他,说:“闭上你的臭嘴,今天的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要是有第三个人知道,一枪崩了你,快滚。”阿信吹了吹枪口,像演电影似的,枪口似乎也冒了一股烟。他迅速把枪装进外衣的内兜里。
阿信有些雀跃。很快到了猴山。假山假石,猴子们也玩得开心。很多人朝山里扔它们爱吃的。几只猴子就会跟过来,不住地朝嘴巴里塞,吃完了,像坐井观天的蛤蟆似的,朝天上望,接着等来食。地位低的、个头小的猴子只能在旁边逡巡,偷偷地下手,又迅速地躲远,像从没来过似的。
两只猴子打起来了。有人喊,打起来了,打起来了,猴子造反了。好多人在拍照。阿信也看了过去。只见两只公猴奔来跳去,呜呜叫着。对峙上一阵,又扑到一块,身上都挂了彩。没过多久战斗结束了,其中一个灰溜溜消失了。有人说,没劲,太没劲了,想看看新猴王登基呢,又失败了。老猴王蹲在最高处,向四处俯瞰,江山还在脚下。另外那只猴子不见了踪影,想它应在某处舔舐伤口吧。
听人说,被打败了的猴子就再也不敢挑战了,一直灰溜溜地活下去,除非猴王换了。有些猴子可能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仍像蛤蟆似的蹲着,望着来食。
有个戴蛤蟆镜的女人就在不远处,不住眼地看着。她好像一个人来的。人都纷纷离了场,只有她还在瞧着那只安静的猴王。阿信一会儿看看猴王,一会儿看看她。
猴王好像有什么心事。突然一跃而下,扑住了一只猴子,裹挟着它上了高处。利爪揪着它的后脑袋。那只猴子知趣地撅起屁股,猴王就势骑了上去。像台机器似的扭起来。高昂的猴头一动不动,好像在说,都是我的,都是我的。阿信捡起一块石头,就扔了过去。砸中了猴王的脖子,他扔得够准的。猴王迅速俯下身,呜呜叫起来,龇着尖牙。阿信说了句他妈的,就走了。回头看了看戴蛤蟆镜的女人。女人正在看他,阿信说:“看什么!”说完扭头走了。
阿信过了一座桥。买了包鱼食,喂池塘里的鱼。他坐下来瞧着那些鱼,像极了老鼠,在水面上爬来爬去,抢东西,也不怕人。鱼食喂完了,他把自己的手指头伸进鱼嘴里。那只鱼嘬呀嘬呀,只好吐出来,张着嘴继续朝向阿信。他竟有些害怕,鱼嘴空洞幽深,通向未知。远远看去,那么多鱼嘴,都张着,一个个幽深的洞,望而生畏。
阿信起身走了,越走越快。腋下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小文说:“上学那会儿总去老四川小饭馆,现在还有这个小饭馆吗?”
他们去了学校旁边的老四川小饭馆。一切还是老样子,老板娘胖了些。小文问她还认识她吗,老板娘摇了摇头,说想不起来了。小文做了个伤心的表情,看了眼老板娘,又看向他。他说:“你还是这么可爱。”忍不住说出来似的,说完有些窘。
等他一坐下来,小文突然很想说说话。说些不该说的,或者不敢说的。也许他的笑鼓励了她。一直在笑,好像说什么,他也会笑下去。
小文说:“其实我想了那个问题,跳下去会怎样。人呆在高处向下看的时候,是不是都有跳下去的冲动?好像有什么说不出来的诱惑。”
“别乱想了,没事爬那么高干什么?”
小文说:“上学的时候,老喜欢在那里玩,可以看到学校的任何角落,拿一罐啤酒边喝边吹风。你不记得了?”
“好几年过去了,时间过得好快呀。我只记得你跟阿信成天黏在一起。阿信现在过得怎么样?”
小文说:“还好,不过不停换工作,他就那样,总是安分不下来。今天又去找工作了,去了家广告公司。”
“你呢?”
小文说:“我?不就是你看到的样子,有些狼狈,灰头土脸。”
“哪有,你倒越来越风趣了。”
小文说:“有没有好电影,吃完饭陪我看场电影吧。好久没看电影了。”
“你们俩是不是闹矛盾了?”
小文说:“没有,连架也懒得吵了。我们有半年没说话了,你信吗?”说完自己笑起来,继续说,“跟你开玩笑,没那么久,不过话越来越少了。”
“我离婚了。”
小文说:“为什么?”问完摇了摇头,也许觉得自己的问题有些愚蠢。
“我看不惯她,她也看不惯我吧,后来我对她一点兴趣都没有了,脱光了站在我身边,我都没反应。我就说,咱们离婚吧,第二天就去了民政局。再简单不过了。没想象中那么复杂。”
小文沉默了一阵,说:“离婚后,你们还联系吗?”
“我们还是好朋友。”
小文问:“真的吗?”
“怎么可能,我们很少联系,见面也没话说,幸亏没孩子,你们为啥不要孩子呢?难道也为离婚做准备吗?对不起。”
小文说:“本来打算要个孩子的。”
“说真的,没孩子,日子过久了挺没意思的。”
小文说:“有什么好电影吗?我想去看场电影。有时间陪我去吗?”
他们去了电影院。小文说:“随便哪部都行。”那人买了两张票,俩人一前一后就进去了。一下子黑了下来,那人的眼睛放出两小片贼亮的光,她不敢看他了。电影放到一半,很多人掉了眼泪,小文也抹眼泪。她的手突然被抓住了。被一团温热包裹。她仍瞧着银幕,也没有拒绝。没过多久,那人就松开了。电影快结束的时候,又过来摸她的腿。后来摸向深处。电影散场了,高灯亮了,照耀下来,所有人都现了形。他们俩说着那部电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从电影院走出来。他们没话可说了。她一路跟着,中了魔似的,跟着进了酒店。也许她只是期待发生点什么。那人急匆匆的,一进酒店就扑倒了她,拼命脱衣服。她在他身下,望着那张脸。扭曲的脸,有汗珠在额头上爬。
小文轻声说:“先去洗澡吧。”
“不洗了。”
小文厉声说:“去洗澡。”
那人翻身下来,进了卫生间。水哗啦啦砸在地上。小文整理好衣服,提着两只高跟鞋,冲出了酒店,一头扎进光里。像只逃命的兽。
阿信从动物园走出来,太阳已偏西。他无事可干,就溜进一家网吧。打了一阵网络游戏,喝了瓶可乐,就从网吧里走出来,天已黑尽,路灯亮起来。他又上路了。过了一座桥,又过一座桥,在一个巷子口停下来。有一只昏黄的灯挂在树杈上。他点着一支烟,朝马路上张望,像在等一个人。
也许想起很多事来。阿信猛地踢飞了一只易拉罐,发出一串串刺耳的声音。他又追上去,倾尽全身力气踢了一脚。易拉罐飞了起来,飞进草丛倏忽不见。月亮早已爬上了树梢,不知是谁吹起了箫,悠悠地呜咽。
要等的人还没来。或者今晚不打算来了。
远远地有人来了。好像是她。阿信迅速转身躲在一棵树后面,偷偷瞧她。好像又不是他要等的人,她一步步走了过来。越走越近,进了巷子。他又露出了头,瞧她的背影。没错,是她。
他悄悄跟了上去,走得极慢。像往常似的,一直跟到小巷深处。他摸着墙壁,每一块砖都好像很熟悉。她停下了,朝后面看了看,好像早就知道有什么人跟踪似的。她转头的样子,像多年前一样动人。巷子深处倒垂着的白炽灯,把女人的影子影到石板路上,很长很长。
她回转头进了另一个巷子。阿信也悄悄拐了进去。连路灯也没了,只有冷清的月光斜下来,阴影里愈发幽暗。
该来的总要来的。她进了一所旧房子,房子早已破败,隐约可看到墙上有个大大的“拆”字。房顶上也许长满了野草,风一吹,地上的影子摇曳开来。
阿信疾跑了几步,追了上去,压低了声音,呵斥:“站住,别动,举起手来。”女人什么也没说,慢悠悠地举起手来。阿信用枪顶着她的后背,又用力顶了一下。她慌乱中说出几个字:“你到底想干什么?”
阿信冷笑了几声,说:“不想干什么,把衣服脱了。老子想看你脱衣服。”那人没动。阿信又喊了一句:“快把衣服脱了,一件件脱。”
那人脱掉一件又一件。终于脱光了,赤条条立着。头上的上弦月更明亮了,光倾泻而下,落在她的身上,泛起晶莹的雪光。阿信揪住了她的头发,像那只猴王似的,都是我的,都是我的。他咬她的脖子。
猴王威风凛凛,风撩起了它的鬃毛。头抬得更高了,后来就对着月亮咆哮起来。她转头看了他一眼,一眼就什么都知道了。后来他就俯在她的身上不出声了。两只身子紧紧贴在一起。
她很快穿上了衣服。“给我支烟。”她说。说完倚在那堵破败的墙上。旁边有个大大的“拆”字。
小文耐心地抽了起来。有些呛,她开始咳嗽。
她从那家酒店离开,就关上了手机。跑到街上,买了身衣服,就继续在街上东游西逛。天终于黑了,后来就黑透了,今晚又是阿信在那里等她的日子。想了很久,到底要不要去,最终还是去了。穿上新衣服就去了。也许是最后一次。
阿信拍她的后背。他也在抽烟。又把那把枪掏了出来,在手里掂量着。手枪在月光下泛着青光,他说:“挺像个真家伙,今天我去了动物园,见那些鳄鱼一动不动,就扔了两块石头,有人过来要罚一百块钱,老子就把枪掏出来了,他差点吓尿了,要给我下跪,人都他妈的怕死,想起他那副样子就想笑。”说完笑了起来,后来捂着肚子笑。
小文说:“有意思吗?”
阿信说:“没意思吗?你也好久没去动物园了吧。改天我带你一起去吧。”
阿信好像有很多话要说,不吐不快似的。比起头几次更显得激动,甚至不安。腿一直抖个不停。小文仍倚着墙,也许在想头几次玩这种游戏时的场景。游戏结束,心情总要好一些,她挽着他走完整条巷子,有时会用两只手挽着他那只胳膊,甚至将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那条手臂上。他拖着她走似的。
阿信接着说:“猴山里的故事更多。有一只公猴挑战猴王,打得很激烈,结果还是失败了,弄了一身伤,听他们说,被打败了的猴子再也没好日子过了。”
小文说:“你不是去面试了吗,怎么又去动物园了?”
阿信说:“你不说,我都快忘了。他问,你知道司迪麦吗,我说知道。”
小文说:“你到底知道不知道?”
阿信说:“我哪知道,谁他妈的知道司迪麦是谁呀。接下来他就问,从第一个人嘴里说出的一句话‘新建筑正在倒塌中,经过许多人的转述,最后变成了哪句话呀。我被问傻了,他们告诉了我答案,最后那句话是,猫在钢琴上昏倒了。猫知道吗?就是贝蒂,像贝蒂一样的动物,它不是老在钢琴上睡觉吗,突然它就昏倒了。”说完又笑了起来,搂着小文一块儿笑。
小文说:“咱们走吧,我有点冷。”
他们走出那栋要拆的老房子。小文回头看了一眼大大的拆字。月光下尤为醒目。要是真拆了,他们要去哪里做游戏呢。
他们在小巷子里悠然地走,一前一后,偶尔抬头看下天空。她没有挽着他,他也并不在意。走到了巷子口,那只从树杈里垂下来的灯仍亮着昏黄的光,把他俩的影子拍在地上,拍成两团,又融在一起了。
小文说:“咱们离婚吧。”
阿信身子一抖,说:“你想好了?”
小文没说话,阿信抓住她的手,求她别离婚,看样子马上要跪下了,膝盖不自然地弯曲。小文说:“信不信,我一头撞死,你信不信?”她指着那棵树。
阿信松开了她的手。
他们还是一起回家了。一路无话。进了家门,阿信就喊:“贝蒂,贝蒂,你在哪儿?”贝蒂又在钢琴上睡着了,他抱起它来,小心地爱抚。他小声说:“你怎么总是睡觉。”说完亲了它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