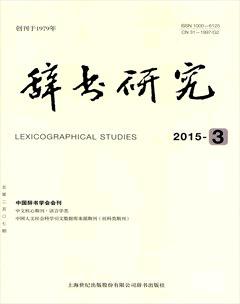汉语词义中的外来义项
侯昌硕
摘要 汉语固有词语从中古就开始从梵语吸收佛教意义,到近现代从英语、日语等外语中吸收新的义项,这表明汉外语言接触中,除了不断吸收外来词,汉语的一些固有词语也在吸收对应的外语词的义项,从而使汉语词语增添了新的义项,丰富了汉语的词义系统。
关键词 语言接触 词义 外来义项
一
不同民族的相互接触必然带来不同语言的相互接触、相互影响,“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最简单的影响是词的‘借贷。只要有文化借贷,就可能把有关的词也借过来”(萨丕尔1985:174)。汉外语言的接触对汉语最直接最明显的影响也在于对外来词的吸收,构词法和句法相对比较保守和封闭,虽然也会受到影响,但影响较小。词义是词的内容,它和语音、语法构成语言最主要的组成成分。在汉外语言接触中,外来概念、意义不断地被借用到汉语中来,一般有三种方式,即借音、借形和借意。借音就是对外来意义连音带义一同借过来,就是所谓音译。其中包括:纯粹音译(如:巴士、沙发),音译加义标(如:卡片、啤酒),谐音音译(如:乌托邦、绷带),半音译半意译(如:因特网、新西兰)。借形,就是把外来意义的书写形式连同意义一起借过来,其中一种是直接借用英文字母的词语,如:AA制、WTO;一种是从日文中直接借用汉字字形,但不借用它的读音。如:干部、手续。借意就是只借用外来意义,而构词语素和构词规则都是汉语自身的,即所谓意译。包括:意译词(如:维生素、民主),仿译词(如:马力、足球)。这三种借用方式,通过借音这种方式借用的外来词语被看成是外来词,是没有争议的,而对于通过借形(主要指日语借形词)和借意词是否是外来词,往往存在较大的分歧,本文暂不讨论。
这三种借用外来概念、意义的方式在汉语中都是以新词的形式出现的,它们为汉语词汇系统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填补了汉语词义的某些空缺。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借用方式,那就是外来概念意义被借用到汉语原有的词语中,而不是另造一个新词。也就是说,汉语原有的某个词语,直接借用与之对应的外语词语的某些义项从而增添新的意义,这就是词义中的外来义项。这些外来义项往往与原有义项并存并用,从而构成了多义词的组成部分。这些新义显然不是由汉语原有词义在本义或基本义的基础上直接衍生发展出来的,所以大多数新义与旧义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这种义项的借用相对前面几种词语的借用,显得更加隐晦和深沉,加之在一般的语言学著作中谈及词义的发展演变时,往往多是讲在本义或基本义基础上引申派生形成一词多义,因此,汉语中一部分多义词里的外来义项的外来身份常常为人们所忽视。
对这种外来词义借用的现象,赵元任(2002:844)早已注意到了:“在翻译外语词的时候,外语里有甲、乙两个意义的词可能等于汉语里只有甲义的词,当外语词用于乙义的时候,这个汉语词也会用来表示它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乙义。……例如‘微妙这个词通常只表示delicate的‘精致‘灵敏等的意思,用于社会或政治形势就讲不通。但是由于英语的delicate还有这种用法,所以现在我们在报上也看到‘微妙用于这个引申的意义。”
伍铁平(1994)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他举例说明汉语的词语“发烧”“爆炸”受到英语词语的影响增加了新的词义,并指出:“通常将外来词分为音译词和意译词两大类,不包括本文所述这种受外语影响获得新词义的现象。这类研究同外来词的研究可纳入‘语言接触学的领域。”
董为光(2004:132)在谈到外来语言以及外来事物对汉语词义理解的影响时指出:“外来词语通过翻译渠道进入汉语,它们所蕴涵的思想观念无形中为说汉语的人接受,也使汉语本土的词语增添了新的意义成分。这种意义移植手段,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汉语词义最直接、最深刻地体现汉民族的思维方式,以及汉文化的历史背景和内涵,因此研究汉语词义系统受到外语的影响、渗透而发生变化,无疑具有很高的语言学价值。
二
其实外来意义被借用到汉语词义中的现象很早就开始了。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大量用梵文书写的佛经相继被翻译成中文,大批佛教词语进入汉语,形成了汉语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外来词的高潮。在翻译佛经时,有一部分佛教思想、概念是用汉语固有词语意译过来的,这样就使得一些汉语固有词语获得了新的表示佛教意义的义项。
词义交融具有不对称性,体现为:A.增加义项;B.覆盖义项;C.减少义项;D.置换义项。(方欣欣2005)佛教意义借人到汉语词语中,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况:
1.增加义项,即汉语固有词语借入新的佛教意义,原义和新义并存并用。如:
功德:本表示功业与德行。《礼记·王制》:“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佛教传人,“功德”获得了一个新的义项,指佛教徒行善、诵经念佛、为死者做佛事及道士打蘸等活动。《南史·循吏传·虞愿》:“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佛图,有何功德!”
寺:本为中国古代官署名,如大理寺、太常寺等;佛教传入,得到新的义项,即用以称僧众供佛和聚居修行的处所,如:少林寺、白马寺。
根:本指植物生长于土中或水中吸收营养的部分。佛教传入,新增义项:用以表示能产生感觉、善恶观念的机体或精神力量。如眼根能生眼识,耳根能生耳识,意根能生意识等。最通用的为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如我们常说“六根清净”。
解脱:原为开脱、解除之义。借入佛教意义,则指解除烦恼业障的束缚而致之自由自在的境地。亦指断绝“生死”原因,同“涅槃”“圆寂”的含义相通。《洛阳伽蓝记·正始寺》:“求解脱于服佩,预参次于山垂。”后来再泛指摆脱苦恼、困境等。
境界:原指疆界;土地的界限。《后汉书·仲长统传》:“当更制其境界,使远者不过二百里。”佛经中的“境界”引申指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无量寿经》:“比丘白佛,斯义弘深,非我境界。”然后再进一步抽象,特指诗、文、画等的意境。
空:本指空虚,中无所有。《管子·五辅》:“公法行而私曲止,仓廪实而囹圄空。”佛教借入的意义很抽象,谓万物从因缘生,没有固定,虚幻不实。《维摩经·入不二法门品》:“色即是空,非色灭空,色性自空。”
2.覆盖义项,即汉语原有词语借入与其本义有关的佛教意义,其原有意义逐渐被冷落,而佛教意义不断加强,成为词语的中心意义,而原有意义反而成为边缘意义甚至很少使用了。如:
因缘:本指机遇。《史记·田叔列传》:“[任安]少孤贫困,为人将车之长安,留,求事为小吏,未有因缘也。”佛教的“因缘”谓使事物生起、变化和坏灭的主要条件为因,辅助条件为缘。《四十二章经》卷十三:“沙门问佛,以何因缘,得知宿命,会其至道。”后来“因缘”又由佛教义派生出“缘分”“人缘”等义。
布施:原指施予;施舍。施恩惠于人。《庄子·外物》:“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佛经中用以专指向僧道施舍财物或斋食。《北史·元太兴传》:“太兴遇患,请诸沙门行道,所有资财,一时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齐。”
修行:本指士大夫按仁义道德去修养德行。《韩非子·问田》:“臣闻服礼辞让,全之术矣;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佛教意义是指出家学佛,即按教义——戒、定、慧三方面修习行持。《晋书·艺术传·鸠摩罗什》:“为性率达,不拘小检,修行者颇共疑之。”
神通:本指人的意识和精神顺畅通达。《亢仓子·用道》:“静则神通,穷则意通,贵则语通,宫则身通,理势然也。”佛教引申指佛、菩萨、阿罗汉等通过修持禅定所得到的神秘法力。《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如来无过功德品》:“何者如来神通智行?答言:大王!沙门瞿昙神通行有六种:一者,天眼通;二者,天耳通;三者,他心通;四者,宿命通;五者,如意通;六者,漏尽通。”后由佛义引申指神奇高超的本领,如“神通广大”。
所以梁晓虹(1994:9)指出:“充分利用汉语的固有词来表示佛教的新内容——‘旧瓶装新酒,则属于佛化汉词。现有词的意义经过有规律的运动变化,从而可用来表示新概念,这语词一般命名的常用方法,在佛典里得到充分运用,使一大批汉语词不同程度地蒙上一层宗教的色彩,丰富了汉语词汇的意义系统。”
从中古佛教思想、概念借入到汉语固有词语中,我们可以看出汉语在吸收外来词的同时,也在利用原有词语吸收外来词义,从而在原词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义项。
三
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汉语吸收外来词又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伴随着大量外来词进入汉语,一些与汉语固有词语对应的外来词的某些义项也被吸收了进来,成为这些汉语固有词语词义的组成部分,丰富了汉语的词义系统。由于它们是在原有词语基础上新增加的意义,往往让人误认为是原有意义引申发展出来的,故其外来身份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这一时期借入的外来词义以英语词义为主。
汉语内部的词义渗透有一种情况是因义同或义近而发生的词义渗透,即如果甲词与乙词核心意义相同或相近,那么,甲词(或乙词)的某一义项就有可能渗透到乙词(或甲词)的涵义范围,从而使乙词(或甲词)也具有这一意义。也就是说如果甲词有A、B两个义项,乙词有一个义项与甲词的A义相同或相近,那么,甲词的B义便也有可能渗透到乙词的涵义范围,从而使乙词也具有B义。(孙雍长1997)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汉英词义的渗透上。汉语词和对应的英语词在意义上存在不完全对应的情况,不仅表现在词的多义现象的参差交错,还表现在同一义项的内涵差异上。由于汉英双方对应的词核心意义相同,用汉语词对译相应的英语词时,英语中跟汉语词义不对应的其他意义就有可能借用到汉语的词义中,从而使汉语的词增添新的义项。如:
“广场”本义是指“面积广阔的场地,特指城市中的广阔的场地”,比如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海的“人民广场”。“广场”对应的英语词是plaza,但是plaza除了这个意义外,还有购物中心、大型商场的意思,即指那些中央有宽敞而高耸的空间,四周有多层连片的商店,集购物、娱乐、办公于一体的商业大厦或大商场。英语plaza的这个义项于是渗透到汉语的“广场”中,所以“广场”现在就有了这个新的义项。不过它先是借入到香港的汉语中,然后再传入大陆,现在大陆各个城市里面涌现出了很多“广场”,如:港汇广场、亚欧广场、隆福广场、世纪广场、东方广场,等等,尽管最初有人对这些“广场”与传统的“广场”不符而不太接受,但逐渐地人们就接受了“广场”的新义,由“广场”构成的词在媒体中出现的频率也随之增加,如:购物广场、美食广场、汽车广场、服饰广场、消费广场、数码广场、商业广场、电脑广场、休闲广场、啤酒广场、海鲜广场、再就业广场、小吃广场、平价广场、商贸广场,等等。
“城”本义就是“城市”,跟这个意义对应的英语词是city。英语city除“城市”义外,还可以指“商业中心”,汉语用“城”对译city,于是也把“商业中心”的意义借过来了,“美食城”就是美食中心。这个意义先在香港使用,20世纪80年代由香港传人内地,当内地城市里出现“香港美食城”的时候,人们还很纳闷:没有城墙,怎么叫“城”?当人们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的时候,接连出现了“鞋城”“家具城”“图书城”“火锅城”等命名为“某某城”的店铺、购物场所。当然现在在内地大大小小的城镇看到“某某城”的时候,人们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因为人们早已经接受“城”的这个新义了。由“城”构成的词语也随处可见,如:服装城、儿童城、灯饰城、电器城、家电城、食品城、小商品城、商贸城、海鲜城、玩具城、家私城、建材城、电脑城、家饰城、华侨城、快餐城、皮具城、洁具城、电影城、金融城、电子城、数码城,等等。
汉语“教父”对译英语的godfather,“教父”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以下简称《现汉》)中有两个义项:①基督教指约公元2-12世纪在制订或阐述教义方面有权威的神学家。②天主教、正教及新教某些教派新入教者接受洗礼时的男性监护人。现在英语godfather还有另外一个词义,指一个组织或团体的发起者,开导者。受其影响,汉语的“教父”也吸收了这一新义,如:金融教父、音乐教父、篮球教父、IT产业教父、苹果教父、保险教父、摇滚教父、时尚教父、职场教父、营销教父、科幻教父,等等。
又如“菜单”对应的英语词是menu。“菜单”在汉语里原来的意义是:“开列各种菜肴名称的单子,多标有价格。”(《现汉》)而英语的menu除了有“菜单”的意义外,还有一个引申义:表示电脑程序命名表、功能选择单,即显示在屏幕上供计算机用户使用的选择单。受英语影响,汉语“菜单”现已吸收了这一引申义,《现汉》对其的解释是:“选单的俗称。”
再如“发烧”对译英语的fever,意义是:发热,即“体温增高”的意思。而英语的fever除了“发烧”的意义外,还有一个引申义:狂热、高度兴奋。受英语影响,汉语中的“发烧”也获得了“狂热”的新义,不过,这个新义也是先在香港汉语中以“发烧友”的形式出现,然后再进入大陆的。如:音乐发烧友、电脑发烧友、游戏发烧友。
“爆炸”对译英语的explosion,意义是:“物体体积急剧膨大,使周围气压发生强烈变化并产生巨大的声响。”(《现汉》)英语的explosion除了这个意义外,还有一个引申义,即“剧增,激增;大规模的、迅猛的扩张(或扩大,发展)”的意义,受英语影响,现在汉语已经吸收了这一引申义,《现汉》释义为:“比喻数量急剧增加,突破极限。如:人口爆炸、信息爆炸、知识爆炸。”
对于“发烧”“爆炸”等词,受英语影响而获得新的意义,伍铁平(1994)说:“我估计,如果不是英语的影响,汉语的‘发烧‘爆炸似乎不可能产生这种转义。”对其他的如“广场”“城”“菜单”等词来说,没有英语的影响,同样也不可能产生现在的新义。因为词义的引申往往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例如英语的ruminate(反刍,倒嚼)引申为“沉思、考虑、熟虑”;与之对应的汉语词“反刍”就不是这种引申义,而是“比喻对过去的事物反复地追忆、回味”(《现汉》)。虽然二者有相似的地方,但英语的引申义强调的是“反复地思索”,而汉语引申义强调的则是“反复地追忆、回味”。目前汉语的“反刍”好像还没有“考虑”的含义。
四
英语词义借入汉语,往往比较容易发现,但是日语词义借入汉语,就不太容易判断了。由于中日两国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日本在其民族文字产生之前曾长期借用汉字记录日语,致使现今日语中仍存有相当数量的汉字词。双方词语相互渗透、交融,有时很难分清彼此。一部分日源汉字词最初可能借自汉语,传入日语后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后来随着中日的交流,这部分新的意义又重新被借入到相应的汉语词中,或者覆盖了原有意义,成为词的基本意义,或者成为汉语词新的义项,与原有意义并存并用。如:
“社会”原有两个义项:①指我国旧时里社举行的集会;②指由志趣相同者结合而成的组织或团体。这两个意义现在都不用了,现在意义是“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和“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现汉》)。这两个意义是从日语借来的,借入以后,“社会”的原有意义就基本不用了。
有的原有意义虽然还在使用,但用得很少了,逐渐成为边缘意义,而借来的意义则成为基本意义。如:
“阶级”原来有四个义项:①台阶;②指尊卑上下的等级;③官的品位、等级;④阶段;段落。(《汉语大词典》)现在“阶级”虽然在《现汉》中还保留有“台阶”和“旧指官职的等级”两个义项,不过这两个意义今天已很少用了,现在其基本意义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和对生产资料关系的不同而分成的集团,如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等”(《现汉》)。这个意义也是来自日语。
近代借入日语意义的词语还有“组织、杂志、劳动、文明、具体、运动、选举、生产、分析、法律、革命、机关、发明、文化”等等。这些词语原有意义都很少用了,取而代之的是借入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日交流频繁,中日语言的接触也越来越密切。受日语的影响,汉语的一些词语正在吸收对应的日语汉字词的意义。不像前面的情况,词语的原有意义被借入的意义覆盖,不用或很少用了,从日语借入的意义成为词语的主要意义,本阶段的汉语词语借入日语的意义,并不是覆盖掉原有的意义,而是与原有意义平行使用,成为汉语词语的一个新的义项,即增加汉语词语的义项,如:
“屋”在汉语里原仅指房子,而日语里的“屋”除了指房子外还可指“店铺”,如:“本屋”(书店)、“酒屋”(酒家、酒店)、“靴屋”(鞋店)。现在日语的这个意义已经进入汉语,随处可见以“××屋”命名的小店铺,如:发屋、饼屋、精品屋、鞋屋、面包屋、咖啡屋、美食屋、服装屋、洗脚屋、图书屋、茶屋、休闲屋、比萨屋、酒吧屋、首饰屋,等等。
“族”除了我们熟悉的“家族”“种族”“民族”等义外,现在还多了一个意义,即表示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的一类人,如“追星族”“上班族”等。这个意义也是来自日语。20世纪70年代,日本一位作家写了一部小说叫《太阳的季节》,书中描写当时年轻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等,影响很大。后来人们就以“太阳族”来称像书中所描写的年轻人那样生活的人群。随后“族”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经常用来指称某一群体。“族”的这个意义和用法先被港台地区吸收,然后再进入大陆,现在已成为一个非常能产的构词成分,如:打工族、外来族、工薪族、手机族、有房族、休闲族、素食族、推销族、集邮族、钓鱼族、炒股族、单身族、哈日族、哈韩族、网络族、爱车族、下海族、减肥族、丁克族、海归族、泡吧族、飙车族、有车族、驾车族、刷卡族、持卡族、本本族、外卖族、失业族、练摊族、SOHO族、移民族。不过这里的“族”只能做语素,所以其意义是语素义。
五
从早期的佛教意义进入汉语固有词语中,到近现代英语、日语等外语词义被借人到汉语相应词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古至今,汉语在与其他语言的接触过程中,在不断吸收外来词语的同时,一些汉语固有词语也在吸收对应外语词的意义,从而使汉语词义增加新的义项。这些新义项或者与原有义项并存共用,或者取代原有义项而成为词义的基本意义,使原有意义成为边缘意义甚至很少使用。这些外来义项与汉语原有义项往往融为一体,成为词义的一部分,丰富了汉语的词义系统。虽然这些外来义项来自外语,但它们没有相应的词形,加上它们已与汉语原有词义融为一体,所以其外来身份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杨锡彭(2007:117)指出:“外语词的语义发生引申、转喻等变化,汉语中与之同义的成分借助于意译而随之发生语义变化,是汉语语言成分语义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汉语语言单位随着同义的外语成分的语义的引申、转喻等变化而发生语义变化,这一语义发展的形式似乎还没有引起注意。”虽然在本义或基本义基础上通过引申发展出新的词义,始终是词义发展变化最主要的途径,但是像这样由于外来语的影响而使汉语词语增添新的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现在中外交流日益频繁,语言接触越来越密切的背景下,外语词义很容易进入到相应的汉语词语中而成为汉语词语新的义项,这是值得关注的。
(责任编辑 李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