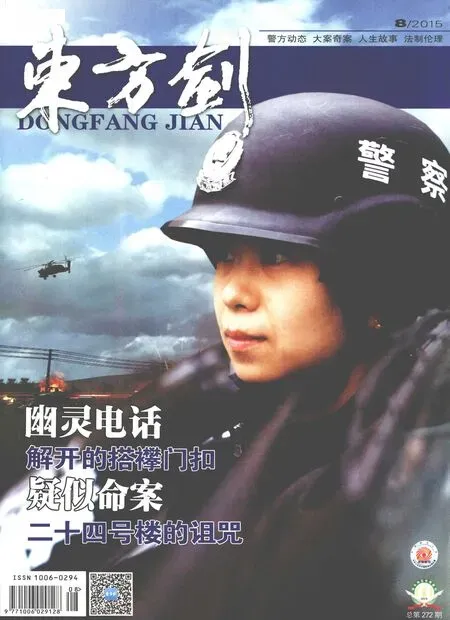深 渊
◆ 昆 金
深 渊
◆ 昆 金

一
刚才狱卒送来一套干净衣裤,一顿丰盛午餐,语气神态中也分明有了一些微妙变化。这些都没有逃过鲁挺的感知,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午后就要被执行死刑。
因为他杀了于文秀。
仔细想想,于文秀应该是鲁挺在青春期唯一暗恋过的女生。
八年前,于文秀跟着经商的父母从浙江来沪,就插班到了鲁挺的班级。鲁挺至今记得,那是一个困意浓重的早春下午,阳光刺眼。上课铃响起后,于文秀上衣下裙,笑盈盈跟在马先生身后走进教室时,他就觉得整个世界突然闪亮了一下,犹如夏夜里一道流星划过天幕。窗外吹进的微风随即变得格外凉爽,树枝上叽叽喳喳的麻雀也顿时安静下来。于文秀在讲台跟前落落大方的自我介绍,更是犹如天籁,在鲁挺的心田里萦绕开来,让他浮想联翩,以至于他根本没有听清于文秀说了哪些得体从容的客套话。而当他从遐想中醒悟过来时,马先生已经带着于文秀走到鲁挺跟前。
鲁挺慌张,猛然站起,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全班同学都看到了他的窘迫相,哄堂大笑起来。最后还是马先生拍拍他肩头,才让他有了一个坐下来的台阶。
鲁挺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慌张中抬头一瞥,意外看到于文秀正微笑着注视自己。但她的笑意中充满了热情、温馨和善意,丝毫不似其他同学的嘲笑那样刻薄。此时此刻他似乎受到了鼓励,竟然跟她对视了几秒钟,之后才败下阵来, 只顾低头用指甲戳着桌上的砚台,懊恼自己的脸色为什么会这样不争气地通红一片。
最后于文秀被安排在鲁挺前排,跟另一个经常给他脸色看的女生同桌。从此也让鲁挺的内心世界开始翻天覆地。
想到这里,鲁挺的眼前突然变得禁缥缈起来。漆黑肮脏的牢房也似乎变得喧闹而明亮。他觉得自己再次坐在课堂里,四周尽是同学和先生的影像,于文秀就坐在他前面,周身被一个淡淡的光环笼罩着,格外清晰。
鲁挺平时极少跟同学们说话,也没有特别要好的同学。他没有同桌,因为没有人愿意跟他同桌。同学们跟他近在咫尺,气息相闻,却分明有一层看不到却感受得到的漠然鄙夷。
他喜欢一个人看书做作业,然后就安静地坐在位子上,看同学们在自己四周说话走动。他记得每个同学的一笑一颦,记得他们对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记得他们吃饭写字开心发怒时的模样,以及每天的衣着更替。在这个世界里他明察一切,却始终无法融入其中。他就像个透明人,没有人关注他的存在,也没有人在意他有没有来上课,中午饭带的是什么菜。而他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反正他已经习惯。
但文秀来了以后,这样的状态就被打破。
鲁挺总觉得于文秀看待自己的眼光有些特别。她是唯一愿意跟自己直视并且微笑轻声说话的同学。鲁挺习惯了这个被人藐视欺凌的氛围,所以于文秀的目光让他多少有些受宠若惊。从那个时候起鲁挺也开始关注起自己来。因为他不知道于文秀会在什么时候冷不丁回头看他。至少在文秀直视他时,尽量改变一些自己那种生硬刻板的呆相。
从那个时候起,鲁挺会在磨墨时特别小心,尽量避免砚台里的墨水洒到桌面上。盛放有墨汁的砚台和笔格也尽量摆放在靠近自己的一端。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墨汁沾染到于文秀的长发上。文秀的长发滋润油亮,瀑布似的垂落在自己的桌面上。一甩头时,发梢时常会在鲁挺的桌面上横扫而过,轻轻巧巧,犹如一阵春风拂过,留下几分芳香。看得鲁挺心都醉了。
鲁挺时常会成为同学们的嘲笑对象。每一次的嘲讽和羞辱都会被他无声吸纳,然后默默消化。因为对他而言,这是唯一一种息事宁人的办法。他从来也没有过想要反驳的冲动。但文秀却非常反感同学们这样对待鲁挺。因此每次有男生想糟蹋鲁挺时,文秀就会挺身呵斥,替鲁挺解围。顽皮的男生们在漂亮愤怒的文秀跟前只有赔笑的份,因此也就不敢再对鲁挺放肆。鲁挺由此扬眉吐气,并慢慢明白何为自尊,何为自强。
但就是这样一个热情漂亮且看上去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女生,却在八年后的一次同学会后,被鲁挺亲手杀害。想到这些,鲁挺一下子恍惚起来。他觉得这一定是梦,但又明白这不是。
二
该从哪说起呢?
那次同学会是班主任马先生发起的,所以鲁挺也收到了邀请函。按鲁挺的本性,他不会参加任何应酬,但看到名单上有于文秀,顿时又令他改变了主意。
在这八年里同学们男婚女嫁,鲁挺依旧孑然一身。独身的原因很多,但很大程度上竟然是因为鲁挺自己。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保留着那道充满善意和热情的目光。遗憾的是这道珍贵的目光只存在于记忆当中,现实生活中的鲁挺,依旧跟学生时代一样,是个被鄙视和被羞辱的对象。他有时候觉得自己是在奢望什么,但随即又觉得这不是奢望。因为他曾经真真切切地遭遇并享受过这种奢望。
而这次同学会却可以令他重温那份久违而又温暖的关切和爱护。这怎么不让鲁挺翘首以盼呢。这份温暖陪伴了他八年,却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它让鲁挺在这些年里始终不觉得生活有多么的艰辛黯然,忘记了曾经以及正在经受着的任何挫败和无望。每次想起,都会令他信心倍增,并沉浸于这份虚无而遥远的力量当中。是的,这是一种力量。
鲁挺在同学会上的出现,一如八年前一样,并没有在同学中间引起多大的反响。仅有的几个问候,也透着一股浓重的敷衍。但这些鲁挺都不在乎,因为他已经习惯这种遭遇。
那天于文秀迟到了,但却丝毫不影响同学们对她的欢迎程度。当于文秀踏进房间时,现场的同学们沸腾起来。而鲁挺也再次感觉到天际间闪亮了那么一下。
于文秀还是那么的漂亮。她的微笑比以前更加恬静而富有感召力。晚餐时文秀大大方方跟每个同学敬酒寒暄。当她走近坐在角落里的鲁挺时,鲁挺就很自然想起文秀第一次走近自己时的那种感受。
“鲁挺,你也来了。”文秀的声音没有变。
“你,你好文秀……”鲁挺支吾着,先前准备好的各种问候措辞此时不知道跑哪去了。同学们一如之前地开始嘲笑起鲁挺来。
于文秀看着鲁挺的窘迫相,笑笑:“鲁挺,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挺好的,你呢?于文秀同学。”
“我也很好呀。”于文秀笑着,然后就被其他同学喊走了。
鲁挺眼看着文秀离开,心满意足。从此后他无论怎么看文秀,都觉得她对别人的微笑,总是不及跟自己微笑时那么真挚,那么深情,那么清澈。
晚饭后大家相邀去了外滩吹风。鲁挺落在后头,遍寻不到文秀,心中烦恼,最后总算在外白渡桥上看到了她。此时夜色阑珊,华灯初上,桥上滞留了好些看风景的人,文秀和几个男女同学就混迹在一大片人群里。凭栏远望,说说笑笑。
鲁挺鼓足勇气,悄悄接近人堆。谁也没有发现他。
于文秀和同学们聊得很开心。昏暗灯光之下,她的笑容还是那样的璀璨热情,一如这美妙的夜色。鲁挺看得醉了,忍不住就继续朝前走了几步,一直接近到可以听见他们的交谈声。
有个叫杜维的男生在说话:“文秀,那么多年了,你怎么还没有结婚?”
文秀笑笑:“别说我,你不是也还单身着吗?”
另一个叫杨修的男生打趣:“文秀同学那么漂亮,自然要寻一个可以跟她匹配的郎君了。”
文秀还是笑笑:“你们都别瞎想。我这几年去了欧洲,也刚回国不久。婚配这件事,一则没有机缘,再则也无暇顾及。就这么简单。”
杜维想了想说:“那现在回国了,工作也稳定了,你就别再矜持,给老同学们一个机会好不好?你可是我们班男生的大众情人呀。”
大家笑。杨修想了想说:“其实我早就发现,当年文秀跟班上某位同学的关系最好。”
杜维在意:“哦,这位幸运者是谁呀?”
杨修:“说出来大家一定不会相信。是鲁挺。”
站在不远处的鲁挺听得分明。黑暗中他的腿肚子当时就软了一下。
大家惊讶。纷纷用猜疑的目光望向于文秀。于文秀有些哭笑不得:“杨修呀杨修,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跟鲁挺关系最好了?”
杨修:“难道不是吗?你跟我们相处时总是很强势,但每次跟鲁挺说话时就会变得极其客气,眼神中也充满了温情。这些你能否定吗?”
不远处的鲁挺听见,顿时有些把持不住自己的眼泪。一刹那间,于文秀的微笑清晰显现在他跟前。
于文秀回忆了一下,突然大笑起来。这一阵大笑,当时就把大家给笑懵了。
杨修:“笑吧笑吧。被我说中,无可反驳了吧?”
于文秀止笑:“好吧,你们说我对鲁挺好,这我承认。但我跟他绝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种关系。”
杜维急:“没听懂,你说明白些好吧。”
于文秀:“我之所以对鲁挺好,是因为你们对他实在是太过分了。鲁挺是个内向敏锐的人,生性懦弱,胆小,我就是看不得这样的人受欺负,所以才要站出来阻止你们对他的欺凌。”
不远处的鲁挺听得目瞪口呆。
杜维:“除此之外,你就真没别的意思了?”
于文秀:“笑话。你们真觉得我跟他合适吗?”
大家想了想,纷纷摇头。
杨修:“原来是这样。文秀你也别怪我瞎想。我也是在偷看了鲁挺的日记以后才这样以为的。”
于文秀:“你还偷看别人的日记本?这也太过分了。”
杨修笑笑:“这有什么。就是被他发现了,也奈何不了我。”
于文秀怒:“你们就是爱欺负他。那么你在日记里看到了什么呢?”
杨修:“现在看来,你当年的所言所行,已经深深被他误解,就像我们误解了你一样。鲁挺在日记中,早已经把你当成他的恋人,而且也想当然地以为你对他也是一片真诚。”
于文秀惊讶:“真的?”
杨修:“这还有假。不信你看,这就是鲁挺当年的日记本。我看到这些事后本来想找你核实,因为我也一直暗恋着你,文秀,但后来我又觉得开不了口,所以就把这事搁下了。但鲁挺的日记本我一直保存至今,无他,只是觉得很好奇,就想找个机会核实一下,你究竟喜欢鲁挺什么?”
“杨修,你说你当初一直在暗恋着我。那我怎么一点都感觉不到呢?”于文秀笑着说。
大家都开始起哄。杨修有些不好意思:“哎呀,那个时候我胆子小,再加上你又那么优秀,我哪里敢自讨没趣呢。”
大家再次哄笑。
杜维:“哎,杨修,那现在你可以好好准备一下,正儿八经地追求于文秀啦。”
于文秀:“哪有你们这样起哄的。都快别说了。”
于文秀说着,从杨修手里接过鲁挺的日记本,翻阅,脸色惊讶:“这个鲁挺,对我还真是误会不浅。哎,我当时只是觉得他很可怜,是班级里最弱的一个,于心不忍,就想着站出来护着他些,让他少受些羞辱欺凌。仅此而已呀。”
不远处的鲁挺早已经羞愤难当了。
他当年的确丢失过一本日记本。因为记载着很多有关于文秀的内容,所以他印象深刻。后来时间久了他也渐渐淡忘。没想到却是被杨修私藏。更加令他难堪和绝望的是,于文秀并不爱自己,她只是可怜自己,所有关于于文秀的良辰美景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这个发现令鲁挺沉痛无比,甚至比遭受当面回绝或者呵斥更加令鲁挺无地自容。顿时,那么多年来所有的温馨回忆,正在慢慢变得冰冷和坚硬起来。一股浓厚的羞愧和痛楚自心底涌起,差点令他呛不过气来。
趁着夜色,鲁挺落荒而逃。
三
然而鲁挺又觉得这件事委实蹊跷。于文秀的那份柔情目光,从八年前到八年后,一直都没有任何变化,这怎么可能不是喜欢自己的真情流露呢?于文秀会不会是在骗杨修他们呢?
他决定亲自找于文秀问个明白。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这份勇气,或许因为这是多年来唯一令他祈盼并获得无限慰藉的一件事。从某种程度上说,要没有这份祈盼和温暖,鲁挺或许撑不到现在这个时候。
于文秀租住的地方并不难找。这个地区属于高档公寓,幽静而整洁,平时进出人员更是稀少。鲁挺走到公寓楼梯口时,却有些胆怯起来。
一旦碰见于文秀,他又该如何开的了那个口?
正在犹豫,突然看到有个人影从楼梯口出来,仔细一看,竟然就是杨修。
这个混账偷走了自己的日记本,并公布于众,也等于是把自己内心最隐秘最脆弱的部分当众撕开,这令鲁挺无地自容,又痛彻心扉。
鲁挺目送杨修消失,竭力想象着杨修和于文秀在一起时的情景。看来杨修已经开始追求于文秀了。一股难以言表的情绪涌上,令鲁挺鼻子一阵酸楚,几乎失控。片刻,他努力镇静,疾步走进了公寓楼梯。
敲门声过后,于文秀出来开门。看到鲁挺,她也似乎有些意外,但还是把鲁挺迎了进去。
于文秀的家里不大,但却布置得非常温馨舒适。鲁挺就在一张桌旁坐下,扭头见桌面上散放有一大堆瓜子糖果。旁边还摆放有一个泰康公司的金鸡饼干铁盒。另外还有一个玻璃鱼缸放在一边,浅浅小小的鱼缸里有两条小金鱼在里面乱窜,似乎并不适应这个狭小的空间。
于文秀给他倒了杯水后,便坐在鲁挺对面,热情招呼他吃些瓜子,又给他剥了一粒水果糖。她的长发依旧那么秀美,微笑还是那样温馨友好,犹如一股甘泉,灌入鲁挺的血脉之中。他感觉非常的好。
“鲁挺,怎么想到要到我这来呢?”于文秀开口问。
鲁挺支吾:“于文秀,我们同学一别八年,我想过来问候一声。”
于文秀噗嗤一笑:“鲁挺,你可真有意思。同学聚会我们不是相互问候过了吗?好吧,你喜欢这样也行,谢谢你的问候。”
于文秀的轻松神态,有些令鲁挺放松下来。他呵呵笑着:“于文秀,你还是跟念书时一样,是大家追捧的偶像。”
于文秀笑了:“鲁挺,你现在也学会讨好人了。”
鲁挺摇摇头:“我一点也没有夸张。于文秀,你对我还是那么的好,我谢谢你。”
于文秀似乎感觉到了某种弦外之音。她顿时想起杨修在外白渡桥上所说的那些话。看来鲁挺对自己果真已经滋生出了某种情愫。
“鲁挺,其实我们之间恐怕有些误会……”
“别说下去了!”鲁挺突然猛喝,制止了于文秀的话。于文秀抬起头,只看到鲁挺的眼眶里已经有些闪亮起来。她顿时就有些气馁,但又不想就此沉默下去。
“鲁挺,我不想让你一直误会下去!”
“于文秀,你对我果真只是可怜和同情吗?你们在外白渡桥上的交谈,我都听见了。”鲁挺的声音有些哽咽。
于文秀即便于心不忍,此时她也不得不让自己冷酷起来。
“没错,鲁挺。我那些都是大实话。如果因此让你误解,或者伤心,我向你道歉。”
鲁挺潸然泪下。他突然觉得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他的脸色由红色渐渐变换成青色。
于文秀望着鲁挺,不知所措。
“你们可以无视我,鄙夷我,甚至欺凌我,这些我都可以视作是你们的无知和无理,是你们的个人修养问题。但我绝不要任何人的怜悯,更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同情。因为这样只会放大我的痛楚,放大我的无能和懦弱。逼着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所面临的悲惨现状。”鲁挺哀嚎着说道。
于文秀震惊了:“鲁挺,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真的很奇怪。”
说着于文秀转过身去,准备走开。鲁挺突然操起桌上的玻璃鱼缸,一挥手就把里面的金鱼和水朝窗外泼出,然后舞动鱼缸,狠狠朝于文秀的后脑勺砸去。
于文秀被击中,摇晃了一下,扑通倒地。
鲁挺眼睁睁看着于文秀倒地,眼珠子几乎就要从眼眶里爆出来。他大口喘息着,蹲下身,眼看着鲜血一点点从于文秀的头发里渗出、流淌开来。
四
这个案子很快便落到周凤岐手里。
案件中有两个嫌疑人,一个叫杨修,另一个叫鲁挺,跟死者都是同学关系。这两人之所以会成为嫌疑人,全是因为他们都主动在案发后向巡捕房报警的缘故。
那个杨修说他当天去了于文秀家两次。第一次去于文秀家后片刻就离开了。再次回到于文秀家时,就看到她已经倒在血泊之中。
而那个叫鲁挺的人则说,他在进入于文秀家之前,就看到杨修慌慌张张从于文秀家出来。等他走到于文秀家时,发现房门虚掩,他喊了两声,便推门而入,结果发现于文秀已经死了。
从问询中周凤岐得知,鲁挺看到杨修从于文秀家出来,是杨修第一次从于文秀家出去的那次。实际上当鲁挺离开于文秀家后,杨修又返回到了于文秀家,并发现尸体。所有这些进出的先后秩序和次数,都被前排公寓里一个在后阳台上闲坐的老太太目睹。两人在进出于文秀家这一点上至少都没说谎。
这样一来,两人的报警也就成为一种很特别的相互指认。因为他们各自的陈述,让对方顿时就成为了案件中的凶杀嫌疑人。于是两人就双双被拘押了起来。这种情况还真不多见。
两人都叫冤。
这个案子的关键点是,这两人分别进出于文秀家,间隔的时间很短,因此单凭于文秀死亡时间来判断谁是凶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另外周凤岐还走访了好些人,对死者和两名嫌疑人的基本情况都有所了解。
“杨修,当天你去于文秀家干什么?”周凤岐把杨修调出拘押室,开始盘问。
“这次同学会后,我意犹未尽,想找于文秀进一步发展关系。从做同学那会起,我就一直喜欢着她。”杨修道。
“你喜欢于文秀,但她的态度呢?”周凤岐追问。
“她……她应该也喜欢我的吧。”杨修有些把握不住。
“应该也喜欢?杨修,这种事可以靠猜的吗?我怎么感觉你根本就是一头热呀。”
“好吧,就算是我一头热,那我也不至于跟这起凶案牵扯到一块呀。”杨修很不耐烦的样子。
周凤岐注视着他,缓缓道:“不,如果你真是一头热的话,事情很有可能朝着不可预知的方向发展。古今中外,由爱及恨所酿成的悲剧,那就太多了。”
杨修一听就急了:“探长,你可不能这样胡思乱想。我真没杀人,你一定要相信我。”
“你嫉妒鲁挺吗?”周凤岐继续追问。
“嫉妒?我干嘛要嫉妒鲁挺?”杨修纳闷。
周凤岐紧盯着他:“因为于文秀很喜欢鲁挺,而鲁挺也中意于文秀。这对你而言,绝对不是个好消息。”
“胡说八道。于文秀根本就不喜欢鲁挺,只是同情他而已。这是于文秀亲口跟我说的。”
“我找过当晚跟你和于文秀一起去外白渡桥聊天的几个同学,得知于文秀的确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我又走访了你们班的大多数同学以后,却得知于文秀当年对鲁挺非常爱护亲近。这样我就有了一个疑惑,于文秀究竟是真心喜欢着鲁挺,还是只是出于同情?因为你要知道,于文秀即便真心喜欢着鲁挺,她也可以在你们面前不承认这一点,然后搬出‘我对他只是同情’类似的理由来敷衍你们。”
杨修不耐烦了:“我没工夫跟你扯这些。你现在要么拿出证据证明我是犯罪,要么赶紧把我放了。”
“我还听说你在念书时,曾经偷走过鲁挺的一个日记本。恰好这个日记本里满满记载着鲁挺对于文秀的好感,是吗?”周凤岐不紧不慢追问。
杨修一愣:“这你都知道?对,没错,有这事。”
周凤岐注视他良久:“在你们三人之间,你的处境很微妙。这样,你把你两次进入于文秀家的经过再跟我说一遍。”
“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我要的是细节。从你一踏进于文秀家开始,越详细越好。”
杨修无奈:“第一次进门后,于文秀很热情招呼我。然后她准备烧水泡茶,却发现茶叶用完了。我这才发现她很喜欢喝茶,就想起家里还有几斤好茶,就跑回去拿茶叶了。”
“那桶饼干是你带来的礼物吗?”
“是。我带了一桶金鸡饼干,一篮子水果。对了,于文秀念书时非常喜欢金鱼,所以这次我还给她带了两条金鱼,讨她欢心。”
“你倒是挺来事的。”
“哎,追女孩子么,怎么可以没些情趣和想法呢?”
“于文秀是怎么招待你的?”
“她拿出了好些瓜子糖果,还没来得及泡茶。”杨修回忆。
“那两条金鱼于文秀喜欢吗?后来是怎么处置的?”
“于文秀很喜欢这两条金鱼。我就用盛放瓜子糖果的那个大玻璃盘子接了点水,再把金鱼放了进去。”
周凤岐恍然:“难怪我看到现场瓜子糖果都直接堆放在桌上了。后来呢?”
“后来于文秀准备泡茶,然后就发现茶叶没了,然后我就出去了。那两条金鱼就一直养在玻璃盆子里。但当我第二次回来时,玻璃盆子上有很多血迹,显然已经成为了凶器,里面的金鱼也不知所向。真是个悲剧。文秀,你死得可真是太冤了。”
“等你第二次回来时,当时是个什么样的场景?”
“我看到于文秀倒在地上,脑袋以及地上很多鲜血。那个糖果盘子就搁在桌上。”
周凤岐想了想,道:“这个厚实的玻璃盘子很明显就是凶器。关键是上面全都是你的指纹。杨修,这件事你想摆脱嫌疑,必须花大力气了。”
杨修急:“屁话,我曾经拿着它盛放金鱼,当然会留下指纹痕迹。你就不能用脑子想一想吗?”
“你当然可以这么说,我也不是完全无视你这个理由,但从实际角度看,这对你是极其不利的。”
说完这话后,周凤岐长久注视着杨修。心里暗暗盘算着眼前这个青年跟自己心目中的罪犯有多少重合度。
五
暂时告别了杨修,周凤岐又把鲁挺叫到跟前询问。
“鲁挺,你跟于文秀的关系怎样?”周凤岐开门见山。
“我喜欢于文秀,她对我也一直有情有义。”鲁挺说完这话时,目光中似乎闪亮了一下。
“鲁挺,那么你当时去找于文秀,是准备去表白吗?”周凤岐继续问。
鲁挺沉吟片刻,点头:“是的。这份勇气我酝酿了整整八年。”
“你说你走到于文秀家附近时,刚好看到杨修慌里慌张跑出楼梯?”
“没错。”鲁挺的声音很轻。
“你进去以后,看到了些什么?尽量说得详细一些。”周凤岐耐心问。
鲁挺想了想,目光始终低垂着,良久才说:“我进去以后,就看到于文秀躺在地上,头发里沾满了血,地上也是。我走过去仔细看了看,又试探了一下她的脉搏,这才知道她死了。”
“还有呢?”
“我当时很害怕,也很难过。起身后我在屋子里外找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人。”鲁挺说到这里,眼眶似乎有些闪烁起来。
“你还看到些什么?没事,你想起什么就说什么,我就想从中找到些有用的东西。”
鲁挺打量着周凤岐,微皱眉头,继续道:“我看到桌上有个饼干桶,还有一些瓜子糖果什么的。对了,桌上面还有个鱼缸,鱼缸上也有血迹,应该就是凶器。我当时突然感觉自己或许会有麻烦,便赶紧跑出去,给巡捕房打了电话。”
鲁挺絮絮叨叨说了很多,周凤岐仔细聆听,一时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现在看来,鲁挺喜欢于文秀是可以肯定的。八年前的那个日记本,周凤岐也已经拜读,但问题是于文秀究竟喜不喜欢鲁挺呢?
如果鲁挺痴心暗恋于文秀,而于文秀却仅仅是出于同情才这样对待鲁挺,那么这对鲁挺而言绝对是个天大的打击。尤其是鲁挺那种忧郁乖张的性格,更加容易做出一些过激极端的行为。因此他出于激愤,绝望,倒是具备杀害于文秀的动机。
至于杨修,他看上去很喜欢于文秀,但至今得不到任何进展,而且八年来一直以为于文秀喜欢的是鲁挺。这次他听于文秀说她对鲁挺只是同情,说不定就信心百倍准备努力一把。而这个时候如果于文秀拒绝的话,杨修会不会因爱生恨,一怒之下对于文秀下毒手呢?从了解到的情况看,同学会当晚杨修对于文秀旁敲侧击甚至是直言不讳的进攻,并没有得到于文秀的任何响应。这说明于文秀喜欢杨修的概率也是极低。
所以这两人都具备因爱生恨,一时冲动铸下大错的潜在因素。凶手用那个沉重的玻璃器皿行凶,很可能就是一时愤怒,临时起意,顺手操起个什么东西就下手了。
而两个都具备杀人动机的人,在相隔很近的时间内先后接触被害者,这确实让人很难分辨。
从相互关系以及个人性情等因素考虑,周凤岐感觉鲁挺作案的可能性要相对大一些,但他找不到支持这种想法的证据。
想要寻找证据,还是要回到案发现场,以及两个人各自的陈述内容这方面来寻找突破口。为此周凤岐重新来到于文秀的家里。
案发现场依旧保持着原样。因为不通风的缘故,房间里隐隐还有一股子血腥味道。于文秀倒下的地方被一道白圈勾勒出来,桌上的东西除了那个凶器,其余都还保持着原样。
周凤岐看着房间里的景致,脑子里努力回忆两名嫌疑人各自的陈述。
突然之间,一个念头跳入他的心田,令他顿时如被当头浇淋了一桶冰水一般。
周凤岐回到巡捕房,拿出那个致于文秀死亡的凶器。然后他又把巡捕房里所有可以叫到的人全部集中到他办公室里。很快就有一二十个人到场,却不知道周探长要干什么,纷纷猜测。
周凤岐站在大家跟前,拿出那个凶器,开口:“我知道大家都有工作要做,但我不得已必须请大家帮我这个忙。”
大家说周探长你有事尽管说便是。
周凤岐举起凶器:“请大家来辨认一下,我手里这是什么东西?你们相互之间不要交流。”
大家朝他手里望去,有些奇怪。
“这不就是一个玻璃盆子么。”
“我知道,这是盛放瓜子糖果的玻璃盆。”
“是不是烟灰缸?”
“我家也有一个,确实是摆放瓜子糖果的。”
……
大家七嘴八舌,说了各自的看法,周凤岐让助手小赵记录着,不动声色。
等大家说完以后,周凤岐又拿起这个玻璃器皿:“非常感谢大家。其实我也同意这就是一个摆放瓜子糖果的玻璃盆子,但是我想问问大家,这为什么不会是一个玻璃鱼缸呢?”
“鱼缸没有这样的。”
“这个玻璃盆子胎厚而且花哨,深度又浅,只能用来装些干货。做鱼缸显然不合适。”
……
大家随后又叽叽喳喳说了一通。总之没有一个人同意这会是一个鱼缸。
周凤岐想了想,面露恍然。
六
“鲁挺,你说你进门后就看到于文秀的尸体,然后又看到那个被当成凶器的鱼缸,是吗?”周凤岐重新找到鲁挺,询问。
鲁挺纳闷,但还是点了点头:“没错。我已经说过两次了。”
周凤岐想了想,笑笑:“经过痕迹对比,于文秀确实是被那个鱼缸砸死的。这一点没有异议。但是鲁挺,你肯定那就是一个鱼缸,对吗?”
鲁挺:“那当然……”
周凤岐长舒一口气:“这样看来,本案的凶手,也只能是你了。”
鲁挺一时还没缓过神来:“周探长,你说什么呢。”
周凤岐注视着鲁挺:“还不准备承认吗?那好,我问你,你说你走进房间,于文秀就已经死亡。然后你又看到了桌上的凶器。但问题是,你凭什么说桌上的那个凶器是鱼缸呢?当时这个玻璃盆子里并没有金鱼,现场也没有任何可以证实这是一个鱼缸的线索,那你是凭借什么来判断的呢?”
鲁挺暗暗倒吸一口凉气。他想了想,努力镇定:“我就这么随便一说。它的样子很像是鱼缸么?”
周凤岐摇摇头:“你说这个盆子很像鱼缸,这一点我有充足的理由反对。因为我做过调查,前后几十个调查对象,没有人在第一眼看到盆子后觉得这是一个鱼缸,所以鲁挺,你把它当成鱼缸,一定是另有原因的。”
鲁挺欲言又止。神色渐渐有些恐慌起来。
周凤岐理了理思绪,开始对鲁挺作最后的总攻:“这个玻璃盆子原本就是用来盛放瓜子糖果的。只是因为在你到达之前,杨修给于文秀买来了两条金鱼,可于文秀那边没有现成的鱼缸,于是杨修才不得已把瓜子糖果倒在桌上,把金鱼暂时放了进去。现在我们已经证实这个玻璃盆子就是凶器,如果我们假设当你进去以后于文秀已经死亡,那么凶手必定就是杨修无疑。但问题是如果杨修用这个盆子砸死了于文秀,那么当你进来以后,你就没有理由把这个盆子跟鱼缸联系起来。除非有一种情况例外。”
“什么情况?”鲁挺有些恍惚起来。
周凤岐注意到了鲁挺的神态变化:“除非是当你走进于文秀家时,那个玻璃盆子里分明养着两条金鱼。这样你把这个凶器认作鱼缸,也就合情合理了。”
鲁挺的汗就出来了。
“而事实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也就可以判断,当你进入于文秀家时,如果玻璃盆子里的金鱼还在,凶案也必定尚未发生。那么杨修也就不可能是罪犯。因为我们在于文秀家窗户外找到了那两条金鱼,足以说明案发后金鱼早就被泼出窗外,所以鲁挺,你从头到尾一直在说谎。”
鲁挺的表情在一刹那间风起云涌。
“事件的真相很可能就是,你走进于文秀家时,于文秀安然无恙,杨修也只是出去拿茶叶了,桌上玻璃盆子里的两条金鱼还在。然后你跟于文秀聊了一阵,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你就拿起正以鱼缸的形式出现在你眼前的这个糖果盆子,把于文秀砸死。这样在你的印象中,凶器很自然就应该是一个鱼缸了。杨修自始至终都说这是一个糖果盆子,只有你一口咬死这是个鱼缸。因为这个东西从进入你的视线开始,就一直以鱼缸的形式出现。你自然就会这么认为。而这恰恰就是你露出的最大破绽。”
鲁挺的喉咙里一阵响动,长久沉默。
“鲁挺,你那么喜欢于文秀,于文秀对你又那么的仗义。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待她?”周凤岐很想知道真相。
鲁挺黯然:“同情和怜悯,有时候比欺凌和压迫更可怕,更容易让人崩溃。人有时能够忍受各种痛苦,但却无法承受这种痛苦被揭示。”
周凤岐百思不解。
发稿编辑/冉利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