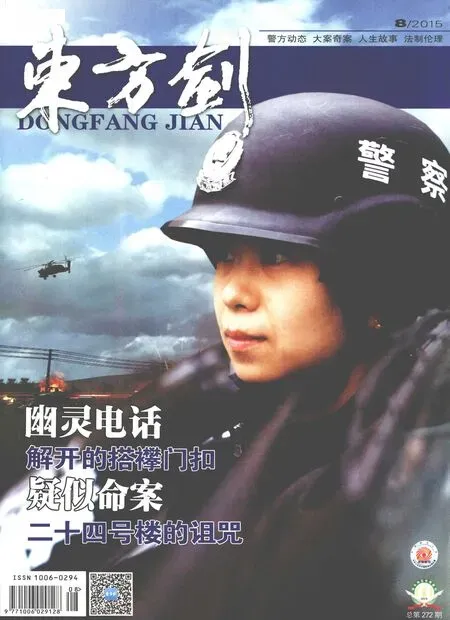他毕竟是个人
◆ 刘永飞
他毕竟是个人
◆ 刘永飞

真没想到,十年之后他还认得我。只是快半天了我才想起他是谁。
这个人叫马本德,当他见我一时间记不起他来,一下子愣住了,不过片刻他就调整过来了,他挠挠头说:“哎呀,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十年前,马家镇的副镇长开车撞死了我家的牛,这货不但不赔我钱,还让我给他修车,这事儿也不知道您怎么听说了,就到我家来采访,说要帮我主持公道,这事儿您总还记得吧?”
“哦,哦。”我想起来了,但同时,我却感到十分羞愧。
那还是十年前的一天,在县委当秘书的同学来找我,求我帮个忙。他说,他舅舅驾车撞死了一个农民的牛,当时他舅舅喝高了些,就说了些“醉话”。偏偏这个农民是个“一根筋”,逢事儿总喜欢讨个说法,这不,他声称要去省里市里讨个“说法”,可眼前正是他舅舅升镇长的关键期,所以来求我帮个忙。
我说,你县委秘书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我这个县报记者能解决什么呀。他说,你去采访采访他,说要把这个事情在报上发一发,替他主持公道就可以了。我说见了报岂不是更糟糕?他说哪能真见报呀,我们就是陪他玩玩,拖住他去上访的步伐,只要过了这个时间点也就随他了。再说了,再刁的民毕竟还是个民!
以后的事儿我就不太记得了,只记得马本德比现在瘦,他当时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让他赔牛钱,难道让他道个歉都不中?”
我当时也是哥们义气,没有是非观念。当然,马本德最终也没去上访,而同学的舅舅也顺利地当上了镇长,可谓皆大欢喜。
可是今天再遇马本德,他口口声声请我吃饭报我恩情,我就羞愧难当了。但是我无论怎么推辞,马本德总能给我顶回来,后来,当我看到他满眼的诚恳与祈求时,我决定接受他的邀请,只是我会席间偷偷地把账结掉,这也算是我的一点自我救赎吧。
席间的马本德又说了不少感激的话,每一句都让我如坐针毡。后来他又自言自语地说:“唉,他出事不能怪别人,只能怪他自己。”我一听不觉窃喜,我知道他说的是谁,至于那个镇长何时出的事儿,出了什么事儿,我一概不知,也许马本德真以为是我的功劳。
此时,我说话不再唯唯诺诺,频频与他碰杯,我边给他倒酒,边自作聪明地附和说:“是啊,不过我都不记得他最后怎么样了。”
“他死啦。淹死的。”他说。
“淹死的?”我的脸皮火辣辣的,于是又厚着脸皮自嘲说,“我还以为我的文章起作用了呢。”
他说:“您能来我家采访就够了,这就是我要的结果,这个结果是给别人看的,是您给个坡让我下了驴,您真以为我会去上访呀,那是气话,气话而已。”
“可,他怎么会淹死呢?”我问。
“唉。”他猛地喝杯酒叹口气说道,“那是他当上镇长半年后吧,不知又在哪里喝多了,结果把车子开进了我家前的池塘里,我当时正恨他入骨呢,根本不想救他。”
“你,是你没去救他,他才……”
“咋可能呢,他是人,又不是畜生。可当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他从车里弄出来时,他已经喝得肚大如鼓了。我们赶紧拨打120,但120的人说,他们离我们这儿太远,赶过来怕也耽误了,就先让我们按他的方法抢救起来,可是我们都不会。后来,那个人又想起了什么似的说,赶紧牵头牲口来,让他趴在牲口背上。”
“那趴了吗?”
“没有。”
“咋啦?”
“咋啦?全村唯一的一头牲口不是被他给撞死了吗!”
酒席结束前,他哭着说:“这么多年了,我给谁都没有提起过,其实,我当时要不去喊人,而是直接跳进塘里,也许他就有救了……”
我的心头不觉一颤。但我还是拍拍他的肩膀说,这不怪你,是他自作自受。可他还是哭着说:“你说的话我也这么想过,可他毕竟是个人啊……”
说着,他的哭声越发的响亮了。
发稿编辑/浦建明
插 图/鲁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