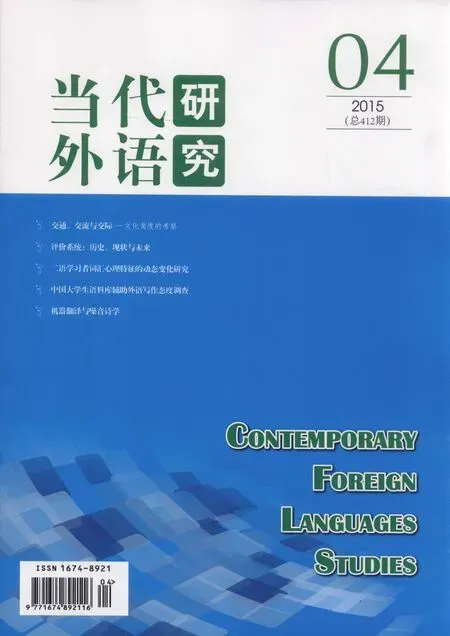交通、交流与交际——文化角度的考察
交通、交流与交际
——文化角度的考察
周流溪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100875)
摘要:交通、交流、交际,是含义宽泛的几个术语,经常见于人文学科的著述中。本文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考察这几个术语所指向的研究,特别说明文化交流和跨文化交际的区别。作者提倡学术研究要有宽广的视野和会通的旨趣,并建言学人应该积极投入文化交流。
关键词:交通、交流、交际,文化交流,跨文化交际
[中图分类号]H0-0
doi[编码] 10.3969/j.issn.1674-8921.2015.04.001
作者简介:周流溪,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并以此贯通各人文学科。电子邮箱:zhouliuqi2013@163.com
在人文学科著述中,尤其在历史和文化研究中,不时会遇到交通、交流、交际几个术语;在外语学科中后两个术语也频繁使用。本文将从文化交流角度考察这些术语的含义和用法,并探讨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文中所谈,有深意存焉;但那将越出一般的“学科”视域,又可能不太墨守“规范”。还望读者耐心一读体察鄙意,再加批评指正。
1.交通
“交通”,在民族“交往”的广泛意义上被使用,由来已久。在历史类著作中很常见。以现代学者而论,如冯承钧、张星烺、向达、阎宗临、方豪和章巽等人都较早进行科学意义的中外交通研究。如张星烺有《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30,1977),冯承钧有《中国南洋交通史》(1937/2011),方豪有《中西交通史》(1983,1987)。最后此书是一部体大思精的代表作。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系列,汇集了交通史籍的诸家校释。
按方豪(1987:2-3)的定义,“交通”英语为relation或intercourse。中西交通史包括的内容是:“民族之迁徙与移殖;血统、语言、习俗之混合;宗教之传布;神话、寓言之流传;文字之借用;科学之交流;艺术之影响;著述之翻译;商货之交易;生物之移植;海陆空之特殊旅行;和平之维系(使节之往还、条约之缔结等);和平之破坏(纠纷、争执与大小规模之战斗等)。”这真是无所不赅。按“交通”一词,原义是互相打通;既可指道路交通,也可指任何其他交往(甚至敌我营垒之间的串通[或在其夹缝中的情报传递,如地下党“交通员”])。故前举诸书以此含义广泛的词来命名原无不可。现在日常语言都将“交通”另限于道路交通运输。①一方面,既然交通又被定义为relation(关系),便真有以此为题的著作,如《中外关系史译丛》和《中外关系史论丛》自19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朱杰勤的《中外关系史论文集》(1984)和《中外关系史》(2011),内容同样非常广泛。
早先这类著作多以“中西”(指“西域”、“欧西”)为题,时限一般是从汉朝至明朝。后来范围扩大至“中外”(包括所有外国),时间范围也推及上至远古、下逮清朝。但是,无所不包的“交通”(或“关系”)研究早晚总要让位于比较具体的领域之研究。现行习惯是把“关系”专用于政治外交等关系(比如有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国际关系学院)。考虑到“中外关系[史]”已成学科建制,我们下面承认“中外关系”这个术语,并暂时把它放在一边。

陈伟明和王元林《古代中外交通史略》(2002)从学科的角度明确指出: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国与外国之间的交往联系,其一分支(或重要内容)是中外交通史;后者“研究历史上中国与世界各国陆海路交通路线的开辟扩展,交通技术与交通工具的提高与改进,中央政权对中外交通的管理控制,以及一些重要的对外交通枢纽与港口的兴衰等等”。过去多以中西交通史代替中外交通史(或中外关系史),是不全面的。有的书已把“关系”用于比较专门的分领域研究,比如张国刚、吴莉苇《中西文化关系史》(2006)。但阎宗临研究古代尤其是16~18世纪中西关系之书仍名《中西交通史》(2007)。黄盛璋的论文集《中外交通与交流史研究》(2002),书名定得较好,明确地把交通和交流结合起来;交通表示重点谈交往路线,交流表示重点谈交往内容,二者实互相补充。集内《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巴次大陆的时间和路线问题》、《关于古代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试论所谓“吐火罗语”及其有关的历史地理和民族问题》等文就是适例,体现了作者的研究思路。
说了半天,可能有人会沉不住气了:你都说到哪里啦?说的什么学科?答曰:可能是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但这样的“学科”值得我们关注吗?这就涉及当下“科学的”分类和“科学的”考核式管理了。我决不反对科学;但科学不是万能的,西方不少科学家承认科学会把人类引向危险的境地。“科学的”学科分类和考核就往往是非科学的甚至是反科学的,或通俗地说是不符合实际的。按“科学的”分类循名责实,“交通”类学校该算哪类?②现在我们的大学实行比几十年前更“科学的”管理,但大家(通才)比那时似还少见;这是为何,岂非值得[作为“科研”题目?]探讨一下?若让非科学的东西打着科学的旗号大行其道,中国的教育和学术研究就要受到阻碍(暂不论其他)。德国有“梵语帝国”之称,其梵语研究长期居于世界首位(令印度人惭愧);其实哲学研究他国亦难望其项背,真不枉了德国历代有那么多世界一流的哲学家。还有人们不大知道的当代的“国际语学”(interlinguistics,研究世界语和各种人造语言)德国人也独占鳌头。但德国并不靠我们这样“科学的”办法来管理大学。康德可以向一两个学生开一门课,这在我们这里简直不能批准。(没人听课,那你即使是唱阳春白雪,“科学地”考核起来也只能是不合格!)又:康德还搞天文学、提出星云假说。这像有点“不务正业”,有误导哲学系学生之嫌。
冯承钧他们当时并无“科学的”管理卡着,能自由地做出可贵的成绩和贡献。做历史学家不容易。司马迁能实现“成一家之言”的理想,班固也有独到的贡献(汉朝没有“科学的”框框限制他们);但这两个人都很不幸。当然他们为史学而献身的精神是不朽的。朱杰勤在抗战年代、在文革期间迭经播迁;1981年终在复校后的暨南大学创办和主持了华侨研究所,得以安定地坚持其中外交通/关系研究工作。黄盛璋中年投身于西部荒野的地理考察,备尝艰险。他原来工作的部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室现已撤销;他多次严厉批评撤销之举,呼吁重建此室。现在各种反华势力掀起的边界纠纷不断,都需要历史地理学家提供铁的证据为我国维护主权而辩护。但历史地理研究室没有了,那些“科学地”搞地理研究的人没有一个出头来关注和承担这个任务(因为地理所里已不存在这种研究“交通史”的任务!)。黄先生已退休多年、今届90高龄;他不顾身孤体弱,以拳拳报国之心奋力写出多篇关于琉球群岛和钓鱼岛历史的大文章,主动为国分忧。(这是我目睹亲知的。)“历史地理学”因属中外交通史“边缘学科”[?]而被撤销,这是科学的决策吗?这样做,受到损失的是国家!
2.历史上民族间的交往/交际和文化交流
华夏民族崛起较早;它是坚强的,又是孤傲的。大约从周朝以来,华夏大国的基本格局就定下来了;它几乎一直是东亚的大国和强国,其影响还不时远及东洋、南海和西域。但在封建社会生产力和儒家思想的框架下,加上周围地理条件尤其是东西两面的海山阻隔,中国的版图不免有个扩展极限。尽管如此,我们的民族(及其统治集团)还是形成了一种强势文化的优越感。中国长期严行华夷之辨(这未必“科学”,见周流溪2001c:282-4):华高于夷,也不必有求于夷!(这有点像现在很多美国人的心态:只有你们各国的人们需要学习英语,我们并不需要学习外语!外国有什么超过美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虽然中原(乃至全国)不止一次被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和主宰过;但他们在文化上是弱者,最终都被中华文明所同化。当然其间也曾经有过严重的思想摩擦和冲突。下面只举南北朝的例子。
北朝是胡人给汉人当家的半壁江山;当时宫廷内外都流行胡语,整个社会是一个语言二元化的社会。《北齐书·孙搴传》记:高祖委任孙搴“署相府主簿,专典文笔;[孙搴]又能通鲜卑语,兼宣传号令,当烦剧之任,大见赏重。”《隋书·经籍志》记有《鲜卑语》五卷、《鲜卑语》十卷之书。这是鲜卑语流行、应用和教学成果的反映。当然汉人也有反抗的行动。如《北齐书·高昂传》:“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髙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昂尝诣相府,掌门者不听。昂怒,引弓射之。髙祖知而不责。”《颜氏家训·教子篇》云:“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可见有人为了当官而学胡语,但不愿当官或当不了官的人是不愿意学习的。再看西边。《周书·列传·异域下》记高昌国:“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高昌深受汉化,在那里汉语居于输出语言的地位(日常生活除外)。
早在两汉之交,佛教已经东来。佛徒凭着强大的传教愿望和能力,渐渐使佛教的声望和影响在中国散布开来。随之那传统深厚的、辉煌的印度文明(其历史比中国更古远)也让中国人感受到了;中国人第一次为外来文化折服,觉得真的需要向外国学习了。思辨哲学、逻辑学、语文学、天文学、医药学等,足为文化补药。西域胡僧在佛教东传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高昌、焉耆、龟兹等地实为中国和中亚、印度以至西亚和欧洲之间交流的桥梁。龟兹国(新疆库车)有高僧佛图澄和鸠摩罗什。佛图澄曾两度到北天竺罽宾(喀什米尔)学佛法,得道;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来洛阳,已79岁,其后授徒成千上万。名僧道安(312~385,曾居东晋、前秦)是其高足。鸠摩罗什曾游学天竺诸国,深通大乘佛教。前秦自龟兹归来的僧人皆称许之;时道安在长安,乃劝苻坚延请罗什来华。苻坚派吕光伐龟兹,得之。苻坚旋败于攻晋之役,吕光乃自立建后凉国。罗什在那里继续潜心学习汉语至于熟练掌握。后秦姚兴立,伐后凉,迎罗什至长安。罗什以国师身份讲经译经(其译经数量巨大,译文也成为典范),为中国佛教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道安在北方讲道,慧远曾从之。后来慧远长住庐山,创立净土宗。佛教的驳杂学说还促使一些僧人西行求取真经。高僧法显(334~422?)是突出的代表。他生于平阳(山西临汾),曾由陆路西行求法遍游西域和天竺;后从海路归国入居东晋。他翻译了《大般涅槃经》(译名《大般泥洹经》)。北凉昙无谶也有译本(421),世称北本。东晋诗人谢灵运(385~433)曾与僧人慧严、慧观对《大般涅槃经》两个译本进行“改治”(即润色)。北本是较忠于原文的;改治者应知其中的胡汉差异。来华高僧和本土高僧如支谦、鸠摩罗什、道安(及唐朝玄奘)等都提出过很好的翻译原则,至今给人以启发。
几百年间,佛教对中国人的思想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故同一个颜之推,也不能不对外族事物的长处表现出一点客观的态度了。《颜氏家训·归心篇》云:“原夫四尘五荫,剖析形有;六舟三驾,运载群生。万行归空、千门入善、辩才智惠,岂徒七经、百氏之博哉?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意思是从本体论、道德哲学和逻辑学来看,儒学众家都不如佛家博大精深。他又说:“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颜氏认为:佛释内典和儒孔外典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故批判佛教是个迷误。他还指出官吏与平民中尽有缺德者,从而为有缺点的佛教徒辩护!对比他在谈论鲜卑语时的态度,这又有些“异哉”!)他在学问上对佛家的肯定,可说已经成为宋人援佛入儒而使儒学哲理化的先导了。
法显译本《大般泥洹经》附有“文字品”;昙无谶译本《大般涅槃经》附有“如来性品”。这两处内容相当,都介绍梵语“十四音”(‘字义’)。慧观了解梵字的性质;他说:“以音为半,字音合说,名之为满也。”(见安然《悉昙藏》卷七引谢灵运传。)意思是:辅音[‘音’]是半个音,与元音[‘字’]拼合,才成为整个音节[字母]。谢灵运与慧远交往甚深。他又从老僧慧睿学习。这个慧睿,曾游历至南天竺,通晓梵语。他后来住在庐山和建康(今南京);当中曾一度到关中咨询鸠摩罗什。谢灵运通过请教慧睿而最后通晓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写成《十四音训叙》,条列胡汉,昭然可了。此著作对“胡语”和“胡字”(其实大都是指Sanskrit)及其汉译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解释,是今知的国人学习梵语之最早成果。及至唐朝,也有不少西游高僧;最著名的玄奘和义净,分别经由陆路和海路去来。玄奘《大唐西域记》曾记载梵文有47个字母。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内有一篇《西方学法》,介绍印度的教育制度包括语文教学情况),说的是49个字母。然而,似乎历代外来的和本土的高僧都从未编写过、甚至没有引进过梵语语法书(包括语法和语音的处理)和梵语词典;这些从未见于中国的历史文献,是中国古代外语教育文献的一段大空白。可能普通僧徒都满足于佛经的汉译本,佛理浅尝即止,没有直接学习梵语(那是外语中最难学的天书!)的需要和欲望。尽管如此,梵语语音知识的传入,还是启发了中国的语言文学研究。十四音,原有两种解释:一指14个元音,一指14类语音。事实证明后一种说法最终影响了中国的音韵研究。中国学人至迟从东晋开始认真接触梵语的学问,一直探讨到唐末(甚至五代和宋初),才完全掌握了其中的真谛并运用它的原理来处理汉语音韵中的问题,最后建立起等韵学(汉语音系学)。这个摸索过程实在太长了。但若没有与佛教和梵文的接触,则中国学人至少还要再多等几百年,到明朝西方传教士把欧洲的拼音文字传过来,方能悟出汉语语音应该正确地分类及音节也能够进行精细的分解和分析!③
汉语近体诗的格律建立得早些,梁代已具雏形,至初盛唐间定型。在此过程中梵文诗论和佛徒唱诵曾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南齐永明年间,竟陵王萧子良周围有一个很大的文学圈子;他们与僧人过从甚密。
上述中印之间上千年的交往或交际,都是和平的、平等的文化交流。这里面是我们获益者多而赠出者少。不过,玄奘曾把经典《大乘起信论》回译为梵文使之在天竺广为传布。(有人考证这是华僧的伪作;那也证明华僧对大乘佛法有独立创造。)禅宗是佛教华化而独创的宗派。曾有印度来华僧人向中国的禅师请教;这也算客方青出于蓝、并对主方有所回赠!佛教在印度衰亡,大量文献却保存在中国,包括少量梵文原本与大量汉译本和藏译本。有的文献已译为梵文回归印度。两国之间也有经济的交流,如张骞在大夏(阿富汗北部)看到的蜀布(蜀锦?)听说是从天竺来的;这说明中印之间这种国际交易很早就发生了(蜀布可能通过滇缅通道入印)。中国的造纸术通过尼泊尔传入印度。
中国广为西方所知之名是cina,china等词形。它最终可追溯到古代印度语言的cinisthāna(支那、脂那、震旦、真丹)。常见的一种解释是,该名来自强大的“秦”(朝)。但这不可能;因为有几种古印度语文献早于秦代就称中国为Cina。较晚的岌多王朝大臣所写《利论》年代在公元前330年间,也早于秦始皇近百年;它提到有成捆的丝来自印度北方外面的Cina(丝国)。意大利藏学家杜奇(Giuseppe Tocci)《尼泊尔两次科学考察报告》指出:象雄时代的印度人把象雄(西藏西部)特别是其南端称为Cina(张琨,1982)。故印度人所说的那个印度北面的地方可包括尼泊尔、西藏、于阗、阿富汗等。于阗曾被称为Chin或Machin,甚至被认为是“中国”(黄盛璋2002:208)。这些地方是与中国本部率先有联系的,也是中国丝绸向西外销首先到达的中转站。印度人起先并不知道很细的区分,笼统把作为中间站的贩丝国和丝绸原产国混同了。当然,最后“丝国”还会被证明(正名)为产丝国的!
不过,最近有文化人类学家林河提出一种最新解释:cina一名源于粳稻!是中国南方[原先不为人知的]远古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远传至阿萨姆邦,为印度人所接受。那里的人(后来及至整个印度)遂称中国为“粳国”,而不是丝国(李建辉2003)!按:这从语音上也可以说得通:粳字古音可能是/*kreng~*kjeng~*kjing~*cing/,故可备一说。⑤但是现在有些人(包括不少大学教授)只粗知china既可指中国又可指瓷器,便信口开河说国名来自瓷器。殊不知这是本末倒置了!中国瓷器在西方造成轰动最早是在北宋时期(公元1000年前后),在西方成为时尚而大批进口则是在明代中叶(15世纪)。17世纪英语中为此出现了chinaware(中国器皿)一词;后来才简化为用china来专指瓷器。此事可小可大,但不得不辨,故顺便提及。
3.文化交流与跨文化交际
有次我听到一位外语教师说,他搞“跨文化研究”;我的脑神经本能地停摆了几秒钟才回应了一声,因为我要先尝试理解他那个大字眼的所指。啊,其实他想说的是“跨文化交际”(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研究。那与“跨文化研究”可不一样;严格说后者一般还不称为“跨文化研究”,而称为“比较文化”(comparative culture)研究:把不止一个文化摆在一起进行研究;那可不是常人所能做的,故不能开口就标榜它。现在先来谈谈我理解的习见的“跨文化交际”。为何不称“文化交际”?这里暗藏玄机,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文化交际”之名实非不能成立,用它指文化交往是无妨的。但“交际”一词在这里毕竟显得生硬,人们更愿意用“文化交流”(cultural exchange/interflow)。英语表述中前一个比较常用;但后一个也不罕见,如Lewis E.Hahn(韩路易)就有名为EnhancingCulturalInterflowbetweenEastandWest之书(interflow与“交流”直接对当)。该书1988年由东美研究所(Thomé H.Fang Institute)出版,中文原题《增进东西文化交融》。我之要举这个例子,因为东美研究所是美籍华人孙智燊以哲学家方东美之名命名创办的。孙智燊早年是台湾大学外文学士,尝从曾约农学习翻译,从方东美学习哲学,出国前曾任台湾大学外文系讲师(这是我们周围的外语学人很熟悉的一种学业和职业背景);当然他后来是辅仁大学哲学硕士,留美后又成了哲学博士。他认可的cultural interflow这个概念,意思应该就是cultural exchange。
现在回头还谈跨文化交际。我随便在本校图书馆的馆藏目录里检索了一下,发现以此为题的中外文书共有约300部。大部分书籍的标题英语都作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只偶或出现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含义相同。但反过来,communication又不是全都对应于“交际”;如耐普(M.Knapp 2014)的《美国老师教你跨文化交流》就用“交流”对译书名Communication。这个行当里面有的书是很浅显的,如J.R.Baldwin(2014)的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forEverydayLife一望而知为探讨日常的交际;又D.Snow的书EncounterswithWesterners:ImprovingSkillsinEnglishand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标题就是跟西方人打交道的“跨文化”技巧。在交际者所“跨”的文化中,有各种各样的大小因素而且其数量很大,但不能都注意到或都记得住。比如一本书里出了这样的习题:某商店门口挂出一面红旗,是什么意思?(1)正在罢工;(2)正在装修;(3)正在卖鲜肉。让学生选答。——正确的答案是(3)。这样的“文化产品”不是毫无意义,以我们的文化出身未必一见就能领会;但若要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学到手、烂熟于心,显然是不容易的。事实上在交往中随时会有自己以前未曾注意到的情况,必须学会及时调整话语方式以作应对。另一方面,在熟人之间,即使各有不同文化背景,也不是处处都要严守初学者那种“规范”。我在一次英语教学会议上讨论到加强文化教学和提高语用能力时,发表了两个点评意见:一是谈文化差异要有根有据不能失去分寸(比如武断地把英语大写的代词“我”说成是个人主义膨胀的表现);二是学生确要培养语用能力,但学英语的目的又不是要学到举手投足都像外国人。到我们真正掌握外语的时候,与外国人的交际就能做到完全平等,所以应该有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周2001b:449)。
在这里,我想表述几点意见:(1)“跨文化交际”作为一个论题,人们在其中所谈论的事情有大小、繁简、深浅之别;还不能说它已成为“学科”,不管在外国还是在中国。有一位颇致力于此的名教授前辈曾对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搞的是什么东西。”这话虽带自谦,却也是实情,比自夸者显得稳重些。(2)此“领域”虽然时新,但因学科性质含糊,而真正愿意下苦功钻研者其实不多;故恕我直言,多数都属于赶潮头的“新生”常谈,而流于肤浅。(3)此中似乎大家能默认的共同旨趣是交际能力的培养。如,朱晓姝(2007)《跨文化成功交际研究》一书副题点明“从误解到更好的理解”(美-中和德-中人士失误交际分析),史兴松(2007)《跨文化语言社会化进程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CultivatingCross-culturalCommunicativeCompetenceThroughInterculturalLanguageSociali-zation)也点明能力培养之旨。(4)此道结合专业讲比较扎实、有用;如S.Măda(2012)ProfessionalCom-municationacrossLanguagesandCultures至少明示了这个宗旨,邢建玉(2007)《跨文化商务交流中的关系管理》是中方商务代表团访英交流的案例分析。
还须指出:这里存在术语和概念的困惑。该领域的权威W.B.Gudykunst所编Cross-culturaland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2003,外教社2007跨文化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标题就难解。其所谓cross-cultural交际侧重从人类学角度看不同文化的交往,偏向静态的整体观察;而intercultural交际则偏向动态地观察不同文化(实包括身份、地位及各种圈子甚至身体状态[正常人和残疾人])的个人之间的交往。按:后者已把“文化”的概念泛化以致滥用了(简直可说是“不同文化程度者”之间的交际[但西方只讲“识字程度”和“教育程度”])。前者若仅称为cross-cultural study,则所谓止于人类学的偏静态整体观察之评价可以成立;然既亦云交际(communi-cation),则它不可能不是动态的。故这种强生分别的意义或价值并非如论者所标榜的那样大。Spencer-Oatey也并用二名。然而朱晓姝认为没有必要作此区分。那么若单立一名cross-cultural study或intercul-tural research,本来未尝不可(上海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Intercultural Institute就有Intercultural Research书系)。但S.L.Hathaway(2012)的Inter-culturalTransmissionintheMedievalMediterranean(中世纪地中海地区的文化传布)论述的是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传布。若译为“跨文化”并无必要,甚至不妥。其实原题用Cultral Transmission便足够了。更重要者,是我们不能一看到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名义就以为指我们现在所谈的“跨文化交际”了。例如麻争旗等译(2003)《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原书名为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AReader。中译名既说是“跨文化交流”又说是“传播”。而普罗瑟(M.H.Prosser)的书AnIntroduc-tionto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2013)译成《文化对话:跨文化传播导论》;我们也要注意。同类著作甚多。“传播”可是另一概念,内容比“交际”更广。我认为:如果把“跨文化传播”说成“文化传播”(cultural communication/transmission)可能更好,有助于消除communication一词的歧义。⑥但上外的书系却又有戴晓东、顾力行主编(2010)的《跨文化交际与传播中的身份认同》(Identityand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并用两个汉语概念来对communication“打擦边球”。作者用意为何,读者需要猜想一番。
有一次我告诉一位外语同行(他说他搞跨文化交际):“我想搞的和你的不一样,我想搞的是文化交流”。从粗浅的层面上说,“跨文化交际”考虑的是如何在[尤其是]面对面的交往中注意双方说话的内容和方式,避免误解对方的意思、伤及对方的面子,以便使对话顺利获得结果。而“文化交流”的含义是文化交换或交易(这是exchange的本义),即我给对方什么文化产品或内容,对方又给我什么作为交换物。显然,这和“跨文化交际”是大不相同的事情。比如中国给印度纸张和造纸术,印度给中国佛教和声明学。这都是“硬货交换”,而且这往往不是个人的事,绝非[主要是]个人接触时考虑对方习俗、注意礼貌、维持正常谈话那么简单。当然,货物交换也有好货和次货之分。所以我不是说,我愿意搞文化交流就一定表明我有硬货在手。想拿出文化产品进行文化交流,就需要钻研文化本身并很好掌握其精髓。这可是很困难的学问。我虽是外语教师,但花在钻研中国语言文化的时间精力还超过中文系的很多人。本族文化的研究已经是如此费劲;“跨文化”研究就更难了。前面我说一般不提“跨文化研究”,但不是不能有这样的研究。比如S.L.Hathaway(2012)叙述地中海地区的文化传布,则当然是跨文化研究。这种书可写成交流事实描写型著作,也可写成文化内容分析型著作。M.Olohan(2000)所编的InterculturalFaultlines:ResearchModelsinTranslationStudiesⅠ,TextualandCognitiveAspects([超越]文化之间的断裂——翻译学研究模式〈一〉:文本和认知方面)和T.Hermans(2002)所编的CrossculturalTransgressions:ResearchModelsinTranslationStudiesⅡ,HistoricalandIdeologicalIssues(跨文化侵越——翻译学研究模式〈二〉:历史与意识形态问题)二书,也都是“跨文化”研究(Hermans时任国际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协会主席);但也可说是结合专业的跨文化交际研究。
我在学术上一贯主张包容;故在此处我绝无意说“跨文化交际”因为其什么地位而不值得研究;前文虽提及多数人对此道的理解流于肤浅,但我没说此道本身一定是肤浅的。这里想补充说明(可算是第5点意见):跨文化交际研究可以是理论研究,自有不可轻视的意义。王玉环主编的《跨文化交际学基础教程》(AFoundationalCourseo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2013)便称此道为“学”(英文题名无“学”字);我们循名责实,看其所言能否成立。考之该书所述,答案基本是肯定的:“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运用相关学科如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传播学、语言学等理论和方法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交际时的交际行为和交际过程的应用性学科。跨文化交际学主要涉及交际与文化、文化感知与价值观、语言与文化、非语言与文化、跨文化适应、跨文化冲突处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等内容。”但这只是一本基础教程;该“学科”的内容当然还可按需要大大扩展和深化。用这种评判眼光来考查别的书,也应该而且可以从学科理据上或曰理论精神上甄别其精华。史兴松(2007)标举的跨文化交往社会化进程便值得探讨。至于怎样运用传播学理论来研究跨文化交际,还可从容探索。前举普罗瑟的书有相当多的内容可以参考。
“跨文化交际学”提供的理论原则在文化交流中是重要的、有用的;主动探讨和掌握这些原则将利于进行交流和理解交流。颜之推怎能对佛教有比较全面的理解?设想一下:他作为高官接触到的谅必是一些高僧;而那些高僧也很懂得“跨文化交际”策略!他们先以自己的道德和学问感化和说服高官,然后其佛法传播就畅通无阻了。严复要宣传天演论(进化论),他自己业已是半个赫胥黎了,他要与本邦人士交流就与赫胥黎亲自要来交流差不了多少。其译文必须首先能被上层官吏和知识精英接受,故他采取衍译法(详后),笔调又模仿晚周诸子散文。“好文章啊!”这些高等读者不知不觉间全被他的文章、同时也被文章的内容和观点感化了。责备严复用古文体是守旧,就没有体会译者身处的环境与他的苦心和明智。严复是懂得跨文化“交际”原则的。
当然,原则也不一定灵验。唐太宗有意将《老子》介绍到印度,令玄奘译成梵文。玄奘将“道”译为bodhi(菩提),道教徒不同意;双方争吵不止,事情便作罢了。菩提是“智识、觉悟”之义,可说是悟道,实不等于“道”。玄奘是以唯识论家的眼光来理解和转达道家的核心概念。道,主要是本体论概念;菩提,是认识论概念;道的倾向是唯物主义,菩提的倾向是唯心主义;即使道也是唯心主义,它终究是客观唯心主义,与菩提的主观唯心主义还不一样。似此一开头就不能在一个核心概念上达到一致的理解,交流自然不可能继续了;换言之,译了过去也是走样的。但话说回来,季羡林曾说过:禅宗没有经典,呵佛骂祖,简直不能说是佛教。这话禅宗之徒肯定接受不了。你说我不是佛教,我就不能存在?印度佛教在佛涅槃后众多部派、乃至后来的小乘大乘两宗,不是也互不承认吗?这时候什么交际原则也没用了,只能听其自行发展各走各路。佛教外传,传到东南亚的都是小乘,传到中国的则以大乘为主。无论如何,从跨文化交际学中了解一些原理或原则总没有害处。但解释世界的理论终不能代替改变世界的行动。文化交流本身永远是第一位该做的事。能将文化交流和跨文化交际研究互相结合,大家一起行动积极去做,那当然最好。
4.努力投身文化研究
在文化研究和文化交流的领域,众多前辈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例如,冯承钧早年在比利时读中学,继之在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后入法兰西学院师从汉学家伯希和,得与当时西欧博学者流(如沙畹、沙海昂、鄂卢梭、伯希和、牟里等)交游。他通晓法语、英语、阿拉伯语、波斯语、蒙古语(和八思巴文)、梵语,兼及古回鹘语、吐火罗语;既广知外国学者的研究著作,又精通中国史籍;故能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历史语言学和考古学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他毕生研究中外交通史和边疆史,擅史地考证,著译等身。像这种学者的外语学识及其功业哪是现在普通的外语教师所能具备的?我们不能学得其百分之一,也应得其万分之一、千分之一才是。我出生那年冯承钧就去世了,我作为下一代学人岂非应接过前辈的薪火奋行向前!
我生虽晚,但还够得着见到20世纪50年代前成名的学者,并师从之、请益之。我的硕士导师吕叔湘先生就是我的叔祖辈。因其提携,我能来北京,得便遍访京城(并及外地)名师与之交游、至少能亲聆教诲,像王力(语言学家)、陈遵妫(天文学家)、钟敬文(民俗学之父、吾乡贤)、李鉴澄(天文学家)、周有光(语言学家)、吴宗济(语音学家)、孙克定(数学家、世界语者)、卞之琳、钱钟书、赵光贤(历史学家)、何兹全(历史学家)等,和我的导师一样都是清朝出生的那一代人。我曾与赵光贤先生住在同一栋楼,我在研究西周年代学时曾请益之,得到他的文章和他提供的文献(反之我也向他提供过韩国人的文献)。稍晚一些的学者是我的伯父辈,如周力(世界语学者)、许国璋、俞敏(语言学家)、王佐良、李赋宁,以及我的叔父辈(人数更多,暂不列举了)。“外语教师”许国璋先生曾欲招我读博士生研究梁启超,“汉语教师”俞敏先生也愿意收我读博研究梵汉对音;这两个“出格的”机会可惜我都错过了。现在青年学子则几乎想拜80年代成名者为师都不易得。当然决不能说,师傅必定越老越好。我也多与同辈和后辈相过从,并受益于他们。我这里想说明的是:我们既看重前辈身上的学问,更领受其特别深挚的献身精神和历史责任感。诚如鲁迅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玄奘就是舍身求法的人(他对中国文化和文化交流贡献都很大)。献身学术的人都可归入此类。这些人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脊梁。文化研究,就要关注民族文化和国际文化,以及文化人的作为和言教。我决心赓续前辈之志,做一个传承中华文化的学人;另一方面,作为外语学人我也要有国际视野,要在国际上弘扬中华文化并主动参与到全球化时代新的国际性文化之构建中去。
我少年时代受到郭沫若的影响,立志做个诗人兼学者。后来则也要学习梁启超和王国维。梁、王、郭都属于钻到哪里哪里通的学者,是我的最高榜样。我也以同类的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饶宗颐等前辈为榜样。(我已养成一个习惯和韧性,不管哪座山,只要我进山寻宝绝不空手而出。否则我不会进去。)以诗而言,我认创作为第一位、研究为第二位。⑦我用汉语、英语、世界语三种语言写诗、译诗。我以维持唐诗传统自任(唐诗的传统不能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断掉!)。我数十年精研中古音韵,谋求诗作表现纯正的唐风、达到几可乱真的地步(我用古音,但也能照顾今[北]音);而格调则以初盛唐大家的高远雄浑为最高榜样。这与郭沫若笔下旧诗越写越差大不一样,也和钱钟书偏爱宋诗那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旨趣不同。我就不信,我写出几百首唐风式的诗竟无一首能与李白的诗相比。(我也不信我的外语诗写到100首还没一首成功。)但“老干体”、“学者体”旧诗90%是不合格的,作者们竟不自知。⑧我编/注了唐诗两部(周2004/2008);编书也是学习。为了唐诗的辑佚和校雠,我把从法国、英国、俄国三个博物馆(还有个别日本藏品)复制回来的海量敦煌文献彻底翻查过了。第二次彻底翻查是为了校编《老子》(周2009)而搜寻古代写本。(为了搞音韵学我第三次彻底翻查过敦煌文献。)在上述三本书里,我把能找到的各种版本和出土文物写本都利用起来,文本校订精确到每一个字的异同。这是极其繁琐的国学基本操作(但由此我对唐诗和《老子》就有更多发言权了)。没人要求我这个“外语教师”来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份外”事;是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和历史责任感驱使我来做的。末了,这些书我还得自费在香港出版。2007年我在北京的学术前沿论坛上讲过一次老子的思想:《和谐社会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追求的理想——从〈老子〉角度所作的考察》。
在唐诗《统编》的前言里、在《韵编》的导言和注解里,我都留意利用一切空间插注哪怕是零碎的内容,并一有机会就“借题发挥”两下,在《西方学法》(周2005)注和《西方哲学史歌》(周2007)注里这样做就更频繁了。这是给读者提供尽量多的信息,也是积极与读者互动。我写诗时虽然力求追求“诗人之诗”的韵味,但有时在注解里也多加按语甚至详作“文人之文”。正文的诗和注解的学术议论不妨共存。这种杂论文笔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跟“大熊猫”钱公学的。我有次在书店碰到一个人,他对我说钱氏写书喜卖弄外文炫博。我极不以为然。你不懂,不可以查书、学习吗?他上下古今贯通中外提供的材料越多,对读者就越有用处。[倒是时下不少人著述中提及外国的观点、地名、人名往往随手乱写(又不加注外语原文),使人难以理解、不敢轻信!]钱公没有(实不屑于)撰写成体系的著作;但他博学而有逸才,善用古人的札记体,而且发挥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完美地步,书中随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甚至有认知语言学的思绪,我真服他)。仇兆鳌详注杜甫诗说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固然不尽是;但他的繁征博引对读者帮助实多;我们自己贵在独立思考善于取舍而已。我在军都山山戎遗址参观时,注意到山戎曾培育出胡豆、冬葱,就禁不住在诗里提及这件事并在注里评论(表扬)一番:毕竟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也有其贡献啊。我在旅途中对古怪的地名都注意记录、考证,许多写进诗里,那都是闪光的地方古代文化微粒。我在贵州游历偶然旁及都江,就考证了一番,认为珠江原名本应作“猪江”(猪、都古音同)。这样自己人揭穿“雅名”的底细可能不讨好!但我感到有“原生态”的收获,还乐在其中。
我赞同认知语言学路线,标举其体验主义(experientalism)原理;既用它来研究语言文学,也用它来观察哲学。从中国文化的宝库里考察,体验主义可谓古已有之。中国上古哲学,包括易学、老学,就是体验主义哲学。中国古代文化既不“土气”,也不“神秘”。把先验、经验的、体验的东西并观,便可见唯有体验的东西是真实而又深刻的;故不必怀疑体验主义(周2005)。《老子》的体验主义体系,在周末汉初曾与别的学说融合成为“黄老之学”(周2013b)。80年代我在钻研《易经》时,发现了一个湮没两千多年的易卦体系。我曾在中国科学院世界语协会的学术会议上用世界语谈过《周易》;与会一位天津的工程师兼教师运用我在报告里介绍的周易卦序口诀歌(周2001a:69),花一个小时背诵就记住了64卦的卦序。而之前他用遍古今人的口诀都记不住。因为我的卦序歌带有半真半假的文学意象,所以好记。此法我也利用来撰写西方哲学史歌。这是我在认真学习西方哲学史中随手创作自助记忆之产物。我对西方哲学向有兴趣;但集中学习西方哲学史却直接与我想回中国社科院读哲学史博士生有关。吾愿未能实现:考试时我无法战胜那些献身哲学的哲学硕士尖子。但我继续关心西方哲学[史]。我也涉猎“西天”哲学,主要是佛学。当然这种“副业”学习也与我的语言学“正业”相关。我最初从俞敏先生处零星接触到梵语,后来肤浅地查过一些书;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写过几个印度语言的词条(这是编写组临时布置的任务,实则我并不具备资格)。我初步读懂义净《寄归传》的《西方学法》一章,是借助欧美学者的英语论著的阐释。后来我详细注解此章,同时也钻研声明学、语言哲学、佛学,又断续查阅梵语材料,阅读季羡林、金克木、徐梵澄的书,甚至到北京大学旁听梵语课以便获得一点该语言的感性知识。我还未学会这种“天书”;但在多年与梵语学者的周旋中我至少获得了登门求教的资格。我要感谢[季羡林和金克木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黄宝生、葛维钧、王邦维、叶少勇、罗鸿以及萨尔吉诸位的无私帮助和指教。
但我学习梵语太晚了。我报考研究生原欲入外文所从卞之琳先生,后选择了语言跟吕先生。卞先生惋惜我跑了;假如我考上外文所,就会接近该所的黄宝生、葛维钧等先生(我实不知其名,也不知其所在)。但假如我在语言所落选,也许就会跟几个人转到南亚所学习印度语言而得以接近季羡林、金克木等先生。吕先生对我有再造之恩,我没齿不忘;我今天的一切皆先生所赐。上述两个“假如”都是事后三十年才知道的可能性。我在语言所学习语言学算是“科班”出身,对于践行自己心目中的理想道路并没有错。只是我毕业后虽未离开社科院但不在语言所工作,与老师廖秋忠先生联系不多,竟错过了向他的邻居(!)、梵学造诣绝不次于季羡林和金克木的徐梵澄先生学习梵语的大好机会(徐为隐士,我并未闻其名)!假如我当时知道廖老师有这个邻居就好了!吕先生是语言学家、语法学家;王力先生也是(他还是语音学家)。但我的志向不止于做个语言学“专家”;我的旨趣是以语言学为基点博通各人文学科。所以我的第一个学术目标是“兼王吕而有之”,且与其他同仁一样想要改造王力所拟的古音系统。⑨这是狂妄不敬吗?非也。王先生1986年就离开我们了;他是中国语言学的集大成者(周2001c),但终无法完成90年代后的任务;它就落在我等晚辈肩上了。
我曾发表过《越人歌解读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3:1-15)、《上古汉语的声调和韵系新拟》(《语言研究》2000.4:97-104)、《从译韵的音似说到音系异同》(《外语与翻译》2000.4:72,79)[以上二文是我决心于新千年之际在音韵学上立足之作]、《上古汉语音系新论》(《古汉语研究》2001.2:5-11)、《上古汉语音系再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4:99-103)、《切韵音系构拟的根本出路》(2006《民俗典籍文字研究》3:239-62,转载于2008《亚洲文明》4:83-104)、《韵图研究的历史性思考》(《庆祝何炳棣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801-21)、《汉语音韵学草创时期著述董理》(载于张渭毅主编《音韵研究》,中华书局2015[即出])。音韵学是与文字学、训诂学互为一体的学问,是解读中国古代文化的钥匙。我自学钻研了几十年,才有这一点收获。若按现在“科学的”考核每年都要拿出核心刊物的论文,我就不可能有这些成果。而这个“小学”(philology)基础是探讨中国古代文史哲和文化现象的本钱。从语言学上说,我能兼治普通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⑩除上举者外,2009年四川大学举办徐中舒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我作了《传统语文学还可有新的作为》的发言,还参加过两次汉藏语言学会议(都有报告)、两次方言学会议(在香港一次有报告)、一次音韵学会议(有报告),不止一次在外校作音韵学讲座,还写过几篇谈语言起源的文章。作为“外语教师”我创造过一个神话: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大古汉语阵地演讲过一次周朝的语音。2012年5月我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声调问题国际研讨会,用英语作了讲座报告《音韵学在古典诗文诵吟中的应用》(Zhou 2012a)。与会的日本老学者第一次从我口中听到中国本土带唐宋遗音风格的赋诵,大为激动和称赏。
我对汉语史的探讨自然导向对汉族(华夏族)历史的探讨,而比较可靠的入手点只能是对周朝历史的研究。我花了上10年时间熟悉以往各家的观点、论证及其遗留问题,钻研各种材料包括天文历法和新旧考古(金文)材料,最后构拟了一个新的西周年代体系,成为一家之言(周1997a,b;周2003)。2004年宝鸡出土一批有铭文的青铜器;各家构拟的体系包括费了国家几千万科研费集中全国各个学科专家而组成的“夏商周年代学工程”项目课题组提出的体系大都被摧垮了(因为解释不了宝鸡那些铭文显示的年代信息),但我的体系稍微调整一下居然还垮不了(周2004a)。我还参加过天文学会议(发言谈天文年代学),写过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和年代考释的专文三篇,还有《谈谈改历》支持在新千年实行历法改革(均见周2001c)。2008年5月我在河南新乡市参加了比干诞辰三千一百年纪念大典,题诗颂扬比干精神。2011年12月我参观了安徽省博物院的双墩遗址展示,读了一些文章,认同考古界视出土祭坛为大禹涂山之盟用物的猜想,作了一首四言长诗缅怀大禹行迹和歌颂华夏精神,寄托了解决夏史问题的希望。2012年11月我与黄盛璋先生到河南省夏邑参加当地举办的夏文化与故都研讨会,作了关于夏史和夏文化的报告(周2012)。夏史是关乎民族渊源的大史。(吾村是南宋时建立的,已经800年。我也写了文章考证村史。——家族小史是民族大史的细胞,也值得研究。)
对于时世混乱的五代十国的历史,我也写了论文探讨(周2001d),并通过歌诀来记忆其令人眼花的年代(周2001a:136-9)。那个乱世虽似一无是处,陈抟老祖和了义和尚都[身不由己]生逢其时;但陈抟的太极图启发了周敦颐作出更好的太极图,了义对韵图的创制也有重要贡献。周敦颐有《爱莲说》和《太极图说》;前者谁都读过,后者知道的人就少了,而能把二文比观又深思其内在统一性者则几乎没有。前一文脱尽污染之旨显然受到佛家影响。但单凭佛法不能救世、救国。我认为前者体现了周子的情操和精神追求(即人生观),后者则体现了他立足本土的世界观和辩证法。二者和谐统合于周子一人的思想中:他有独立的信念和坚定的立场(周2007:69)。这些话我写在《游法门寺》一诗的注解里,算是借题发挥。我在唐诗注解(周2008)里对一些西域地名也作了考证(这对读者应有帮助),而西域又是在与黄盛璋先生交游中常常议论的话题。我把他表述其终生学问和心迹的“文明求源百咏”译成英语(载于《亚洲文明》4),后来又用他的名义详作注解;为此我认真学习了有关领域的知识,向他问学实多(偶或也有献疑问难)。黄盛璋(2002)对吐火罗语的考证很有见解,反复证明那是大月氏人西迁时留在焉耆、龟兹的部族所用之语言。但此语言属印欧语系西支;这些印欧人怎么来到敦煌祁连间(大月氏人的故乡)?若被齐桓公[从冀晋]驱逐[至流沙即今内蒙西部以远]的大夏人与中亚的大夏人(吐火罗人Tocharians)是一族,则这些印欧人竟东来直达华北了!“我们”是谁?黄公坚持中国文明本土起源论,对此不置一词;我则不忌讳这点(相信“我们”来自“西土”,但也可能先绕道漠北而南下),执意想找到黄种人和白种人分手的地方(那只能在中亚或西亚)[周2001e],否则无法解释人类[语言]同源(如牛,英语cow、梵语go、温州广州ngau,是欧亚同源词)。
我通过学习欧西的和“西天”的历史、哲学和文化,感到要让更多人分享我的心得(这里虽无可以自矜的创见,但也非人人都重视此道),就是:要以“同情之了解”耐心地、虚心地学习和理解西方文化的文献、体会其中的思想和经验,然后加以扬弃而努力创新。我用了相当于《西方学法》原文15倍的篇幅把该注的地方都作了注释(或加按语解说),如对梵语语法及其中体现的语言哲学思想萌芽、印度的教育制度、佛教的流派及其学说,及玄奘和义净的取经行事,都给读者提供了尽量多的信息(周2004c)。这是我的学习心得,拿出来与读者交流和切磋。在语言哲学方面,我曾专门写出一篇文章(周2015b),并以此在第五届中西语言哲学国际研讨会(2014哈尔滨)作了报告。我公开了自己学习西方哲学史的心得(周2007);最后,也结合阿罗频多对赫拉克利特的评述以及徐梵澄对阿氏的笺注、特别是徐氏自己的《玄理参同》(徐梵澄2006[1])和我对中国哲学的理解,特地写了“补注二”以为《史歌》余义之发挥——除了旌扬徐氏的学问和精神,也提出了如何重视对“西天”哲学的了解、学习和扬弃的问题。
5.主动践行文化交流
人类既然分散为不同的文化族群,其间总会发生交流。文化具有一定的稳固性,这是维持族群的前提之一;但交流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常态;而且主动者昌,被动者亡。上引普罗瑟的书里有“文化稳定和文化变迁:哪一个更危险?”“文化传播的固有属性是文化帝国主义吗?”等等主题;不管我们怎样想,必须面对现实采取行动。又韩路易的书Cultural Interflow汉译名是《文化交融》,暗示着交流、交换的结果将导致交融即融合。这可说主要是从结果(而非动因和过程)来看问题。这也值得思考和研究。我说过学外语不必学到举手投足都像外国人。但事实上就有人学成这样还顾盼得意。在这里,便有主动自行更化和被动潜移默化、强(长效)更化和弱(短效)更化、内里更化和外表更化之别,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更化的问题;都需要详加探讨。
文化交流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例,莫过于古代中印交流中佛法在中国的广泛流布。这里只论士人作居士之有所修为。如东坡居士(苏轼)并不信佛,但又能在学佛中养成一种宠辱不惊的心性:他被贬惠州,却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又被贬海南,更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比坚决反佛的韩愈被贬潮州时还乐观些。徐梵澄论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时,已研究佛学,…但先生能入乎佛学,亦能出乎佛学。…胸襟达到了一极大的沉静境界,…这冷静境界,在思想上成就了精辟的见解,看事物异常深透,所谓‘靜则生明’。…其冷静,‘渊默’,不能纯粹是对辛亥革命后的许多事情的失望造成的,必亦是由于一长期的修养,即内中的省察存养而致。换言之,在自己下过绝大的工夫。显然,这必是受了佛经或老、庄的影响”(见徐梵澄2006[4])。对鲁迅心境这种探讨有助于更好理解其坚定立场的底蕴。佛法影响到中国人的心性,那是内里的、长效的更化。这是思想的交流成为交融了。吸收外来文化的养分,可以是主动的或被动的;在知识分子当然是主动的居多。宋明理学主动吸收佛学精华将儒学哲理化,是对儒学的发展;陆王心学尤其得到徐梵澄的重视,他把它与印度现代圣哲阿罗频多的精神哲学比观,标举其高扬主体性之宗旨(徐梵澄2006[1])。梁启超、郭沫若等都对王阳明心学有正面的评价。但鲁迅对宋明理学没有好感,认为它是无益社会改革的、与社会和百姓无关的老调子,一直唱到皇朝的灭亡(周2007:167)。五四运动要革儒学的命、引进民主和科学,大方向并没有错。接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导致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这是另一次意义最重大的中外文化交流;当务之急是如何提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程度(包括体制改革和思想教育的实效)以开创中华腾飞的新局面。但是为什么宋明理学或陆王心学至少是宋明皇朝灭亡的部分原因,而它却会促成日本的明治维新和欧洲的启蒙运动?文化交流到底在怎样的条件下会产生怎样的效果,仍然值得深入研究。
文化交融往往可以通过主动整合各种文化成分而获得较好的结果。当前中国人如何把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古今哲学参较整合成为中国的新哲学,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任务。中国正在巨变中,又面临全球化浪潮;欧洲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和文化融合的经验也许能成为借鉴。不管怎样,历史已向我们提出挑战(周2007:100)!如何建立新的价值观和道德哲学?能否建立新的本体论?在学习和思考中我反复比较中国和希腊古代哲学,最后悟出可以利用“是、諟、寔”来对应ont(=being)之类而将ontology(原译本体论,未善)得体地译为“諟论”(周2015a);希望这有助于解决困扰哲学界(尤其西方哲学研究圈)多年的老问题,促进中西哲学的会通研究。
諟论是形而上学,但形而上学还可有其他范式(周2007:96)。中、印、西三大派哲学和文化的会通研究有极广极高的空间。张君劢、梁簌溟、牟宗三、徐梵澄及吴森等人都能会通三派哲学和文化。张有《明日之中国文化——中印欧文化十讲》、《新儒家思想史》。牟比较过儒、佛、康德;尝言康德之后无哲学。吴痛批之。吴曾比较易经和杜威的思想;他指出国人普遍误解杜威的pragmatism为实用主义(按近有人提出重译为实效主义),它应正名为实践主义[哲学]!他自谓对佛教精神的体会实得力于比较哲学研究;重点阐述了佛教的无我论在世界哲学中的地位、禅宗的语言观对现代语言哲学的贡献。他认同怀特海之说,称佛教为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应用形而上学系统。武汉大学设有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心,出版了《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多辑。福建师大林可济有《‘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中西哲学比较的重要视角》(2010);他还赞扬薛德震勇于破除极左禁区的精神(薛反复论证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为“以人为本”的治国新政提供理论根据)。薛氏还指出哲学追寻真善美。按:此言异于亚里士多德所说哲学是求[真]知的学问;又,潭中也从华印比较里提出真善美是东方文化的精神。
我在多处讲过中西文化交流,在复旦大学讲演时还录进超星视频网。我也常常以身作则,鼓励友生多关心语言文化问题和从事有关文化的研究。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在各族之间就有文化交流[和跨文化交际]。有一年我指导的两名硕士生提出放弃原先自选的语言教学方向,改为民族语言研究,我大力支持立即同意。那两个姑娘能主动关心这种宏观社会语言学问题,是可嘉的;一位还不远万里到云南独龙族社区去做调查。最后答辩时我特意请了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来主持,提高其答辩规格以作鼓励,并向其他学生示范。友生左秀兰有《面对英语渗透的语言规划:词汇借贷研究》之作(2006)。我在序中指出:“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人应该有一种社会责任感,而且要宣传它。有人对强势语言和强势文化的压力感到无可奈何,于是随波逐流,听之任之;他们认为抵抗是徒劳的,干脆不要抵抗。然而只要国家民族的界限还未泯灭,民族语言的认同感和维护民族语言的努力就仍然要受到肯定。[今按:南明在清朝确立后还要抵抗;汉人无法甘被胡化。]我国设有专门负责语言规范化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04年又在其中成立了‘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境内外语应用分技术委员会’[按:周流溪也是委员],以指导和规范外语的使用。我们既不能闭关自守,又不能全盘西化。这里有许多工作要做,也有许多理论问题要解决。”“在社会语言学的宏观研究中,有语言选择和语言政策问题,有语言规范化问题,有方言问题、少数民族语言问题,甚至国际语问题,以及与之相连带的文化问题。……大家都应该来关心语言生态和文化生态问题。”


此行的一个收获是在越南应李士俊同志之命买到了为庆祝UK而出版的世界语版《翘传》。它是从阮攸的越南语版《翘传》翻译而成的,而阮攸的《翘传》是根据清代小说家青心才人的《金银翘传》原著重新创作的长诗。但是,会后不久李士俊同志就逝世了。因此我自告奋勇把研究《翘传》的任务担当起来,从比较文学/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金银翘传》的翻译和传播过程。
2012年我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谭平山》新书发布会。谭平山在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Visva-Bharati)主持汉学教育数十年,有“当代玄奘”之誉。当日与会者有其哲嗣谭中教授和新德里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学者,会上决定同时在印度和中国开展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纪念活动。到了中方学者启动此事时,莫言也获奖了。因此2013年6月将二人获奖之事并联,在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召开学术研讨会,名为“从泰戈尔到莫言:百年东方文化的世界意义”。我荣幸与会,在发言中谈了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启示(周2013c)。值此中国作家取得重大突破之契机,我提出要从文本创作、文本翻译、学术研究和传播手段四方面合力创新,使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更多地走向世界;这既是传播中国文化(使之在国际文化中享有应得的份额),也是直接参与全球化形势下的国际新文化之创造和构建。在发言中我从莫言作品能被国际读者接受的一个重要因素(及成功的翻译)之启发特别论及:外国译者采取的是有效的衍译(paraphrasing translation)。这是我改造已有译论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从汉译佛经和严复的翻译里也可见到不同程度的衍译。故从翻译之第一目的是被接受着眼,不能老在直译和意译上纠缠。此外,还要争取更多中外合译的机会(按:此实为中国古代译场的经验)。——联系《金银翘传》,它被越南大诗人改写后不但成了越南文学的瑰宝(不少因素竟至深入越南语和越南人的思想了),而且被广泛译为外语又成为世界文学名著;但原作在中国只是一部二流作品(尽管也有胜于《红楼梦》之处)。这里最大的启示,仍然是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所以我寻得阮译(并咨询专家弄懂越南语的文义)和英译,对照原作和世界语译本,尽量从中发掘原著的义蕴并阐发其传播带给我们的启发,写成了北京市学术前沿论坛的世界语分组发言(周2014)。
上海的会开过后,我又飞赴新德里、随后再东至国际大学(在加尔各答附近);在两地的泰戈尔纪念活动中我都作了学术报告(Zhou 2013a,b)。此行是我至今为止从事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经历。我和中国的与会同行都受到印度友人的热情接待。我在发言中称颂泰戈尔复兴东方文明的历史责任感和留下的丰厚人文遗产,表达了努力实现中印携手共建文明国家的愿望。这既是学术和文化交流,也是民间外交的行动。印度是重视精神生活、重视道德教化和个人修为的国度,中国何尝不然!以前有人认为:梁启超邀请泰戈尔访华,是因为他在新旧文化的大辩论中输了才引外人来助势;这至少是莫大的误解。实则梁氏在近代是勇于接触世界、努力介绍外国新思想新文化以创造“少年中国”的旗手;他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议论纵横而笔端常带感情,不知曾有多少人受其鼓舞而奋起。他邀请泰戈尔访华是出于对文化交流的自觉认识。他认为要以新的教育造就“新民”;他的家庭教育也很有办法。当我向印度友人介绍他有三个儿子当了院士,听者无不啧啧赞叹。这在中国应该是空前绝后的事了吧。我在印度期间,还顺道访问了佛祖得道处和说法处以及玄奘留学的那烂陀寺遗址。我在印度的大学里看到老教师授课时师生坐席而谈,感到异常亲切,仿佛孔子、马融就在面前。师徒融洽、其乐无穷,教育传统值得珍视!我也注意观察印度人的生活和社会状况。印度虽经英国百年统治,但看上去总的说来还像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样子(当然人家的先进处我未尽看到)。我从而更深地领悟到:我们一定要珍惜现在的大好形势,加倍努力建设我们的国家,并勇于参与国际新秩序和国际新文化的建设。
我们应该深入研究文化,学好外语并用好外语,积极主动投身于文化交流的伟大事业。
附注
① 以“交通”一类概念为名的学校,最初兴起于洋务运动中(如船政学堂)。但后来就不一定只与交通相关了。
② 比如上海交通大学不知该属哪类,其英译名也不好办。它曾是“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国家现有交通[运输]部Ministry of Transport);用transport[ation]称呼它不算冤枉。但现在却不能称为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nsport[ation]!它的名称是Chiao Tung University(1921)和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现用者)。其姐妹学校西安交通大学英语名称是Xi’an Jiaotong University。若用transport[ation]称呼,就有意无意把它们贬低了!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好办法翻译这种校名,只好借助于拼音Jiaotong。不知上海海运学院之名该怎样译成英语。其现名上海海事大学英语称为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它不是青岛海洋学院(中国海洋大学)那样的“海洋”学校;后者现名的英译是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该名外国人看了未必不惊奇。]有次我在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学,我对学生说:“你们将来要当大副、当远洋公司经理助手之类;我今天就不讲英语教学了,也不讲语言学。我要讲与发展远洋贸易和打破第二岛链有关的事。”我是作了准备的。这是我讲学里最出格的一次;但反映还很热烈。后来我把游洋山新港的七律一首赠给学院,学院把它作为对学生进行日常教育的材料了。
③ 我在四川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古前期汉语音系的韵图式解读》即试图系统清理这上千年的学习和创造过程。
④ 参见周流溪《“八病”後考》。这是我当中学教师时的习作。刊于社科院《学习与思考》1981年第2期(后收入周2001c)。我根据多年古典诗歌学习和创作的体会以及对音韵学的钻研,试图对八病作出合理的诠释;故而也勇敢地对古代文学理论权威郭绍虞前辈的观点提出批评商榷。但我当时未接触梵语,故也不能从根本上说明诗病说的梵学渊源,如后文梅维恒、梅祖麟(2007)之文所揭示者。
⑤ Cina的终极词源尚未定论。有兴趣者可以找一些相关考证文章来看。说不定这就是你进入文化研究的契机和开始。
⑥ “交际”、“传播”都对译communication,有时教人不得要领。窃以为该词用得太滥。不知谁是始作俑者,把communi-cation用如各种信息交流之义,后来就多指[新闻]传播,然后人们也就一窝蜂地跟风了。它已成为传播学的专用词(但“传播学”所关注的不止是报纸电视之类)。中国传媒大学校名翻成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很多大学里的新闻(或艺术)传媒学院都翻成School of Journalism(或arts) and Communication。把传播说成communication是不幸的,用transmission更好。中国传媒大学前身是北京广播学院,那个名字应只能翻成broadcasting。“传播”给人的主要印象是信息的单向流动(比如官方、记者对大众的宣传),或曰暗示着单向的主动行为;而“交际”(communi-cation)则令人直观地主要想到人与人之间的[包括信息的和行动的]双向交流。应该承认:以communication(交际)为基础而得到的合用术语communicative competence(交际能力),绝不是“communication”(“传播”)所能导致的。但面对communication(传播)的强势,communication(交际)似乎亦可以休矣。不过若改用俗词intercourse来表示“交际”,偶然入句说说犹可,当作专业术语就有所顾虑了。故communication虽有“传播”的异解,要表达“交际”我们还得继续用它。
⑦ 我在诗学方面的少量成果有:《“八病”後考》、《“大历十才子”小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6:142)、《诗歌格律综览》(《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6.2:1-9,涉及中外各体)、《卢纶诗中的至德、鄱阳和池州》(《池州学院学报》2012.4:95-98)和两部唐诗选集(周2004d,2008)。这两部选集的学术性在不止一个方面超过业内的同类著述。我在书中综述了唐诗的演变史,也对格律作了新的归纳并辨析出于王力未指出的特殊律句。我在各地讲学谈过从语言结构(或音韵)、生态、西域等角度看唐诗,也涉及从语篇学、认知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等角度看汉语诗歌。在中国政法大学儒学院讲过《〈诗经〉的史诗学解读》。在2012年(北京)首届中华吟诵高端论坛上报告了《汉语诗文口头表现形式的系统分类》,按音乐性高低提出一个读唱六层次(念、读、诵、吟、咏、唱)的完整分类框架。
⑧ 比如我所作长篇古风《长城行》(见周流溪2001a:62-64),自命不输于李白仅提及长城的诗。李白趾高气扬之时唐朝是世界第一强国,根本不需要长城。李白之后中国弱时多于强日,有长城也无用了。李白没有看到吴三桂的卖国史;我看到了,也写到诗里了,故吾诗内容即比李诗丰富。吴三桂本来在观望,准备归附已入京的李自成。但李自成的军队进城后不讲政策全无纪律而侵害到吴三桂,致吴引狼入室。清兵入关大加破坏,后又封锁海疆,明朝已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到恢复时中国早已被欧洲甩在后面老远,只好等着在鸦片战争中挨打了(而且可悲的是挨打50年后还不能变法)。我们要记住:“民族精神要发扬,闭关愚行不可再”。

⑨ 我有诗贻郑张尚芳(周2001a:72):“天下英雄君与操,祖生先著某藏韬。潜心竞定周原韵,不让洋儒我亦豪。”周原韻,指周朝的语音,即上古音。洋儒(汉学家)很多生活优裕而驰骋于汉学各个领域(包括上古汉语音系研究)并有建树,值得我们高度敬畏。当然我有志于从洋儒手里夺回一点地盘,至少要虚心学习他们而谋求自身学问的发展。但如果我们自己很浅薄,那是随时会被洋儒打败的;不自觉认识到这一点不行。有些外国“小教”在真学问上就有可能比我们弱(比如有次我与一位英语“小教”谈到英国哲学时便立马打败了他),是同样的道理。故我总不甘愿只“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语言。比如:“张三说自己聪明。”“李四谈到张三说自己聪明。”“王五不相信李四谈到张三说自己聪明。”这些‘自己’可能各有所指。有人已经写了硕士论文、甚至博士论文来讨论这种“结构”或“转换”了。但我不认为有什么大意义;所以我也不主张我的一个博士生写这样的论文。又如有一位搞功能语言学的同事递交科研立项申请,北京市科研管理者要他填写该项目对首都的经济建设有什么作用或贡献;这使他无所适从、哭笑不得。那要求固然是高了些。但如英语句子:He is seriously ill;he must go to see the doctor at once又被说成He is seriously ill;he must go see the doctor at once,为什么?我能用“功能语言学”给你解释:他病得太厉害;我急死了,以致连说to的时间也没有了——就是这种冥冥中的力量让我选择了更省时省力的句式。但能这样解释又有什么贡献?我不愿迷于这样的纯句法研究,宁愿把语言研究和人文研究结合起来试图在解决什么问题上有点作为。
⑩ 与上述历史语言学的成果相关者还有我在语音学上的见解,一是对国际音标表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待刊);二是改造前人的音节结构分析而提出了一个最完整的音节结构模型(首见于上引《上古汉语音系新论》,续见于《上古汉语音系再探》),可适用于古今语音分析和跨语言比较;三是对英国南部英语的音系提出独特的见解,认定它只有41个音位。这首载于我主编的《中国中学英语教育百科全书》(1995:313-20),又见于《当代英语的音系》(收入周2001b:189-91),也刊于《谈谈英汉语音对比》(收入杨自俭主编《英汉语比较与翻译》[2000:34-43]和周2001b:197-207);这样认定的音系音位数量最少而解释力更强,胜过英国学者自己提出的系统。我也支持友生研究生成音系学,见我为马秋武(2003)《优选论与汉语普通话的音节组构》所写的序言,及我与谭外元合写的《汉语的节律结构的语素制约分析》(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8[6])。我因长年讲授语言学,一直留心该学科的宏观问题,形成了我在语言学基本问题上的主要心得:(一)明确提出结构、功能、认知三条研究路线的观点。从初步形成此理念(周1997c,d,1998),到在教学和在各地讲学中大力宣传,并进而说明三条路线各可有描写、比较、解释、计算的旨趣(见我为王德亮《基于向心理论的汉语回指消解研究》[2011]所写的序及我为帕默尔《语言学概论》[2013]所写的译校后记),我的思想在学界的风浪里坚定不移。我实际指导的学生遵从认知路线者不少;但我于宣传此道也不走极端。极少有人能像我这样超越自守的门户来明确地全方位宣传语言学的路线,也极少有人像我这样敢于对外国权威提出严厉的批评(见我为Radford等编《语言学教程》[第一版(2000)和第二版(2013)]所作的两篇导读)。国外学者亦非人人都有很强的路线观念,例如莱普希《结构语言学通论》就将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归入结构语言学(周1997c)。现在三条路线虽然是客观存在的“简单事实”,但吾说仍为一家之言的“创见”:因为在各派自大门户者那里,别派的路线或者根本不存在(不成路线)或者可以宣称把它纳入自家路线范围,或者虽似存在而无甚价值即形同不存在。这是不能不加分辨的。我认为我的说法有纠偏的意义。关于如何区分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我在武姜生《语域变异与语境关系的多维度分析》(2007)序言里表述了基本的意见。在结构语言学方面,我赞同句法-语义界面的新思路(见我和张连文合写的《生成语法的全新论述——〈更简句法〉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2);我特别安排三位博士生率先在国内撰写了这方面的学位论文。我认为可以把这个思路归入认知语言学的逻辑主义派(周长银2008《结果句式的事件句法学研究》代序)。(二)准确地提出“言语、语言、话言”(langage/langue/parole)的三维术语译名,力倡纠正至今还在广为使用的、陈旧欠妥的二维术语“语言、言语”(langue/parole)[见《索绪尔的辩证语言观新探》,载《外语与翻译》2001.4;收入周(2001b)]。《新探》提出要分别语言的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还强调普通语言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仍然是要研究语言的性质和运作机制。依此认识并联系研究路线,我努力为一些分支学科正名、划界、开拓。《新探》和周(1997d,1998)都认定语用学、语篇学、社会语言学是语言的动态研究。在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发生纠缠时,我提出了判别标准(1998:45)。(三)在语用学里提出“规避准则”和“最大信息[量]原则”。前者见《指称词语的语用学地位及其使用准则》(载陈治安等主编《语用学:语言理解、社会文化与外语教学》2000:52,周2001b:299),后者见周(2008:1)。我认为:关联理论与其说是在语用学里加进认知因素,不如说是用认知路线来研究语用学。关联理论是认知语用学,而后者是认知语言学的分支(见文旭2004《反讽话语的认知语用研究》周序,尽管《MIT认知科学百科全书》并不承认这种分类)。循此路向我指导一批博士生研究反讽、隐喻、转喻、仿拟的语用推理。我分别与陈香兰、樊玲等人合写过认知推理的文章。(四)明确认定语篇学的地位。主张把欧洲学者的textlinguistics译为语篇学并定为学科名,取代含混的“话语分析”和稍好但仍不足的“话语语言学”。自(周1998)提出以后,又为李美霞2004《话语样类及其整合分析模式》作序申述,在首届全国话语语言学学术研讨会(河北大学2006)大力宣传。此名在我影响所及的范围内已被接受。我还提倡建立认知语篇学,及使语篇学结合于辞章学(自造术语textology)而互补出新[王义娜2006《指称的概念参照视点——认知语篇学的探索》周序(又刊《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7.1)及我与她合写的《人文学科研究的语篇学视角》(《山东外语教学》2007.6)]。我在认知语言学会议上讲过Talmy的认知语义学理论,也讲过认知语言学应在与各部门交叉渗透中开创新领域。按:述谓迁移里有转喻,汉语常见省略或偷换主语/宾语,都可从认知角度来解释。(五)准确提出“施指、受指、所指”(signifier/signified/referent[denotatum])的三维术语译名,力倡纠正陈旧欠妥的二维术语“能指、所指”(signifier/signified)[见《谈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的结合——语言学巨匠雅柯布遜的治学一瞥》(周2001c,又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1)]。必须指出:旧的术语至今还广泛见于语义学、语言哲学的著述中,而且别的人文学科还在继续使用,亟需纠正。(六)强调语言的三个主要功能:交际功能、认知功能、美学功能(poetic function);若无美学功能,至少难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有力解释汪洋大海一般的文学现象和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参见前述论雅柯布遜一文及《从认知的角度深入观照语言的使用》(为杨成虎2011《语法转喻的认知研究》所作的序)和上述《语言学教程》(2013)导读。我的观点已为友生王庆采纳,见于其与伍铁平主编的《普通语言学概要》(2014年第三版)第一章第三节。(七)关心语言的社会性研究,积极主张语言规划化。为国内国际语学和世界语学极少几个领头学者之一。有论文集《社会语言学和国际语学》(周2004b)及另一些国际语学著述(周1992、1999、2015c等)。
参考文献
黄盛璋.2002.中外交通与交流史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李建辉.2003.中国为什么叫“China”?——访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林河[J].中国民族(2):34-36.
梅维恒、梅祖麟.2007.近体诗律的梵文来源(王继红译)[J].国际汉学(16):171-233.
徐梵澄.2006.徐梵澄文集(1)、(4)[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琨.1982.论象雄(玉文华译)[J].西藏研究(2):103-14.
周流溪.1992.国际语和国际语学[A].威尔斯.世界语学概论(周流溪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52-61.
1997a.西周年代考辨[J].史学史研究(2):51-65.
1997b.公元前1030年克殷新说[A].武王克商之年研究[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565-73.
1997c.近五十年来语言学的发展[J].(上)外语教学与研究(3):21-27.(中)1997d:同刊(4):12-19.(下)1998.同刊(1):29-34.
1999.世界语学和国际语学研究[A].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C].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297-337.
2001a.流溪诗编[M].香港:华人出版社.
2001b.语言研究与语言教学[C].香港:华人出版社.
2001c.语言研究与人文研究[C].香港:华人出版社.
2001d.五代十国纪年与史书[J].史学史研究(4):67-72.
2001e.漫说华夷[A].周流溪.语言研究与人文研究[C].香港:华人出版社.282-4.
2003.《西周年代考辨》订补[J].史学史研究(2):71-73.
2004a.西周年代学札记[J].史学史研究(3):73.
2004b.社会语言学与国际语学[C].香港:华人出版社.
2004c.人文研究与语言教学[C].香港:华人出版社.
2004d.唐人集选唐诗统编[M].香港:华人出版社.
2007.流溪诗续编[M].香港:华人出版社.
2008.唐诗三百首韵编[M].香港:华人出版社.
2009.老子校编[M].香港:华人出版社.
2012.关于夏史和夏文化的思考[R].夏文化与故都研讨会(夏邑,2012年11月)论文.
2013a.互文与“互文性”[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3):137-41.
2013b.楚人对黄老学说的重要贡献[A].彭祖文化纵横谈[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42-65.
2013c.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启示[J].(待刊).
2014.《金云翘传》的原文本与衍译本——不及《红楼梦》,又胜过《红楼梦》[J].(待刊).
2015a.Ontology及其中译名探讨[J].外语教学与研究(1):9-18.
2015b.浅谈古印度的语言哲学思想[J].外语学刊(4,即出).
2015c.新世纪的国际语学[A].北京市语言学会精选文集[C].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即出).
Zhou, Liuxi.2012a.Th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phonemics to the chanting of classical verse and prose [R].TutorialSpeechattheThirdInternationalSymposiumonTonalAspectsofLanguages,Nanjing,China(May 26).

2013a.The humanistic legacy of Tagore for a renaissance of civilization states [R].SpeechattheInternationalCon-ferenceofTagore’sLegacyofInter-culturalInteraction:India,ChinaandCivilizationStates.NewDelhi,India(November 8).
2013b.Tagore’s sense of historical mission[R].SpeechattheInternationalSeminaronTagoreAcrossCultures:TheNobelPrizeandBeyond.Santiniketan,India(November 14).
(责任编辑林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