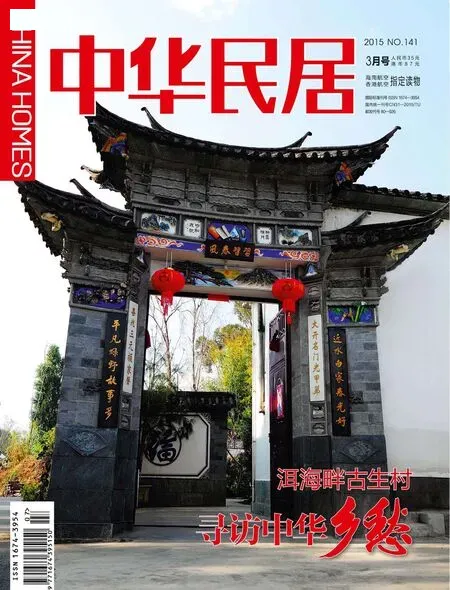方言吟乡愁
撰文/向明
方言吟乡愁
撰文/向明
从咿呀学语时起,语言就植入了我们的记忆。无论你在乡村或城市长大,我们最初始的语言版本,无不被打上地方特色的烙印。我们的语言生命便根植于一片特定区域的地理人文,一方特色水土的文化风情。甚至,它不仅仅包括素日言谈,还包括某些地方戏曲、歌谣等元素。


家乡话的幽默和乐趣
在华夏九州,汉语是我们的母语。但因天阔地广,而方言各异。尤其在南方,有时仅有一山之隔,彼此方言却不尽相同。
江西与湖南、广东相邻,但方言却相隔甚远。一字之差,差之千里。相传,位于江西境内的“井冈山”地名,却是广东、湖南方言而来。在明末清初,有两户广东人家来到江西五指峰下择地而居。他们居住的地方四面环山,好像住在井里,还有一条江水从屋前流过,于是他们就称此地为“井江村”,群山便谓之为“井江山”。因他们家乡方言中“江”与“冈”发音相同,外人都以为这里就叫井冈山。后来,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巧合的是,湖南方言“江”与“岗”发音亦相同。不久后,毛泽东便首次正式使用“井冈山”之名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从此“井冈山”渐渐名声鹊起,进而名声大震,并永垂青史。
还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在我们老家湖南有一方新化腔,承袭古汉语而来,有时连邻县的人都听得云里雾里。比如,一句“他确实要来,就让他来,没关系的”,用地道的新化腔道出来便是“其丁梆旺要犁,就要其犁,何乐”。若不解其一二词汇,则当真犹如听天书了。这难以捉摸的新化腔,或许会令你忍俊不禁。但冷静想想,当外人旁听你的方言,又何尝不是如此?似懂非懂,似明非明,或是只明其一,难明其二。方言就如一堵半透明的围城,把一群人圈在里面,而把另一大群人圈在外面,似在昭告各辈:方言是家乡人才能真正共享的东西。
《章台夜思》
韦庄·唐代
清瑟怨遥夜,绕弦风雨哀。孤灯闻楚角,残月下章台。芳草已云暮,故人殊未来。乡书不可寄,秋雁又南回。


生于一隅而行遍天下
《除夜作》
高适·唐代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
方言生于一隅,却也能行遍天下。它始终是传递和铭记乡情的重要纽带。人们须借它载着亲亲乡韵、浓浓乡愁,穿越五湖四海,踏遍天涯海角。无论走到哪里,人们便永远忘不了那最熟悉的乡音乡韵。哪怕是唇间吐出带有一丝熟韵的一个字、一个词,一听便醒。
两个有着共同方言的人相遇,尽管素昧平生,但因为共同的乡音,便可瞬间拉近距离,甚至从此结缘。试想,又有什么能让两个素昧平生的人,在相遇一刻即能在瞬间拉近距离并互留电话?唯有共同的乡音能有如此魔力。
倘能在偌大城市的茫茫人海中偶遇同乡,则更是算得上有几分机缘了。那正是去年春末夏初时分,北京的天空尚飘着些小雨。妻子在医院待产,我前去水果超市买些水果。正挑选时,忽然走进几人一边漫步一边说着邵阳话。久违的乡音立刻唤我起身,匆忙上前招呼。在距离家乡近两千公里外的北京,能像如此偶遇同乡,实难掩兴奋之情。一阵家乡话寒暄之后得知,我们竟是同一个县、同一个乡的。世界竟是如此渺小!
听到家乡话,好像回到家。共同的乡音便将彼此引向共同的情感闸口,一倾如注。我们从家乡的人、家乡的事,一直谈到现在生活状况的方方面面……“酒逢知己千杯少,话逢老乡不嫌多”。在短短一刻钟的叙谈中,一种近乎于家人的亲切感便已油然而生。
今天,社会进入高速时代,人们四处奔波,亲友愈是聚少离多,最盼望的莫过于佳节团圆,与旧友齐聚,一起把酒言欢。平素里,我们面对异乡的繁华和孤寂,临近而遥远,熟悉而陌生。唯有当与家人通信时,才能感觉到乡音犹在,心生波澜。虽相隔千里,但那通过电磁波传递的汩汩乡音、浓浓亲情,不会有丝毫的减损,令人倍感亲切。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变迁,我们与家人的联系也早已不再仅限于电话,更是有了各种网聊工具。有趣的是,我们无论是通过文字或是语言沟通,仍会下意识地用方言来表达。
“妈,掐饭了么?”
“正在掐。你们呢?”
“哦,我们也正在掐。屋里一切都好吧?”
“嗯,都好。你们在外头要多注意身体。”
“嗯,晓得。我们年轻滴,莫要担心。你们要多照顾好自己。”
“嗯,晓得。我们天天在屋里,也莫得么子事。”
一串串“怪异”的方言,恰似在考验彼此的心有灵犀。值得一提的是,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更曾被用苏州“家乡话”谱成评弹,搬上舞台。世人只知普通话版《乡愁》,又岂能轻解“家乡话”版评弹之妙?

《关山月》
李白·唐代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地方戏也是家乡话
说到这儿,也就不得不提到另一种奇妙的家乡话——地方戏曲、歌谣。它曾同样融入我们的生命,镌入我们的语言基因。它亦往往成为老乡与老乡之间交流的共同话题。有的甚至还要唱上一段,以解其痒。譬如,我们湖南人便酷爱花鼓戏、湖南民歌,而且其不少戏曲、歌谣更是早已红遍全国。如花鼓戏《刘海砍樵》、湖南民歌《浏阳河》,甭说是湖南人,几乎全国男女老少都已耳熟能唱了。
然而,有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即使全国男女老少会歌会唱,那也只是用普通话唱。而那真正用方言拿捏出来的腔调,是常人无法模仿的。即便模仿得再好,也仍有画瓢之感,难以去伪存真。这就好比我们听外国人说汉语,说得再像,也一听便知真伪。因为那深埋语言骨髓里的东西,是他人无法轻易模仿的。
一口方言可意会,最是乡音解乡愁。那深植基因的方言,一如瓷上的青釉,历经时间洗礼,却永不褪色。古诗且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即便是两鬓斑白,也依然记得故乡的口音,这就是乡愁。正道是,乡音犹在,又何忧乡愁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