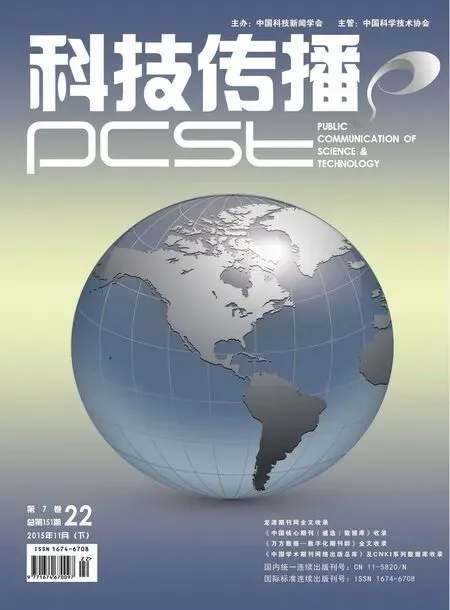对媒体与科学传播关系的反思
王大鹏
中国科普研究所,北京 100081
对媒体与科学传播关系的反思
王大鹏
中国科普研究所,北京 100081
科学传播与媒体的关系一直是理论和实践领域关注的焦点,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科学传播的发展,但是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些隔阂,同时科学传播反过来也对媒体提供了一些机遇和挑战,本文试图分析媒体对科学传播的促进作用,以及科学传播给媒体带来的挑战,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媒体;科学传播;科学新闻
作为有组织的实践活动,科学传播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1但是对科学开展传播和普及的活动却有着悠久的历史,甚至“科学新闻出现在大众媒体中的历史和这些媒体渠道存在的历史一样悠久。”。[2]在实践过程中,科普、科学传播、公众理解科学经常被不同的研究者交替使用。马丁·鲍尔对过去25年间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认为用“科学素质(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以及“科学与社会(科学传播)”三个范式可以概括过去25年中公众对科学发展的理解过程,每一个范式都联系着公众与科学之间关系的特定问题框架、特定研究问题以及优先的介入策略,并且每个阶段都比前一个阶段有“进步”,[3]但同时,我们在每个范式中都可以看到媒体的影子,可以说每次传播技术的个性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传播的发展,而媒体与科学传播的关系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可以从相关的文献中得到印证;本文拟着重探讨媒体对科学传播的作用体现在哪里?科学传播自身理念、范式的发展对从事科学传播的媒体所产生的(反制)作用,在媒体形态(自媒体、新媒体)多元的当代,又该如何完善媒体与科学传播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国家科学传播体系的构建?
1 媒体之于科学传播
2015全国科普日期间,中国科协发布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公民利用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获取科技信息(53.4%),电视仍是我国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最常用渠道(93.4%)。[4]可见,媒体仍然是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最主要渠道。同时媒体成为公众获取科技信息主要渠道的这一结论在历次调查中都所有呈现。而媒体与科学传播之间的关系自从科学建制化和科学家职业化发端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甚至在科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媒体就成为科学家向公众传播和普及科学知识的渠道和途径,比如1866年,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出版了法文刊物《科普画报》,1881年由《波士顿化学学报》改名为《科普消息》的杂志,19世纪晚期美国已经出现的包括《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和《大众科学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在内的几本科普杂志等。
同时科学家们认为科普是作为科学家的他们的一部分工作,他们感到应该把自己拥有的实用知识传播给公众,意识到了科学研究需要公众支持,并且他们欣然地利用那个时代的媒体渠道同公众分享他们开展科学探索的故事。[2]当然科学家们还通过其他途径将最前沿的科技成果传播给广大公众,比如英国科学促进会年会。该年会始于1831年,很多科技领域的重大成果都是在这个年会上首次发布的,其中包括19世纪40年代,焦耳的热功当量实验;贝西莫的炼钢工艺(1856);瑞利和拉姆齐首次发现惰性气体——氩(1894);奥利弗爵士在几百码的距离中进行无线传输的首次公开亮相(1984);约瑟夫·约翰·汤姆森发现了电子(1899)。同时也正是在这些会议上,“科学家”这个词被“杜撰”出来,“恐龙”这个词被正式使用。[5]
虽然起初科学家利用媒体开展科学传播活动,但是一些科学共同体和科学组织对于科学家开展科普活动的“不务正业”行为采取了某些处罚措施,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家参与科普的热情。
上述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媒体承担起了科学传播的工作,媒体被看作是科学传播的桥梁,二传手,纽带。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了技术创新,联邦政府在二战后加大科研投入的决定、20世纪60年代的太空竞赛以及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不断出现的对环保的关注唤醒了美国很多的媒体机构,他们争前恐后地发掘科学和环境方面的记者,以对他们认为的本世纪的一些主要话题进行新闻报道。[2]因而有关SHER(科学、健康、环境和风险传播)的报道在媒体中大量出现,进一步促进了媒体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同时2002年成立的世界科学记者联盟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媒体记者对科学的报道。世界科学记者联盟由来自于非洲、美洲、亚太、欧州和非洲的51个科学记者组织组成,该联盟鼓励对科学、技术、环境、健康、医药、农业和相关领域的批判性科学报道。世界科学记者联盟的目标包括:通过媒体能力的建设来增加对科学新闻的认知;通过教育、培训、会议等方式培养科学记者,并致力于强化科学新闻网络等。[6]
但是随着科学的边界不断扩展,科学也呈现出政治化的倾向。在当代,公共政策越来越依赖把科学标准作为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各个领域由此形成了大量专家群体,他们彼此所持的相反观点打破了“科学就是正确的”传统认识。这一过程使科学更容易变成争议对象。同时政客们(政治家)在确保哪些话题能获得媒体报道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政客们“被看作是意见领袖;他们是首要的定义者,那些登上媒体头版的科学新闻,往往是那些带上了政治色彩的信息。[7]因而媒体上的有关争议性话题的科学报道往往会将科学事实和价值判断混为一谈,从而给科学传播带来不利的影响。传统上,媒体被称为“第四权力”,即公众把对信息进行“把关”的权利让渡给了媒体,媒体负责为公众提供及时、准确、科学的信息,但是往往媒体的议程设置和媒介间议程设置会左右公众该想什么。
另外一方面,随着媒体对科学报道的不断深入,科学也有越来越媒体化的倾向。德国学者魏加特(Peter Weingart)提出了科学的媒体化(medialization)的概念,借以比喻媒体与科学日益紧密的纽带以及科研的媒体导向。实际上科学的媒体化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这种做法有助于提高科学研究的媒体曝光率,进而促进科学家获得更多的科研经费和研究项目。同时既有的研究也指出,媒体对科研成果的报道对于科研论文本身的引用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991年发表的一项以1978-1979年该刊所发论文为数据进行的研究,该研究表明;如果《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某篇论文被《纽约时报》报道,一年内它被引用的次数将增加72%。[8]另外,以文献计量手段对2007—2011年在中国科协领导下举行的科技期刊与新闻媒体见面会活动发布的新闻稿与科研论文引用率的分析考察也验证了上述结论。[9]
2 科学传播对媒体的反制作用
总体上看,媒体促进了科学传播的发展,但是媒介议程与公共议程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同时媒体之间还存在着彼此的议程设置导向。而科学与公众(媒体)之间往往被认为存在着隔阂(gap),障碍(barrier),藩篱(fence),甚至二者之间是水火不容(oil and water)。[10]作为对公众不信任科学的反应,科学家们既把媒体作为引起公众对科学信任下降的原因,有不得不把媒体作为解决这种不信任的一种途径。[11]二者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着,然而科学传播本身也给媒体带来了一些挑战,甚至可以说是(反)作用。因为传统上,科研机构和科学家是科学传播的第一发球员,而媒体是二传手,科研机构的成果通过媒体的“转述”和“翻译”变成了公众可以理解的语言,从而实现了科学传播的效果,但是因为各种因素的交织,科研机构开始变被动为主动,不仅继续承担发球员的角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科研机构直接到受众的点对点的科学传播。
由于经济利益的压力,一些新闻媒体开始压缩科学报道的数量和板块,压缩了科学新闻报道的空间。比如1989年美国每周有科学报道的媒体达到95家,但是仅仅3年之后,这个数量下降到了44家,随着出现的是科学板块的减少和压缩,这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体现在篇幅上,特别是那些小报,到了2005年,仅存24家。[12]
随着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呼声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开始关注科研项目的科学传播问题。同时新媒体和自媒体的不断发展也为科研人员提供了多元的传播渠道。科学家们开始“重操旧业”,从科学传播的幕后走向台前,利用各种渠道开展科学传播活动。科学家和科研机构纷纷利用博客等新媒体开展科学传播活动,有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尼尔森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共追踪了1.81亿个博客,较2006年的3600万博客数量有了大幅增长。科学网博客上每日都不断更新着各种科学相关的资讯和新闻,果壳网的日均浏览量400多万次,微信订阅人数高达40万(2014年7月数据)。
特别是随着微信公共账号的不断增加,其中科学传播相关的公共账号也备受公众关注。根据微信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近80%的微信用户关注微信公共账号,用户关注微信公共号主要目的是获取资讯(41.1%)。众多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也开始独自运行微信公共账号,主动发布相关的科学新闻和信息,满足公众对科技信息的需求,比如中国科协的“科普中国”定期发布“移动互联科学传播榜”,致力于向公众推介科学健康、内容优质的科普类移动互联平台、专家及科普内容。[13]这其中既涉及到科研机构,又包括科研人员本身。而某些媒体也反过来转载科研机构通过官方微信公共账号发布的相关信息和新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科研机构的议程设置影响到了媒体的议程设置,科研机构对从事科学传播的媒体产生了一定的反作用。
另外从受众的视角来看,公众已经不再是传统上的被动接受者,他们也主动获取科学,特别是与自身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技信息,从而也给科研机构开展科普提供了良好的生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媒体的科技传播功能。
3 改善媒体与科学传播的一些反思
如上所述,自从现代科学出现以来,媒体就对科学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广大公众在完成正规教育之后也主要通过媒体获取科技信息,但是媒体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复杂,学界用众多比喻来形容媒体与科学(公众)之间的关系,而这些比喻也往往将二者看作是相对对立的状态。在科学传播发展过程中,媒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科学的媒体化(为迎合媒体口味而追求轰动效应等),科学的政治化等等,同时在新媒体和自媒体时代,科学传播也相对应地给媒体科学传播带来一些挑战和反作用,因而有必要对如何改善媒体与科学传播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
首先,开展科学传播的媒体起源于科学需要公众对科学研究的支持,从而使得科研成果既要通过学术期刊发表出来,又要通过传统媒体予以传播[14],这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科学和新闻的边界,但是通常在科学家和科学记者如何解释和阐述研究过程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断层。比如,科学论文是“冷冰冰的”量化的,而媒体文章通常以人文为视角并同普通公众联系在一起。科学论文的受众是“一小撮”专业人员,而媒体文章则以广大的公众为受众。[15]因而科学和新闻都需要认识到各自的边界以及区别,从而更好地合作,促进科学传播的发展。
其次,在新媒体时代,科学共同体也给传播科学的媒体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同时也是机遇。因而媒体应该充分加强与科学共同体的互动,并加强媒体融合,从而及时、准确地传播来自科学共同体的声音,提升媒体在科学传播的作用。
最后,媒体作为“第四权”应该确保科学传播的正当性和公益性,避免为追求轰动效应而做出的有悖于科学事实的报道,特别是要注意科学报道过程中对科学事实与价值判断的区别,梳理科学共同体对媒体的信任,从而提升科学传播的效果。
[1]石顺科.英文“科普”称谓探识[J].科普研究,2007(2):62-66.
[2]Sharon Dunwoody,Science Journalism. in Handbook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edsBucchi M. & Trench B.)[M].Routledge.
[3]Bauer M.The Vicissitudes of‘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from‘Literacy’to‘ Science in Society’[J].科普研究,2006(8):14-22.
[4]中国科协.中国科协发布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EB/OL].[2015-9-22] http://www.cast.org.cn/n35081/ n35096/n10225918/16670746.html.
[5]British Science Association.The History of The Festival[EB/OL].2015-9-23 http://www. britishscienceassociation.org/the-history-of-thefestival.
[6]World Federation of Science Journalists[EB/OL].2015年9月23日http://wfsj.org/v2/mission-statement/
[7]贾鹤鹏,刘立,王大鹏,任安波.科学传播的科学——科学传播研究的新阶段[J].科学学研究,2015(33):332.
[8]Phillips D P, Kanter E J, Bednarczyk B et al. Importance of the lay pres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medical knowledge to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J].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1991,325(16):1180-1183.
[9]贾鹤鹏,王大鹏,杨琳,王玥.科学传播系统视角下的科技期刊与大众媒体合作[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5(26):445-450.
[10]Fischhoff B,Scheufele D A.The scien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3,110(suppl.3):14102.
[11]Encyclopedi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Ed. Susanna Hornig Priest)[M]. Sage.2010:152.
[12]王大鹏,钟琦.科学新闻的新挑战[J].科技传播,2014,1(下):247.
[13]新浪科技.科普中国权威发布移动互联科学传播榜[EB/ OL].2015-4-13 http://tech.sina.com.cn/d/i/2015-04-13/doc-ichmifpy7625333.shtml.
[14]Encyclopedi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Ed. Susanna Hornig Priest)[M]. Sage.2010P87
[15]Tania Bubela,etc. Science Communication Reconsidered[J].nature biotechnologyvolume 27 number 6.
G2
A
1674-6708(2015)151-005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