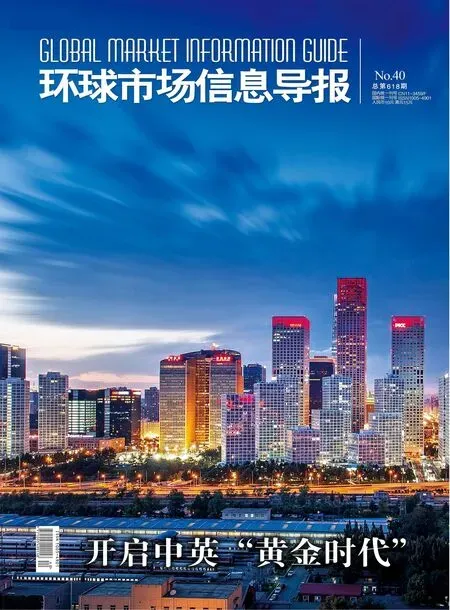你有夏洛式的中年危机吗?
你有夏洛式的中年危机吗?
Point
“如果杰克当年爬上了木板,他和露丝现在就是这副德性。”青春不复,逝者不可追,既有的一切令人厌倦,而衰老与迟暮的恐惧又挥之不去,不少中年人便在青春与衰老、爱与死、责任与欲望、现实与想象之间纠缠与撕扯。
电影里的中国中年男人也开始遭遇中年危机了。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档”,两部大热的电影《港囧》和《夏洛特烦恼》不约而同讲述了一个相同的故事:一个中年男人的危机。在这之前,华语电影(尤其是中国大陆电影)较少触碰这一题材,观众也较少留意。

“中年危机”是一个心理学名词,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指的是一个人很可能在中年阶段遭遇事业、健康、心理、婚姻等各种关卡和危机。“中年”确实是一个尴尬的时间点:青春不复,逝者不可追,既有的一切令人厌倦,而衰老与迟暮的恐惧又挥之不去,不少中年人便在青春与衰老、爱与死、责任与欲望、现实与想象之间纠缠与撕扯。
化用托尔斯泰的话说,幸福的中年是相似的,不幸的中年却各有各的不幸。那么,那些不幸的中年人因何而陷入危机?他们又是如何从危机中自救的?解析他人的痛业失败的中年人,相反,徐来也算是个成功人士,他所经营的乳罩事业在行业里好歹占据一席之地。从物质条件看,徐来也过得颇为滋润。但徐来并不幸福:与妻子的性生活像是例行公事,倒插门女婿的身份令他尴尬,妻子的家人过分干涉他的生苦,我们也是在反躬自省,并探寻人生的救赎之道。
自我实现危机
《港囧》里徐峥扮演的徐来并不是一个事活,他的画画理想被遗弃……

不难发现,徐来的中年危机与中产危机是叠加在一起的。他们是这样一群人:认认真真工作,事业有成,对家庭负责,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性格保守中庸,为人踏实;他们过的是模范的中产阶层生活:衣食无忧、家庭和睦、夫妻恩爱。可实际上,他们却被失望感所深深困扰——他们的自我消失了,他们的理想与自由被日复一日反反复复的庸常生活所压抑。人的最高需求不正是马斯洛提到的“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吗?这正是他们所缺少的。
徐来的危机是西方国家中产阶层普遍遭遇的危机。《革命之路》里,《泰坦尼克号》的男女主角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斯莱特饰演一对中年夫妻。曾几何时,弗兰克是高谈阔论的有志青年,爱波是向往成为名演员的未来之星;而今,他变成了做着无趣工作的无聊上班族,她成了不入流的糟糕演员。他们都厌倦了这种平庸的生活,他们渴望通过一次“全家搬到巴黎”的计划过上梦想中充满艺术气息的生活。可临行前,弗兰克动摇了,爱波在绝望中通过自残让自己流产,死在了医院里。
“如果杰克当年爬上了木板,他和露丝现在就是这副德性。”《革命之路》以死亡作结,象征了困境的无解;《港囧》里糟糠之妻和“小三”都如此通情达理,直男癌不说,危机的化解过于戏剧化和理想化,没多少参考价值;相较之下,周防正行的《谈谈情,跳跳舞》的处理方式有着谨慎的乐观:在既定的人生框架里,仍可以尝试去追求自己所热爱的,困顿的生活困不住一颗向往自由的心。
失意人的失意人生
如果说徐来纠结于“自我实现的需求”,那么马斯洛五大层次心理需求,没一个不是《夏洛特烦恼》里的夏洛所纠结的。他们是一群彻头彻尾的Loser:事业不顺遂,生活拮据,婚姻里无休止的争吵,不被家人也不被外人所待见。在人生的歧路、绝路前,一事无成的他们不知该何去何从。
无论是在影视中,还是在我们身边,我们常常看到这些失意小人物的影子:他是《杯酒人生》里的迈克斯:婚姻失败、作家梦遥不可及、干着无聊枯燥的职业;是《阳光小美女》里的同性恋舅舅,自称是美国最好的普鲁斯特研究学者,可恋人和同事跑掉、失业、自杀未遂、生活混乱;也是《忘了去懂你》里中国重庆白沙小镇里的蔡伟航,所在的家具厂停产,没有出路,失意带来的自卑和愤恨让他对妻子充满猜疑,两人关系濒临崩溃……
失意人面对失意人生,逆袭的总是少数,他们和解的方式更多是放低期待、转变想法、安贫乐道。是的,我就是一个Loser,但这世界本来就是有人成功有人失意、有人是白天鹅有人是丑小鸭,何必受困于“成功才是幸福”的评价体系呢?那就过好小人物的生活,享受小人物的悲欢,轻松一点,诙谐一点。《夏洛特烦恼》里夏洛一次穿越后才发现平平淡淡才是真,《杯酒人生》里的迈克斯最后在快餐店喝完了那瓶他珍藏的美酒。知足精神与阿Q精神还是有所差别的,前者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也值得尘世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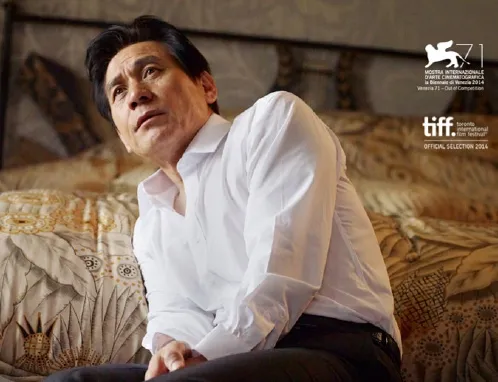
社会危机下的个体危机
在《美国丽人》中,莱斯特人到中年,事业中庸,与妻子关系紧张;妻子卡罗琳比他混得出色,一派女强人作风,与莱斯特早已没了爱情,她在与竞争对手的虐恋中寻找快感。可怕的不仅仅是中年人的危机,而是中年人这种了无乐趣、沮丧绝望的状态已经蔓延到下一代、蔓延到每个人身上:莱斯特的女儿一直想杀掉父亲,整天嚷嚷和谁做爱的小姑娘其实是个处女……固然《美国丽人》一直被视为反映中年危机的代表作,但导演的意图并不仅于此,他想深入反思的是一种被视为理想化的美国生活“美丽”外表下的千疮百孔:自由、开放等价值的边界在哪里?
某种意义上说,《东京奏鸣曲》是日本版的《美国丽人》,电影同样聚焦于一个中产家庭内部的崩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父亲失业了,可为了维护尊严,每天仍装作去上班,实则是在找工作、领救济餐;妻子尽力扮演好为人妻母的角色,却抵挡不住失望情绪的侵扰,因为自己已被家庭死死困住;夫妻俩分床而眠,不交流也没有感情。与此同时,大儿子因参军而陷入自我认同危机,小儿子是个钢琴神童却不被父亲允许弹琴……当日本经济长期萎靡不振,“无缘社会”成为一种常态,陷入孤立、孤独、孤绝状态的个体该如何与他人建立联系?当生活布满失望和沮丧,又该用什么抵抗或化解?
显然,这并不仅仅是个体危机与中产危机,而是一种普遍性社会危机,因此它常常是无解的,如同《美国丽人》堵死了所有出口,只是完美地叙述了绝望。
“中年”的本体性危机
当然,中年人陷入危机,并不尽然是因为婚姻、事业、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也有可能仅仅是因为“人到中年”了,自然而然便有了这个年纪所自发的焦灼和沉重,或是生理的或是心理的。
《回光奏鸣曲》(2014)聚焦的是一个中年女人的危机。独居高雄的阿玲正经历着更年期,丈夫常年在大陆经商联系不上,女儿在外读书很少回家、叛逆不听管教,她一个人辛苦上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照顾生病住院的婆婆。高雄的天气潮湿闷热压抑,就像中年女子阿玲的情绪,欲望的汗不停地流,身体和心灵仍渴求跃动,却找寻不到出口,她成了一条搁浅的鱼。这是中年人的本体性困境:仍渴望青春与放肆,却受困于身体的时间与伦理的边界。
《花葬》是韩国国宝级导演林权泽的第102部作品。中年男子吴正锡虽事业有成,但他身边却被一种腐朽和死亡的气息所环绕,自己随身携带尿袋,还得照顾行动不便的罹癌妻子,帮她把屎把尿。吴正锡被新进员工秋恩珠迷住了,她有着清新的妆容、明亮缤纷的洋装、甜美的笑容,充满青春气息和生命力。吴正锡对秋恩珠的情欲表现得隐晦和压抑,从不逾越边界。与其说吴正锡对妻子不忠,毋宁说是即将迈入迟暮的中年男子对青春的恋恋不舍与徒劳捕风。这正是《花葬》的高明之处,它将中年男子的情欲解构于青春与衰老、生与死的生命进程中。
《回光奏鸣曲》的结尾是阿玲数分钟的用力破门,她仿佛是在释放所有的压抑和绝望,但即便打开了门,她也无路可去。《花葬》最后,在妻子去世之后,面对秋恩珠的来访,吴正锡选择了离开,留下踉踉跄跄踽踽独行的背影,他洞悉了生命的真谛,看清了自己的执迷。这是期颐之年的林权泽给出的通透见解:中年是生命的必经之路,中年人的困境也是生命的组成部分,与其徒劳无功地逃离困境或饮鸩止渴去弥补空虚,倒不如正视困境、正视缺陷,然后自然而然地去经历它。
(文/曾于里,原载于《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