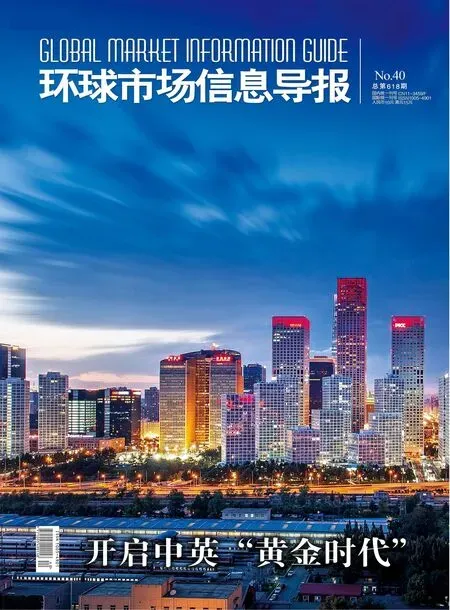回到中国:从鲍明钤到许章润
回到中国:从鲍明钤到许章润
Point
中国传统的法律智慧真的能给现代中国的法治带来什么吗?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而又亟需声明的问题。从某种狭隘的,线性的历史决定论来看,落后的过去只是美好的未来的垫脚石,在传统里面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东西。传统的信仰即是迷信,传统的扬弃即是进步。这样的一种看法,对于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和今天这个处在发展初期的中国而言,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一
三年前在北京,我赴约前往中国政法大学,拜访一位我敬慕的教授,那是我在美国修习法律的第一年暑假,在那里,我背负沉重的学业、未知的前途,还有迅速消退的信心。北京同时也是某种巨大的失望,我觉得过去一年我在美国努力学习的东西离这里的生活是如此之远,这里没什么人能和你讨论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或者美国媒体上热炒的同性恋婚姻诉讼,大家关心的是VIE,避税和移民。在和那位教授吃了一顿糊里糊涂的饭后,我接到一件意外的礼物,一本厚厚的、有暗红色封皮的《鲍明钤文集》。
我从未听说过他,但是书的开头对他经历的简单介绍却让我拿起了这本书。他是获庚款去美国留学的民国学人之一,在美国学习政治学和神学,回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教授政治学和法学。1932年,他因为自己的政治活动被迫短暂逃往菲律宾,他的书遭到查禁,而且他本人也被禁止在任何国内大学担任教职。后来他去了已经沦陷的东北,却一直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直到抗战胜利。内战期间,他同情共产党,反感腐败的国民政府,但解放之后,因为院系调整却没有事情做,而且一直拒绝思想改造。1956年他莫名其妙地被捕入狱,5年之后他病死在狱中,时年67岁。
那本文集中绝大多数的文章,都是在他1922年从美国回国到1932年他流亡菲律宾之间的十年间写成的。那是时局动荡,但也是思想激荡的民国时代。鲍明钤的所有思考与写作,都和那个时代中国的历史走向息息相关。他反思临时约法的缺点,谈论民主政体在中国的兴起和帝制的复辟,他谈论废除督军制的必要和宪制国家的建设,他比较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先进国家间政体的优劣:内阁制和总统制,联邦制和单一制,他探讨立法机关的构造、组织、职务及权力,行政机关的选举和权力,司法机关的独立,解释中国的省为什么要有一个高度自治的政府,还有政党政治的条件以及对于国民私权的保障。
从今天的目光看来,这简直是一本实现共和宪政的指导教材;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其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用英文写成,后来再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的。他用英文著述的原因,是想让国际社会相信,中国已不复是那个腐朽的、落后的、不文明的国度,而是完全可以通过改革,吸纳西方文明的成果,加之自身的本位文化,最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民族。他让自己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是想引导当时国内少数的精英,为民国政治的困局打开新的出路。他以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础,结合自身对于清政府立宪到民国中期这二十余年间中国政治史的观察和反思,也以中华文化本位的精神,总结出所谓“中国民治主义”的学说。
在美国继续学习的第二年,在埋头于企业并购、公司上市、跨国纠纷的众多资料案例之余,我也在斯坦福浩瀚的东亚图书收藏中,发现了一大批让我振奋的作品。吴经熊、张佛泉、钱端升、王宠惠,他们都和鲍氏相似,是早年留学欧美的学习政治、法律的留学生,都试图以现代的法治精神改造中国,都希望改革后的中国,不为世界诸强所轻视,在内繁荣富强,在外平等独立。他们的理念不完全相同,但是都对自身的学说和理念持有相当的自信和勇气。这样的自信和勇气,不仅仅是在面对外在的政治压力和迫害的,而且是在各种思想大潮下,做到独立的思考和陈说。他们都认为东西方之法理智慧不可偏废,在实现“正义”和“良善”这些终极目的上,学习西方和因袭中国传统并不互相抵触。可悲的是,他们在当时都或多或少为现实政治所抛弃。因为他们都不是某一个政党,某一种单一价值理念的良好代言人,而我们在建立历史博物馆时,却无意把他们收纳其中。他们属于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的那些人。

二
中国传统的法律智慧真的能给现代中国的法治带来什么吗?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而又亟需声明的问题。从某种狭隘的,线性的历史决定论来看,落后的过去只是美好的未来的垫脚石,在传统里面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东西。传统的信仰即是迷信,传统的扬弃即是进步。这样的一种看法,对于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和今天这个处在发展初期的中国而言,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圣人的训谕是要不得的,因为圣人从未见过洋枪;传统的文学是要不得的,因为文学付不了赔款;传统中国的整个制度都是应当废弃的,因为废弃了这制度的日本不仅打赢了中国,还打赢了西洋的俄国。这是清末民初的普遍情绪。
到了今天,这一情绪的表象变化了,可是内核并没有什么改变:中国富裕、强大了,是因为我们向西方要来了先进的技术,是因为我们终于不管他是白猫和黑猫,不管是中国外国,只要是能捉到老鼠赚到钱,那就是上帝,那就是真理。按照这样一种朴素到近乎愚蠢的逻辑,向后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终于摆脱了历史的枷锁和束缚,可以大步向钱。因此,还有什么必要谈论中国的传统呢?
这种荒谬的,根本上是反历史的看法,今天成为大多数人所谓的“历史观”。在此一片荒芜之上是复兴不出什么东西的,甚至连做梦也都是空洞的。文化本来就是一个变动的连续体,中国文化不是例外,虽然经历了二十世纪人为的撕裂,但是再冲击、再断裂,中华文明整体巨大的体量,和其长期的历史延续性和丰富性,也能充分吸纳这些冲击。那些积累已久的地层,虽然不曾言说,但是总会在默默中塑造今日的风景。
从法学本身的角度,这里可以稍举一个小例子,来说明认识传统在现代化道路上的重要性。中华帝国在漫长的时间中形成了独特而复杂的土地制度。在这一点上,中国和西方的产权制度的历史演变是非常不同的。对于佃农的权利保障,还有农业生产资料(如土地、水源、道路)相关的争议解决方案,中国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独特的,和西方基于土地财产权的成文法完全不同的一套法理和习惯法体系。20世纪中国尽管经历了多次大规模、极端的土地改革,执政者一次又一次,出于意识形态和自身利益的原因改革土地制度,但是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古代中国形成的一种基本习惯:土地及其相关的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和在地社会成员的地位紧密相关这一原则,仍然普遍适用。在农村中,当地社区的核心人物(不管是具体何种职务的人),在解决土地纠纷问题上仍然担任了法官和行政主管的职位,对本地人利益的保护,对外地人的普遍怀疑,还有对土地使用权的干涉,这些都和传统中国的习俗是相连的。
抛开传统中国的这些习俗不论,仅仅以所谓的“市场经济”的名义征用土地,无论其代价是公平还是腐败的,其过程是“合法”还是“违法”的,都一定会遭到反抗、抵制甚至激起社会运动。纵观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土地改革历程,所有价值判断先行的改革,都失败了,而结合中国传统和本地实际的改革都成功了。在土地这一基本问题上,你不需要马克思、亚当·斯密和诺斯,也许你只需要稍微向前看一些,看看民国时的梁漱溟、费孝通。不过你要真的会看他们,而不是仅仅会在讲话稿上念出他们的名字。这只是一个小例子,看到许章润教授的新书《汉语法学论纲》,我觉得一个一个的小例子找到了可以栖身的光明大殿。清华大学法学院的许章润教授是“文革”后第一批法学的本科生和硕士生,年届三十又远赴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学成后归国任教,自身著述和编撰丛书成绩斐然。这本新出版的小书实际上是由他之前在法学专业期刊上的论文和《南风窗》上发表过的一篇采访结集而成,主旨在于倡导中华的、汉语的法学体系和法学研究。虽然他上溯战国春秋,下至当代,但是看得出来,他最关心的还是如何接续民国以来,他所谓的“新学时代”的中华法学传统。这一传统是由接受了西方近代法律文明,却又设身处地地为当时中国思虑的那批法学家和法律人所开创的。按照许章润自己的话说,他谈论的“汉语法学”,可以说是“清末以还五代以上中国法学家群体的百年奋斗,所要集成者”,其主要思路,是“自由民族主义的共和法理”;最终的追求,是建立一种“以法权相笼统,赖法权以措置,借法权来伸张”的法律文明秩序。全书即围绕以上几点展开,分别申说了他所谓“汉语法学”的纲领,“法学历史主义”的纲领,最后以德国为比较个案,说明了当代中国在转型时期,为何历史法学登场既有学理依据,亦有现实必然。这是一本小书,却包含了许章润全面重思当下中国法律体系的雄心,和他对中国下几代法律人的寄托。这是本名副其实的“论纲”(Discourse), 有处理重大问题的视野,宏大的论调和斩截的判断。但是这本书并不好读,在仔细看了全书的2/3时,我甚至告诉自己,在中国,学习法律的人也没几个人能耐下性子仔细读完这本书。和鲍明钤简单、清新的语言不同,许章润用词华丽、古雅,但是在许多说理的段落时却带有强烈的口语化风格。他的书是需要用他自己著名的、抑扬顿挫的语调读出来的,那有一种法官宣读判词的气势,可是从阅读本身来看,他字里留给读者的空间太少了。如果说中国古代法律的传统智慧他有一点错过了的话,那就是沉默的智慧。传统中国经典的惜字如金,和对于某些话题的刻意回避,反而给读者更大的启发。排山倒海、饱含情感的申说,完全可以由更为节制的语言阐发。

三
其次,在这本书中我期待更多的具体、详细的实例,来说明汉语法学的传承究竟有哪些。许章润在提到有限的几个例子时一般是蜻蜓点水,但是这样的例子其实是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了,仅需要简单一提就可以。
我们埋葬了观念意义上的“传统”,并常常不惜一切代价摧毁实际存在的延续的“传统”,那么,到底有哪些中国传统需要被重建,到底有哪些还未被摧毁,需要我们在全盘西化的法学体系中加以调整?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更具现实关照,和支撑“汉语法学”这一宏大体系更有说服力的论据。威廉·布莱克在批评雷诺兹爵士的论纲的时候曾说“泛泛而谈是愚蠢之举,具体细论本身就是一种优点。”博而能约,才是理想之境。
不过,没有什么瑕疵可以掩盖这部著作整体价值关怀的重要性。其实,无论是在法学,还是历史学,哲学,美学,甚至是金融学,新闻学这些所谓更“实用”的领域中,我们都应重新阅读那些被遗忘的民国著作,我们都应该在接续传统的基础上,再开始谈论什么“创新”。这才是真正的进步。可悲的是,在这个简单的历史进步主义占领绝对主流的国家中,我们的历史却一再陷入循环。今天,唯一滚滚向前的是我们的GDP数字,统计本身既不完全可靠,而且即使可靠,也无法反映经济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的经济生活水平。
历史有的时候真叫人感喟:1922年,鲍明钤在离美回国前,给时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著名宪法专家古德诺(F.J.Goodnow)写了一封告别信。在信中他写道:“如果我只考虑个人利益,我会选择一个获利更多和风险较小的职业,而不是去从事公共服务事业。但我已享受的非同寻常的特殊利益,我的道义感却推动我要走一条敢冒风险的道路。我相信上帝和我的人民不会使我失败。”从1952年起就赋闲在家,后来又被抓捕的他,不知是否曾想起这封信里的话,他的内心又是什么样的感受呢?然而如果他泉下有知,知道他的文字在八十年后又被人认真阅读,曾经照亮了一颗迷茫的心灵,他是否也会有一些欣慰呢?

(文/方墨,原载于《经济观察报》)
好书推荐
阿弥陀佛么么哒
本书是大冰继百万畅销书《乖,摸摸头》之后的又一力作,依旧是独一无二的江湖故事、特立独行的泼墨文笔,却愈发有情有义、有侠者魂、有赤子心,有如一碗酒,可以慰风尘。原来和《乖,摸摸头》一样,《阿弥陀佛么么哒》一书的这些主人公、这些故事都是真的;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在过着你想要的生活:既可以朝九晚五,又能够浪迹天涯。


锌皮娃娃兵
本书为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S.A.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著。本书记录了阿富汗战争中苏联军官、士兵、护士、妻子、情人、父母、孩子的血泪记忆,是20世纪纪实文学经典作品。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些娃娃兵的母亲,尤其是当娃娃兵被装到锌皮棺材里运回家时,母亲们在墓地里讲述着儿子们的事,就好像他们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