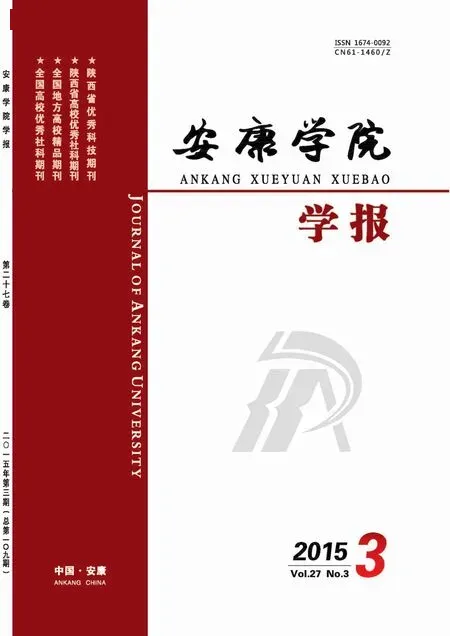再议“咬死猎人的狗”
孟荣延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一般认为,“咬死猎人的狗”是结构关系和语义关系都不同的典型的歧义短语。即:理解成动宾结构,语义关系是“动作+受事”(咬死了狗,而这狗是猎人的);理解成偏正结构,语义关系是“动作+受事+施事”(有一只狗,这只狗咬死了猎人)。这种理解忽视了多义词对短语意义的影响。沈家煊曾说:“一个词不止一个意思叫多义词。句子里有多义词,就可能产生歧义。”赵强在《从“咬死猎人的狗”说开去》一文中认为,由于“咬死”有认定、咬定之意,所以,除了前两种理解之外,本短语完全还可以理解为认定了就是猎人的狗,而不是别人的狗或者别的什么狗。本文认同上述观点,并认为有必要对这一歧义短语进行重新审视和分析。
一、多义究竟有多少
“咬死”有“认定”之义,不过还需再补充一点,“咬死”中的语素“死”也是多义的,既可作为动结式第二成分表示死亡,又可表示程度。这样一来,“咬死”就有“死死地咬住”之义,于是“咬死猎人的狗”就出现了另外两种含义:“猎人的狗被死死地咬住”和“狗死死地咬住猎人”。因此,这一歧义短语的意义不止两种,而应有五种:
1.狗咬死了猎人。
2.猎人的狗被咬死了。
3.认定了就是猎人的狗。
4.猎人的狗被死死地咬住。
5.狗死死地咬住猎人。
所以,对于“咬死猎人的狗”这一歧义短语,我们有必要重新加以审视和分析。分析的第一步就是先判断这个短语中是否有多义词,以及多义词是否会影响整个短语意义的表达,然后再从语法结构和语义关系方面进行审视。
二、对五种意义的分析
在“咬死猎人的狗”这一短语中,“的”是结构助词,表明附加成分和中心语之间的修饰关系,它是只有语法意义而没有词汇意义的虚词。“猎人”和“狗”是意义单纯的名词。这些词都不会使短语出现歧义。“咬死”则比较复杂,它有三个意思,分别是:“咬这一动作导致受事死亡”“死死地咬住”和“认定”,它们都能出现在同一语境“咬死猎人的狗”中,也就是说多义词“咬死”会影响整个短语的意义。为了行文方便,我们把表示三个意义的“咬死”分别记作“咬死1”“咬死2”“咬死3”。那么,“咬死猎人的狗”就可以有以下三种形式:
1.咬死1猎人的狗。
2.咬死2猎人的狗。
3.咬死3猎人的狗。
接下来,从语法关系和语义关系两方面对以上三个句子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1.咬死1猎人的狗。
——咬死了猎人,是这只狗咬死的。
——咬死了狗,狗是猎人的。
2.咬死2猎人的狗。
——狗死死地咬住了猎人。
——死死地咬住了狗,狗是猎人的。
3.咬死3猎人的狗。
——认定是猎人的狗。
现在我们说说“咬死”这个复合词。认知语言学认为,复合词是通过两种隐喻形式构成的:一种是“零件式”的隐喻构造,即整体是由部件组配而成。也就是说,复合词的意义是构成语素意义的叠加;还有一种是“脚手架式”的隐喻构造,构成语素好像是盖楼用的脚手架,楼房盖成后脚手架就可以撤去。
“咬死1”和“咬死2”就是“零件式”隐喻构造的补充型复合词,它们的意义是“咬”和“死”意义的叠加。语素“咬”的意义再清楚不过,而“死”却可以有多重解释,既可以表示“死亡”,又可以表示“极深的程度”。“咬”这个动作和表示死亡的“死”叠加就是“咬死1”,和表示程度极深的“死”叠加,就是“咬死2”。至于“咬死3”则是“脚手架式”隐喻构造的联合型复合词,“咬”和“死”的意义已经隐去,变成了“咬定”之意。传统的理解是“咬死1”形式,而《从“咬死猎人的狗”说开去》添加的第三种意义则是采用了“咬死3”的形式,而意义四、五则是采用了“咬死2”的形式。
在北大中文语料库中,输入关键词“咬死”,共搜索到语料355条(当代语料312条,古代11条,现代32条)。其中,意义一332条;意义二16条;意义三2条(另外5条语料是“咬死”的另一种用法,这里不涉及,略举一例:“这蚊子,快咬死我了。”此时“咬死”表示死亡,达到极点,带有夸张的说法)。之所以要统计北大中文语料库中“咬死”的用例,是为了说明“咬死”的三个意义是有据可寻且有语用价值的。以下各举两例:
咬使受事宾语死亡
1.然而即使如此警戒,有时还会有猛兽在半夜里忽然袭来,[咬死]几匹马…… 【施蛰存《驮马》】
2.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厌了。
【鲁迅《朝花夕拾》】
咬定
1.记着,你爸要是问起这事,你要[咬死]就这五千。
【柳建伟《突出重围》】
2.因此,她一口[咬死],完全不肯承认:“我没有男朋友,我年纪还轻嘛,我连功课都应付不……”
【岑凯伦《合家欢》】
死死地咬住
1.这些鱼太肯吃钩了,刚丢下去就咬钩,一口[咬死]就再不肯松口,一抬竿一条一抬竿又一条,弄得我手忙脚乱,高兴得浑…… 【崔晓《麻子阿哥》】
2.把弓上硬,把弦绷紧,把牙[咬死],一个也不能松了饶了!要叫他一个个都尝一回辣子辣。【陈忠实《白鹿原》】
另外,在机械工程学科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咬死”(摩擦表面产生严重黏着或转移,使相对运动停止的现象),它就是文中所说的“咬死2”,也可以作为一个例证。
到这里,“咬死猎人的狗”这个典型的多义短语,由于多义词“咬死”、结构关系和语义关系的影响,形成了五种意义。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把其中的名词性词语进行替换,多义的数量则又会有所不同,例如:
1.咬死猎人的鸡——只有四个意思:猎人的鸡被咬死了;死死地咬住鸡,鸡是猎人的;鸡死死地咬住猎人;咬定是猎人的鸡。
2.咬死猎人的虎——只有两个意思:老虎咬死了猎人;老虎死死地咬住猎人。
3.咬死鸡的狗——只有两个意思:狗咬死了鸡;死死地咬住鸡的狗。
这些例子的意义数量之所以不同,主要是因为人们有“鸡不能把人咬死、猎人不养虎”这样的日常经验。在例1中,鸡不能咬死猎人,因而可以有四种理解。在例2中,猎人不养虎,所以也不会形成“猎人的虎”的认识,因而可以理解为两种含义。例3中,鸡不能是狗的领有者,因而不存在咬死狗和认定是鸡的狗这样的认识,所以也只可以理解为两种含义。也就是说,“咬死猎人的狗(咬死NP1的NP2)”这种歧义短语的五种含义的出现是有一定的条件的:NP1和NP2都是有生命的活物;NP1和NP2有领属关系,或者说NP1是NP2的领有者;NP2可以咬死NP1。几个条件只要有一条不成立,整个句子就不会存在五种含义。例如,我们知道在鲁迅的作品《祝福》中,祥林嫂的儿子阿毛是被狼咬死的,所以我们在说“咬死阿毛的狼”时并不存在歧义。这是因为阿毛不可能养狼做宠物,而狼又能够咬死阿毛,阿毛确实是死了。所以,“咬死猎人的狗”之所以能够有五种意义,除了是多义词、结构关系和语义关系的影响外,还因为“猎人”和“狗”这两个单纯意义的名词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语义关系,即:猎人和狗之间可能存在领属关系;狗可以咬死猎人。
三、远未结束的解释
“咬死猎人的狗”是书面表达,在口语中很少出现。如果我们可以还原出这句话的语境来,一般都不会理解错。即使无从判断语境,在读这句话时不同的重音、停顿、句调也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这句话在表达哪一种具体的意义,同样不会造成多义误解。对于现代汉语共时平面的分析,我们常常要注意到某些语料来源于哪一种基础方言,不从任何基础方言中产生的语句往往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有不可捉摸的成分在其中,这样的语句会造成语法分析上的困难。除语料来源于哪一种基础方言的问题外,现代汉语共时平面的分析有时还要触及历时层面的分析。
“咬死猎人的狗”这种表达方式大概是受欧化句式的影响而产生的,因而我们就需要探讨欧化句式发展变化的历史,以及这种表达产生、演变的历史。“咬死猎人的狗”这一短语最早出现在哪种语料中?它在“VP+NP1的NP2”这种欧化句式中是否具有代表性?还是它只是“VP+NP1的NP2”中的特例,或是语言学家为了研究语法而拟造的一个句式?如果“咬死猎人的狗”是“VP+NP1的NP2”句式中的一个真实的、普通的用例,那么,结合“咬死猎人的狗”来分析“VP+NP1的NP2”以及其他欧化句式的产生、发展、演变就非常有语言学的意义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分析这样的宏观架构比分析“咬死猎人的狗”之所以有五重意义更有价值,但目前笔者尚无能力研究这个问题,在此提出来,旨在抛砖引玉,引起语言学界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