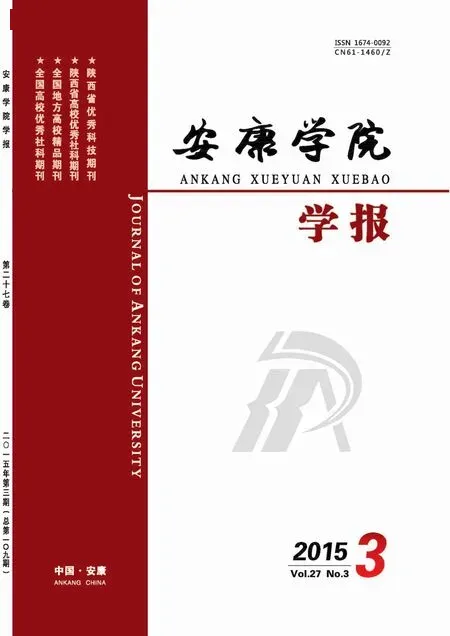音乐美的特殊性——论实验派美学家的音乐美
刘智强
(四川文理学院 音乐与演艺学院,四川 达州 635000)
英国美学家佩特(W.Pater)认为:“一切艺术其表现达到最高境界时,都逼近于音乐,因为音乐在内容与形式上达到了天衣无缝的极高境界。”[1]叔本华认为:“音乐是最高的艺术,因为它除了能表现意象世界外,还能、也能充分表现意志世界”[2]。其他艺术不能描绘、传达的,而音乐却能曲尽其蕴。音乐的旋律、节奏、和声能表现恰合人心的精微变化。个人的性格、民族的特征、时代的精神都可以从音乐中窥出。音乐不但最能表现人的心灵,更能感动人的心灵。其他艺术感动人心常常不免先假道于理智,再触及于情感,音乐固然也含有理智成分,但它的情感感召力来得最快,能直接引起心弦的共鸣。所有的人都能受到音乐的感动,只是程度不同罢了。音乐所表现的往往是超乎于理智所能分析的。在所有艺术中,音乐产生最早,和群众关系最为密切,人类离不开音乐,别的动物也少不了对音乐的嗜好。“瓠巴鼓瑟,游鱼出听”,这并不是不近情理的传说。但是音乐也是最难理解的,抽象的艺术。音乐的情感表现力大多数人都能体验到,但具体细节的表现和描写却难以寻出。对于同一首乐曲,欣赏者的感受从大的方面能取得一致,但细节描述却各有千秋。音乐美在何处?争议颇大,不要说一般听众难以回答,专家也难以给出个标准答案。表现派美学家说“音乐之所以美:在于表现情感和思想”[3];而形式美学派则说“音乐之所以美,在于音乐自身与形式之完备,情感和思想在于它的形式之外,是偶然的、不必要的”[4]。这个论争在音乐学上一直在延续,直到今日也没有权威的结论。我们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对此,可以求助于现代实验派美学家们,听听他们讲的道理及由实验所得的证据,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启示。
一、从情感价值和精神价值评判音乐的审美价值
当今活跃的西方实验派美学家有英国剑桥大学马尧斯教授(prof.C·SMyers)、美国美学家浮龙·李(VernonLee)、英国女王大学瓦伦丁教授(prof.C·W·Valentine)、盖尔尼教授(prof.Gurney)、美国心理学家奥特曼(Ortman)和休恩(Schoen)等。他们通过实验来论证音乐美的本质,提出音乐的实验材料为:关于听音乐者的反应的区别;关于音乐与想象的关系;关于音乐与情感的关系;关于音乐与生理的关系。
马尧斯教授将听音乐者分为四类。选出六种名曲在受验者背后播放,每首曲子播放两次。让受验者听完第一次之后,把音乐引起的感想说出来。第二次播放时尽量让效果更好,让受验者镇静细听,须把心中感想详细记录下来。从15个受验者内省所得的报告中,马尧斯分析出以下四种感受类型:
第一,主观类(生理类)。受验者注重音乐对于感觉情绪和意志的影响。受验者的报告中只谈到一些官能感受,比如:“非常愉快,很兴奋,像流水似”的等等。
第二,联想类。专注音乐所引起的联想,以联想事物为标准来断定音乐的美丑。受验的生活阅历、文化程度、个人爱好、整体素质将起到重要作用,直觉能力的大小也起相当重要的作用。一位受验者说:“我仿佛坐在皇后的大厅里。一位穿红衣裳的女子在拉提琴,另一位女子在对着琴谱唱歌。那位拉琴者面容很凄惨,她生平一定有什么失意的事。”联想到了一个具体的事件画面,不同受验者联想的事件各不相同,但讲得都很具体。
第三,客观类。用作品音响结构客观的标准来感受音乐,从音乐语言本身论技巧的表现优劣。受验者具有专业知识,只顾及作品陈述过程中所运用的技术手段。比如受验者说:“我觉得第二小号声音太洪亮。到第三小节弦乐不够力度”[5]“在贝多芬的作品中应注意力度的反衬,尤其是展开部动力反衬不够。转调手法新颖”“小提琴颤音太过火”[6]等等。都是从专业角度感受音乐。完全关注于作品本身的物质表现。
第四,性格类。把音乐加以拟人化,突出作品的性格。不同的作品表现出不同的性格,有悲惨的、忧郁的、神秘的、狂放的、幽默的、幻想的、戏游的、欢愉的、激昂的、果断的、愤怒的等等。如报告中:“它本想显出高兴的样子,但最终于很悲惨”“有些部分带有悔悼的声调”等等。完全赋予音乐某种定型化的情感。
以上四种音乐审美类型,马尧斯以审美价值的原则做出高低排序:最高类——性格类,次之客观类和联想类,最低类——主观类。性格类最高的原因,主要在于它能使欣赏者主体达到“物我两忘”的最高境界。性格类中必然少不了另外三类的作用,它包含了主观类、联想类和客观类。尤其是联想类,没有联想就不会唤起情感,没有情感就很难实现“物我两忘”。主观类是初级的,也是大众的、普及的。因为它只注意到官能满足,而忽略了音乐本身的形式及特性语言的表现作用。这种态度没有从审美的角度达到目的,把音乐作为功利性工具,没有意识到布洛所说的“心理距离”,或距离为零。联想类的优点在于意识到了直觉的作用,找到了音乐感受的合理途径,但片面强调了感性,缺乏必要的理性。自由联想可超越时空,及时获得情感,但这种情感往往是暂时的、模糊的、零碎的、偶然的。如果将联想的情景与客观类、性格类融合为一体,化成一气,契合无间,它就能增大音乐美感了。音乐专家大半属于客观类,这是由于他们受学习及系统训练的影响,只注意偏向技艺方面,忽略了情感和联想。就技术论技术,其态度是批评的多而欣赏的少。
马尧斯的音乐心理实验,将音乐感受分成四类,对音乐美的本质认识有一定的价值,通过事实得出结论让欣赏者多去关注音乐的性格表现,音乐与人类情感的高度统一,从人类情感价值、精神价值去评判音乐的审美价值,他的观点是非常激进的。
与马尧斯实验相接近的美国美学家浮龙·李用同样的方法证明,音乐欣赏的经验不外乎有两种:一是只顾音乐本身;二是音乐所联带的意义。在受验者中,只顾音乐本身意义者是多数,而肯定音乐别有意义的所谓“意义”大半是模糊隐约的。否定音乐别有意义的人们大半只留意形式的配合,如呼应、起—转—合、抑扬顿挫等。较多的受验者都否定音乐于本身之外别有意义。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浮龙·李实际上通过实验提出了音乐的自律与他律问题——这正是历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
二、将“固象”转化为“动象”,呈现出流散音乐语言
历史上长期以来音乐笼罩在他律的迷雾中。奥地利美术家汉期力克首先提出音乐的内容在于音乐自身,却遭到多数人的反对。从此,音乐学中围绕音乐美的本质舌战不止。浮龙·李通过实验再次欲想澄清音乐自律这个问题,然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但可证明音乐的意义在于本身确为多数人所肯定,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对于大多数听众而言,只注意到了音乐的实际感受,构成不定的幻想画面,联想起了很大作用。音乐这种“非具象性”的“形象性”的确能激发人的情感。意象来自于浩瀚的幻想。光怪离奇,只是玩味而没有真正达到欣赏。法国心理学家里波(Ribot)的实验证明玩味意象和审美欣赏是两回事,他通过受验者得出结论:欣赏音乐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有音乐修养的,音乐却很少引起意象。受验者说:“我绝对意想不到什么视觉的印象;我浑身被音乐的快感占据着;我完全在听觉世界里尽情地享受快乐。我根据自己的音乐知识去分析各部分的呼应,但也不过于仔细推敲。我只留心乐调的发展”。这是纯形式的欣赏。一类是没有音乐修养而欣赏力平凡的。这些人听音乐时常发生很鲜明的视觉意象,因为只顾玩味意象,而不注意音乐本身的形式。意象分为造型的“固象”和流散的“动象”。造型的“固象”以知觉为中心,宜于图画,因为它能产生极明确的意象。而流散的“动象”以直觉情感为中心,宜于音乐,因为它所产生的意象虽极模糊而却常常深邃微妙。里波认为“古典乐派”的作品注重客观,富于“造型的想象”;浪漫乐派、印象乐派和表现乐派注重于主观,富于“流散的想象”。想象在于造型者喜欢把迷茫隐约的东西变成固定清晰的东西。所以在听音乐时,常把耳所闻者以为目所见的图画。然而,作曲家在创作音乐时,心理过程则恰与此相反,将“固象”转化为“动象”以不易描绘的流散音乐语言构成作品,这正是音乐本质的表征。
音乐中的幻想,并不是无根据的想象。幻想之前必须有联想。联想经历直觉和认知过程。直觉之前又少不了潜意识过程。“潜意识到显意识,再到意识。这个思维过程不可颠倒”[7]。幻想是音乐思维不可缺少的想象。它不能脱离由直觉到知觉的思维过程,更不能脱离潜意识的积累过程。盖尔尼认为,凡是一种幻想唤起某种意象时,它的节奏、音调大半和事物的动作有直接的类似点。瓦格纳取鸟语入乐曲,肖邦取急雨堕瓦声入乐曲,都是著例。音乐具有模仿、象征和暗示的功能。如:飘荡幽婉的舞曲可暗示仙女,沉重低缓的舞曲可暗示巨人。普赛尔(Purcell)用向下移调暗示特洛伊城(Troy)的衰落。用特殊音调去象征某一声件或某一事物的特性。还可用谷鲁斯所说的“内模仿”以情代景等等。
音乐中的意象模仿(情感模仿)——“内模仿”很复杂。美国梵斯华兹教授(prof.Farnsworth)和贝蒙教授(prof.Bemont)安排一班学图画的学生听两首性质不同的音乐,要求学生将感受的意象画在纸上,作品主题和作家都不让学生知道。结果,同学们所画的图画彼此很少有类似点。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作品所营造的环境气氛则很相近,突出表现在所选用的色彩上。音乐凄惨时图画的基调色彩很黯淡;音乐喜悦时图画的基调色彩却很鲜丽。可以看出音乐虽不能唤起一种固定意象,却可以引起一种固定的情调。人类感受艺术的共性来源于艺术审美的共性,隐含着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和“原型观念”。同样的作品引起了同样感受,只在于表面轮廓。而实际过程却因人的性格和经验而异。正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幻想都是意识欲望的涌现,所以,幻想中的意象都象征情欲中的一种倾向。人的幻想欲望是原始的、普遍的,而音乐幻想是使被压抑的幻想欲望得以化装涌现,于是才有音乐的意象。
音乐幻想中有一种奇妙的现象——“着色的听觉”(Colour-hearing)。用耳朵“看见”色彩,用眼睛“听见”声音。这在心理学上叫做知觉通感。的确是这样,有的人听音乐就会联想到相应的色彩——颜色。同一个作品各听者联想起的色觉往往不一致。美国心理学家奥特曼通过实验告诉大家,有些人听高音产生白色的感觉;中音产生灰色的感觉;低音产生黑色的感觉。从低音到高音顺次产生黑、棕、紫、红、橙、黄、白诸色。德拉库瓦做同样的实验在报告中说,他也曾见过一位瑞士学生每逢听大提琴的声音,都仿佛见到一条波动的黑色蓝边的长带;听到柴可夫斯基的悲怆音乐时,眼前好像看到了蓝色。有人说瓦格纳在创作《尼伯龙根的指环》时,在莱茵河上观日落之后得到了灵感一挥而就。这种“着色的听觉”对于每个人都是基础的,它是听觉神经和视觉神经混合产生的生理现象。法国印象派运用“通感说”(Correspondance)发展了这一理论。实际上也是谷鲁斯所说的“内模仿”。自然界中声色形象虽似各不相谋,其实是遥相呼应的,由视觉得来的印象往往可以和听觉得来的印象相感通。所以,某一种颜色可以象征某一种形象或是某一种音调。
三、音乐对人的神经有影响,对筋肉及血脉运动也有影响
实验美学对于研究音乐与情绪的关系所得的成绩比音乐和想象的研究更为丰富。音乐与人的情绪有着必然的联系,不单是人类,动物对音乐也具有嗜好。据美国音乐心理学家休恩(Schoen)所引例证,不同动物对音乐的反应各不相同,在动物园里拉琴,观察到:蝎子舞动,随旋律的高低而异其兴奋;蟒蛇昂首静听,随音乐的节奏左右摇摆;熊兀立静听;狼则恐惧号啼;大象常喘气表示愤怒;牛则增加乳量;猴子点头作势。音乐唤起动物的不同反应,说明音乐的感染力是原始普遍的。达尔文以为音乐的起源在异性的引诱,所以在动物中以雄性的声音为最洪亮、最和谐,弗洛伊德学派学说颇近于此。
古希腊人就知道情绪与调的关系,给流行的各种调以固定的情绪。如E大调安定、D大调热烈、C大调和蔼、B大调哀怨、A大调昂扬、G大调浮躁、F大调淫荡。亚里士多德最推崇C大调,因为它和蔼,易于陶冶青年的情操。虽然,古希腊人对各调情绪论述不一定合理,但说明古人是如此地重视音乐与情绪的联系。近代英国人鲍威尔(E·Power)也作了同样的研究。他认为:C大调纯洁、果断、沉着有力,且具有宗教色彩;G大调真挚、诚恳、平静友爱,具有田园风格;g小调忧愁、叹息;A大调自信、和悦;a小调柔情、伤感、虔敬;B大调嘹亮、勇敢、豪爽;b小调悲哀、恬静;#F大调情感饱满,充满热情;#f小调阴沉、神秘;bA大调梦境的情感;F大调悔悼;f小调悲愁。对于音程鲍威尔也有其说,按协和程度确定其相对固定的情绪:纯八度最完美,间或表现激情、焦躁或哀悼;纯五度平静、欣喜,间或带有伤感;纯四度欣喜、满足、颜色、力量、发扬、间或伤感;大三度勇敢果断、自信;小三度悲伤、愁苦、骚动等;小六度静穆;大六度柔情、希望略带伤感;大二度愉快、严肃气;小七度疑虑;小二度悲伤、痛悼、焦躁、疑虑;大七度疑虑、信仰,间或表示希望等。以上情绪与音程的关系是否有科学的依据,无法下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情绪是音乐的基础对象。音乐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其表现手段构成本身的特殊形式。每一种语言要素其表现手段都离不开情绪的反映。
听众对音乐的接受,少不了关注音乐语言。各人所关注的语言要素不同,有人偏重于节奏,有人偏重于音色,有人偏重于形式,有人则偏重于织体等等。美国心理学家华希邦(M·F·Washburn)和狄金生(G.·R·Dickinson)把音乐美感的来源分为节奏、旋律、曲式、和声、音色五种。他们通过问卷测试学音乐的在校生,得出结论为:旋律最重要,依次是节奏、和声、曲式、音色。旋律在一般音乐家那里占第一位,在亨德尔、勃拉姆斯、德彪西等人的作品中占第二位;节奏在勃拉姆斯的作品中占第一位;和声在海顿、贝多芬、舒曼、肖邦、门德尔松、德彪西等人的作品中占第一位;曲式没有音乐家把它摆在第一位,只是在巴赫、莫扎特的作品中占第二位;音色只有德彪西把它放在第一位,其余青年音乐家都把它放在第三、四位。美国心理学家宾汉(W·V·Bingham)、休恩(M·Schoen),通过对两万人的实验测试,得到以下重要结论:第一,每首乐曲都要引起听者情绪的变化;第二,同一首乐曲在不同时间给许多教育环境不同的人们听,所引起的情绪变化往往很近似;第三,情绪变化的大小与欣赏水平的高低成比例;第四,音乐的陌生往往能影响欣赏程度的深浅,但欣赏水平的高低不易受陌生差异的影响,欣赏力愈差者愈苦于陌生的新音乐不易欣赏;第五,听音乐者可分三类:欣赏力弱者欣赏时甚少,欣赏的强度也甚小;欣赏力平庸者欣赏时甚多,欣赏的强度却甚小;欣赏力强者欣赏时甚少(因为慎于批评),但欣赏的强度却很大(因为了解技艺);第六,情绪的种类与欣赏的强度无直接关系,惟由和悦而严肃时比由严肃而和悦时所生的美感较小;第七,对于乐曲价值的评判与欣赏的强度成比例;第八,音乐只能引起抽象的普遍的情绪,如平息、欣喜、凄恻、虔诚、希冀、眷恋等等,不能引起具体的特殊的情绪,如愤怒、畏惧、妒忌等等。音乐所以能影响情绪者大半由于生理作用。关于声音的生理基础,学说颇多,实验美学家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进行论证,认为音乐不但对神经有影响,对肉身的筋肉及血脉运动也有影响。据斐芮(Feary)、斯库普秋(Scripture)诸人的研究认为,声音都可以使筋肉增加能力,迅速的和愉快的音乐尤其可以消除筋肉的疲劳。孟慈(Mentz)发现凡在音调完全和谐时、音的强度猛然更换时以及一曲乐曲将结束时,血脉和呼吸都变慢;在听者注意分析乐曲时,血脉和呼吸都变快。据福斯特(Foster)和干伯尔(Gamble)的研究,人在平常呼吸时很有规律,而在听音乐时大半没有规律。据海依德(Ha M.·Hyde)的报告,悲伤的音乐可以使血脉速度变缓,愉快的音乐可以使血脉速度变快,生理的变化和心理的变化是相平行的。对于音乐的生理反映,心理学家还在不断探索,把音乐纳入医疗学已不再只是初显端倪。
四、结语
大量的实验证明,音乐美的素质来源是多方面的,无论从“本我”“自我”和“超我”都能找到理论依据。叔本华给音乐的定义是“意志的客体化”(The objectification of will),其他艺术表现心灵都须借助于意象,只有音乐才能不假意象的帮助而直接表现意志。瓦格纳追随叔本华的意志论,进一步倡导音乐的“戏剧化”,开近代“乐剧”(music drama)的先河。这种音乐表情说与当时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相吻合,都是注重情感,薄视古典派的明晰的形式。浪漫时期的音乐大半迷离隐约,没有明确的轮廓,就是受表现说的影响。
表现说认为音乐与语言同源,语言背后本已有一种潜在的音乐,正式的音乐不过就语言所已有的音乐加以铺张润色。英国美学家斯宾塞(Spencer)说,音乐是一种“光彩化的语言”(glorified language),他以为情感可影响筋肉的变化,而筋肉的变化则可以影响音调的强弱、高低、长短。乐器所演奏的音乐是由歌唱演化出来的。形式派美学家汉斯力克极力反驳瓦格纳的音乐表情说,他认为音乐就是拿许多高低长短不同的音砌成一种很美的形式,在形式之后绝对没有什么意义,音乐的美完全是一种形式的美。也就是说音乐的美不在于它能唤起情感,它除了形式之外别无所有。如果审美能引起快感,这是音响和“美”的本身不是一件事,音乐的目的能引起快感,但这个目的与“美”的本身却不相干。“美”纵然不能引起任何快感,纵使没有人去看它,它却仍不失其为美。也就是说美虽是为给欣赏者以愉快而存在的,但其可否存在却不依赖它能否给人以愉快。这是形式主义昭示的内涵。他律论与自律论各自持之有理,然而音乐都是抒情的表现,都是实质和形式婚媾后所产生的宠儿。有内容而无形式则粗疏,有形式而无内容则空洞。专在形式上下功夫而不能表现任何情感的音乐究非上品;专在表现上寻求固定的具体情思也没明白音乐表现的真实涵义。德拉库瓦说得好:“音乐把情感加以音乐化”。音乐所表现的情感既有殊相,又有共相,是普遍的抽象性情感。对于特殊的具体的情感,音乐的确无能为力。由普遍的抽象的情调而引起特殊的具体的情思,这是由全体到部分的联想,一般人因为听某种乐曲时引起某种特殊的情感或意象,便以为该首乐曲就是表现某种特殊的情感或意象,这就陷入以偏概全的谬误。前面梵斯华兹、贝蒙、宾汉、休恩等人的实验报告,均已澄清了这一问题,证实了音乐美的本质所在和特殊性。
[1]KGROOSK.(1)The play of Animals,(2) The play of Men[M].Washington:Washington press,2008.
[2]GROSSE.Origin of Art[M].Washington:Washington press,2006.
[3]SPENCER.Essays[M].New York:New York press,2008.
[4]BERGSON.Essai Surdonnees im mediates do la conscience[M].New York:New York art press,2009:256,320.
[5]阿恩海姆,霍兰,蔡尔德.艺术的心理世界[M].周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62.
[6]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142.
[7]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6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