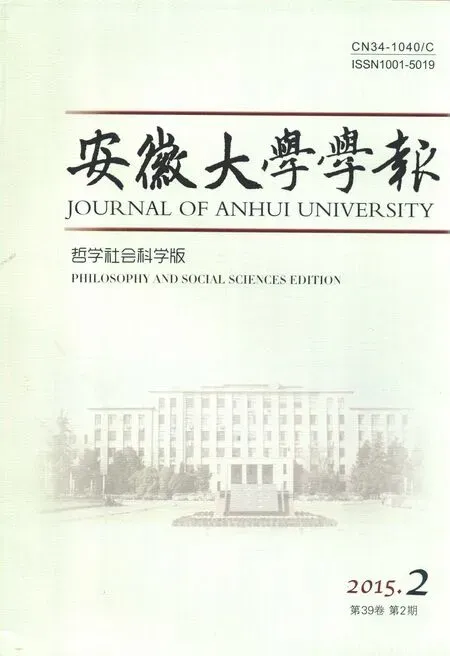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方汉奇先生治学答问
方汉奇 口述,王天根 访问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方汉奇先生治学答问
方汉奇 口述,王天根 访问
摘要:方汉奇认为,新中国的前30年,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不多,中央党校编写的《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是代表性成果,其重要意义是填补了1949年以前中国新闻史领域有关中共党报历史的空白;改革开放后,由其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凝聚全国新闻史研究力量的成果,但由于种种局限,《通史》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阶段性成果,等待今天的研究者填平补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未来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应注重史料积累,不断解放思想,开拓新领域。
关键词:方汉奇;中国新闻史;新闻史史料;口述史
方汉奇,广东普宁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曾被评为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1984年),著作两次获吴玉章新闻学奖一等奖(1987年、2002年)。著有《中国近代报刊史》《报史与报人》《新闻史的奇情壮采》《发现与探索》等书,主编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新闻传播史》等书,发表论文200余篇。是1949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拓者和组织者,为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日,笔者就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历程、现状及未来展望等学术问题与方汉奇先生进行了对话。
一、新中国前30年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回顾
王天根:方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中国新闻史的教学、研究,可以说是新中国建立后新闻史研究工作的最早参与者之一。您能否谈一谈建国初期中国新闻史的研究状况?
方汉奇:新中国建立以后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这30年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不多。这一时期新闻史研究工作的重点,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报刊史,比较大的成果就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史轮廓给勾画出来了,留了一套中央党校的《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这部讲义是50年代初期中央党校编写的,着重介绍和论述了五四运动以后到建国以前的近30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报刊的历史。1959年,这部讲义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作为内部教材铅印出版。当时出版的讲义并未署名,实际上是中央党校新闻班的“四大金刚”——李龙牧、丁树奇、黄河、刘爱芝共同编写的。这四人在50年代初期被调到中央党校组织一个新闻班,给他们一个任务,将党的革命报刊史写出来。写作中有分工,李龙牧写得多些,有两章,即第一章、第五章,黄河写了第二章,丁树奇写了第三章,刘爱芝写第四章。这部讲义虽有五册,但字数不多,印得也粗糙,基本上就是用五章篇幅讲述完建党至建国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革命报刊史。后来李龙牧、丁树奇去了复旦大学任教,黄河、刘爱芝去了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他们分别又编写了各自学校所需要的教材,这就是: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讲义》,196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印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实际上这两本教材都是以中央党校讲义为基础,各自重新编写出来的,所以1959年的讲义就有了复旦版、人大版。
总的来说,这几部讲义和教材是新中国前30年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弥补了旧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的空白,奠定了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史学的基础。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这几部讲义和教材确实属于建设性的工作。你看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他基本上不谈中国共产党的报纸,《向导》《新青年》《每周评论》等都提到,但主要是用一些基本的数据,大概一两行、两三行就完了,几十个字、百把字就完了。那是因为戈公振的书是1927年白色恐怖时期写成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报纸基本上就不能提了,当然他的书重点也不在后头。以今天的眼光看,尽管《中国报学史》后面部分还是很注意当代新闻史,但是它的当代新闻史主要是反映在经营管理、硬件建设、新闻实践等方面,重点还是早期的报刊史,即古代至清末的报刊史。所以,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新中国前30年新闻史的重点成果就是复旦、人大出的教材和讲义,它填补了过去新闻史研究未曾注意的方面。当然,在这个缺口以外很多问题(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在这30年里没有得到重视和研究。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不重视,二是当时的阶级斗争为纲,旧的东西、过时的东西只能批判。
王天根:您觉得这30年里还有没有其他值得称道的研究成果?
方汉奇:其他的研究也是有的,但总体看是七零八碎、不成系统的,没有上面提到的几部讲义和教材有系统、有整体感。比如李龙牧所写的有关《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历史的文章,丁树奇所写的有关《向导》历史的文章,以及王芸生、曹谷冰合写的有关《大公报》历史的文章,吴范寰所写的有关《世界日报》历史的文章,这些文章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在党的革命报刊史以外,有个别研究者对古代的新闻事业有兴趣,比如黄卓明。黄卓明的古代新闻史研究还是下了功夫的,他是解放前的老报人,1983年出版了《中国古代报纸探源》。但黄卓明的研究不是很规范,一些内容没有详细的出处,比如他引用某本书就只有作者、书名,没有出版社,没有页数,核实起来比较困难。我在50年代也写了几篇关于古代报纸的文章,主要是发表在《新闻战线》上的《谈邸报》《历代封建王朝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迫害》等。
不过,这一时期出版了不少带有资料性质的新闻史参考用书,即便在今天也仍然有价值。比如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三集《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潘梓年等编撰的《新华日报的回忆》,张静庐编辑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阿英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和徐忍寒辑录的《申报七十七年史料》等等。
王天根:新中国的前30年里,中国新闻史研究折射了特定历史阶段的某些特点,比如对阶级斗争的强调等。作为亲历者,您觉得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中国新闻史研究有何特征?
方汉奇:上世纪50年代初期新华社出了一个杂志《新闻业务》,这是单独出版的新闻业务刊物中比较早的。此外,《人民日报》经常隔几个礼拜或者隔一个礼拜有半个版面是关于新闻工作的探讨,主要是针对现实的新闻工作方式方法的一些讨论。到了1957年,人民日报社就出了一份《新闻战线》杂志。我们可以做个统计,看看从50年代初期到1978年这段时间,新闻业务刊物上或者报纸上有关新闻史的文章有多少,恐怕只有几十篇。这些新闻业务刊物上的文章大部分是关于现实的,涉及现实新闻工作中采、写、编、管等问题的探讨,还有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方法;新闻史是一点花花草草,都是作为点缀的。我在198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繁盛状况*指的是方汉奇《花枝春满 蝶舞蜂喧——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闻史研究工作》一文,见《新闻研究资料》1986年第34辑,后收入《方汉奇文集》《方汉奇自选集》等。按,文中的脚注均为访问者添加。。写这篇文章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到七年的时间,我当时统计:公开出版的新闻史教材、专著和文集有20余种,公开发表的有关新闻史的文章累计达3683篇,新闻史座谈会和研讨会不下12次,陆续创办了《新闻研究资料》、《新华社史料》、天津《新闻史史料》、《湖北省武汉市新闻志参考史料》、《武汉新闻史料》、《新闻界人物》等新闻史专业刊物。所以说,前30年和后30年真不可同日而语。
在前30年,我观察新闻史教学和研究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阶级斗争一抓紧了,刊物上关于新闻史的文章就没有了;等到阶级斗争这根弦略有放松,刊物的编辑就各处找研究人员、高校教师组稿。像1956年,就是50年代最好的一年。那一年是科学一片天,“脱帽加冕”,给知识分子说好话,是知识分子在前30年最风光的一年。我那时候在北京大学任教,教授理发不排队,洗澡也是优先进去。那时候还组织知识分子去东北参观、去西北参观。那一年北京大学在暑期组织教师去东北,我参加过那次活动,从北京到长春看第一汽车制造厂,到沈阳看重工机床厂,到大连看造船厂,然后坐船回到天津、北京,这就是1956年最风光的时候。当时大家都很高兴,以为明年还有机会,结果第二年就开始反右了。
1956年在新闻史上也是值得记忆的一年。那一年《人民日报》改版,主要目的就是把报纸上的“八股”文风稍微改一改,让报纸的可读性更强一些。当时《人民日报》还推出杂文专栏,很多北大中文系的教授被邀请去写文章,其中一位阎简弼教授写的很多。报纸上的杂文,实际上类似于副刊文字,有点像是《燕山夜话》那种类型的。这位阎老师经常两个礼拜发表一篇,篇幅都不长,也都是大一点的豆腐干,但是《人民日报》的影响大、读者多,大家都说写得不错,他也挺高兴。后来反右斗争开始,这个阎老师调到沈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自杀了*另说阎简弼在1968年被迫害毒打致死,见马千里《阎简弼先生遗事》,《燕大校友通讯》第58期,2010年6月。。总的来说,前30年基本上是阶级斗争为纲,所以新闻史的教学研究重点就是完成了一部《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就是党的报刊史,基本上将基础打好了;后来的教材都是在那个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拓宽的。
另一个方面,是书写体例、研究思路上的模式化。这方面有两个特点:一是学习苏联模式,二是强调革命模式。解放以后我们有一个比较传统的模式,那是受苏共报刊史的影响建立起来的。50年代初期,我们翻译出版了苏共报刊史、布尔什维克的报刊文集,还有苏共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苏共报刊史的特点就是突出苏共党内的路线斗争,每一章都是什么什么报为了什么什么而斗争,和党当时的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紧密联系,主要内容就是介绍前期的《火星报》、列宁早期办报活动,加上马克思恩格斯编辑《新莱茵报》等。所以,翻译、介绍、引进、学习苏共报刊史是建国初期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的重要部分。当然,这方面的教学研究活动也就到5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党开始分道扬镳之后就画上了句号。现在我们知道苏共报刊史是斯大林搞的那一套,完全是为他自己做铺垫的。但当时我们是学习那套模式的,甚至在5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后也远没有结束,前面提到的中央党校编写的内部教材《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以及复旦版、人大版教材等都是按照这个模式编写的。
前期新闻史研究的另一个特征就是革命模式,研究历史基本上都要往革命史上靠。那个时候我写过一篇关于太平天国的新闻史文章,发表在1958年《新闻战线》第3期,题目是《太平天国的革命宣传活动》。后来出版的《报史与报人》及汕头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文集时,收录了该文,但对部分内容进行了改写和扩充。50年代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花了很大功夫,用了半年的时间把太平天国的文献看了一遍,也就只写了3000多字,多了没有。太平天国是革命,是革命的就可以研究,而且要加以弘扬,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洪仁玕是想办报纸的,但到最后没有办成。然后就是义和团可以研究,只是义和团也没有报纸。改革开放前,还可以研究的是鲁迅。关于鲁迅的办报活动我写过四篇,其中两篇牵强附会,最后只选了两篇放在文集里。后来编《发现与探索》自选集的时候,就只留下一篇,因为那一篇写鲁迅如何批判资产阶级报刊的,用了不少“大批判”的语言,带有无限上纲的“文化大革命”的色彩,就从略了*实际上,2003年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汉奇文集》选的是3篇,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汉奇自选集》选的是2篇,2009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发现与探索:方汉奇自选集》只选了1篇。。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新闻史研究
王天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新闻史研究进入繁荣时代。您于1981年出版了《中国近代报刊史》。后又组织全国新闻史研究力量,主编了《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从总体上,您如何评价两个时期的中国新闻史研究?
方汉奇:前30年真是乏善可陈,主要是后30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新闻史也就那样了,也就是在党报史上有一些基本建设,这正好弥补了包括戈公振在内的解放前的新闻史研究者的不足。1978年以后,中国新闻史研究有了迅猛发展,这首先表现在人才队伍扩大了。前30年做新闻史的也就四五个学校、十多个研究者,利用课余时间惨淡经营。现在新闻学教学点有七八百个,大学的新闻专业也有六百余个,数得上成规模的新闻院系也有几十个。在人才队伍方面,前30年和后30年简直没法比。所以说,改革开放以后是新闻史研究的黄金时期,到今天仍是方兴未艾。现在的中国新闻史研究不光是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局面,在世界新闻史的学术史上也是空前的。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新闻学研究队伍,研究它本国的新闻史,或者世界的新闻史,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新闻史研究投入这么多力量,比如中国新闻史学会不仅有中国的研究者,还有华裔新加坡人卓南生(日本龙谷大学教授,现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人足立义雄(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参加,这是全世界没有的。中国新闻史教学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即将完成的成果和正在研究中的成果都是空前的,中国人有重视历史研究的传统,而中国新闻史确实有丰富的实证研究的内容,这个矿是个富矿。可以期待,像王老师你牵头的民国新闻史研究完成以后都是皇皇巨著。如今新闻史研究的成果真是前30年没法比的,赶上了就是有幸。
另一个巨大差别是研究领域的不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了。前面说过,前30年基本上就是党的革命报刊史研究,其他的研究主题也要往革命上靠。现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从单一的中共党报史扩展到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其他党报史的研究,还有几个比较具有特色的研究方向,比如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史研究、港澳新闻事业史研究、海外华文报刊史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报刊史研究等等。另外,地方新闻史志的研究和编写工作也有很大的进展,不少省市都建立了专门的机构,组织人员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成为新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军。重要报纸刊物历史的个案研究和新闻界人物——著名报刊活动家、著名报刊政论家和名记者的研究,过去是一片空白,现在这方面的成果最为丰硕。
王天根:您在1985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新闻史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新闻史的研究尤其要注意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但直到今天,学习和研究新闻史的专家仍然更多注重新闻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您提出“新闻史是文化史的范畴”这一观点有何特殊的背景?
方汉奇:确实,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方汉奇《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见《新闻纵横》1985年第3期,后收入《方汉奇文集》《方汉奇自选集》等。。这个观点,我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或者说理当如此。之所以在前30年里没有觉得它是理当如此,是因为在观念上把新闻给窄化了,把新闻史的研究窄化了,窄化得非常现实,非常功利化,也是将媒介的现实功能考虑得太多了。实际上,报刊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会永远被后人保存下去。我看王老师也开掘了那么多古代的近代的报刊,不都是表现为当时文化的一种载体,才被你纳入研究对象的吗?如果报刊没有“内容”,它的价值也就大大降低了。建国以后我们考虑的报刊一个是斯大林所称的“最远的炮弹”,一个是毛主席的“几个功能”,都是从革命需要、从宣传需要的角度考虑的。革命家当然首先要考虑报刊的现实功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相关的言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学者、研究者来说,视野、思考的方面应更宽一些,不能只局限于革命的现实功用。这就跟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对文艺的界定类似。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将文艺的功能界定为“为政治服务”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但是文艺只有政治功能吗?肯定不完全是政治功能。作为学者从事的研究工作,和作为革命家、政治家去研究相比,视野应该是更宽一些。过去是革命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考虑报刊的功利性更多一些,所以报刊的政治功能成为唯一的功能。但其实不是唯一的,只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像延安文艺座谈会所强调的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革命家当然是这么提倡,但是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诠释,文艺还可以拯救灵魂,可是灵魂和政治有什么关系呢?
王天根:您主持编写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可以说是建国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一定程度上说,正是这部《通史》奠定了中国新闻史在学术界的地位。作为新闻史研究者,我从2003年开始也带领一些研究生编写新闻史史料,但写《中国近代报刊史探索》一直是我一个人在写。我感觉,一个人写的好处就是语气、文笔都是一贯的,风格非常一致,某个问题没有研究到,可能马上就能感觉到;但另一方面,一个人写对自己的知识结构是很大挑战,明显感到自己对编辑技术、印刷技术、纸张之类的知识,力不从心。所以,很好奇的是:这部皇皇巨著从1987年立项到1992年出版,仅仅用了五年的时间,您是如何聚集全国新闻史研究力量的?
方汉奇:确如你所说,这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在研究、写作时间上不长。如果不是集中全国的力量,几乎不可能完成。实际上,我在组织力量撰写《通史》之前,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的编写工作,我负责的是“中国新闻事业”部分。我这个负责人只是做联系工作、组织工作,每一个词条都需要一个作者,每个作者都是这方面的专家。词条的字数从300字、500字一直到最大,像《人民日报》也就是给5000字,可能还不到。但是大百科全书的编写要求相对的稳定、高度的权威,这就需要大量组织工作。我主要负责中国新闻事业这一部分,就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和现状,所以就广结善缘。在这个基础上,和全国许多院校、新闻研究所建立了联系,后来大家就有合作的可能,否则短期内完成一个大课题是不容易做到的。再加上上世纪80年代是修地方志的高潮,全国都在修地方志,地方志都有新闻志,因此又有一批从第一线下来的老报人从事地方新闻史的研究,这批力量是80年代新闻史研究队伍当中的一个方面军。所以80年代之后,新闻史学术研究的团队一方面是高校的新闻史老师,一方面是各地新闻研究所的新闻史研究人员,还有就是各地方搞新闻志的老报人。编写新闻志只是他们退下来以后的一种社会工作,但是这些人都是老报人,对中国新闻事业的某些方面非常熟悉。所以,《通史》就是这三方面的力量凑起来的,共计24个单位47位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否则短期内完成也是有困难的。
王天根:这部著作出版于1992年,距今已有二十余年了,您有没有打算对这部著作进行修订?如果修订的话,打算从哪些方面着手?
方汉奇:如果有机会修改的话,主要是“填平补缺”。《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内容只写到1987年,距现在都快30年了,而这30年变化很大。最近十多年出现了一大堆新媒体,而《通史》连互联网都没提。从媒介史的角度看,最近30年太关键了。20世纪之前的新闻事业就是纸媒体,上千年没有变化;但20世纪初有了无线电,1922年有了广播,1958年有了电视,到了1987年有了互联网。第一个E-mail是1987年清华大学发出的,这又过去了二十多年,然而这二十多年的新闻事业、传播事业发展太快了。上世纪80年代初,“传播”这个词从美国引进的时候,施拉姆师徒二人来中国宣扬、介绍传播学的时候,官方还是反对的。曾担任过中宣部副部长、广播电视部部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就认为“传播”是资产阶级的,不是无产阶级的,反对使用“传播”这个词和有关传播学的研究。可是没过多少年,现在很多大学的新闻学院、新闻系都叫新闻传播学院、新闻传播系。观念在变化、形势在变化、媒体在变化、手段在变化,这30年变化太大了。所以我认为,《通史》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它放在那里等待后来的研究者填平补缺。
王天根:是的。从1987年到现在,无论是现实中的传播环境、传播媒介、传媒运作等,还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主题、视野等均有较大变化。我们知道,您不仅关注历史上的新闻事业,对现实中的新媒体也很感兴趣,使用微博、微信等。您在这方面有何经验呢?
方汉奇:只要当一天老师,就得学习一天,就得关注新闻事业的发展,我是出于这个目的去了解这些新媒体。我使用微博,现在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是做研究者,可以去研究它,如果是做个文学家、作家,最好别写微博,因为微博就是把你的观点、材料碎片化,就形成不了拳头。所以我知道微博是怎么回事后,就不写了,太花时间了。微信不一样,微信是沟通信息的。在熟人之间运用微信进行信息交流,你说什么显然要经过思考;微博不一样,碎片化的方式意味着你得胡说八道。
三、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展望
王天根:您不仅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创者、组织者、实践者,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中青年人才。您觉得年轻一代的研究者,特别是现在的硕士博士,跟老一辈相比有何不同?
方汉奇:老一辈和新一代年轻研究者相比,在知识结构上差别很大。就以语言方面来说,新一代青年研究者在外语上强调更多,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古文水平弱化了,还有就是读繁体字也存在障碍。现在年轻人一开始接受的就是简体字,有时候查资料搜集档案,就会相形之下受点影响。作为研究者,应该在传统的这些方面是无障碍的,再加上外语方面无障碍,那就全面了。外语无障碍、繁体字包括文献资料的运用无障碍,那就如虎添翼了,否则的话就是一种缺陷了。
王天根:您说中国新闻史是一个富矿,您觉得这个领域还有哪些值得开拓的课题?
方汉奇:就以《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来说吧。这部《通史》从改革开放(1978年)开始筹划,到1987年正式列入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再到1992年才写完;但这只是完成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是全国院校和当时媒体的一些新闻史教学研究人员通力合作完成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现在的新闻史研究者可以考虑将《通史》再写一遍,因为20多年前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有那个时代的局限,甚至可以说,那个时代的局限还是很多很多。当时刚刚改革开放,思想也刚刚解放,而思想解放不是一步到位的,现在也仍然处在不断解放的过程中。《通史》是那个时代的客观条件允许下的那个时代的成果,现在早就应该往前发展。《通史》里面的很多材料当然有缺失,很多论点也有问题,还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还没有完全摆脱。30年就是一个generation,该写第二套了。当然这第二套也仍然要集中全国的力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1992年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现在已经出了英文版,是新加坡翻译出版的。他们把三大本翻译成十本,但删节了很多。这十本他们卖5600元,主要是卖给国外的图书馆。这也说明中国强大了,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开始被国际社会所关注,所以这个英文版是面向国外的图书馆的,销路很好。
王天根:您对正在从事和即将从事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有何期待?
方汉奇:首先,在研究思想上应进一步解放,研究视野上进一步拓宽。我在上世纪80年代很多场合的发言中,都强调新闻史研究中的思想解放问题,我说我的《中国近代报刊史》“还是个半大的解放脚,基本上还是采用了按政治运动分期的那种体例,只是适当地照顾了一些新闻的特点”。今天看来,中国新闻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的那套思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但如果再写第二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该运用怎样的体例,拥有怎样的视野呢?这还是需要讨论,还是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的。
其次就是要重视新闻史资料的积累。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历史研究主要就是掌握第一手材料。在建国初期,也就是1959年,曾有一次保存新闻史“活史料”的机会,只是时间很短,保存下来的很少,很是可惜。那一年彭真当北京市委书记,他想编写一套北京地方志,地方志里就应该有新闻史。当时,北京市委就让中国人民大学(北大新闻专业已经并入人大)的教师编写北京新闻史,刚好那个时候还有很多老报人健在,写新闻史的老师就有了一次机会去搞口述历史。那时候老报人不少,可惜那个时间很短,总共也就一年多时间,访问过一些老报人,可惜这个活动很快就中断了。因为1959年开始“大跃进”运动,三年困难,这个事被搁置了。到了1962年,阶级斗争又开始抓起来了,这个事也就完全放下了。不过这一年多的采访,也有一定成果。当时采访得来的材料都集中在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主任黄河那里,他后来就是以这些材料为基础,编写了一本《北京报刊史话》。今天看来,那是一次机会,一次和老报人接触的机会,那时候建国才十年左右,老报人都还在。那个机会一过,接着就是十年“文革”,等到知道口述历史的重要性了,那些老报人也都去世了,就没有机会了。建国初期搞口述史印象比较深的,有无锡的老报人秦墨哂。他是民国初年《申报》驻北京的记者,后来是南京记者站的站长,他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成了文化汉奸,相当于管翼贤。管翼贤是北京的文化汉奸,他算是上海、南京那一片的文化汉奸。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坐牢是在北京。1959年刑满释放,那时候他非常愿意合作,就跟溥仪被改造之后那种心态一样。所以他愿意为人民政府做点事,他也自谴自责,你问他什么他告诉你什么,没有保留。可惜当年没有这种意识,让他好好地口述一番,系统地口述一番。改革开放以后才知道口述历史是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弄的一个计划。当时有那么好的机会,可以用口述历史这种方式保存下来的,没有把握住。当时秦墨哂也提供了不少材料,至今记忆犹新。他提供的材料主要是这个报纸有什么背景、那个报纸有什么后台等等。因为我们看报纸的版面,就像看商店里的橱窗似的,看的是商品最鲜活最风光的那一面,他怎么进的货,这里面有什么猫腻,你是不知道的。他告诉我们哪个报纸有什么政治背景,北洋的军政党员给哪个报纸多少钱,哪些记者拿过钱等等。那个时候大概新闻工作者没拿钱的很少,林白水、邵飘萍都是拿人钱的。当年秦墨哂还写过一两页,可惜我让人找这个卡片都没找到。这么一次机会,但是没有很好利用,等到改革开放以后有这个条件,时机已经错过。所以说,新闻史研究关键是史料,今后新闻史研究要获得进展,前提是把史料保存好、积累好,当然也要挖掘更多的史料。
再就是要重视重点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和通讯社的个案研究。对历史上曾经起过重大影响的新闻单位和新闻工作者,应该逐个研究。有了较深入的个案研究,才能进行必要的定量、定性分析和面上的综合概括。这一类研究,在最近三十多年里已经取得很大成果,比如《申报》《大公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人民日报》《世界日报》等等。但是还有不少缺口,还有不少课题有待青年新闻史研究者继续探讨。只有个案研究的水平提高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才能得到提高。对于年轻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来说,从个案研究入手也较易出成果,比泛泛的面上讨论也更有价值。
王天根:谢谢方老在百忙中接受访问。
(张朋、马静做了录音整理等协助性工作)
责任编校:张朝胜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5.02.013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5)02-0098-07
作者简介:方汉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王天根,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 合肥23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