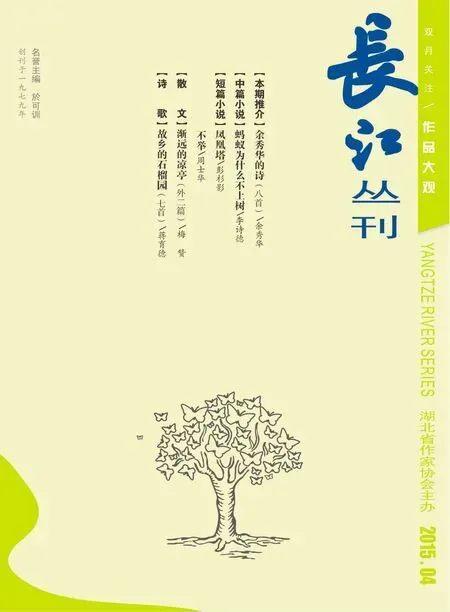神灵安住何方
肖雅芳
神灵安住何方
肖雅芳

肖雅芳,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仙桃市人,曾在《长江文艺》发表《色调》《春草图》《另类治疗》等小说。
这天下乌鸦还不是一般黑,燕儿不明这个理,你这当外婆的也有责任教育教育。
死心眼,咋说咋不听,她妈妈平时说的还少啊。
哎哟,老姐姐我跟你说,女孩儿拖不起哟,我没有记错的话,翻年就二十八了吧。真是的,我们都是过来人,谁不晓得男人就那么回事,有啥子七挑八选的。
是的是的,可是小姑娘少不更事的哪会这么想,人家有知识有文化自以为有见识,谁听我们这些老古董唠叨。
虽说时代在变,可道理变不了喔……
院子里的两个老姊妹在幽香的合欢树下闲扯,粉红的花瓣落了一地。虽然她们的神态看起来煞有介事,像在商讨一件改变人生的大事,在刚好路过此地的易菲琳看来,不过是些零碎的闲话而已。这样的理论及这样的老太太让她心情沉郁,她不禁抬头望了望前面,权子的车还没有出现。
初夏的天空十分明朗,全然失去了春天乍暖还寒的含蓄,阳光毫不费力地洒下来,草儿绿得劲道,花儿开得正好。她弯腰拾起一朵散落在地的合欢,细细端详起丝绒一样的花儿,又迎着阳光晃了晃,轻轻吹口气,然后松开手指,有些失望地放飞了它。
等我老了,万万不要那样琐碎。她在心里对自己说的时候,有点惊愕,因为她常常拿类似的话骗自己,而每一次被骗她都信得真切,真是劣根性。
一阵轻悄悄的风吹过来,她抚了抚微痒的额头,又是一朵花,挠得她恼火。无声无息地,仿佛是一夜之间,绿意浓浓的合欢树笼上了一层粉嘟嘟的小东西,一团团一簇簇妖艳极了,黝黑的沥青路给染了,就连光洁的鹅卵石小径也胭红胭红的,空气中弥漫着阴柔的气息。这也是一种力量!
易菲琳悚然一惊,它一定有灵知,它说什么时候让树绿,什么时候让花红,它要让一切都列队而行,不容商量。它要让天下乌鸦都一样黑。往后的日子怎么过,的确是个问题。易菲琳不禁打了个冷战,在这艳阳高照的六月里,她的心还停留在冬季。
嘀嘀。权子的车开来了,就在这当儿她已抓到了一星半点儿思维火花,如果由着这个路子探下去,答案想必会有些眉目,可是权子来了。
他们说好了中午去看姨妈的,姨妈一个人生活了一辈子,无儿无女,现在老了,得有亲人常去看看。
蜻蜓点水式的招呼早就省略了,两个熟透了的人不需要这些没用的,缄默取代了一切。权子的眉头有股力道,这让易菲琳不放松。易菲琳是实验高中的化学老师,却有着文科职业的敏感,其实这也不矛盾,因为她是个女人,女人天生是灵性的动物。权子是她的老公,一起生活了这么久,她对他的每一个细微的表情都了如指掌,但这并不代表熟悉,相反地,常常有股陌生感油然而生,就像此时此刻。
权子的牙咬得紧紧的一个字也不说,仿佛这会儿副驾上根本没有上来一个人,更进一步说,车从来就没有停过,他在心里别着一股劲,开车,开车,他只知道向前再向前,或者说他根本没有心。
她正欲开口,立即止住了,想起刚才对自己的告诫,不能琐碎,从现在做起。变则通,通则久。而且看看权子目不斜视,一脸尊贵与不怒自威,更加显得自身要怀锦握玉了。
呀,我的快递还没取。
真是一念无明,她忽然想起前天邮局打电话说有一个包裹要去取。可是这突然蹦出来的一闪念,根本由不得她控制。
要不我们顺道去趟邮局吧,现在离开饭还早呢!
权子浓浓的眉毛一拧,额头上的抬头纹挤得像刚刻上去的,连带前额的头发竖得更直了。
你怎么做事一点安排都没有,你知道开车多麻烦吗,我拐弯都拐过来了,又要绕过去那么长。这个问题我给你说过好多次了,怎么就不长一点记性……权子一下开了闸,他所有的不快都合着先前那份攥住的力道一泄而下。
易菲琳紧紧地咬住嘴唇,一阵懊悔,可是说出来的话收不回去了。
你看,又碰到了红灯,该死的红灯!说不定前面还得等红灯,你说你烦不烦人,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你自己去,不要赖上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谁有那么多闲工夫陪你瞎转悠。
气急败坏,权子目不斜视地抓起座位旁的矿泉水瓶,仰起头咕噜咕噜地喝了一大口,嘴边渗出来的水也不抹,只顾恶狠狠地盯着红灯。
从前那个憨厚阳光的大男孩到哪里去了?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叫我做牛做马都愿意。易菲琳想起了初和权子在一起的时候,他这样表白,像一只温柔的羊。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想到这里心里掠过一阵凄凉。
易菲琳通常是沉默的,多次失败的教训已让她明白,她不可能斗过一头发怒的狮子。这当儿,想起女友夏妮的经典论断——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女人打不过男人。她不禁攥了攥拳头,忽然感到好酸,又悲哀得想笑。
叫你去学车,拖,拖,都快拖一年了还不去学,你怎么就这么懒呢,一个女人怎么能什么事都依赖别人,幸好你还是有老公的,人家单身的都怎么过?没法过!权子自说自话,简直想拿方向盘当枪使,一下子把敌人击毙。
算了,不去了。根本没有斗一个回合,没出息的易菲琳就缴械投降。她完全没有心思争斗,那个问题像一团乱麻困扰着她,如果不解开,斗得头破血流都是枉然。
什么?我刚过十字路口,你说话经不经大脑,啊?你的死脑袋到底想的什么,骷髅子进水了!她的不温不火,意想不到地达到了举重若轻的效果,面前的男人已被顽固得不近人情的易菲琳调戏得几近疯狂。他那双骨节绷得发白的手,抓得方向盘上的真皮套子都要破了,嘴里呼呼地直喘粗气。
毕竟是夫妻,他意识到自己的话太多太盛,吞了口唾沫,克制地压低声音浓缩成了三个字:死婆子。
死乌鸦!易菲琳以牙还牙,冷冷地吐出三个字。
他才懒得管她在说什么,只当她是昏了头。
夏妮对她说过,男人都受过集训,婚前婚后完全两个样。张小彤也说,男人一结婚就变了。那天四丫在茶楼里过生日,一边喝红酒一边流着泪历数家里男人的种种罪状,奉陪的姐妹们纷纷咋舌道:一样啊,一样。当时,一贯以实惠主义著称的唐娜十分后悔,早知道这样在人堆里随便拎个四肢健全的男性公民结了呗,何必害得我妈操碎了心。
还有姨妈,是不是也因为淡了心,才坚持一个人过一辈子的呢?易菲琳完全没有心思吵架了。
既然都是一个空,为什么一茬又一茬的人不要命地往围城里冲啊?其实他们只需要向身边的过来人打听打听,便知自己将来的处境。不过,过来人想必不会明说,自己的弯儿还得要自己去绕啊。这真是一场未经谋划又不谋而合的集体骗局,之前是不会有人告诉你真相的,而且还营造得一派和乐,张灯结彩,敲锣打鼓,仿佛新的生活就此才算拉开序幕。当然姨妈和少数明智的独身主义者除外。
真理真的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吗?要知道,其间如果有一个人说破就会豁开一道大口子,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游戏。为什么要认同那帮老太太呢,为什么要伙同那世俗的邪恶家伙呢,偏要做出个别样来!可是,四围都没有路,在车里怎么会有路呢?这车关闭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简直是个囚人的牢笼,窒息,压迫,步步紧逼……找不到方向我宁可去死……
突然,易菲琳冲权子大吼一声:你怎么不去死啊!
权子显然被吓着了,一个激灵。从未有过这样的经验,本能地急煞车。嘎的一声,易菲琳的头险些撞到前面的玻璃上,尖厉的声音把车上的两个人都吓着了。这声音划破喧闹的长空,路就在脚下。
易菲琳拉开车门,把自己扔在大马路上。黑色的车子旋风一样扬长而去,消失在斑驳的车流中。让这个疯婆子在这里发疯吧,发完疯就好了,这是权子的经验。又能怎么样呢,易菲琳其实无数遍地分析过他们相处的多种可能性——离婚不离家、周末夫妻、改变自己或者改变权子、带孩子单过、一个人消失等等,都不具有可操作性,真是无穷无尽的烦恼深渊。再者,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女儿豆豆,这是无法割舍的。
其实权子是个好人。不怪他。究竟是谁把他变成了今天的模样,以时间为线索理智地分析,罪魁祸首还是我易菲琳,因为结婚前他不是这样的,他是个那么阳光热情的大男孩,结婚之后,他就变成这样了。可是张小彤、四丫、夏妮她们的男人呢?易菲琳进一步推论,好像有了些启发,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权子和任何一个女人结婚,都会演变成今天这种局面。推动这一切的还是那样的一股力量,这股强大的力量悄无声息地侵蚀一切鲜活的、有形的东西,达到一体化才干休,它是虚空里的王。她担心这没头没脑迸现出的灵感火花稍纵即逝,甚至来不及想一个更为贴切的词。
想到这里,易菲琳打开手机的收件箱,夏妮发来的短信还在:所谓爱情也不过是看上了,追求了,好上了,开心了;不久后,腻了,吵了,淡了,散了。
唉,夏妮倒是看得开。
是的,最后都一刀断了,空苦无常收了场,这算什么。
她纳闷地看看头顶的天空,大块洁白的云朵棉花糖一样软绵绵地浮动着,阳光闪烁,柳絮轻舞,擦肩而过的路人步履轻盈,车道上各色车辆文明有序而过,一切都是那么善意而良好,现世安稳。她有点怀疑自己的推论。
难道说从此我就认命了,在毫无悬念的寡淡日子里,和权子耳鬓厮磨互相嫌弃地终了此生?那么,每个生机勃勃的早晨,玫瑰色的红太阳不再让人充满期待了,阳光变成了X射线,大地上行走的将是一具又一具没有血肉的骨架,从一个空走到另一个空,然后走向死亡,全黑掉。
这个结论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此时,易菲琳路经一家杂货店,在门口的公用电话旁停住了。一个学生模样的小女孩在看店,可能帮大人临时照管,一边玩手机一边啃着红苹果,漫不经心地瞄了易菲琳一眼。
易菲琳眼里突然生出一道光亮——现在有一个绝好的机会摆在眼前。她其实一直惦记着一个人。而且此时此刻,她特别想听到他的声音。她认为只有他才能给她注入一支清醒剂,告诉她生活中还是有激情,有期待的。他有力量把她从那套荒谬的老掉牙的理论里拯救出来,和那虚空里的王淋漓地干一仗!
就在举起话筒的瞬间,她觉得这一瞬在她的生命中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就看你的了!她慎重地拨通了他的电话。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听到这不厌其烦的孙氏调侃,易菲琳舒了口气,呵呵……由衷地一笑,太亲切了,孙扬还是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她这些年从未主动和他联系过,只是节假日很有礼貌地回个短信。她知道孙扬还记挂着她,因为他换过几次手机号都告诉了她。去年元宵节的时候,她还接到过孙扬的电话,他们聊了很多,情到深处,孙扬还孩子气地问她心中有没有留一块地。她虽然努力不触及情感方面的问题,但这样的话很好地满足了一个女人的虚荣心,毕竟他是她的初恋,那份圣洁的情感值得珍藏一生。
你在干嘛呢,帅哥。易菲琳最近参加优质课堂大比武,普通话练得非常标准。
我在家里。孙扬也跟着戏谑地普通上了。以前他们都习惯用方言的,因为在大学时家乡话互相都能听懂。
没去上班吗?
我上什么班呀,美女。
你难道……
呵呵,你是谁呀?孙扬调皮地问。
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易菲琳才不会上他的当。
我当然忘不了,你是……林丹丹。孙扬稍显迟疑的语气,说明他对自己的判断并无十足的把握。
是的哟,记忆力还不错嘛。易菲琳反应很快地表扬道,心中顿时一片苦涩。
傻瓜,你在我心中是什么地位,忘了谁也忘不了你哟。你能不能现出真身不这样说话,声音听起来别别扭扭的。
讲普通话不好吗,不想理我就挂啦。
呃,这人,对了,你在哪里?
我在出差。
我就说,这不是成都的区号咧,好像是宜昌的,你在宜昌吗?
易菲琳心里一阵悲凉,你还记得有个地方叫宜昌啊。是的,办完事就走。易菲琳觉得没有再聊下去的必要了。
来我这里玩嘛。
不去。易菲琳在生气,时光倒流,就像在大学里对着孙扬耍小性子,可如今的孙扬已不再是痴情的大男孩了。
我开车去接你。
不好玩。易菲琳甚至噘起了嘴。
请你吃我们这里的特色小吃,你说过很喜欢的。
我刚刚吃饱了。易菲琳拒绝道。
那我请你来这里睡觉,你不会又睡过了吧?
那边还在嬉皮笑脸地调侃。这种百毒不侵的自我主义精神,曾给大学时代的孙扬蒙上一层英雄主义的面纱,而此刻,易菲琳站在一个可以俯看的角度,轻而易举地用小指撩开了真相。
她是一个残酷的家伙,这就是探究带来的结局,硬要把自己逼进死胡同。阳光的味道其实是烤焦的螨虫,彩色的肥皂泡是因为光的散射作用,浪漫的雾是近地面空气中的水蒸气发生的凝结现象,等等。拆开,解剖,显微镜,计算,透过现象深入本质,最后得出结论,这是她当化学老师的职业习惯。
是啊,我睡了大半天,刚刚才起床。怀了满心满意的春,被这不经意之举割开了一道大口子,原来万花筒里除了一颗花心什么也没有,经不起推敲。
哈哈哈哈。
有什么好笑的?电话里头有点吵,易菲琳冷冷地问。
哦,我身边的朋友让我把电话挂了,我说在和美女聊天咧,要是个男的我才懒得理呢,我又不是同性恋,你说呢丹丹。
我现在有事,先走了。
喂,有空再联系,喂……喂……没等他说完,易菲琳以快刀斩乱麻的决绝挂断了电话。
转身离开之时,她还是核对了一遍拨出去的号,确定没有打错之后,拿出手机,沉吟片刻,删掉了孙扬的号码。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她臣服了。不用猜测,不用遐想,从此她的天空将是一片确定的黑。这世间竟没有一样东西让她感到踏实。
没有退路了,她拉了拉裙摆,正了正身子,纤细的小蛮腰挺得直直的,看起来有些悲壮。
与此同时,一种从未有过的确定感油然而生,她的心反而充实起来。她牢牢地把握住这种感觉。笃定。既然结果都是一个黑字,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或者说既然结局已定,不用再徘徊,不用再疑惑,那么不用再恐惧了,过好鲜活的当下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是的,只有那些被生活揉碎了又重新振作起来的人,方有能力去热爱生活。
正午的阳光很有力道地射在马路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易菲琳的高跟鞋铿锵有力。她疾疾行走,意气风发,踏着五色的光,踏着一波又一波的声浪,轻而易举就穿过了街心最繁华最喧闹之地。她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那个明确的方向走,不再像一只幼鸟一样无助,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这个家完全是她的了,她要做这小小世界里的王。她要做自己的王。
易菲琳出现在阳台上,柔弱俏丽的身姿显得是那样镇定,束腰的金黄色长裙在风里轻歌曼舞,蕾丝衣袖上的紫色手工镶钻熠熠生辉。阳光给她的周身沐浴上了神圣的光辉,她扬起手优雅地挡住前额,目光所及全是明媚。落英缤纷,一缕缕似有似无的合欢花在眼前飘过,是的,就像这花儿一样,终有一天会谢完的,迎接它的是黑漆漆的泥土,可是她仍然以最美的姿态在阳光下盛放,这就是生活的况味。它们早就明白了,这帮狡黠的家伙。继续放眼时,她发现面前有一棵合欢树遮住了远方的亭角。这不算什么,她什么都能摆平,一段插曲而已。
工人们来了,她命令他们砍掉那棵大树,一小时之内,动作要快,尽量不要吵到小区里的居民。
嘿哟,嘿哟,老练的工人们抡起锋利的斧子。很快,合欢树摇摇欲坠,动静变得越来越大起来。
灵敏的居民们很快接收到这个信号,哐哐哐地拉开窗子引颈张望。插曲,可爱的插曲。死板的居民楼活跃起来:有人顾不上正吃着的饭,放下筷子匆匆跑到院子里看热闹;有人刚好吃完午饭没事干,踱着小步子下楼了;有人刚从外面回来,也不忙着进屋,围着合欢树转悠;做完家务的老太太们索性搬了板凳,抓起一把瓜子在树旁聊起天来;有人甚至一改午睡的习惯,走出了屋……就是没有人管为什么要砍掉这棵树,这棵树碍了什么事。人们才懒得去问那么多为什么,只管聊天,只顾玩笑。因为他们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自有它的理,日子会像水一样淌过去,寻常人家,烟火百姓,还不是这样一天一天地过。
一缕青烟从树林中升起,一位老人正跪在林中焚香祷告。这个简单的仪式吸引了不少人,老人说,不能随便砍一棵超过一人高的树,因为神灵住在树上。
神灵?有吗?如果有的话,神在哪里呢,靠得住吗?不过是些传说罢了。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世界总有那么多让人困扰的问号。
当易菲琳再抬起头来的时候,合欢树倒下了,视野开阔了许多。小小的胜利令她豁然开朗,原来神灵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在智者的心中。易菲琳站在阳台上浅笑,唇边漾起的酒窝让她看起来有点孩子气。
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穿过绿色的草坪飘过来,那一扭一扭摇曳生姿的步态,一看就知道是夏妮。易菲琳一直觉得她身上有一股有别于庸常女人的神采,那顾盼生辉的眼角眉梢透出一种风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力量。想来,她日子过得那么活色生香,应该是早就悟透了这些的,这个小妖精!
责任编辑:陶 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