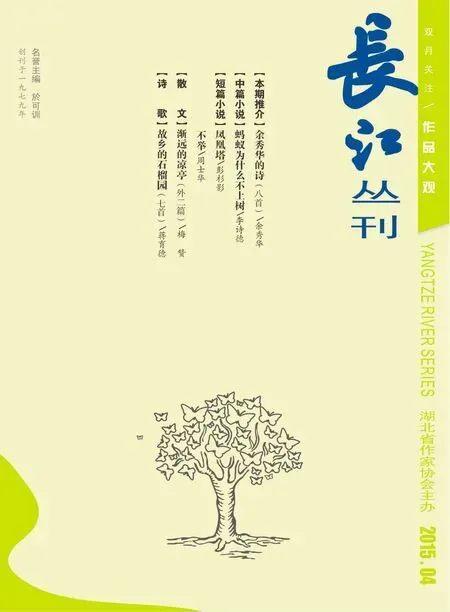灰月亮
戢建华
灰月亮
戢建华

戢建华,男,1976年生。现供职于湖北房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业余写作,1999年发表第一篇散文,2010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现已发表散文、小说三十余篇,十万余字。
一见面,民政局安置办那胖胖的略秃顶的主任就对我说,你小子真幸运!农村兵从来不在安置范围内,考虑到你在部队立了二等功,所以才安排到县文工团,这可是个副科级事业单位,好多人挤破脑袋都进不去。符合安置条件的城镇兵才安排到企业单位。说是企业单位,这年头都是私人企业,说白了就是介绍去给私人老板打工。转业军官好多都还没安排……一番话说得我只有感恩戴德的份儿。其实我也知道有几个城镇兵战友是安排到了政府部门的,不过这事儿不能摆在台面上说。退伍时指导员是告诫过的,地方上和部队不同,不是光靠表现的,要多用耳朵少动嘴。那几个战友是有背景的,而我的父亲则在离县城十几公里的山沟里刨地,祖坟更没冒过什么青烟儿。
我将消息告诉父亲。这个年届六十的老农民乐呵得不得了,好啊,文化干部啊,以后就是城里人了。因为高兴,满是皱纹的脸像攥紧了的破抹布。
文工团地处文化广场,那是县城最热闹的地方。当兵前在县城读书时也没少去,环着广场的是文化局、影剧院、图书馆、博物馆、文化宫和一些歌舞厅、茶屋、游戏室、影碟图书出租店等,总之都是与文化娱乐沾边的。影剧院就是文工团的经营活动场所,小时候父亲曾带我来看过电影,母亲带我来看过戏。有部戏记不起叫什么名字了,但有个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舞台上,男女主角各据一隅互诉天涯相思,背景音乐是《十五的月亮》,他们头顶上就挂着一轮明月,男的英俊挺拔;女的贤淑娇媚;俩人唱得千回百转,缠绵缱绻……没想到如今我却成了这个单位的一员。
当我拿着工资介绍信敲开团长办公室时,还是有些吃惊,尽管之前听人说过团长白丽华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精明能干,风姿绰约。而面前的白团长没那么老,顶多也就三十五六岁,待人平易亲切。见到我就招呼道,小李,李红军是吧。我说,是,白团长。白丽华笑,这里不是部队,以后叫白姐就行了。我点头,嗯,白姐。白丽华看了会儿介绍信,又问,你会开车吗。我说,在部队学的驾照,消防车开过。白丽华又笑了,那开小车就像骑自行车了。团长办公室宽敞风雅,书柜、老板桌、电脑、沙发、饮水机等一应俱全,墙上还挂着字画。白丽华转身取了串钥匙带我下楼打开一楼临楼梯的办公室,然后把钥匙交给我,说以后你就在团办公室上班吧,这是团里办公楼和影剧院的钥匙,就交给你保管了。
办公室桌椅柜子落满了灰尘,一看就知道闲置很久了。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发黄的文工团通讯录,打印的名字有十多个,后面又补充了一些手写的名字,其间又划去不少。想必这些都是团里的职工我的同事了,但奇怪的是我只见到了白丽华一个人。
花了一上午时间拾掇好了办公室,下午白丽华买来了电烧水壶和开水瓶,说单位就得有单位的样儿,赶明儿我叫人给你装电话送报纸来。我说谢谢白姐。是得谢谢,我原以为来文工团是要当演员演戏呢,没想到会安排在办公室,幸甚幸甚。
办公室很是清闲,每天喝茶看报纸,一部电话几天来没响过一声,通讯录上面的同事更是没见着一个,白丽华也没分配我具体工作。我每天只是按时上下班,实在无聊时就拿着那串钥匙端详,那钥匙每把都贴着胶布,字迹依稀可辨,会议室、练功房、道具室、剧场前后门、售票房等。
周五下午终于有人进来了,我起身一看,却是影剧院大门口卖香烟零食的。他不等我招呼就径直坐到我对面,自言自语:我说又不逢年过节的,办公室这些天咋开着呢,原来真有人。见我诧异,他便自我介绍:我叫杨世禄,也是团里的。“杨世禄?”我马上想起来了,他的名字在通讯录里是打印的。我连忙找杯子倒水。杨世禄说,不用了,我杯子在外面,以后会经常来倒水的。你是请来的吧?
我说不是,我是退伍军人安置到团里的。
杨世禄哦一声道:我还以为是请来写什么材料的呢。团里多少年没进过新人了,老人手大多都是像我这样五十多岁了,年轻的也有四十五六了。每年白丽华都要到河南去招聘几个小姑娘,要不下乡搞个慰问演出都没人手,单位上写个总结报告都得临时请人。
我问,团里多少职工?
杨世禄说,正式职工十二个,招聘的就不清楚了,来了走,走了来,不固定。
我说,这通讯录上不是有二十多人吗。
杨世禄说,前面打印的是团里正式职工,后面手写的都是招聘来的河南姑娘。
我问,怎么都去河南招聘呢。
杨世禄说,河南人会唱戏,工价低;艺校学生也招不起啊。我们团前身就是曲剧团。
我问,那团里的人呢。
杨世禄说,我,这你知道,摆个柜台挣点儿零钱。道具师傅刘连元开着家具店,占的就是团里的门店;二胡师傅傅登甲在图书馆二楼办了个二胡培训班;苏彩云舞跳得好,在文化馆二楼办了个舞蹈培训班,这三位都是发了的。田从贵歌唱得最好,和团里几个敲锣打鼓吹唢呐的凑在一起搞了个丧鼓班子,专给死人唱丧歌;会计老孙十天半月来做一回帐,其他几个就在家伺候儿媳妇照顾孙子了。这团里的事啊,说起来跟戏似的。
这时楼上下来一阵高跟鞋的声音。杨世禄看看表说,你也该下班了,下回聊。起身走了。我关上门,看见白丽华正朝一辆红色别克轿车走去,听见我关门,回头招呼我:“小李,你家住哪儿,姐捎你一程。”我说,我家住农村,城里租的房子就在附近。白丽华有些责怪地拉下脸:“怎么不早说,团里有的是空房子,赶明儿给你一间。”说完上了车。我纳闷,团里怎么会买辆红车,转念一想,团长是女的嘛,于是自嘲地笑笑。
星期一再上班时,白丽华就带我到了影剧院后面一排老旧的小平房,打开一间,说,这里以前是职工宿舍,现在住着团里几个临时演员,你就住这儿吧。
只要我在,杨世禄每天都会到办公室来倒开水,没什么生意的时候就会坐下来闲聊。杨世禄怀旧,聊的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工团红火的时候,票如何难买,他查票如何威风,又如何给熟人放水。聊完又有些失落,现在不行了,家家都有电视了,没人看电影看戏了。
一天中午临下班时,电话响了,白丽华要我马上赶到如意酒店。去了才知道是白丽华请文化局的局长和几位副局长吃饭。酒桌上白丽华一个劲儿的鼓动我敬酒,我也不知道到底喝了多少酒,也不知道怎样离开酒店的。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沙发上,身上盖了条毛毯,白丽华坐在一旁吃零食看电视。我问,这是哪儿?见我醒来,白丽华给我倒了一杯酽茶解酒,说,阳光花园,我家。我说,白姐,不好意思,出丑了。白丽华笑,你还挺有酒量的,客陪得不错,就是只会喝,不会说,太老实,跟你的名字一样。
我出生时已经改革开放了,别的孩子都叫波呀涛的,父亲却给我起名叫“红军”。初到部队时,指导员说一看名字就知道你娃老实。果然,塑料厂失火那次,大家都忙着灭火,我听见有人喊仓库里还有人,就冲了进去。好不容易摸索到人背到背上,艰难的趟出大火浓烟,脸和脖子都被烧伤,半年后才恢复。事后指导员问我,你娃知道浓烟有毒吗?我说,当时没顾得想那些。指导员笑笑,你娃命大。后来有战友告诉我,其实不止我一个听见喊声了的,就我老实。我知道老实并不是褒义词,只是比说傻瓜好听一些。
我红着脸喝了一会茶,见白丽华没再说什么,于是起身告辞。白丽华说,别,晚上就在我这儿吃吧,天天我一个人吃饭凑合惯了,有你我正好炒两个菜,自己也好好吃一顿。见我不解,又笑着解释,老公在外面,一年难得回来一次,女儿在省城念大学。
白丽华做饭的手艺实在不敢恭维,但为人挺热情,让人感觉不到一点儿做客的拘束。临走,白丽华把车钥匙交给我,叮嘱我明天一早把车开去花店扎彩,听宣传部万副部长调用,他外甥结婚,红车喜气。
不久,我发觉找白丽华借车的人挺多的,不是县委县政府的,就是财政局文化局的,反正都是领导,而我的工作就是给他们开车。白丽华自己也说,幸亏我这车是个红色,他们不好意思坐,否则我自己用都难了。我说,我也觉得一个大男人开个红车挺别扭的。白丽华笑,省厅马上要给团里拨个多功能舞台车,到时候你开,不比消防车小。
端午节时,团里每人发二百元购物卡两箱啤酒。我也见到了团里所有的职工,大多数面相竟然都还熟,虽然叫不上名字,但都是在文化广场见过的。老职工领完东西相互寒暄了一番乐呵呵地走了。白丽华召集几个临时演员说,准备节目,马上排练,等我和小李从省里提车回来就得演出了。
去省城的高速公路上的4个小时,白丽华一直放着前苏联歌曲,山楂树,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听得人想睡觉。白丽华说,说说话吧。我说,说什么呢。白丽华说,你说我这个人怎么样。我说,挺好的。白丽华问,没有了?我“嗯”。了一声。沉默了一会儿,白丽华说,有时候我也在想,其实我不缺钱,我呆在这个破单位干什么?财政局拨的那点钱只够老职工的基本工资,作为一个文艺单位是有演出任务的,慰问演出,年终会演,这都要人。老职工已经演不动了,包分配的艺校生也没人愿意来,我只好招聘些临时演员完成任务,但临时演员也得工资啊,只好到县财政局、文化局里周旋争取,再联系税务局、烟草局这些有钱的单位和知名企业给他们做些宣传,挣点儿演出费。我一个女人支撑这个场面难啊,有时候真想找个肩膀痛快地哭一场,可是老公女儿又不在身边……可是我不呆在这个破单位又去干什么呢?我知道自己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你说我命苦不?我说,我觉得你挺潇洒的。白丽华苦笑。
我说的是假话。杨世禄闲聊时已经说过,白丽华老公是工程师,以往小两口过得不错。但白丽华是个事业型女人,自己要强不说,硬是唆使老公下了海,钱倒是挣着了,白丽华四十岁生日时,老公一出手就送她一辆红色别克,但人就是不愿回来。
登记下酒店,和白丽华一起逛商场。白丽华自己买了两件衣服,又在手机柜买了一款一千八百元的诺基亚手机,问我怎么样。我说还可以。白丽华说送给你的。我一愣,这可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啊。白丽华笑,算是团里给你配的。我受宠若惊,连声谢白姐。白丽华说,要谢就谢这舞台车吧,不是这车,想给你配手机还没个名目呢。
从省城提了舞台车回来不久,白丽华就率领文工团随县委书记一起慰问椿树垭隧道施工单位。演出节目除了说唱快板等传统曲艺之外,又加了几个年轻人喜欢的热歌劲舞,那几个河南小姑娘或聚或分的上台,把一台节目演绎得有声有色,现场气氛调动得十分热烈。我问白丽华,节目谁编排的,真还不错。白丽华说,练功房里的影碟教的。
第二次和团里职工聚在一起是因为苏彩云母亲的去世。由于是丧事,白丽华的红色别克显得太不庄重就没开,安排我买了花圈和奠品一起走着去了。白丽华慰问完苏彩云,又说,你知道团里没人手,也帮不上什么忙,我一个女人家又熬不了夜,要不怎么也得陪阿姨一晚上的。我见团里人都在,晚上的丧鼓班子正好是田从贵他们,就想留下来听一下,于是说,白姐忙,我来吧,反正我一个单身汉。白丽华看了我一眼,说不上什么意味,坐了一会就走了。
一阵急如雨点的锣鼓声中,田从贵从灵前百步焚香而来,入灵堂后绕棺且行且唱:一杆竹子青幽幽,孝家请我开歌路,歌路不是容易开,未曾启齿泪满腮——委婉的低吟浅唱,如诉如泣,有点儿像越剧里的尺调。接着几个人轮番上阵从混沌初开,女娲造人,历朝历代地唱下去,最后颂唱亡灵的生平事迹,直至翌日拂晓。田从贵虽已头发花白,但我依然听得出他就是我记忆深处扮演那个柔情军人的演员,只是经岁月磨砺得有些佝偻颓废。
苏家的亲朋好友大多在灵堂外打通宵麻将,仅我始终伴在灵侧听丧歌。长这么大我是头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地听完。丧歌间或说史间或劝诫,听得我世相顿悟,心境无比清澈透明。期间苏彩云过来续过几次水,关心我要不要去睡一会儿。我摇摇头,说不困。苏彩云问,你怎么哭了。我用手拭拭眼角,果然湿的。
没几天,苏彩云找我借人字梯换家里的灯,说是记得道具室里有。我称呼她苏大姐。她一脸不高心,我比白丽华老吗?我说,不是,你们看起来都挺年轻的。我说的是实话。苏彩云讪笑着,你白姐今天又开着鳖壳跑哪儿耍去了,把你撂家里。我没吱声,拿起钥匙奔道具室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打开道具室。道具室虽然门窗紧闭,一眼看去却都是灰蒙蒙的,一如沙尘暴过后的废品收购站。好不容易才发现人字梯靠在墙角,我踮着脚小心翼翼地跨过零乱的道具去取梯子时,脚碰到了一轮硕大的月亮。我一眼就认出它就是我记忆深处那美轮美奂温柔诗意的月亮,此刻,它却满是灰尘地被遗忘在寂寞的道具室里,永远都不会再挂上夜空。我愣愣地看着它,看着它的灰尘,看着它灰尘下的白布,看着它白布下的日光灯管,说不上落寞的是它,还是我心目中那轮散着淡淡月华的月亮,抑或是我。
我还以为道具室里的老鼠把你吃了呢。苏彩云的催促将我从记忆的泥沼中拔出,见我搬的人字梯满是灰尘。她笑道,那就再麻烦你帮姐搬下楼吧。我一笑,没事。下了楼,我见苏彩云还犹豫着,知道她是怕脏了衣服,其实我还担心她扛不动。于是说,我直接给你扛家里得了,挺重的。苏彩云满意地一笑,前边走了。我突然发觉她步态的优雅竟像极了舞台步。
苏彩云家就在文化广场附近。梯子扛到门前,苏彩云说,谢了啊。我转身刚下两步台阶突然想到她是个女的。于是又折身回来说,我好人做到底,干脆灯我帮你换,顺便把梯子再扛回去。苏彩云倚门有些夸张地妩媚一笑,那敢情好,不过我可是单身离异女人哦,别怪我没告诉你。
换灯对于男人来说不算事儿,很快就完。苏彩云端来了西瓜,说洗洗手,坐一会儿吧。我说不了。苏彩云怪异地笑,吓着了?放心,姐吃不了你。于是只好坐下。苏彩云家很典雅,氤氲着一种文化氛围,墙上挂着苏彩云演出的大幅照片,花架上垂着不知名的藤萝,幽幽地青,可以瞥见阳台上的钢琴,书房里的电脑,玻璃茶几下几本书刊影碟。我随手抽出一本书,看封面竟然是《灯草和尚传》,我脸一红,不知道是该放回去还是拿在手里继续翻。苏彩云看出了我的尴尬,说,拿去看吧。我说,这好像是黄色书籍吧,你哪儿弄的?苏彩云说,准确的说应该叫明清禁书,我是从文化局稽查队里找的。《金瓶梅》不也是禁书吗,现在还成文学经典了。这就看你怎么去看它,是娱乐性地去看裤裆里的那点儿情节,还是探究它的时代背景,包括文化,风尚,道德理法等。苏彩云这番话是一本正经的。我只好揣着书扛着梯子走了。她说得有板有眼,我要是不带上看,怕她看不起我,或者在心里嘲笑我虚伪。
第二天黄昏时分,我躺在宿舍床上看《灯草和尚传》,我得承认我不是一个坐怀不乱的君子,书中那些引人入胜的情节看得人劣根暴起,根本无暇去探究苏彩云说的那些文绉绉的学问。而诺基亚却在这个时候响起,我以为是白丽华又要我去陪什么客人,一接却是苏彩云。你快来再帮我看看灯吧,又坏了,一闪一闪的,我差点儿把饭喂进鼻子里。苏彩云的话又是急切又像是戏谑。
我还是扛着梯子去了。我取下灯罩察看的时候,苏彩云就在下面拿停电宝给我照明。鼓捣了一阵,我终于发现了接触不良的地方,于是拿螺丝刀拧紧。灯亮的时候,我说,好了。低头看苏彩云,眼睛不禁直了。苏彩云一袭粉色低胸吊带裙,居高临下一对白皙挺拔的乳房暴露无遗。苏彩云发现了我的异样,低头忙把肩带往上提了提,说,不好意思又麻烦你,下来陪姐喝两杯吧,天怪热的。然后不容分说推搡着肩膀将我按到餐桌前坐下。
菜是凉拌和烧卤,苏彩云又拿来几听冰冻青岛啤酒,扑哧打开一听,咚地竖在我面前。一股雪白的酒花涌出来,我忙就着罐口吸了一气。一听啤酒下肚,彼此话就多了起来。苏彩云问,在部队喝酒吗。
我说,喝。有一回指导员要我们几个兵去陪他老乡,喝的是白干,二两半的杯子,我们几个兵都是站着一口闷,然后敬个礼,等客人喝完,斟满才坐下。
苏彩云笑,没看出你还是好酒量啊,今儿就陪姐痛痛快快喝几个。我发现苏彩云笑的时候很妖艳,眼睛里恨不得伸出一双小手来。又问,你以前看过我演的戏吗。
我说,我还是小时候来影剧院看过戏,别的记不清楚,就是对田从贵演的那个军人印象挺深,我记得当时唱的还是十五的月亮。
苏彩云说,那场戏就是我演的女主角。
我说,我记得你当时怀里抱着个婴儿。
苏彩云说,就是个包袱卷儿——姐那时漂亮不。
我说,没注意看。
苏彩云笑,也是,你那时还是个小屁孩。
酒中日月长。聊着聊着,苏彩云就扯到了白丽华身上。说是八十年代初,文工团的团长还是刘连元的父亲老刘团长,白丽华的母亲是团里的演员。当时团里下乡演出多,有时男女演员就睡在帐篷里,中间拉道布帘隔开。上厕所时女的就在帐篷里拿个盆子解决,男的就尿到帐篷外的野地里。偏偏那天白丽华的母亲吃坏了,蹲在外面的草丛里拉肚子,碰巧老刘团长也出去方便,黑灯瞎火地,白丽华的母亲就薅住老刘团长的领口,说老刘团长耍流氓,在她面前解裤腰带,还把那玩意儿都掏出来了。那年头正值大逮捕,耍流氓弄不好是要挨枪子的,事情闹到文化局,局里把在家待业的白丽华招工到文工团里卖票,才算安抚妥当。
苏彩云说,现在刘连元占着影剧院的门店做生意,房租爱交不交,白丽华也不好管。那些河南小演员不排练时都在歌厅酒吧里打工,有的还沦落为暗娼,去年扫黄,警察把抓到的鸡拉到街上游行,大家亲眼所见,中间就有文工团招聘来的河南演员。白丽华的工于心计也是承传她母亲的。知道吗,白丽华在活动着想当文化局副局长呢。
我说,那她走了,谁来当团长。
苏彩云说,你傻呀,到时候她就是文化局副局长主持文工团工作了,团长好歹是一把手,能签字同意报销呢。再说了,局里哪个副局长的办公室有她的大。
不知不觉中,桌上的啤酒罐已有十来个了。苏彩云起身又要去拿,她那饱满丰润而又不失曲线的胴体在玲珑剔透的短裙下若隐若现,冥冥中,我好像是拉住了苏彩云不让她再拿啤酒,但接下来就记不清了,不知道是谁主动,反正我们拥在了一起。欲火焚去了我们体表的赘布,我们像一对赤裸冤家,从客厅的沙发纠缠到卧室的床榻。
苏彩云推醒我时已是凌晨,她一只胳膊支撑着头侧着身体好奇地看着我,一如凝视她的婴儿。没有意外,没有羞恼,没有责怨,一切仿佛水到渠成。半晌,她问,《灯草和尚传》看得怎么样了。
我说,看了一些,好像就是和尚女人偷情淫乱的那点儿事。
苏彩云说,那是表象,以女人的眼光看,肯定人性,蔑视礼法才是它真正要表达的。苏彩云说话时,零乱的长发萦绕着我的颈间和胸膛,痒痒的,我忍不住伸手揽住她的肩膀,苏彩云咯咯笑着,又是一番耳鬓厮磨。
夏天的文化广场人少,杨世禄来我这儿坐的时间就长些。那天我突然想到苏彩云和白丽华之间的隐隐敌意,于是问,苏彩云和白团长往年是不是有过节啊。杨世禄说,这说来可就话长了——
那时白丽华才招工不久,还在团里卖票,苏彩云已经是团里的台柱子了,能歌善舞,还能编排节目。她们是闺中密友,当时有人给苏彩云介绍了一个在交通局上班的对象,看电影都是三个人一起,逢苏彩云演戏时,就白丽华陪着苏彩云的对象在下面看,后来苏彩云的对象就喜欢上了白丽华,两人就结婚了,夺夫之恨呢,矛盾能不大吗。我问,苏彩云那么优秀,怎么会输给白团长呢。杨世禄说,搁我也不会选择苏彩云,拿腔捏调地说话,风摆柳地走路,搁舞台上好看,搁家里谁受得了!男人娶的是能过平淡日子的老婆,不是狐狸精。苏彩云后来找了个老师,两人儿子都多大了,那老师还是看不惯她那风骚劲儿,又因为跳舞和别人搂搂抱抱的,打了一架就离了。
和白丽华一起在场面上应酬,总能有所领悟。白丽华宴请财政局预算股高股长的规格是罕见的高,在车上白丽华对我讲,这高股长虽然级别不高,可是财神爷呢,笔头子一崴就能多划拨个十万八万的,对我们这样的单位可不是小数目。那次喝的是五粮液,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喝五粮液。吃完饭到酒吧唱歌,白丽华特地嘱咐,我的任务就是陪好预算股那唯一的女会计。
定了包厢,领班带进来十几个小姐让客人挑选。正如苏彩云所说,我一眼就看见了和我同住一楼的河南小姑娘。我相信白丽华也应该是认识的,而她们更应该认识白团长。但这里是酒吧,白团长是消费者,她们和桌上的水果红酒一样是被消费者,我看到她们都如陌生人那样自然。被挑中的小姐夸张地傍到客人身边,有的径直就坐到了客人腿上。白丽华和高股长合作了几首情歌之后是的士高,大家相继拥伴儿而舞,就我不知所措地陪那位女会计在黑暗中坐着。他们扭曲张扬的身体在忽闪的激光灯中充满着诱惑和欲望,又碰了一杯红酒,女会计说,我们跳舞吧。我说,我不会。女会计笑一下,一杯红酒一饮而尽。这一切竟未逃过白丽华的眼睛,回去途中,白丽华对我说了句,记住,女人在酒吧里就单纯是女人。我没听明白。
国庆前夕,影剧院放映了《张思德》,县委宣传部要求各战线组织干部职工和中学生观看。门票十元,学生半票。虽然门票收入要和宣传部五五分成,但这也是团里继财政拨款之外的又一大进项。电影由徐会计放映,没有人检票,更没有人中途查票,观众随便进,随便坐,尽管如此,硬性售出的两千多张票,也只进来了不到三百人。虽然这电影我以前在网上看过,但还是进去重温了一下影院里看电影的感觉。尽管是很有怀旧感的黑白电影,却丝毫感觉不到记忆里空旷的黑暗中弥漫着的寂静,更别说什么艺术享受。我身临其境地感觉到人们对电影的热情褪了,正如杨世禄所说,影剧院的辉煌不再了。
十一长假,我回了趟老家。等车时正好遇到老同学王诚,就搭了他的顺风车,我问王诚,在哪儿高就呢。王诚说,在家当猪倌儿。见我不明白,他介绍他在老家的山沟里建了一个养猪场,接着说如今猪肉怎样俏,政府怎样补贴养殖户。末了又说,你怎么不停薪留职回来自己干呢,你家现成的山场坡地,种树养羊点香菇,那都是钱啊,你父亲搞农业又是行家。
我把王诚的建议据为自己的主意,在闲聊中告诉了苏彩云。苏彩云说,早就该这样想了。论事业吧,在文工团里男人永远都是配角,你看哪有观众冲着男演员去的;论收入吧,撑不着饿不死,尚且不说买房买车养老婆孩子了。我说,我想明年就走,年底就跟团长说明。苏彩云说,一年也快到头了,接下来团里就该准备到市里会演的节目了,估计白丽华也该安排你写年终工作总结了。我突然想编排个节目,来证明我在文工团里的分量。
正如苏彩云所料,白丽华安排我写年终工作总结,并开导说就照以往的模式套,具体数字按年初工作方案里的填,超一点儿也可以。我点头,然后说,白姐,我想编排个节目参加市里的会演。白丽华笑,那好,今年就不用花钱去请局里创作组的那帮人了——也别太复杂,搞个小品就可以了。我也笑,我知道白丽华笑的意思是说无所谓,她是重利不重名的人,工作只要能应付过去就可以,维持单位运转才是最重要的。说到底,钱才是硬道理。
即使是排小品,我觉得也应该排个有深度的,这毕竟和我们那帮大头兵在部队联欢会的自编自演的小节目不同,这是文艺单位的年终考评。我查阅了往年团里参演小品的影像资料,无一不是歌颂干部廉洁政府惠农的题材。经过几天思考,我决定以县志中记载的剿匪史实为蓝本,结合我县的特征地貌,以曾参加过剿匪的老姑父为原型来创作。有一段细节是我饰演的解放军连长带人追击几个残匪到鄂川边界的高山湿地时,被原始景象所感染,突然放弃追击。
演出时,当背景大屏幕上出现碧水长天落霞孤鸿的湿地风景时,我手向后一扬,战士们收起枪,表情同画面里的景象一样清澈空灵。台下观众席也是一片静谧,生怕惊扰了屏幕里那片世外桃源和几个像在接受大自然洗礼的演员。
但是评委之间却产生了分歧,有人说连长未继续追击是不作为,是对敌人的投降,有人说它打破了传统颂唱的庸俗,最后一位主抓文化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说,此小品以自然的美丽净化了人们的灵魂,特别创新的是,展示了当地的自然风景,起到了“名片”的作用。有了权威的定调,我的小品获得了全市会演一等奖,这也是团里十年来头一回获此殊荣。随之县委宣传部、文化局的荣誉也接踵而来。白丽华笑着说,没想到啊,你小试牛刀就不同凡响,有前途啊。看得出这次是发自肺腑的惊喜的笑。
苏彩云也特地向我祝贺,但她更担心的是我会因此而放弃之前的决定。她问,你会因此留下来吗?我说,不会,我的初衷只是证明男人在文工团也可以做主角。苏彩云说,我错了。我说,你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苏彩云笑,我会支持你的,比如资金方面。我也笑,你不怕血本无归。苏彩云摇摇头,说,现在流行一种情感叫性友谊,就是朋友在适当的环境,适当的时机碰出性的火花,它没有情人的暧昧,只是比朋友更深入一些。
年终,白丽华给我单独发了个红包。我知道这是对我的特别奖励。嗫嚅了半天,我还是鼓起勇气向白丽华说了我的想法,怕她不同意,又补充一句,办停薪留职也行。
白丽华很吃惊,半晌才说,当初你来时,我就怕怠慢了你,没人帮我,想不到最终你还是不肯帮我。
我说,白姐,我只是想外面的天地更宽一些。
白丽华说,我知道你是嫌一个男人在文工团里没出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文工团的春天马上就来了,你是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我可以保证,以后我会提你当副团长,甚至团长,或者帮你活动到文化局,你要相信我说到做到。
我说,我相信,白副局长。边掏出诺基亚退还给她。
白丽华摇摇头没有接,说,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想你要是做不成功就好了,还回来上班。
我说,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等我发达了,也在阳光花园买房子,跟你做邻居。
责任编辑:陈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