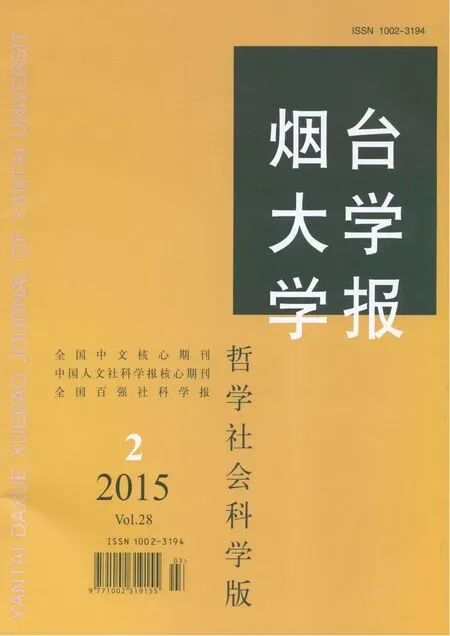冒顿请婚新说
景凯旋
(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62)
冒顿请婚新说
景凯旋
(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汉书·匈奴传》所载冒顿向吕后请婚被视为汉匈关系中极为典型之事,而《史记》中却不载此事。前人多认为司马迁出于政治“忌讳”不载此事,东汉时班固不再“忌讳”,因而在《汉书》中重新记载此事。这种解释虽有合理之处,但也存在一些疑问。从《汉书》增补内容的疑点以及匈奴对汉朝社会的影响来看,冒顿请婚一事应为谣言。谣言约产生于太初四年之后,为司马迁所未见,故《史记》不载。东汉初年,由于汉匈关系再度紧张,冒顿请婚之事重新被勾起或被创作出来,又为班固所见,从而被载入《汉书》之中。谣言虽然不可信,却反应了时人恐惧匈奴、憎恨匈奴、希望德化匈奴以及不满吕后女主干政等社会情境。
冒顿;匈奴;谣言;汉匈关系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15.02.014
据《汉书·匈奴传》记载,高祖逝世后匈奴冒顿单于曾遗书汉朝,向吕后请婚。吕后对此十分生气,召集陈平、樊哙、季布等人商议。樊哙主动请命,称其“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以报复冒顿的无礼。樊哙此议遭到季布的强烈反对,季布以平城之战为鉴,认为此时汉朝国力尚未恢复,不宜对匈奴发动战争。最终,吕后采纳季布的建议,不得已采用卑辞厚礼的方式回绝了冒顿的无礼请求。①《汉书》卷九四《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54-3755页。在此一事件中,匈奴的狂妄无礼、汉朝的忍辱求和表现得极为明显。因此,冒顿请婚被视作汉匈关系极为典型之事,像钱穆、陈序经、田继周、林剑鸣、田昌五等许多秦汉史、民族史的学者都引用此事以说明汉初汉匈关系的不平等。②此类讨论如钱穆:《秦汉史》,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67页;陈序经:《匈奴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1-202页;田继周:《秦汉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92页;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6-287页;田昌五:《秦汉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9页。据笔者所见仅有彭年《冒顿请婚新议》(《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蔡敏慧《冒顿请婚再议》(《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4期)从匈奴社会习惯出发,认为冒顿请婚之事不存在挑衅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同样记载汉初百年历史的《史记》却没有请婚之事。《史记》《汉书》的记载何以会出现这种差异?对此,前人早已注意到,且从马班二人著史才能、心理、背景作出过一些解释。这些解释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另外,前人也忽略了一些重要的疑点以及相关记载处的差异。鉴于此事在汉匈关系中的重要性,笔者欲对此事再作进一步探讨。
一
《史记》《汉书》关于冒顿请婚之事记载的差异,早已为前人所注意到。如唐人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就利用《汉书·匈奴传》所载的冒顿遗书内容来补充《史记》的记载。*司马贞:《史记索隐》卷二五,见《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95页。清代学者牛运震较早对《史记》《汉书》记载差异的原因作出解释,他认为冒顿与吕后往来书信“污嫚无礼”、“猥陋不成体度”,没有记载的价值。*崔凡芝:《空山堂史记评注校释》卷十,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45页。司马迁出于为国避讳,所以在《史记》中不载此事。*牛运震:《读史纠谬》卷二,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117页。之后,赵翼、杨树达、朱东润、曹仕邦等学者也都作出过解释,观点与牛运震的解释基本相同,均认为司马迁出于忌讳而不载此事,只是对《汉书》为何记载此事见解不同。牛运震认为班固记载此事“殊失体”,而赵翼则指出是由于班固没有史识,不懂得取舍,才将双方“秽亵”的书信“详录不遗”;*赵翼:《陔余丛考》卷五,“史记四”条,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87页。杨树达以光武帝时改尊薄太后为高皇后为据,认为东汉时期吕太后地位下降,班固此时不再为吕后避讳此事;*杨树达:《汉书窥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739-740页。朱东润从民族心理出发,认为东汉明帝永元三年(91年)汉朝已经击败匈奴,汉匈实力对比关系彻底扭转。对时人以及班固来说,“在胜利到来的时候,追溯以往曾经受过如何的屈辱,愈加感到一种忻(欣)慰”;*朱东润:《〈史记〉〈汉书〉所用史料之关系》,《史记考索(外二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8-299页。曹仕邦认为除了胜利后的欣喜之外,班固还考虑到记载此事可以警示时人不忘防范匈奴。*曹仕邦:《浅论〈史记〉〈汉书〉对“冒顿单于求婚吕后书”的取舍》,《故宫图书季刊》(台北)1973年第2期。
以上学者的解释看似都比较合理,但也存在一些疑问。第一,《史记》为司马迁私修,修成之后又无立即公布的打算。因此,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对现实政治的忌讳较少,会尽可能如实记录当时统治阶级的一些“丑闻”。比如《史记》记载了高祖好酒色、吕后残暴成性、景帝冤死周亚夫等。正因为如此,班固才称赞《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2738页。。退一步来说,假如说上述事件不是国与国之间交往,不涉及“国体”的话,那么《史记》中多处记载平城之战时高祖通过“厚遗阏氏”解围又作何解释?*司马迁在陈平、韩王信、夏侯婴等人传记以及《匈奴列传》中均强调高祖是通过“厚遗阏氏”才得以解围,分见《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2057页)、卷九十三《韩王信》(第2634页)、卷九十五《夏侯婴》(第2666页)、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894页)。况且高祖地位远较吕后高,是更应该避讳的。
第二,冒顿向吕后请婚时,吕后已身为汉朝皇太后且年近五十。冒顿向她请婚,十分荒唐且有悖常理;冒顿请婚书又颇具文采,能以韵文的形式、*杨树达:《汉书窥管》,第740页。比喻的方式、调侃的语气写出,颇为奇妙有趣。*《史记》记载匈奴没有文字,假如存在冒顿遗书肯定是用汉文写成。从遗书的文采来看,不论作者是匈奴人还是汉人,对汉文化必有相当了解,不会不知道此事是对汉朝及吕后的极大侮辱,况且汉朝还有公主在匈奴。因此,彭年、蔡敏慧两人说法很值得怀疑。而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喜欢记载“奇事、奇文、奇语”。*可参见刘振东:《论司马迁之“爱奇”》,《文学评论》1984年第4期。请婚之事荒唐有悖常理、冒顿遗书奇妙有趣,这十分符合司马迁的史学写作风格,能被记载的可能性比较大。
第三,在《史记》中司马迁也有意记载匈奴的狂妄无礼。如在《匈奴列传》中就特别收录了文帝时期匈奴遗书一封、汉朝遗书两封以及一则文帝下的诏书。遗书中匈奴单于自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并对文帝说:“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第2896页。意思是说假如汉朝不愿意看到匈奴近塞(侵扰边塞的委婉说法),那么就请你下诏将吏民内迁。接到书信之后文帝十分生气,想要进攻匈奴,最后在群臣的进谏下才作罢。又比如记载单于遗汉书写在一尺二的木牍上、匈奴官员印章“广大长”,以及此后单于“倨傲其辞”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等。*《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第2899页。可以看出,司马迁也是有意记载匈奴的无礼,对最能表明匈奴无礼的冒顿请婚却不记载,这让人颇为疑惑。
第四,《汉书》为什么记载此事?以上学者的解释也存在问题。赵翼认为班固没有史识,这与雷海宗认为司马迁史学才能低劣漏载此事一样,*雷海宗:《司马迁的史学》,《伯伦史学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236-242页。论断明显有些武断,显然不足信。吕后的社会地位,自然是在吕后逝世后群臣发动政变诛杀诸吕时最低。《史记》中就记载了许多吕后的凶残行径,可以说司马迁没有为吕后避讳,或避讳甚少。再者,光武帝改尊薄太后为高皇后并非有意贬低吕后。光武帝为高祖九世孙、景帝的后裔,由于年代久远,血缘已疏。薄太后为文帝之母,景帝之祖母,光武帝尊崇薄太后的目的在于强调自己作为天子的正统性。这正如《后汉书·光武帝纪》开篇所写的“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高祖九世之孙也,出自景帝生长沙定王发”一样,*《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页。强调光武帝的正统地位。因此,杨树达的解释并非完全合理。在汉武帝时代,汉朝多次征伐匈奴,尽管付出很大代价,但已经取得了“漠南无王庭”的成绩。汉匈关系已经扭转过来,而且是第一次改变了高祖、惠帝、文帝、景帝以来的不平等状况。司马迁称赞“汉兴五世,隆在建元”,而武帝两项功绩之一便是“外攘夷狄”。*《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3303页。司马迁也当有班固那种“在胜利到来的时候,追溯到以往曾经受过如何的屈辱,愈加感觉到一种忻(欣)慰”的感觉。因此,朱东润解释不是很具有说服力。司马迁自述其作《匈奴列传》的目的:“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3317页。这与曹仕邦所说班固警示人们防范匈奴目的相同。因此,曹仕邦的解释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五,最为重要的是,前人忽略了《汉书·匈奴传》记载的一些错误。《汉书·匈奴传》记载季布以平城之战为鉴反对樊哙讨伐匈奴,却认为高祖是在讨伐陈豨之时被围。平城之战是高祖平定韩王信叛乱,《汉书·匈奴传》此处记载明显错误,这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早已指出;*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一,上海: 商务印书馆,1926年影印宋刊本,第2页b。季布称在平城之战时“哙为上将军”,而《史记·樊哙传》中记载,平城之战时“以将军从高祖攻反韩王信于代”。*《史记》卷九五《樊哙传》,第2657页。上将军、将军为两种不同职官,上将军地位远较将军显赫;陈平是在孝惠帝六年(前189年)任左丞相,而此事发生在惠帝三年(前192年)与匈奴和亲之前。史书自有体例,*赵翼:《陔余丛考》卷五,“史记二”条,第86页。不应该在惠帝三年之前称陈平为丞相。
最后,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关于冒顿遗书侮辱吕后一事,《史记·匈奴列传》《史记·季布传》《汉书·匈奴传》《汉书·季布传》都有记载。而仔细阅读这些记载,我们会发现除了《汉书·季布传》文字因袭《史记·季布传》,两传记载相同外,与《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记载各不相同。比如《史记·匈奴列传》中在讨论此事时,群臣都反对出兵。而在《史记·季布传》之中,群臣态度发生很大的改变,变为阿谀奉承之徒都在讨好吕后,赞成樊哙出兵。《史记·季布传》中季布进谏之后,“是时殿上皆恐,太后罢朝,遂不复议击匈奴事”。而在《汉书·匈奴传》中,吕后对季布进谏欣然接受,称“善”,吕后态度明显不同。对于这些细节上的差异,以前学者几乎都忽略了。
二
如何理解《汉书·匈奴传》增补内容的错误以及《史记·匈奴列传》《史记·季布传》《汉书·匈奴传》三传记载的不同?我们有必要从史料来源作一些分析。司马迁、班固记载此事的资料来源可能有三:一是利用的原始档案文献写成,二是参考其他著作而成,三是采信社会中传闻而成。据乔治忠的研究,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已经有较为完备的史官记事制度,史官以君主为中心记载国家所发生的大事。西汉建立后承袭了这一制度,史官所做记载在当时被称作“著记”(又称“著纪”或“注记”),这也是司马迁、班固著史的重要依据。*乔治忠、刘文英:《中国古代“起居注”记史体制的形成》,《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2期。冒顿遗书侮辱吕后是当时汉匈关系中一件重要的大事,群臣对此还有一番激烈的讨论,必当见于惠帝或吕后时期的“著记”之中,这也当是关于此事最初、最准确记载。假如陈平参加当时讨论,“著记”绝不会将陈平称作丞相。就算是季布引述有误,但史官对“著记”后期整理时很可能会改正这一无关讨论主旨的常识性错误。另外,《史记》中没有《汉书·匈奴传》中出现的这些错误,这也能从侧面证明“著记”的可靠性。再假如班固利用的不是当时史官所写“著记”,而是冒顿与吕后双方往来书信的原件或者抄本,那么《汉书》增补内容的疑点依然无法解释。以班固的史学才能,断然不会虚构一些自己想象的情节,并且这些增加的情节存在一些明显的错误。很显然《汉书·匈奴传》不是仅依据“著记”或者参考原始档案而成,更可能参考了其他一些记载或传闻,其可信度也就值得怀疑。
将社会中的一些谣言当做史实记载到历史中,这在《史记》《汉书》中并不少见。比如社会中将平城之战时匈奴兵力数夸大到四十万或三十多万、*曾宪法:《“白登之围”兵员数目考》,《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刘敬以长公主为和亲首选人、*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54页。郭吉出使匈奴时说“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等*徐朔方:《史汉论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68页。。谣言的产生与汉初社会情境紧密相连,从西汉建立到班固时代的近三百年时间里,汉朝与匈奴大多处于一种紧张对立的状态中。匈奴对汉朝社会影响如此之大,自然会成为社会中舆论关注的重点。各种信息在社会上长期传播的过程中,自然会产生一些与匈奴相关的谣言。而当时信息闭塞,普通人甚至是官员获得匈奴信息是有限的,因而也就无法辨别一些谣言真伪。谣言一方面满足时人对匈奴信息的渴求,一方面时人也借此表达他们对汉匈关系的意愿以及诉求。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谣言不仅普通人无法辨别,并且还乐意相信、传播,就是像司马迁、班固这样的大史学家也受影响。
那么,冒顿请婚这一谣言是如何产生的?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颁布的一则诏书很值得注意。在征服大宛之后,汉武帝志得意满昭示天下:“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第2917页。汉武帝向国人宣告他征伐匈奴的目的,是为了一雪高祖、吕后以来所受的耻辱,而现在目的已经基本实现。可以想象,武帝这封诏书颁布之后,时人除了了解武帝对匈奴开战原因之外,也会有人因为好奇而猜测单于遗书的内容。由于匈奴对汉朝社会的影响,与此类似例子在两汉时期很多。比如桓谭猜测陈平利用了匈奴阏氏的妒忌心理,称汉有好丽美女,将要进献给单于,“单于见此人,必大好爱之;爱之则阏氏日益远疏”,使得高祖解围。*桓谭:《新论》,见《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裴骃注,第2057-2058页。应劭猜测,陈平派人说服阏氏时,“使画工图美女”,向阏氏诈称将要向单于进献的汉朝女子如此美丽。*见《汉书》卷一《高祖纪》颜师古注引,第63页。《三辅故事》中记载,刘敬出使匈奴时与匈奴割土盟誓,作丹书铁券。*见李昉:《太平御览》卷七七九《奉使部三·奉使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七册,第837页。由于女性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往往与流言蜚语和丑闻联系起来。*奥尔波特等:《谣言心理学》,刘永平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9页。因此,便可能产生了冒顿向吕后请婚这一说法,更在此基础上编造出冒顿请婚书以及吕后回信。
司马迁为何没有记载请婚之事?这应与谣言产生的时间以及流通范围有关系。冒顿请婚的谣言产生于武帝太初四年以后,太初四年据司马迁去世约有十余年。*司马迁卒年史书无明确记载,但卒于汉武帝末年则是可以肯定。从太初四年(前101年)到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中间约14年。可参见程金造:《司马迁卒年之商榷》,《史记管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5-124页。请婚谣言以及伪造书信是否在这段时间被创造出还很难说,就算被创造出来司马迁也不一定见到。另外,天汉二年(前99年)司马迁受李陵事件牵连被下狱受腐刑,可能对此也造成了一些影响。
汉武帝为何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这与中国人强调孝道的观念有关,汉武帝是在告诉人们,自己征讨匈奴不是为了发泄自己愤怒,而是为了一雪祖上的耻辱。为何冒顿遗书使得汉朝如此愤怒,这又与高祖末年与匈奴的和亲有关。高祖征讨淮南王英布时“为流矢所中”身受重伤,开始为自己身后之事作出安排。对内大封功臣笼络人心,对外则与匈奴进行和亲。在这次和亲中,汉朝作出重大让步,“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第2895页。这次和亲也起到一些作用,匈奴对汉朝侵扰明显减少。到了惠帝三年(前192年),冒顿遗书挑衅汉朝,这距双方签订合约仅有三年。在汉朝看来,汉匈“和亲”已作出巨大让步,而匈奴却不遵守和约挑衅汉朝,自然使得汉朝上下对此极为愤怒。汉朝将此视为极大耻辱,汉初几位皇帝视作国仇而“谨记”。
接着,我们再来看《史记·季布传》的资料来源。季布为人勇敢、遵守诺言,具有侠者的气概,在当时社会中富有名气,自然会出现一些夸大季布形象的“英雄故事”。季布曾为项羽将领,汉朝建立之后不得不装作奴隶逃命,最终得到高祖赦免而成为汉朝名将。在司马迁看来,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与季布极为相似。在《季布传》的论赞中,司马迁所说的“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史记》卷一○○《季布传》,第2735页。与《报任安书》对比来看,这无异是司马迁在自明其志。司马迁对季布比较推崇,引以为榜样,自然容易相信、记载一些夸大季布的“英雄故事”。
了解《史记·季布传》《汉书·匈奴传》资料来源之后,我们就容易解释《史记·匈奴列传》《史记·季布传》《汉书·匈奴传》记载的差异。首先我们来看季布的形象,在《史记·匈奴列传》中群臣都反对战争,没有特别提及季布。而在《史记·季布传》之中,采信了社会中季布的英雄故事,为了突出季布,群臣都变成阿谀奉承之徒,为了讨好吕后皆赞成樊哙出兵,而季布据理力争、直言犯谏,季布的英雄形象得以彰显。《史记·季布传》中,季布进谏之后,“是时殿上皆恐,太后罢朝,遂不复议击匈奴事”,突出季布进谏后的震撼效果。而在《汉书·匈奴传》中,吕后态度发生很大变化,听完季布进谏之后,高后曰“善”。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史记·季布传》目的在于突出季布形象,而《汉书·匈奴传》记载此事的完整过程,记载了之后汉朝与匈奴的和亲,以及冒顿的悔过。为了纪事的连贯性,因此吕后态度转变为虚心接受季布建议。
除了这些差异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汉书·匈奴传》一些说法是从《史记》发展而来。《史记·匈奴列传》《史记·季布传》记载内容发生较早,为《汉书·匈奴传》对此事的记载提供框架。《史记·季布传》中记载了樊哙、季布的讨论情况,《汉书·匈奴传》则称“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哙、季布等”。季布官职为中郎将,地位远不及中央的三公九卿,季布也并非为吕后宠臣,吕后为此事特别召见不太可能。吕后特别召见季布,这只是后人对《史记·季布传》的一种想当然的演绎。《史记·季布传》称讨论此事时樊哙为上将军,《汉书·匈奴传》则误以为在平城之战时樊哙就为上将军。上将军为汉初极为显赫的军职,《史记·樊哙传》中却没有记载樊哙曾为上将军,樊哙是否曾为上将军,不得而知。但在平城之战时,樊哙“以将军从高祖攻反韩王信于代”,*《史记》卷九五《樊哙传》,第2657页。此时他绝非上将军。后人根据《史记·季布传》樊哙为上将军的记载,误以为平城之战时樊哙为上将军。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有故事演变的痕迹。
三
社会学认为谣言并非凭空产生,它的产生、流传有一定的规律,与当时社会情境、人们的知识背景、情感有着密切关系。谣言虽然不可信,却能准确反应出人们的意愿以及诉求。*奥尔波特等:《谣言心理学》,第17-27页。因此,我们也可以结合当时社会背景、时人情感,对冒顿请婚这则谣言的内涵进行分析。
第一,恐惧匈奴。平城之战后高祖开始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这一政策延续到武帝执政初期。汉朝除了多次将公主嫁于匈奴单于之外,每年还要给予匈奴一定数量实物。虽然付出不小的代价,但仍未能避免匈奴的入寇。匈奴不时入寇,汉朝民众除物质受损失之外,也容易产生一种恐惧心理。武帝即位后不久,对匈奴进行了大规模的征伐。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付出“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巨大代价。在这种社会情境之下,人们很容易将原因归结于匈奴的强大。匈奴自恃其实力的强大,经常做一些狂妄无礼之事。因此,人们对冒顿请婚这则谣言误以为真。
第二,憎恨匈奴。由于汉朝与匈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中,匈奴的不时入侵给汉朝社会带来巨大灾难,时人对匈奴有着莫大的仇视。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朝对匈奴战争取得阶段性成果,匈奴浑邪王投降汉朝。为了迎接浑邪王的投降,汉朝想要出兵两万乘。由于国力不足,从民间强行赊购马匹,许多人都将马藏匿起来。这些投降的匈奴人来了之后,汉朝又取用民间财富用于赏赐。汉武帝这样做自然有其政治目的,但民众则很不能理解。这些政策使得百姓再次受累,民众对匈奴仇视进一步加深。汲黯的态度很能代表当时民众的想法,他认为应该把俘获的匈奴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将获得的战利品也一并赏赐给百姓。就算不能如此,也不能“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史记》卷一二○《汲黯传》,第3109-3110页。对武帝优待匈奴归降者,普通民众无法改变。民众通过宣扬匈奴狂妄无礼,借以表达了对匈奴的憎恨、对武帝优待匈奴归降者政策的讽刺与不满。
第三,德化匈奴。“德化”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处理与四夷关系的一种重要的主张,为中原王朝处理与四夷关系提供了除战争之外的另一种选择。由于这种方式损失较少,在道德上易得到更多的支持,尤其是面对那些力量强大、不易征服的少数民族更是如此。文帝将匈奴入寇原因归咎于自己,“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史记》卷一○《文帝本纪》,第431页。在具体实施方面,通过派遣使臣宣慰修好,使得赵佗去帝称臣。*《史记》卷一三○《南越列传》,第2970页。这种成功的案例,自然也会增强时人对“德化匈奴”的信心。冒顿请婚,最后却以冒顿感于中国礼仪而“遣使谢罪”结束,表达了时人对德化的认可,也表达希望通过德化政策解决匈奴问题的美好愿望。
第四,不满吕后执政。高祖逝世,吕后掌权之后与诸大臣存在很大的矛盾,为了巩固其统治,一面排挤残杀刘姓宗族、功臣宿将,一面任命诸吕担任重要职位,这自然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吕后逝世后,周勃与陈平诸人尽诛吕氏,拥戴代王刘恒为帝。吕后的势力被剪除后,时人对吕后的不满得以发泄,种种劣行被公布于众,其中也存在不少捏造污蔑之事。此外,吕后以女性身份执掌大权,本身也受时人非议。由于社会中吕后形象较差,不受时人尊重,故会成为时人戏谑调侃的对象。因此,当时人猜测冒顿遗书具体内容时,便产生了冒顿向吕后请婚这一谣言。吕后“女主干政”不仅自身受辱,而且也使得汉朝国体受到侮辱,时人借冒顿请婚表达对吕后的不满。
四
两汉时期,匈奴的强势对汉朝社会影响极大,是社会舆论关注的重点。在信息社会传播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与匈奴相关的谣言。由于当时信息的闭塞,时人无法辨别一些谣言,加之一些谣言与当时社会情境、心态十分吻合,时人很容易对此信以为真。这些谣言虽不一定曾发生,但却为我们展现了当时的社会情境和时人的心态,《汉书·匈奴传》所载冒顿请婚之事,即为此一例。《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了此事的最初版本,《史记·季布传》记载了汉武帝时期社会上对此事的了解,这也是太初四年之后人们想象的故事框架。在《汉书·匈奴传》中,对《史记·匈奴列传》《史记·季布传》内容又增补很多内容。最明显的增补是冒顿遗书以及吕后回信的内容、冒顿最后的反应。在一些细节上增补的地方则更多,比如称吕后大怒,召集陈平、樊哙、季布等人商议此事,增加季布的反对理由“且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等。另外,在一些地方有删减和改动,比如删减了《史记》中群臣反对或同意的态度,改变了《史记·季布传》中吕后的态度。通过这些修改,使得纪事情节更加饱满、连贯、完整。
谣言固然不可尽信,却反应了时人恐惧匈奴、憎恨匈奴、希望德化匈奴以及不满吕后女主干政等社会情境。谣言产生于太初四年之后,司马迁没有见到,因此《史记》中没有记载。东汉初年,匈奴再次兴盛,又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冒顿请婚之事在时人记忆里重新被勾起或创作出来,并为班固所知,从而将其载入《汉书》之中。冒顿请婚从谣言进入历史,这也再次印证了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经典论断。*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9-66页。
[责任编辑:曹鲁超]
New Explanation for Modu’ Proposal to Empress Lü
JING Kai-xuan
(InstituteforWesternFrontierRegionofChina,Sh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062,China)
In the record of the Huns Biography in theHanshu(《汉书》), Modu(冒顿) made a proposal to the Empress Lü(吕后)which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typical examp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n Dynasty and Huns. However, the account for this historical event can not be found inShiji(《史记》). To explain this phenomenon, most historians believe that due to political taboo, SIMA Qian didn't mention it, and BAN Gu in Eastern Han Dynasty didn't taboo any longer. Although it is reasonable, there are also some doubtful points.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doubtful point supplemented in the History of Han, the influence of Huns to the society of Han Dynasty, this paper speculates that Modu's proposal to Empress Lü is a rumor which started after the fourth year of Tai Chu (101 B.C.) when Sima Qian had died, so he could not record that.
Modu; the Huns; rum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n dynasty and Huns
2014-10-13
景凯旋(1988- ),陕西乾县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边疆民族史研究。
K
A
1002-3194(2015)02-01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