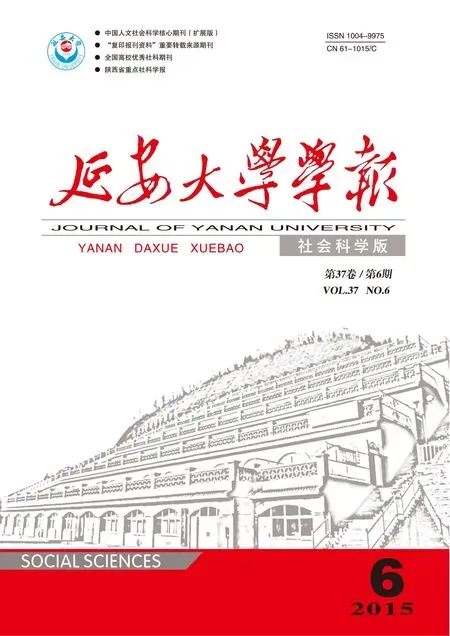被“开发”的乡土及其伦理现实主义省思——贾平凹《带灯》论析
周 涛
(黄山学院文学院,安徽黄山242700)
被“开发”的乡土及其伦理现实主义省思
——贾平凹《带灯》论析
周涛
(黄山学院文学院,安徽黄山242700)

摘要:面对当代中国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城镇化进程,贾平凹的《带灯》聚焦于乡村生活世界的独特伦理景观,发掘和评估当下乡村社会所遭遇的现代性困境以及由此提炼而成的“中国经验”。“带灯”形象的塑造体现了贾平凹复苏传统伦理记忆的努力,她的悲剧则突出了现实主义叙事逻辑的力量。“写伦理”的诉求与现实主义原则构成了《带灯》伦理现实主义的创作范式,为当代文学进入目前的乡村社会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
关键词:带灯;“写伦理”;现实主义;现代性困境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带灯》出版以后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由于和当下的新农村和城镇化建设有关,《带灯》的主题和题材无疑是重大而尖锐的,但如果仅仅指出这是贾平凹的“又一部现实主义乡土力作”[1],“重建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维度”[2],显然并不能洞察其在现实主义范畴内所提供的新的审美经验。贾平凹本人不止一次地说过:“写实就是写日常,写伦理”[3],“我们需要学会写伦理,写出人情之美”[4]。《怀念狼》对人作为万物主宰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秦腔》奏响了传统道德理念与生产、生活秩序的挽歌;《古炉》借助“善人说病”的特殊方式表达了“重建伦理秩序的诉求”[5]。贾平凹近年来的创作或隐或显地贯串着一条伦理脉线,在《带灯》中进一步发展为伦理现实主义的创作范式*本文所提出的“伦理现实主义”概念有别于贺绍俊先生的观点,他认为“所谓伦理现实主义,是中国文学传统中关注现实的一种普遍态度和立场在现代小说中的自然延伸。这种关注现实的普遍态度和立场就是一种重视社会正常发展的人伦秩序并进行鲜明的扬善惩恶的宣谕”。参见《伦理现实主义的魅力——细读赵德发的一种方式》,《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3期。,即在创作理念、人物形象、叙事结构等方面浸润伦理精神,在情节和细节层面呈现当下乡村社会的伦理生态图景,进而发现和思考隐伏在这些现象中的时代动因和特质,直面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里的各种难题和困境,建构现实主义文学的伦理品格,精心营造既凝聚了特定的时代信息、又烙有自身鲜明印记的乡村生活世界,达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去突破和提升”[6]的创作意图。
一、乡村生活世界的伦理图景
《带灯》开篇伊始,作者便指出“这年代人都发了疯似地要富裕,这年代是开发的年代”*贾平凹:《带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后文来自《带灯》的引文均出此版本,不再一一作注。。生活的富裕,物质的富足,无疑是历史进步的标尺,但突出这一历史进程的“疯狂”性,则透露了作者一贯的隐忧:“历史的进步是否会带来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和浮虚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只适应于闭塞的自然经济环境呢?社会朝现代的推移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趋尚实利世风的萌发呢?”[7]历史进步并不必然导致人情与道德伦理的凋零,两者的相悖恰恰显示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乡村社会的独特遭遇。
带灯和丈夫的感情不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一心想着要发财出名当画家”;“十三个妇女”的丈夫在大矿区打工得了矽肺病,只能在家中坐以待毙;元薛两家的男丁由于沙厂利益冲突发生大规模械斗而死伤惨重,留下了一群妇女。“家和万事兴”,这是中国人传统的家庭伦理诉求,小说中所呈现的这些家庭的不幸和悲剧看似形态各异,实际上都渗透了来自于经济利益与物质追求的欲望和冲动。类似的伦理失谐现象在小说中也发生在亲戚和邻里之间,乡村文化向来有“娘亲舅大”的传统,王中茂的女儿结婚办酒席,孩子的舅舅竟然不知情,乡人们问起,这位舅舅悲愤地说:“没钱的舅舅算个屁!”而来赴宴的客人也有惊人之举,吃完饭离去时将碗碟丢在尿窖子里。刘慧芹结婚时,要给男方五元开口钱,却被帮厨人将五元钱换成了一毛钱,导致刘慧芹受辱自杀。张膏药家失火,邻居没有先去救火,而是忙着“搭梯子往自家屋檐角上苫”,张膏药最终被烧死。俗谚“远亲不如近邻”,传统邻里间“亲仁善邻”(《左传·隐公六年》)、“守望相助”(《孟子·滕文公上》)、宽容礼让的道德伦理原则在当下的中国乡村正在渐行渐远,以至于带灯不无愤激地说:“我现在才知道农民是那么的庞杂混乱施虐无信,只有现实的生存和后代依靠这两方面对他们有制约作用。”其深层原因不能不让人深思。
带灯所在的镇政府根据形势的需要,“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寻找经济新的增长点和维护社会稳定上”,两者之间理应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经济发展能促进社会稳定,也只有在社会稳定的条件下,经济才能获得有保障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在小说中,它们之间的关系却颇耐人寻味。“仓廪实而知礼节”(《史记·管晏列传》),物质生活的富足有助于道德水准的提高,然而对于物质财富本身,乡土社会又有“均贫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理念,所以至少应该是在社会整体生活较为富裕并且没有较大贫富差距的情形,道德水平才有随之提高的可能性。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历史的绝大多数时候,这样的情形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因此也就愈加突出道德伦理教化的重要性。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血缘亲情的凝聚力,对生命所出的敬畏心,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形态,以及转世轮回、因果相报的劝谕,都赋予了宗族与宗教在伦理教化过程中的权威力量。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随着以“破四旧”、反对封建迷信等为名义的社会改造运动的展开,“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伦理资源以及以宗族和宗教为主体的制度与组织保障在广大乡村被渐次舍弃或摧毁。一些诸如“阶级情、同志爱”、“斗私批修”、“舍小家为大家”等新的道德文化观念与人民公社等政治经济制度相配合,借助于国家意识形态的规训力量,逐步规范人们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
然而正如带灯所说:“以前不讲法制的时候,老百姓过日子,村子里就有庙,有祠堂,有仁义礼智信,再往后,又有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老百姓是当不了家也做不了主,可倒也社会安宁。现在讲究起法制了,过去的那些东西全不要了,而真正的法制观念和法制体系又没有完全建立,人人都知道了要维护自己利益,该维护的维护,不该维护的也就胡搅蛮缠着。”无论是传统的伦理规范还是基于阶级理论的道德原则在当下的乡村社会都已式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追逐物质财富的欲望被空前地调动。小说中的薛家兄弟和元家兄弟开歌厅、设赌场、办沙厂,已经先富起来,而另一些人如范库荣、杨二猫等尚靠救济和“低保”度日。乡村社会的贫困现象依然存在,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却未能有效形成如历史上曾有的道德伦理机制,种种伦理失谐、妨碍社会稳定现象的发生也就不难理解了。
樱镇所发生的上访以及其它种种影响社会稳定的现象还与日益恶化的自然生态环境有关。与樱镇毗邻的大矿区已出现种种灾害现象,所以当王后生散布大工厂进驻樱镇后,排出的废水会使地里不长庄稼、河里的鱼全死掉的传言时,人们有理由会产生恐慌,也引起书记的高度重视。对于大自然的侵犯最终会使人类吞下自酿的苦酒,正如张炜所指出的:“事实上,哪里林木葱笼,哪里的人类就和蔼可亲,发育正常。绿树抚慰下的人更容易和平度日,享受天年。土地的荒芜总是伴随着人类心灵上的荒芜,土地的苍白同时也显示了人类头脑的苍白。”[8]大自然的报复不仅严重威胁人们的物质生存基础,而且会促使人心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异化与变质。水灾发生后,樱镇人本来在闹,但当听说周边乡镇死伤惨重时,“樱镇人就庆幸:咱还没死人么!就不闹了,还有救济和慰问而以受灾得意了”。天灾愈益突显了人心的冷漠与卑劣。大工厂给樱镇带来了滚滚烟尘,从此樱镇的夜晚不复有静谧、鸟鸣、古人的诗句及其意境,樱镇人甚至将大树上砍下的树枝埋进土里冒充树,只为了能从大工厂多获取一些移树费用,传统的信义原则在利益的诱惑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元氏兄弟的沙厂也是为大工厂而建,他们在河滩任意圈地、刨地、毁坏菜地,刨出来的地再也种不成了,沙厂最终成为元、薛两家发生大规模恶性械斗的导火索。
自然生态的恶化、人文道德的崩溃以及两者之间的恶性循环见证了当下中国乡村发展工业化的尴尬处境。或许真的如带灯一语成谶:“美丽和富饶其实从来都统一不了。”离开了工业化、现代化,人们守住的只能是贫穷的美丽,无法改善自己的生存境遇;但真正步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轨道,环境的污染、自然和人文生态的崩毁最终仍然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舍弃了美丽的富饶对于人类又能有多大的意义呢?“人砍伐树木而猛兽又吃人,谁得到长久的永生了呢?”(带灯的这句感喟不啻是生态伦理的追问,也道出了当下乡村那种无力、无奈乃至无解的现代性困境。在《带灯》中,贾平凹延续了他一贯的生态关怀的美学愿景,以更多的细节更广泛地描画出当前危机重重的生态环境,其意义不仅在于以一种破碎的方式发出构筑人与万物自然间和谐有序的新型生态伦理关系的召唤,更会引发人们对凝聚在这些现象中的处于两难境地的当前乡村社会的现代性发展逻辑进行冷峻思考。
二、乡村政治生态的伦理镜像
“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9]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中国乡村的权力主要是国家的行政权力力量。[10]那么,如何实现权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规范政治行为主体的价值观念,保障政治实践方式的公平正当,这些都是属于政治伦理范畴的问题,是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无法绕开、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小说《带灯》中,一句“樱镇废干部”,道尽了当下乡镇干部的严峻生态处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乡土社会政治伦理失范的表征。和谐融洽的干群关系无疑是政治伦理建设的重要目标,但正如贾平凹在《带灯·后记》中所说的:“他们(指乡镇干部)面对的是农民,怨恨像污水一样泼向他们。”小说中的镇长由衷地感叹乡镇干部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乡镇干部也必定会罪大恶极”。樱镇人惋惜带灯:“多好的一个女人,哪里工作不了,怎么却到镇政府当个干部呢?”村寨里的老婆子也对竹子说:“这么好个姑娘咋是镇政府的?”当带灯让陈大夫编假话吓唬王后生以阻止他上访时,“陈大夫说:这不符合医生道德。竹子说:这是政治你明白不?”小说令人难堪地将“政治”与“道德”,作为国家权力符号的“镇政府”、“镇干部”与伦理意义的“好姑娘”、“好女人”对峙,不经意间流露出政治伦理的反讽意味。
尽管带灯明确地认识到“实际上村民自治化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方式”,但从小说反映的情形来看,这项制度的实行亟待完善和规范。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带灯》中镇干部不仅要作为“联络员”参与村委会的选举过程,而且正如镇书记所言:“选干部就是要把和咱们一心的人提上来,把和咱们不一心的人撸下去,再具体地说吧,要能听招呼,就像换布,换布听招呼!”选举过程本身也充斥送礼、贿选、私扣选票、镇干部和选委会的人代填选票等种种虚假不公现象,这样选出的干部人品如何,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群众的意愿、代表群众的利益,显然都是令人质疑的,就像书记称道的换布,他是镇中街村的村长,正是由他和镇西街村村长元黑眼为了各自的家族利益共同上演了一场“十五年来全县特大恶性暴力事件”。村干部品行不端、以权谋私、侵占集体财产,而村民则对干部产生严重信任危机,以至于发生上访、村民和镇政府干部发生集体冲突等事件。樱镇一年内需要化解稳控的三十八项上访纠纷问题中,至少有十项与村干部有关。
小说所展现的这些场景、事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对于官员的道德品质,合理正当的干群关系的建立,维护民众利益的“善政”以及为保障“善政”施行而准备的一系列规则、制度的思考。至迟到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广大乡村还存在比较完备的地方自治制度,政权机构通常只设到县一级,县以下的广大乡村由民众出于公益需要自发组织的团体实行地方自治,当政令和地方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自治团体的头面人物可以动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和影响力尽力交涉,*参见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156页。既减少了公权力对于乡村日常生活的过多干预,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限制权力滥用的制衡机制,其政治伦理意义自是不言而喻。而在当下乡村社会的权力格局中,国家政权机构一直延伸到县以下的乡镇,乡镇干部直接置身于乡村社会的种种矛盾冲突。虽然实行了村民自治制度,其运行机制显然已不同于传统的地方自治,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和落叶归根的文化传统为“乡土中国”留住了实行地方自治的人才。但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见证了乡土人才的持续流失,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城镇化步伐加速,进城务工经商已成为乡村生活的常态,不仅是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青年学生,就连一般的青壮年也不再依恋乡土,留守乡村的以老人和儿童为主,从而从人力和人才资源方面消蚀了村民自治的主体。这不能不影响到村民自治制度真正依照公正民主的原则实施和运行,选拔出有德行、有能力、有公心的干部队伍,规范有序地对权力监督和制衡。
并且,乡村社会的人才流失和留乡农民整体素质的下降也为政府权力进入本应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务提供了理由和空间,干群(官民)冲突的概率随之上升。难怪《带灯》中的镇书记可以毫不讳言自己并非一定要做到“民主、法治、清廉、公平”,宣称“选干部”就是要把和自己一心的人提上来、和自己异心的人撸下去。而换布、元黑眼这样的村干部的权位既然并非来自于民主选举而是由于诸如书记、镇长等上级领导的属意,他们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听话”而非“对话”,又怎能指望他们能有效地维护村民利益。进而,他们自己的种种胡作非为也极易带累政府形象,正如《带灯》中有村民“骂镇政府是狼,村干部是狼娃”,村民们甚至认为无论“谁想当干部也是想成为村里自动的包工头弄点钱罢了”。有些学者已经对这种现象提出了警告,针对当下中国“开放搞活”的现实语境,他们“开始将乡村干部视为国家政权与村民之间的‘承包者’或经纪人”,[11]184将其与晚清和民国时期曾经存在的“赢利性国家经纪”[11]30-31体制联系起来,认为“在这种经纪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国家不仅丧失利源予经纪人,而且经纪者们利用贿赂、分成等手段以打通与官府的关系……(官员)自身也渐渐地半经纪化,从而忘却国家利益”[11]52。诸如此类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限于政治伦理维度,但毫无疑问进一步凸显了在当下乡村通过包括村民自治制度在内的各项规章制度的建立完善不断推进政治伦理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贾平凹在《带灯》中不仅在情节和细节层面呈现了大量具有政治伦理意义的事件和现象,其思想的穿透力更在于引导人们抽丝剥茧地思考和清理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乡村社会特有的丰富内涵。
三、“带灯”的伦理光芒及其限度
小说中“带灯”和“天亮”的命名无疑具有隐喻意味,其共同的指向是对暗夜的抗拒,对光明的期望。按照《带灯》的叙事逻辑,由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自然等多面的问题错综交织,积聚成极为严峻独特的伦理生态景观,严重干扰了正常稳定的乡村生活秩序,因此以带灯为主任的“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综治办”)的成立可谓顺理成章。作为直接和乡民打交道、进入他们日常生活的政府机构,综治办是代表政府形象的窗口单位,必然要承担建构新型和谐干群关系的政治伦理职能。并且正像带灯所说的,综治办是国家法制建设中的一个缓冲带,“干综治办的活儿是凭责任也是凭良心”,而“良心”是属于道德伦理范畴的概念,可见综治办的“维稳”工作和责任同时也被赋予了道德感召与伦理规训的功能。这尤其体现在带灯形象的塑造上。丈夫伤了带灯的心,但她对后房婆婆却颇孝顺,资助王采采葬父,怒打对公婆“不孝”的马连翘。“不孝”在传统文化语境中是极为严厉的指责,当贫困现象依然袭扰当前的乡村社会,在成熟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有效建立和切实施行前,“孝敬亲长”、“养儿得济”等传统伦理信念仍将是应对生存困境,支撑正常稳定的家庭和社会秩序的可靠凭依。正是借助于这种传统伦理资源及其在当下生活中的延续与生成,带灯的人格魅力得以确立,并获得道德叙事的合法性和权威力量。
作为肩负“维稳”职责的综治办主任,带灯工作中的一项主要内容是处置各类上访事件,除了在不得已时采取“截访”措施,更重要的是在平时的日常工作中要能掌握社情民意,及时化解矛盾冲突,这就要求带灯必须与乡村里的民众建立广泛深入的社会联系。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存在着所谓“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此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只有在私人联系中才会发生意义。[12]在小说中,带灯“村村都有老伙计”,她告诉竹子无论什么时候到任何村寨去都可以找这些“老伙计”了解情况。这种“老伙计”关系类似于民间社会常见的“干姊妹”、“干兄弟”或“结义兄弟”,其实质是人们为了应对现实生活的压力而形成的一种互助互利关系。一旦结成这种拟兄弟姊妹的关系,通常必须遵循“义”的伦理原则与规范,突出的是“义”中之“利”,包括“不相负”[13]34、“施恩报恩”[13]35、重诺守信、济危救困等具体内容。带灯通过发救济,办低保,为群众照相、治病,帮助他们提高经济收入和摆脱受欺凌的无助境地等方式赢得了“老伙计”的尊重和情意。这样的“老伙计”关系既有利于从客观上消弭乡村社会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并且由于带灯的镇干部身份,她的行为和品质也有助于改善政府官员的形象,建立和谐融洽的新型干群关系,使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落到实处,从而显示出凝聚在“老伙计”关系中的政治伦理建设意义。而“老伙计”们由于感念带灯的恩情,进而支持她的“维稳”工作并理解其意义,进一步表明小说主要是从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传统记忆出发,借助于“老伙计”之间的私人联系建构起带灯和樱镇乡村的具体社会关系,为她履行综治办主任的工作与职责提供了来自于传统伦理关系及规范的支撑与动力。
然而,“现代化技术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和伦理观念,而这一套东西绝不可能自然地在原来的专制制度中生长出来。”[14]在以现代性发展为现实逻辑的当下乡村社会,传统的伦理道德由于未能转化为面向现实语境的制度体系而缺乏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规范力量。在“老伙计”之间私人联系的范围内,带灯能够建立与樱镇社会的具体关系,但她不可能与樱镇的所有人都结成“老伙计”,那么由“老伙计”的伦理角色所带来的“义”的约定也就无法成为通用于整个社会的普遍性伦理规范,并进而构成带灯履行工作职责的可靠保障。王后生和王随风都是樱镇的“老上访户”,带灯曾经想和王随风“认个干姊妹”以便“能稳定好她”,却未能如愿。王随风多次到县城上访,带灯所能做的只是一次次无效的“截访”,听任月儿滩村村长与杨二猫等人对王随风拳打脚踢。在带灯、竹子和镇政府的司机阻止王后生怂恿张膏药上访的过程中,“司机先冲了过去按住王后生就打。再打王后生不下炕,头发扯下来了一撮仍是不下来”,而“带灯点着一根纸烟靠着里屋门吃,竟然吐出个烟圈晃晃悠悠在空里飘”。
当传统伦理交往的恩义互报模式不足以支持带灯建立社会联系和开展“维稳”工作,现行权力体制显示了与传统道德礼制相对的现代性话语逻辑,甚至带灯本人也面临被这种权力话语收编的尴尬境地时,或许正如她所说:“咱们无法躲避邪恶,但咱们还是要善,善对那些可怜的农民,善对那些可恶的上访者,善或许得不到回报,但可以找到安慰。”带灯基于传统道德伦理的行为方式以及对此作出的“善”的价值判断最终还是为了自己能够安“心”,是一个自我证明的过程,其力量源泉来自于内心。难怪带灯多次宣称:“我的花只按我的时序开”、“我愿化作雨滴,默默浸泽你身下泥土”、“我这是小鸟临水自娱”。即便是常为人称道的带灯写给元天亮的二十六封手机短信,其实并不构成一种小说文体的创新意义,现当代文学史上出色的书信、日记体小说并不罕见。元天亮在小说中始终没有出场,却挡不住带灯对他一再深情呼唤:“你已经是我的神”、“你是我心的归宿情的家园”,表明他实际上是带灯为自己营造的一面“心像”,为她的种种“善行”提供绵绵不绝的原动力。
那么,既然带灯的道德行为是返观自身,是为了自我内心安宁,这种道德实践过程必然会逻辑地导致单向履行伦理义务而不必过多考虑社会或他人是否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这就又回到了传统的“君子求诸己”(《论语·卫灵公》)的道德建构模式,即所谓“道德的自我主义”或“高尚的自我主义”,它在历史上曾造就“一批具有圣贤人格的道德楷模”[15]277,但它“推不出平等的责任和适度的义务”[15]281,开不出新的社会伦理,“也开不出民主和法治”[15]290。因为建基于自我提高,将自我排除在外,这种向内转的道德原则和行为方式不可能生长出现代意义上的面向所有社会公民的制度化、普遍化的伦理义务体系。所以在阻止元黑眼和拉布等人争夺沙厂利益的械斗时,带灯拥有的道德优势并不能构成对于元黑眼等人的有效约束,而后者的利益诉求却可以援“发展经济”的话语逻辑取得来自于体制的支持。一场看似义、利之间的传统冲突由于现代性强势话语的介入愈益凸显出“义”(带灯)对于“利”(元黑眼等人)的退却与无力,昭示在带灯偶然的不幸遭遇中潜藏的历史必然意义。
四、伦理现实主义的建构与意义
面对当下乡村表现在家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习俗、自然生态等方面种种失序、杂芜的伦理境况,贾平凹“写伦理”的诉求与现实主义原则的合流建构了《带灯》伦理现实主义的创作范式。一方面,现实主义的原则使他在《带灯》中通过大量细节对乡村生活世界的伦理图景进行了冷峻呈现,引导人们洞察蕴藏在其中属于我们这个“开发的年代”特有的由各种难题和困境、机遇与风险交织而成的丰富内容,进一步体认和把握时代的特质和真相;另一方面,“写伦理”的诉求实质上体现了他对传统伦理记忆的守望,并且将其移情于“带灯”形象的塑造。他对带灯是如此偏爱,而基于传统伦理记忆的带灯与当下处于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乡村社会又是如此格格不入。所以带灯的悲剧突出了现实主义的叙事逻辑对于作家主观愿景的“修正”,彰显伦理现实主义的力量,从而接通中国文学的伦理精神传统,为当代文学进入目前的乡村社会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
进而,贾平凹通过带灯复苏传统伦理记忆的努力依然是有意义的。在现代性镜像映照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谈论传统道德伦理的话题多少显得有些陈旧、沉重和不合时宜。而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现实主义的方法和原则由于曾经和政治的结缘而风光不再,在政治激情逐渐淡化以后,就连其中的理想精神和批判视野也一再受到质疑,剩下的也就是所谓无限接近事物本身的“零度写实”,以至于拒绝或丧失任何有关善恶美丑的价值判明和呈现,文学的伦理精神愈显凋零。所以当曾经萦绕乡村生活的传统伦理和人情渐行渐远,人们越来越难以寻觅那份难舍的“乡愁”时,贾平凹在现实主义的框架中执著于“写伦理”,通过《带灯》及时为正在远去的乡村背影留下一份现场的实录,发掘和评估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城镇化进程中当代中国人所遭遇的生存困境、发展难题、心灵阵痛以及由此提炼而成的独特的“中国经验”,考察的不仅是他作为作家的文学能力,更有一份难得的担当、勇气和良知。这何尝不是另一次“带灯”行走——“夜行自带了一盏小灯”,尽管只能发出如萤火虫一般的明灭微光,但对于“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16]
参考文献:
[1]陈理慧.敞向乡村大地的写作——评贾平凹的新作《带灯》[J].小说评论,2013(4):100.
[2]张丽军.“新乡镇中国”的“当下现实主义”审美书写——贾平凹《带灯》论[J].文学评论,2014(1):61.
[3]贾平凹.古炉·后记[M]//古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607.
[4]贾平凹.面对当下社会的文学——在咸阳的报告[M]//天气.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241.
[5]姜彩燕.《古炉》中的疾病叙事与伦理诉求[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99.
[6]贾平凹.带灯·后记[M]//带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359.
[7]贾平凹.变革声浪中的思索——《腊月·正月》后记[J].十月,1984(6):226.
[8]张炜.美妙雨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313.
[9]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82.
[10]王光东,毕会雪.乡土旷野上的行走——贾平凹《带灯》带来的思考[J].当代作家评论,2013(6):76.
[11]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2]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5.
[13]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14]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77.
[15]何怀宏.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
[16]汉娜·阿伦特.作者序[M]//黑暗时代的人们.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3.
[责任编辑王俊虎]
■陕西文学研究
The Developed Rural Soil Refle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Realism:On “DaiDeng(带灯)” Novel
Written by Jia Pingwa
ZHOU Tao
(Literature College,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 245041,Anhui)
Abstract:Facing the unprecedented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novel “Dai deng” written by Jia Pingwa focuses on the unique ethical scenery in rural life world,exploring and estimating the China experience extracted from the modernity dilemma encountered in present rural society.The sculpture of Dai Deng’s character shows Jia Pingw’s effort to recover the traditional ethical memories,and her tragedy highlights the power of realistic narration logic.It composes the creation paradigm of ethical realism that the claim for writing ethics is combined with realistic principle in “Dai Deng” novel,providing new aesthetic experience fo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o get into present rural society.
Key Words:Dai Deng; writing ethics; realism; modernity dilemma
作者简介:周涛(1973—),男,江苏高邮人,黄山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收稿日期:2015-07-19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5)06-006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