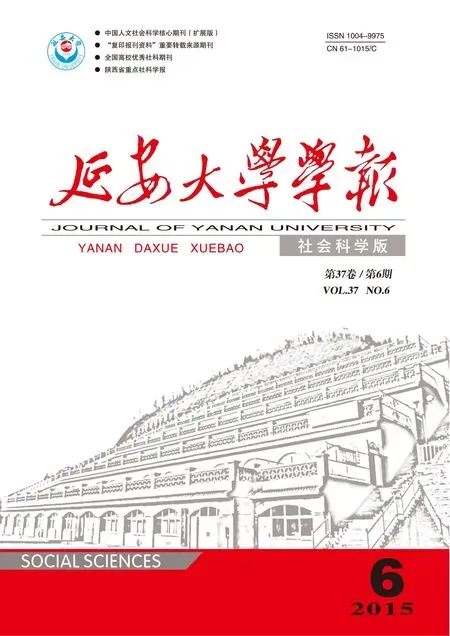当代中国转型发展期的风险识别
何小勇
(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陕西西安710063)
当代中国转型发展期的风险识别
何小勇
(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陕西西安710063)

摘要:我国转型发展期经济领域中的主要风险是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固化的风险,贫富差距日趋扩大和过分悬殊的风险,就业压力快速增大的风险,劳资矛盾和生产事故风险,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带来的经济金融风险。政治领域中的主要风险有主要社会群体弱势化和精英群体结盟化的风险,政治腐败与政府公信力下降的风险,国际政治冲突与军事冲突带来的风险。文化领域中的主要风险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淡化的风险,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入侵的风险,大众消费主义文化泛滥的风险。生态领域中的主要风险有自然灾害型生态风险、资源枯竭型生态风险、公共环境与公共卫生型生态风险。
关键词:现代化;转型发展期;风险识别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正经历着改革开放推动的现代性转型,与此同时,西方现代性也经历着全球化转型,这就使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广度、深度和复杂程度等都史无前例,其中既有难得的历史机遇又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国内外众多学者都认同当代中国已进入风险社会甚至高风险社会的时代这样的说法。当前中国的转型发展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社会形态转换,而是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形态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开放实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具体体制变革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具有高度复杂性的社会历史过程,既有内在的必然性、规律性和连续性,又有偶然性、不确定性和非连续性隐匿其中。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总是涉及风险观念”[1]。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转型发展尤为复杂,各种风险不断形成、累积、叠加又被社会放大,威胁着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和社会进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揭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情势的“新常态”的提出,也是对当代中国转型发展阶段性和特殊性背景下风险问题的清醒认识和积极应对。辩证分析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运行状态,深刻反省由风险外化而来的重大危机事件,识别并确定主要风险,是促进中国社会良性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转型发展期经济领域中的主要风险
经济风险已成为当代中国转型发展期风险衍生的核心。这是急速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方式转轨造成的城乡关系、供求关系、劳资关系、国内外经济关系日趋紧张带来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本身是一种风险型的经济运行方式,在简单的商品经济中就蕴藏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现在的市场经济已然是全球范围内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必然体现出来。虽然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避免了大规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爆发,但当前中国快速转型的高度复杂性使多种因素促动的经济风险也快速累积,应对不当也会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危机。
第一,城乡二元经济格局逐渐固化的风险。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本社会,从19世纪中叶开始城乡经济逐渐分离,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现代化进程中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有其必然性和过渡性,但当代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和状态有其特殊性。改革开放前,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及其一系列相应的制度安排阻断了城乡之间生产要素、产品及人口的流动,铸就了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的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经济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尚未解体,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快速的工业化水平,城市优先发展的政策偏向导致各种资源向城市集结,使中国二元经济格局具有了不断强化的态势和刚性,致使“三农”问题成为当前制约我国现代化全局的重大难题。城乡二元经济格局的固化使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断裂程度加深,相互依赖和相互支撑程度降低,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和风险源。
第二,贫富差距日趋扩大和过分悬殊的风险。收入差距维持在合理的区间有助于激发大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并合理流动。然而贫富悬殊过分则会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严重危机。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平均主义比较严重的同质化国度,改革开放后短短30多年的时间就使它变成了一个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性别之间、单位之间、同一单位内部的不同层级之间收入差距悬殊的高度分化的异质性社会。基尼系数是现在国际上通用的描述收入整体差距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收入分配比较合理的基尼系数区间范围是0.3-0.4,基尼系数在0.4-0.5之间表示收入差距已经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1980年是0.30,1990年上升到0.36,1997年已经达到0.4这个临界点,进入21世纪以后就基本上在0.4以上的水平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数据,2003年至2014年均在0.4以上,2008年最高0.491,以后逐步有所回落,2014年最新数据为0.469。贫富差距的拉大和悬殊使有效需求长期不足,产业升级艰难,产生了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第三,就业压力快速增大的风险。取得合法职业是劳动者谋取收入以解决自身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最基本手段,是劳动者融入社会、增强国家认同、维护自身尊严、实现自身价值的最主要途径。随着现代高新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应用,社会总资本的技术构成不断快速提高,吸纳劳动力的数量相对降低。我国当前转型发展时期的就业矛盾特别突出。我国城乡每年新增劳动力超过2000万人,还要安置由于企业改革造成的大量下岗职工和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和快速城市化造成的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也日渐突出。近年来,国家统计局调查的城镇失业率为5.1%左右。失业增多必然使无业和隐性失业者收入下降,加剧贫富分化,还有可能滋生愤懑情绪,引发反社会行为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第四,劳资矛盾和生产事故风险。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以及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劳资关系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最近几年,劳动时间过长问题、劳动条件恶劣问题、工资报酬过低问题、恶意拖欠工资问题等时有报道,劳资关系紧张、冲突甚至激化的趋势未有根本性转机。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和2010年“深圳富士康十多名员工跳楼事件可以说是这类问题中比较极端的缩影。不良的劳资关系直接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频发,重特大事故呈多发势头。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直接影响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对经济秩序和社会安全形成了重要挑战。
第五,信息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金融风险。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正式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此后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就时刻受到世界经济规则和经济形式的巨大影响。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平等,限制了民族国家调控经济发展的能力和范围,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经济风险。在当前的全球金融体系中,国际金融市场的任何微小波动都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经济风险,更不用说发达国家千方百计地向市场广阔的中国转嫁经济和金融危机了。全球蔓延的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而言,可能造成短期资本大量涌入造成投机泡沫,可能引发以美元资产为主的中国外汇储备大量缩水,可能导致进出口剧烈变化加剧贸易摩擦,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持续稳定发展埋下隐患。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带来,互联网金融近年来经历了“野蛮生长”,信息技术风险和经济金融风险叠加,使非法集资事件爆发。
二、转型发展期政治领域中的主要风险
在政治领域,迟滞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经济利益主体快速多元化的需要,形成了弱势群体与精英群体之间的矛盾、腐败现象滋长等突出问题,再加上国际政治格局的调整和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冲突、军事挑衅和威胁,从而使当代中国转型发展期的主权完整和政治合法性的基础都面临着挑战和风险。
第一,主要社会群体弱势化和精英群体结盟化的风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是当前中国的主要社会群体。改革开放以来,这个群体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都获得了大幅度的改善和提高。但是,在当代中国急剧的转型发展进程中,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现象不仅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的主要表现有:农民和工人这两个传统主体阶层经受着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双重困扰,具有十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劳动者基本权利的维护弱化,受损害情况比较严重;社会保障状况和水平令人担忧,医疗、教育、住房等基本民生问题不堪重负;劳动技能总体水准下降,生存竞争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削弱;程度不同的被边缘化,社会及政治地位逐步下降;主要群体中的很多人开始游离于社会主流生活之外,社会活动空间受到种种限制和歧视;主要群体中许多成员的基本权利没有制度层面的保障,使其基本生活和生存底线没有安全感;社会阶层结构演变中的不平等、封闭性,各阶层之间利益增进的低相关性甚至反向相关性致使主要群体向上流动的平台和机会十分缺乏。[2]当前中国转型发展中主要社会群体的弱势化对政治合法性构成了极其严峻的威胁,严重削弱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会抵消发展的意义,危害整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在当前中国的转型发展中,与主要社会群体的弱势化趋势并行不悖的是社会精英群体的结盟化趋势。现代社会发展的高度专业化、职业化、知识化使精英人士及其群体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催生了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英群体、经济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这些群体属于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上层,身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潮头浪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起了领航的重大作用,但由于极其复杂的原因出现了利益结盟的不良发展趋向并且有进一步发展的势头。政治精英群体由于强烈的利益冲动把公共权力向经济领域渗透,出现了官员热衷于参股、控股实体经济的现象;经济精英群体为了寻求政治庇护对参与政治有异乎寻常的热情,争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愿望极为强烈;知识精英群体为了获取自身利益和现实认可忙于争取政界商界组织设置的各类评奖和项目。“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的实质在于,不同精英群体越过各自的职业边界,通过非正常的方式,以损害公众利益为代价,实现利益互换。”[3]社会精英群体结盟化使他们既掌控政策制定权,又掌控经济收益权,还掌控公共话语权,缺乏必要的相互制衡、相互监督和批评反思,呈现出一定的自我封闭化和排他性倾向,始终处于强势地位,甚至具有了一定的代际传承性。当前中国主要社会群体弱势化和精英群体结盟化使整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开始逐步定型化,整个社会面临“断裂”的危险。针对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断裂的风险,从社会阶层分析范式重返马克思传统的阶级分析范式正在成为学界的一种呼声,有的学者认为在当前中国的形势下,阶级分析范式所蕴含的理论关切和洞察力非常宝贵,它能用来揭示当前中国社会分配和社会整合的独特性。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经济利益的博弈,总体上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但这种矛盾的激化的确隐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第二,政治腐败与政府公信力下降的风险。政治腐败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全球性难题,塞缪尔·亨廷顿的研究表明,“腐败程度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4]。后发式现代化国家由于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快速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政治腐败现象尤为严重。在当前中国的急剧转型发展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市场经济对利益动机的刺激和释放以及长期的“官本位”文化传统等因素使我国的政治腐败形势严峻,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腐败问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各个领域,范围十分广泛,并且出现了固化现象,对社会结构的优化具有消极影响;有组织的群体性腐败特征明显,使反腐败难度加大;腐败问题与鼓励试错的改革背景交织在一起,腐败可能借试错探索改革的名义扩张。[5]近年来,我国政治腐败蔓延的势头有所遏制,但仍属于比较严重国家的行列。根据国际透明组织的“腐败排行榜”(Corruption PerceptionIndex),2008年至2014年中国分别位列第72、79、78、75、80、80、100位,排名总体上处于世界上中等偏下的水平,在主要大国中则非常靠后。政治腐败的直接后果是政府形象受损、权威弱化,激发民众的不满和仇视情绪,致使政治合法性丧失群众基础,遭到质疑和威胁。政治腐败还会向其他领域扩散、蔓延,加剧贫富分化,严重败坏社会风气,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埋下政局动荡的祸根。政治腐败以及政府面对公共事件时的信息不公开、程序不规范、操作不透明等必然大大降低政府的公信力,使政府决策和执行的科学性、目的性和有效性不能获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使一些群众对政府丧失了信心,向黑恶势力求助甚至参与其活动,这是当代中国转型发展期一种后果十分严重的政治风险。2007年陕西“华南虎照事件”、2008年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2009年武汉“经适房六连号事件”和郑州“农民工开胸验肺事件”等一再表明地方政府公信力不足导致的政治风险和危机。
第三,国际政治冲突与军事冲突带来的风险。当代全球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民族国家主权的冲击。快速崛起的中国对当今世界格局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也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国际政治冲突与军事冲突带来的政治风险。虽然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国际形势总体上比较稳定,但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错综复杂,其中大多都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直接相关,迫使中国在国际政治层面做出恰当的回应和行动。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仍然视社会主义如洪水猛兽,它们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和崛起,不承认中国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蓄意制造借口和事端,培植、扶持反政府势力、地方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策划并煽动破坏中国政治稳定和政权统一的事件和活动。2008年西藏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和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暴力事件表明境外敌对势力的存在和活动造成的巨大政治风险已经不容忽视。中国的快速崛起引起了中国与世界各大国之间以及周边国家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和调整,其中极其复杂的矛盾冲突和不确定性因素使中国不仅面临着片面化的国际舆论的攻势和压力,而且面临着现实的军事威胁。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的军事存在,朝鲜半岛核问题的日益激化、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核军备竞赛等等都使中国的和平发展面临的军事安全风险增大。最近十几年来,世界范围内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迅速兴起,给世界各国都造成了难以预测的风险,中国也不例外。
三、转型发展期文化领域中的主要风险
与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风险相比,文化风险具有间接性、隐蔽性、广泛性等特征,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政治认同和信仰,对于既要坚守社会主义理想、弘扬民族精神又要快速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来说,文化风险是一个关乎发展方向和民族存亡的重大现实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存在的中西文化与体用之争以新的形式从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中挣脱出来,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粉墨登场轮番论战,大众流行文化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理想,各种亚文化的流行在主流精英文化之外大行其道。文化领域的快速市场化与意识形态化的惯性相互纠缠,对生活意义的追问与对商品符号的消费并行不悖,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激荡起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冲突。然而,当前中国的文化氛围对此似乎没有足够清醒的意识,总体上陷入了盛世想象的文化愉悦之中。
第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淡化的风险。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一个国家文化价值体系的中枢和核心,起着扩大政治认同、进行政治整合、增强政治合法性、促进政治稳定的巨大作用,构成一个民族精神信仰的基础和载体。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转型发展的加速推进,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日益发达,各种思想流派、学说观点纷纷浮现、相互激荡,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多样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当今世界上流行的各种主义和思潮在中国当前几乎都有其信奉者和宣传者,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和指导作用遭受到巨大的冲击,影响力和整合力被弱化,一些人对主流意识形态冷漠、疏远、反感甚至恶意地解构,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认同危机。
第二,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入侵的风险。早在苏联解体之前,邓小平就富有远见地指出:“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6]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形势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文化领域变成了控制和掠夺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主战场。正如萨义德所说,在全球化时代,“文化成为了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文化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7]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高度发达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信息传播体系和各种文化教育交流合作项目,推广它们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企图培养青年一代对西方文化的崇拜,瓦解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传统,以实现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战略和根本利益。美国中情局还专门制定了针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工作守则,提出要运用物质引诱、宣传、制造新闻和事端等方式使中国青年向往他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藐视、鄙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所受的共产主义教育。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和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推销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对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造成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行径直接威胁着我国的文化主权。
第三,大众消费主义文化泛滥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和宽容度,各种文化价值观念都开始生发出来,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大众消费主义文化的迅速形成和扩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文化后果之一就是人们把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来源从形而上的神圣理想转到形而下的物质消费。可以说大众消费主义文化既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又是其必然产物。资本无限增殖的内在逻辑借助广告等文化传媒构成的文化工业不断创造出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文化把物质欲望的满足及其炫耀和象征功能看作人生价值的实现,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核心。消费主义文化所追求和崇尚的物质欲望是不断地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无限膨胀的欲望,社会文化赋予消费的象征意义遮蔽了人的生命本身的意义,人被物化为消费的机器,为了消费而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的事实表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也要面对大众消费主义文化的挑战。在中国发展的当前阶段,虽然消费主义的行为实践仅限于部分高收入和中等收入人群,但是消费主义文化的价值观念已日益深入到整个社会意识和社会心态的底层,并显现出对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人本文化的巨大消解和破坏作用。大众消费主义文化的泛滥使所有文化体验都卷入到商品化的漩涡之中,把人类文化的丰富性简化为物质占有和消费的单维性,使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均质化,使人的精神结构丧失高层次的境界追求。文化既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过去发展智慧的积淀,更蕴育着它走向未来的文化基因。文化系统承担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重任,当前中国转型发展期大众消费主义文化的泛滥必然给它带来更多的压力和风险。
四、转型发展期生态领域中的主要风险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无机的身体”。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生态危机的出现和不断加剧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当代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水平极低,因而快速发展经济的任务十分紧迫。发达国家在生态环境问题上不断给我国施加限制和压力,又利用科技优势和全球化转移污染密集产业和工业废弃物,这就使生态风险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的威胁日益严峻。
第一,自然灾害型生态风险。我国的自然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是世界上遭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海洋灾害等几乎所有自然灾害都在我国出现过。我国70%以上的城市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由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造成的各种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自然灾害型生态风险虽然主要是由自然生态系统的运动变化直接引发的,但也与现代人的实践活动有关,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态风险的人为因素越发突出。即使单纯的自然灾难,其造成的危害和损失也在现代化条件下被放大。
第二,资源枯竭型生态风险。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占有水平极低,人均耕地面积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目前我国的主要矿产资源开采量增长高于已探明储量增长,资源的消耗量又大于开采量增长,国内资源保障程度下降,对进口资源的依赖日益增强。加之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组织结构不尽合理、工业技术水平比较落后,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浪费严重,单位GDP的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至4倍,从而又加重了资源的紧张程度。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发动机,随着我国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需求迅速增长与资源不足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我国当前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使我国只能主要依靠自身的资源进行现代化建设,资源枯竭型生态风险是我国快速而又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
第三,环境破坏型生态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年平均10%左右,经济的高速增长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和有机污水排放量已占世界第1位,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2014年6月4日发布的《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依据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对主要污染物进行评价,74个实施新监测标准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比例仅为4.1%,其他256个城市执行空气质量旧标准,达标比例为69.5%,2013年全国共发生突发环境事件712起,涉及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的突发环境事件分别占45.2%和30.1%,严重的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心肺之患”。2008年世界“环境绩效指数”(EPI)显示,在全球149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名第105位。根据《2014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评估报告》的数据显示,在全世界178个参加排名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名118位,比较靠后。我国自身的环境容量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使生态问题日益社会化、政治化,成为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
第四,公共环境与公共卫生型生态风险。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现代原子能技术、化工技术、生物技术、电子技术等高科技已经广泛地运用于工农业生产,这些高新技术由于其本身的高度不确定以及不合理的运用,迅速地改变着食物链和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使大面积的剧毒物质和放射性物质的危害、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品和药品致病致命事件等公共安全型生态风险对公众的生命和社会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我国是一个核大国,核电等产业大规模发展而核安全监管力量已远不能适应核能和核技术发展的实际需要,这就使核风险问题日益凸显。自2008年起,我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位列世界第六,转基因作物的生态风险及其食品的安全性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2013年以来,名人崔永元和方舟子关于转基因的旷日持久争辩更使转基因风险问题甚嚣尘上。据统计,全世界的电子垃圾,80%被运到亚洲,其中90%丢弃在中国,而我国正在进入电子产品淘汰高峰期,每年都产生数以亿计的废旧电器。电子垃圾含有多种有毒有害物质,一旦处理不当,就将对公共环境造成严重污染。2014年11月,中国内地公民当年出境旅游首次突破1亿人次。每年出入境人次逾4.5亿人次。频繁的人员往来使世界各地的流行病等公共卫生型风险传入国内的风险也大大增加了。
现代化进程总是伴随着风险的扩张,在现代性日益激进的全球化发展阶段确实形成了诸多可能性低但后果极其严重的风险。风险是潜在的危机,是发生危害导致损失的可能性,如果缺乏有效的控制和治理,就会转化成现实的危害和灾难。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问题是在转型发展的独特过程中形成的,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形成的,只有充分发挥各种社会主体的能动性,高度重视风险、理性对待风险、科学识别风险、有效治理风险,改变宿命论和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才能在更具历史合理性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规避和化解风险,从而实现低风险的发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M].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22.
[2]吴忠民.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研究[J].东岳论丛,2006(2):12.
[3]吴忠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英群体的演进及问题(上)[J].文史哲,2008(3):157.
[4][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54.
[5]吴忠民.中国转型期腐败问题的主要特征分析[J].教学与研究,2014(6):5.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44.
[7][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4.
[责任编辑刘国荣]
■政治学研究
Risk Identification during Contemporary China′s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Period
HE Xiao-yong
(School of Marxism Education & Research,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Xi′an 710063,Shaanxi)
Abstract:The main risks in economic field include the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the increased employment stress,labor conflicts and production accidents,economic and financial risk originated from globalization and networking.The main social groups become vulnerable,the alliance of elite groups,corruption and the decline of government's credibility,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onflict are main reasons of political risk.Cultural risks come from the reduction of Marxist ideology,cultural colonialism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and consumerist culture.The main ecological risks contain natural disasters,resources exhaustion and public-health risks.
Key Words:modernization; the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process; risk identification
作者简介:何小勇(1974—),男,陕西白水人,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问题研究”(14BZX018)
收稿日期:2015-05-01
中图分类号:D6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5)06-003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