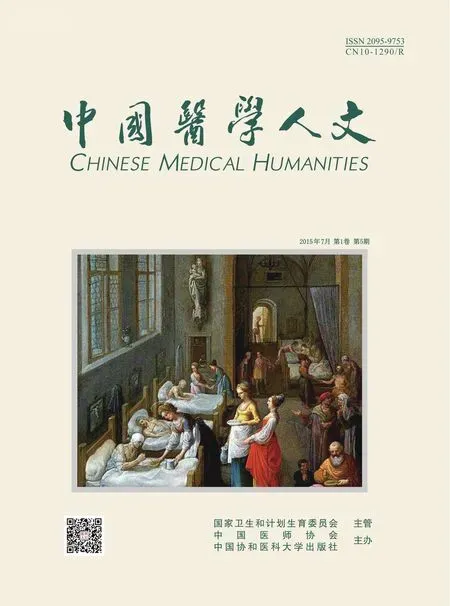大体老师
文/李丛冉
大体老师
文/李丛冉
人体解剖实验室,那里安放着我们可能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大体老师”(医学界对遗体捐赠者的尊称),我们不曾有过哪怕一句话的交流,但我们可能是最了解他们身体的人。他们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教会了我们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知识,他们是我们这些医学“朝圣者”的无语良师。
对他们,首先我是很敬佩的。我时常想象,当他们被病痛折磨,面临死亡的威胁时,看过太多人对死亡的恐惧,对离去的不舍,他们是怀着怎样一种心情做出捐献遗体的决定的?有一个良师得知自己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时对医学学子们如是说:“你们将来会成为医师,我要把我的身体交给你们。你们可以在我身上划错几十刀、几百刀,将来千万不能在病人身上划错一刀!”或许这就是答案吧,一种从心底散发出的大舍大爱。仅此一点,他们教会我们的又岂止是医学知识,更教会我们懂得尊敬与感恩。
人体之复杂与精妙让人惊叹,人类即在探索人体生老病死的道路上一点点寻求着答案。可尽管经过数千年的不懈努力,如果想用言语来书写人体的奥秘,只怕千牍万册都不足以尽载。我们拿着人体解剖教科书一遍又一遍反复翻看记忆,却依旧无法理解“水在桥下走”是何其的形象;无法理解臂丛的分支是何其的精到;无法理解神经是如何完美地从肌肉间隙中穿过而又支配它的运动……于是乎,我们一遍一遍地忘记,脑袋如浆糊一般。而医学偏偏是一门精确到不能差之毫厘的学科,如果我们依靠着这样的认识在病人身上做手术,不敢想象会有多少悲剧发生。我们茫然不知所措之时,是大体老师的无私奉献,为我们揭示深埋在肌理之中,深奥晦涩而令人屏息的解剖知识。
我们不再拘泥于教科书,不再受限于解剖图谱,不再通宵达旦死记硬背。日复一日,在大体老师冰凉的肌肤上,我们试着理清皮肤的层次,细心梳理着发黄的脉管,区分动脉、静脉与神经,感叹于血液循环、淋巴循环的巧妙;我们循着肌肉的纹理寻找它的起止点,探寻行走于其间的血管神经,想象着肌群、关节如何协调使机体做出各种优美的动作;我们一遍遍端详各种器官,模拟它的运作,思考疾病如何使它失去正常的功能;我们对照着书本,终于明了:什么是“水在桥下走”,臂丛拥有怎样复杂的分支,腹股沟管里面到底有什么,坐骨神经从哪里穿出来,为什么会坐骨神经痛,心脏瓣膜到底是怎么回事?许许多多曾经懵懂模糊的知识渐渐清晰起来,曾经让人头晕眼花的文字转变成见得到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器官与结构。我们有时会想,曾经,在我们面前的老师,他的皮肤红润而温暖;他的血管仍然充盈,血液依旧流动,心脏也在规律地搏动;他的大脑很聪明,神经很敏感;他的肌肉结实,运动协调……他曾为人父母、为人子女、为人伴侣,生前他也曾经历风雨、享受幸福、为人类事业奉献青春,就是这么一个丰满的人,身后仍然传递着大舍大爱,不求回报,而他与我们素不相识,念及此,每每动容以致哽咽。
“大体老师”是我们的第一个手术对象,我们不断地犯错:误切神经、找不到应该存在的血管、辨认不出是哪块肌肉、搞不清脊椎骨的区别……而这一切全都是我们成为医生的时候可能会犯的错误,这些误差甚至是致命的。而正是“大体老师”试图用行将腐朽的躯体,教授着我们这一群初入医学殿堂的懵懂医学生,生命是如何运转,疾病是如何产生,人体结构是如何巧妙而又复杂,在医学修行的漫漫长路上给予我们指引。在“大体老师”们的身上,除了修习到行医者必备的基础知识外,我们亦逐渐解读生命的故事,并开始了解生命是如何存在,领悟善与大爱的真谛。
当我们上完最后一次解剖课,整理好大体老师的遗体,离开实验室之前,我们深深鞠躬,各位亲爱的“大体老师”们,感谢你们不畏裸身赤膀、不惧刀剪加肤,献身教职,使医学教育得以延续与传承。我们不曾有过一句对话,我们不曾收到过您的批评或赞扬,然而却比任何一次都清楚自己所犯的错误,也比任何一次能将老师的教诲铭记于心。
这是无法言说的大爱!

某医学院学生送别“大体老师”
/广州市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