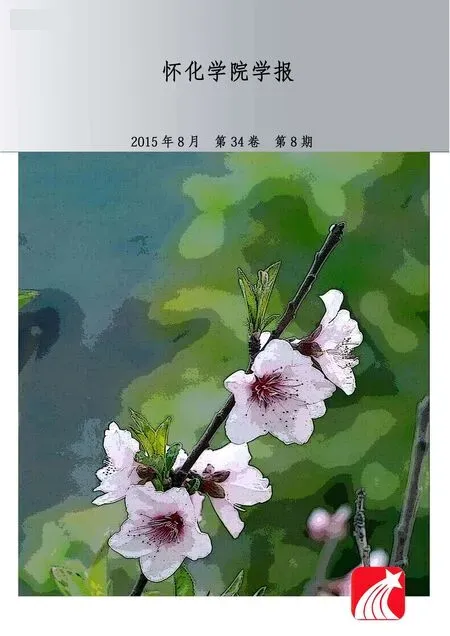从“补拉”联姻和拟制血缘到地域社会整合——坪坦河申遗侗寨的迁徙与聚居
姜又春
(1.怀化学院 非物质文化研究基地,湖南 怀化418008;2.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400715)
坪坦河位于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南20余公里,自南而北流经23个侗寨,其中的中步、高铺、阳烂、坪坦、横岭、芋头六个侗寨因其聚落保存完整、规模宏大、历史悠久而于2013年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六个侗寨与广西、贵州接壤,近200 平方公里,共有居民1 630余户,人口约7 701人。
依据当地人的历史记忆,坪坦河申遗侗寨大致在宋元时期建寨,到明清时期,尤其是清朝中叶以后得到了繁荣。从当地人口头传承所透露的资料看,坪坦河申遗侗寨既是湖南土著侗族的历史延续,也是从江西迁徙而来的移民村寨。本文所关注的是,作为“移民后裔”的坪坦侗寨是如何融合到土著族群之中,村寨与村寨之间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实现整合从而形成地域社会,以及后来的移民是如何融入到早期移民之中的,最终达到整个坪坦河申遗侗寨的社会整合。
所谓社会整合最初是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提出来的,他认为“每一种文化在其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都有着一系列的组织类型,这些类型不仅越来越复杂,而且代表了各种新兴的形式。它们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层次,即家庭、部落、国家。其中每个层次都代表了社会文化的一定水准……而社会文化整合水平可以为分析文化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变异过程提供条件,也可以为进一步开展文化比较研究,探讨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创造条件。”经由村落社会文化整合来透视社会结构,一直是社会人类学中国研究的传统。已有的研究表明,亲属体系理论[1]与市场共同体理论[2]是中国社会结构维持稳定的两种基本的分析模式,而民间信仰是解释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整合的结合点。由于中国社会拥有悠久的宗族文化传统,因此宗族的文化功能对村落社会整合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3]。对于坪坦河申遗侗寨地域社会来说,从以婚姻制度与宗族传统为内涵的亲属体系的角度讨论其地域社会整合,也许是符合实际的切入点。
一、侗寨迁徙的历史记忆
坪坦河自南而北在县城“双江口”注入渠水——古代“五溪”流域之雄溪,并经渠水进入沅江,最后经洞庭入长江。因此,坪坦河流域的侗族当属古代“武陵五溪蛮”的文化区域。今天生活在坪坦河流域的当地人主要是吴、杨、石、龙、粟等大姓,其中夹杂肖、冯、陈、李等十几个小姓。无论大姓还是小姓,他们一方面认为自己是原汁原味的侗族,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是宋元或明清时期从外地迁徙而来的“移民”。问题是,他们这一自相矛盾的身份认同何以成为大小十几个姓的共同话语模式的?侗族是湖南的土著少数民族,而“移民”身份则是外来汉族。坪坦河族群声称既是土著侗族又是外来汉族移民,他们是如何建构和叙述自己的家族史的呢?这就需要我们借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经由族群“移居”的历史分析来考察村落共同体形成。
从可靠的历史记载看,侗族形成主要有两支:一是由古代“濮”人分化出来的“僚”;一是古越人的一个支系。早在宋元时期,官方文献即有大量吴、杨两姓侗族的记载。如宋熙宁八年(1075年),诚州杨光福、杨光亻替率其族姓二十二峒“归附”,“出租赋为汉民”[4]。北宋元祐二年 (1087年),“瞿阳蛮”以杨晟台为首起义,并“结广西融州蛮寨粟仁崔,往来两路为民患”[5]。宋建炎元年(1131年)临冈侗人杨再兴及其子正修、正棋率九十团侗、瑶起义。绍兴三十年(1160年)因杨再思尝有功于郡,追封为威远侯。侗族地区村寨均有飞山庙供奉威远侯,每年六月六日祭祀[6]。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吴天保、杨留总起义。《元史·顺帝本记》记载,闰十月,“靖州徭”吴天保“陷黔阳”。《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四、二五三)载:洪武十八年(1385年)七月,“五开洞蛮”吴面儿,“复聚众为乱”。洪武三十年(1397年)五月,“靖州洞蛮”杨高等“作乱”。
尽管这些史料都是为记载“苗变”、“瑶乱”而存在,但可以肯定的是,杨、吴等姓确为历史上侗族地区的大姓。可见,今坪坦河杨、吴等姓的侗族人应当与历史上湘黔桂边界的土著侗族杨、吴先民有着逻辑上的耦合关系。但此杨、吴二姓并不等同于历史上土著侗族杨、吴的纯粹后裔,因为就当地人关于他们先祖迁徙的历史记忆看,两者之间不能简单归为血缘承合关系。由于没有明确的族谱记载,仅凭当地人口耳相传的历史叙述,他们将祖源地分为两类:一是认为祖先源自于江西省泰和县;一是认为自己源自于贵州古州或广西梧州;而且所有姓氏的先祖都有共同的迁徙“中转地”——靖州的飞山或绥宁的东山。在他们看来,祖辈口耳相传的族源历史的“事实性”和“虚构性”是不存在界限的,他们相信自己的传说就是一个“统一”的、“真实”的存在。
以坪坦村杨、吴、石三姓的历史记忆为例,他们认为祖先“三公”均来自于江西省泰和县。大致在宋朝,“三公”首先落脚在会同县的官保渡,以后吴、杨二姓的迁徙路线为:“会同官保渡→靖州飞山→靖州太阳坪→通道县江口→坪坦寨和横岭寨之间的务坪寨→坪坦寨。而石姓的迁徙路线为:会同官保渡→靖州飞山→绥宁县东山→拢城→务坪寨→坪坦寨。构成今坪坦寨杨姓还有另外一支,名为“杨初四”,其迁徙路线为:拢城(中步寨的杨初四)→务坪寨→坪坦寨。
虽然未能如汉族那样以连续的历史文献——“族谱”来记载本家族的迁徙史,但侗族人通过自己特有的历史叙事来传承自己的文化。这些叙事文献主要有《侗款集》、款词《宗族从古州孟等来》、《尝民册示》、《族源款·宗支薄》、碑刻等。据款词《族源款·宗支薄》记载杨姓的来源:“我们的祖先,从江西府太和县来到衡州,去到湖洋、洋学……我们的祖先,金鸡起步,雁鹅飞天,来到靖州飞山寨。……沿河而上,来到通道犁头咀岭……沿河而上,来到河边、江口、太阳坪……”[7]而当地学者根据民间散碎的文献写成的《庚辰村寨志》认为:杨姓始祖起源于江西白虎塘,后到湖南靖州。杨再思公始于靖州称为杨姓之一世祖也,再思公时为辰阳刺史部统兵马叙州长史,娶五氏生有十子,故杨始节日十盘则从此起源也。杨再思分别娶韩氏、蒙氏为妻,前者生正隆、正光和正修三子;后者生正约、正款两子。第四子正约,即杨初四的二世祖于宋庚辰年(980年)由靖州迁居今通道拢城乡中步村一带[8]。
大量的民间材料似乎都指向于坪坦河申遗侗寨是“移民村”的结论,但这又与其土著侗族的族群身份是不相符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9]坪坦河侗族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历史逻辑建构了族群的社会发展史,为他们作为一个统一的族群身份奠定了合理性基础。首先,他们的基本成分应该是古代生活在五溪流域这一广泛地域范围内杨、吴等姓“峒蛮”、“苗蛮”的后裔,这些侗族先民应当在宋元之际便定居在今坪坦河流域;其次,在宋元之后的所谓“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人口大迁徙中,来自“江西”的“移民”确也大批进入坪坦河。因此,当前定居于坪坦河的侗族人应当是历史上多元族群互动融合而成的文化共同体,其中土著侗族为今坪坦河居民基本的构成部分。作为文化融合的共同体,坪坦河的侗族一方面保留着侗族先民的历史想象,另一方面又传承着先民从江西辗转迁徙来到此处的“移民身份”的想象。“集体记忆”论者认为:“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人们从社会中得到记忆,也在社会中拾回、重组这些记忆。每一种社会群体皆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籍此该群体得以凝聚及延续。”[10]作为“移民”,他们一方面需要从土著身份中吸取生存的文化资本,即认同为原汁原味的“侗族”,另一方面又在集体记忆中保留其“根基资源”,即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来自江西的移民身份。这些有选择性的集体记忆是为了重塑其文化融合体的族群身份,增强族群内部凝聚力的文化手段。
二、拟制血缘与宗姓联合
坪坦河申遗侗寨地域社会整合过程中,他们至少要面临三重关系需要解决。一是宋元时期迁徙而来的杨、吴等大姓如何处理与更早的土著居民的关系;二是以后陆续迁徙而来的各姓如何处理与早期移居而来的杨、吴大姓之间的关系;三是各个村寨之间如何整合。
如何处理第一重关系,是坪坦河申遗侗寨实现区域整合的历史起点。据当地人记忆,他们的先祖来到坪坦河定居之前,这里就已经有苗族人居住了。至于苗族人为什么要搬离坪坦河而迁居他乡,目前尚未有历史依据可以说明。当地人的解释是,随着杨、吴人口的不断扩张,原住民苗族人与侗族人围绕生计、资源发生了冲突和隔阂而不得不迁移出去。杨、吴人口繁衍得益于他们的先祖运用风水等“天才般”的设计而带来的好运。他们通过构建鼓楼、风雨桥等设施,改造耕地和龙脉,使得风水朝着有利于侗族移民的方向发展。相反,原住民“苗人”却人口不济,他们认为坪坦河已经变得不适合其居住了而迁居到贵州、广西和湖南的其他地区。在坪坦河各侗寨都保留有关苗人的零星记忆,而横岭村侗族人至今仍需要处理与“苗族祖先”和谐相处的关系。与其他各侗寨信仰祖母神——“萨”不同的是,横岭村侗族人信仰的是“莫老爷”——据说是该寨最早的苗族定居者首领。原住民苗族头领莫老爷因为不满力量日益壮大的侗族人,他只好带领族人离开了横岭。但此后多年,横岭寨六畜不旺,生产歉收,灾难连连。人们占卜后认为,原因是之前没有协调好与原住民苗族人的关系,得罪了莫老爷。横岭寨决定找回莫老爷,希望得到他的原谅,并邀请他回来共同居住。但这时的莫老爷已经去世,横岭寨只好请回他的灵魂,为他设置了祭台,将其作为寨子的创始神世代崇拜,沿袭至今。
横岭村侗族人关于与原住民互动关系的传说和他们的“莫老爷”崇拜,叙述的是坪坦侗寨在开发扩张过程中的文化冲突和调适。尽管只是残留的历史记忆,也许还带有文化偏见,但我们可以洞察其村寨发展历程中那种断裂式的“历史真实”。“莫老爷”成为历史上苗族人和侗族人共同开发横岭寨所发生的冲突和调适的“社会事实”[11]的象征符号,以“集体记忆”的形式向人们不断讲述过去的“社会建构”状况[12]。
如何处理第二与第三重关系,是坪坦侗寨实现区域整合,保持侗文化完整性、统一性的关键。整个坪坦河流域,占主导地位的大姓是杨、吴、龙、石等姓,而李、陆、肖、冼、陈、黄、梁、银等小姓杂居其间。大姓与小姓之间、大姓内部各支系之间以及各个村寨之间,主要是通过“拟制血缘”和“补拉联姻”的方式实现整合的。
拟制血缘是坪坦侗寨的后期移居者处理与早期移居者之间关系的重要文化手段。后期移居者通过向村落大姓的依附而实现文化融合,避免村落冲突和分裂而达到区域整合。拟制血缘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术语,主要是指“在社会结合的人与人的关系中,在生理上、血缘上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用以与家和亲属相类似的关系来设定他们之间的关系。”[13]坪坦河申遗侗寨各姓的拟制血缘关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改姓”;二是“同姓联合”。后期移居者通过“改姓”入籍“大姓”,以寻求大姓庇护,这是华南地区很多宗族社会极为常见的文化手段。坪坦河各侗寨的杨姓和吴姓并不是纯粹血缘基础上的继嗣性世系族群,而是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吸纳了刁量其他姓氏的后期移居者而成为独立鳌头的大姓。譬如,坪坦寨、横岭寨有“伍”姓改为“吴”、“胡”姓改为“吴”的现象;高铺寨有“李”姓改为“吴”;坪坦寨有“梁”姓改为“杨”等现象。由于没有家谱记载,加之年代久远,很多人对自己先祖的实际姓氏已经记不清楚了,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对现有姓氏的文化认同。籍由“改姓”的方式实现了不同姓氏在村落社会中的整合。
在中国,“姓”是某一个人宗族身份的象征符号,但同姓不一定源于同一个祖先,也就是说,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传统。“五百年前是一家”,反映的是人们对宗族血缘的一种虚拟认同[14]。坪坦河各侗寨几乎都有杨姓和吴姓,虽然他们没有族谱之类的“家族文献”,也没有汉族人所谓的“合谱”之说,但他们相互认同为“本家”,以“同姓联合”的方式实现村寨内外的区域整合。譬如同是“杨”姓,并且共享同一个“江西移民”的传说,但其内部在来源上区别很大。坪坦侗寨的“杨”姓,有来自靖州飞山的,有来自中步寨的,而阳烂寨的“杨”姓源自江西的“杨爷”和“杨父”两个不同的先祖。同是姓杨,但相互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即不拥有同一个开基祖,但他们可以认同为同一个家族,按照同一家族的原则开展各种社会关系[15]。
三、从“补拉”联姻到地域社会的整合
补拉联姻是坪坦河申遗侗寨实现村落社会整合,维持社会结构延续稳定最富有文化特色的手段。在坪坦侗寨社会结构中,“补拉”是基本的划分单元,经由这样的划分,可以确定同一姓氏内部不同支系的边界。这是侗族人为了避免单一社会结构的一种文化安排。正如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关于“社会结构”的经验主义定义所言:“社会关系网络的绵延构成了社会结构,或者说社会结构是一种在制度控制下或在已确定的关系中所做的人事安排。”[14]构成坪坦河流域侗族人社会结构的主要是杨姓、吴姓等大姓。“姓”是一个父系血缘集团的文化符号,在婚姻制度中,一般实行严格的“族外婚”,即同姓不婚的限制性制度。但在坪坦河流域绝大部分村寨都以杨、吴姓氏为主,若严格实行同姓不婚制度,那就意味着坪坦河的男女青年必须要远距离与外姓缔结婚姻,这在交通条件极不方便的古代是不利于婚姻缔结和村落社会结构的稳定与绵延的。为此,侗族人将自己的社会结构分割成一种叫“补拉”的社会组织,将“族外婚”制度限定在“补拉”这一社会结构层面上,解决了“同姓不婚”的父系血缘婚姻制度在坪坦河申遗侗寨中的现实困境。
“补拉”,伺语为“Pu4la∶k10,即“父亲与儿子”之义,是当今侗族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组织,每个“补拉”户数为二三十户至一百户不等。如前所述,侗族的姓氏本来不是严格的纯粹父系血缘集团,其各大姓氏只是拟制血缘或者同姓联合而聚集起来的集团。因此,即使是同姓,其内部各个小集团的区分是很明显的,这就为“补拉”的建立奠定了社会学基础。在同一个姓氏内部,按照一定的原则分成几个不同的“补拉”,每个“补拉”的成员都认同为兄弟姐妹,具有血缘关系或拟制的血缘关系,因此,他们具有父系大家族所具备的各种文化限制,譬如,同一“补拉”严格禁止结婚,成员之间须遵守严格的伦理禁忌,成员之间相互拥有家族性的社会义务等等。可见,所谓“补拉”,是以某一父系血缘为基础,通过拟制血缘的文化手段在同一姓氏内部分化为不同内聚力强烈的文化整合体;这个文化整合体常常体现出通婚、祭祀、生产生活以及互助等文化功能。
“补拉”所具有的文化功能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补拉”是原始氏族组织的残余,是父系血缘组织的次级组织形式,一个大姓可以分成多个“补拉”。因此,“补拉”对内维持父系血缘集团的团结和完整,对于破坏父系血缘组织的行为行使教育、规劝、惩罚、调节的文化功能。对外,具有动员“补拉”成员开展集体行动,协调“补拉”之间关系的文化功能。第二,“补拉”是一个仪式单位,各种红白喜事,如婚姻、丧葬仪式只能在“补拉”之内开展,每个“补拉”成员对这些仪式的完成负有义务和责任。第三,“补拉”是外婚制的基本单位,青年男女只能在别的“补拉”中寻求配偶。因此,即使是同姓男女,只要不在同一个“补拉”中,相互可以婚配。第四,“补拉”是一个祭祀单位,同一个“补拉”成员常常要集体参与祭祀祖先、创世神灵、飞山公等的祭祀活动。同一个“补拉”在某些特定节日中要组织集体庆典。第五,“补拉”是一个自足、开放的组织。它具有“家”、“家族”等血缘组织的基本特征,是所有成员主要社会生活的载体。一个人必须归属于特定的“补拉”他才能得到群体的认可。同时,“补拉”组织又是开放的。其成员可以是同姓也可以是异性;可以是相同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也可以是拟制的血缘关系;一个人可以加入这个“补拉”,也可以加入别的“补拉”。
因为创造性地划分了“补拉”组织,坪坦河申遗侗寨的各姓氏可以在内部也可以在相互之间进行婚配。这种方式,将整个坪坦河流域各个村寨整合为大小不一的婚姻集团,形成了较稳定的婚姻圈。这些姓氏虽没有像汉族那样同一姓氏可以跨越地缘关系而整合为高度统一的区域性宗族组织,但他们可以通过不同“补拉”之间的联姻关系,从而跨越了血缘关系以达到地域社会的整合。
在坪坦河流域,大小姓氏十余姓,不同寨子的各姓又分化成各不相同的“补拉”。这些大小不一的“补拉”组织不仅整合了同村寨中的社会成员,而且使得整个坪坦河流域形成为一个庞大的通婚集团,籍由通婚制度实现了侗寨的区域社会整合。坪坦侗寨“补拉”组织的分布如表1。
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角度看,“补拉”联姻是原始社会血缘婚的文化遗存,且流传至今仍然是坪坦河流域侗族人最基本的婚姻缔结方式,具有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是研究人类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时期的社会组织和婚姻制度的“活化石”。据说,清朝乾隆年间,湘黔桂三省侗族地区九十九公合款,决议“破姓开亲”,即同姓的不同“补拉”之间可以结婚,弥补了传统的“姑舅表婚”的不足。由九十九公合款的传说,足见侗族社会经由“补拉联姻”的方式实现了湘黔桂更大范围的超地缘性的区域整合。
九十九公合款的依据来自于侗族人关于创世神话的记忆。传说上古时期,洪水滔天,淹没了人类,只剩下了创世先祖姜良与姜妹。据侗族款词《创世款》载:“只剩姜良、姜妹创造人。姜良、姜妹两兄妹,男无处配,女无处婚,他俩破常规成亲。”[15]姜良、姜妹成婚是人们对远古时期血缘婚姻的一种集体记忆,这种记忆为九十九公合款,实行“破姓开亲”提供了历史依据。据款词《破姓结亲》记载:“黎妹、央妹去结亲,远嫁四黄、六坝村。路上水獭把鱼吃,鱼肉吃光剩个人。只剩央妹转回程。央妹说,父亲啊父亲!成亲不要论同姓,白天走不到男人寨,夜里回不到娘屋门。王幽破姓娶姑婆,杨家破姓娶姨妹。吴姓娶吴女,杨姓嫁杨姓,陈郎陈家婿,分宗可结亲……好比当初姜妹配姜良。”[15]这一款词既是对“补拉联姻”的一种合理性规定,也是侗族人对其“血缘婚”这一民俗遗存的合理性阐释。

表1 坪坦侗寨部分“补拉”组织一览表
四、结语
总之,坪坦河流域申遗侗寨均为规模宏大的杂姓聚居,他们通过“改姓”和“宗姓联合”的方式确保村落的社会整合,使得不同姓氏的家庭和谐相处并结合为村落共同体。“改姓”和“宗姓联合”是坪坦河侗族独特的社会整合模式。“改姓”意味着对自己父系血缘的“背叛”,“宗姓联合”则意味着对大姓的依附,但正是“改姓”和“宗姓联合”表明侗族人社会整合模式的灵活性和文化适应性。坪坦河流域申遗侗寨大多为历史上的“移民社会”,不同姓氏之间原本拥有异质的文化传统,但这并没有造成各侗寨内部的文化冲突和族群偏见。可以说,坪坦河流域申遗侗寨社会整合模式为当今世界各地因为文化偏见而导致的社会动荡和不平等提供了反思的样本,具有普遍性的价值。
这种普遍性价值的特殊性还体现在实行“补拉联姻”的同姓通婚制度。“补拉联姻”显然既是人类历史上血亲婚的文化遗存现象,也是侗族人适应山区环境的一种文化选择。“补拉”为拟制的父系血缘集团。由于“补拉”为一个大型父系血缘集团的次级组织,因此,“补拉联姻”意味着同一个父系血缘集团内部可以通婚,这显然与人类告别了血亲婚后世界普遍实行的“族外婚”的婚姻制度相矛盾。但在山区环境下,侗族人不便于翻山越岭实现外族联姻,因此,侗族聚落通过“补拉”联姻既创造性破解了实施“族外婚”制度在侗族聚居环境下的困境,又可以成功地排斥近亲结婚的可能。
[1]Freedman,M.,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M].The Athlone Press,1958.
[2]Skinner,G.W.,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M].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64.
[3]姜又春.人类学语境下村落社会文化整合研究[J].求索,2009 (2).
[4]宋史·诚徽州传.
[5]宋史·西南溪峒诸蛮传.
[6]通道侗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编.通道侗族自治县民族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1.
[7]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编.侗款[M].长沙:岳麓书社,1988:297.
[8]庚辰村寨志编纂委员会.庚辰村寨志[M].香港: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2008:49.
[9][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分布[M].吴睿又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5.
[10]王明柯.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2001:50.
[11][法]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4.
[12][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9.
[13]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126.
[14][英]A.R 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M].潘蛟,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11-12.
[15]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编.侗款[M].长沙:岳麓书社,1988:341,437-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