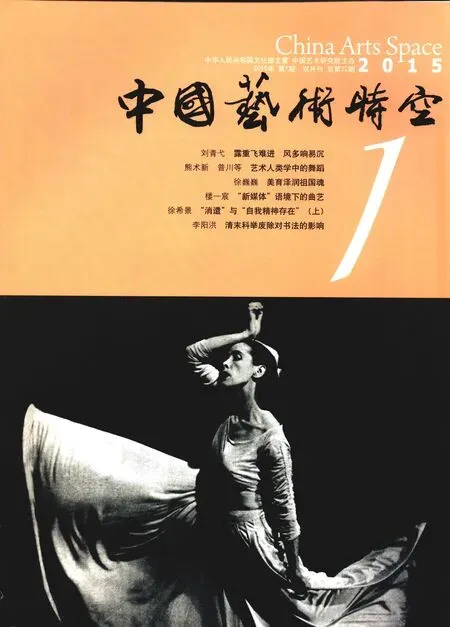“新媒体”语境下的曲艺
楼一宸
“新媒体”语境下的曲艺
楼一宸
曲艺作为以口头语言“说唱”叙述的表演艺术,历史悠久,它可以溯源至春秋战国时期,其确切可证之史也可以从隋唐时期找寻。
在千年的变化发展中,曲艺的传播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勾栏瓦舍”以及“撂地”的表演是曲艺最传统的传播方法。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阶层的壮大,曲艺艺人开始进入茶馆、书场进行表演,表演场地开始固定化。而子弟书等一些文学性较高的曲种的曲本也以案头作品的形式在市面流传。随着人民对精神文化需求的增长,加上1949年后新政权对于曲艺工作的重视,曲艺表演开始进入剧场高台,并且借助新的科技手段在广播、电视上频繁亮相,成为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时代在发展,如今社会步入了“新媒体”时代,人们的生活与网络、移动科技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新媒体”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曲艺作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必然要受其影响,它也必将以“新媒体”为媒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曲艺目前的发展遇到了一定的阻碍,在接受“新媒体”的步伐上也要慢上几拍,但这并不意味着曲艺可以脱离“新媒体”独自存在发展,任何艺术形式故步自封而不与时俱进,必然是要被淘汰的。因而,“新媒体”与曲艺的结合问题便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时代命题。
一、曲艺与媒体结合的历史传统
曲艺与媒体的结合,由来已久。广播和电影电视等作为新的媒介,他们充分发挥了音像的优势,为曲艺的传播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一)广播时期
——民间与官方层面的共赢
20世纪曲艺是人民所钟爱的表演艺术形式,近400个曲种,拥有广阔的市场,观众渴望欣赏到曲艺节目,因此必然会有大量的广播媒体播放曲艺节目,侯宝林等名家就曾灌制过唱片在各电台播放,在全国发行。
战争年代,曲艺工作者创演了许多爱国、抗日等题材的节目在广播上播出,如延安电台大量播送“红色曲艺”节目,撇开政治目的不谈,这也是曲艺与媒体结合的典型形式。
1949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曲艺界第一次被列入到全国文学艺术界。国家扶持曲艺以达到控制舆论导向、宣传意识形态的目的,观众对曲艺节目有极高的热情,由此,国家、曲艺与观众达成了“三赢”,曲艺在延续着辉煌。
电视普及前的广播时期,曲艺与媒体结合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1953年成立的国家级的曲艺表演团体——中国广播说唱团,团内的侯宝林、刘宝瑞、马增芬、孙书筠、白凤鸣、马季等名家都是广播时代的明星。评书《烈火金钢》、鼓书《新儿女英雄传》、相声《买猴儿》、快板书《劫刑车》等作品广受赞誉。

陈烽、谢瑛在表演苏州弹词
(二)电视时期——成也电视,败也电视
1958年,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试验播出,标志着中国电视事业的诞生,限于人民经济水平的落后与政治社会环境的复杂,中国的电视产业并没有突破性的发展。直至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的物质水平开始提升,在长期压抑后人们对精神文化有着迫切的需求,电视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及,电视节目渐渐成为了人们娱乐生活的主要方式,其中曲艺节目特别是相声节目格外地引人注目,《如此照相》、《帽子工厂》、《假大空》等相声作品一方面让全国人民一起乐起来,另一方面也让人民开始反思过去艰难时期的困境。
80年代中央电视台开设“电视书场”栏目,邀请了田连元等名家讲说评书,90年代相声TV兴起,以“声配像”形式演绎经典段子。
作为曲艺繁盛的一个侧面,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拉开了全民看“春晚”的序幕,就在那一届“春晚”中,四个主持人中两个是相声演员,以相声为代表的曲艺节目占据了较大的时长,而后的“春晚”,曲艺则成了“主菜”,《虎口遐想》、《五官争功》等节目红遍了全国。
然而,在电视进入千家万户后,大众文化也悄然兴起,可供人们选择的消遣方式越来越多,更年轻、更符合潮流的娱乐形式挤压了曲艺等传统艺术的生存空间。
进入90年代后,随着曲艺市场的缩小,在全国能够引发轰动的曲艺节目越来越缺乏,曲艺的大腕越来越少,曲艺队伍在萎缩,曲艺创作能力也在减退,这些都是曲艺陷入“瓶颈”的写照。

刘颖、浩楠在表演相声
2005年,郭德纲“横空出世”般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他喊着“让相声回归小剧场”的口号再一次让相声受到了千万人的关注,至今他除了说相声,还干主持、做产业,成了风口浪尖的曲艺艺人。回顾郭德纲的成名,看似他是在广播走红之后利用电视进一步巩固名声,其实大部分的观众都是通过网络形式收看或收听到了他的节目——这已然成了曲艺与“新媒体”结合的先例与前兆。
二、曲艺与“新媒体”特征的契合
对于“新媒体”(New Media)的定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究其原因,是因为“新媒体”的“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十年前的新在今天叫作旧,今天的新在十年后也会成为旧。
但基本可以认同的是,“新媒体”是相对于书信、电话、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的。从技术来说,新媒体是指依托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新技术向受众提供信息服务的新兴的媒体形态。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更新。
“新媒体”基于以上的时代和技术特征,便具有了自己的传播特性,而这些特性,对于曲艺来说,基本都是非常契合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传播效率上看,“新媒体”具有快速及时的特点。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中国曲艺形式,如大鼓、说书等,简单而又富于表现力,极便于迅速反映现实,应当予以重视。”这里明确指出了曲艺灵活性的特点。
曲艺的基本材质只是口头语言,对器乐要求较低,一个人可以表演长篇评书,两个人可以表演相声或者表演弹词,形式灵活多变,内容无所不包,在抗战时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鼓舞士气的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后曲艺也能够快速地编演作品配合国家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宣传工作。
其次,从受众群体上看,“新媒体”是一种大众化的传播方式。大众化并不是指受众的数量,而指的是目标受众的群体层次,如昆曲、歌剧、交响乐等形式的受众便是小众化的艺术。
曲艺自其产生开始就带着大众化的标签,曲艺最初的观众大都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老百姓,必须要以最亲切、最简明直白的语言让观众听懂。曲艺表演的方式只是说唱,用的语言也全部都是大白话,这便是其大众化的特点。
再者,从传播方式上看,“新媒体”具有交互性特点。和戏剧、电影等姊妹艺术相比较,曲艺具有更加强烈的“现场感”。在书馆听书、听相声,演员与观众之间没有太多的距离,观众可以随时插话,演员也准备好了随时搭话,这种观演关系也成为曲艺吸引观众的一大法宝。
另外,从审美需求上看,“新媒体”具有娱乐化倾向。观众喜欢欣赏曲艺节目,是在消费一种审美享受,而这种审美享受归根结底是一种娱乐性质的享受,侯宝林的相声逗乐,骆玉笙的唱腔高亢,这都是直接作用于感官的享受,曲艺的娱乐性也不需赘述。
三、曲艺与“新媒体”结合中存在的“冲突”
以上说了曲艺与“新媒体”的契合,但应当看到,由于“新媒体”与曲艺诞生的社会土壤存在差异,也由于“新媒体”在利用曲艺的现实过程中,由于不够熟悉曲艺,或者未能把握好与曲艺的“优势互补”,而在事实上存在着的不相适宜乃至“冲突”,都需要在今后的发展中予以正视。
(一)听觉性与视觉性的“冲突”
自从社会步入电视时代以来,文字的地位开始下降,图片和视频的地位开始上升。生活节奏的加快让人们需要更为直观明了的接受信息的方式,因此视觉成为人们更为依赖的感官。新媒体出现前后,社会也正步入“读图时代”,因此以“新媒体”为传播介质的艺术形式,必然也要求对视觉进行强化。
对于曲艺来说,它虽然是一门综合性的表演艺术,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听觉的艺术,连阔如说评书,观众可以闭着眼睛听,依旧可以展开丰富的联想,但是只看图像而听不到声音,则很难提取到表演的信息了。
听觉与视觉的主宾关系的处理将成为“新媒体”与曲艺“联姻”的根本难题。
(二)写意性与写实性的“冲突”
这个“冲突”实质上是以西方美学为主导的写实美学与中国传统的写意美学之间的“冲突”。不仅是曲艺面临这个问题,姊妹艺术戏曲也在此问题上犯了难。
曲艺演员在表演时,演员“起脚色”在叙述者与“脚色”之间“跳进跳出”,乃是“装文装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场景的切换与叙述视角的转移全凭演员一张嘴,千军万马的大场面全由演员引领观众的想象而完成,这也是曲艺的魅力所在。
而以视觉性为主的“新媒体”对于传播内容的要求自然是讲求逼真,就算不是要求影像化,至少也是要求具象化,人们心中原本姿态万千的人物形象就被同一化了,这等于削弱了了曲艺的生命力。
(三)完整性与片段性的“冲突”
上文已说,“新媒体”要求快速及时的内容,其实还有一点,就是“短平快”的内容。就目前的“新媒体”市场,即微博、微信、网络等平台来看,碎片化的,片段式的东西还是占据着主导的位置。
曲艺虽然在这方面比起戏剧等艺术的创作周期是短了许多,但是其艺术规律依旧遵循完整性。一个相声需要有“垫话”稳场,“瓢把儿”引入“活儿”,以一个“底”结束作品,一段弹词光开篇就可以唱上几分钟,这都是在新媒体传播中很难容忍的。但如果曲艺作品一味地迎合片段性的要求,那么曲艺的韵味、程式性都将受到损伤,思想性也将大打折扣了。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以上提出的“冲突”,并不是“悖论”,而是在“新媒体”语境下需要克服的问题,扬长避短,知己知彼,才能更好发展曲艺。
四、“新媒体”语境下曲艺发展的误区与不良倾向
由于曲艺与“新媒体”的结合尚在摸索期,所以出现了许多认识的偏差与不良倾向,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新媒体曲艺”就是记录表演
这是一种落后的观点,其错误原因是没看到“新媒体”的特性,如果在网络和移动平台依旧原封不动播放曲艺表演,那便失去了“新媒体”存在的意义,充其量还是传统媒体的播演方式,并不能让“新媒体”曲艺得到发展,因此这也并不在“新媒体曲艺”的探究范畴。
(二)以舞台技术手段冒充“新媒体”曲艺形态
笔者在查阅资料时,发现许多人在探讨“新媒体”舞台艺术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进行概念偷换,认为舞台上运用光影技术便是“新媒体”舞台艺术。其实,这实质上只是科技手段充当了舞台表达方式,是一种辅助表演的呈现的方式,并没有以“新媒体”为平台拓展相关艺术种类的内涵与外延。
(三)将曲艺化节目与曲艺元素节目取代曲艺的本体
在当今众多的电视节目中,能看到许多曲艺演员跨行当主持人,如郭德纲主持天津卫视“今夜有戏”,王自建主持东方卫视“今晚80后脱口秀”,这其中不乏包袱的运用,但充其量只是电视节目中曲艺元素的出现。
有打着电视的旗号吸纳曲艺元素的,还有一类是打着曲艺的旗号吸纳其他元素的,如“刘老根大舞台”,它以二人转为噱头,进行小品化、歌舞化的表演。又如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他以新派曲艺的噱头说电视脱口秀,这些归根结底都不是真正的曲艺。
这种不良倾向存在于剧场与电视节目中,但必然也是“新媒体曲艺”需要防微杜渐的。新媒体的曲艺必然要求形式上的创新,但是需要遵循艺术规律,守住曲艺的本体。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以允许这种形式的存在,但必须清楚认识到的是,它们并不是曲艺。
(四)以段子拼凑与网络抄袭取代曲本创作
因为“新媒体曲艺”要有比较及时的作品,因此它对创作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既能联系到社会当下,又要符合艺术规律。当下的曲艺创作网络抄袭与段子拼凑的痕迹十分明显,在近几年春晚的相声作品中可见一斑。一个作品的内容没有主线串联,一个作品的主题靠最后几句口号体现,这并不能完全怪春晚对于时间的苛刻,更多应该将原因归结到创作者的才能匮乏之上了。
五、“新媒体”语境下曲艺的传承与保护
由上所述,“新媒体”对于曲艺的发展而言,既是一个机遇,同时也存在挑战。至少,在曲艺的传承和保护意义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与便利,不妨加以注重和利用。
(一)留存曲艺全国性的数字性资料
全国轰轰烈烈的“非遗”保护活动证明了一件事:中国并不缺少好东西,而是缺少发现好东西与分享好东西的平台。有许多技艺高超的曲艺艺人与纯正道地的曲艺表演都在不为人知的地方,随着老艺人们“人去艺绝”,好的东西也就愈发稀少,因此如果能够进行系统性的数字化保存,将会是留住经典的好方法。
当年戏曲“音配像”工程还曾受到质疑,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项目愈发显得有意义,曲艺也正需要这样的方式来记录历史。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全国记录在案的曲种有300多种,每个曲种有自己的分支流布,每个分支也会有不同的派别,每个派别又会有不同的代表人物,这其中的工作量不亚于《中国曲艺志》的编撰。这需要国家层面调动全国资源,发挥社会主义社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方可实行。
数字化资料的留存对象,不仅包括活态的表演,还包括当地的曲艺生态、曲种的器乐、代表性作品的曲本等等,以此完成一个立体的曲种描摹。
(二)建构虚拟博物馆
为了让大家能够清晰地了解曲艺的历史与现状,需要搭建一个全民共享的资料性平台,暂且命名为“虚拟博物馆”。
在这个“博物馆”里,既可以进行按地域划分的检索,如天津地区曲艺;也可以进行按构成形态划分,如说书类曲种、鼓曲类曲种、谐趣类曲种等;也可以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检索,如明代曲艺、新中国曲艺等;甚至还能够以多条件进行检索,如清代北京相声、民国上海弹词等。
这里需要大量的数字型资料方才得以支撑,也可以看作是曲艺资料数字化项目的一个延伸。
(三)搭建网络互动平台
且观当下网络社交平台,如微博、微信等,少有曲艺与观众的互动,更别说曲艺学者与观众、曲艺学者与曲艺创作的互动,因此在这个平台上很有必要加强建设。
曲艺是一个全国性的艺术门类,各地区之间有同有异,特别需要互通有无,各地方现实存在一定的物理空间,但在网络上则基本都是“同时同地”的,如果这一个平台能够通晓各地区曲艺的发展现状、曲艺活动、曲艺演出动态等,很大程度上能够提升曲艺的影响力。当下曲艺话语权的主导者们大多对“新媒体”不大感冒,而年轻一代人心理上可能存在着不自信,在“新媒体”中曲艺的分量并不重,这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如果依靠“新媒体”能够联系起曲艺界与普通观众,打通曲艺创作、曲艺研究和曲艺表演的关联,对曲艺的进一步发展来说必然是一个利好消息。

施敏在表演四川清音
在“新媒体”的影响下,电影率先做出反应,产生了微电影,动画、平面设计等都开始发展“新媒体”的形态,近些年来戏曲也在渐渐地随大流,因此“新媒体”语境下的地方曲艺的发展,也需要重新起步。
近年来,曲艺动漫、曲艺MV相继出现,这些都是曲艺与“新媒体”结合的先声,但是它们到底效果怎样,今后的发展中在多大程度保存了曲艺的基因,都还是有待于时间检验的。
曲艺由许多各具特色的地方性曲种构成,每个地方的曲种在面临“新媒体”挑战的表现如何,都会深深影响曲艺这一整体艺术门类的发展。历经千百年的古老艺术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发展变化,这是所有热爱它的人所关注和期待的。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