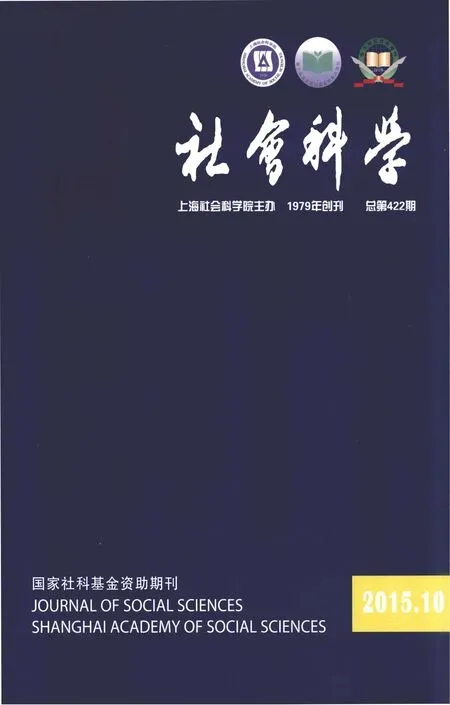“消遣经济”的迷失:兼论当下中国生产、消费与休闲关系的失衡*
张敦福
对费孝通教授学术贡献的分析、反思、评论和重访主要来自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界的研究者,他们从多变的视角探讨了费孝通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领域的众多议题。但已有研究中关于消费、消遣、休闲、工作与娱乐的关系的探讨是缺失的、不在场的。为弥补缺憾,笔者曾仔细考察主要体现在费孝通早期著作中的“消遣经济”的概念,梳理出以下发现:“消遣经济”指的是传统农村社会的经济态度,其核心是少劳作、少消费、有休闲;空闲时间被消耗于茶坊、酒肆,一起抽烟、说长说短,甚至“鬼混”,其中不少是参与公共生活;那些雇工自营或把田租给别人经营的脱离劳动的土地所有者,在这方面有着共同的、明显的倾向;这种生活态度与中国当初普遍存在的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相关,构成了乡土中国独特的消费文化①张敦福:《乡土中国的消费文化》,《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对这一社会事实及其特征的梳理尽管具有开拓新领域的意义,但尚未从理论上阐发这种消费文化及其在世界社会大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这里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消遣经济”对社会生活的意义何在?放在世界经济形态变化、尤其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如何看待中国人生产、消费、休闲的结构和关系?在当下中国,怎样平衡工作、消费与休闲三者之间的关系,使我们的社会生活既有灵性、又有质量?
生计经济与社会整合形式:消遣经济的意义
消遣经济的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消遣经济涉及到传统中国农村的经济形态、经济特征和社会性质等问题。对此,有研究者曾作出一个十分中肯的概括:中国农村问题,尽管错综复杂,“底子里却十分简单,一言以蔽之,是现有资源不足以维持那么多人口”①R.H.Tawney,Land and Labor in China,Octagon Books,1979.p.103.。费孝通笔下的禄村情况大致如此。与禄村类似的村落在中国比比皆是。由于宅地和农田的不可搬运性,农民采取了村落集居的形式。这些村庄规模不等,从最小的“三家村”到数百农户集聚的大寨子,散布于农田和山野之间。土地是村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村民绝大部分的生活资料,衣、食、住、行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取诸土地。人力和畜力,到1960年代之前,一直是农业生产的最主要动力来源,被称为“传统的农业投入”②Dwight Perkins and Shahid Yusuf,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4;Shenggen Fan,Regiona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s Agriculture,Boulder:Westview,1990.。在禄村所属的中国西南,山冈上整修的层层梯田正是人类筋肉所创造的纪念碑;在东南水乡泽国,拥挤的中国人年复一年地把秧苗插到世界上最大的水田中去,用双手来养活他们自己③[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3,5、60页。。因为人口膨胀造成劳动力便宜得一钱不值,乃至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肩挑背驮、摇橹划桨、锄头铁锨,要比使用任何机械都划算,有时畜力都处于不利地位④[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3,5、60页。。这种精耕细作,不断向土里寻求生存能量来源的做法被称之为农业的“过密化”⑤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
靠人力、畜力的投入在有限的土地里讨生活,这样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是可谓生计(subsistence)经济。这类经济形态在农业社会之前就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社会生活形态。萨林斯曾富有说服力地表明,采集狩猎时代的人们尽管不如现代人生产率高,但他们欲望不多,实际上过着丰裕而悠闲的生活。比如,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工作的比我们要少,干活断断续续,没那么辛苦,每人每天获取和准备食物的时间就四五个小时,空闲时间很多,睡眠时间很长⑥Marshall Sahlins,“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in M.Sahlins,Stone Age Economics,Aldine Transaction,1972.pp.108-109.。妇女经常休息,并非整天寻找和准备吃食,男人打猎找吃食也有一搭没一搭地干,某天收获颇丰,则好几天闲着⑦Margaret McArthur,“Food Consumption and Dietary Levels of Groups of Aborigines Living on Naturally Occurring Foods”,in C.P.Mountford,ed.,Records of the Australian-American Scientific-Expedition to Arnhem Land,Vol.2:Anthropology and Nutrition,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60.p.92.。
这些发现具有破旧立新的意义,采集狩猎时代(有时被称之为“原始社会”)、农业社会的工作曾被认为辛苦难耐,现在看来很可能是个错误的判断。对农民经济生活,尤其是消费实践和日常生活形态的观察和分析,应从这一研究理路中得到启发。让我们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不同学科是如何解释这种现象的。
经济学界的解释注重边际生产效率和农民的理性判断。由于过密化的极限普遍为人所知,小农宁愿空闲而不愿劳作,乃是对边际生产效率低下的理性认识。因而,传统农业不是农民偏好游手好闲的结果,相反,游手好闲似乎是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结果。农民把微薄的收入作为储蓄投资于传统生产要素时,这种储蓄的收益率是非常低的,并不需要求助于文化差别来解释特定的工作与节约行为,因为经济因素就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解释。促使这些人去做更多工作的刺激是微弱的,因为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非常低;促使这些人进行更多储蓄的刺激同样也是微弱的,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也非常低⑧[美]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1—23页。。不应当忽视这样一种观点:即农民是非常节省的,他们允许自己所进行的消费总是十分节省,特别是当他们考虑到子女的福利时更是如此。
恰亚诺夫及其合作者的观察和解释,着重对农民经济组织和行为的细致考察和统计分析。在俄罗斯,农民一年全部劳动日中,劳动只有很小的比例——综计之仅有25—40%——被用于农业。即便将手工业和商业劳动加上,其比例也不超过50%,远不是充分利用的①[俄]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105页。。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无疑在于农业劳动组织的特殊性质,如季节性和气候影响等。另外,这一理论路径深入到农民家庭消费上,认为自我开发的程度取决于劳动者承受的来自于家庭消费需求的压力有多大。家庭经济活动的量由消费者的数量决定,而根本不由劳动者的数量决定。换句话说,如果家庭致富很难,维持全家温饱就能让农民满足,从而并不在意投入更多更苦的劳动。
恰亚诺夫进一步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农业生产形态:商品生产型和实物生产型。禄村为代表的多数中国村落,大多属于后者。不同于商品生产型农场,实物型农场经营者的行为所针对的是一连串互不相干的消费需求,并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一种追求产品的质的特征。为了家庭消费必须获得产品甲乙丙丁,恰恰就是这几种,而别的一概不要。产品的量则只按单个消费需求来度量:“够了”或者“不够”。由于消费需求本身具有弹性,这种度量不可能是很精确的②[俄]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105页。。
同样触及到需求和生计经济,博兰尼的理论观点超越了经济学的解释和路径,从社会结合形式找到了阐释农民休闲与工作乃同等重要的根基。在博兰尼看来,以稀缺(scarcity)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无法涵盖以生计为目标的社会总体要求。为了满足社会的总体需要,必须运用多种准则来共同形成所谓的整合形式(forms of integration),而这些整合形式并不具备发展阶段的涵义③[匈]卡尔·博兰尼:《经济:制度化的过程》,载许宝强、渠敬东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47页。。这种阐释不把采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看作是单线发展、依次向前进步的阶梯,而是强调生计经济的社会总体要求。其中,社会整合形式具有超越经济需求的重要意义。换句话说,任何一种社会关系从来都不完全是功利性和工具性的。如果人们要参与到这种社会关系中,他们就必须为之付出努力,以劳务、物质或金钱投入生命事件的重要礼仪中,这些投资具有维系人们所归属的社区凝聚力的作用。因而,中国农村时常发生的像别家有事时去帮这样那样的忙,这样的劳务支出是必要的,帮忙者也不必直接考量或很少考虑价格和利润等经济因素。
禄村的乡民尽力减少劳作并贪图闲暇,既有边际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更有上述仪式投资、排场张罗、彼此借贷中所涵盖的人情世故。很有可能的是,舒尔茨的理论只看到了消遣经济作为经济行为的一面,但难以解释乡民消遣中的面子问题和熟人社会考量。乡民行为中的消遣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并已经嵌入到当地日常生活形态中。费先生论及的禄村的一些消遣活动(如“吹洞经”、“讲圣谕”、“唱花灯”)中,透露了村落公共仪式的信息,主持这些公共仪式活动的正是那些有田而且有闲的地方精英。以洞经会为主的活动,利用公共仪式构建禄村的地方社会空间,凝聚禄村村民的认同感,同时建立了以地方精英为主的等级体系④张宏明:《土地象征——禄村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概而言之,中国农民的彼此走动、帮忙、礼物馈赠、闲聊、吹牛、在茶馆酒肆消磨时光等等,都是这类整合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构这类整合形式的其他社会空间则有“麦场”、“井边”、“村头”、村里某个建筑物(如庙宇、杂货店等)等村民悠闲而聚、谈天说地的所在。
社会交往具有休闲的意义,反之亦然。大部分被看作是休闲的活动及场景都贯穿着社会交往的层面和因素。要发展某种亲密关系或初级关系,除了具有共同的任务外,还需要共同的休闲机会。许多休闲活动的设计宗旨是“重在参与”,活动胜负的评判根本不重要。齐美尔把那种以快乐相处为主要目的的交往称作“交谊(sociability)”⑤Simmel,Georg,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Trans.and ed.By Kurt H.Wolf,New York:The Free Press,1950.。游玩也罢,庆典活动也罢,闲聊也罢,所有参与者都被看作是平等的、无利害纠葛的,结果并不重要,人们都关注友谊、尤其是交谊中的乐趣,交往过程是最重要的,在这类休闲活动中分享和交流,即便是在一起发呆、闲聊,都注重社会交往过程的基本意义、注重社会整合形式的形成。
长久的定居生活导致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村落成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那是一个彼此熟悉、较少拘束、温情脉脉的小地方社会。村落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惠、总体性社会需求的存在、社会整合形式的构建、交往与闲暇的融通,均与乡民社会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离开那个固定的、封闭的、熟识的社区,离开了农耕生存背景,这些公共仪式、交谊活动、互惠方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人际关系的处理可能比家产的丰裕与否更为重要,或至少占据同等重要的位置。村落成员的社会关系往往反映在大事件上,婚丧嫁娶等礼仪尤其疏忽不得。村民在劳作之余,花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物质在人际往来上,实际上在编织和维系人际关系网络,在创造和再生产着共同体的历史。
三种经济形态与中国社会变迁的难题:富裕之后的社会后果
费孝通发现,消遣经济与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截然相反。在消遣经济态度下,货币收入并不被看作是具有很高价值的东西。这一观念与西方经济学“利益最大化”假设虽然不是截然相反,也是大异其趣的。“消遣经济中,工资提得愈高,劳作的冲动愈低,生产的效果以个人说,也跟着愈少,这是和我们通常所熟悉的经济学原理刚刚相反。”①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二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81页。。通过中西对比,费先生确证了禄村存在一种不同于西方新教伦理的传统经济态度。在这种经济态度的支配下,那批拥有田地的人好逸恶劳,他们减少劳动,减少消费,产生闲暇,终日消磨时光②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116页。。其基本精神是宁愿少得,不愿劳动。费孝通认为,在西洋的都市中,还存在另外一种把消费和娱乐看作生活中心的经济形态:一个人整天的忙,忙于工作、忙于享受,所谓休息日也不得闲,把娱乐当作正经事做,一样累人。这是19世纪以来西洋论经济者的“最少痛苦来换取最大快感”,是作为个人经济打算的基本原则——快乐主义的假定。每个人都这样打算,相互间合作达到这目的而发生经济行为,行为所循之方式固定化而成经济制度,造成一个社会秩序③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116页。。两者适得其反:我们的村民知道如何不以痛苦为代价来获取快感,这就是所谓消遣。西方人以购买、使用和消耗物资(消费)来获取快感的过程。不同于消费,消遣不必消耗物资,所消耗不过是一些空闲的时间。
如此,三种经济形态得以区分开来:资本主义兴起时以生产为核心的形态;资本主义成熟期以消费为核心的形态;中国传统农村流行的“消遣经济”。不同时期休闲的多寡呈现如下趋势:随着文化的进化,工作时间越来越多,休闲的时间越来越少。必须说明的是,资本主义成熟期,人们把消费和休闲当作工作、事业做,虽然“生产”时间减少,“工作”时间却增加了。三种经济形态大致适用于不同国度的不同历史时期,有各自或具明显代表性的个案,它们在劳动生产、休闲和消费的结构安排上、在对待生活的基本伦理上,各有凸显的特征,在物质富裕程度上也有分别,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构成了消费主义演变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所谓主流价值系统④Peter N.,Stearns,Consumerism in World History: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Desire,Routeledge,2001.pp.3-6,p.4.。我们以“+”表示该项目的多寡,可以建构出以下表格中三种经济形态的理想类型。(参见下页表1)
重新厘清生产与消费、工作与休闲分配关系的不同结构类型,强调休闲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有助于从理论上进一步探索中国与资本主义产生问题的新解释。消遣经济是通过减少消费来减少劳动,向内求,主张压抑自身欲望——传统社会匮乏经济特有的态度。传统中国居主导地位的儒教,其价值系统被认为是重视世俗生活而不是宗教目标的,它产生的社会氛围是拒斥消费主义的⑤Peter N.,Stearns,Consumerism in World History: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Desire,Routeledge,2001.pp.3-6,p.4。按照新教伦理,人在俗世拼命劳动和生产,挣钱是为上帝积累财富,即所谓拼命挣钱,但反对放纵物欲。“清教禁欲主义竭尽全力所反对的只有一样东西——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所提供的一切。”⑥[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0页。这种以生产为核心的生活伦理被认为与资本主义的产生有着亲和性关系:“当浪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①[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1页。把消费和娱乐看作生活中心的经济形态,也很早出现:一个存在于前资本主义和早期资本主义文化之中的观念:体面只适合于花钱而不适合于挣钱②[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15、150页。。但这一观念只限于贵族和上层社会,并未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没有深入到普罗大众,尽管它同样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产出了资本主义。”③[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15、150页。换句话说,奢侈促进了将要形成的经济形式(工业、制造业、财富增殖等),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④[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15、150页。。

表1 三种经济形态的理想类型与中国社会的生产、消费与休闲
新教伦理过于注重生产、劳动和财富增殖本身,快乐主义浪漫伦理过于注重消费和休闲。就生产和消费的平衡而言,消遣经济似是一种适宜的选择:虽压抑了消费,但增加了休闲,因而虽然物质产品不富裕,但因为有了足够的闲暇和公共娱乐、人际交谊,可谓“原始的富裕社会”——这里的富裕更多的指生活的闲适,充裕而无拘无束的休闲。这种“休闲”的充裕往往被追求进步、天天向上的现代人看作是“懒惰”或“好逸恶劳”。这实际上完全误解或没看到休闲的价值和意义。布希亚的《懒惰颂》中的几句话颇发人深省:“这种懒惰的本质是农民式的。它的基础建立在一个功劳报偿和‘自然’平衡的感情上。从来不要做太多。这是一项慎重和尊重的原则,对象是工作和土地的对等:农人有所付出,但是由土地和神祇来给予所余之物:(那是)最本质必要的……我憎恶我身边市民们的扰攘活动,他们的主动积极、社会责任、野心、竞争。这些都是外原的、城市的、有竞争力有表现的、自命不凡的价值。这些是工业文明的品质。懒惰呢,则是一个自然的能量。”⑤[法]布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2001年版,译序第5—6页。孟德拉斯则如此看待农民的时间观:农业劳动者是在一定的时间界限中生活、思考和作出决定的。这种时间界限不仅仅是自然周期和大气条件强加给农业劳动者的,而且也是、还可能主要是传统文化的遗产⑥[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6页。。
韦伯在讨论“理性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未能在中国首先发生时指出,儒教的影响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其他原因可称之为中国的“社会学基础”:虽然货币体制发展了,但中国社会仍然踯躅于传统主义⑦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154页。;社会生活组织,自上而下都打上了父权制的烙印;长期以来以血缘结合和地缘结合为主体的社会生活,深深地影响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所有这一切都与从事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现代理性劳动组织的要求、以业缘为主实行人的组合必须奉行的普遍主义的社会性道德相反,客观上必然会阻碍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韦伯的解释固然富有说服力,但在消费和闲暇方面似乎还存在“缺失的环节”(lost link),即在这个领域找到中国未产生资本主义的新解释。如果我们把韦伯的“禁欲”说和桑巴特的“奢侈”说延伸到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中,可以看出:中国民众存在明显的限制消费和个人物质欲望的现象;就绝大多数资源稀缺、生活贫困的普罗大众而言,这样的禁欲只是维系基本的生活需要,根本产生不了可以投资扩大再生产的“剩余”,他们的闲暇也是以很低的耗费寻求生活中的乐趣。权贵阶层、乡村的大地主等有产者可以不劳作、有休闲,收取的地租和其他利润多用于享受,结果是巩固封建制度而非蕴育资本主义精神。由于士农工商阶层分化的封闭性特征明显,上层社会的“奢侈”也未能像欧洲社会曾经出现的那样通过“时尚”向下层社会普及,从而扩大需求,带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理性劳动组织的形成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形成被看作是进步的、理性化被看作是高级的、以效率和物质财富扩张为目标的,事功主义被认为是优越的。而禄村人消遣经济的生活态度并不把财富积累看作人生第一要务或目标,也不认为资本主义是理想的、进步的、好的。他们所祈求的,是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后,有充分的闲暇可以度过,有相熟的人可以一起玩。韦伯看到了理性化的限制,坎贝尔挖掘出理性主义的反动——浪漫伦理的价值和意义,而中国禄村等地的农民在漫长的农耕生活中已经累积了平衡生产与消费、工作与休闲、物欲与人际往来之间关系的文化传统。
基于有限的实证资料,本文只能粗线条地勾勒中国社会变迁中劳作、消费和休闲变化与互动的图景。从现有经验资料和初步观察看,人们对待生产与消费、工作与休闲的态度和行为呈现出一些值得忧虑的趋势。随着市场化经济改革和各个领域的对外开放,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生产和工作成为经济生活的核心,农民工、城市工人、专业人士、管理阶层、大小企业家,很少有清闲自在地享受生活的;另一方面,来自欧美的消费主义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从城市到乡村急剧蔓延和扩散,力量强劲,势不可挡。无论如何,工作和消费,或工作伦理和消费主义成为1990年以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图景中两个最为凸显的重要部分。
从公社制度转变为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之后,由于土地被重新分配到各个家庭中,生计经济的特征在解除政治控制后有所恢复。在河南,乡村的生活比过去好了,但生计经济的特征未变,或许这是长期农耕社会根深蒂固的特征。“生活好多了,表现在哪里?”“解放前,全村只有一户大地主才全年吃白馍。如今全年能吃上白馍了。”“有白馍吃,我们都心满意足了,还是改革开放好!”①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农村1985年前后,生产效益被挖掘殆尽,后来乡村青年男女的外流和乡村的凋敝就不足为奇了。其中起重大作用的,是承包经营后,农民对边际生产效率的理性判断。在四川,乡间的俗语是“挨一些饿,得一些坐”。在山东农村,那些极少数不知歇息、卖命干活的人,容易被别的村民讥讽为“怨种”。很重要的一点是,乡村地区对闲暇的重视依然延续着。
但与此伴生的公共生活的失落则值得忧虑。部分经过改革而富裕起来的农村,在社会生活领域却出现了令人忧虑的现象。经过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的重塑,基于土地占有不平等的地方等级体系已经不复存在,地方性的公共仪式虽然出现了所谓的恢复和重建,但却与传统社会的逻辑完全不同。在禄村,花灯在人民公社时期还由新成立的花灯剧团维系,但政治功能越来越明显,分田到户尤其是1990年代后,花灯表演越来越萧条,并且越来越失去公共仪式的意义,而成为一种纯粹的娱乐形式,洞经则被看成是几个人的个人爱好②申端锋:《新农村建设的文化与伦理维度》,《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8期。。花灯丧失了地方影响力,洞经则在社区和国家的夹缝中生存。村民共同体认同的意义基础丧失了,村民在村庄内部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一袋马铃薯”,村民已经原子化了,禄村成了“缺乏认同的社区”③张宏明:《土地象征——禄村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页。。
从农村留守人员的闲暇时间安排来看,一些研究者发现湖北荆门、辽宁大古村、山西董西村农民的农闲时间相当多,其中大多数农闲时间都用来打麻将和串门,其中也有买六合彩的,而没有被组织起来进行公共或个人生产。一些农村在超出家庭层面不再有一个主导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这类村庄被称为“原子化村庄”。湖北荆门、湖南衡阳、安徽徽州宅坦村、辽宁大古村都是原子化村庄①贺雪峰:《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宗族势力曾经在南方强盛,目前快速解体;北方农村容易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比如从共产主义理想到拜金主义的飞跃。在河南巩义某镇,急于暴富的人们往往走上“黄、伪”一路;既富之后,吃喝嫖赌之风大盛,使得管仲所谓“仓廪实而知礼仪”为虚,“饱暖思淫欲”为实②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193页。。贫困会产生贫困病,富裕也会产生富裕病,后者比前者更难治。变化中的社会风尚似乎自动培育着各种赚钱手段与目的,很少受到什么伦理精神的制约。对于早已超出生存与安全需要的少数富裕户来说,赚钱的基本动机便是享受与攀比。他们通过消费来攀比,从而将消费标准逐渐提高到社会一般消费能力之上,并无形中规定着消费的内容和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前中国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既不在官方手中,也不在知识分子手中,而在先富者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即通过享受与攀比形成的消费标准与消费方式中。数据表明,当中小城市中有较多人向往休闲放松的生活方式时,而农民群体对于物质富裕的追求则更加突出③零点调查:《中国消费文化调查报告》,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页。。
乡村社会内的这个标准来源于城市。在消费主义的源头——大城市,一方面是闲暇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一方面是生活世界的祛魅化。与中产阶级家庭大规模参与国内外的跟团游和自助游相比,农民工和城市新贫困群体却不得不为了基本的生活资料和住房保障而把生命中主要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现代化的生产线上。同时,大城市充满了过劳死、浮躁,急匆匆的脚步、繁忙的交通和拥挤的人群,其中不乏被“成功”之梦驱使的城市新生白领。那里,日常消费生活领域充斥着“虚无之物”④张敦福:《迈向“虚无之物”的日常生活消费实践》,《社会》2006年第2期。;经济生活的“沃尔玛化”剥夺了“消费个性”,甚至休闲也被作为一种产业过度商业化,民众的旅游也遭致麦当劳化⑤张敦福:《消费的社会形式及其社会后果——旅游的案例》,载《社会理论》第四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好生活”的标准竟然是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在物欲横流的城市里,人们更多地体味到“失乐园”。
结语与讨论:何处娱人性灵?
已故美国农民学家丹尼尔·托尼曾说,即使在当代发达工业化国家,“农民与农民的子孙”仍构成人口的多数。而在中国,农民及其子孙则几乎构成了人口的全部。直至今天,环顾中国国情,不能不承认,我们的农民绝大多部分还没有真正从传统的小生产及自然经济中走出来,我们的工人、士兵、干部、企业家,有不少只是分别穿上了工装、军装、制服和西装的农民,我们的知识分子,也有那么一批实际上为小生产意识所笼罩、可以称之为戴着眼镜的农民⑥姜义华:《百年蹒跚——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中国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3页。。历史事实告诉人们,中国还没有真正从传统的小农社会中走出来,中国今日的统治模式、经济生活、意识形态、价值取向、行为模式等等,有很大一部分仍然笼罩在历史的巨大阴影之中。然而,二十多年来急剧的社会变迁给这个以农民、农业和农村为根基的国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的凋敝使得作为共同体意义的村落不再具有往日的魅力,有知识、有技能、有劳动力的,争相跑到商品、金钱、人和服务大规模集中、快速流动的城市。人们的社会网络变得分散而疏离,社会成员变得原子化和个体化。千城一面的都市拥有的只是“失巷的文明”。
就生产与消费、工作与休闲的结构关系变革而言,一方面中国是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商品遍及全世界。另一方面,中国是最庞大的消费品市场,中国的消费力崛起了,日常生活中出现和形成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正在形成为一种新型的支配权力⑦陈昕:《消费与救赎: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经过消费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中国从苦行者社会急剧地转变为消费者社会①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这里,主要是由工人制造,中上层社会消费;绝大多数人工作,少部分人休闲。生产与消费、工作与休闲的不平衡昭然若揭。人们多了很多消费,少了休闲。大众消费的后果之一是造就了终日忙碌、很少休闲的人群。在工业化国家,目前的工作时间仍然超过了工业革命前的平均工作时间。曾经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作为生活理想的民族拥有了众多的过度工作的人。现代化、工业化、机械化并没有减少人的工作时间,反而增加了人们的工作时间,减少了休闲②Julia Schor,The Overworked America:The Unexpected Decline of Leisure,New York:Basic Books,1992.。正如经济学家舒马赫的经济学定律:“一个社会真正可用的闲暇的数量通常是与这个社会用以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的数量成反比。”③E.F.Schumacher,Good Work,New York:Harper & Row,1979.人们越绞尽脑汁地提高效率,就越不可能放松和享有它。所谓“20世纪科学技术对人类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将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人有了充裕的休闲时间”④休闲研究译丛编委会:《休闲研究译丛》,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编者的话”。,显然是简单、虚构的单线进步主义的迷魂汤。
重视休闲、公共生活,重新发掘乡土社会的人生智慧,并非提倡走回头路。费孝通教授看得很清楚:在一个已经工业化了的西洋的旁边,绝没有保持匮乏经济在东方的可能。适应于匮乏经济的一套生活方式,维持这套生活方式的价值体系是不能再帮助我们生存在这个新的处境里了:“悠然见南山”的情景尽管高,尽管可以娱人性灵,但是逼人而来的新处境里已找不到无邪的东篱了⑤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四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07—308页。。如何面对今天的学习和生活、工作和休闲、劳动和消费,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也可能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不尝试就难以获致多种可能。不管怎么说,我们目前急切需要本自乡土社会的休闲、消遣观念和方式来平衡过多的繁忙、急躁与焦虑,更多一些缓慢之德和闲适之态,更少一些事功主义、消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