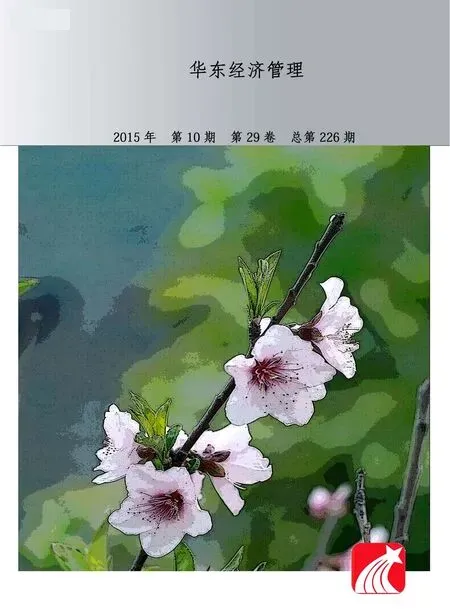应对“新常态”下城市治理挑战的地方探索
——以杭州市社会治理实践为例
杨 帅,兰永海,温铁军
(1.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081;2.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100872)
●华东经济
应对“新常态”下城市治理挑战的地方探索
——以杭州市社会治理实践为例
杨 帅1,兰永海2,温铁军2
(1.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081;2.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100872)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城市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给现代城市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文章在反思和借鉴东西方治理模式的基础上,选取杭州市作为典型案例,从自组织建设及其对社会治理的影响的角度,对杭州在社会治理领域的诸多创新性实践进行了分析。并指出通过推动自组织建设、形成多元化社会主体的共同治理和协作治理,有利于形成社会资本,从而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最终重塑东方社会传统的“群体理性”机制,为形成适应中国自身特点的治理模式找到根基。
社会结构;社会治理;城市治理;新常态;自组织
一、引言
在金融资本主导全球化的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正经历着的深刻变化:自新中国成立开始,中国经历了一个从产业资本积累到扩张(前30年由中央政府主导、后由地方政府主导)的过程。到20世纪末,学者逐渐开始指出中国经济已经告别短缺开始进入过剩(林毅夫,1999)[1],并在进入21世纪后的10年间进一步形成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三大资本的同步过剩。而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7%~8%的增速区间,告别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同期,城市经济增长结构随二产退出逐渐转向以消费、服务业为主,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步入后工业化时代。以此为内涵的“新常态”成为新时期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变化。
与经济结构转变相对应的是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突出表现在两大社会阶层(中产阶层和新工人
群体)的崛起。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土地改革,使近90%的农民获得了小块土地财产,如果按照西方经典理论分析,中国陡然变为小有产者阶层约占人口90%的社会(温铁军,2011)[2]。然而随着当前经济结构的转变,这种以小资为主的社会结构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服务业在GDP中占比越大,中产阶层人口占比越高。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的分析,认为中国的中间阶层总数达3亿多人,占到社会总人口的23%,到2015年后将会达到5~7亿人。2010年亚洲开发银行发布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按其提出的标准来估算,中国的中产阶级绝对数量为8.17亿人。该报告将中产阶级划作“底层”、“中层”、“高”三类,除去属于底层中产阶级的3.03亿人,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还有5.14亿人[3]。这种社会结构的巨变意味着在城市治理中面对的群众基础完全不同于过去。
同时,中国因承接产业国际转移成为“世界工厂”而带来一般制造业飞速发展的同时,还造就了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大规模的流动农民工群体。2013年,据国家统计局监测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农民工总数超过2.6亿人。2010年首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主要由80后和90后组成,当年总人数已达到约1个亿,占农民工外出打工的62%[4],这是在城市化浪潮中涌向城市、却又无法在城市立足的群体。如何满足他们的自我表达需求也成为构建城市有效治理的重要内容。
社会结构的多元巨变,加之社区人口老龄化、城市扩张中农民“市民化”等一系列变化,都对当前的城市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本文在对现有社会治理形态经典认识进行反思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杭州近年来的社会治理实践,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二、东西方治理模式的反思与借鉴
(一)当前西方治理的困境与反思
以往提及现代社会的治理,总会既定地以西方的“国家—社会”两分对立基础上的“公民社会”为参照框架。而当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进而导致当前西欧国家陷入主权债务危机无法自拔的时候,理论界需对此进行更深入的反思(董筱丹、薛翠、温铁军,2011)[5]。
在现有的认知中,尽管人们往往将市民社会形成的历史上溯到17世纪后期英国和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兴起时与王权的斗争中,但现代公民社会治理模式真正得以实现,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完成向外产业转移进入金融资本阶段之后。西方在此期间的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史中,先后经历了两次大的社会结构转型,并相应形成了对社会治理形态的两种经典认识:一是欧洲19世纪产业资本时代逐渐形成的劳—资两大阶级对立的社会结构及相应的阶级政治理论表达,并在后来随着西方实体产业的外移而渐趋于缓和;二是欧美20世纪中后叶形成的中产阶级社会及相应的公民社会治理与政治现代化理论。
西方经济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这种所谓现代社会治理,不过是生产领域的“福特主义”向公共管理领域的延伸,拓展到公共行政和社会政治领域后,集中体现为科学管理原则和严格的科层制;经济危机的出现导致西方国家因社会保障开支过大而出现福利危机,演化成一场缩小政府职能边界的改革运动,并随着新自由主义影响全世界。
虽然西方治理结构和功能的演变有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的适应性,但整体而言,却是一套高成本的现代化上层建筑。随着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延续到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愈发表现出这套高成本的上层建筑在西方发达国家尚难维持,更不用说复制到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
(二)东方社会治理的基本经验与借鉴
东方小农村社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大多数人口聚集在乡土社会,因资源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以及小农经济的剩余过少,不可能支撑科层制的、高成本的现代化政治和治理结构,而是依托村社的内部化功能,以乡土社会的自我组织和简约治理,形成了长达千年的超级稳态结构(温铁军,1999)[6]。学界也习惯于用建立在大规模协作体制上的民族国家这样的大共同体以及具有高度内聚力和认同感的村落小共同体的概念来描述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钞晓鸿,2006)[7]。这种稳态结构直到近现代追求工业化的进程中才逐渐被打破。
与西方充满了阶级矛盾派生的各种社会冲突风险的工业化历程相比较的是:中国在“土改”之后面对“一盘散沙”的小资产阶级社会结构,通过高度组织化的制度安排——城市的“单位制”和农村的“集体制”,内部化地吸纳了工业化原始积累中严重的制度代价。
所以,纵观中国各个时期能够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一以贯之的经验,就在于依靠组织手段和群体协作将各种外部风险内部化消化。
三、杭州的经济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实践
(一)杭州经济社会转型中的社会治理挑战
1.经济上步入后工业时期的“新常态”
近年来,杭州市的经济增速开始逐渐步入7%~
8%的新常态,并且呈现出明显的“去工业化”的趋势,表现为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逐渐下降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相应上升,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杭州市GDP及第二、三产业增长趋势
这种去工业化的趋势可以从杭州市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结构的变化中更明显地看出来。21世纪以来,杭州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一直呈现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在2004年达到最大值后开始缓慢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在持续稳定上升(表1)。结合库兹涅茨(2007)对工业化阶段的划分,当工业结构中第一、二、三产业结构分别达到<14、>50、>36时就达到了工业化后期阶段[8]。从杭州的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来看,杭州市目前处于工业化后期并偏向于结束阶段。

表1 杭州市2001-2013年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
同时,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变化趋势看,杭州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在2004年之前呈上升趋势,之后虽有起伏徘徊,但到2009年之后一直呈下降趋势;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自2004年以来呈现上升趋势,且可以预期在不久的将来,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将超过第二产业。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当三次产业就业比例达到17.0:45.6:37.4时就可认为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9-10]。根据这个标准,从表2数据来看杭州也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

表2 杭州市2001-2013年三次产业就业结构

续表2
2.社会结构多元化带来的治理挑战
随着杭州市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上的转变,社会结构的日益多元化和多元群体共生形成的张力,也带来了社会治理的新挑战。
构成杭州社会结构最主要的有三大群体:
一是城市新兴中产群体(Middle-class)。包括大中型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机关及事业单位职员、知识分子群体、私营企业主、移民杭州的新富阶层以及城市中小有产者等,人数在200万左右,约占杭州市区就业人群的半数左右。从西方发展经验来看,中产群体在政治领域和社会生活的一般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参与诉求。对于这个数量庞大、构成复杂、政治影响巨大的群体,如何构建有效的治理机制,是杭州也是整个中国社会未来社会治理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二是外来务工群体。至2013年末,杭州外来务工群体数量在250万人左右,而且年轻化趋势越来越明显。2010年,杭州市经委组织的大规模外来务工调查显示,35周岁以下占82.7%①。对于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很不愿再回到农村生活,但受制于现实的资源占有和分配格局以及城市经济容纳能力的条件,他们也难以真正融入城市。对于这些新工人群体,如何构建满足其多元文化需求的社会治理以缓和社会矛盾,就显得十分重要。
三是城市化过程中成为城市社区居民的原农民群体。随着杭州城市的扩张,大量城郊村庄被征地开发成为城市社区。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农地被征用开发。因此,如何保障这些农民群体的利益并构建与之适应的社会治理,也是中国当前快速城镇化所面临的主要议题之一。
此外,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城市社区老年群体的治理也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根据杭州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普查数据,市区城镇人口的老龄化水平在20%以上,其中65周岁及以上的人口占常住人口9.02%。面对这些老龄化群体,如何构建与之适应的低成本治理模式,对杭州而言也是一种巨大挑战。
(二)杭州社会治理实践
杭州市社会治理创新的做法可以简单概括为:
针对多元社会结构中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引导和促进其进行组织创新,以组织为载体构建满足不同群体多元诉求的治理结构,从而在这种动态稳定的组织创新中实现对多元社会的适应性治理。本文选取杭州社会治理实践中的几个典型案例对此加以简要说明。
1.服务于区域产业整合的组织创新:以丝绸女装联盟为例
丝绸和服装是杭州本地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产业,在外部资本整体过剩的条件下,这些文化资源传统有了被资本化以提高产品附加价值的巨大空间。但是,由于“杭丝”、“杭装”作为一种带有明显地域性、整体性的品牌,其品牌升值无疑具有外部性特征,杭州每个企业几乎都可以无偿的使用,但每个企业都不会也难以独自承担打造地区品牌的成本,这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杭州市政府成立了丝绸与女装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由其推动行业协会组织、龙头企业与研究机构、媒体相结合,形成政府、行业、知识界、媒体界四位一体的复合组织——“丝绸女装联盟”,然后再由这个组织来推动“杭丝”与“杭装”品牌的扩展与升值,推动区域内产业结构性升级。
在这个复合组织中,政府的适当介入成为重要因素。杭州市政府的目标是将杭州打造成“丝绸之府”、“女装之都”,为此,需要不断地发掘和重塑这个区域传统产业的文化内涵,在文化与产业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中实现传统资源价值空间的提升,也使得城市品牌建设和产业品牌建设得到相互促进和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丝绸女装战略联盟”既是一个行业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共同体。
类似的例子还有“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茶行业联盟”、“西湖博览会”带动西湖相关产业、“休博会”推动休闲娱乐产业的发展等。
2.打破原有部门或组织边界的组织复合创新:以“网群”组织为例
“城市品牌网群”(以下简称“网群”)是杭州市进行“生活品质之城”城市品牌建设的组织载体或者说是工作平台。从组织架构上看,网群是由不同性质的组织综合而成的一个综合性社会组织。网群不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它由很多具有法人资格的不同社会组织构成,网群的主体构架表现为点、线、面、块的纵横交错、多层复合,呈现出网络状的扁平结构特征。其中,点是网群中工作的单个个人,整个网群有100左右员工(其中7人属于正式的事业编制,其他则是流动性较强的合同制);线是由专家牵头,在网群工作和项目运行中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协调线,如目标线、研究线等,整个网群有14条线;面是由常设在网群中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组成,包括杭州城市品牌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杭州市发展研究中心、杭州生活品质研究与评价中心(这三个属党政界单位)、杭州城市品牌促进会、杭州发展研究会、杭州创业研究与交流中心(这三个属社团组织);块是网群的具体操作实体,与网群常设机构相联系的专职人员挂职在块上,主要有综合办公室、运行中心、研究室、目标室、财务室、策划部、活动部、外联部等部门,以及生活品质网站、生活品质视厅、生活品质期刊、生活品质调查中心、生活品质展示展览中心、生活品质纪念品服务中心、杭州城市标志管理中心、杭州生活品质传媒有限公司等实体单位。
网群的运行以项目为依托。以项目整合资源,集聚相关研究、宣传、推广机构。网群目前运行的项目主要有5大类:一是杭州生活品质展评会系列活动;二是城市品牌联动系列活动;三是城标应用推广系列活动;四是生活品质标准发布系列活动;五是研究论坛系列活动。通过以上5大类项目的运行来实现城市公共议题的市民参与、对内对外宣传和城市品牌建设。换个角度看,这5大类项目基本都是服务于一个中产社会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多元化公共需求。
“网群”的组织构建和组织运行得以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问题的机制有两个:
其一,“网群”通过组织创新,把本处于分散状态的、分属于不同社会主体的中产阶层纳入一个组织体系内,把具备不同社会资源的社会主体组织成一个单位参与社会治理,降低了政府部门与分处于行业企业界、知识界、媒体界及市民在内的这些不同社会主体的中产阶层之间的交易费用。
其二,“网群”作为杭州根据“多方参与,协作共治”理念构建的根本上区别于传统科层组织的组织性治理工具,其内部组织结构为扁平化形态,并且内部组织成员对其具有高度的组织认同感,这节约了包括组织内部沟通协调成本和监督管理成本在内的交易成本。
3.流动群体的自我文化表达:以“草根之家”自组织为例
草根之家是一个由农民工志愿者组织的自助互助的公益机构。针对当地外来务工人员开展各种文艺活动、文化讲座、职业培训、维权援助等系列社会志愿服务,为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打造一个更好的公共活动空间和交流平台,以使他们能够在“栖息”城市时找到更多的群体归属感。
“草根之家”组织在2006年形成之初,是通过搭建网络平台来呼吁社会各界关注打工群体,通过网络的传播和扩散在工友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2008年草根之家建立实体组织,并租赁门面,成为工友们工作之余聚集活动的场地;到2010年,浙江省以及杭州市各级政府对该组织给予了大力支持。所在的格畈社区免费为工友提供一栋两层楼300多平方米的活动场所,成立了新杭州人志愿者服务站,“致力于打造新市民融入都市的典范工程”,影响越来越大。
目前,草根之家针对工友推动开展的服务类型有:各种娱乐交流平台、互助学习型组织、每周一期的“草根大讲堂”、供工友们展示才艺的草根艺术团以及用于表达草根心声和交流学习的《草根》杂志、连续几年与外界共同举办具有影响力的草根文化艺术节/会等。
根据调研人员在社区内的随机采访,工友对这种形式的服务普遍认同。而且还有些工友反映同等待遇条件下大家会愿意在这里工作,因为在这里能有认同感和归属感。
4.多元社区类型中多样化治理探索:自组织实践与内部化机制
社区是城市社会的“细胞”,是承载市民生活的最基本单位。在各种不同人群混合居住的社区,客观上也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多样化治理模式的需求。杭州的社区治理中,值得关注的是正在探索前述治理难题的这样一些社区。
一是城市老社区。社区老龄化严重,其社会需求主要是社区养老、社区内部矛盾纠纷的调解、公共事务治理等问题。针对这种需求,杭州市的许多社区都探索了符合自身特点的管理创新。如上城区湖滨街道的湖滨晴雨工作室,将退休老干部、老教师等吸纳为民情观察员、民情预报员,及时协助发现和解决社区相应问题;成立“时间银行”,通过为志愿者积累时间币的方法激励50岁及以下的人群服务社区老年群体;在其他很多社区,也都有“和事佬”、“老娘舅”组织来协助调解民间纠纷以及发动社区志愿者对居家老年人结对帮扶;在上城区的老旧社区的庭院改善和背街小巷改造工程中,广泛吸纳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退休老职工成立“民间庭院改善监督办”,对于关乎社区和自身利益的市政工程实施直接的监督,并代表社区居民提出自己合意的意见;在江岸区凯旋街道的南肖埠社区、清波门社区、清风社区,企事业单位的家属小区较多,因此,除了社区党委组织外,社区辖域内还有各单位的基层党组织29家,于是这三个社区便采用“SPO峰会”(辖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联合峰会)的形式,吸纳30家基层党组织为会员,推举理事长、会长、理事以及会员,以一种非正式组织的形式将原有的党组织资源再整合,以达到资源共享、共同协商治理社区的效果。总之,这些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核心理念是调动和发挥社区内的组织或个体成员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
二是城市化过程中被纳入城市的原农民小有产者的社区。其最大的利益诉求是适当合理的财产权益补偿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社区治理。杭州市对被征地农村除了各种正常的征地补偿外,还推出了留地安置的政策。即将征地总面积的10%留存给被征地村落,由其自主开发,当然也制定了严格的规管措施(土地开发只能以物业出租方式经营,不能进行商业地产开发)。然后将集体资产作股量化到个人,形成股份合作制的社区经济治理结构。这一方面使得集体获得了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治理的财力支撑,另一方面在理顺了集体与成员之间以及成员间财产关系的基础上,使农村原有的治理组织和治理结构能够顺利平滑地转变为新的城市社区治理组织;同时,也更有可能使乡土社会内部以熟人社会为基础产生的各种低成本治理机制得以保存,从而有益于降低城市化进程中基层社区治理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变迁成本。比如,在拱墅区的一个征地村落就自发形成了完善的“村规民约”来处理征地过程中的违建以及社区生活所产生的各种常见矛盾。近几年杭州城市化进程加快,形成的此类社区很多,此类社会治理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多。
四、结束语
从杭州市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可以总结出有益的经验以供借鉴。
(一)杭州社会治理创新的核心机制:通过自组织建设产生社会资本
杭州实践的核心机制在于通过增强自组织建设形成和利用已有社会资源产生社会资本,以此提高社会可治理性。具体路径有两个:
第一个路径在于通过自组织建设调动已有的组织、人力、文化等资源,提高不同群体的参与性,在形成社会资本的基础上降低社会管理成本。例如,在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中,那些退休老人身上蕴含的丰富的社会文化资源以及各项专业技能都被调动起来。再如,在行业治理中出现的“丝绸女装行业联盟”、城市公共治理出现的“网群”复合组织以及社区中形成的“联合峰会”组织,都是把原有的政府组织资源和社会组织资源进行了充分的调动。在这个再组织化的过程中重新形成社会资本,
成为社区实现低成本治理的基础;并且使不同群体参与到社会治理中,使其有表达自身多元诉求的渠道,从而有利于分散社会治理压力,缓解和弱化社会冲突。
第二个路径是通过各种功能性组织对接外部市场,在外部资本整体性过剩的环境下,本地特有的文化资源成为过剩资本新的具有高回报率的投资领域。这就使这些文化资源获得了重新定价的机会,产生新增的资本化收益,提高了社会整体收益水平。这在杭州本地特色的丝绸、服装、茶、休闲、动漫等诸多产业集聚和升级的过程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这种增量收益一方面使得以这些产业为基础形成的白领阶层的发展需求获得满足,另一方面也为城市治理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撑。
这两种社会资本形成的路径可以用图2表示。

图2 自组织促进社会资本生成的机制
(二)对杭州实践的进一步认识:东方社会的“群体理性”
杭州在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中,针对不同社会群体推动自组织建设,本质上在于提高不同群体中的个体参与性及主体性,从而在组织的运作和参与中重新形成群体性文化,形成利益或文化“共同体”,使不同群体的多样化利益诉求得到合理的表达,化解多元文化共生的社会结构中的内生性张力,从而使社会的可治理性得以提高。这与以往“单位制”和“集体制”——以组织为载体化解小资社会过于分散的交易费用的机制有相似性。
进一步地看,这种通过群体文化来内部化处理各种治理问题的机制也存在于中国几千年来社会最基本的单元——村社中。村社以亲缘、地缘聚合,聚落而居,在长期抗御自然风险、兵荒匪患等外部风险的过程中,内部逐渐形成了高度的协作机制,并呈现出追求群体收益最大、而非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特征。这种村社内部的“群体理性”(Group Rationality),成为东西方社会最本质的不同。其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住奥斯特罗姆(2000)在其著作中已经着重论述了这种来自东方社会建基于群体文化之上的社群自组织在使用“公共池塘资源”时的内部化机制[1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方社会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共同体形态和“群体理性”特征,或许是理解中国本土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钥匙。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杭州市经委组织宣传处“杭州市工业企业外来务工人员生活工作现状及对策研究”,《杭州文明在线》2010-03-10,http://www.hzwmw.com/article.htm1?id=1140328.
[1]林毅夫.新农村运动与启动内需[J].中国物资流通,1999(10):8-12.
[2]温铁军.从小资社会向中资社会转型[J].杭州(我们),2011(11):14-15.
[3]陈代阳.亚行:中国中产阶层已超8亿人、专家回应称数量偏大[N].华西都市报,2010-08-30(18).
[4]白田田.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年梦想:面向城市、春暖花开[N].经济参考报,2010-02-12(5).
[5]董筱丹,薛翠,温铁军.发达国家的双重危机及其突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转嫁[J].红旗文稿,2011(21):4-9.
[6]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J].读书,1999(12):3-11.
[7]钞晓鸿.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基于清代关中中部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6(4):190-205.
[8]吴珊.工业化后期城市产业布局优化研究——以杭州市为例[D].杭州:浙江大学,2011.
[9]威廉·配第.政治算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2-23.
[10]克拉克.经济进步的条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57-61.
[11]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137-158.
[责任编辑:余志虎]
Local Experience of Coping with the Challenges of Urban Govern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New Normal’—Evidence from the Practice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Hangzhou City
YANG Shuai1,LAN Yong-hai2,WEN Tie-jun2
(1.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081,China;2.School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With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o the‘new normal’,urban economic struc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which bring a new challenge to the modern urban governance.This paper draws lessons from the east and west governance modes,and selects Hangzhou city as a typical case,then analyzes its innovative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lf-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its impact on social governance.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social capital could be created by promoting the self-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forming the joint governance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diversified social subjects,so as to reduce the cost of social governance.Eventually,the‘group rationality’mecha⁃nism in traditional oriental society can be reshaped,which would be the foundation of a governance model to adapt to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 structure;social governance;urban governance;the new normal;self-organization
F290;F127
A
1007-5097(2015)10-0015-06
10.3969/j.issn.1007-5097.2015.10.003
2014-02-0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4ZDA06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5CGL015);杭州市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3661102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6批面上资助项目(2014M561123)
杨帅(1984-),男,湖北襄阳人,北京理工大学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社会治理,农
村发展,新制度经济学;
兰永海(1987-),男,河南南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乡村治理,区域经济发展;
温铁军(1951-),男,北京人,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乡村治理,城乡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