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
华伟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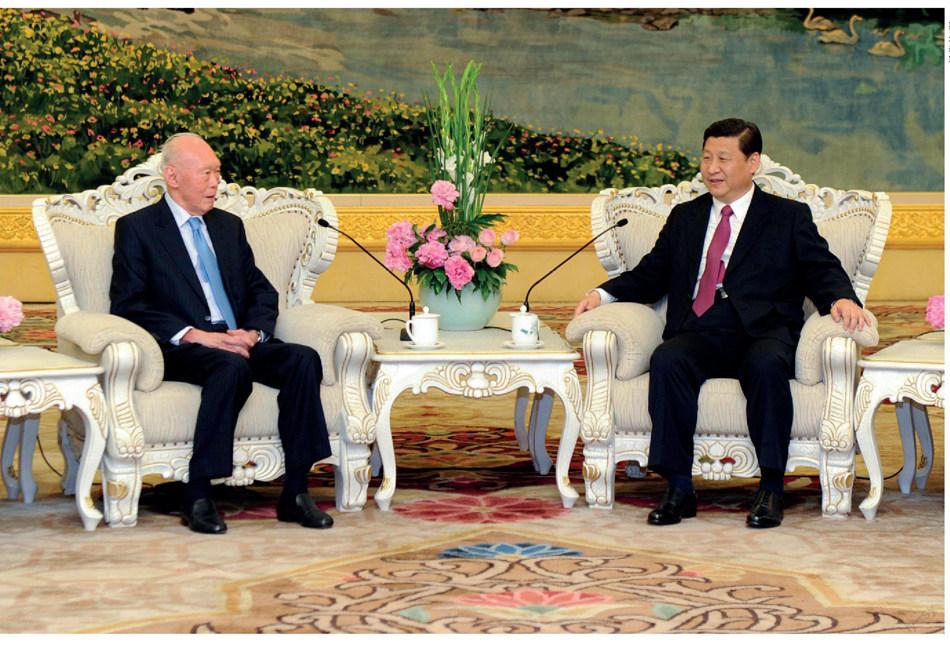


安娉是在车站发现站牌上张贴的那张招聘广告的。她二十三岁,身材匀称,长得娟秀,在这座城市飘泊了好几年。对她而言,并不知道下一刻预示着什么,大多数故事会在又一个季节里遗忘,被风染上枯萎的锈黄色,然后飞舞着落在不知何处的所在,在凛冽的气候里变得无踪无影。四月初的一天,她应聘到了那家张贴招聘广告的公司工作。
这是一家销售办公用品的贸易公司,在火车站附近一幢商务大楼里。老板姓史,穿着西服,四十多岁,中等个子,稍显发胖,脸上皮肤粗糙,却显出志得意满神情,眼睛里有种干练与狡黠。他扔下老婆孩子从老家出来打拼,几年翻滚爬摸有了眼前这片天地。招聘条件很简单:大浪淘沙,面试合格,试用期两个月,每月五百元生活费,没有其它任何待遇,两个月销售额不能达到指标走人。安娉刚离开一家濒临倒闭的工厂,很想尝试一下,拥有这份工作。因此,她瞧着史老板那张疙疙瘩瘩,令人捉摸不透的脸庞,并没有感到特别恶心。
史老板问她: “你做过销售?”
安娉摇了摇头。
史老板看了她一眼,又看了她一眼。
安娉心里忐忑。
史老板脸上露出不屑神情,不紧不慢从烟盒弹出香烟,衔在嘴里用打火机点燃。烟雾弥漫起来。他像在思考,“好吧,暂时留下来试试。”他目光透过烟雾,在她脸上逗留,若有所思地道。
安娉悬着的心放下来。她租的住处离公司比较远,不过房租便宜,附近就有地铁还算方便。她开始在公司上班,相信勤能补拙,大多数时间在外面跑,穿梭于高楼大厦,殚精竭虑寻找客户,有时也回公司吃午饭。商务大楼和火车站周围有商务套餐和午市套餐,一般人均消费在三十元左右,电话外卖送上门的盒饭也要十五元。即便销售员每月底薪一千五百元,其它按销售额百分比提存,每天一顿午饭,来回地铁公交费用,就占了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加上租房和其它杂七杂八费用,月薪基本上没有剩余的钱,销售业绩上去才会有些积蓄。离火车站远一点,多走十几分钟,有家小饮食店,提供馄饨和面点,五元钱一份,面点上加浇头,另外加钱。安娉有时没有准备午饭,情愿多走十几分钟,在小饮食店吃着烫嘴的馄饨,会想起老家过年时吃饺子的情景。
两个月转瞬即逝。安娉含辛茹苦,奔波忙碌,推销产品,销售毫无起色。销售办公室不大,被隔成好几块,销售员在外面跑,还不显得拥挤。里面是经理办公室,另外一间是财务室。这天,史老板经过销售办公室,朝她招了一下手。安娉明白怎么回事,心里忐忑,起身跟他走进里间经理室。史老板一屁股坐在老板椅上,拍着办公桌上销售台账,唬起脸劈头盖脑斥责道:“安娉,你怎么搞的?两个月过去,销售额还这么差,付你底薪都不够。按照公司规定,销售额不达标,我不能白养活你。”
安娉脸颊羞红。
“这里不是慈善机构。钱是靠辛苦,靠本事赚的。”史老板涨红脸,嗓门越来越大,像对钱过不去,要将她生吞活剥。
安娉窘迫,怯生生地看着他,脑子里嗡嗡作响。史老板皮肤粗糙愤怒的脸庞,令她想起村口那棵老槐树的皮。她心朝下沉,等待着辞退。
“好吧,我给你一次机会,再宽限你一个月,销售额不达标只能走人。”史老板发泄完,忽然缓和口气,点上一支烟,开恩似地说,脸上有种意味深长的笑。
安娉尴尬地笑。她回到自己销售办公室,发现办公室的同事都抬起头,目光齐刷刷盯着她,随着她在办公桌前坐下。她心里涌起说不出的滋味。午餐时候,那家小饮食店客人特别多,弥漫着葱油和其它味,不断传出锅碗瓢盆撞击声。安娉到小饮食店去吃馄饨,惊奇地发现同事张昕在吃面,旁边的坐位空着,她迟疑了一下,端着馄饨坐下。安娉在办公室和张听见面,只是礼节性地点下头,平时没有太多的交往。她下意识地笑了笑。他吃的是五元钱一碗的光面,飘着葱花,没有浇头。她低下头去吃烫嘴的馄饨。
张昕二十五岁,轮廓分明的脸庞,长得还算周正,打扮干净拎着包,形象明显加分。他做了两年多销售,脸上呈现出纯真,又掺杂着某种自信,和年龄不符的成熟与稳重。他在公司沉默寡言,不苛言笑,不属于张扬的类型。他没有和她说话,闷着头吃面,直到碗里只剩下一点清汤,才坐直身子,目光凝视着小饮食店门外,或看她细嚼慢咽。她不好意思起来,侧过脸去问,你喜欢吃面条。他脸上依然没有太多表情,只是说馄饨吃腻了,吃面条换换口味。他的回答更像是敷衍。她说你不常来这家小饮食店吃午餐。他没有回答。她吃完馄饨,他才说道:“其实,你不适合做销售工作。”
安娉心里一沉,明白公司同事,看着自己目光的含义。她脑海里飘浮起:西装革履行走在春末夏初大街上的男士,穿着时髦裸露出圆润小脚自信满满的白领……她心里萌生羡慕,又有种失落感觉。她渴望能有份稳定工作。这种愿望像吹过的风,温湿、腻人,在心里滋润地拂过。她不想轻易放弃,自己学历不高,经济又不景气,要找到工作很难。她瞧着他,沉吟未语,暗自思忖,要争口气。“其实,销售是一种累积的过程。”张昕像是安慰她,又像对自己嘟哝。二
天气逐渐炎热起来,风从办公室窗外扑来,有了一种溽热感觉。办公室空调还没有启用,风扇发出很响的声音。南方的天气,一大早就是桑拿天,中午更是骄阳似火。安娉一大早出门,冒着烈日,不辞辛劳,寻找客户,推销产品,有些公司没等她说完来意就下了逐客令,有些公司主管施舍的目光瞧着她,她口干舌燥介绍了很长时间,才敷衍地勉强同意考虑考虑,电话再打过去却回答你烦不烦?又追问这笔生意凭什么给你做?她被泼了冷水,脸上无奈地笑。她毫不气馁穿行于各个公司,汗水把衣服濡湿了一大片。一个月要过去了。她打电话,四处奔忙,除了有几个小客户,销售依然没有起色。她心里越来越焦灼起来,办公室风扇的声音摇晃着,和她心情一样变得烦躁。这天,她下班前一刻从外面赶回办公室,擦了下脸上汗涔涔细密的汗珠,拉开抽屉发现缝隙塞有两张销售单子。她惊讶地瞧着销售单子抬起头,目光移向前面办公桌张昕的背影,心里漾起一阵潋滟。下班以后,安娉跟随张昕一起乘电梯,下到底层走到大楼门口,她把两张销售单子悄悄递还给他。张昕转过脸,瞧着她道:“噢,这是我的新客户。你先接过去做吧。”
安娉推辞道:“不!这不行……而且,这不是两笔小生意,你做销售也不容易。”她态度坚决。
张昕道:“我这个月销售额已经完成。”
安娉心里过意不去,又掺杂着些许不安,目光和他撞在一起,像要从他脸上窥视什么。
大楼里下班的人群不断从电梯里涌出来。
安娉犹豫着,思考后道:“要不这样,我到时候把提存的钱算给你。”
张昕道:“好吧。”
安娉既感激又忐忑,拉开大楼玻璃门,朝他羞涩地笑笑,一头闯进落日余晖的街市。
天气已是盛夏,办公室终于开了空调。公司月末结完账,扣去杂七杂八费用,月头上五日发薪水。此刻,史老板喜欢站在销售办公室隔开的挡板前,瞪着不大不小的眼睛,扯开嗓门,口头禅是:“天上会掉下馅饼,但是,不会轻易掉馅饼!”这个月的销售额有明显增长,他赚了钱,绷紧的脸庞明显活泛起来,甩出五十元钱,请人去买冷饮慰劳大家,趾高气扬地走回经理室。同事一阵欢呼雀跃之后,有人调侃史老板就值五十元钱,一元硬币攥在手心能渗出汗,大家忙得拼命应该请客吃顿饭,有人无不担忧地嚷道,说不准过些日子销售指标又会往上加。安娉谨慎地对张听说,今天中午我请你吃饭。张昕愣怔一下,还过神来,说我请你吃饭。午餐时刻,两人在小饮食店买了两碗面,加了蚝油牛肉浇头。另外,她给他要了一瓶啤酒。安娉已经算好两笔销售额的提存款,从口袋里掏出六百二十元钱递给他。张听说你留着用吧。安娉说你帮我忙,已经感激不尽。他说你先寄五百元钱回家。安娉知道前两天,他听到自己在办公室接听的电话。她心里有种东西飘浮上来。
安娉的销售业绩逐渐好起来,张昕给她传授销售经验,有时陪她一起去拜访客户。同事中有些闲言碎语,有人妒嫉她白命清高。
女同事的丝袜勾破了,从腿部撕裂出一条垂直线,脸上呈现愠怒。那个屏风摆放在办公室进门中间,谁也觉得碍事,谁也没有在乎,张昕将屏风朝边上斜着稍为挪动一些,显得更加协调。安娉朝张昕投去赞许的目光。
夏蝉短长急促此起彼伏。这天下午,安娉一个人在办公室和客户打电话。空调发出咝咝声响,有气无力吐出冷气。史老板从外面回来,瞥了她一眼,又瞥她一眼,走进经理室,很快又回到办公室,手里拿着一盒包装精美的化妆品递给她。安娉从办公桌上抬起头,眨巴着眼睛,惊诧地瞧着他。史老板脸上神情变得暖昧。她明白史老板的意思,心里惴惴不安起来,漫过不舒服的感觉。她拼命谢绝他的礼物。史老板脸上尴尬,嘴唇不断在嚅动,声音变得颤抖。她没有听清他在唠叨什么,慌乩地盯着他干裂的嘴唇,脑子里奇怪地蹦跳出一个字:渴。她记得那次,看见史老板和那个女财务走出办公室,在电梯前等候时,手迫不及待在她瘦削的屁股上捏了一把。她假意躲闪,脸上堆满笑,他的手不安份地从裙子下面伸进去,两条纤细的腿可怜地稍为叉了开来。三
城市染上一片秋意,梧桐树叶随风飘落,街市呈现出另一种浪漫风情。这天下午,安娉和张昕在一家公司洽谈完业务,秋雨飘落下来,密集得像张网,四处笼罩在雨雾里,两人跑到就近一家超市去躲雨。超市里比平时嘈杂,许多是进来躲雨的,也有推着小推车在货架前挑选,把需要的物品扔进小推车。两人在超市闲逛,走到服装货柜前,安娉目光在一条紫色丝巾前滞留,张昕伸手想取下那条丝巾,安娉拉住他走了。她心里在忖思,那件挂在衣架上的大衣,款式很新颖,估计张昕穿上会很帅气。两人在人群里挤来挤去,安娉感觉张昕不喜欢挤在人多的地方,两人走到货架后面墙旮旯窗前,瞧着雨景闲聊,等待着雨停歇。
黄昏一刻,雨停了,路面湿漉漉的。走出超市,安娉说不想回去烧饭,想犒劳一下自己,征询的目光瞧着张昕。她更多的意思是想感谢他。张听说好吧,省得一个人回去,再简单也要张罗吃的。两人在饭店点菜,他喝了一瓶啤酒。安娉说好今天自己付费,两人推搡了一会儿,结果还是张昕抢先埋了单。安娉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走出饭店,风很凉爽,被雨洗刷过的街市在夜晚的灯光下显现出很洁净的感觉。安娉穿着那种薄的牛仔套装,上衣很短,齐到腰间,里面穿件白色圆领衫,显出匀称苗条的身材。张听说我送你回去。安娉说不用送,并关切地嘱咐,你也累了一天,该回去早点休息。张昕迟疑了一会儿,说我送你到地铁口。安娉想了想说好吧。两人走在路上,都没有说什么,快到地铁站的时候,安娉有些依恋,犹豫地说:“要不然我们再走一站吧,反正下一站也不是很远。”
张昕点了点头。
两人走了一站,最后上了地铁。张昕一直把她送到出租屋弄堂口。弄堂里很暗很窄小,低矮的房屋挨得很紧,和周围的高楼形成鲜明对照。这里的老房子还没有拆迁,大多数出租给了外来人员。弄堂里从窗户漏出昏暗的灯光,寂静中能嗅到男人粗重喘息与女人尖细喊叫声,混杂在一阵如雨的麻将声里,空气中裹挟着生活的酸甜苦辣与悲欢离合,有了一种暖意,在昏暗狭窄的弄堂里弥漫。分手时,张昕迟疑片刻,冲动地搂抱住了安娉。安娉心里一阵紧缩,惊疑的目光瞧着他。他眼睛里有种渴望。他显得紧张,局促而慌乱,抚摸着她,变得激动起来。她没有说话,脸颊赧然泛红。过了几秒钟,张昕松开了手,脸上闪现出窘迫与歉疚。
安娉对张昕的感觉变得浑沌。她不清楚自己是因为心存感激,还是别的原因,心里变得烦乱。她上班时谨小慎微想尽量躲避他,他不在时心里又感觉像缺了什么,有种浅浅的怅然。这种感觉很微妙。她下班后,凝视窗外,一个模糊的影子在心海若隐若现,像一只小船从遥远处轻轻地划来。她扪心白问:自己爱张昕吗?他会是人生中昙花一现的一个故事?还是生命中一个匆匆即逝的过客?夜深了,风吹过,一绺散发粘在脸颊,她想用手轻轻拂开,总有一两根看不到扯不着,心里若有若无被发丝缠绕。她脸上一热,感觉是红了。张昕像忘记了那天晚上的事,一如既往对待她。她心里有种叙述不清的情结。
转眼冬天了。
张昕在外面忙碌,有时累了,一个人不想做饭,给安娉打电话,在外面忙完事顺便买点菜过来。安娉就忙着做饭,抽空帮他把衣服洗干净。安娉并不感觉嫌弃,心里反而有种暖意。这天晚上,张昕把安娉送到弄堂,“天真冷……”他吸了口寒气,轻声抱怨,风将他的声音刮走。
夜已很深。安娉矜持地看着他,心里有种东西飘浮上来,见他没有马上想离去的意思,犹豫着小心翼翼地道:“外面太冷,要不到我房间里去坐一会吧。”
张昕迟疑,点了点头。
出租屋很简陋,但比外面暖和。微弱的月亮映在窗前,屋子里很静。安娉关上房门,感到心头鹿撞,手足无措,踌躇地道:“坐吧。”
张昕紧紧拥抱住她,心里涌起一股暖流。安娉脸颊羞红。他的手隔着毛衣和厚厚的牛仔裤,感觉到了她胸部与两腿间的体温。他亢奋起来,激情被点燃。安娉闭上眼睛,屏息静气,一动不动。张昕贴着她耳边,激动地喘息着道:“安娉,我想要。”他的声音发颤,疯狂地亲吻她。
安娉对这一切已有预料。她光滑的身子钻人被窝,目光紧紧盯着天花板。她感觉身体烫得怕人,他的身体也很烫。他是个好人,她想报答他,眼眶湿润了,清澈的眼睛蒙上一层薄雾。他滚烫的身体贴近时,她心里哆嗦了一下,忽然颤声说道:“张昕,结婚时给你好吗?”
张昕怔住了,像骤然惊醒,心被什么撞击了一下,脸上显出惭愧神情。微弱光晕下,她紧抿嘴唇,脸上泛着圣洁的光泽。忽然,他从床上坐起身,摸索着穿起衣服。
黑暗中,安娉瞪大眼睛,惊愕地瞧着他。
张昕侧过身瞧着她,想紧紧拥抱住她,忘情地亲吻着她,吻遍她整个身心。他冷峻地道: “安娉,我不会和你结婚。”
安娉紧张地问道:“为什么?”
张昕脸上露出落寞神情,忧郁的眼睛瞧着窗外,像要穿透迷茫的暗夜,往事电影般在脑海呈现。他缓缓地收敛目光,停顿片刻,沉郁地道:“我是一名逃犯。”他的声音很轻很冷,带有一种穿透力,穿透宁静和忧郁,在寂静的小屋里回响。
“逃犯?”
张昕眼睛里有种冷意,清纯而深不可测:“我从小和爷爷一起过日子。那年,我到镇上去寻找爷爷,饿得饥肠辘辘,抢了点心店两个馒头,被发现后为了逃脱,把老板娘砍成了重伤。我心里害怕,一直很后悔。我弄张假身份证,在各处漂泊打工潜逃了八年。”
安娉惊呆了,心里抽搐,被恐惧包围。
屋子里很静。
张昕平静地道:“我不可能和你结婚。你心底善良,我不能伤害你,害你这一辈子!”他脸上掠过一丝歉疚,把头痛苦地埋在两腿之间。他穿上裤子站起身,目光揉进了一种依恋。
空气凝固了。
安娉抬起头,从他眼睛窥视到了那缕依恋,看到了一种真诚与情义,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被触痛了,这种疼痛在变成温馨,浓稠得融化不开,从心底涌到喉头再到眼眶,一下子袭遍整个身心。她脑海浮现和他认识、交往、相处的日子,心灵震颤,有种难言的滋味蔓延开来。她意识到自己根本离不开他,心被一种巨大的空虚攫住。这一刻,她恍然明白,自己深爱着他,这种爱在不知不觉中,已逐渐渗透进了心底。她觉得他很真诚,真诚得十分残酷,这种感觉遥远得无法回忆却又真切。她披上衣服侧过身去,忽然,歇斯底里紧紧抱住他。时间仿佛停止流动,万物停止了声息。她让他坐在床沿,心里一片宁静。窗口映现了沉黛色……四
南方的冬天,有种潮湿的阴冷,光秃的树枝在寒风中颤抖,街市呈现出冬日景致。暮色四拢。这天,安娉回公司路过火车站后面那条街,看见史老板从一家店面玻璃移门出来,背后一个脸上涂着浓妆的女孩裹着外套,领子开口处裸露出显眼乳沟,从门里探出身子和他挥手道别。安娉想躲避已经来不及。史老板神秘兮兮的样子,看见她一怔,脸上马上掠过尴尬神情,掩饰地用手抹一下嘴,显得极其猥琐。安娉局促地瞥他一眼,感觉他嘴里像刚塞进一只肥腻的母鸡,有种狼吞虎咽偷食饱餐后的满足神情。她心里泛起嫌厌,知道史老板缺乏文化底蕴,既便穿着西服,系着领带,拥有一片天地,远没有达到脱胎换骨的程度,骨子里仍然是暴发户本质。史老板恢复常态,搭讪地问她回不回公司,安娉应付地点头。
春节临近,史老板说请大家吃顿年夜饭,也算是提早给大家拜个早年,吩咐安娉到酒店预订一间包房,菜肴标准在两千元左右。安娉犹犹豫豫怕自己不熟悉,不知道预订那一家酒店好,更怕点不好菜。张听说我陪你一起去吧,就着节前的快乐气氛,同事们脸上纷纷显出心领神会的笑容。史老板看了看安娉又看了看张昕,脸上的肌肉抽搐一下,也随着大家略显窘迫地笑起来。
公司在火车站附近一家酒店提前吃年夜饭,整个公司同事济济一堂坐在包房里。大家忙碌一年,聚在一起七嘴八舌,气氛十分融洽,酒菜上桌后气氛更加热烈。有人举杯,请史老板先说几句。史老板脱下大衣,穿件紫绛红暗条西服,里面白衬衣配着一根鲜红领带,脸上努力修饰过,比平时显得光亮。他神采奕奕地道,大家都干了一年,我先敬大家一杯!接着充满豪情地说,只要跟着我史老板,我赚钱,保证大家也能赚钱,希望明年大家兜里塞得更满。来,大家一起干杯!油爆虾、椒盐羊排,松籽鲈鱼、馋嘴蛙……一道道菜上来,史老板喝多了,一只手搭在女财务肩上。在公司里,他平时最器重张昕,张昕销售一直名列前茅。他举起杯子摇晃着说,来敬张昕和安娉一杯。大家哄笑起来。桌子上变得杯盘狼藉。史老板体内酒精起了作用,筷子击打着白瓷盘子,似醉非醉,夹起一块馋嘴蛙肥嫩大腿,塞进嘴里,眼前飘荡起女人白皙的大腿。他舌头有些僵硬,发泄似地道,操!憋了一年,终于可以回家踏踏实实抱女人了。在外面赚钱好是好,就是憋不住想解馋……没有猫不贪腥的。人嘛!大家放假回去,该抱女人的抱女人,该抱男人的抱男人。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女同事也毫不掩饰地大笑。张昕和安娉也被这种气氛感染,只是心里搁着事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冬天的夜晚,走出酒店门外,霓虹灯神秘地闪烁着,天空显得空旷而莫测。
时间过得很快。公司过几天就要放假,办公室同事变得兴高采烈,出租屋弄堂里也热闹起来,人们开始忙碌着准备回家,空气中弥漫着节前的气氛。安娉说:“张昕,我想回家去过年。”
张昕瞧着她。
安娉道:“我想和你一起回家,去见我父母亲,再去见你爷爷。”
张昕心弦颤动。
“然后,我陪你去自首。”
张昕倚在门框旁,眼睛眺望着远天。
“你不能一直生活在不堪回首的阴影里,你去自首,会得到宽大处理,这样还会有希望。”安娉真挚地道,“无论你被判几年,我都会在外面等你。”
张昕目光深沉,回过头来,冷峻地道: “好吧,我去自首,你必须答应,永远离开我。”他似乎思考过这个问题。
安娉明白他的意思,有股酸楚涌上来,心里痛苦挣扎着。她思忖着点了点头。她从他眼睛里看到了一种暖意。
冬天的城市裹在寒冷里,阳光被风吹得没有暖意。这天,张昕和安娉说好,一早去排队买车票。史老板兴致勃勃赶到安娉住处,送来糖果给安娉和张昕,让他们带回家去过年吃。安娉感谢他,让他进屋坐,史老板呼着热气,说还有急事等着。上午,太阳露了一会儿脸,之后隐人云层后,天色阴沉,像要下雨。安娉出门去买了些东西,赶到那次躲雨的超市,给张昕买了那件新大衣。午后,她到公司把一些琐碎的事情办妥,填写完每笔销售清单,又整理了一下抽屉,然后赶回出租屋。
黄昏时分,冬天的雨挟着寒意落下来。安娉做着晚饭,整理行李,边等待着张昕。她望着窗外阴霾的天空,雨淅淅沥沥下着,城市像裹在雾茫茫水汽里,变得湿淋淋而冷阴阴的。她不知张昕是否买到车票,心里惦记给张昕打了电话,张听说还在排队,售票大厅人头攒动,堵得水泄不通。安娉做好晚饭,张昕还没回来。她瞧着水珠顺着屋檐滴落下来,犹豫着要不要出门,最终还是想去看他。她拿上伞,锁上房门,一头钻进雨雾里。
南方的天气很少下雪,雨挟着雪花,竟纷纷扬扬飘落下来。正是下班一刻,街市人来车往,十分繁忙。
安娉撑着伞,赶到售票处,售票大厅拥挤不堪,门外四周都是人群。她打张昕的手机。张听说票买好了,已离开售票大厅,正走在外面那条街上。安娉松口气,离开售票处,急忙到外面那条街上去寻找他。雨雪不断下着。她朝两边张望着,没有看见他身影。她须臾有种离奇感觉,这座城市变得遥远而陌生。她隐约听见不远处传来喊叫声,在马路那边聚集起一大簇人。安娉走过去挤进人群。天色黯淡下来,雨和雪天女散花般从空中飘落下来。她感到周围影影绰绰,议论声抵达心灵深处:“这辆法兰红出租车开得太快,雨雪天气刹车都来不及!”“是啊!做母亲的也有责任,过马路不该让小男孩乱跑。”“哎!多亏年轻人眼疾手快,推开小男孩,可自己却被出租车撞了……”安娉耳边嗡嗡作响,不断传来嘈杂声,夹杂着110警笛声,120救护车呼啸声。安娉跪在马路上,浑身湿透,毫无知觉,心像被掏空,有种飘浮感。
雨什么时候停了,雪积起来,城市一片银妆素裹。五 圩家沟。 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十分偏僻的小山村,群山环抱,郁郁葱葱。安娉辗转来到这里。风吹来挟着一丝凉意,山上开着各种野花,山脚下村庄升腾起袅袅饮烟。她穿件浅色风衣,秀发朝后盘成一个髻,显得矜持而冷静,伫立在山坡墓碑前。太阳从山后爬上来,照耀着大山,在晶莹露珠上闪烁。她将一束鲜花敬献在墓碑前。她沐浴在早晨的阳光里,想坐下来,陪他说话,脑海里闪现起那个画面。
重症监护室,他昏迷不醒,脸色惨白,像张薄纸。倏忽间,他苏醒过来,有了反应,微微睁开眼睛,嘴唇蠕动。她俯伏下身,贴近他脸庞。他的心跳很微弱,声音缥缈而温馨:“安娉,我、我很好。在外面飘、飘泊八年,东躲西藏,像生活在黑暗里……我感到疲惫,很、很想回家!遇到你有种温馨,有了家、家的感觉;和你认识、相处的……日子,就像走在回、回家的归途……”
群山宁谧、肃穆。安娉眼圈红了,想不到他会以这种方式回家,感觉灵魂在絮叨,不断叙述着什么,和他在一起的时光,就像是沿途的风景。太阳爬上山顶,风吹来有了暖意,轻拂她脸颊,更像他在细语。她记得他曾告诉自己,看着她洗衣做饭,让他想起冬日的阳光,暖和地斜照进窗。他感到身上的那层冰冷坚硬在分崩离析,忧伤不再凛冽。其实,她知道自己的心。她轻轻闭上眼睛,感觉他的嘴唇湿润温柔,抵达心灵深处。她浑身颤栗,清秀的脸上有种近似于痴迷的爱。她睁开眼睛,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天空中白云在悠闲地移动。安娉眼睛里蕴含着无限深情,呈现出他轮廓分明的脸庞,冷峻的嘴角艰难地露出最后笑容。那一刻,他神情凝固,像一尊雕塑,却栩栩如生。她心猛地抽搐,像被什么堵塞,有种悲恸在弥漫。她恍若还在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