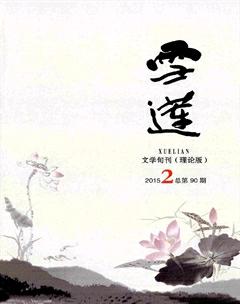论托尼?莫里森《爵士乐》中的畸形之爱
李智毓
【摘要】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性作家,托尼·莫里森的作品一直有一个不变的主题,那就是爱与爱的缺失。继《秀拉》中的姐妹情谊、《所罗门之歌》里的纯真爱情、《宠儿》中的浓浓母爱之后,《爵士乐》讲述了乔、维奥莱特以及多卡丝之间的三角畸恋。本文将着重分析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纽约大都会的背景下,三个主人公之间错综复杂的爱情故事,并深入挖掘这种畸形之爱背后的历史根源及情感动机。小说以死亡开始,以新生结束,表达了作者希望黑人种族能够重拾自我,用爱去抚平过去创伤的美好愿望。【关键词】莫里森;《爵士乐》畸形之爱;种族歧视;母爱的缺失中图分类号:I106
托尼-莫里森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摘此桂冠的第一位黑人女性作家,其在美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莫里森心系黑人种族历史与命运,擅长以故事的形式表达其对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的关怀。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或感人至深、或动人心魄的故事。而这些看似千差万别的故事同时又有着相同的主题,那就是爱与爱的缺失。在独特的历史语境及种族语境下,这种爱有时会发生异化,以极端或反常的形式表现出来。《秀拉》穿插秀拉与其好友内尔的丈夫的偷情故事,《所罗门之歌》包含奶娃与其外甥女的乱伦之恋,《宠儿》以塞丝杀女为主线倾诉浓浓母爱……《爵士乐>以1926年的纽约黑人聚居区哈莱姆为背景,是莫里森追寻历史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宠儿》的续篇。乔、维奥莱特以及多卡丝三者之间的爱恨情仇,在莫里森动人而婉转的讲述下,娓娓道来。小说的男主角乔出生于1873年,女主角维奥莱特正好年届半百。他们已不再是弗吉尼亚魏斯伯尔县一无所有的黑奴,而是纽约大都会里经济上能够自立的新一代美国人:乔推销妇女美容品,维奥莱特是美发师。然而过去南方农村的记忆、尤其是失去母亲的记忆一直伴随着他们,这些记忆在大都会令人窒息的生存压力下发酵、变异,乔内心空虚、另觅新欢,维奥莱特精神失常、沉默寡言,夫妻关系冷漠、形同陌路,最终酿成杀害情人的惨剧。然而,在小说的结尾,莫里森寄予黑人种族以希望,乔与维奥莱特重拾迷失的自己,彼此相爱,获得了精神上的新生。
《爵士乐》以一个男人开枪打死一位十八岁姑娘、他的妻子大闹葬礼开头,扣人心弦。通过多个叙述者的讲述,读者得知这个男人乔及其妻子维奥莱特是生活在纽约哈莱姆聚居区的一对黑人夫妻,死去的姑娘是乔的情人。乔因为不能接受自己的情人和自己分手,结交新的男友,而开枪打死了她。可以说,乔是出于对多卡丝的畸形之爱,而杀死了她。这与《宠儿》中塞丝杀死宠儿是有异曲同工之处,杀人动机都是出于浓浓的爱,不同的只是时间、地点以及人物关系罢了。枪杀流血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种族歧视对美国黑人身心的深刻影响。小说主人公乔和妻子维奥莱特都是受缚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北方现代都市生活的黑人。从奴隶制的枷锁下解脱出来,他们义无反顾地融入了纽约这个大都会的生活。一方面,大都会那让人心悸的生活节奏使他们脱离了南方农村的根:另一方面,和大多数莫里森笔下的人物一样,他们的内心深处仍然摆脱不了过去南方农村生活的记忆。这种记忆在赋予他们现在生活意义的同时,也阻碍了他们过上真正幸福的大都会生活。对于小说的男主人公乔而言,这种记忆既有对过去自由自在的南方丛林生活的怀念,也有被自己母亲抛弃后的极度空虚,二者相互交织,使他感到失望、空虚,“他深信只有他一个人还记得那些日子,还想让它们回来:虽然还记得当初的情形,却根本找不到当初的感觉了,所以他就在别处给自己找了个伴侣”[1]37。被母亲遗弃的阴影无时无刻不笼罩着乔,使他的内心极度空虚。他迫切想知道母亲的存在,渴望母亲能把手从树叶中间、从白色花朵中间伸出来让他看一眼。乔曾三度寻母,均无结果。在最后一次寻母失败后,乔十分绝望,此时他遇到了维奥莱特,因此和她结婚,以期弥补被母亲遗弃的耻辱、母爱缺失的空虚等心理不平衡感,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爱情。内心空虚依然如影随形、时刻伴随着乔,这为他后来移情别恋埋下了祸根。这种空虚直到遇到多卡丝才得到真正的缓解。
多卡丝的父母死于1917年东圣路易斯市的种族骚乱:父亲被人从有轨电车上拉下来活活跺死,母亲在家里被烧死。她五天里参加两次葬礼,内心也是一片空虚。相同的遭遇使他们拥有共同语言。多卡丝于乔,不仅仅只是一个漂亮的情人,更是遗弃自己的母亲的象征。在多卡丝身上,乔找到了缺失的母爱。他跟多卡丝在一起的时候,眼前浮现的是母亲的身影。乔的母亲是个野姑娘,她无处不在,却又无法找到。甘蔗田是她的藏身之处,有时候她也跑到树林里去,乔第三次找她时还在石洞里发现她生活的痕迹
“一条绿裙子。一把少了一个扶手的摇椅。一个圈垒起来做饭用的石头。罐子、篮子、锅;一个布娃娃,一个纺锤,几个耳环,一张照片,一堆柴火……”[195]而乔的情人多卡丝与这个野姑娘有许多相似之处:乔第一次看见多卡丝时,她正在一家杂货铺买糖果,这个情景让他想起自己母亲身上甜蜜的甘蔗味;多卡丝那吃糖吃坏了的肤质使乔想到母亲被甘蔗田的大火烧坏了的脸;她野灌木丛似的头发使乔想起母亲的蓬乱不堪;她脸上的蹄印仿佛是自己母亲留下的踪迹。乔在去枪杀多卡丝的路上,回想起当年去岩洞找他母亲的情景,乔感慨道,“但是她在哪儿?”[195],这个她既指多卡丝,也指乔的母亲。从母亲的岩洞出来,是一条名叫“叛逆”的大河,河的名字具有很强的隐喻意义,它预示着乔将再次被自己的情人背叛、抛弃,事实也证明如此。所以,当多卡丝要和他分手时,被母亲抛弃的空虚又一次吞噬了他、嚼碎了他,让他丧失理智,他再也无法接受被第二次被抛弃的打击,因此开枪杀死了她。笔者认为,乔杀死的是他所爱的情人多卡丝,也是遗弃他的母亲,更是饱受被母亲遗弃、缺乏母爱、感到极度空虚、偏执的乔自己。枪是猎人的捕猎工具,乔开枪打死多卡丝,同时也意味着他向青年时代南方农村猎人本性的回归,二十年的大都市压抑了过去的记忆,而多卡丝的到来释放了这种本性,让他重拾过去热爱的树林生活。看似畸形的爱情,实则意料之内、情理之中。如果说迷恋多卡丝是出于对母爱的执着追寻,那爱到极致开枪打死她则是这种执着的高潮,是对过去几十年记忆的彻底抹去,是一种放下,也是一种重拾,放下的是过去亲昵的回忆、是母爱的替代品、是对母亲的追寻、对母爱的渴望以及空虚、执着的自己,重拾的是来到大都会之前的南方丛林生活、是那个真实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乔。因此,多卡丝的死代表着乔的新生。当从多卡丝的好友费莉丝那儿得知多卡丝至死都爱着他后,乔才最终从悲伤中走出来,树立了生活的信心,与维奥莱特重新相爱。
过去的记忆给维奥莱特带来的影响和造成的创伤也是显而易见的。童年时代维奥莱特经常受到外祖母特鲁·贝尔的熏陶,听她讲金色少年戈尔登·格雷的故事,这在她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从未见过他,少女时代却给他撕了个粉粹,就好像我们真的曾是最最相爱的情人。”…戈尔登·格雷是特鲁·贝尔服侍的白人女主人薇拉·路易斯和一个黑种男人所生的孩子。他有着金灿灿的肤色,一头松软的黄发卷遮住了他的脑袋和耳垂。维奥莱特对他、尤其是对他的金色头发和肤色的迷恋实际上反映了她作为黑人的自卑心理,从文化层面上来说,这种迷恋也折射出白种人的优越地位及其这种种族优越感给黑人心理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维奥莱特之所以选择嫁给乔、死缠着他,也只是把他当作这个金色少年的替身。所以这种爱并不是真正的爱情,而是在种族歧视的土壤下孕育的畸形之爱。当环境发生变化时,这种爱终究会发生变异,造成她与乔感情的瓦解。
如果说种族歧视给黑人带来的心理自卑感是造成维奥莱特爱上乔的历史根源,大都会是使这种爱发生畸变的催化剂,那么母爱的缺失则把这种爱推向了极致,使她的情感不能得到正常的表达,从而出现精神失常。家园被摧毁后,维奥莱特的母亲罗丝·蒂尔跳井自杀。作为自杀者后代的维奥莱特内心是撕裂的,她头脑中有裂纹,“不是裂口,也不是裂缝,而是白天的阳光中那些黑暗的缝隙……阳光也有裂痕、粘得很糟的接缝和不知所终的脆弱之处”[1]22。这一裂纹不仅代表着母亲罗丝·蒂尔自杀的那口深井,也暗示着维奥莱特心理的崩溃,那些她无力应对的时刻
无缘无故一盘腿坐到大街中央、突然抱走别人的婴儿以及用刀子划死去的多卡丝的脸,都是她内心裂纹的表现。“维奥莱特从父母的经验中得出的重大教训,最大的教训,就是永远永远不要孩子”[1]106。大都会生活压力太大,夫妻俩无力起抚养孩子,“再说没有孩子对于城市生活会好得多”[1]112。维奥莱特一共经历了三次流产,“两次在田里,只有一次是在床上”[1]112,她沉浸在最后那个流产的孩子的伤痛中不能自拔,经常想象给那个女孩做最漂亮的头发。随着时间的推移、年华逝去,这种热望越来越强烈,“当维奥莱特四十岁的时候,她已经在盯着小孩子们看,在圣诞节展销的玩具前面踯躅不前了。要是一个孩子挨了骂,要是一个女人抱孩子的样子别别扭扭或者漫不经心,她总是气不打一处来”[1]112,“母性的饥渴像一把锤子一样击中了她,将她击倒击垮”[1]114。因为不能抚养孩子,也不能正常地爱乔,她把这种对孩子的渴望转化为对动物和玩具的依恋,她每晚抱着一个布娃娃入睡,还跟一只鹦鹉说话。维奥莱特正是想借此克服母亲自杀留给她的阴影,并医治自己不能当母亲的心理创伤。此外,尽管乔对维奥莱特来说只是金色少年的替身,她不爱乔也没有能力爱乔,但她却不允许别人占有他。在这种近乎疯狂的嫉妒心和畸形之爱的驱使下,她大闹多卡丝的葬礼,并用小刀划伤死者的脸。后来,她逐步了解多卡丝,爱心萌发,开始思索自己是否也爱上了她,并产生了多卡丝是自己流产孩子的念头。在爱丽丝和费莉丝的帮助下,她开始重拾过去,消除怨恨,杀死了那个要杀多卡丝的自己,并开始重新去爱乔。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维奥莱特与《宠儿》中的塞丝都是失去孩子的可怜母亲,都被剥夺了正常做母亲的机会,不同的是,塞丝是在奴隶制和浓浓母爱的共同作用下,不得已杀死了自己的女儿,而维奥莱特则是在种族歧视的阴影和大都会紧张生活的压力下,错失做母亲的机会,并产生了对流产女儿的畸形母爱。
而真正把维奥莱特与乔的过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件则是小说第六章戈尔登·格雷在寻父途中与乔的母亲野姑娘的相遇。二者的相遇看似与本书内容联系不紧,实则意义重大。可以说该章是全书的高潮,它揭示了乔与维奥莱特畸形之爱的深层原因。在驾着马车找寻父亲的途中,天降暴雨,马车的左轮撞上了~块石头,戈尔登·格雷下车整理行李时,看见了一个像莓子一样黑的裸体女人。而这个女人因为太害怕,一看见他拔腿就跑。他对黑黝黝、赤裸裸、亮晶晶、湿淋淋的马又有安全感又喜欢,而那个黑女人却让他感到恶心,在他的眼中只是一个幻影,而非真的女人。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了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以及黑人对白人的惧怕心理。戈尔登·格雷与乔的相遇不仅是乔与维奥莱特产生畸形之爱的根源,而且也是这部小说最根本的矛盾和冲突之所在:在美国社会的形成时期,黑人和白人应如何相处。戈尔登-格雷是黑白混血儿,有着金灿灿的肤色,金色的头发,这些都是白人的特征,但并不能掩盖他的父亲是黑人这一现实。野姑娘则具有典型的黑人特征,她邋遢、神出鬼没、四处撒野、不识字、不会说话、没有母亲,她让我们联想起《宠儿》中的那个鬼魂般的“宠儿”,她们都是千千万万个奴隶制下被压迫、被残害的黑人的象征。因此,戈尔登·格雷与野姑娘的偶遇一方面预示着乔与维奥莱特二十年后的相遇,另一方面也代表着白人文化与黑人文化的正面交锋。莫里森是想通过他们的相遇,让读者思考黑人在当今美国社会所处的地位问题。而维奥莱特与乔的畸形之爱作为以戈尔登·格雷与野姑娘为代表的黑白文化的冲突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北方大都会的具体体现,就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含义。乔和维奥莱特都是正值奴隶制废除后、黑人文化运动处于高潮时期从美国南方北迁至大都会的新一代黑人,历史留给他们的伤痛还在,但他们的经济地位已经提高,如何在新的环境里正常地生活是他们要面临的问题。
毫无疑问,小说的三个主人公都经历了极其严重的母爱的缺失。母亲的遗弃使乔陷入了极度的空虚,而母亲的跳井自杀则使维奥莱特不敢正常地拥有自己的孩子,直到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而母亲点燃房屋自杀的经历在小小的多卡丝体内生根发芽,永远定格,让她陷入了跟乔一样的巨大空虚之中,只能靠纵欲去缓解这种伤痛。与此同时,二十年的大都会生活似乎让乔与维奥莱特夫妇迷失了自我,忘记了自己的根,最终酿成乔枪杀年轻情人的惨剧。但仔细想来,多卡丝似乎更像是他与维奥莱特过去痛苦回忆的化身。乔在她身上找回了逝去的母爱,维奥莱特把她看成了自己流产的女儿,在她身上体会到了做母亲的滋味。与其说多卡丝是乔与维奥莱特这对夫妇婚姻的破坏者,不如说正是这位十八岁姑娘挽救了他们名存实亡的婚姻。可以说,多卡丝是乔与维奥莱特的救星,她让夫妇俩重新找回迷失的自己,使乔从被母亲遗弃的耻辱和空虚中走出来,也填补了维奥莱特大脑中的裂纹,让爱的阳光照进了她的心房,驱散了她心中的阴霾,重新获得了爱与被爱的能力。多卡丝的死意义重大,它意味着乔和维奥莱特的新生,是他们重归和睦,彼此互爱的开始。正如叙述者在小说结尾处发出的充满深情的爱的呼唤:“我只爱过你,把我的整个自我不顾一切地献给了你,除你之外没有任何人。我想让你也用爱回报我,向我表达你的爱”[1]244。的确,过去的伤痛、母爱的缺失剥夺了男女主人公爱与被爱的能力,最终让他们陷入一场悲剧的三角畸恋中。然而,沉溺于过去而不能自拔显然不是出路,在《爵士乐》中,莫里森给出了答案:黑人种族只有走出历史、重拾自我、用爱感化彼此,才能真正走出种族歧视的创伤,重获新生。
参考文献:
[l]jiao Xiaoting. Dream of Dreams: QuiltingAesthetics and Toni Morrison's Artistic Appeal [M].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08.
[2][关]托尼·莫里森.爵士乐[M].潘岳,雷格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3]Russell, Danielle. Between the Angle and theCurve:Mapping Gender,Race,Space,and Identity in WillaCather and Toni Morrison [M].New York: Routledge,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