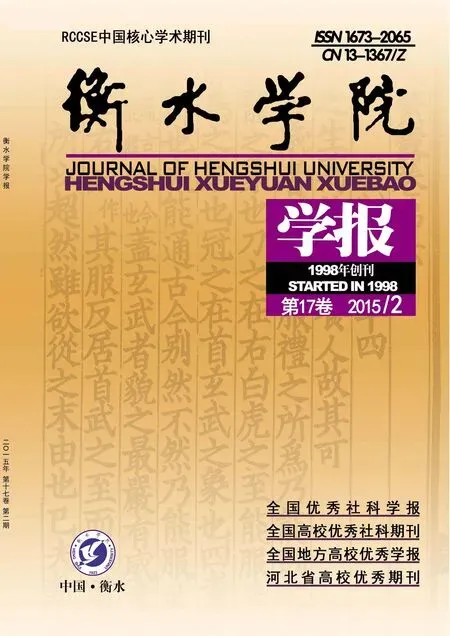朱子所谓“四子”何指——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石立善
朱子所谓“四子”何指——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石立善
朱子;四子;四书;《近思录》;“好看”;宋代;六经
昨晚一个研究生发来电子邮件问学:“石老师:《近思录》后有朱子评语,‘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四子’是什么意思?是《四书》吗?没有标书名号,可见不是书名。我在网上查了,很多学者都说这句话中的‘四子’不是指《四书》,而是指宋代的周、张、二程四子。一个师兄告诉我,《哲学研究》有一篇文章说‘四子’并非是指《四书》,是说《近思录》是读周、张、二程之书的入门读物。记得您在课堂上说过‘四子就是《四书》’。这里的‘四子’究竟是什么意思?请老师赐教。”
我回信解答如下:恕我孤陋寡闻,将这句话中的“四子”解作北宋道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这个说法我还是初次听说,很是骇人听闻。我手头也没有《哲学研究》杂志,这段话涉及到哲学史和学术史的关键处,暂就我所知回答你吧!你问的那段话是朱子的高足陈淳(字安卿)记录的,原文为:
《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此语载于南宋黎靖德编纂的《朱子语类》卷一百五《论自注书》,含义丰富,乃朱子告诉弟子们《近思录》的地位及其与四子六经的关系、入道之次序。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近思录》,后人多将朱子此语附在书后。历代理学家很重视这段话,时至清代,张伯行还收入他编纂的《续近思录》卷三。
我的看法是,“四子”就是《四书》,即《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四子”这个用法很特别,在朱子之前,似乎没有人这样用过。“四子”,即先秦儒家最重要的四家——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朱子是用《四书》的主人公、作者或传述者来命名称呼的。“四子”与《四书》都是“四子书”的略称、省文,后世又称作《四子书》。近来也有人说“四书”是指“四部书籍”,其实也是望文生义的误解。
《论语》是孔门所记述的孔子言行录。《孟子》是孟子所撰,朱子认为七篇首尾文字浑然一体,如熔铸而成,当出自孟子本人自著。至于《中庸》,作者是孔子的孙子——子思,乃担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大学》则出于孔子的弟子曾子及其门人,经一章是曾子所述孔子之言,传十章是曾子门人记录的曾子之意。——这些都是朱子自身对于《四书》的作者及成书的看法。绍熙元年(1190年),朱子61岁,出任福建漳州知州时,同年十月与十二月在临漳先后刊刻了《四经》与《四子》。《四经》即《尚书》《毛诗》《周易》《春秋左传》,《四子》即《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书刻成后,朱子分送与一些友人和弟子(《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二《答张元德》)。当时的《四子》刻本没有传下来,幸好其《后序》还保存在朱子的文集里,题为《书临漳所刊〈四子〉后》。朱子云:
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故今刻四古经而遂及乎此四书者,以先后之。且考旧闻,为之音训,以便观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于此者,附于其后,以见读之之法,学者得以览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
《四子》经文下附有朱子的音训,卷末则附录二程的相关论评,以便阅读。朱子在《序》中表明了他对《四书》的理解乃源自二程,我们将其中的“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与“四子,六经之阶梯”加以比较,可知朱子这段话的思想源头是出自二程。而且,朱子与吕祖谦编纂《近思录》十四卷六百二十二条,原意是为初学者提供一部可以自学的道学入门书,尤其是那些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者,后来此书地位不断上升,在南宋末就已被尊奉为“宋之一经”(叶采《近思录集解序》)。至于为何将四子之书合刊,朱子在写给杨方的信中解释说:因《大学》字数少,太薄,装不成册,无法单行,合刊时就题名为《四子》,另外也想藉此提示这四部古典的阅读进阶次序(《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答杨子直二》)。朱子将自身刊刻的《四书》(《大学》《论语》《中庸》《孟子》)题名为“四子”,是确凿无疑的。而且,将“四子”理解为《四书》,也符合朱子一贯的学术主张。我们从义理层面看这段话,也与其思想体系相吻合。朱子曾多次言及《四书》与六经的关系及阅读次序:
熹尝闻之师友,《大学》一篇乃入德之门户,学者当先讲习,知得为学次第规模,乃可读《语》《孟》《中庸》,先见义理根源、体用之大略,然后徐考诸经,以极其趣,庶几有得。(《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六《与陈丞相别纸》)
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易三》)
《诗》固可以兴,然亦自难,先儒之说,亦多失之。某枉费许多年工夫,近来于《诗》、《易》略得圣人之意。今学者不如且看《大学》《语》《孟》《中庸》四书,且就见成道理精心细求,自应有得。待读此四书精透,然后去读他经,却易为力。(《朱子语类》卷一百十五《训门人三》)
朱子的话浅显明白,须先读《四书》,再读其他儒家经典,可见他是如何重视与抬高《四书》的。这些看似不经意的谈话记录,其实就是学术转折的关键,透射出南宋时代《四书》与五经的地位之升降,以及理学的信仰及其依据,须细细体会品味。朱子在临漳先后刊刻《四经》《四子》,有深意存焉。朱子当然不会反六经,但他极力抬升和确立《四书》的地位,取而代之,后来他的确做到了。
这段话的记录者陈淳也是将“四子”理解为《四书》。陈淳云:“若所谓《近思录》者,又《四书》之阶梯也。”(《北溪大全集》卷三十《答梁伯翔一》)即用“四书”来替换“四子”。又云:“向闻先生亦曰:‘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四子之阶梯。’……大抵圣贤示人入德,所以为理义之要者,莫要于《四书》。但绝学失传,寥寥千载,直至四先生而后明,而四先生平日抽关其发钥,所以讲明孔孟精微严密之旨者又杂见于诸书,不可类考,幸吾先生辍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为此篇。……故吾先生所以发明《四书》之宏纲大义者,亦自四先生之书得之。”(《北溪大全集》卷十四《书李推近思录跋后》)“四先生”即周、张、二程,陈淳认为朱子发明《四书》之义理,也是从四先生之书得之。又云:“若据古《四书》本文,非先有得乎此录四先生之说,则亦将从何而入?而孔孟所不传之秘旨亦将从何而窥测其藴乎?”(《答李公晦三》)说的都是要从《近思录》而至《四书》。“此录”即《近思录》,意思是学者先于《近思录》所载四先生之学说有所习得体会,然后再入《四书》而探究其深蕴。
我们回头再看那段话,“《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从逻辑上分析,将“四子”理解为《四书》,就可与上面所引朱子的其他语录贯穿起来,也会明白为何要遵从《近思录》到《四书》,《四书》到六经的次序。朱子的意思是,读书要从记载了北宋理学家周、张、二程的话语的《近思录》入手,《近思录》是通往《大学》《论语》《中庸》《孟子》的阶梯,而《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又是通往《周易》《尚书》《毛诗》《三礼》《春秋》等六经的阶梯。细绎文意,可以看出朱子这段话的构造是递进式的,即《近思录》→《四书》→六经,三者都是书名。但是,如果将“四子”解作周、张、二程的话,就变成了《近思录》→周张二程→六经,可《近思录》本身就是周、张、二程的哲学精粹的汇编,这样的解释令“《近思录》”与“周张二程”相重复,在话语表述的逻辑上是根本说不通的。而且朱子从未说过由周张二程的学问可以通往六经的话,也从未称周张二程为“四子”。
朱子将《四书》称作“四子”的说法,为其后学所继承,像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九《语孟纲领》第一条小注即标出“六经四子”,这里“六经”与“四子”对举,“四子”就是《四书》。朱子之后的历代学者无一例外,都是将“四子”理解为《四书》。如真德秀很重视朱子那段话,即以“四子”为《四书》(《西山读书记》卷三十一)。又如《近思录集解》的编者叶采在序文中引用朱子语,并称赞《近思录》将与《四子》并列诏启后学而垂无穷,这里的“四子”当然就是《四书》。又如黄仲元云:“《论》《孟》,六经之阶梯。”元代汪克宽为倪士毅《四书辑释》撰写的序文云:“《四书》者,六经之阶梯。”(《环谷集》卷四《重订四书辑释》)又如明代高攀龙云:“以周、程、张、朱为《四书》之阶梯,以《四书》为五经之阶梯,自得之而道可几矣。”(《高子遗书》卷七《崇正学辟异说疏》)又云:“朱子曰:‘《四书》为五经之阶梯,《近思录》为《四书》之阶梯’,言所由以从入之序也。”(卷九上《重锲近思录序》)何乔新亦云:“《四书》之精详,为六经之阶梯。”(《椒邱文集》卷二《道统》)或用“四书”替代“四子”,或以“周程张朱”替代《近思录》,理解并无二致,清代学者亦然,例多不赘。
《四书》是六经的阶梯,此不言自明,而《近思录》为何是《四书》的阶梯呢?你去读周张二程的著作与语录,多读,读懂就知道了,他们的哲学与工夫论都根植于《四书》,只是侧重不同而已,《论语》是他们四人共通的源头,周敦颐与张载的学问主要得力于《中庸》,程明道得力于《中庸》和《孟子》,程伊川得力于《大学》《孟子》。《近思录》的许多内容皆源自《四书》或阐发《四书》的。因此,朱子说通过《近思录》这部周张二程的哲学汇编,即可通往孔门之《四书》。在宋末,叶采已经视《近思录》为宋朝之一经。(《近思录集解序》)至清代,江永谓《近思录》非寻常之编录,直亚于《四书》(《近思录集注序》),一语即道出该书的历史地位。《近思录》虽为编纂,却至关重要。朱子学的思想体系中,《小学》为修身之法,《近思录》则为义理之渊薮。读一部书,研究一个时代或一个人的哲学与思想,关键是眼光,眼光要力透纸背,抓住其最根本的“依据”与“源头”,反复思绎体察,其他则迎刃而解。令人痛心的是,当今很多做中国哲学与思想研究的学者性庸识暗,又不肯虚心读古书,像“四子”一类最基本的术语都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的话,根本没有资格研究宋明理学,遑言传统学术!
以上,我们从朱子本人对“四子”一词的用法,从朱子对“四子”与“六经”的关系的认识与阐发,从记录者陈淳对“四子”一词的理解,从朱子这段话的内在逻辑结构,从后世儒者对朱子这段话的理解等5个层面进行了分析,结论是:“四子”无疑就是指《四书》。将“四子”解作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看似合理,其实是非常荒谬可笑的。今后为了防止初学者和一般读者对这段话产生误解、误读,应该将“四子”加上书名号,这样标点为宜:“《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附言之,朱子本人万万没有料到,在他过世后,朱门围绕着陈淳记录的这段话产生了很大分歧,相关争论一直持续到清代。首先是朱子弟子兼女婿的黄榦,他在写给同门李方子的信中说:
先《近思》而后《四子》,却不见朱先生有此语。陈安卿所谓“《近思》,《四子》之阶梯”,亦不知何所据而云。朱先生以《大学》为先者,特以为学之法,其条目、纲领莫如此书耳。若《近思》则无所不载,不应在《大学》之先。至于首卷,则尝见先生说其初本不欲立此一卷,后来觉得无头,只得存之,今《近思》反成‘远思’也。以故二先生之《序》皆寓此意,亦可见矣。今观学者若不识本领,亦是无下手处。如安卿之论亦善,但非先师之意。若善学者亦无所不可也。(《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六《复李公晦书》)
可以看出,黄榦亦将“四子”理解为《四书》。他质疑陈淳所记语录非朱子本意,间接地批评了真德秀和李方子的态度。据说另一个同门林夔孙(字子武)对陈淳记录的那段话也不以为然(《北溪大全集》卷十四《书李推近思录跋后》),可知朱门内部的歧见与对立。清代学者王懋竑在《朱子年谱》卷二“淳熙二年乙未四十六歲”条中虽载录了这段话,但他根据黄榦写给李方子的信函,认为其中的“《近思录》,《四子》之阶梯”可能不是朱子的原话,他的理由是那段话与朱子另一个弟子叶贺孙所记语录不合。叶贺孙记云:
或问《近思录》。曰:“且熟看《大学》了,即读《语》《孟》。《近思录》又难看。”(《朱子语类》卷一百五《论自注书》)
另一位清代朱子学者夏炘也赞同王懋竑的看法,他说:
朱子云:“义理精微,《近思录》详之。”何得以为“好看”?朱子平日教人读书,先《大学》,次《语》《孟》,而后《中庸》,《近思录》开首所说“太极”、“性命”皆《中庸》之奥旨,余亦《大学》《语》《孟》之精义,何得以此先于《四书》?(《述朱质疑》卷七《跋近思录》)
近人邓艾民的《朱熹王守仁哲学硏究》也因循黄榦的看法:“说《近思录》为四子的阶梯,既不符合这里所说难易、远近之序的标准,也与他人记载的语录有相互矛盾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页)这些人的看法,我不敢苟同,逐条驳之如下:
甲,陈淳记录的那段朱子语录,类似主旨的话语的确不见于朱子的其他著作和语录集,但我们要知道朱子讲学,往往因人而发,因时而发,黄榦没有亲耳听到朱子讲这段话,不足为奇。另外,黄榦怀疑陈淳的记录,与他认为门人所记语录未必尽传朱子之本旨也有重要的关系(《池州刊朱子语录后序》)。
乙,黄榦说《近思录》不应在《大学》之先,话虽如此,但《近思录》中的很多言论都是阐发《四书》之性质与义理,以及与其他经典的关系,当可作为读《大学》乃至《四书》的预备和参考。
丙,读语录必须注意的是朱子的话是对谁讲的?语录的记录者是谁?其学力如何?以及记录时间之早晚。陈淳虽是朱子晚年(61岁)才入门的弟子,而朱子欣喜地说:“南来,吾道喜得陈淳。”(《宋史·陈淳传》)并称赞他“看得道理侭密,此间诸生亦未有及之者”。(《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七《答李尧卿(一)》)陈淳勤学深思,嗜学如饥渴,入门后学问长进很大,(《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一《答黄直卿(九十九)》)他很会提问,故朱子曾在众人问学之后,单独留下他一人讲话。对陈淳而言,《近思录》是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书,在他22岁那年,从其乡贤林宗臣(字实夫,高登弟子)那里得到此书后,遂诵读研习而入道学之门。(《北溪大全集》卷末附陈沂撰《敘述》)绍熙元年十一月十八日,陈淳在初次拜见朱子时所呈的投书《初见晦庵先生书》中,在开端就特别提到他是从《近思录》上溯北宋诸先生及朱子著作的(《北溪大全集》卷五),那么朱子对陈淳讲述那番话就不奇怪了。在理解那段话时,我们须考虑到陈淳和他的学问背景。我统计过,《朱子语类》载陈淳所记语录多达600余条,数量居门人之首,且每一条都非常详细而传神。陈淳最后诀别考亭是在庆元六年(1200年)正月,三个月后朱子辞世,从时间上判断,他所记语录亦可谓“朱子晚年定论”。
丁,黄榦信中说的一句话——“若善学者亦无所不可也”,颇耐人寻味,即便是朱子的话也并非金科玉律,圣贤书与思想的理解与阐发,关键还是在于学者自身。
戊,王懋竑、夏炘认为陈淳与叶贺孙的记录相反,一记“好看”,一记“难看”,因而起疑。我认为:两者并不矛盾,恰恰是王、夏二人不通训诂,误解了朱子“好看”一词的意思。此处的“好看”并非是指好读、容易读,其正确的意思是“关键”“重要”。我举《朱子语类》中的两个例子:
《周礼》一书好看,广大精密,周家法度在里,但未敢令学者看。(卷八十六,李方子记录)
方云:“此去欲看《论语》,如何?”曰:“经皆好看,但有次第耳。”(小注:前此曾令方熟看《礼记》。)(卷一百十九,杨方记录)
第一条语录若依照王、夏二人的解释,理解为《周礼》这部书容易阅读的话,那么整段话就不通了,因为朱子认为此书广大精密,周朝礼乐制度俱在其中,还明确道出不敢让学人读《周礼》。第二条语录的“好看”也不能理解为好读或容易读,众所周知,儒家诸经皆非轻易就可以读懂的典籍。同样道理,《近思录》卷首《道体》专论宇宙、性命,乃义理本原之说,又岂是好读之书?我结合这几条朱子语录的文意,发现“好看”的意思应当是“关键”“重要”,如此理解则文通义顺。朱子所谓“《近思录》好看”,乃点出《近思录》的地位与重要性,提醒门人须重视并仔细研读。总之,朱子本意为:《近思录》很关键,因为《四书》为六经之阶梯,《近思录》为《四书》之阶梯。王懋竑、夏炘皆为笃实的朱子学者,竟怀疑和误解朱子话语至此,尤其王懋竑同时也是一位擅长考据的学者,可见读书之难。须知读宋代以后的典籍,亦须先通词语训诂。朱子此语仅20字,却关涉到《四书》的命名缘起、《近思录》的地位评价及与六经的关系、入道之次第等大问题。一缕之任,实系千钧之重。予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朱子门人众多,虽然黄榦作为女婿继承衣钵,但仍可视为集体接班。朱子是不世出的天才学者,学问博大精深,一两个弟子是接不住的。大哲学家、大学问家的弟子,不容易当。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此之谓也。仅就有著述流传下来的朱门弟子而言,黄榦、陈淳、蔡沈、辅广、杨复、张洽等堪称翘楚,然皆祖述朱子学问之一端而已。黄榦气象狭窄,才能不过中人,其治学虽勤苦过人,而守成有余,创发不足。在义理方面,我更欣赏和推崇陈淳,他的《北溪字义》的确做到了接着朱子往下讲,难能可贵。陈淳的主要著作《北溪字义》是阐发性理概念的讲学笔记,这些概念大都出自《四书》,故又名《四书性理字义》,可见他的确得到朱子之真传。迄今研究宋代《四书》学与《四书》学史的中外学人都没有注意到《北溪字义》,这是很不应该的。重视《四书》虽然发轫于二程兄弟,而《四书》学的成立与体系化则要归功于朱子。记得朱子有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四书》是熟饭,而读其他儒家经典是打禾为饭,终究差了几重。他还说:“《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朱子语类》卷十九《语孟纲领》)朱子最重视的是“体之于身”,即于自身切己处体认涵养,读书已是第二义,理会经典的目的是要超越文本、穿透语言,反复体验力行,使自身与古代圣贤的义理合而为一,那么义理粲然的《四书》自然要比《周易》《尚书》《毛诗》等经典来得更为直接,更为有效。所以朱子慨叹,若是读懂读透《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理学的发展直到明代的王阳明,他们的道德信仰及工夫论的概念、依据仍然没有越出《四书》的范围。所以说,哲学家光有才能与见识是不够的,古今中外凡开创时代者皆有常人所不及的大气魄和大气力,像朱子这样的贤哲,几百年才出一位。
(责任编校:耿春红)
作者介绍:石立善(1973-),男,吉林长春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日本京都大学),“申江学者”特聘教授,台湾大学访问学者,浙江大学、河北大学兼职教授,朱子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史、古代经学、敦煌吐鲁番学、日本汉学史。

博文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5db7c30100cdv8.html
1673-2065(2014)06-0060-04
10.3969/j.issn.1673-2065.2015.0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