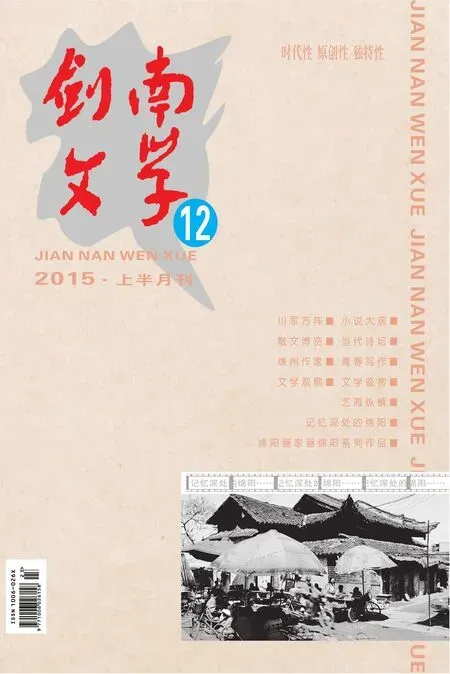想念稻草人
■蒋克明
想念稻草人
■蒋克明
前几天读到篇文章,是一个父亲回忆自己女儿的。看到他女儿名字的那一刻,我的心不禁一阵悸动。因为她叫陈平。
台湾的陈平,雨季的河童,沙漠的ECHO,皇冠的三毛。
我的中学时代就是她陪我一路湿淋淋地走过来的。上大学以后,我告别了三毛,迷上了张爱玲、司汤达和昆德拉。年华流水般地流淌,许多年过去了。某个无眠的午夜,当记忆的沙砾偶然撞击我疲惫的心时;某个雨季,当我穿着黄胶鞋肆意地淋着雨时,我知道,我想起了一个人,而且我很想念这个人。因为她曾陪我走过少年维特式的青涩青春,陪我走过那些阳光并不灿烂的日子。那段三毛岁月就像铅华洗尽的黑白老照片一样,永远地刻下了我生命的瞬间。
这个戏称自己为三毛的女子,在她寂寞的成长岁月,经历了无法逃避的伤痛后,孤身飞向茫茫无际的撒哈拉,开始了流浪的一生。她将一种属于前生回忆似的乡愁,不能解释地、毫无保留地交给了那一片陌生大地。"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我在想,如果三毛还在人世,如今已过花甲之年了,她会不会还穿着牛仔裤戴着黑色的旅行帽踽踽独行呢?
她父亲说,少年三毛在家第一次听到西班牙古典吉他时就非常憧憬西班牙的小白房子、毛驴和一望无际的葡萄园。她的这段往事此前我并不知晓。或许这就是所谓缘分,如今我不但学会了古典吉他,喜欢边弹吉他边唱《橄榄树》,CD架上钟爱的西班牙古典吉他唱片不下十张,而且我极爱西班牙的异国风情。《白手起家》的结尾,三毛庆祝乔迁之喜时放的音乐就是德沃夏克的那首《新世界交响曲》,三毛的家人讲,荷西过世后,她也常常听他的钢琴曲。最初看《白手起家》的时候我并不了解这个捷克民乐大师。大三的一个燥热的夏天,我的心冰一样的寒。我失恋了。我拿着男朋友分手时给我的德沃夏克的《幽默曲》听了整整一天一夜。第二天,我打电话给他,一共说了三句话:"我终于知道三毛为什么爱德沃夏克了。谢谢你的CD。我想我长大了。
于平常中,于匆匆中,坦言自己的真性情;平中见奇,平中溅泪。她前期的作品,风格轻快明朗,但深度显然不够。这一时期我最推崇的是《稻草人手记》的自序。短短的二三百字,温馨和怡然自乐扑面而至。每次读到结尾,“当晚风拍打着它(稻草人)单薄的破衣服时,竟露出了那不变的微笑来。”这时,我总会想到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想到一大片金黄金黄的麦田和一群可爱的孩子。我喜欢三毛的“万物静观皆自得”的心态,我喜欢做个稻草人,我喜欢做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走出撒哈拉的三毛面对着残酷的现实,厮守六年的亲人被上帝无情地收回,不晓得梦里花落多少,不晓得不死鸟身在何处,只能在生与死的夹缝与早逝的亲人梦幻般地短聚,然后再去清醒地承受那痛彻心扉的思念,万水千山走遍也无法摆脱。千万年,千万人,千万言,理不清,道不明,说不完的一个情字在这个台北女子的笔下可以让人哭,让人笑,让人沉思;或惋惜,或惊喜,或悲痛。我认为不光是这个传奇般女子的灵异魅力,更是因为荷西。我常想,没有荷西,或许就不会有三毛。荷西和三毛自己共同创造了人们心目中的三毛。前两天晚上睡不着就去翻《三毛全集》,翻到篇文章叫《说给自己听》。忽然觉得这五个字几乎可以概括她的全部作品。她在用情地自言自语着。她是一个任情而动的女子。她自爱,自恋,她用文字创造了一个纯属自己的情感世界。而我们,她的读者,哭哭笑笑,或许她并没在意过,因为太专注。三毛和她的文字终于渐渐地成熟了,深沉了。所以我更爱后期沧桑的三毛,爱听后期平静的三毛。《背影》、《爱和信任》、《雨禅台北》。这三篇文章使我在痛苦于两代人之间的难以沟通和无法妥协,困惑于责任与自由的矛盾的时候,不至于过分地自责和无助。我曾经不懈地追问过生命沉重的意义,曾经呐喊,曾经彷徨。终于悟了。生活本是一捧水,我们用指缝感受着它的重量;若没了重力,恐怕也就没了所谓的意义。生命正像西西弗斯的神话,因苦难而绚烂;生活正像稻草人的微笑,平凡而丰富。所以,当听到有人说三毛就是个言情作家的时候,我总是不屑一顾。
电影《滚滚红尘》我看过四五遍,可还是看不够。除了林青霞、张曼玉和秦汉的出色表演,除了那是在演绎张爱玲的乱世爱情,除了罗大佑那首让人柔肠百转的 《滚滚红尘》。还因为这个电影的剧本是三毛的绝笔。我从韶华凄然的眼神中总会有看到的了三毛的感觉。
有人说,死亡是一种解脱。可是活着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解脱呢?生与死瞬间的较量,她却做出了让万万千千的人扼腕叹息的选择。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想念稻草人的微笑,想念三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