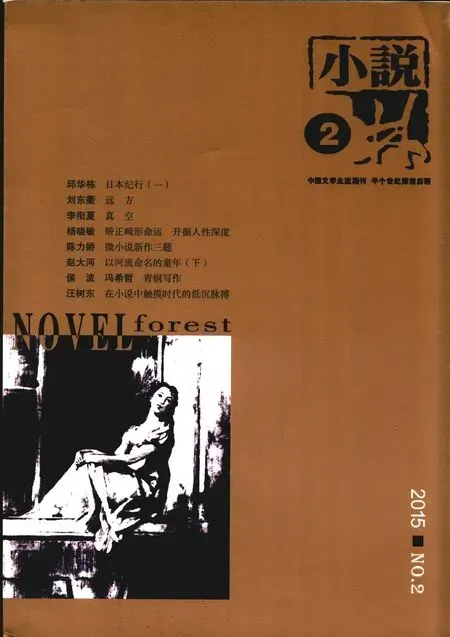微小说新作三题
◎陈力娇
微小说新作三题
◎陈力娇
第二条路
战争打得很苦,一个连的兵力被吞噬。敌人的炮火还在猛攻,连长举着望远镜,对身边的丁二娃说,活着是出不去了,看看我们是文死还是武死吧。丁二娃的一只耳朵已经被削掉了,一圈绷带斜缠在脑门和下巴上。他问连长,文怎么讲?武怎么讲?连长放下望远镜,掏出烟,指指身后的山崖说,看到了吧,那有一线天,不怕死就从那攀上去,或许有救;还有就是做假投降,等敌人上来和他们同归于尽。
丁二娃想了想,说,听你的,连长,我这命,活着是你的,死了是阎王的。
连长听了丁二娃的话,把烟放在嘴里要嚼,他找不到火,浑身上下没一根火柴。丁二娃看了,忙跑到不远处一棵烧焦的树桩,拾过一块木炭。
连长高兴了,拍着丁二娃的肩说,好小子,下辈子若带兵,我还带你。
丁二娃嘿嘿地笑,黑一块白一块的脸,到处是憨相。
鬼子的又一轮冲锋开始了。这回比上一次还猛烈。众多的迫击炮,把他们身后的树都炸飞了,他们躲在掩体里,一层层泥土落了一头一脸。
丁二娃说,妈的,鬼子可真坏透了,连棵树都不给留。丁二娃指的是山崖前方,从岩缝里长出的那棵松树,如果它不被炸飞,攀着它正好能上一线天。
连长可没丁二娃的心思,他在往腰间绑手榴弹,十几颗手榴弹被他依次捆在内衣里。连长瘦,穿上衣服和没捆一个样。
丁二娃也想像连长那样往腰间捆,可是办不到,没有了,他除了有七颗子弹,别的什么都没有了,这让他很沮丧,一身的力气没处使,只等着送死。
山上起雾了,五十米之外看不见人,只有一股股风吹过的时候,鬼子猫着的腰身才露一下,但马上又像两片幕,迅速合上了。
连长捆好手榴弹,他回过头对丁二娃说,娃子,你上一线天吧,全国解放那天,你给我立个碑,也好在人世留个念想儿。丁二娃听了连长的话,啪地打了个立正,连长,丁二娃誓死和你战斗到底!
连长的眼睛湿了,他咬咬嘴唇,又一次拿起望远镜,看到小鬼子如同水中的船,正互相乱撞。连长说,二娃,看到了吗?鬼子再前进二十米,你就到掩体的北侧打枪,打两枪后,再到掩体的南侧打枪,动作要快,迷惑敌人,让他们摸不清我们的人数。二娃点头,并做好准备。
鬼子越来越近了,前一排已经直起了腰身。
二娃,把前边那个军官干掉,连长说。二娃躲在树后,只一抬手,那个军官应声倒下。二娃退下来,跑向南边的阵地,还是手起枪落,又一个鬼子应声倒下。
鬼子开始小心了,他们由站着迫近改为匍匐前进,而二娃的子弹也快用完了。
二娃只有在死去的战友身上寻找武器,正翻着,就听连长哼了一声,之后倒在了他的脚下。二娃看到,一颗子弹,正中连长的眉心,就像小时候,妈妈在姐姐的眉心点上个小红点。
妈的小日本!二娃向着鬼子的队伍甩了两枪,可是子弹太贵重了,就剩三颗了,由不得他浪费。他勉强在一战友身下翻出一颗手榴弹,迅速抛了出去。随着轰隆一声巨响,二娃突然改了主意,何不趁机逃跑,逃跑可比和敌人同归于尽更有赚头。二娃看一眼连长说,连长,反正你也死了,我就不跟你去了,我会给你报仇的!他把刚才对连长的许诺忘得一干二净。
二娃双手遮住嘴巴对着鬼子喊,别开枪,我们投降!
二娃又喊,我们身上都捆着手榴弹,你们若开枪,就连你们一起炸飞喽。
鬼子真就没有开枪,但也没有向前半步,二娃趁机把连长抱起放在战壕沿上,只露出上半身,两边用战友的尸体支撑着。
一杆步枪被二娃插在地上,二娃脱下自己的白衬衣挂在上面,白衬衣带着血迹十分醒眼,在连长的头上飘呀飘。二娃说,连长,莫怪我呀,我这也是万不得已呀,都做鬼了谁还来打鬼子啊。二娃极力把道理说得更像道理。
连长好像听懂了,他的头一直傲立着,不偏也不倒,两眼怒目圆睁,身旁的战友也簇拥着他,如同抬一顶轿子,去和小日本算账。阵地静了下来,小鬼子在一步步靠近,而这会儿的二娃,已经不在连长的身边了,他凭着一身好功夫,两腿蹬住崖壁,双手倒换着,一点儿一点儿攀上一米宽、二十几米高的一线天。
几乎是一眨眼的光景,也就三五分钟吧,鬼子上来了,他们战战兢兢、层层叠叠围住了连长,判断他是否还活着,就在他们举棋不定,想上前试试连长还有没有气息时,不知从什么方向,射来三枪,一枪打死鬼子为首的军官,一枪打翻了想试连长是否还活着的那个士兵,而第三枪则打在连长腰间那捆手榴弹上。
顿时,数声爆炸,火光冲天,一朵朵红蘑菇瞬间绽放,染红了半个阵地。
烟雾弥漫了许久,少数从地上爬起来的鬼子,稀里糊涂地听到不远处的一线天方向,传来野狼一样的哭声,那声音撕心裂肺,痛苦悠长,可是他们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只是哭,而没再对他们形成任何威胁。
尊重
她的妈妈是个侏儒,她的爸爸是个瘸腿男人。而她却出奇的好看,且有一副百灵鸟的嗓子。
县里文工团招歌唱演员,她去了,一镖中的,录取了。接下来是追求她的男人成群结队。老团长说,你可别被胜利冲昏头脑,这个世上的男人都是苍蝇,你如果是“天仙”,他们就不叮你了,事业为重。
她把老团长的话记在心里,每天刻苦练功,精心钻研,力争做个天仙。
做天仙容易也不容易,容易的是业务上心无旁骛,不管窗外事,把那些男人关在“心”外,就没人骚扰了;不容易的是巨大的寂寞,空洞一样让人难以忍受,每早她都练嗓,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吃饭把饭菜打到寝室吃,一边吃一边琢磨五线谱,不到一年,她的乐理和唱功全团第一。
老团长对她的要求也是步步紧逼,学通了五线谱,又让她学钢琴,这可是个尖端的行当,别人学钢琴都是四五岁开始学,她都二十岁了才想学,团里的男男女女开始对她嘲笑了。
老团长不管这些,老团长说她悟性好,二十岁学和四五岁学一样,结果她用了三年的时间,把钢琴的技艺又推向了顶峰。这三年的辛苦只有她自知,她除了正常的演唱练唱,其余时间全用在了学钢琴上。最终的结果是,她自弹自唱,全场观众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艺术到了顶点,老团长也要退休了。看着老团长花白的头发,她落下了眼泪,老团长爱惜地看着她,说,哭什么,人都有这天,人若没这天,新生力量怎么登场,新生力量不登场,艺术怎么能前行?
她知道老团长这是安慰她,她不知道老团长离开她后,她还能不能做得了天仙,就泪水涟涟地和老团长说,我还想做天仙,我能做到吗?老团长摇摇头,半晌说,别做了,太清苦了,而且你的年岁也大了,二十四五岁正是找伴侣的好时段,回到人间吧。
老团长的话在理,说完这些,老团长就解甲归田了。
老团长走后,她的处境就变化起来,嫉妒她的人倒没多少,“爱”她的人却络绎不绝。她这才明白,老团长在实力上的重点培养,为她扫清了多少日后的障碍,人到了让人嫉妒不了的时候,她的本事不是超群,就是太过于完蛋。显然她属于前者,所以她事业的道路挺顺,而不顺的是情感。
情感由清淡变浑浊,出于一个原因,就是她没有了护身符,或者说没了指引。
老团长在时,一切都不用她考虑,老团长就像一个大围巾,为她挡住了风寒,那些想亲近她的人,一看这围巾的威力,没人敢轻举妄动。而现在不同了,现在那些男人都疯了,叫小骚的那个萨克斯手甚至把她堵在洗手间,吻了她。
更可恨的是这些男人中,有不少还是已婚,他们手牵着媳妇,眼睛却在她的身上瞄来瞄去,王小毛甚至拿演出要挟她,如果她不答应嫁给他,他就在县领导来看演出时,拔刀自尽。
王小毛神经质,他说他什么都干得出来,她害怕了。晚上在食堂里吃过饭,她去拜访老团长,实则是让老团长帮帮她。
老团长正和老伴在灯下修古筝,他的老伴一辈子热爱古筝,一辈子都想进剧团演出,只是老团长太正直,太认真,也就一辈子没让她进剧团。奇怪的是,她的老伴一点儿都不怪他,她说她的艺术在心里,在哪里都不耽误音乐的流淌。
她敲响他们的门时,老团长已经笑盈盈等在门前了。老团长说,我就知道你会来。老团长这句话,让她顿时泪眼婆娑。老团长却笑,说,好办好办,不就那几个毛贼吗,要想制服他们,就得知道他们的本质是什么。
果然老团长把自己的计划一说,她破涕而笑。
在老团长和夫人的建议与协助下,她开了个人演唱会。每唱一首歌,说一段成长的故事,或是自己的,或是别人的;或是经历的,或是看到的,然后由这个故事派生出相应的歌曲,观众听得热泪盈眶,掌声如潮如浪。
她就是一本书,她的成长道路就是一本书。和别人不同的是,她这本书,从初起到完成,都有老团长的批注。她把这个意思传达给观众,观众都肃然起敬,小县城太小,谁都知道谁,老团长早就是他们心中最敬重的人。
演唱会结尾,她请出了自己的父母,这是意想不到的亮点,全场的人顿时目瞪口呆。她的侏儒妈妈一个劲给大家鞠躬,她的瘸腿爸爸勾着头只看自己的脚,她坦然地、落落大方地、声情并茂地介绍了她的身世,介绍了她的父母在乡间低矮的屋檐下,一点点把她拉扯大,她说她的音乐启蒙,就是她的侏儒妈妈为她哼唱的摇篮曲,哼着哼着她就长大了,侏儒妈妈望着比自己高一半儿的孩子,停止了她的哼唱。她说,以后的歌,由你自己唱了。
她的故事讲完了,全场静止了足有一分钟,之后唏嘘声和掌声一同响起。
演唱会开得很成功,从此她的身前身后,没有了那些纠缠不清的人了,她明白,是她的侏儒妈妈起了作用,侏儒妈妈为她唤回了人类最本质的尊重。
四重奏
一人家五世同堂,太太姥姥,太姥姥,妈妈,女儿和小外孙子。
他们每人递减二十五岁,依次排列,排到小外孙那儿,刚好五个月。
太太姥姥年龄最大,今年整一百零一岁,她没有牙,牙都脱光了,嘴巴揪成个包子口儿,给她做了一副假牙,她说什么也不戴,理由是,没看见谁没了牙,去用别人的牙,这是从哪个死人嘴里撬出来的?说着哭了起来,嫌家人慢待了她。
太姥姥看自己的妈妈这样,也不去劝她,她知道她的脾气不好,越劝越上样儿,就把自己的假牙纸包纸裹放在柜底,把妈妈的牙拿过来戴在自己口里。她想,戴坏她的,再戴自己的,不能让钱白花了呀。
假牙毕竟不合她的口,她的牙龈磨出了血,她的女儿看到她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一把抢过来,吼道,妈,你老糊涂了,不知这是有尺码的吗?
看女儿暴跳如雷,当妈妈的只有不吭气,但她拿准主意,等牙龈好了,她还用它,就跟鞋子一样,穿着不合脚,磨出老茧就好了。
她们这样,有一个人一边奶孩子一边笑,这个人叫小旧,是小外孙子的妈妈。小旧性格好,不参与她们的争斗,像这样观念不同的事,每天都发生,她管得过来吗?再说了,那样的仅仅是她们,那是整个旧时代呀,一个人再有能力,能矫正一个时代吗?
可是小旧不矫正她们,并不一定她们不矫正小旧,事情就发生在小旧出国上。
小旧出国是没办法,她在单位里是会计,单位在国外要考察新项目,这不是领导一个人能办的事。小旧只有把孩子托付给妈妈,启程了。
小旧走,首先提出抗议的是儿子小新,小新自出生从没离开过妈妈,现在由姥姥抱着他不踏实,他一定要找妈妈,他的方式就是哭,哭得山摇地动。小旧的妈妈抱着他满地乱走,急得满身是汗,她说,这可怎么好,你妈妈是出国,这会儿还没到呢,那可不是说回来就回来的。
小新可不管这些,他没死拉活地嚎,不把妈妈嚎回来他绝不罢休。
小新一嚎,太太姥姥说话了,她质问自己的孙女:你就不能把他放那儿,哭不死的孩子,饿不死的狼,哭够了他就不哭了。小新的姥姥想,你倒是想得好,哪有那么简单,现在的孩子个个娇惯得跟爹似的。
见孙女没听她的,她就指派自己的女儿,你去,把他剥光了,晾在那,冻死他,不信还治不了他了。说着想撇手中的烟袋锅子,这是她二十岁时就不离手的武器。
小新的太姥姥不敢不听母亲的,她劝自己的女儿,孩子哭哭好,我生你时,刚迈门槛你就落地了,你哥哭了一整天,亏了他哭,他不哭,我哪知他还活着。
小新的姥姥瞪了自己母亲一眼,把孩子抱到另一个屋去了。
小新像是听明白了太姥姥的话,他的哭声减弱了,但他也有绝招,不吃奶,奶瓶放在嘴里,他就用舌头顶出来,或者咬住,任奶流出来,敢情小家伙绝食了。
持续到第二天,小新的太太姥姥吃不住劲了,她说,孩子不吃奶,就是“紧牙关”了,用两根筷子在他的舌底下按,不愁他不吃奶。听自己的妈妈这样说,小新太姥姥对女儿说,我看是起“马牙子”了,火大,他妈妈走他能不上火吗?小新的姥姥问,那怎么办?小新的太姥姥说,弄一块新黑布,蘸白矾,蹭牙床,火就出来了。小新的姥姥将信将疑,但她还是决定试试。
白矾弄来了,黑布也弄来了,把白矾压成面,三个老太太开始对付小新,由小新的太姥姥把小新放在膝盖上,小新的姥姥把住小新的头,没死拉活地蹭。不一会儿,小新的嘴角淌出了血沫子。小新姥姥说,行了,妈,再蹭蹭死了。小新太姥姥回答,死什么死,你们哪一个不是这么过来的。
理是这么个理,但是这是新时代呀,新时代的孩子你听谁这么处理过。
小新的姥姥终于挺不住了,她拉住了妈妈的手,让她停下。谁知太太姥姥不让了,她开始用筷子为小新松舌底,一边松一边说,都是富裕生活惯的,在早那孩子,见奶就跟见命似的。太太姥姥戴着老花镜,哆哆嗦嗦地在小新的嘴里一阵乱捅。
可是尽管她们忙了半上午,在哭喊中疲惫不堪的小新,还是不吃奶,不但不吃奶,还发高烧。这时太太姥姥又说话了,放放血,放放血他就不烧了。小新的姥姥不明白,用眼神问她的妈妈。她的妈妈告诉她后,她明白了,就是用针在孩子的心口窝扎七针,然后用火罐拔,把毒血拔出去。这太残忍了,小新的姥姥再也没听她俩的,抱起孩子去医院了。
小新在医院里住了三天,病好了,也吃奶了,也不再哭了。小新的姥姥就很后悔,后悔外孙子遭了那么多的罪。医生听说后也说,那是扯淡,一百多年前的人,怎么赶得上现代医学。又查看小新的舌底,忽然说,舌弦断了,不及时修复,孩子长大会“秃舌子”。说完又一锤定音:所以呀,人不能总活着,总活着,现代文明就得让他们糟蹋完了。
一回头,小新姥姥晕过去了。
在《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北京文学》等文学报刊发表作品300余万字。已出版长篇小说《草本爱情》,中短篇小说集《青花瓷碗》《非常邻里》《平民百姓》等,小小说集《不朽的情人》《赢你一生》《爸爸,我是卡拉》等。作品多次获奖,多次选入各种版本或被选刊转载,部分作品国外发表。其中《一位普通母亲与大学生儿子的对话》获2005年“全国读者最喜爱的微型小说”奖;2008年获中国新世纪小小说风云人物榜·新36星座奖;小小说《败将》荣获第12届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2012年获黑龙江文艺奖;2011年荣获全国“第五届小小说金麻雀奖”。
陈力娇,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和上海复旦大学作家班。黑龙江省萧红文学院签约作家,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