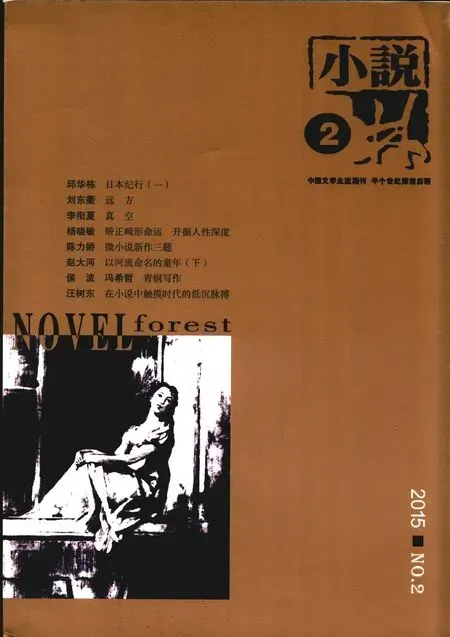母女亲情的畸形悲剧——评雨桦的中篇小说《母女》
◎欧阳澜
自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之日起,父子关系和母女关系就分别是男作家和女作家最乐于书写的两种人情,文化批判和人性考量、政治归属和性别歧异等因素自然会附着其上,构筑出极为丰富复杂的文学景观。父子关系且不说,单表母女关系。五四时期,苏雪林、冰心、庐隐、冯沅君等女作家大都讴歌纯洁丰盈的母爱,致力于书写母女关系的温情一面,表达着对父权制权威的疏离和批判。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笔下,母女关系的复杂性开始呈现,《金锁记》《倾城之恋》《花凋》等小说中母女相仇纠缠不休的噩梦场景层出不穷。20世纪90年代以来,张洁、王安忆、铁凝、徐小斌、徐坤、池莉等女作家笔下的母女关系更是波诡云谲,彻底颠覆了五四时期那种清新单纯的母女关系,展示了人性的多彩戏剧。时代在前进,文化在变化,母女关系的人间戏剧依然在演绎着。雨桦的中篇小说《母女》就聚焦于当前中国社会中一个单身母亲和独生女儿之间的感情悲剧,叩问着人性和时代文化的症结,呼唤着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家庭的和谐。
该小说中的母亲梅姐,原名梅艳芳,父亲是个大字不识的环卫工人,为其取名艳芳,无非是希望她的人生像鲜花一样鲜亮美好。但梅姐在工厂当工人时,就被师傅强奸,未婚先孕,不得不离开自己所爱的人,和师傅结婚。婚后,丈夫对梅姐非常不好,非打即骂,幸好他不久便醉死了,梅姐才能和不同的男人来往。女儿席小雯从小对母亲和各种男人的来往深感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心灵备受伤害,母女间缺乏基本的信任和亲密,就像陌生人一样。由于是单身母亲培养独生子女,梅姐也经常对席小雯横加干涉,例如当席小雯在中学谈恋爱时,梅姐就无端阻止。等席小雯离开家乡青岛到北京读大学时,她便很少回家,连电话也懒得打。大学毕业后,有机会也没有回青岛工作,而是追随男朋友一起去了上海。在爱情失败之后,席小雯才于无奈之中回到青岛工作,但依然无法和梅姐友好相处,对她不顾年龄不停地和不同男人交往的状况更是鄙薄不堪。席小雯和原来的中学同学易彬结婚后,依然怀念着原来的男朋友,没有办法适应婚姻生活,也不愿意生孩子。最后她从梅姐口中得知,原来她和易彬结婚还是梅姐从中撮合的,这让她极度失望,决定和易彬离婚。
要理解梅姐和席小雯这对母女的纠结情感,自然要追溯梅姐的个人生命史。在席小雯和易彬结婚后,两人无法共同生活,梅姐便质问席小雯为何如此,席小雯倒是反问她为什么结婚后反而和别的男人睡在一起,于是梅姐就把她当初是如何被师傅强奸的实情告诉了女儿,并为自己的悲剧命运辩护道:“我是想告他强奸我,那我还能生存下去吗?我还能嫁人结婚吗?你以为我们那个时代可以想爱谁就是谁吗?我唯一的出路就是嫁给他,我以为有了孩子,他会像他承诺的那样对我好,事实上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而己。婚后,他不但对我不好,稍有不满张口就骂举手就打,打牌,喝酒,抽烟……家里的钱都让他输光了。那天早晨,他打完我,我就含着眼泪去上班了,谁知他一个人在家喝酒,喝得太多,最后,喝死了……”
可以说,这段倾诉是理解梅姐悲剧的关键。她的悲剧最直接的起因无疑是那个先强奸了她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师傅。这和个人的欲望过度、不知节制、不知尊重他人、品德堕落有关。当然也和那个时代整体氛围有关。那就是社会氛围较为封闭,弱者无处诉求公道和正义,强者凭借专制的权力肆意妄为,人们没有更多主宰个人命运的自由空间。在这种社会中,像梅姐这样的弱者又会有什么样的出路?肯定不可能有人对她进行精神和道德的启蒙,启发她去理解生命的目的、理解社会的运转、理解历史的大道,并进而发现内在生命不可磨灭的自主和尊严。她只能依凭着自然性情像流水一样不断地向卑下处流去,为了生存,为了获得一点欲望的享乐,而把道德伦理抛诸脑后,一步步走向卑俗的深渊。因此,只要有可能,她就会找不同的男人,从他们身上获得财物和放纵之乐,并由此形成得过且过的享乐主义人生观:
“就算她们瞧得起自己,梅姐也不屑于她们那种老妈子似的活法,每天柴米油盐,养完了儿子养孙子,养完孙子,自己却没人养了。人活一世,太可悲了,莫不如好好享受自己的余生,她从来不指望席小雯对她有多孝顺。”
“就像现在,自己虽然单身多年,但并不缺少快乐,爱情时刻都来找她。五十多岁的女人,每天都能享受到不同男人的爱慕,也是人生的一大风景。”
她甚至对自己的女儿这样说道:“你那是书读多了,忧国忧民,我呢,大字不识几个,自己活得开心就行了,想那么多干嘛?人活一辈子,不就是吃喝玩乐吗?不就是有男人疼男人爱男人宠吗?我要的就是这个。”
该小说中的梅姐形象就是定位于这样一种粗俗的享乐主义者形象。单就个人的选择而言,像梅姐这样的享乐主义也是令人鄙视的。享乐主义者的错误,关键在于侮辱生命的尊严。人生在世,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都不是为了享乐而来的。生命有其内在的使命和尊严,那就是要实现生命的潜能,实现生命的创造性。享乐主义却把生命变得极为狭隘和鄙陋。享乐主义者终究会沦陷于虚无主义的泥沼中。当然,像梅姐这样的享乐主义,在当前消费主义社会中,也是国人的一种普遍状态,显示的乃是国人的沉沦和鄙俗。作为母亲,梅姐这种享乐主义人生观更使得她在女儿席小雯眼中显得粗俗,斯文扫地。
当然,梅姐毕竟是一个中国母亲。无论女儿席小雯多么不耐烦她,也无论到了五十多岁还有多少男人和她来往,她终究还是在情感上依赖女儿。因此小说写道:
“可是,和席小雯在一起那种感觉,终究是与那些男人不能代替的。梅姐对席小雯没有奢求,只要能常常回来看她一眼,那种喜悦就会长久地停留在内心,使她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充实,欢快之感。”
“毕竟,年龄渐大,她需要一个依靠,虽然梅姐的老年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但席小雯离开她在上海的这三年,还是让她有种无依无靠的感觉。那种感觉就像独自漂在海上的一片树叶一样孤单。梅姐也在席小雯面前不止一次说过老了不用她管的大话,但是,到头来,梅姐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内心对席小雯的依赖越来越浓。”
这就是中国母亲的心理。由于大部分中国人没有真实的信仰,无法发现自己生命中不可摧毁的真理,在儒家伦理的长期熏陶下他们往往就倾向于在子女身上去寻找生命的寄托。如果说传统中国人更倾向于祖先崇拜那么当前家庭核心化后,大部分中国人无疑更倾向于子孙崇拜。无论祖先崇拜,还是子孙崇拜,都是把有限当无限来崇拜的偶像崇拜这种偶像崇拜,无疑会颠倒生命的价值等级造成生命的混乱无序。
没有真实的信仰,人就不可能确立生命的主体性,他就只能颠簸奔波于客体化的异化世界。像梅姐这样的母亲没有自己的生命主体性,她就不能理解和尊重其他生命的主体性,因此她会去干涉席小雯中学时期的恋爱,在席小雯读大学时带男同学回家她也会反对,最终又撮合席小雯和她明明不感兴趣的易彬结婚。梅姐打的旗号,就像所有没有真实信仰、缺乏主体性的中国父母打的旗号一样,都是“为了你好”。其实,所谓的“为了你好”,说到底乃是这样的父母没有实现自己的生命目的,隐隐地感觉到自己生命的空虚和无聊,然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弱势的子女而已。这是最可怕的自私,是最可怕的生命劫持。在这种情势下,弱势的子女如果屈从于强势的父母,就会终生不幸。生命获得幸福的基本前提,就是他具有自由意志,能够自由选择。而在这种中国式的父母和子女关系中,子女的自由意志恰恰是被否定的。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席小雯不断地从母亲梅姐身边逃离,一方面自然是要逃离梅姐的粗俗和鄙陋,另一方面也是要逃离梅姐的控制和干预,维护独立个人的自由空间。
相对于梅姐形象而言,席小雯形象在该小说中更为单薄一点。作家在塑造她的形象时,偏重于动作的叙述,而缺乏内在心理的足够开掘,也没有赋予多少深刻的人性内涵。不过,我们在字里行间依然可以看到这个80后的年轻人的些许时代特征。她成长于物质较为丰富的时代,生活工作于城市里,从小就被单身母亲教导着只需专注于学业获得好成绩就万事大吉。因此她没有多少为人处事的能力,对母亲梅姐缺乏理解的兴趣和能力,刻薄寡恩之处比比皆是。后来和男朋友许威分手,许威曾对她说:“除了你自己,你谁也没有爱过!”就连她自己也认识到她“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别人”。这是一个存在严重心理疾患的病态之人,是一个在世俗化的小时代里长大的没有精神追求、没有理想的尼采所说的“末人”。她回到青岛后轻易地答应了易彬求婚,婚后又固执己见无法生活,最后又断然决定离婚,都显示了她的自私本质和生命深处的迷茫。
该中篇小说比较出彩的地方是对梅姐和席小雯这对母女之间那种撕裂、纠缠、欲言又止式的情感纠葛的细腻书写。例如小说写到席小雯要离开青岛到北京读大学,梅姐舍不得她离开自己,深情不由得自然流露,但是席小雯却故意表示疏远。“梅姐仰脸,微愕地看着席小雯,突然,她伸手抱住席小雯,哭出声来。席小雯的手僵直了一下,片刻,只是象征性地拍了拍梅姐的后背,就将她厌恶地推开。好像抱她的不是养育自己近二十年的母亲,而是任何一个陌生的与她毫无相关的女人。推开梅姐的那一瞬,她看到梅姐的身体有些颤抖和摇晃。但席小雯制止了心里涌上来的温情与难过。她不习惯与梅姐这样亲近。因为从来没有亲近过,显然对于梅姐这样的煽情,除了拒绝外,无所适从”。这样的细腻书写让小说增加了较为难得的艺术韵致。
整体看来,该小说叙述较为生动细腻,人物塑造较成功,选材也富有现实意义,是一部较为优秀的小说。不过,在主题开掘方面,尚存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贾平凹曾对作家说:“你在写一个人的故事和命运的时候,他个人的命运与历史、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交叉的地方的那一段故事,或者个人的命运和社会的命运、时代的命运在某一点投合、交接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这个点,这样的个人命运,也就是时代的命运,是社会的命运,写出来就是个人的、历史的、社会的。一定要学会抓住这个交接点,这样写出来的故事才能引起大家的共鸣。”的确,一部好小说必须找到个人命运和社会命运、时代命运的交接点,或者能够像张爱玲那样能够往人性的深处挖掘,这样才能获得较为丰富的意蕴。像《母女》这样的小说在通过个人命运透视社会命运、时代命运,或者在个人身上挖掘人性的深层内蕴等方面,还是可以做出更多探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