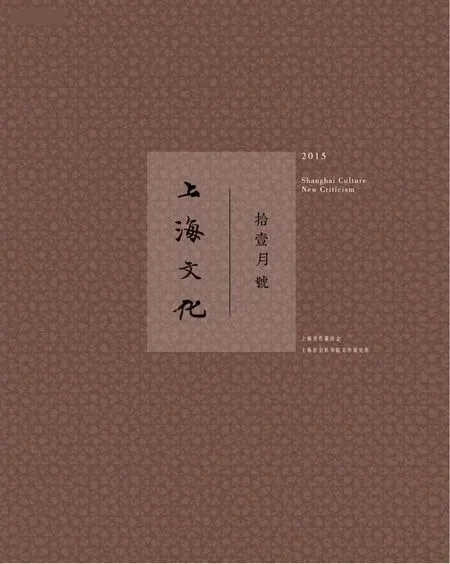传说与伪造的分野重读1930—1931年钱穆与顾颉刚“刘歆伪经”之争
王尔
传说与伪造的分野重读1930—1931年钱穆与顾颉刚“刘歆伪经”之争
王尔
民国十九年(1930年),史学界诞生了两篇别有意味的文章:五月,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刊载于《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六月,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刊于《燕京学报》第七期。《刘向歆父子年谱》的成文早于顾颉刚文,因为顾颉刚写《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时,已经参考了《刘向歆父子年谱》,对此,顾文有明确的标注。此时,钱穆还是无锡的中学教师,而顾颉刚已经是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带出了1930-1931年钱、顾两人对古史、今古文经学一系列问题的辩论。
两篇文章的出发点不一样。钱穆在《刘向歆父子年谱自序》和《〈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中,两次述及他的这篇文章是针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专主刘歆伪造古文经之说”而作的,他分析了长期以来今文经学者“谓歆伪诸经以媚莽助篡”之说“人易信服,不复察也”之后,说:
南海康氏《新学伪经考》持其说最备,余详按之皆虚。要而述之,其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
基于此,钱穆对“刘向歆父子年谱”的编写,处处含有反驳“伪经”说之意。但他不为反驳而反驳,澄清真相才是他真正的学术目标,他说:“本书之所用心,则不在乎排击清儒说经之非,而重在乎发见古人学术之真相。亦唯真相显,而后伪说可以息,浮辨可以止。”这是他作《刘向歆父子年谱》的用心。
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则旨在讨论从驺衍五德终始说到《世经》之说的“政治与历史”。也涉及西汉政治、刘向父子、刘歆作伪经、古今文经学等一系列问题。虽然顾颉刚说:“我很佩服钱宾四先生,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寻出许多替新代学术开先路的汉代材料,使我草此文时得到很多的方便。”他在文中却屡屡提出与钱穆针锋相对的观点。钱文与顾文有各自的研究目标,但涉及的内容又互相交叉,而且两文的核心观点颇为针锋相对。两篇文章观点的冲突显示着当时学术界在古史问题、今古文经学问题上的复杂态度。实际上,在论辩过程中,又可看出,钱、顾的历史观念和研究方法其实是一致的。
一
《刘向歆父子年谱》用年谱的方式记叙了从西汉昭帝元凤二年(刘向出生)到王莽的新朝覆灭这近百年间重要的政治事件,以刘向、刘歆父子的生平事迹为主线索,以“月”为时间段,详细记述这近百年每月间发生的事情。比如:
地节二年,癸丑。(六八)
向年十二,以父德任为辇郎。
霍光卒,
龙胜生。
地节三年,甲寅。(六七)
六月,魏相相。
霍禹为大司马。
此处还援引《汉书·张禹传》为证。《年谱》经由刘向、刘歆父子及相关人物生平事迹记录,客观地呈现刘氏父子在生之年的所作所为,时间和事件的坐实,直接间接地反驳了康有为、崔述等人“谓歆伪诸经以媚莽助篡”的观点。诚如钱穆在《刘向歆父子年谱自序》中详细对照刘氏父子年谱,一一举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有二十八处“不可通”。如:“向未死,歆已编伪诸经,向何弗知?不可通一也。”这二十八处“不可通”中,最重要的,是证明《周礼》、《左传》诸经书于事实、于情理皆不可能为刘歆所伪造,刘歆不可能为了“媚莽篡汉”而去造伪经书。钱穆说:“此姑举其可略论者,其他牵引既广,不能尽辨。余读康氏书,深疾其牴牾,欲为疏通证明,因先编《刘向歆父子年谱》,著其实事”。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份年谱中,钱穆以“按”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历史的评述。这些评述蕴含一种深刻的历史理念:王莽的新朝,不是王莽、刘歆等人简单、刻意地伪造经书篡夺来的,而是西汉元帝、成帝以来政治学术风气之推演、汉末儒生之共同推拥的结果。正如文中评论元成以来的学风时所说:
时学者可分两派:一好言灾异,一好言礼制。言灾异,本之天意。言礼制,揆之民生。京房、翼奉、刘向、谷永、李寻之徒言灾异,贡禹、韦玄成、匡衡、翟方进、何武之徒言礼制。……莽、歆新政,托于符命,则言灾异之变也。其措施多慕古昔,切民事,则言礼制之裔也。然亦盛誇饰,兼习武、宣遗风。史言王莽兴辟雍,欲耀众庶,而必谓成帝、刘向意在美教化,何也?弃虚文,循实迹,则莽之兴辟雍,其议端自刘向开之。
钱穆认为,新朝是元帝以来“言灾异”与“言礼制”两派共同发展、互相渗透制约的结果,甚至还带有武帝、宣帝时期的遗风。新朝的政治不是简单地由刘歆伪造经书便能够搭建起来的,它是元成以来历史时代自然而然的生成物。论及哀帝绥和二年下诏除任子令等制度,钱穆评道:
除任子令,创议自王吉。止齐三服官作输,出嫁掖庭宫人,免官奴婢为庶人,贡禹皆已言之。制节谨度,追复古礼以恤民生,自元帝以来,王(吉)、贡(禹)、韦(玄成)、匡(衡)诸儒迭唱之,今乃见诸诏令也。
可见,汉末至王莽时期“追复古礼以恤民生”的现象,是由“汉自元、成以来,儒者言礼制,美古昔,于武、宣所兴颇有矫革”的风气渐渐形成的。钱穆下面这一句话,对我们理解新朝是如何建立的,独具启发性意义:
莽之创制立法,亦皆远有端绪,当自元、成以下汉廷诸儒议论意态推迹之,不得谓由歆伪诸经,乃有新莽一朝之制度也。
这一观点与他在《秦汉史》中所言“王莽所抱政治理想,亦自此等时代及时代思潮下酝酿而来”相一致。这一观点如果成立,刘歆伪造诸经书就失去“媚莽篡汉”的理由,王莽代汉亦不甚需要刘歆去伪造经书才实现。若刘歆学派实有造伪,也是当时政治学术风气推动所致。需要指出的是,钱文在反驳康有为“伪经”说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发见古人学术之真相”,“亦唯真相显,而后伪说息,浮辨可以止”。这里的“浮辨”指谁?指什么?从紧接着钱穆对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一文的批评看来,这句话并非泛泛之言。
二
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主要讨论“五德终始说”在西汉到新朝的发展流变情况。在交代了战国邹衍对五德终始说的创立、汉初信奉的水德如何转变为汉武帝信奉的土德后,顾文从《〈世经〉的出现》一节开始,重点讨论《世经》的问题。《世经》出现于刘歆的《三统历》中(见《汉书·律历志下》),所记载的尧帝火、舜帝土的古史系统,都极有可能是汉末刘歆及其学派的伪造。顾颉刚用很长的篇幅讨论:汉武帝之后为什么出现汉代受命火德的呼声,《世经》所展示的前所未闻的古史系统以及它与汉受火德的关系,“汉为尧后”说以及尧帝与火德的关系,王莽“火德销尽,土德当代”的篡汉理论等。顾文的核心观点是:汉受火德说(包括《史记》中记载刘邦赤帝斩白蛇一事)、汉为尧后说、《世经》为了让王莽(自称土德)篡汉比附于舜帝(土德)接受尧帝(火德)的禅让,伪造了从伏羲(木德)、共工(闰水)、神农(火德)、黄帝(土德)、少皞(金德)……到汉高祖(火德)的古史帝系。在这个帝系中,五行相生,王莽称帝实属受命于天——为王莽篡权提供合法性根据。这种造伪,构筑了以后百年来不易的古史帝系,顾颉刚说:
(《世经》)这篇文字,是中国上古史材料中最重要的一件。二千年来的传统的上古史记载以及一班人的上古史观念,谁能不受它的支配!虽是从我们的眼光里看出来是七穿八洞的,但要是我们生早了若干年,我们便未必能看出;就使看出了也未必敢这样说。这便叫作权威,叫作偶像!
与钱文最为针锋相对的是,顾文基本支持刘歆“伪经”说。他称:
康长素先生的《新学伪经考》、崔觯甫先生的《史记探源》,抉出刘歆作伪之迹,使学术界中认识新代的学术及其改变汉学的情状,自然是巨眼烛照。
尽管顾颉刚也指出康氏“把这个改变的责任一起归在刘歆身上,以为都是他想出来、造出来的,未免把他的本领看得太大”。“现在《世经》之说把驺衍的五德终始说彻底改造,而又为后世所遒用,是其所积之因必多,且必酝酿已久……”“倘使前无所因,则无源之水,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唯其所改变的东西在汉代已酝酿了二百年,或一百年,大家耳濡目染已久,一旦逢到机会,取而易之……”这些观点,显然受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影响,同时也是其秉承古史辨派的历史渐变说的表现。但就基本的立场、态度而言,他仍肯定刘歆“实有许多为所窜乱和臆造的文件”。顾文找到了若干材料,证明《左传》是刘歆根据《国语》改作的,把《文公十三年》、《襄公二十四年》、《昭公二十九年》几条材料综合起来看,刘氏是陶唐氏(尧,火德)的后代。《世经》如何证明汉受命于火德,进而为“火德销尽,土德当代”、王莽称帝以土代火造势。论述至此,顾颉刚不可避免地站到今文经学家的立场上来抨击以《左传》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他说:
古文经既是这样地整齐而且完备,但传经的系统不完全,也是一个缺陷。所以他们(案:以刘歆学派为代表的古文家)又为它造出许多传授的源流来。《汉书·儒林传》云:……。照这样讲,古文学派的渊源至长,学者甚重,且有两种是河间献王已立博士的,它简直是个‘显学’,为什么刘歆竟小觑它而称它为‘微学’?……对于这些记载,实在可提出的疑问太多了!自清代学者重提出了今古文问题之后,作最严正的批评的,首推康长素先生的《新学伪经考》。
关于《左传》的问题,关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意义问题,钱穆与顾颉刚的观点截然相反。两人在今古文问题上、在刘歆等作伪与否问题上存在极大分歧。这种分歧,既有在古史辨派兴盛背景下历史观念和思想体系的分歧问题,也有相关的历史研究的概念术语没有厘清的问题,更有当时今古文两派学者激烈论辩的学术背景的影响等。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在顾颉刚文章的激发下,正是在与顾颉刚的论辩中,钱穆梳理并厘定了历史研究中两个重要的概念:“伪造”与“传说”的基本内涵及其含义差别。他向顾颉刚指出:政治舆论与学术风向所造之势,究竟属于“传说”的范畴或是属于“伪造”的范畴,需要细致区分。这种分野可能为古史辨派学者所忽视。
三
1931年4月,钱穆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刊出《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一文。钱穆说:“顾颉刚先生屡次要我批评他的近著《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为我在他那文以前,曾有一篇《刘向歆王莽年谱》,载《燕京学报》第七期。和他的议论正好相反,我读了他的文章,自应有一些异同的见解。”钱文就几方面问题与顾颉刚进行商榷。首先,《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天文训》记载了一种按方位配以五德的五帝系统,包含了皇帝之前的帝系,故《世经》所载帝系并非全无根据。其次,五行相生的系统,早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与《三代改制质文》中已有详细记述,可见《世经》中的五行相生并非刘歆伪造。再次,汉初时汉尚赤是确实存在的,只因楚在南方是赤帝子,《史记》相关记载并非伪造。武帝以后主张汉为火德也是客观存在的,这一切发生于刘向之前。“汉为尧后”说,也在刘向前。
这篇文章与前此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呈现历史观念的一致性。这种史学思想的独到之处必须放在当时古史辨派继兴盛一时的今文经学派之后登上历史舞台这一大的学术背景下,才能更好理解。钱穆写道:
曾记得梁任公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有一番话,大意是说,清代一代学术,以复古为解放;最后到今文学家复西汉之古来解放东汉许、郑之学,譬如高山下石,不达不止,为学术思想上必有之一境。其说良是。惟尚不免自站今文学家一面,专为清代学术立说,其实所谓以复古为解放者,至于晚清今文学派,尚未达到最后之一境。自今以往,正该复先秦七国之古来解放西汉,再复东周春秋之古来解放七国,复西周之古来解放东周,复殷商之古来解放西周,复虞夏之古来解放殷商,溯源追根,把中国从来的文化学术思想从头整理一过,给与一种较为新鲜而近真的认识,对于将来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上定有极大帮助。
他认为“以今文学家复西汉之古”来解放东汉的古文学,还远远不够,仍会陷入今文经学的固定视角中而受其遮蔽。在当时今古文两派学者纷争、辩论的学术界,钱穆声称要破除二派门户之见来治学,还历史以原貌。他说:
此四文(案:《刘向歆父子年谱》、《两汉博士家法考》、《孔子与春秋》、《周官著作时代考》)皆为两汉经学之今、古文问题而发。其实此问题仅起于晚清道、咸以下,而百年来掩胁学术界,几乎不主杨,则主墨,各持门户,互争是非,渺不得定论所在,而夷求之于两汉经学之实况,则并无如此所云云也。
顾颉刚同样声称自己持破除今古文二派门户之见的立场来研究古史问题。钱玄同对他说过:“今文学是孔子学派的传衍,经长期的蜕化而失掉它的真面目的。……古文家得到了一点古代材料,用自己的意思加以整理改造,七拼八凑而成其古文学。……所以今文家攻击古文经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的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相。”顾颉刚“觉得这是一个极锐利、极彻底的批评,是一个击碎玉连环的解决方法”。可见顾、钱两人都反对以今文古文的立场研究学术。略为不同的是,钱穆希望完全撇开今、古文偏见直接着手经学史真相的研究,而顾颉刚则希望能以今古文问题为对象作“破坏”、“重建”的工作。
作为对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与钱穆本人《刘向歆父子年谱》的“议论正好相反”问题的回应,同时也是对古史辨派的回应,钱穆在《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一文中着重表达了几层意思:
一、“在此学术新旧交替之际,又恰承着清儒那种以复古为解放的未竟之余波,让一辈合宜做古史考辨的学者,粗枝大叶地,先整理出一个中国古代文化学术思想的较近真的面相来,为此后新文化萌茁生机的一个旁助,实是至重要的事。……顾先生的《古史辨》,不用说是一个应着上述的趋势和需要而产生的可宝贵的新芽。”
二、“《古史辨》也是一种以复古为解放的运动,沿袭清代今文学的趋势而来,可是其间也确有几许相异。”
三、“胡适之先生所指顾先生讨论古史里那个根本的见解与方法,是重在传说的经历和演进,而康有为一辈人所主张的今文学,却说是孔子改制托古,六经为儒家伪造,此后又经刘歆、王莽一番伪造,而成所谓新学伪经。”
这三个层次有退一步说的转折性的含义。首先,钱穆只是肯定古史辨派“粗枝大叶”地整理出历史的“真的面相”,在新旧交替时期是“至重要”的。但要是在平常时期又怎样呢?钱穆的保留态度显而易见。其次,古史辨派显然“沿袭清代今文学的趋势而来”,但有“几许相异”——指出二者的关系。再次,正是这种“相异”启发钱穆去作进一步的厘清:古史辨派的“重在传说”与康有为一辈今文学的咬定“伪造”之别。为此,他提出该文最重要的一组概念厘析:“伪造”与“传说”的分野。他说:
造伪和传说,其间究是两样。传说是演进生长的,而伪造却可以一气呵成,一手创立。传说是社会上共同的有意无意——而无意为多——的一种演进生长,而伪造却专是一人或一派人的特意制造。传说是自然的,而伪造是人为的。传说是连续的,而伪造是改换的。传说渐变,而伪造突异。
钱穆将“伪造”与“传说”二说应用于他的历史分析中,指出,在宣帝复兴《毂梁》学、元帝改革到新莽建立的过程中,是“传说”在推波助澜。期间出现有关于祥瑞、灾异的社会舆论,汉代受命于火或土的政治舆论,《世经》对古史帝系的重新编排,乃至王莽的张扬礼乐、托古改制,都是在学术界、政治界、社会界诸演变中“有意无意”形成的传说,而不是“一气呵成”、“特意人为”、“突异剧变”的伪造。王莽代汉,与刘歆是否伪造经书、伪造古史帝系,没有必然联系。这正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中“莽之创制立法,亦皆远有端绪,当自元、成以下汉廷诸儒议论意态推迹之,不得谓由歆伪诸经,乃有新莽一朝之制度也”的观点。康有为等今文家把元成以后一切有利于王莽代汉的事件皆归于刘歆的伪造,是“粗糙武断,不合情理”的。而顾颉刚《五德终始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似乎混淆了传说与伪造之间的区别,脱离了古史辨派的见解和方法,倒向了今文家一边。
如上所述,钱穆也看到,胡适、顾颉刚等古史辨派比今文经学家进了一大步。他称,顾颉刚在观察、分析历史上,采用的是“传说”的演进流变的研究方法,与今文经学家的方法完全不同,他同意胡适这么评价顾颉刚:
他(顾颉刚)说:“我们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的变迁是怎样。”这种见解,重在每一种传说的经历和演进,这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这是顾先生这次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
顾颉刚的这一方法恰恰与钱穆在《刘向歆父子年谱》中使用的分析方法和研究理念相一致。但由于顾颉刚等古史辨派以复古为解放,不由自主地“沿袭清代今文学的趋势而来”,“粗枝大叶”地论断历史,使《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中一些观点背离这一基本方法。钱穆敏锐地指出,顾颉刚虽持辨伪精神,却仍不出今文学家的偏见,“时时不免根据今文学派的态度和议论来为自己的古史观张目”: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那篇论文,便是一个例子。无论政治和学说,在我看来,从汉武到王莽,从董仲舒到刘歆,也只是一线的演进和生长,而今文学家见解,则认为期间定有一番盛大的伪造与突异的改换。顾先生那篇文里,蒙其采纳我《刘向歆父子年谱》里不少取材和意见,而同时顾先生和今文学家同样主张歆、莽一切的作伪。
在古史辨派的学术作风备受推崇的当时,钱穆的眼光是敏锐而独到的。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的撰写,他对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的批评、他“伪造与传说相分野”观点的提出,针对的不仅仅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清代今文学派,更是代表史学研究新生力量的古史辨派,以及由古史辨派带来的粗疏的学术风气。他厘清“伪造与传说”两个词的含义及其差别,并非是某种派别之争的回应,而是在实践一种更科学、更合理的治史观念和方法——那种能摆脱门户之见,更贴近历史、更能“发见古人学术之真相”的历史态度和方法,诚如他自己所言:
诚使此书(按:指收入《刘向歆年谱》的《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一书)能于学术界有贡献,则实不尽于为经学上之今古文问题持平论、作调人,而更要在其于古人之学术思想有其探原抉微、钩沉阐晦之一得。读吾书者,亦必先自破弃学术上一切门户之成见,乃始有以体会于本书之所欲阐述也。
钱穆通过年谱的撰写和呈现,订正沿袭已久且在清末颇为流行的历史之说。在订正基础上区分“伪造”与“传说”之别,赋予两者以不同的含义。同时,划出古史辨派与晚清今文派不同之处,肯定古史辨学派的进步性,又指出其“粗枝大叶”,不自觉地落入晚清今文派窠臼的事实。这种态度比顾颉刚更为成熟。在当时的史学界,钱、顾的这场论辩,强化了由古史辨派提出的、而后在具体实践中又出现偏离的历史渐变演进的观念,强调“史迹的创造”,必须放入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多方位的观察、分析,既要紧贴微观层面的历史细节,又要把握宏观层面的、涵括历史的长度与深度的整体形态,对历史做“观前顾后”的考量。若忽视历史的关联性,夸大个人对历史的改造、编造作用,把“传说”划入“伪造”范畴,就会偏离历史事件环环相扣的渐变的真相,忽视社会风气的细节性酝酿及其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描述历史中,“传说”与“伪造”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概念,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历史认知态度,需要特别加以关注。钱穆“伪造与传说相分野”观点的提出,使钱、顾论争,获得了新的意义。它不仅澄清了相关的历史事实,更提出了一种历史研究的新观念,推进了历史研究的现代转型。
另者,钱穆的两文《刘向歆父子年谱》和《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首次把经学、经学史问题纳入历史研究的范围中,以辩证的历史态度和严谨客观的研究方法审视经学问题,不仅纠正今古文经学的偏见,也指出古史辨派将疑古观念带入研究中而可能出现的偏差。顾颉刚的古史辨派,本来也持“演进”的方法论来研究经学,他们的治学方法与目标,与钱穆基本一致。但由于他们始终以“疑古”作为研究的一种基本态度,过度的“疑”会使他们忽略对历史的正常形态作更深入的考量。以疑古为突破,以疑古为解放,也极有可能使他们陷入偏见之中。他们对古文经学的疑,与他们发现并利用今文经学的观念和研究成果几乎同时发生,协助他们进攻古史。从这种观念出发,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力主将西汉元、成以来出现的按“五行相生”顺序排列的古史帝系,打入汉末人“造伪”的冷宫,而不愿意将其视为元、成以来历史潮流推动的结果。顾文受疑古观念所遮蔽的情况也显然。
1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收入《古史辨自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2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收入《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
3 5 35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2页;第2页;第4页。
4 8 9 15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自序》,《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1页;第1页;第5-6页;第55页;第1页。
6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古史辨自序》下册,第530-531页。
7 10 12 13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11页;第58页;第57页;第59页。
14 钱穆:《秦汉史》,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03页。
16 班固:《汉书·王莽传中》,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38页。
17 18 19 20 21 23 24 25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古史辨自序》下册,第645页;第530页;第530页;第529页;第530页;第550-551页;第585页;第670页。
22 参见“我很佩服钱四宾先生……”一语,《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古史辨自序》下册,第530页
26 30 31 32 33 34 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古史辨自序》下册,第673页;第671-673页;第673页;第672页;第673页;第673-674页。
27 钱穆:《自序》,《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1-2页。
28 29 转引自王煦华:《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前言》,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第4页。
编辑/黄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