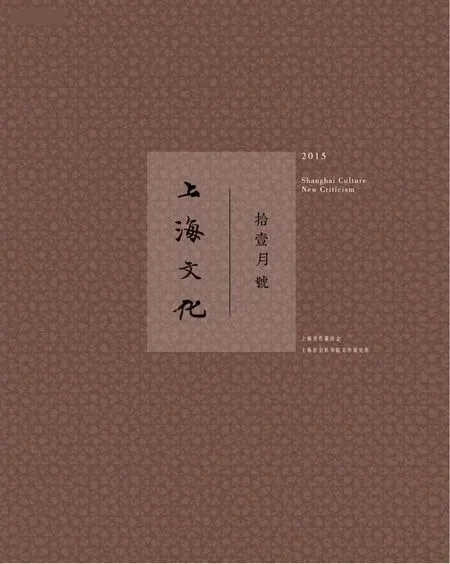奥尔特加的“生命理性”
张伟劼
奥尔特加的“生命理性”
张伟劼
在这个思想体系中,有几个关键词,“艺术”或许并不在其列,但“生命理性”(razón vital)一定是其中之一
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在中国最为熟知的理论大概就是他关于现代主义艺术的见解。他使用了deshumanización这个词来解释在20世纪初出现的、难以为大众所接受的新艺术。这一概念最早被译成艺术的“非人化”,后又被译为艺术的“去人性化”。艺术当然不能离开人,大猩猩的涂鸦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都不能算得是艺术作品,艺术终究是由人创造出来给人欣赏的。奥尔特加的意思是,新艺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拉开了距离,积极地摈弃一切自然形态、去除人性化因素,“画出一个人,而尽可能地让他不像一个人;要画一栋房子,却只保留必须的要素让我们能看清它的变形过程”,使得欣赏者在接受这些艺术作品时,不是在体验人类生活,而是在进行纯粹的美学享受。
我自己的一段经历也促使我在“艺术的去人性化”理论之外进一步阅读奥尔特加的著作。一年以前,我认识了一位西班牙学者,他告诉我他在做西班牙美学史研究。我与他谈起奥尔特加,要知道在中国,提起20世纪西方美学,这位大师是绝不可忽略的!然而他告诉我说,他正在撰写的西班牙美学史根本就没有提到奥尔特加;奥尔特加的著作在西班牙美学研究中仅仅处在一个很边缘的地带。他的回答让我想到,或许奥尔特加从没有试图建构一个美学体系。他的《艺术的去人性化》终究只是一篇美学散文而已,与他发表的其他零散的艺评杂文一起,仅仅构成他宏大的思想体系的一个侧面。在这个思想体系中,有几个关键词,“艺术”或许并不在其列,但“生命理性”(razón vital)一定是其中之一。
西方的危机
奥尔特加发表宏论的年代,正是西班牙文学、艺术与思想高潮迭出的时代,史称西班牙文化的“白银时代”。这一时代的开端,是西班牙政治危机的总爆发。整个19世纪,这个曾经辉煌的古老王国都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激烈角逐中飘摇,国势日颓,至1898年,在与美国的战争中痛失帝国的最后几块海外殖民地。1898年的危机促使一批有识之士开始积极地思考西班牙的过去与未来,以期重新树立西班牙民族国家的价值,史称“九八代”作家。
奥尔特加比大部分“九八代”作家成名稍晚,其思想倾向也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面对如何拯救积贫积弱的西班牙这个问题,“九八代”致力于在西班牙帝国的辉煌过去寻找答案,奥尔特加则把目光投向同时代更为发达的欧洲国家。“九八代”思考的出发点往往是西班牙,而奥尔特加虽则也常常思考西班牙问题,他的出发点却总在欧洲,在于整个西方文明。当“九八代”中西班牙国粹的捍卫者如乌纳穆诺为选择信仰还是选择理性的矛盾在内心苦苦挣扎时,奥尔特加却远远超越了在西班牙根深蒂固的天主教信仰,热情而冷静地思考现代世界的繁华乱象,既调侃信仰也批判理性,与同时代的欧洲思想家展开对话。
奥尔特加经常在著作中提及、试图反驳其观点的同时代思想家就有德国的斯宾格勒。一战结束之后,斯宾格勒的“西方没落说”盛行于欧洲思想界。根据斯宾格勒勾勒的历史形态学,19世纪以来的西方艺术已经失去了古典时代艺术的活力和风格,是一种没落衰败的艺术,这是西方文明走向灭亡的明证。而在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看来,则是资本主义文明正在走向“颓废”“没落”,旧的生产方式和政治体制将为一个全新的人类社会所取代。奥尔特加认为,西方并没有走向没落、衰颓,西方文明只是处在危机之中;时代的新旧交替的确在发生,但这种大变革并不主要是政治经济意义上的。
在1923年出版的《我们时代的主题》一书中,奥尔特加指出了问题的所在:
“今天,西方历史正在遭遇严重的危机,有些人坚持无视它的存在,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危机的症状极为明显,即使是最坚持不懈地否认这些症状存在的人,也会在内心里感受到它们的存在。在整个欧洲社会,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正在逐渐地蔓延开来,这种现象我们不妨称之为‘生命的迷失’。”
奥尔特加指出,人生总是需要一套坐标体系来做导引的,现在,这套体系出了问题:
“有这样一个过渡时刻,昨天还为我们的人生风景勾勒明确框架的宏大目标,今天已经失去了光泽,失去了它们的吸引力和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权威,而将要取代它们的新目标还没有取得完全的明确性和足够的活力。”于是,欧洲人的人生风景模糊了,欧洲人的脚步变得迟疑不决了。“这就是今天欧洲人的生存处境。三十年前为欧洲人的一切活动制定规则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如今已经失去了明晰性、吸引力和统领力。西方人彻底迷失了方向,他不知道该去哪个星球上生活。”
奥尔特加观察到的是,由启蒙理性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价值观,已经不复过去的说服力和生命力。18世纪末,正是这些价值观成为了人心中的牢固信念,促成了推翻旧制度的大革命。19世纪的欧洲人为这些理念所驱动,享受他们的“文化生活”,对公平、正义、科学、文明等等概念深信不疑。这些词汇在那时候还是有具体内容的,是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崇高理想。然而,到了20世纪初,这些理念越发显得苍白空洞,“理性”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世界大战造成的悲惨景象和年轻艺术家勾勒的支离破碎的世界,构成了末日般的图景。还有什么样的价值可以紧紧抓住呢?欧洲人该往何处去?
不同于斯宾格勒的悲观,奥尔特加对现代欧洲的未来持乐观态度。正如中国人常言,危机意味着转机,并不意味着一蹶不振。奥尔特加预见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我们时代的主题》中,他指出新时代的标志是重新确立生命的价值,让文化、理性、艺术和道德为人生服务。在后来发表的《艺术的去人性化》及更为经典的《大众的反叛》中,他进一步描绘了他所看到的新的时代,指出欧洲不仅不在走向垂暮,反而正在进入“稚气”时代,其标志是体育和电影的勃兴,二者都表明了对身体的崇拜,而只有稚气未脱才会崇拜身体;他以人口的增长和生活条件的巨大改善来驳斥斯宾格勒的西方没落说,并将现代欧洲人比作从学校里逃出来的学童,应感到欢欣才是:“现在我们不知道明天世界上会发生什么了,这让我们暗喜不已;因为正是无法预知未来,正是成为一个向一切可能性敞开的时空,才是真正的生活,才是生命的真正完满。”奥尔特加的这种乐观或许跟西班牙与欧洲保持一定的距离有关:西班牙没有被直接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反而因向交战国出售军需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现代化进程,使得现代文明的各种新事物在这个长期落后于欧洲中心的古老国家不断涌现。西班牙思想家在哀叹西班牙落后的同时,又对一个西班牙能融入欧洲发展步伐的未来作积极的观望,尽管在大战后两败俱伤的法国和德国的思想家那里,欧洲的未来并不那么乐观。
从纯粹理性到生命理性
西班牙的欧洲边缘地位或许也为奥尔特加提供了一种批判理性的独特视角。作为一个曾经在德国的大学里接受学术训练的西班牙人,奥尔特加领略了德意志古典哲学的博大精深,也看到了它的问题所在。他觉得,19世纪的德国人对“理性”“文化生活”深信不疑,正如他的迟迟走不出中世纪的西班牙同胞们对“上帝”“宗教生活”深信不疑。“从康德到1900年间的德国伟大思想,都可以统一在这样一个标志之下:文化的哲学。我们无需在其中走得太深,就能看到它在形式上与中世纪神学的相似。只是把旧的名称换成了新的名称而已,过去的基督教思想家讲‘上帝’,德国思想家则把‘上帝’替换成‘理念’(黑格尔),或是‘实践理性至上’(康德、费希特),或是‘文化’(柯亨、文德尔班、李凯尔特)。”
奥尔特加指出,人类生活既有生物性的一面,也有精神性的一面,因此,文化既要服从客观的、理性的规律,又要服从生命的、人生的规律。人类生活应当是有文化的,但文化又应当是生命性的。“没有文化的生活即是野蛮,脱离了人生的文化则是浮夸。”德国人、欧洲人引以为豪的“文化生活”已经失去了活力,“今天的欧洲文化在竭力成为唯一的理性文化、唯一的建立在理性之上的文化的同时,不再是有生命体验的文化了,欧洲人不再以理性来感受他们的文化,而是以神秘主义的方式来接受它”。启蒙理想成了新的宗教,欧洲人用以取代基督教信仰的科学真理成了唯一的真理,人们毫不怀疑地接受“真、善、美”的信条,不管它们与自己的实际生活有多少联系。理性要求进步,要求不断地向前发展,指向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在奥尔特加看来,“文化主义、进步主义、未来主义和乌托邦主义是同一个唯一的主义。不管是叫这个名字还是叫那个名字,我们发现的是同一种态度,对于这一种态度而言,生命是无所谓的,生命只有在成为通向那个文化‘天国’的工具和踏板时,才是有价值的。”正如中世纪的欧洲人在追求身后世界的同时忽略了此生、现世,进入现代的欧洲人在追求抽象理性、未来乌托邦的同时忽略了现实的人生。这种倾向应当得到改变。奥尔特加提出,“不要再说‘人生为文化服务’了,应该说‘文化为人生服务’”,而“我们时代的主题”就是:“让理性服从于生命性,将理性置于生物性的范围之内,让理性为人的内心意愿服务。”也就是说,“纯粹理性应当将它的君主宝座让位给生命理性”。
奥尔特加提出“生命理性”,并不是否定理性的意义、用人生取代理性,而是想纠正理性至上的偏激。真理、理性倾向于不变性、唯一性,倾向于涵盖一切可能性,而每一个人生个体都是不尽相同的,都是发展变化着的。如果不承认真理、理性的存在,只承认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相对真理”,那就落入了“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既然对所有普适性真理都表示怀疑、拒斥一切理论,终而是一种“自杀”式的理论。因此,作为现代文明的根基,“理性”不应被消灭。
奥尔特加反对的是“纯粹理性”。纯粹理性意味着勾勒一个几何学形状的世界,意味着绝对真理——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意味着绝对正确的理想,如果人类自诞生之初就遵循纯粹理性的轨道,人类就不会犯任何错误,就不会有人类历史了——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历史就是人的意志犯下的一系列的错误。纯粹理性是静止不动的真理,历史-人生则是永远变动不居的。因此,纯粹理性与历史-人生构成了一对矛盾。纯粹理性是反历史的,当它与政治相结合时,就成了革命。在奥尔特加看来,法国大革命喊出的关于人的宣言,就像数学课本那样精确而绝对。纯粹理性演变成了激进主义,在理性的君临之下,历史消失了——其象征是代表旧制度、代表过去的贵族被砍了头,人类个体之间的差异消弭了,人生的多样性、人的意愿的偶发性都被抽象的、唯一的“人”的概念所取代了。为了克服纯粹理性的弊病,必须用结合了生命的理性来取代纯粹理性。
奥尔特加对纯粹理性的批判自然就包括了对启蒙运动的批判,或者说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今天的学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积极思考全球性与地方性、西方的“普世价值”与本地的传统价值之间的矛盾,而奥尔特加在20世纪初已经对文化的相对性问题有所阐发了。在奥尔特加看来,欧洲把启蒙理想当成了唯一的、适用于一切民族和所有时代的真理,并强行将之推广到世界的各个地区,但别的文化亦有各自独特的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奥尔特加经常在他的著述中引用印度、中国等“东方”民族的传统思想观点,也像其他西方思想家那样把“东方”作为一个他者进行观照,但在他的论述中,东方不是被作为反衬西方文明发达的野蛮文化而呈现的,而是往往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比西方更高明:“东方人并不喜欢让文化与人生相脱离,因为他们总是要求文化具有生命性。东方人在西方的行为举止中看到的是绝对的虚伪,在与欧洲的接触中不能不感到由衷的鄙视。”在“生命理性”的基础上,奥尔特加提出了“视角主义”的概念。每一个人观察世界都采用了不同的视角,每一种文化亦如此。要认清这个世界,就要承认每一个观察视角的合理性,不把某一种视角当作唯一的视角。要获得真知,就要把理性置于具体的生命、具体的民族、具体的时代之中,将自己所见与他人所见整合起来,让思想的地平线永远打开而非封闭。“纯粹理性应当为生命理性所取代,在生命理性中,理性才能确立,获得灵动性和变化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奥尔特加并没有对理性作全面的颠覆而走向“非理性”的境地,相比欧陆的一众激进思想家,奥尔特加始终是冷静的、中庸的,不会为反对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
别把艺术太当回事
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奥尔特加熟读中国思想典籍,但他在著述中偶尔阐发的关于东西方比较的见解,往往是极有见地的。如前文所述,在论证他的“生命理性”时,他拿东方人来作参照:“东方人并不喜欢让文化与人生相脱离”……我记得自己在修读西方艺术史论时,关于中西艺术观的不同,我的导师说过一段话:西方人往往是拿生命来作画,如梵高,如塞尚,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体弱气衰,拿出一幅精彩绝伦的作品,贝多芬亦是使尽浑身气力来作曲;中国文人则是拿艺术来养生,把写字画画作为陶冶性情、延年益寿的手段,故而许多艺术大家都长寿。“文化为人生服务”的理想,不是已在我们中国人这里实现了吗?
在一个宗教精神并不占主导的文化里,中国传统文人只是“写意”、“言志”,并无“艺术”的概念,并没有将此高尚风雅之事奉若神明。而西方艺术家的艺术人生则往往蕴含着强烈的宗教意味,不管他是虔诚的教徒还是反宗教人士——在他们的心目中,艺术具有神圣的地位,艺术甚而就是上帝。古典作品总是厚重的、严肃的甚而是悲怆的,让欣赏者全身心地沉醉于艺术的世界中,忘乎所以。然而,20世纪初出现的“新艺术”则一反常态,让习惯于欣赏古典艺术的人全然不解继而恼羞成怒。关于现代主义艺术有很多种解释,奥尔特加的“去人性化”是其中一种。事实上,在发表《艺术的去人性化》两年之前,奥尔特加已经在《我们时代的主题》中对新艺术有所论述了。他认为,新艺术相比19世纪艺术的不同,关键不在表现对象上,而在于主体与艺术的距离,也即人对艺术采取的态度:“新风格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其总体特征在于,艺术已经从人生的‘严肃’区域中被移出去了,已经不再是生命引力的中心了。两百年来美学欣赏所具有的半宗教的、深情感伤的性质,已经完全被剔除了。”奥尔特加还不无幽默地对比了两代人的不同:“对于老一辈来说,严肃性的缺失,是新艺术的致命缺陷,而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种严肃性的缺失,恰恰是艺术的最高价值。”
在《艺术的去人性化》中,奥尔特加进一步发展了自己关于新艺术的观点,指出新艺术的特征之一就是游戏性,就是拒绝深刻意义,甚至是滑稽。在奥尔特加看来,滑稽并不意味着低下,古典诗人也能以玩笑见长。在他评论西班牙17世纪巴洛克诗人贡戈拉的一篇文章中,他就写道:“在贡戈拉的作品里,艺术真诚地展现为它本来就是的样子:彻头彻尾的玩笑……难道玩笑就不能伟大了吗?”拒绝严肃深沉、专事滑稽取笑,并不意味着玩世不恭。有些批评者误解了奥尔特加的深意,比如秘鲁思想家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就紧抓着“新的艺术风格必然总是滑稽的”这句话不放,认为奥尔特加诱使年轻艺术家走上了堕落之路。西班牙艺术史论家恩里克·拉富恩特·费拉里则认为,面对新艺术现象,奥尔特加表示理解、加以解释,但显然并不赞同,并且指出,奥尔特加后来是对新艺术的过度“去人性化”表示反对的。奥尔特加是否赞成新艺术呢?在我看来,奥尔特加并不排斥新艺术,他对同时代的那一批反叛精神十足的年轻艺术家是宽容的,甚而是寄予希望的。他并不担心艺术步入歧途或是堕落,因为他并没有把艺术的前途、文化的命运太当回事。
还是回到他的“生命理性”上来,回到具体的文本中。在《艺术的去人性化》中,奥尔特加提出了令人深省的问题:“这种对艺术中的人性的厌恶意味着什么呢?这究竟是厌恶人性、厌恶现实、厌恶人生,还是正相反:这是对人生的尊重,他们不愿看到人生与艺术这么次要的东西相混淆?”奥尔特加念念不忘他的“生命理性”。在他的体系里,人生才是第一位的,艺术、科学、道德等等都应当围绕着人生来运转。他接着说:“看得出,新艺术最讨厌的就是界限的模糊,新科学、新政治、新生活也是如此。希望事物之间界限分明,是头脑清楚的表现。”艺术的去人性化,就是要让艺术的归艺术,人生的归人生。因此,艺术走向人类生活的边缘,艺术不再承载生命之重,艺术成为无足轻重、无关紧要的东西,都没有关系,因为比艺术、比文化更重要的是人生。艺术家为艺术呕心沥血、欣赏者为艺术死去活来的时代过去了。不过,奥尔特加或许并没有考虑到艺术的两种可能:变成政治宣传的工具,甚而沦为极权统治的帮凶,或是彻底委身于资本市场,成为大规模复制的消费品。艺术的这两种遭遇,恐怕是奥尔特加所不能赞同的。他只能站在他所生活的时代的高度提出问题。
艺术的去人性化,就是要让艺术的归艺术,人生的归人生
1 见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2 见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艺术的去人性化》,莫娅妮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
3 6 José Ortega y Gasset.La deshumanización del arte y otros ensayos de estética.Madrid:Alianza Editorial,2006,p28;p51.
4 5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José Ortega y Gasset.Obras completas.Tomo III.Madrid:Santillana Ediciones Generales,2005,p606;p607;p600;p584;p585;p600;p600;p593;p587;p615;p608;p608.
7 José Ortega y Gasset.La rebelión de las masas. Madrid:Editorial Castalia,1998,p150.
18 Víctor García de la Concha.Poetas del 27:la generación y su entorno.Madrid:Espasa Calpe,S.A.,1998,p63.
19 José Carlos Mariátegui.“Arte,revolución y decadencia.”en Celina Manzoni:Vanguardistas en su tinta:documentos de la vanguardia en América Latina,Buenos Aires:Ediciones Corregidor,2008,p157-p158.
20 Enrique Lafuente Ferrari.Ortega y las artes visuales.Madrid:Revista de Occidente,1970,p85-p86.
21 22 José Ortega y Gasset.La deshumanización del arte y otros ensayos de estética.Madrid:Alianza Editorial,2006,p33.
编辑/黄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