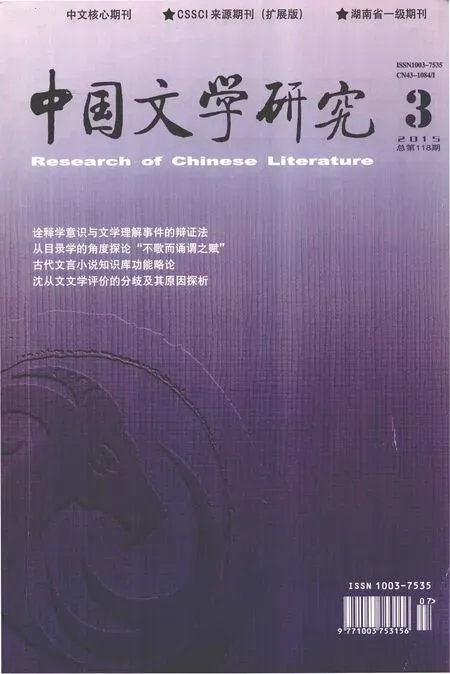探寻民间宗教与小说关系研究的新路径——评易瑛《巫文化与中国现当代小说》
陈进武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3)
从中国文化形态构成来说,巫文化不仅是其中的重要方面,而且还对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巫文化的发展演进来看,巫文化已经从最初的民间宗教信仰转化成了一种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渗透到了民族的骨髓。对于巫文化的研究,学术界已经作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也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成果。上世纪30 年代,陈梦家的《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等论文就着重探讨了商周时期的巫术。新时期以来,有学者讨论了上古巫术思维与楚辞的关系,有学者则着重考察了作为神秘文化核心的巫文化。不难看出,研究者对古老的巫文化的兴趣始终方兴未艾。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有学者从个案视角探寻了作家与巫文化的关系,但令人遗憾的是,关于中国新文学与巫文化的整体互动关系这一论题,却较少有学者涉及。即便有些论者也涉及过,但大多是简单事实的罗列,而对于巫(巫文化)本身所具有的诗性以及这种诗性的文学表现的分析,往往没有涉及,而或多或少有涉及的也多是语焉不详。
从上述意义来说,易瑛博士的新著《巫风浸润下的诗意想象——巫文化与中国现当代小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深入探讨了巫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关系问题,从巫文化这一角度切入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艺术本体之中,运用充分的细读与分析手段对于民间宗教与20 世纪中国小说的关系进行了独特的审美与理论研究路径的建构,尤其是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巫的诗性力量体现的学理空间上升到了新高度。这既为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提供了新理念与新方法,又为民间宗教与小说的关系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借鉴与启示。当然,这部著作的可贵之处也正如当代学者谭桂林在该书序《文学离不开巫性的诗意与迷狂》中所言的,这部著作不仅清晰勾勒了“20 世纪中国文学中巫的诗性力量的体现图景”,而且“对于20 世纪中国小说中的巫文化现象的梳理,其资料之翔实、分辨之细致、理路之清晰,可谓前所未见,而其对于巫性思维的诗性力量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各种体现的分析,不乏闪射着作者自己独到的艺术颖悟与生命体验。”
在词源上,“巫”即“祝也。……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原本指称能以舞降神的人。鉴于中西方学者对“巫术”界定的不一致,著者经过仔细辨析后认为,巫术既是行为状态,又是信仰系统,“是指人类试图通过某种仪式、利用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对客体加以影响或控制的行为方式”,包括完成巫术行为的人、巫术仪式和巫术意识等三个基本要素。而“巫文化”是指“以巫师、巫术及鬼神信仰为总体特征的文化,又被称为巫鬼文化、神巫文化、巫傩文化或萨满文化。”由此可见,著者从一开始用分析方式对“巫”及其相关概念的自身谱系进行了追根溯源,并辨析与界定了“巫”、“巫术”与“巫文化”等核心概念。尽管这些理论界定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一家之言”,但透过分析正显示了著者的扎实与稳健。
该著以20 世纪的中国小说为研究对象,将小说置于巫文化的视野中进行考察。著者自始至终站在分析的视角,运用分析的手段,并且在对于具体小说文本的解读与分析中来呈现问题、解决问题。比如,探讨现代小说家理性上的启蒙主义和艺术上的近巫传统之间的主体悖论及其呈现出的艺术张力问题。著者既从鲁迅《祝福》、巴金《家》、陈炜谟《夜》、鲁彦《菊英的出嫁》、阎连科《耙耧天歌》等小说中发现启蒙者对巫术信仰的理性批判,又洞察到受到心灵创伤的启蒙者在这些创作中潜藏在最深处的巫鬼信仰的情感慰藉。可以说,著者对启蒙叙事与巫文化呈现出的这种“启蒙”与“审美”纠缠状况的探索,无疑是建立在有效的分析基础之上的独到发现。著者对少数民族文学与巫文化的“诗性”与“神性”的追寻、政治叙事与巫文化的革命诉求下的“对立”“合谋”和“流离”、寻根文学与巫文化的“寻根”与“寻巫”的交融,以及先锋小说与巫文化的“现代”与“传统”的对接等现象的揭示,都是得益于这种精细的分析。
著者在提出自己的相关观点时,并不仅仅是从横向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分析,而且还从纵向上对小说与巫文化的关系变迁作出解释,以此保证了自身论述体系的细致、独到与严密,显示出了该著较强的逻辑性。为合理呈现出巫文化与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历时性变化,著者引证了大量第一手相关理论与小说文本材料,用丰赡的材料说话。她收集了大量的理论著述和20 世纪中国小说中有关巫文化的材料,尤为细致地将原本显得零散的材料累积起来,并且进行了有机的融合,由此来系统、翔实地论证所提出的观点。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有关巫文化的材料,还是相关的小说文本,无不是资料浩繁,复杂纷乱,但著者巧妙地化繁为简,将这种复杂关系分为启蒙叙事、少数民族文学、政治叙事、寻根文学与先锋小说等专题,分别论述与论证,从而显示出清晰的线索与思路。
著者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建构的体系并不仅仅是纯粹的文本分析。在她看来,这种关系的研究就是要“将以往对某一作家或某一地域作家的小说创作与巫文化的关系的个别性研究,提升到对‘巫文化影响下20 世纪中国小说’的整体性研究,全面梳理20 世纪由传统向现代嬗变的文化转型期,中国现当代作家对巫文化重新选择的同与异,追溯与辨析巫文化在20 世纪小说中存在方式的历时性变化,探究巫文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能以种种隐蔽的方式合理存在的原因,试图对巫文化影响下中国现当代作家参与20 世纪中国民族文化建构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审美经验的创造进行归类分析和系统考察。”从选择的几个切入点来看,著者有效地揭示了巫文化与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紧密关系。她以20 世纪中国小说文本为中心,采取点面结合,仔细梳理了思想特征(审美探寻)与巫文化的关系,尤其是对于中国现当代小说和巫之诗性的联系进行了深层的探究。
从方法论上看,著者的这种整合还体现在她对诸多学科理论方法的借鉴和综合之上。虽然著者对巫文化与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考察是以小说文本为中心,但她突破了以往局限于小说的思想、主题、人物、情节等的研究模式,而是从巫文化的视野出发,紧扣巫文化本身与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具体内容,充分运用了宗教学、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心理学和文艺美学等学科研究成果及理论来分析与整合小说作品和文学现象。简要梳理,我们会发现,该著涉及的西方理论主要有弗雷泽的巫术理论、荣格的人格分析心理学、列维·施特劳斯的人类学理论、卡西尔的人学理论、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学理论、巴赫金的诗学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诺依曼的原型分析理论等。而著者参考的国内相关研究著作也是相当丰富的。从表面上,该著的理论涉及相当庞杂,但从深层来看,一方面,著者并非机械地以某种理论分析某个小说文本或文学现象,而是特别注重在相关理论融合的前提下以研究主题为核心对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诗性进行科学归纳与分析。另一方面,尽管著者在立论和方法上多借鉴西方资源,但她又并非一味沉溺于“西学”难以自拔,而是将中西相关理论加以整合并结合小说文本和文学现象言说。
这种融合众家之长的研究方法无疑使得这部著作有效避免了研究思维的局限,既对小说作品进行了有新意的解读,开辟了小说文本研究的新路径,又显示出了该著逻辑结构的严谨性,增强了理论观点的可靠性。更为重要的是,著者这种将多种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交错使用,也促使她借此提出了诸多创造性的观念或见解。比如,关于启蒙叙事与巫文化的问题,著者敏锐发现启蒙者在质疑与批判被认为是反理性与反现代的巫文化的同时在情感上却又存在着难以割舍的寄托与慰藉。又如,对于政治与巫文化的关系,著者又察觉到了两者的微妙关系,亦即巫文化与政治“有时是敌对、有时是同谋,在夹缝中得以延续下来。”再如,对于上世纪80 年代的“文化寻根”现象,著者又发现了当时及其后一批作者的文学创作,并不仅仅是“寻根”,同时也是一种“寻巫”的探索。由此可见,著者将相关的理论思考与具体的小说文本分析有机融合,透过她的理性分析与整合,涉及的许多小说得到了某种全新解释,而不少观点更是发他人所未发。可以说,透过这部厚实的著作,我们找寻到的并不仅仅是巫文化与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精神联系,而且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复杂性与深刻性,也会获得更为深入的体认。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易瑛博士的这部著作其实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文学与文化的关系研究,而是达到了更为深层的研究目的,这种探寻也为当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拓展了新的研究视野。
不可否认,巫文化本身就是世界性的共同话题,而巫文化和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关系研究同样是有着极强的延展性的课题。对于这样的高难度的重大命题,易瑛博士的这部著作也并非完美无缺的,尽管她把巫文化与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关系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正是在这种提升中能够察觉到对于这一问题还有进一步开掘的余地,还有不少亟需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实际上,著者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在“后记”中这样说到,“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不断产生新的困惑,如巫术仪式与文学的关系、巫文化对中国戏剧的影响、中国巫文化与西方巫文化比较等问题,还有待今后进一步探讨。”〔1〕然而,略有遗憾的是,虽然该书是以中国现当代小说为考察中心,又试图对其作出历时性分析与阐述,但在具体作品的选取与分析中并未能完全达成这一研究目标。不过,在我看来,面对庞杂的材料与有限的著述篇幅,该著的这一不足也正是目前研究者难以避免的。
总的来说,该著为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民间宗教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开辟了新的思维空间与新的研究路径。尽管这种研究体系的构建和原创性观点的提出,尚未成为一种学术共识,但是对于这一重大命题的完善与突破,以及著者的质疑、辨析、探索与发现其本身无疑就是一种独特的贡献。
〔1〕易瑛.巫风浸润下的诗意想象——巫文化与中国现当代小说〔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