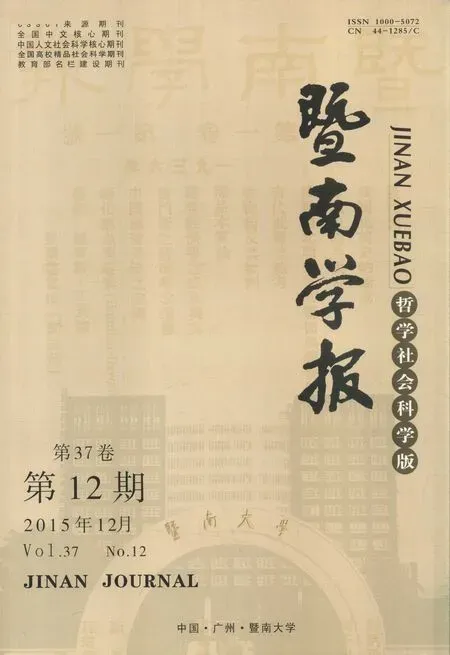宫体诗文献记载之矛盾分析
徐国荣,梁必彪
(1.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2.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尽管学术界对宫体诗的具体内涵与评价尚有争议,但基本一致地认为其名称起于梁简文帝萧纲,一直流行到唐太宗之时,其最主要的特征是“艳情”,也就是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所说:“宫体诗就是宫廷的,或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它是个有历史性的名词,所以严格地讲,宫体诗又当指以梁简文帝为太子时的东宫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但是,如果我们将历史上有关宫体诗记载的文献梳理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这些记载有着较强的模糊性,有些材料的真实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甚至完全是杜撰的,如《大唐新语》和《资治通鉴》所载之类,是作者当代意识的反映。这些文献之间甚至存在着矛盾,而这些模糊与矛盾的记载既与文献记录者的主观意图相关,又往往影响着人们对萧纲及宫体诗本身的价值判断。事实上,萧纲及宫体诗何以被妖魔化,宫体诗的名称究竟起于何时,唐宋时期的史料何以有着模糊而矛盾的记载,对萧纲及宫体诗的评价又为什么相差较大,学界仍然没有清晰的辨析。所以,如要对宫体诗作一公正客观的价值评判,就需先厘清这些原始性的文献记载之先后及其渊源,进而分析其矛盾及其原因。
一、政治需求与材料杜撰:从《大唐新语》的一则材料说起
刘肃《大唐新语》卷三《公直第五》:
(唐)太宗谓侍臣曰:“朕戏作艳诗。”虞世南便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而今而后,请不奉诏。”太宗曰:“卿恳诚如此,朕用嘉之。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乃赐绢五十匹。先是,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永兴之谏,颇因故事。
刘肃于唐元和时曾为江都主簿,生活于中唐时期,这段关于宫体诗与《玉台新咏》关系的记载,常被后人引用,作为评论宫体诗之产生及价值判断的原始依据,如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等皆信从其说。其中,关于虞世南的劝谏故事,应是真实而合理的,《旧唐书·虞世南传》不载其事,而《新唐书·虞世南传》则采之入史,且将第一句改为:“帝尝作宫体诗,使(虞世南)赓和。”也就是将“艳诗”直接改作“宫体诗”。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虞世南”条不载此事,而归之于卷一“太宗”条,盖亦取之《新唐书》。但两唐书与《唐诗纪事》都没有记载所谓萧纲令徐陵撰《玉台新咏》“以大其体”的“故事”。本来,这是两件不同的事,《大唐新语》的作者为了达到劝谏的目的,强行将两者牵扯到一起,所以最后加上一句:“永兴之谏,颇因故事。”永兴,即虞世南,因其尝受封为永兴县子。事实上,刘肃距离徐陵已有二百余年,此前相关宫体诗和《玉台新咏》的记载,从未出现所谓萧纲“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之说,更无令徐陵撰《玉台新咏》“以大其体”的说法。而且,从古今常理及逻辑推理来说,这也是情理不通的:既然已经追悔少作,何以还要变本加厉地“以大其体”?所以,后人在梳理宫体诗的渊源时,或引之而不作解释,或者亦难以释之而不引,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关于宫体诗的渊源,引用了诸多材料而没有征引此条。本来,刘肃作《大唐新语》的目的便是为了政治鉴戒,正如其《大唐新语后总论》所云:“自微言既绝,异端斯起,庄、列以仁义为刍狗,申、韩以礼乐为痈疣,徒有著述之名,无裨政教之阙。圣人遗训几乎息矣。昔荀爽纪汉事可为鉴戒者以为《汉语》,今之所记,庶嗣前修。”所以,刘肃为了达到政治劝诫目的,解释“永兴之谏,颇因故事”的可能性,在他生活的当时,萧纲及其宫体诗的淫靡艳诗已为定评的大背景下,他借机杜撰出“以大其体”的故事,将两件本不相干的事情嫁接在一起,以为其书的鉴戒动机而张目。对于“大其体”这种明显不通情理与不合逻辑的说法,由于材料出自唐代,人们总是认为其可信,努力地为其寻找合理的解释,故有论者以为:“这样编选一部历代艳诗的总集,重点选录宫体之作,同时沿波讨源,选录汉魏以来有关妇女题材的作品,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从历史渊源方面为宫体诗的存在找到了依据,从而达到为宫体诗‘大其体’,抬高地位的目的。这种努力虽不可能充分地消解正统派的责难,但也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为宫体诗辩护的作用,自有其理论上的价值与意义。”事实上,当时宫体诗风炽行,根本不需要什么理论依据与历史渊源作为支撑,裴子野《雕虫论》中所批评的“淫文破典,斐尔为功”乃指萧齐时的学风,而非针对宫体诗。萧纲也从未有“追悔”之说,“晚年”云云更与史实不合。所以,有域外学者以他者眼光指出:“在故事里,虞世南根本没有提到萧纲或者《玉台新咏》,是刘肃给故事加上了一个‘道德尾巴’,在这个‘道德尾巴’里,通过推断和联想,传达出刘肃本人希望传达的道德教训。”刘肃之记确实甚为“笨拙”,他说简文帝既悔其少作,却反欲“大其体”,因而令徐陵作《玉台新咏》。这与此前关于宫体的记载完全不合,也无其他文献依据。而且,这与虞世南的劝谏毫无关联,只是为了衬托出唐太宗的英明,将梁简文帝拉过来作为反面教材,硬生生地加上“道德尾巴”,萧纲也被妖魔化,成就了刘肃完全不合逻辑的道德说教。这只能说明,在刘肃《大唐新语》的时代,萧纲与宫体诗本身已经是“艳诗”或丽靡、淫靡、妖艳诗歌的代名词,是负面诗歌的化身,故而,在需要正面说教的时候,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其信手拈来,当作反面教材。
当然,刘肃杜撰出虞世南“颇因故事”的劝谏,也是利用了虞世南与徐陵的关系。因为徐陵在陈代乃“一代文宗”,虞世南为其后辈,曾受其嘉许,《旧唐书·虞世南传》说他“善属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新唐书》虞氏本传亦曰:“文章婉缛,慕仆射徐陵,陵白以类己,由是有名。”若徐陵《玉台新咏》真有“大其体”之事,与虞世南劝谏唐太宗作宫体诗正相牵连,两唐书本传中不容不载之。而唐太宗弘文馆学士中,褚亮、姚思廉等人皆与徐陵有旧,属徐后辈,亦皆崇徐陵。姚思廉之父姚察,在陈时亦受徐陵推重。即使姚思廉在史书中有所避讳,对徐陵撰作《玉台新咏》曲笔而讳之,但两唐书没有隐讳的必要,却也没有将《大唐新语》之载与虞世南联系在一起。当然,姚氏父子在《梁书》《陈书》的相关记载中,对萧纲以及徐陵、庾信的记载与评价,包括对宫体诗的态度,与魏徵、令狐德棻等人确实明显不同,涉及到相关宫体诗的评价问题,后文详论之。
事实上,在刘肃之前的开元时期,李康成撰《玉台后集》,在序言曾说过:“昔(徐)陵在梁世,父子俱事东朝,特承优遇。时承华好文,雅尚宫体,故采西汉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虽然徐陵撰《玉台新咏》的时间尚有争议,但这个“以备讽览”的说法比“以大其体”之论明显要合理得多,也完全符合正常的逻辑。其“时承华好文,雅尚宫体”的说法也与初唐时期的史书记载完全一致。只是,他没有明确指出“宫体”名称的具体由来。那么,初唐距离梁陈最近,今天保存下来的正史资料亦多,这些材料是如何描述“宫体”诗的来龙去脉及其与萧纲之关系的呢?
二、初唐时期对“宫体”之号的记载及魏徵、姚思廉的不同评价
据现存资料,最早对“宫体”之号记载的是初唐时期的几部史书:
(姚思廉)《梁书·徐摛传》: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
《梁书·简文帝纪》:(萧纲)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
(魏徵)《隋书·经籍志》: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迄于丧亡。
姚思廉与魏徵以及《周书》署名作者令狐德棻是同时代人,《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也约略同时,但因为身份地位以及南北二史成书较后的关系,李延寿对“宫体”的记载完全因袭姚、魏二氏。既名曰“宫体”,当然是指梁简文帝萧纲为东宫太子之时,而萧纲为太子始于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 年)五月,时年二十九岁。在此之前,类于“宫体”的新变之诗已经流行开来,所以《梁书·简文帝纪》说他“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后紧接着又说:“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这样的记载当然并不是说萧纲七岁尚不是太子时就有“宫体”的称号,所谓的“当时”乃是姚氏的追述,笼统地指称前朝简文帝的时代。同样的情况,《梁书·徐摛传》中所谓“‘宫体’之号,自斯而起”云云,也是姚思廉有意模糊的一种表述。因为徐摛在天监八年(509 年)三十六岁时被梁武帝选为萧纲侍读,当时萧纲七岁,为晋安王,徐摛诗风的流行,当然不能说“春坊(东宫)尽学之”,更不能说“‘宫体’之号,自斯而起”。这样的表述是史书作者时间延后的表述方式,若不仔细辨析而还原历史现场,确实易起误会。况且,梁武帝因恐此风的盛行而召见徐摛,不可能是在二十多年后“‘宫体’之号,自斯而起”的时候,只能是萧纲为太子之前的少年时期。萧纲自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是否正好与徐摛为侍读相关,抑或是巧合,我们不得而知,但在中大通三年——即萧纲为太子之年,徐摛出为新安太守,可以说,他一直伴随着萧纲的青少年时期,对萧纲的影响确是很大。从天监八年到中大通三年,二十多年间,萧纲不是太子,虽然艳体诗风盛行,却不能说“宫体诗”流行朝野,只能说“徐庾体”的兴盛。因为这段时间只有“徐庾体”之号而无“宫体”之称。下列资料可为证据:
《梁书·庾肩吾传》:初,太宗(萧纲)在藩,雅好文章士,时肩吾与东海徐摛,吴郡陆杲,彭城刘遵、刘孝仪,仪弟孝威,同被赏接。及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脁、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
《周书·庾信传》: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摛为左卫率。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
《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传》:赵僭王招,字豆卢突。幼聪颖,博涉群书,好属文。学庾信体,词多轻艳。
从时间的重合、内容与形式的相同上看,“徐庾体”与“宫体”并无差别。只不过,徐摛与庾肩吾年龄较萧纲为长,他们围绕在萧纲身边,也影响着萧纲,当萧纲年纪尚轻,未能产生广泛影响时,这种诗风被称为“徐庾体”。等到萧纲长大,在社会与诗坛都产生重大影响时,尤其是为东宫太子之后,这种诗风更加兴盛,且以萧纲为中心,故称“宫体”。徐陵和庾信与萧纲同辈,受到萧纲及其父辈的影响,当然也是这种诗风的实践者与拥护者。庾信入北后,虽然诗风变得苍凉了,但在北方的影响依然是其以前的风格,所以赵僭王招“学庾信体”的结果只能是“词多轻艳”。徐陵、庾信后来在文学成就与影响上均超过其父徐摛、庾肩吾,他们又同时服务于萧纲左右,使得人们认为“徐庾体”之称是以徐陵与庾信为中心,并且一直存在到萧纲死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八谓徐陵“文章绮丽,与庾信齐名,世号徐庾体”。又谓庾信“初在南朝,与徐陵齐名。故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称:‘徐陵、庾信,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采。词尚轻险,情多哀思。’……然此自指台城应教之日,二人以宫体相高耳”。一曰“徐庾体”,一曰“宫体”,将两者完全等同。且以《周书》与《北史》为依据,实不足凭。事实上,“徐庾体”只是“宫体”之前的称谓,当以徐摛与庾肩吾为主,从以上所引材料可以看出他俩对萧纲及徐陵、庾信的影响,而当萧纲入主东宫——“宫体”之号因之而起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徐庾体”的称号了。特别是萧纲死后,徐陵、庾信再也没有机会共同在一起倡导与写作艳体诗,当然更谈不上什么“徐庾体”了。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也是笼统而模糊的,从严格的逻辑推理上说,是不够严谨的。而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正在于唐初史书和唐宋时期相关文献的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上引《梁书·庾肩吾传》所谓“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的诗风当然指的就是宫体诗,但姚思廉并没有使用“宫体”一词。事实上,在宫体诗最为流行的梁陈时代,姚氏父子的《陈书》中没有只字记载“宫体”,《梁书》中也只有上述两处如此笼统模糊的记载,且没有负面的价值评判。所以,上引《梁书·徐摛传》将这些不同时间发生的事件杂糅在一起叙述,容易让人对宫体诗的流行产生错觉与误解,模糊了具体时间,淡化了“宫体”作为“淫靡”“淫艳”的负面形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宫体”诗在初唐时期所承受的负面评价,让人对其保持政治上的高度警惕,另一方面是姚氏父子对萧纲及徐庾父子特殊的情感与曲为回护的同情态度。
萧纲与宫体诗在初唐时期已经成为“亡国之主”与“亡国之音”的代名词,宫体诗作为淫靡艳诗已成定评,萧纲时开始盛行的宫体诗影响甚远,这是不容回避的客观史实。萧纲个人品行无亏,梁朝亡于侯景之乱也并非他的责任,但他毕竟有着“亡国之主”之实,加上“宫体”之号自他而起,此后的陈后主、隋炀帝两者声名不佳,也都是真正的“亡国之主”,也都爱好宫体诗,并且倡导与创作了《玉树后庭花》等宫体诗歌,于是,在“亡国之主”必有“亡国之音”的政治想象中,“宫体”等同于“亡国之音”。而唐太宗时期的政治氛围一直对此保持高度敏感,史书在记载陈后主、隋炀帝及其相关文学活动时,总是持以警戒的口吻与批判的目光。魏徵尤其关注这些,他不但常常在唐太宗面前劝谏,在相关史书中一再表达此意,如:
《隋书·音乐志上》:及后主嗣位,耽荒于酒,视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声乐,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又于清乐中造《黄鹂留》及《玉树后庭花》《金钗两臂垂》等曲,与幸臣等制其歌词,绮艳相高,极于轻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
《陈书·后主纪论》:(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后主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既属邦国殄瘁,不知稼穑艰难。初惧阽危,屡有哀矜之诏,后稍安集,复扇淫侈之风。宾礼诸公,唯寄情于文酒,昵近群小,皆委之以衡轴。谋谟所及,遂无骨鲠之臣,权要所在,莫匪侵渔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众叛亲离,临机不寤,自投于井,冀以苟生,视其以此求全,抑亦民斯下矣。……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
《梁书》和《陈书》虽由姚思廉在其父姚察的旧书上最后撰成,但当时魏徵是五代史的监修官,《梁书》《陈书》的本纪史论皆由魏徵所写。有意思的是,姚思廉虽然并不完全同意魏徵的相关观点,却只能采用曲笔隐讳的方法表态。如上引《陈书·后主纪论》中,他先引用了“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云云,以见魏徵对陈后主崇尚宫体而“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风”的批判态度与引以为戒的修史目的,而他自己紧接着却以“史臣曰”表明自己的态度:“后主昔在储宫,早标令德,及南面继业,寔允天人之望矣。至于礼乐刑政,咸遵故典,加以深弘六艺,广辟四门,是以待诏之徒,争趋金马,稽古之秀,云集石渠。且梯山航海,朝贡者往往岁至矣。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故施文庆、沈客卿之徒,专掌军国要务,奸黠左道,以裒刻为功,自取身荣,不存国计,是以朝经墮废,祸生邻国。斯亦运钟百六,鼎玉迁变,非唯人事不昌,盖天意然也。”魏徵每以政教目光以视文学,加以陈后主、隋炀帝之荒淫而确有才艺,所以能够轻易地得出“亡国之主,多有才艺”的结论,看似颇有历史依据。他将梁陈隋三朝相连,萧纲在个人品行上虽然与陈后主、隋炀帝甚为不同,还颇得好评,但他毕竟是“亡国之主”,又颇好宫体,容易被当作“亡国之音”的始作俑者。所以魏徵在批评陈后主、隋炀帝的同时,用道德批判的目光顺便将萧纲拉来陪斗。而姚思廉面对着同样的人物、同样的问题,连陈后主这样的人物都以“天意”为之开脱,也就无怪乎他没有对萧纲及其宫体诗作什么非难,因而在《梁书·简文纪论》中充满同情地说:“太宗幼年聪睿,令问夙标,天才纵逸,冠于今古。文则时以轻华为累,君子所不取焉。及养德东朝,声被夷夏,洎乎继统,实有人君之懿矣。方符文、景,运钟《屯》、《剥》,受制贼臣,弗展所蕴,终罹怀、愍之酷,哀哉!”对于萧纲宫体诗仅以“文则以轻华为累”轻轻一带而过,绝不像魏徵和令狐德棻那样把宫体诗等同于“亡国之音”。魏徵在《隋书·经籍志》中认为宫体诗的盛行“流宕不已,迄于丧亡”,直接将亡国的责任推之于宫体诗,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更有一段为后人反复引用的评判: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李延寿《北史》卷八十三《文学传序》完全袭之)
令狐德棻则在《周书·庾信传》中说:
然则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杨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
庾信对唐初文学影响甚大,虽然入北后文风有变,集南北之大成,但在需要对宫体诗风作政治检讨时,对他与萧纲进行批判,当然是最好的目标对象。这种情况其实最早在陈朝时已经出现。就现存资料看,最早对萧纲及其宫体诗从政治实用的角度来要求的是何之元《梁典总论》中的一段话:“太宗(萧纲)孝慈仁爱,实守文之君,惜乎为贼所杀。至乎文章妖艳,隳坠风典,诵于妇人之口,不及君子之听,斯乃文士之深病,政教之厚疵。然雕虫之技,非关治忽,壮士不为,人君焉用。”这里只是说妖艳之文章无关乎实用之政教,还没有使用“亡国之音”的评价。李延寿在《南史》中就是沿用这样的观点:“简文文明之姿,禀乎天授,粤自支庶,入居明两,经国之算,其道弗闻。宫体所传,且变朝野,虽主虚号,何救灭亡。”在他自己的这段论述后,又刻意引用魏徵的观点:“善乎!郑文贞公(魏徵)论之曰:……太宗敏睿过人,神采秀发,多闻博达,富赡词藻。然文艳用寡,华而不实,体穷淫丽,义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风俗,以此而贞万国,异乎周诵、汉庄矣。”虽然皆承认萧纲的个人品行与文采,却认为“宫体所传,且变朝野”的情况不能救亡,只能起到“哀思之音,遂移风俗”的坏作用。
而当陈朝与隋朝相继灭亡,陈后主与隋炀帝又是宫体诗的爱好者与提倡者,初唐人自然而然地得出“亡国之主”必有“亡国之音”的结论。以史为鉴的史书对于近在目前的历史事实当然更加保持警惕,这是魏徵等人乐于看到的结果。但史载唐太宗确实喜欢宫体诗,宫体诗的“艳”不仅体现在题材与字词的内容上,也包括在格律的“新声”形式与音乐的演奏上,《贞观政要》卷七《论礼乐》载:
贞观二年,太常少卿祖孝孙奏所定新乐。太宗曰:“礼乐之作,是圣人象物设教,以为撙节,治乱善恶,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实由于乐。”太宗曰:“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所感,故闻而则悲耳。何有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当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书右丞魏徵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
史称魏徵直臣,实则他也善于见风使舵,能够揣摩唐太宗心意,此处顺着唐太宗意旨而论乐,实则与其对宫体诗等之评价并不相合。而唐太宗倒颇为弘通,论旨近于嵇康《声无哀乐论》之意,也可看出他确实喜爱艳曲与宫体诗。唐太宗在个人喜好上与政治需求上可以将宫体诗与“亡国之音”分开,而他身边的大臣们则总是对宫体诗保持警惕,这是他们各自的身份与视角的不同所致。前引材料中杜淹的论乐,在唐人后来的政治生活中仍然出现。《新唐书》卷一一九《武平一传》中载,唐玄宗时的武平一上谏,所举之例完全因袭杜淹。
既然姚氏父子在《梁书》《陈书》中对萧纲以及徐庾父子评价较高,那么在记载宫体诗及其流行的客观情况时便处于尴尬的局面:既要直笔宫体诗流行与萧纲作为“亡国之主”的客观史实,又要回护萧纲及徐、庾父子,只好采用追叙而又较为模糊的语言表述。既不能回避“宫体”流行的恶谥,又笼统地称述“当时”宫体诗的流变情况。钱大昕《廿二史札记》中认为梁陈二史多忌讳,实有其因。可以说,姚思廉与魏徵等人虽然出发点不同,对待萧纲与宫体诗的视角与态度也不一样,但都由于各自的主观意愿,在记载与评述萧纲及宫体诗时,都有意无意地模糊了萧纲与宫体诗的具体内容,在文献记载上也采用了笼统而模糊的方式,只不过,姚氏是曲意回护的态度,魏氏是刻意批判的眼光。但从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上来看,魏徵之论占了上风,也给唐宋时期对萧纲及宫体诗“淫艳”的论点定下了基调。这样的基调甚至影响到宋代司马光等人,以致其《资治通鉴》中突然凭空出现一段从未有过的萧纲及其宫体诗的文献资料。这段材料的出现,其实正是萧纲及宫体诗在文学上被“淫艳”化、在政治上被妖魔化的直接结果。
三、《资治通鉴》的记载:萧纲与宫体诗被妖魔化的定型
经过唐太宗时期编纂的前朝八史之后,魏徵和令狐德棻等对待萧纲与宫体诗的观点深深地影响着唐人,《大唐新语》的作者刘肃之所以不顾逻辑地联系宫体与政治的关系,当然是因为这种观点已成定论的历史背景。从魏徵到刘肃之间,在现存的唐代史料中,还可以看出这种观点得到不断强化的痕迹。唐睿宗玄宗时期的丘悦撰《三国典略》,其中徐摛之事完全抄自《梁书·徐摛传》,又载曰:
齐主尝问于魏收曰:“卿才何如徐陵?”收对曰:“臣大国之才,典以雅;徐陵亡国之才,丽以艳。”
无论此事是否为实,至少反映了当时人的观念:大国之才典以雅,亡国之才丽以艳,徐陵正是后者的代表。而为官于唐德宗贞元时期的杜确撰《岑嘉州集序》则云:“自古文体变易多矣,梁简文帝及庾肩吾之属,始为轻浮绮靡之词,名曰宫体。自后沿袭,务于妖艳,谓之摛锦布绣焉。”从观点上看,自是无所发明,在文献上也只是因袭。这些材料,包括前引李康成的《玉台后集序》,皆出现在《大唐新语》之前,虽然没有出现所谓《玉台新咏》为宫体诗张目“以大其体”的说法,但对宫体诗“淫艳”“淫靡”“妖艳”的评语基本一致。《大唐新语》的记载虽无文献依据,却与一直以来的惯性思维与定性评价相符合,因而也就躲过了千年以来的质疑。至中晚唐,艳体诗风(或称宫体诗风)又起,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所谓“遐思宫体,未敢称庾信工文;却诮《玉台》,何必倩徐陵作序”。到了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虽然距离萧梁之亡已近五百年,但在叙述侯景之乱与梁朝灭亡时,出于“资治”的目的,他借机指斥萧纲与宫体诗,而且横亘隋唐五代而突然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
(侯)景遂上启,陈(梁武)帝十失,且曰:“臣方事暌违,所以冒陈谠直。陛下崇饰虚诞,恶闻实录,以祅怪为嘉祯,以天谴为无咎。敷演六艺,排摈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铁为货,轻重无常,公孙之制也。烂羊镌印,朝章鄙杂,更始、赵伦之化也。豫章以所天为血雠,邵陵以父存而冠布,石虎之风也。修建浮图,百度糜费,使四民饥馁,笮融、姚兴之代也。”又言:“建康宫室崇侈,陛下唯与主书参断万机,政以贿成,诸阉豪盛,众僧殷实。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邵陵所在残破,湘东群下贪纵;南康、定襄之属,皆如沐猴而冠耳。亲为孙侄,位则藩屏,臣至百日,谁肯勤王!此而灵长,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谏,王卒改善,今日之举,复奚罪乎!伏愿陛下小惩大戒,放谗纳忠,使臣无再举之忧,陛下无婴城之辱,则万姓幸甚!”上览启,且惭且怒。(胡三省注:言皆指实而无如之何,有惭怒而已。)
《资治通鉴》的这两段“且曰”与“又言”,为侯景数武帝之失(当出于其谋臣王伟之手),但《梁书》与《南史》均不载,《南史》于此仅云:“时景奸计既成,乃表陈帝失,复举兵向阙。”《梁书·侯景传》详载其“十失”之论,于此亦不闻一言。且在数落武帝“十失”之前,对梁武帝之功德颇有称颂,其云:“窃惟陛下睿智在躬,多才多艺。昔因世季,龙翔汉、沔,夷凶翦乱,克雪家怨,然后踵武前王,光宅江表,宪章文武,祖述尧舜。兼属魏国凌迟,外无勍敌,故能西取华陵,北封淮泗,结好高氏,輶轩相属,疆场无虞,十有余载。躬览万机,劬劳治道。刊正周孔之遗文,训释真如之秘奥。享年长久,本枝盘石。人君艺业,莫之与京。臣所以踊跃一隅,望南风而叹息也。岂图名与实爽,闻见不同。”虽然下文说其“名与实爽”,其“十失”主要因其对待侯景自己之薄,并没有对梁武帝之佞佛有何诃斥与不满,更没有将简文帝之“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当作罪状。在“十失”最后,他还是以“清君侧”之名义,表示“愿得升赤墀,践文石,口陈枉直,指画臧否,诛君侧之恶臣,清国朝之秕政,然后还守藩翰,以保忠节,实臣之至愿也”。尽管《梁书》作者同情梁武帝父子,但于重要史实还是客观尊重的。对于萧纲“吐言止于轻薄”的宫体诗风,唐人早已视为“淫艳”,若此段指斥为实,唐人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恐怕早已据为批评萧纲与宫体诗之利器了。但现存的唐人资料中根本不见这两段话,也无任何痕迹说明其存在。而司马光于五百余年后忽出此言,在文献上没有任何依据,究其实,当是其当代意识之反映。胡三省注所谓“言皆指实而无如之何,有惭怒而已”,更是想当然尔。此两段主要说明:佞佛之患,甚于水火,而简文宫体,乃为亡国之音耳。这两个判断,都是北宋时代司马光等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常识性认同,也是由于宫体诗被妖魔化已经定型,成为历史的文化认同。正因为如此,《资治通鉴》的这段记载,特别是对于萧纲与宫体诗的评价,在思维定式上符合唐宋以来的通行看法,在文献上虽无依凭,却并不为人所疑。直到现在,学术界在论及萧纲与宫体诗时,仍有引用这段材料作为依据者。但从学理本身来说,这是需要厘清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宫体”之号确切地起于简文帝萧纲为东宫太子之时,但类似的艳体诗风早已流行,此前则称为“徐庾体”。而由于初唐时期的政治需要,随着“亡国之主”必有“亡国之音”的政治想象,姚思廉与魏徵等史学家在记载与评价萧纲及其宫体诗时,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却均给出了模糊的记载。但宫体诗被认定为艳体诗,且与“亡国之音”相联系,是唐代的主基调,且一直影响到宋代及整个后世,《大唐新语》及《资治通鉴》中对萧纲及宫体诗的记载,在文献上没有依据,也不能说明其来源,当属推想,甚至是杜撰,它们只是作者当代意识的反映,不能作为原始的文献依据以说明宫体诗之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