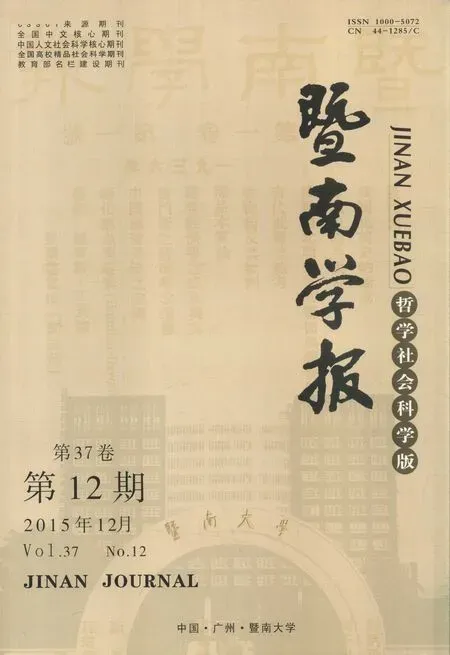学术为体、教育为用——胡适与1947 年“学术独立”论战
童 亮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近代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使得学术独立的追求具有多面的含义,也使其摆脱了单一的思想史内涵,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建立起多种关联。在近代学术史的脉络中,“学术独立”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受到学人的持续关注。关于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其流变已经有较多的研究,但具体到特定个案尚缺乏深入的分析。1947 年9 月,胡适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在学界引起震荡,众多学人先后加入论战。关于此次论战,既有研究多将其前后割裂,或只是在梳理“学术独立”观念的过程中偶尔提及,或在胡适研究中一笔带过,鲜有深入研究。本文在上述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着力弥合两种思路,还原其前后相继的论战过程,并将个人与时局、胡适多重身份、胡适与参战学人等多重面相纳入视野,以期更为全面地展示这场论战,以及挖掘争论背后的丰富信息。
一、个人与时局:从教育计划到学术计划
学术独立是近代学术开始高度发达以后才产生的一种主张,自其被提出以来,经由学人的长期讨论与宣传,已逐渐成为知识界的共识。自20 世纪20 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开始从各个层次反思中国学术的独立性问题,经由深刻反省,逐渐从“欧化”过渡到“本土化”的思路,试图摆脱对欧美学术体系的单一依赖。抗日战争胜利后,一方面,国民政府收紧了对教育领域的控制,激起学界的反弹,“学术独立”的呼声再次高涨;另一方面,在民族前途的再次探索过程中,更多学人将学术视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一剂良药,学术独立被置于更高的“功用”之下。知识界的主体意识日渐增进,且空前高涨。在此背景下,“学术独立”问题不仅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还为教育界、政界所注意。
值此学界复兴之声高涨之时,胡适归国并出任北大校长。1946 年7 月20 日,刚接受北大聘请的胡适赴国际饭店出席欢迎茶会,发表归国后之感想,鼓励“全国上下,尤其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应多下研究工夫,探求问题症结,努力改善,则国家民族前途自极光明。”同年9 月,胡适正式出任北大校长,在北大开学典礼上,胡适延续了其一贯关于学术发展的思路,告诫学生要“独立的研究”。北大在战后元气大伤,校舍与人事都亟待修复,其所需的大额经费迫使胡适不得不为之奔波。然而,彼时深陷内战泥潭的国民政府,自然无暇顾及北大等校的复校困难,胡适一面为北大经费问题奔波,一面有感于无力改变外部环境,开始着力于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前来讲学。10 月20 日,胡适出席中研院评议会第二届第三次年会,提出政府如能给予十年安定的环境,“并作财力人力之补助”,中研院也可建设为世界著名的博士院之一。23 日,在答南京对《申报》记者发表谈话,重申十年安定之环境内则“学术必可大有进展,大学教育情形亦属如此”。胡适由北大复校之困难从教育家的身份出发,初步阐述了十年培养学术机构,以促进学术进步的初步构想。
1947 年,在拒绝了蒋介石出任国府委员之邀请后,胡适将注意力置于北大的建设上,4 月24日,北大历史系《历史研究法》一课开讲,胡适亲自开讲第一讲。5 月4 日,胡适出席北京大学校友聚餐会,对蔡元培高度肯定,认为北大之“新”主要在于:第一,真正提倡学术自由精神;第二,不独揽大权。其在北大的治校思路可见一斑。8 月26 日,胡适再为筹备“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一事面见蒋介石,期间正式提出发展教育的十年计划。其主要内容有两点:第一,要选择两批大学,每批5 所,以给予充足的经费建成国际上第一流大学;第二,反对花大宗外汇派人出国留学,称如此“不如用来发展国内大学”。
9 月8 日,《大公报》披露了胡适向蒋介石提出的十年教育计划全部内容。胡适称“自己学术上有了地位,又何必非要到外国第二三四流学校去镀金不可?”进而又提出“我这个学术独立十年计划,就是第一个五年由政府指定五个大学作到第一等地位,这自然非有一点偏私不可,依我推荐,这五个大学应为北大、清华、浙大、武大及中大,到第二个五年再培植五个大学,以此达到争取世界学术地位(至少要比外国的二三等大学有地位)”。此后,他还先后在上海、北京向记者发表讲话,进一步阐述其“十年计划”。多地媒体争相转载或报道,一时间沸沸扬扬,以至于沉寂已久的南北教育界都因其“十年计划”,“引起许多意见”。
二、教育界风波初起
(一)公与私
针对胡适的教育“计划”,南开大学教务长陈序经首先发难,围绕其优先扶植五所大学是否偏私这一话题展开讨论。陈质疑胡适提出教育计划的初衷,质问其所提率先发展五所学校“何所根据”?他指责道,胡适出国已久,对国内形势未必了解,其立场则不止“一点偏私”。随后,关于五大高校是否有资格担当重点扶植之责任,胡适是否有失公允一事引起各高校关注。大致从自身利益出发,参与争论的高校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列入“五大”之中的高校自然“咸表赞同”,对胡适的计划大加赞赏。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对胡先生的计划,在原则上完全赞成”,称其“所提出的各点改善办法,也是将来必然的趋势”。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更是大赞“胡校长是我们的领导者,他的意见也可以说是我们大家的意见”,言语间唯胡适马首是瞻。
相形之下,被排除在“五大”之外的名校则免不了“齐声责难”。复旦校务章益对胡适即极尽讽刺,称其将北大列入五大乃“自吹自擂”。交通大学校长程孝刚则强调以学科专长为基础来发展重点大学,认为“政府应就各校所长而分别发展之”。北洋大学工学院院长李书田称本校“不仅历史比北大悠久,而且战前北洋工科研究所出版的研究丛刊,是经常与欧美第一流研究机关互相交换,且深得国外同道之赞许”,言外之意,该校未能列入五大实属不公。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也认为“五大”的提出“确实缺乏标准”。更有化名“胡不适”的读者批评“十年教育计划”“似非公论”,认为“其他尚有较优者”,还提出北大培养官僚及党棍、非建设人才之迂儒,清华学生中“未出洋者,程度实未见高明”。批评之余,他还讽刺胡适为“北大吹吹牛”,揣测其提出计划之动机不纯,“明明希望教育部将所有教育经费以供养北大,格于舆情,勉强提出四校作陪客,偏私之心,路人皆知”。
在诸多反对声中,以“中大派”声音最甚。胡适提出的五大高校中虽有“中大”,但究竟指中央大学还是中山大学,时人起初不甚明了。中山大学原校长邹鲁曾为此事专门致信胡适,在得知并非中山大学后,即对胡适进行指责。其后,中山大学教授胡先骕为中山大学呐喊,称中山大学实力之强,“五大学皆非其匹也”。中山大学教授陈安仁也致信胡适,更是抬出“国父”,并列出四条理由,要求将中山大学列入“五大”之内。
胡适所提计划的反对者中,不仅有非“五大”的传统名校,也有实力较弱的高校。他们希望在教育资源方面获得政府支持,利益均沾,极力反对优先扶植个别高校。如国立中正大学校长林一民就认为:“政府对于历史短,设备差之大学,应尽力扶植,使与历史久,设备佳之各大学,并驾齐驱,然后再谋各校之普遍发展。”北平大学法学院院长石志泉更是代表私立学校大吐苦水,博取同情,称其“经费支绌,学校,教授,学生均在困难中求发展,毫无奢望被选为该计划中之前五校或后五校,只希望政府及从事教育的同人,不要存有歧视或不重视的心理,给办私立学校的人一些精神的鼓励”。
(二)留学之利弊
纵观胡适的教育计划,除了重点发展五大高校之提议为人诟病外,关于留学耗资巨大、不如用于国内教育发展之论调也颇引人注意。在反思派遣留学生的诸多弊病之后,胡适大胆提出“不如取消留学生的派遣,节省外汇以充实国内教育”。这一主张引来众多学人的批评。曾留学海外的学人对此问题最为重视,他们或从自身经验出发,或从教育前途入手,反思留学制度之利弊。有意思的是,不少曾经受过留学之惠的学人站在胡适一边,反思现有留学制度的弊端,敢于指出其不足。如胡先骕就指出,“大批公费私费学生,在国内准备既未充分,甚且外国语之准备均不足,仅图往国外镀金,不惜耗费大量外汇,殊属不智”。王重民也认为,“今日的留学制度”已经成风,“既不能统制,又无政策,以致流为虚伪与浪费,相习成风,而教部又明明规定非在国外得到什么头衔的人,不能当教授”,实属“上有好之,下必有甚焉”。
也有学人持反对意见,他们充分肯定留学在培养人才方面的积极作用。如齐思和即认为,“直到现在,我国仍以使青年赴外国留学为训练高等专家的唯一方法,在现今学术落后的环境里当然舍此也没有更好的方法”。与之相似,许国璋回顾个人际遇,认为“青年人出国留学是无奈之举”,因“不少学生大学毕业后苦于在国内无适当的机会与场所继续做研究工作,不得已到国外去留学的”。在他看来,胡适对留学制度的诘难,多少犯了因果倒置的错误。
三、学界再起风波
教育界对胡适计划开展热烈讨论,或批评或声援,一时甚嚣尘上。先有陈序经发表长文,后有邹鲁去信质问,已有“发展为论战之可能”。1947 年9 月18 日,胡适将前述想法连同部分回应撰写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较之此前口头上的教育计划,文中关于十年计划的设想措辞更为严谨,立场趋于平和,且删去了最为人诟病的五大高校名单,在留学的存废问题上也开展了辩证陈述。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中,胡适开篇即提出计划之宗旨,即“中国的高等教育应该有一个自觉的十年计划,其目的是要在十年之中建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
关于此“十年计划”,胡适信心满满,却不料在校内受到冷遇。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了他9 月23日携十年计划奔赴北大“教授会”的情况。各位教授所谈之事相当“实际”,“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更有先生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受挫后的胡适心里颇感悲观,甚至抱怨“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然而,在遭遇短暂的冷遇之后,胡适的十年计划受到各大报纸的热捧,不独《中央日报》转载,《大公报》、《申报》等也竞相报道。在其十年计划中,胡适以四项条件定义何谓“学术独立”,以八项措施回答“何以实现学术独立”的问题,因而参战学人多以“何谓学术独立”、“如何实现学术独立”为焦点展开论争。
(一)何谓学术独立?
胡适的“十年计划”以“学术独立”为名,颇为扎眼。早在胡适提出教育计划之初,就因使用“学术独立”一词受到攻击。许国璋即认为“学术独立的提法”有两点不当之处:其一,“这一名词,太容易为顽固派所利用,故其界说必须谨慎”;其二,“中国为世界学术界中的一员,世界上有经济的繁荣,也有智慧的繁荣。中国有责任提高它的学术水准,以有助于世界的智慧繁荣,正像有责任提高他的生活水准,以由助于世界的经济发展荣。以这个角度看,胡氏争取学术独立之议,终不免有流于狭隘的国族观念之嫌。”在撰写计划之时,为避免众人对这一概念的误会,胡适特别对“学术独立”一词加以解释,称其所指的学术独立“当然不是一般守旧的人们心里想的汉家自有学术,何必远法欧美”。他借助四个条件进一步对学术独立的内涵进行界定。其一,“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其二,“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和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作专门的科学研究”。其三,“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如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都应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寻求得解决”。其四,“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构应该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构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此条侧重学术的交流问题,即学术独立不是学术孤立,但中国学术也不应该是附庸于他国的。通观这四个条件,胡适所言的学术独立,其实是追求中国学术相对于世界学术尤其是西方学术的独立性。他所提出的前三个条件,是其提出八条措施的根本原因所在。在胡适看来,只有发展出第一流大学,才能在国内实现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才能使受过基本训练的人继续从事专门研究,也才能有专门解决本国问题的学术的可能。概言之,胡适所说的学术独立,是建立在中国西学化的基础上,使西学中国化,使中国能够自我进行西学培养,用西学解决自己的问题。换言之,胡适提出学术独立这一口号,就是认为中国应该从对西学的模仿、引进开始转入对西学的创造。
尽管胡适小心翼翼地对“学术独立”一词进行了界定,但这一话题仍旧引起了诸多猜测。胡适的学术独立计划甫经刊出,立即有学人对之进行攻讦。有学者质疑,《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这个标题不甚妥当。“‘学术’没有独立的……胡先生虽对于‘学术独立’的含义有所解释,仍恐被守旧的人们断章取义,而‘另走一条孤立的途径’”。《世纪评论》的社论更是尖锐,认为胡适用‘独立学术’一词“实为不幸”,“不敢苟同”,因为“学术本无国界,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学者所研究出来的成绩,都是全世界学术界的公产,谈不到什么独立不独立”。该社论甚至认为,“学术独立是学术自杀最有效的方法”。
反对胡适主张的学者中,也有人较为平和、理性。如潘菽撰文指出,学术本身就具有其独特性,所谓“时代不同,实际环境不同,所需要的学术也自然因之而异,所以学术必须因时代的演变而演变,也必须因环境的有别而别有其独特性”。据此他认为,“学术独立的要求当然并不是故意立异而是把学术适合于时代并适合环境所必然产生的结果。凡真正服务于一个民族的生活的学术必然具有其特殊性,即独立性。反过来,凡以一个民族的生活要求为背景所发展而成的学术也必然具有其特殊性,即独立性”。与胡适相似,潘菽也认为学术独立是要中国自己来解决面临的学术问题,然而与胡适强调学术的普世性不同,他认为学术更有其特殊性。在一片质疑、攻讦的声音之下,也不乏同情、附和之人。如张作人认为,“固然学术二字的意义及范围,不甚清楚,但提出人一再申明,是必须要教授与研究生做着独立的科学研究。则所谓学术的也者,当系指狭义的科学的研究而言”。
大体言之,在这场论战中,一般所言的学术独立的依据还是以胡适所做出的解释为基础。批评者多局限于“破”,缺乏足够的“立”。关于学术独立的内涵的讨论并未成为当时论战的焦点,也没有充分展开。
(二)何以实现学术独立?
胡适在十年计划中延续了教育计划的基本思路,仍字字切“教育”之题,不仅在何谓“学术独立”的问题上以教育之独立作出解释,还切实提出以下措施,将学术独立之实现寄望于发展教育之行动。具体而言,以十年为限,其措施包括:不再增建新校;沿革遵照宪法执行教育经费;制定两期共十年的高等教育发展计划;分两期分别重点扶植五所大学,使其短期内成为现代学术中心;对国立大学、独立学院以及优秀的私立学校增加经费,促成其发展;在选拔重点扶植的每期五大校之时需实现公私院校的平等对待;不仅以变更教育制度为目的,还须实现大学的彻底变更。
然而,胡适提出的由十年教育计划达成学术独立的举措却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大部分学人还是习惯于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虽一致认可“学术独立”之必要,但关于如何践行,却是言人人殊。如在谢佐禹看来,思想自主才是学术独立“更根本的问题”,如“这更根本的问题解决不了,学术仍不会独立”。因此,他提出只有“思想免除其自身的束缚,不为传统思想所囿,也不为外来思想所侷”,才能谈学术独立。陈旭麓认为学术独立的发展,“需要高度的思想自由,让学人纵横驰骋于精神生活的天地间”。他怀疑胡适是以学术独立为名,行讨要经费之实,提出“北大今日在国内拥有的学术地位,与其说是经费的充分,不如说是蔡孑民先生领导思想自由之功”。他甚至讽刺道,胡适如此提倡学术独立,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店”的学术独立。与之相似,徐旭生也认为胡适的计划本末倒置,称“如果没有独立自主的治学精神,那就有好的制度和设备,也还不够。必须治学的精神,不受牵扯,不受限制,而后制度和设备,乃得有附丽和领导,不至成为无用之物。”许国璋也提出,国内学术界要争取学术的独立,第一步要先得争取国内学术的自由。
在此基础上,另有不少学者由学术独立将话题进一步延伸,认为“自主性的学术研究不仅要前人的一切发明和创造我们差不多都跟得上;而且要凡是前人没有发表,没有创造的,我们亦有发明,亦有创造。要做到这样的学术独立,只是要求知识的成果是自己发明的是不够的,连获得这成果的方法也是自己所独创的。反之,虚伪的学术独立,在这两个条件中,只能具备第一个条件,但未能具备第二个条件,即只有某些知识成果是自己所发明的,但获得这些知识和成果的方法完全是别人的。”
也有人以切实的举措与胡适相争辩。如潘菽认为,建立中国的独立学术的努力应包含三方面,“一方面要吸收其他民族的学术而使之中国化。另一方面要承继前代的学术遗产而使之现代化。再一方面要淘洗民间的生活经验而使之科学化。创造独立的中国学术所可以利用的资源不外来自这三方面。惟有这样所发展而成的学术才能适当有效地帮助中国人民改进其生活,才能真正解决中国所有的许多问题。”
不过,大多数学人对于以教育促学术的设想,似乎并不给予特别的注意;教育界虽有注意,但缺乏理性的分析与建设性的意见。一片喧嚣声中,关于学术独立的论战最终不了了之。胡适在北大仅任职三年,其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自然也无力执行。然而,包括他在内的知识人对于学术独立、民族复兴的追求,却仍在战后的中国继续。
结 语
在近代学术史的脉络之中,“学术独立”一直作为学人的追求而存在,不独在政治高压下被知识分子视为安身立命之本,也在民族危亡之时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被寄予众望。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学术独立”也呈现出多重面相,为学人所津津乐道。1947 年关于学术独立的论战由胡适发言而起,首先引起学界关于教育的争论;其后以胡适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为拐点,学界再起波澜。在关于何谓学术独立以及何以实现学术独立的问题上,学人言人人殊。胡适以教育家的角色出现,寄希望于以教育促学术独立,逐渐形成“学术为体,教育为用”的思路。虽其他知识人对此不无异议,然论其最终目的,却与胡适殊途同归。以学术独立促民族复兴之愿望,可视为战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结果。
1947 年胡适提出十年计划,虽延续了其一贯对学术自由、独立的追求,但特殊的历史情境也使之出现了新的特点。北大校长的身份促使其以教育家的身份重新审视彼时中国的学术界。因此,他行学界领头羊之责,不惜主动“惹火上身”,提出引发众议的大胆计划。此举不独使沉寂已久的教育界燃起新的希望,亦使近代以来令学人辗转反侧的西学中学关系问题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也通过报纸、杂志的广泛传播,将高等教育重新拉回大众视野。
胡适关于学术独立之十年计划最终虽然流产,但其以教育促学术的理想却从未泯灭。1958 年3 月26 日,胡适在日记中再次忆起这段往事:“十一年前我曾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主张‘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最大的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正如余英时所言,胡适以“学术独立”作为其终身追求的一个中心价值。而在这一追求的背后,是胡适作为民族主义者对于中华民族振兴的不懈努力。这既是胡适的追求所在,也是近代以来学人的愿景,从而构成了近代中国学术发展川流不息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