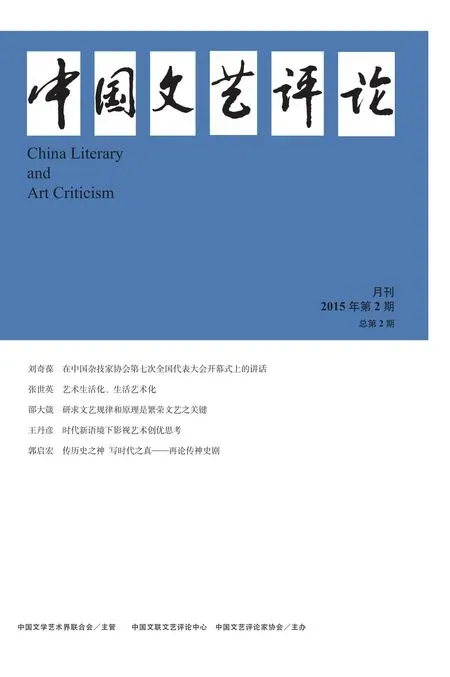孤独的冼星海
——近年来抗战题材音乐创作掠影及思考
项筱刚
孤独的冼星海——近年来抗战题材音乐创作掠影及思考
项筱刚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理论上讲,如此纵深的时间跨度足够中国的艺术家们以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去缅怀、追忆和思考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遗憾的是,与美术界、电影界、文学界等姊妹艺术领域对抗战题材的创作趋之若鹜相比,音乐界稍显滞后——既没有多产,似乎也没有太多的高产(即高质量的作品)。环顾近期大部分国内的“纪念”演出舞台,好像只有孤零零的“两个黄河”——《黄河大合唱》和钢琴协奏曲《黄河》,使得作曲家冼星海顿显孤独。个中原因除了《黄河》作品本身和冼星海的伟大之外,难道就没有其他原因值得今天的中国作曲家深思吗?
除了“两个黄河”,屈指数来,能够给笔者留下较深刻印象的有十余部“纯音乐”作品,基本为“大部头”创作,如交响乐、交响合唱、协奏曲和歌剧、舞剧等。相比之下,“影视音乐”的创作相对活跃,至少首先做到了“多产”,少部分作品亦能够列入“高产”的行列。
一、“纯音乐”创作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期作曲家汪立三曾说过:“我国音乐创作(不光是交响乐),从技术上看,最差的是和声,最缺的是复调”。言中所提状况在此后的一个时间段内一直存在。令人欣喜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纯音乐”的创作水准不论在作曲技术上,还是在立意的深度上,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近年来推出的若干部抗战题材的“纯音乐”作品就颇有说服力,如交响合唱《血祭》(徐景新曲,1994)、交响合唱《金陵祭》(金湘曲,1997)、民族交响乐《和平颂》(赵季平曲,2004)、为大提琴与乐队而作的《我遥远的南京》(叶小纲曲,2005)、交响合唱《和平祭》(叶小纲曲,2007)、管弦乐《让历史告诉未来——南京安魂曲》(徐振民曲,2007)、交响合唱《永不忘却》(关峡曲,2014),以及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张卓娅、王祖皆曲,2005)、舞剧《铁道游击队》(赵麟曲,2010)等。
叶小纲的这部单乐章的大提琴协奏曲《我遥远的南京》,其实是一首深情的交响诗。相比较钢琴、小提琴等其他乐器,单就乐器的独特音色和音乐表现力,大提琴可能是最适于演奏如是历史题材“悲歌”的。张弛有度、寓热情于理性之中的独奏部分,更是携乐队一道将现场听众带回到那段令人心痛的时光。兴许是作品的基调比较沉痛而庄重,整个作品似乎过于冷峻,缺少了些协奏曲常见的戏剧性高潮,尤其是独奏大提琴和乐队之间的“竞奏”好像还没有完全深入展开,故而大提琴部分显得略微拘谨,但这都丝毫没有动摇该协奏曲“凝重、悲愤、深刻地表达了当代音乐家对那件历史事件的看法”。笔者曾两次现场聆听此作。首次是在2005年,由刚刚从法国归国任教的大提琴演奏家朱亦兵演奏。2014年再听旅居澳洲的大提琴演奏家秦立巍的演奏,不难发现:可能是受教育环境和性格的不同吧,“朱版”的演奏比较华彩、较富有激情,而“秦版”则更冷静,充满着“文雅的乐感”。
《和平祭》是作曲家叶小纲应江苏演艺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委约,于2007年为新落成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落成而创作。面对这部为女高音、男中音、合唱队和交响乐队而写的作品,笔者再次想到一个问题:近年来叶小纲似乎对为“人声”和“乐队”而写的“宏大叙事”情有独钟,如《大地之歌》(Op.47)、《岭南四首》(Op.62)、《〈临安七部〉——为女高音、男高音、男中音与乐队而作》(Op.63)、《〈共和之路〉——为清唱剧而作》(Op.64)、《悲欣之歌——为男中音与乐队而作》(Op.67)和《喜马拉雅之光》(Op.68)等;或许是有感于“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或许是一个成熟的作曲家对自己以往器乐创作思维的超越……交响合唱《和平祭》的第一乐章《南京》、第二乐章《石头城》和同名第三乐章,依然承袭了作曲家近年来的一贯作风——“游走于传统与现代手法之间”。在该乐章带再现的单三部曲式结构中,频繁的调性转移赋予了音乐丰富多彩的音色,而3个核心旋律音调的贯串进行,使得该乐章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而恰恰是这种调性与无调性、旋律与非旋律的并存,反而为抒发这种难以言表的“让孩童入睡,让母亲安心”之情感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选自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碑文的歌词虽也押韵,但基本上都是结束在闭口音上,不论是语言美感,还是朗朗上口方面,都留下了少许的遗憾,虽然这不在作曲家本人的掌控范围之内。
叶小纲的上述两部作品,不论是大提琴协奏曲《我遥远的南京》,还是交响合唱《和平祭》,既没有“用音乐来图解画面”,也没有“大写意式”的“泼墨”,而是以“叶氏风格”独有的“用器乐化思维来歌唱”。作为一位同时活跃于“纯音乐”和“影视音乐”领域并跃居为中国现代音乐和影视音乐的领军人物之一的作曲家,叶小纲在这两个领域内的创作已逐步相互渗透、影响,并产生双赢的艺术效果。就“纯音乐”而言,其以高产的作品引领着国内现代音乐创作和受众前行;就“影视音乐”而言,其以多产的作品——电影《人约黄昏》(1995)、《半生缘》(1997)、《洗澡》(1999)、《刮痧》(2001)、《太行山上》(2005)和电视剧《玉观音》(2003)、《大国崛起》(2006)等让自己的音乐理念飞入“寻常百姓家”,并在不经意间使得自己的“纯音乐”创作能够多少“接地气”。
徐振民的《让历史告诉未来——南京安魂曲》是江苏省文联和音协的委约之作,完成于2007年。该曲完全改变了原先笔者对作曲家1991年创作的音诗《枫桥夜泊》之“幽远意境”的印象。7个部分的不间断演奏,简洁、形象、完整地讲诉了那段难忘的历史惨剧,即使不看节目单,也不难看出作曲家有着用音乐来图解画面的“企图”。虽然创作手法比较传统,但结构之严谨、旋律之酣畅、音色之丰富、张力之层层递进,足显老辈作曲家徐振民创作笔法之炉火纯青。毋庸讳言,与今天的很多中、青年作曲家相比,此《南京安魂曲》没有追求“超理性”的复杂技术,而是代之以简练的技法,以期将受众的“听得懂”和“可听性”置于首位,从而唤起受众与作曲家之间的通畅交流。换言之,作曲家显然在下笔之初将“受众群”指向了普通大众,而并非有着良好音乐修养的音乐爱好者或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专业音乐家们。很明显,作曲家的本意亦希望自己的这部安魂曲能够被包括南京市民在内的广大受众所接受。令人欣慰的是,通过音乐会现场受众的反应,足见此良好愿望已然实现。
在聆听此《南京安魂曲》之时,笔者不禁想起了令人难忘的、如火如荼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交响音乐创作。尽管时光飞逝,然今天重温《第二交响曲——抗日战争》(王云阶曲,1959)等50年代的作品或如是风格的“老作曲家”(即50年代的青年作曲家)的新作品,仍倍感亲切。原因何在?因为诸作品具备50年代中国交响乐创作的普遍性特点——浓郁的民族风格,直观的作品标题,鲜明的音乐形象,甘美的旋律,对西方古典派、浪漫派和苏俄乐派的模仿与借鉴……时过境迁,虽然今天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作曲家渴望与听众心心相印、听众希望能够从音乐中感受到“美”或“启迪”,到任何时候应该都不会发生变化。对此,笔者坚信不疑!
与笔者听过的诸追忆历史题材的乐队作品不同,上述作品均一扫以往诸同类题材作品第二人称的“冷静”或第三人称的“发问”,而取而代之的是以第一人称的叙述,其中以叶小纲的《我遥远的南京》尤甚。几位作曲家虽有着年龄差距,但在叙述时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第一人称的语气,讲述了一个好像是发生在自己或自己家人身上的故事,自始至终流露的都是浓浓的哀思、深深的祈福,几乎难觅声嘶力竭的怒吼和板起面孔的说教。也许换个角度,这不正是中国作曲家和中国交响音乐创作茁壮成长的脚步声吗?
二、“影视音乐”创作
与清静的“纯音乐”创作相比,近年来抗战题材的“影视音乐”创作则显得相对活跃,尤其是电视剧音乐。包括前文提到的几位作曲大家在内的一批中、青年作曲家纷纷将关注的笔触指向抗战题材的“影视音乐”创作,并在不经意间形成了一支颇具梯队建设的创作队伍。在这支队伍中,既有造诣享誉海内外的叶小纲、赵季平、陈其钢、邹野,亦有响彻大江南北的印青、董立强、李海鹰、李戈,以及已然在当下影视舞台崭露头角的林朝阳、丁薇、常馨内、徐之彤、张征、冯达、马上又和阿鲲等。诸作曲家由于“职业”、经历和受教育的履历不同,相应的在作品中呈现出风格迥异的特点:如电视剧《新四军》(印青曲,2003)和《亮剑》(李海鹰曲,2005)中旋律之流动及甘美,电视剧《八路军》(董立强曲,2005)和《中国远征军》(张征曲,2011)中交响化思维及其悲壮性,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林朝阳、丁薇曲,2009)和《太行山上》(徐之彤曲,2015)中弦乐的如歌,电视剧《狼烟北平》(常馨内曲,2009)和《远去的飞鹰》(冯达曲,2011)中对人物性格刻画的惜墨如金,电视剧《悬崖》(马上又曲,2012)和电视剧《红高粱》(阿鲲曲,2014)中常规手法与非常规手法的适度融合等。
在诸代表作品中,叶小纲作于2005年的电影《太行山上》音乐给笔者印象颇为深刻,彰显出浓烈的“叶氏风格”。不论是和同代作曲家相比,还是与年轻一代作曲家相比,叶小纲无疑拥有得天独厚的接受音乐教育的重要资源——家庭的熏陶。其父叶纯之(1926—1997)于20世纪50年代为港台的多家电影公司创作配乐和插曲。尤其是为林黛的电影处女作《翠翠》谱写的插曲,被香港学界誉为“一扫当时海派歌曲的颓风,正式开展了‘港式时代曲’的道路”。现如今,叶小纲不仅有着乃父之风——同时活跃于“纯音乐”和“影视音乐”创作领域,并跃居为中国现代音乐和影视音乐的领军人物之一。从表面上看,叶小纲之所以在征战“纯音乐”舞台的同时还选择纵横于“影视音乐”舞台,除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必须考虑到大众的审美。其近年来在两个舞台上取得的成绩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当然,也许是时代使然,也许是审美标准发生了微妙变化,也许是今天的人们选择文化生活的途径更加多元化,叶小纲的影视歌曲更倾向于“流行歌曲化的艺术歌曲”,且其插曲创作的数量和传播与乃父相比要略显逊色,尽管这丝毫不会削弱叶小纲影视音乐在中国当代影视音乐史上的地位。
作为新时期影视音乐创作的领军人物之一,赵季平于1991年后进入了他的影视音乐创作的第三个阶段。在电影《烈火金刚》(1991)、《铁血昆仑关》(1994)、《飞虎队》(1995)、《一九四二》(2012)和电视剧《狼毒花》(2007)等作品中,作曲家总是能够根据剧本故事发生地来谨慎地选择相关音乐素材和地域特色浓郁的主奏乐器,不论是戏曲曲牌,还是各地民间音乐,都能够在融入西洋交响乐、现代多调性等作曲技法同时而形成二者不协调的碰撞,从而体现出他的影视音乐创作已经走向成熟,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在立意、创新方面已经超越了影视作品本身。故而,上述代表作反映出较为鲜明的“赵氏风格”,尤其是其浓厚的地域色彩,使得其影视音乐作品的“画面感”很强。
与鲜明的“赵氏风格”相比,邹野的“邹氏风格”初见端倪,尤其是其严谨的弦乐对位部分,为电视剧母体平添了几多历史的厚重感。这一点在电影《张思德》(2004)和电视剧《闯关东》(2009)、《长沙保卫战》(2014)、《大河儿女》(2014)中表现得尤甚。
叶小纲、赵季平、邹野三人影视音乐创作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对弦乐群集团音色的情有独钟,与那种完全靠单一的电子合成器支撑全剧的风格大相径庭,在与影视母体形成“血浓于水”的同时,也给受众群体带来了另一种审美体验。抛开作曲家也要“食人间烟火”这个因素,三位大家对音乐艺术的敬畏、执著,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内,恐怕令同时代的部分作曲家难以望其项背。笔者斗胆地畅想:当越来越多的“叶氏风格”、“赵氏风格”、“邹氏风格”……逐步登上中国影视音乐创作的舞台,一个新的音乐流派——“中国影视音乐创作群”遂将崛起。
正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影视音乐一样,近年来部分抗战题材影视音乐创作表现出与其所依附的影视母体极不相称——没有能够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的状况。确切地讲,2007、2009、2010、2012、2015年,均有颇能吸引人眼球的抗战影视大戏推出,不论是剧本,还是演员表演,也不论是舞美,还是导演,都令人叹为观止。唯独音乐,令人听后顿生恨铁不成钢之感慨。说得再通俗点,就是影视剧很好,音乐却不好。究其原因,除了主创者“开源节流”,影视编导自身音乐修养的有待提高、作曲家的闭门造车亦同样不容忽视。
此外,与激情燃烧的“十七年”(即1949年—1966年)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即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相比,近年来的影视音乐创作队伍缺乏像吕其明、高如星、雷振邦、傅庚辰、王酩、王立平和谷建芬等那样备受广大受众欢迎的影视歌曲作曲家。“十七年”“新时期”的电影音乐多为“声乐思维”,缺少“器乐思维”;上个世纪90年代后,乃至近年来,影视音乐创作似乎生怕别人指责自己“落伍”,故而矫枉过正——一头扎进“器乐思维”的怀抱,反而将中国受众最情有独钟的“声乐思维”——旋律给冷落了。君不见“十七年”“新时期”的诸多影视插曲即为当时的妇孺皆知的流行歌曲吗?此现象如再不给予必要的重视,笔者担心一部分影视音乐作曲家或许将丧失歌曲写作的能力。但愿这仅仅是笔者的杞人忧天。
三、问题与思考
毫无疑问,抗战题材的“纯音乐”创作和“影视音乐”创作未能并驾齐驱。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然有一点却很清晰——“影视音乐”创作首先是面向大众的,而“纯音乐”创作却不单单是面向大众的,故“影视音乐”创作能够乘着“影视”作品的翅膀传播更远、辐射更广、影响更大。就这一点而言,二者未能平衡发展好像也是在情理之中。
纵观近年来的抗战题材音乐创作,无论是“纯音乐”创作,还是“影视音乐”创作,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一)题材撞车、重复,如关于“南京大屠杀”、“铁道游击队”均颇受编导、出品方和作曲家的青睐。前者如为大提琴与乐队而作的《我遥远的南京》(叶小纲曲,2005)与交响合唱《和平祭》(叶小纲曲,2007)、管弦乐《让历史告诉未来——南京安魂曲》(徐振民曲,2007)、交响合唱《金陵祭》(金湘曲,1997)、民族交响乐《和平颂》(赵季平曲,2004)、电影《南京大屠杀》(谭盾曲,1996)和《金陵十三钗》(陈其钢曲,2011)等。后者如电影《铁道游击队》(吕其明曲,1956)和《飞虎队》(赵季平曲,1995)、电视剧《铁道游击队》(郭建勇曲,2005)和舞剧《铁道游击队》(赵麟曲,2010)等。
(二)一部分影视音乐作品将“音乐”与“音效”近似等同化,甚至完全以“音效”代替“音乐”。对此,笔者则不然。曾听一位影视音乐作曲家说过,近年来影视音乐创作存在着一个趋势——“音乐”的“音效化”或“音效”的“音乐化”。 “音乐”是艺术,“音效”是技术。换言之,技术最终是为艺术服务的。如果将技术和艺术混淆,或将技术由“手段”上升为艺术这个“目的”,那就南辕北辙了。遗憾的是,此现象大有愈演愈烈之风,不知是作曲家的“大题小做”,还是经济利益使然?
(三)不论是“纯音乐”作品,还是“影视音乐”作品,均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缺少时代特征。有些“纯音乐”作品,如果离开了标题、节目单或歌词,听众很难从中判断出此乃“抗战题材”。相比之下,此特征在“影视音乐”作品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众所周知,抗战时期,无论是“沦陷区”“国统区”,还是“根据地”,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各有千秋,却依然呈现出相对统一的时代特征。但是,此时代特征在相当一部分抗战题材的影视音乐作品中可谓难觅。更有甚者,竟然有剧中人在“抗战期间”演唱/欣赏“抗战胜利”后的歌曲/音乐,在损害影视作品母体历史真实性的同时,也令人顿生拿历史当儿戏的担忧。
(四)民族风格是一个永远说不清、道不尽的话题,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本文中,民族风格可以狭义的理解为:不论是“纯音乐”作品,还是“影视音乐”作品,最终将主要面向中国受众群体。换句话说,如果某抗战题材音乐作品公演/开播后,大部分国内受众竟然没听出这是写“中国”的抗战的,那我们只能说该作品民族风格不甚明显。在2007年公映的亚历山大·迪斯普拉特(Alexandre Desplat, 1961— )创作的电影《色戒》音乐中,虽然编导为了加强影片的历史真实感,特意在剧情中巧妙地穿插了聂耳的《毕业歌》、贺绿汀的《天涯歌女》等多首在民国时期广为流传的歌曲,也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效果,但仍无法遮掩外国作曲家配乐民族风格淡化的局限。换言之,该影片讲的是“中国故事”,然音乐却完全是“好莱坞式”的,令人很难将听觉和视觉效果合二为一,虽然该片配乐荣获第44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奖。就这一点而言,作曲家赵季平的作品为其他作曲家提供了多个成功的范例。
笔走至此,笔者有两个愿望油然而生:第一,寄希望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时,国内的舞台上将会涌现出“几部”或“一批”可以与“两个黄河”比肩的作品。第二,寄希望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时,有更多的作曲家加盟抗战题材的音乐创作,包括“纯音乐”和“影视音乐”创作。
上述两个愿望一旦实现,笔者坚信“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站在高山之巅”一定不会像现在如是孤独。但愿,这不仅仅是笔者的一厢情愿。
注释
[1] 为了以示与“影视音乐”创作的区别,本文将传统意义上的音乐创作称之为“纯音乐”创作。
[2] 汪立三:《在全国交响音乐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人民音乐》1983年第4期,第13页。
[3][4] 详见2014年12月12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和平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纪念音乐会”节目单。
[5] 电影《太行山上》2005年荣获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
[6] 详见黄奇智编著:《时代曲的流光岁月(1930-1970)》,第88页,香港三联书店,2000年。
[7] 详见拙文:《从四部作品看新时期电影音乐的中国流派》,《电影艺术》2007年第6期。
项筱刚:中央音乐学院副研究员、中国当代音乐博士
(责任编辑:张玉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