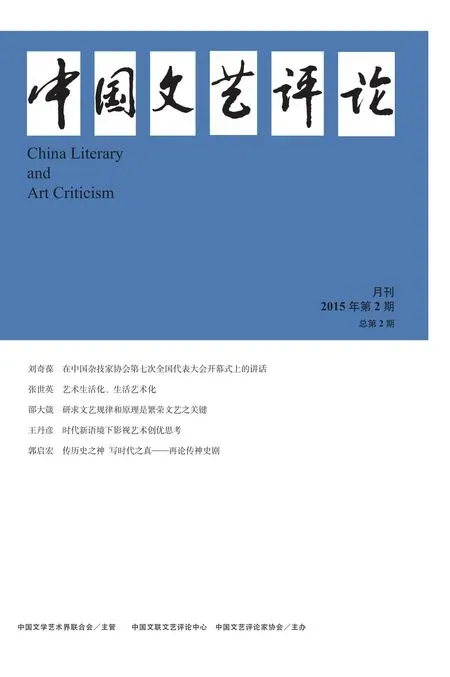中国艺术的三个维度:自然、心灵和文化
彭锋
中国艺术的三个维度:自然、心灵和文化
彭锋
清代画家郑板桥(1693—1765)有一段题竹的文字,能够很好说明中国艺术所蕴涵的多重审美维度。那段脍炙人口的文字是这样的:
“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
在这段文字中,郑板桥区分了三种竹,即“眼中之竹”、“胸中之竹”和“手中之竹”。笼统地说,所谓“眼中之竹”,就是画家亲眼所见的竹子,可以称之为自然的竹子;所谓“胸中之竹”,就是画家心灵领会的竹子,可以称之为心灵的竹子;所谓“手中之竹”,就是画家用笔墨画在纸上的竹子,可以称之为文化的竹子。弄清楚这三种竹子的实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理解中国艺术的关键。
一
郑板桥那段题竹的文字是从艺术家创作的角度来描述的。从艺术家创作的角度来说,他首先要有“眼中之竹”,要对客观存在的事物有仔细的观察;中国艺术家常常描绘自己所熟悉的事物。比如,清代画家邹一桂曾经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宋曾云巢无疑,工画草虫,年愈迈愈精。或问其何传,无疑笑曰:‘此岂有法可传哉?某自少时,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夜不厌。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复就草丛间观之,于是斯得其天。方其落笔之时,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也?此与造化生物之机缄盖无以异。岂有可传之法哉?’”
曾云巢对草虫的观察之仔细,恐怕会让今天的许多画家叹为观止。在邹一桂看来,曾云巢画草虫之所以出神入化,关键在于他的观察的精细。诸如此类的故事在中国绘画史上屡见不鲜。但是,如果据此以为中国画家是在描述自己的观察对象,那就错了。作为观察对象的“眼中之竹”并不是艺术家直接描绘的对象,艺术家直接描绘的对象是“胸中之竹”。现在的问题是,“眼中之竹”与“胸中之竹”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有两种哲学主张“眼中之竹”与“胸中之竹”之间没有区别。一种是尼采(Friedrich Nietzche)式的透视主义,它主张“眼中之竹”就是“胸中之竹”,因为我们不可能离开心灵的解释看见纯粹自然的竹子。纯粹自然的竹子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关于竹子的解释。如尼采所说,“准确地说,事实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解释。”如果我们眼睛看见的竹子就是我们心灵解释的竹子,那么就只有心灵的竹子而没有自然的竹子,因为我们以为眼见的是纯粹自然的竹子而事实上已经经过了我们心灵的解释。这样,“胸中之竹”与“眼中之竹”的区别就没有意义。另一种是一般的认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它强调“胸中之竹”就是“眼中之竹”。由于我们心灵所理解的竹子是对眼睛所看见的竹子的精确反映,因此“胸中之竹”与“眼中之竹”之间尽管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区别,但这些区别都无关紧要。换句话说,由于这种反映不允许加入心灵的解释,因此实际上只有自然的竹子而没有心灵的竹子。尽管这两种哲学视野非常不同,但它们取消“眼中之竹”与“胸中之竹”之间的差异是共同的。因此,这两种哲学视野都无法解释郑板桥对“眼中之竹”与“胸中之竹”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因为郑板桥明确指出“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
如何来理解“眼中之竹”与“胸中之竹”之间的差异呢?我们可以简单地说,“眼中之竹”与“胸中之竹”是两类在本体论上完全不同的事物,“眼中之竹”是物理的存在,“胸中之竹”是心理的存在。但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中这种本体论的区分并不明确,因此郑板桥所理解的“眼中之竹”与“胸中之竹”之间的差异一定不止于这种本体论的差异。“胸中之竹”除了代表或反映“眼中之竹”外,还代表或反映了某些别的东西,这种别的东西就是画家的“画意”,它包括画家的意图、情感、理解乃至整个人格等等。当然,这里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而将“胸中之竹”分解为两个方面来说,而实际上只有不可分割的、完整的“胸中之竹”。
“胸中之竹”是画家对“眼中之竹”的理解,体现了画家独特的内心世界。中国艺术强调除了再现事物的外部世界之外,还要着重表现艺术家的内心世界。如果只着重描绘“眼中之竹”,艺术家的任务就最多只完成了一半,即忠实地再现外部事物。只有着重描绘“胸中之竹”,艺术家才能完成他的全部目的,即既再现外部事物又表现内心情感。更重要的是,根据中国古典美学的主张,只有经过“胸中之竹”的阶段,才能把握外在事物的精神,进而更准确地再现外在事物的形态。这是因为“胸中之竹”是画家对“眼中之竹”的主要特征的把握,它摆脱了“眼中之竹”的各种与主题无关的细节,从而能够集中突出竹子的某些内在品性。因此,中国艺术中所说的表现不仅是表现艺术家的主观精神世界,而且也表现事物的客观精神世界,进而能够更加精确地再现事物的外在形态。比如,明代画家祝允明就特别强调“物物有一种生意”。他说:
“绘事不难于写形而难于得意,得其意而点出之,则万物之理,挽于尺寸间矣,不甚难哉!或曰:‘草木无情,岂有意耶?’不知天地间,物物有一种生意,造化之妙,勃如荡如,不可形容也。”
显然,这种“生意”与“形状”不同,“生意”是心灵领会的对象,“形状”是眼睛观看的对象。“生意”属于“胸中之竹”,“形状”属于“眼中之竹”。中国古典美学甚至强调,只有先用心灵领会到事物的“生意”,然后才能用眼睛“看清”事物的“形状”。如柳宗元有一段著名的评论:
“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
兰亭有水有竹,但如果没有王羲之的心灵的领会,兰亭的水就没有那样的“清”,竹就没有那样的“修”。在这里,“清”和“修”不是指兰亭的水和竹的物理性质,而是指水和竹的一种感觉性质,是属于水和竹的“生意”方面的内容。由于王羲之的心灵的领会,凸显或照亮了兰亭之水和竹的“生意”或感觉性质,从而使兰亭之水和竹成为审美欣赏的对象。
心灵的领会对事物的“ 生意”或感觉性质的凸显或照亮,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创造。清初哲学家王夫之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说:
“‘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谯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
在王夫之看来,诗人的创作并非是先有一个确定的风景如“长河落日圆”,然后再找适当的词语去描绘这种风景,而是相反,诗人用他的诗句“长河落日圆”创造了如此这般的风景。如果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里的情况就不是像郑板桥所说的那样,先有“眼中之竹”,然后才有“胸中之竹”,而似乎先有“胸中之竹”然后才有“眼中之竹”。但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王夫之所说的创造,实际上并不是一种主观臆想,而是一种重新发现。王夫之对“现量”的解释是:
“现量,现者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
通过心灵领会凸显、照亮或创造的东西,其实就是事物的本来面貌。心灵的创造越活跃,事物的显现越真实。换句话说,越经过心灵洗礼的东西就越自然。这是中国美学最为独特的地方,当然也是最费解的地方。
现在,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代表自然的“眼中之竹”与代表心灵的“胸中之竹”的关系。我们前面已经指出,一方面,中国古代美学家并没有采取尼采式的极端的解释学立场,认为“眼中之竹”就是“胸中之竹”。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美学家又强调“胸中之竹”对“眼中之竹”的凸显、照亮甚至创造。如何来理解这种看似矛盾的关系呢?这种矛盾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交叠的关系,即自然与心灵的交叉影响的关系。“眼中之竹”影响到“胸中之竹”,“胸中之竹”又影响到“眼中之竹”,这种交互影响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也不知道在哪里结束。正是由于自然与心灵的这种交叠关系,尽管我们可以将自然与心灵分别开来,但它们实际上是互相纠缠、相互限制的。这种交叠在艺术上导致的结果是:无论“胸中之竹”多么不同于“眼中之竹”,我们都应该能够在“胸中之竹”中辨认出“眼中之竹”。
二
如果仔细分析,说从“胸中之竹”中辨认出“眼中之竹”,这种说法好像是有问题的,因为纯粹的“胸中之竹”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之所以能够说从“胸中之竹”中辨认出“眼中之竹”,原因在于我们假定画面上描绘的就是“胸中之竹”,至少我们可以说画面上描绘的竹子更接近“胸中之竹”而不是“眼中之竹”。但是,画面上直接呈现的不是“胸中之竹”,而是“手中之竹”。郑板桥明确说到“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这里,“胸中之竹”与“手中之竹”又具有怎样的差别呢?
当然,我们仍然可以从本体论上来指出它们之间的差别:“胸中之竹”是一种心理的存在,“手中之竹”是一种物理的存在。但是,这种本体论的区分并不能充分解释郑板桥心目中的那种区分。根据一般的理解,“胸中之竹”应该是“眼中之竹”的再现,而“手中之竹”又应该是“胸中之竹”的再现,因此“手中之竹”也就是“眼中之竹”的再现。绘画就是对事物外形的忠实描绘。但是,郑板桥对绘画的理解与这种一般看法不同。“胸中之竹”包含并大于“眼中之竹”,“手中之竹”包含并大于“胸中之竹”。如果说“胸中之竹”比“眼中之竹”多出来的东西是画家的心灵和人格,那么“手中之竹”比“胸中之竹”多出来的东西就是中国绘画的历史和文化。
绘画是一种文化符号形式,一种语言形式,这在中国绘画的历史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一个画家要画竹子,首先要掌握画竹子的语言。画家是在用语言说话,而不是直接地、机械地复制“胸中之竹”和“眼中之竹”。由于绘画语言(如各种笔法和墨法)有自身的语法和历史,因此符合它的语法进入它的历史的东西才能称得上是绘画。如果没有掌握中国绘画的语言,不管画出来的东西多么逼真,在中国画家看来,它们都不是绘画。比如,清代画家邹一桂曾经对西洋画做过这样的评价:
“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布影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学者能参用一一,亦具醒法。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
从这段评论中可以看出,邹一桂承认西洋绘画非常逼真,而且并不反对绘画追求逼真性,不反对中国画家学习西洋绘画的某些方法。但是,邹一桂强调绘画的关键并不在于逼真性,而在于绘画语言即笔法。不用绘画语言描绘的东西无论多么逼真也不能称得上是绘画,在这种意义上,也许在某些中国画家看来,中国绘画与西洋古典油画之间的差别差不多就像西洋古典油画与照相之间的差别一样。
由于中国画家特别强调绘画语言本身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绘画能够很好地支持古德曼(Nelson Goodman)美学理论。在古德曼看来,艺术跟自然和心灵的再现或表现无关,判断一个东西是否是艺术作品,不是看它是否忠实地再现了它所描绘的对象,而是看它的语言是否符合艺术语言的特征。根据古德曼的总结,艺术语言的特征或审美征候(symptoms of the aesthetic)有这样五种:
(1)句法密度,其中在某些方面的最细微差别构成了符号间的差异——比如,一支没有刻度的水银温度计同一个电子读数仪器的对比;(2)语义密度,其中符号是由以某些方面的最细微差别区别开来的事物所规定的(不仅仍可以以那支没有刻度的温度计为例,而且可以以日常英语为例,尽管这种英语并不具有句法上的密度);(3)相对的充盈,其中比较而言,一个符号的许多方面都有意义——比如,由北斋(Hokusai)所作的工笔山水画,其中形状、线条和厚度等等每个方面的特征都有价值,这与股市日均线图上的也许完全相同的条线形成对照,那里线条的全部意义就是在底部之上的线条的高度;(4)例示,其中一个符号,无论其是否有所指谓,都会因为作为它在字面上或在隐喻意义上所具有的特性的例子而具有符号的作用;最后(5)多重的和复杂的含义,其中一个符号起几个整合的和相互作用的意指功能,某些是直接的,某些是通过其他符号中介的。
中国艺术家对艺术语言本身意义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古德曼从语言的特征上去确定它的审美征候。比如,五代画家荆浩强调笔有四势:“谓筋、肉、骨、气。笔绝不断谓之筋,起伏成实谓之肉,生死刚劲谓之骨,迹画不败谓之气。故知墨大质者失其体,色微者败正气,筋死者无肉,迹断者无筋,苟媚者无骨。”我们可以把这里的“筋”、“肉”、“骨”、“气”看作中国绘画语言的四种审美征候。近代美学家王国维对“古雅”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艺术语言本身的审美价值的强调,即对文化而不是自然和心灵的审美价值的强调。王国维说:“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就美之自身言之,则一切优美皆存于形式之对称变化及调和。至宏壮之对象,汗德(即康德)虽谓之无形式,然以此种无形式之形式能唤起宏壮之情,故谓之形式之一种,无不可也。……除吾人之感情外,凡属于美之对象者,皆形式而非材质也。而一切形式之美,又不可无它形式以表之,惟经过此第二之形式,斯美者愈增其美,而吾人之所谓古雅,即此第二种之形式。即形式之无优美与宏壮之属性者,亦因此第二形式故,而得一种独立之价值,故古雅者,可谓之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也。”
王国维这里说的“古雅”如同古德曼所说的审美征候一样,与艺术表达的内容完全无关,只是艺术形式或语言本身的特征,因此王国维称之为“形式美之形式美”。不过,跟古德曼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美学家对艺术语言的强调并没有导致他们彻底否定艺术的再现或表现功能。甚至,为了突出艺术的再现或表现功能,艺术家常常需要对艺术语言加以限制。清代画家布颜图有段话很能够说明问题:
“意之为用大矣哉!非独绘事然也,普济万化一意耳。夫意,先天地而有,在《易》为几,万变由是乎生;在画为神,万象由是乎出。故善画者,必意在笔先。宁使意到而笔不到,不可笔到而意不到。意到笔不到,不到即到也;笔到而意不到,到犹未到也。何也?夫飞潜动植,灿然宇内者,意使然也。如物无斯意,则无生气,即泥牛、木马、陶犬、瓦鸡,虽形体备具,久视之则索然矣。如绘染山川,林木丛秀,岩嶂奇丽,令观者瞻恋不已,亦意使然也。如画无斯意,则无神气。即成刻板舆图,照描行乐,虽形体不移,久视之则索然矣。”
如前面谈到的“生意”一样,布颜图这里所说的“意”也不是指一种主观情意,“意”在这里似乎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如果说“笔”指的是艺术语言,“意”指的是艺术语言所传达的对象,那么很明显,布颜图更强调艺术语言所传达对象的重要性。如果说艺术语言在更大的范围内属于文化,而艺术语言所传达的对象在更大的范围内属于自然和心灵,那么布颜图似乎更强调心灵和自然在艺术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了一种交叠关系,即心灵(包括自然在内)与文化之间的交叉影响,“手中之竹”影响“胸中之竹”,“胸中之竹”影响“手中之竹”。如同在心灵中显现的自然更自然一样,在文化中显现的心灵更灵动,这种对比关系似乎是不难理解的。
三
至此为止,我们已经分析了“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含义,并且着重分析了“眼中之竹”与“胸中之竹”、“胸中之竹”与“手中之竹”之间的关系。我把这种关系称之为交叠关系,即自然与心灵之间、心灵与文化之间的交叉影响。不过,在郑板桥的那段题字中还隐含着一层意思向来为人所忽视,这就是文化与自然之间的交叠关系,也就是“手中之竹”与“眼中之竹”之间的交叠关系。显然,这种交叠关系比上述两种交叠关系要晦暗得多。这种关系隐含在这样的文字之中:“落笔倏作变相”;“趣在法外者,化机也”。
我们把“手中之竹”大致归属到艺术语言的范围,认为它与艺术的历史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任何语言都是有法则的,任何文化都是讲规则的,“手中之竹”同样如此。欣赏“手中之竹”事实上主要欣赏的是笔墨的规则和历史。但艺术不是抽象地执行规则,艺术并不等于语言。“手中之竹”不仅是艺术语言的体现,同时是艺术家身体动作的体现。通过身体动作这个环节,我们可以找到文化与自然之间的一种曲折的交叠关系。
倏即快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果断,理解为身体执行的自然而然。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在中国美学史上屡见不鲜。比如,苏轼描写文与可画竹的情景说: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
苏轼在这里讲的不仅是时间上的快捷,而且是身体动作上的果断、自然流畅、毫不迟疑。《清稗类钞》中记载傅青主于中秋之夜作画的故事:
“天气晴爽,风定月明之际,命侍者取所研浓墨一巨钵,置旁几,屏退诸人,独自命笔。友远立窃视,但见舞蹈踊跃,其状若狂。友迳趋至背后,力抱其腰。傅狂叫,叹曰:‘孺子败吾清兴,奈何!’遂掷笔搓纸而缀。”
中国美学对身体动作,对执行行为的自律性的强调,为我们理解自然与文化之间的隐晦的交叠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契机。笔墨是“手中之竹”的体现形式,身体动作是“手中之竹”的执行形式。笔墨是中国绘画的独特语言,属于文化的范畴;身体动作是绘画语言的执行形式,属于自然的范畴(我们完全可以把人的身体也适当地看作自然的一部分)。由此,中国艺术中自然与文化的交叠,不是直接表现在“眼中之竹”与“手中之竹”的交叠上,而是表现在属于文化的笔墨与属于自然的身体动作的交叠上。中国艺术中讲的“自然”,更多的不是自然对象,而是指自然状态。比如,如果说文与可画的竹子具有自然的品格,并不是指文与可画的竹子跟自然生长的竹子一模一样,而是指他的绘画语言的表达自然而然、毫不迟疑,这种自然而然建立在一种完全自律的身体动作上。因此,中国美学中讲的“自然”或“不自然”,很少是在对象的“像”或“不像”的意义上讲,而是在动作的自律或不自律的意义上讲。一个京剧表演大师表演骑马很自然,他的徒弟则不那么自然,并不是说大师手中的那根马鞭比徒弟手中的那根马鞭更像马儿奔跑的样子,而是说大师的动作比徒弟的动作更果断、更干脆、更自然。当然,中国艺术家也相信,如果动作自然了,动作所表达的对象也就会更像,不仅形似而且神似。
作为绘画语言的笔墨不仅是抽象的规则,而且是具体的动作;中国艺术家既要尊重规则的必然性,又要体现动作的自然(自由)性。这里的交叠也就在所难免。如果说中国艺术由于强调语言而导致向高度的符号化或程式化方向发展的话,那么由于强调身体动作的自律性又导致对超符号表达的境界的追求。例如,在传为荆浩所作的《山水节要》中,作者强调“使笔不可反为笔使,用墨不可反为墨用”。对超符号表达的自然境界的追求,是中国艺术的最终目的。
四
最后,让我从欣赏者的角度对上述讨论做点简要的总结。我们要欣赏中国艺术,不仅要欣赏艺术家所描绘的自然对象(“眼中之竹”),而且要进入艺术家的心灵世界(“胸中之竹”),与艺术家进行精神上的沟通和交流,同时还要能够欣赏艺术语言,进入中国艺术的文化世界和历史语境。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欣赏自然、心灵和文化这三种看似矛盾的因素如何在一种交叠影响关系中达成平衡。中国艺术对心灵领会(“胸中之竹”)的强调,原因在于它要将表现对象从自然束缚中解放出来,以便能够采取自由的符号表达的方式。但符号表达的自由本身不是目的,中国艺术的更高目的是一种超符号表达的自然境界。对于这种自然境界的把握需要我们想象艺术家的身体动作,乃至艺术家的整个生活方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艺术的精髓也许既不在于观察(“眼中之竹”),也不在于冥想(“胸中之竹”),而在于表演(“手中之竹”)。
注释
[1] 郑板桥:《郑板桥集·题画》,见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6页。
[2] 邹一桂:《小山画谱·卷下·草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比如,苏辙在《墨竹赋》中也尤其强调文与可对竹子的仔细观察。苏辙转述文与可的话说:“夫予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始予隐乎崇山之阳,庐乎修竹之林。视听漠然,无概乎予心。朝与竹乎为游,暮与竹乎为朋。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阴,观竹之变也多矣。”(《栾城集·卷十七·墨竹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Friedrich Nietzche.The Will to Power.New York:Vintage Press, 1968.481
[5] 关于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分析,见Amie L. Thomasson.“The Ontology of Art”.In:Peter Kivy,ed.The Blackwell Guide to Aesthetics.Oxford: Blackwell, 2004.78~92
[6] 祝允明:《枝山题画花果》,同治刊本《枝山文集》。
[7] 柳宗元:《邕州马退山茅亭记》,见叶朗总主编:《中国历代美学文库·隋唐五代卷·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4页。
[8] 关于审美体验的“照亮”和“唤醒”功能的分析,见叶朗主编:《现代美学体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65-569页。
[9] 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见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4册),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820页。
[10] 王夫之:《相宗络索·三量》,见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3册),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536页。
[11] 邹一桂:《小山画谱·卷下·西洋画》,见叶朗总主编:《中国历代美学文库·清代卷·中》,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0页。
[12] Nelson Goodman.“When Is Art?”.In:Thomas E.Wartenberg.The Nature of Art:An Anthology.Beijing:Peking University,2002.207
[13] 荆浩:《笔法记》,见叶朗总主编:《中国历代美学文库·隋唐五代卷·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52页。
[14] 见:《王国维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2页。
[15] 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见叶朗总主编:《中国历代美学文库·清代卷·中》,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20页。
[16] 苏轼:《文与可画篔簹谷偃竹记》,《苏东坡全集(上册)》,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1986年,第394页。苏轼对孙知微的作画过程也作过生动的描写:“始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数岁,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笔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苏轼:《书蒲永升画后》,《苏东坡全集(上册)》,第303页)
[17]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038页。
[18] 叶朗总主编:《中国历代美学文库·隋唐五代卷·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55页。
彭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胡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