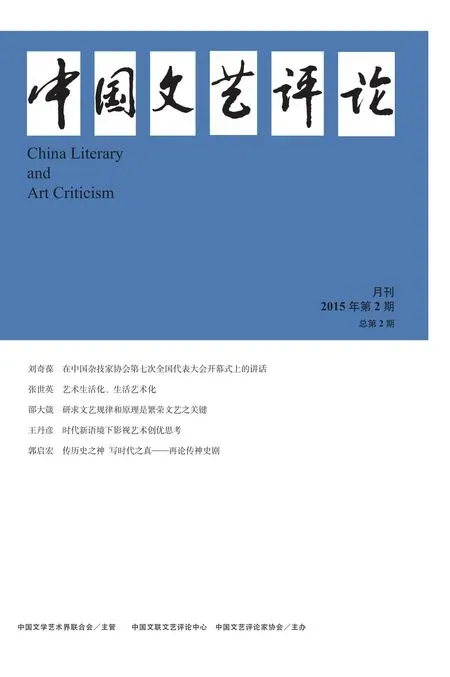季札观乐与中国审美批评之诞生
刘成纪
季札观乐与中国审美批评之诞生
刘成纪
近代以来,在由真、善、美构建的人类知识体系中,真指向科学,善指向道德,美则指向文学艺术。也就是说,文学艺术虽然具有启人心智、增进道德等种种功能,但审美价值却对其构成了最本质的规定。所谓的文学艺术史,必然是一部以美为核心价值的历史,与此相关的文学艺术批评史则必然是一部以美为评判尺度的历史。在这一历史中,美学精神是文学艺术的主导精神,审美批评则是衡量文学艺术批评是否具有专业品格的标志。
那么,中国传统的审美批评起于何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美学和艺术理论界一直认为,它的起点在魏晋时期。这一时代被视为人的自觉、美的自觉和艺术自觉的时代,连带也被视为中国关于文学艺术审美批评的发韧期。但事实并非如此。从文献看,起码自春秋时期始,中国已出现了关于美的专论,如伍举论美。同时也出现了成体系的文学艺术批评,如季札观乐。在这类文献中,出现了对美的定义性解释以及大量对乐诗之“美”的赞词。但是,现代美学家和文论家大多不愿将其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审美批评,原因在于这些资料往往以审美发端,最后将问题引向了社会伦理和政治。但我认为,所谓审美批评,应该是从审美出发的批评,它向社会伦理、政治的引申,不但不意味着这种批评缺乏美的纯粹性,反而说明美的视角具有强大的介入现实问题的功能。在西方,康德一方面说美是自由的形式,但同时他也讲美是对无限的眺望,讲美是道德的象征。他的后继者也往往是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中将审美批评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据此来看,中国现代美学和艺术理论家之所以在面对中国传统时恪守过于严苛的标准,一方面是因为缺乏对西方美学的真正了解,以至于将审美批评等同于唯美主义批评,另一方面则是将西方原本富有弹性的标准奉为了不可摇移的圭臬。现在,确实到了对这种状况做出改变的时候了。
下面,我将以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季札观乐”为例,谈中国审美批评的诞生问题。
一、关于“季札观乐”
春秋时期对音乐功能的定位,基本上存在两个维度,一是教化的维度,二是欲望的维度。前者是理性的,后者是感性的。但是,就音乐之作为艺术而言,无论要藉此达成理性目标,还是藉此满足耳目之欲,都无法否认它首先必须以乐音之美对人构成情感的触动为前提。正如《礼记·乐记》云:“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免也。”“情动于中,而形于声。”“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也就是说,构成音乐真正目的的不是教化也不是欲望,而是审美;构成音乐本体的不是理性也不是感性,而是情感。艺术的审美价值和情感特性,是对这门艺术的本质规定。据此,春秋时期的音乐艺术观念,如果仅仅在新与旧、雅与俗、教化与欲望、理性与感性摆动,就意味着对这门艺术的定位仍然是功利性的,都意味着对音乐之作为音乐的最具本质性的审美价值和情感特性的遗忘。在这种背景下,艺术观念的第三种维度,即审美与情感的维度是否存在,就成为判断春秋时期是否将音乐作为艺术来认知的标志。
春秋时期,“季札观乐”是最具代表性的艺术批评文献。季札(公元前576~前484年),春秋后期吴国公子,也是那一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艺术鉴赏家。公元前544年,他奉命出使中原诸国,在鲁地聆听了周乐的演奏。季札对每首乐歌都作了深富艺术见地的评价。相关记载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矣,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矣。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矣,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可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箾》、《南龠》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季札观乐,是“流传至今的孔子论诗以前最完整的文艺(音乐和诗歌)批评”。论者之所以说它“最完整”,一是因为它按照风、雅、颂的顺序,评价对象几乎囊括了今本《诗经》的全部内容,而且顺序也与《诗经》所涉歌乐大致相当。二是今本《诗经》中的风、雅、颂,仅余文字性的诗歌,乐已遗失,但季札所观,则不但诗、歌、乐兼俱,而且乐形成了对歌诗的主导和整体覆盖。三是季札的评论对象,除风、雅、颂之外,还包括上古舞蹈。这一方面说明春秋时期诗、乐、舞仍是一体的,另一方面也说明音乐特性是诗、舞的共同特性。乐包括歌、舞,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季札观乐作为艺术批评文本的完整性,在于它几乎囊括了那一时代的所有艺术对象,也在于它涉及了那一时代主要的艺术形式。同时,在批评方法上,既有对周乐的审美评价,又藉此引申到各侯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甚至以诗为谶,对国家运势做出预测,表现出批评方式的多元性。
二、审美批评诸层次
在诸种批评方式中,季札观乐表现出的最鲜明的特质是对周乐的审美评价,这也是中国艺术批评史开始从一般的社会历史批评向审美批评跃升的标志。通观《左传》中记载的季札“观乐”过程,他对周乐的评价共有18次,其中11次用到“美哉!”这一赞词。这种对音乐之美的高密度赞叹,不仅在春秋时代独有,而且也为中国艺术批评史鲜见。除了这类纯粹的审美评价外,他也对其中一些地区音乐的风格和形式特征做出了更具体的点评。比如他用“美哉渊乎!”评价《邶》《鄘》《卫》,这是说殷商王畿之地的乐歌,美在它传达出了幽深辽远的意蕴。他用“美哉,其细已甚”评价《郑》,则点出郑乐之美在其曲式的细腻和婉约。与此一致,他用“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评《齐》,是说齐乐美在曲风的宏大博广;用“美哉,荡乎!乐而不淫”评《豳》,是说豳地之乐美在其曲风洒荡而有节制;用“美哉,沨沨乎!大而婉”评《魏》,是说魏地之乐美在音律中和、博大而婉约。另外,他用“大之至”评《秦》,显然是注意到了起于西戎的秦乐既宏壮又粗鄙的特点;用“思深哉!”评《唐》,是注意到了尧帝旧都之乐表现出的深邃历史感;用“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评《大雅》,则是注意到了周王畿之乐温润而繁丰、委婉而有力的雍容气象。
在风、雅、颂三部分,季札对《颂》给予的曲风分析最多,即:“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在这段评价中,他注意到了典礼性音乐(“颂”)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它避免音乐情感表达和技法使用的偏至,以中道立场传达音乐的庄严肃穆感,并进而达至神性的崇高。论者一般认为,季札“连用了十四个类似的排比句来称美《颂》,表现了对中和之美的无比推崇”,并认为中和是季札评价《诗》乐之美的尺度。就季札总是在差异性范畴中寻找中间态、并避免音乐表情偏至的评价方式而言,这种讲法并没有什么错误,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中和并不是诸种力量由对峙导致的零和状态,从而导致音乐无风格,而是要让一种崇高的力量在中间地带汇聚并超拔而起。或者说,季札观乐,与其说凸显的是中和之美,倒不如说是中正之美更为确当。在由风、雅、颂形成的音乐体验序列中,惟有这中间地带的不断上升,最终才能使《颂》逼近人与神的交会和感通,也才能让季札感悟到先祖盛德的神圣与庄严,并对其做出“至矣哉!”的评价。
在这一渐次向音乐的最高境界挺进的过程中,季札的审美评价并没有到《颂》的演奏而终结,而是进一步由歌乐延伸到舞乐,即从《诗》走向了六代舞乐。就歌与舞的不同特性而言,歌虽然表达情感,但表达者与表达对象依然是分离的,也即:演奏或歌唱者的静立与歌乐本身的流动感存在着差异。到了舞乐,最大的变化是表演者由静转动,即以身体舍身投入舞蹈,从而使演员与作品的分离得到了最终克服。在内容方面,《风》和《雅》是对现实生活的歌咏,是音乐的空间展开形态;《颂》是对先祖的追忆,涉及音乐与时间及历史的关系。比较言之,上古乐舞也是时间性或历史性的,但它比歌颂王室近亲的《颂》涉及的历史更幽长、更宏大。这种乐舞也具空间性,但这种空间比被《风》和《雅》限定的国家地理空间更广远。同时,按照春秋时代即已存在的圣王谱系,愈接近历史的发端期,这圣王愈是具有更高的神力和德行。季札在鲁国所观乐舞,正是遵循了这种由近及远的历史顺序。其中,《象箾》《南龠》一武一文,当是有周一代常规性的典礼音乐,《大武》是武王之乐,《韶濩》是商汤之乐,《大夏》是禹乐,《韶箾》是舜乐。在此,《韶箾》显然代表了历史久远的极致,也代表了上古帝王德行的极致。
按照《尚书·益稷》的讲法:“萧韶九成,凤凰来仪。”这意味着《韶乐》不仅穷极人德,而且跨越了人的现实和历史经验的边界,通达于自然的无边神秘。从《左传》所记看,季札也在这种贯通天人的音乐中获得了审美体验的高峰状态,所以他说:“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地之无不载也。”在季札看来,这里的《韶箾》,既是对现实和历史性的审美经验的最终汇聚,也是向神性世界登临的最后一个阶梯。在现实层面,它冲破了被国家地理(《风》《雅》)限定的空间边界,进一步通向了浩渺的天地自然;在历史层面,它则冲破了被祖灵限定的亲族史,从对祖宗神的追忆扩及到消解时空意义的自然神。面对这种人神交会的超越之境,季札进入峰巅式的审美体验是可以想见的。如其所言:“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三、政治批评与审美批评之辨
季札观乐,不仅是“流传至今的孔子论诗以前最完整的文艺批评”,而且是孔子以前最完整的对音乐艺术的审美批评文献。它打破了西周以来政治、伦理观念对艺术的全方位笼罩和覆盖,使音乐艺术的审美价值得到凸显。它也不同于春秋乐论在理与欲、古与今之间的两极摆荡,而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介入音乐批评的新维度,即情感,并将实现精神超越作为音乐价值的最高表现。
当然,对于这一结论,学界有不同看法,甚至有些看法截然相反。如王运熙、顾易生云:“季札是用社会的、政治的眼光去看‘诗三百’的,他将‘诗三百’看作是社会、政治状况的反映。”再如张少康云:“观诗知政说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时发表的评论中。……季札从音乐(包括诗歌)的风格上去考察其中所体现的思想感情,从而借以辨别政治优劣,风俗好坏。这就把文艺看做是政治斗争的晴雨表,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提到一种极端化的高度,似乎政治完全可以决定文艺。”王运熙、顾易生将“季札观乐”视为社会政治批评,张少康将“季札观乐”等同于春秋时代流行的观诗知政说,他们重要的失误就是理论论述上的以果统因,即将由审美引发的政治余论视为这段音乐评论的重心。事实上,季札对风、雅、颂歌乐发出的“美哉”赞词,对于后发的社会、政治、民俗引申而言,是奠基性的。没有乐歌带来的深层的审美感动,后面的引发将无从谈起。也就是说,政治结论与其说是审美评价的归宿,毋宁说是审美评价的余物。
同时,王、顾、张对季札观乐所下的判断,也反映了音乐批评与文学批评对同一段文献的不同理解方式。文学性的理解往往将这段文献视为诗歌评论,重视诗的义解;音乐性的理解则将其视为音乐评论,重视乐的听觉感受。比较言之,重视诗的义解,就必然从中读出政治、民俗等诸多理性意义;重视听觉感受则必然关注季札从中获得的情感震撼。但事实很明确,季札在这段文献中观的是乐,而不是诗。将其当诗来理解,就忽略了其作为乐论存在的本质属性。对于这种因定位差异导致的对季札观乐价值取向的不同判断,我们不妨借公元前546年发生在郑国的一次赋诗活动做比较: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借诗言志,赋诗观志,是春秋时期用诗的通例。诗之所以包蕴人的心志,是因为它是语言艺术,其作用在于承载并传递思想,即以微言彰显大义。同样道理,诗之所以更易反映一个地区的社会政治状况,也在于诗可以通过怨刺、讽谏等手段使人的所思所想得到显明。先秦时期,虽然《乐记》中也谈到“审乐以知政”、“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但人们一般还是将此视为一种神秘而夸张的乐用观,真正能实现这一功能的还是当时公卿列士的献诗活动。通过上引文献与“季札观乐”的比较亦可看出:赵孟是借诗(而不是借乐)这种语言性的艺术来考察郑臣的思想状况,这已经反映出了诗与乐在功能上的重大差异。同时,对诗这种以语义传达见长的艺术,赵孟用的最重要的赞词是“善哉”,与此相对,季札对周乐用的最重要的赞词则是“美哉”。这已经说明,音乐作为乐音的运动形式,它直接诉诸人的听觉,无需思想的介入就可以对其做出价值判断;诗作为承载思想的艺术,它的价值重心在内容而非形式,也即思想内容的善恶是诗的根本问题。这种“美哉”与“善哉”的差异,可视为春秋时期音乐批评与诗歌批评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异,也说明审美批评在“季札观乐”中的凸显是源于春秋时代诗与乐的分离。
音乐鉴赏,是一种极简易又极复杂的艺术活动。就简易而言,音乐作为与人的听觉建立直接关联的艺术,只要人有感觉,就会从中获得快感。这就是音乐与文学相比表现出的更强的直观性。现代实验表明,一头母牛倾听音乐,也会因身体性快感而增加牛奶产量,这足可说明音乐快感的简易及效能。就复杂而言,音乐的快感又不是纯感觉的,它需要通过感性形式实现对其包蕴意义的纵深领悟和穿透,从而使音乐鉴赏从生理性快感向精神的超越之境擢升。这种精神意义的实现,意味着音乐的直观性,不是一般的感性直观,而是本质直观。这两个层面的差异,就像上面说的那只母牛,倾听音乐虽然有助于它产奶,但我们仍会说“对牛弹琴牛不懂”。母牛“不懂”的这个层面,就是借助感性形式实现的对内部意义的直接洞悉。由此看“季札观乐”就会发现,这位春秋时代伟大的音乐鉴赏者和批评家,虽然一听周乐马上就得出了“美哉”的判断,但这种判断既基于感性又超越感性,既诉诸直观又包蕴理性,既立足形式又顿悟意义,既无目的又合乎目的。一句话,它既是审美判断,又必然指向合目的的善。正是在这种看似背反、实则符合音乐鉴赏一般规律的意义上,季札将纯粹的音乐鉴赏引向社会政治、风俗和道德问题,才是合理的。这也是中国从春秋时代起,一方面将音乐视为一种“听”的艺术,同时又作为“知”的对象的原因。
可以认为,知解力或理性对直观性快乐的校正或补充,保证了季札观乐不同于当时一般人对郑卫之音的欲望化追逐。同时,也正是季札对音乐的纯感性切入方式,或者个体在音乐中的直接在场,才避免了他以当时业已固化的伦理原则对音乐做出先入为主的判断。这是一种双向的挟持,前者保证了音乐的合目的性,后者保证了个体经验的鲜活性。我们之所以说“季札观乐”是春秋时代音乐审美批评的典范性文本,原因就在于这种双向的挟持,使鉴赏者可以沿着中间隆起的第三条路径垂直上升。这中间的道路,是从音乐的具体体验走向概念的一般,而不是以概念的一般去预先检验音乐体验的合法性。按照康德的讲法,也即它是基于反思性的判断力,而非规定性的判断力。同时,按照人类先天的向善原则,它又自然地与道德的普遍要求相联结,使“审乐以知政”成为可能。或者,审美评价并非天然地拒绝政治或伦理评价,根本问题在于这种评价是源自个体审美经验的引发,还是在审美之前已经先行介入。从这段文献可以看出,季札的方式是从对周乐的审美体验自然走向了政治和伦理评价,所以政治、伦理评价的出现并不会影响这一“观乐”活动作为审美批评存在的属性。四、音乐认知模式与审美批评
对于春秋时期的音乐理论,在政治伦理批评和审美批评之间做出辨析是重要的,这是因为,当时人对音乐的认知面对着一个悠久而强大的传统,这就是自西周开始的乐教。按《周礼·大司乐》,西周贵族子弟13岁开始接受音乐教育,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乐德,即音乐中传达的“中、和、祗、庸、孝、友”等观念,对音乐的定位和解释也是泛政治化和道德化的。此类教育固然有助于人在幼年时代德性的养成,但由此形成并逐渐固化的音乐认知模式,必然使人在介入音乐鉴赏之前,已预设了一套先入为主的判断标准,从而使人感受音乐的真切性和鲜活性受到威胁。同时,音乐欣赏过程也极易成为对固有标准的真理性的印证,而非以“纯真之耳”感受的过程。
据此来看,春秋时期产生旧乐与新乐或者雅乐与郑声的重大争论不是偶然的。所谓雅乐,无非就是与通过后天教育形成的音乐认知模式相一致的音乐,它因印证了这种模式而让人感觉舒适。相反,新乐或郑声则与这种预在的接受模式相冲撞,必然会因让人心理不适而产生道德上的恶感。但是,新乐作为冲出预在的乐教模式的音乐,它的存在却仍具有无以复加的重要性,即:它虽然因溢出了旧乐规定的审美惯例而被称为“淫声”、“过声”,但音乐欣赏却正因为无章可循,而为审美的当下直观提供了契机。或者,新声的无章可循,使其可以轻易摆脱传统乐教鉴赏模式的遮蔽,使人获得生动、鲜活的审美体验。魏文侯之所以听“郑卫之音不知倦”,应与此种体验的非模式化密切相关。
关于春秋时期音乐鉴赏中认知模式与情感态度之间的矛盾,《左传·桓公九年》提供了一件重要的案例。其中记云:“冬,曹太子来朝。宾之以上卿,礼也。享曹太子。初献,乐奏而叹。施父曰:‘曹太子其有忧乎!非叹所也。’”文中的曹国太子,在鲁国听到初献之乐发出了一声叹息。按照当时侯国间的交往礼仪,这种叹息是非礼的,也证明曹国太子缺乏良好的音乐训练,但这又是曹太子对初献之乐的直接情感反应。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对于音乐,到底是应该根据传统乐教做出程序性的反应,还是纯任审美直觉,将观乐而叹视为理所当然。当然,就鲁国作为春秋时期周礼最坚定的堡垒而言,曹太子受到施父的指责是有道理的,但也提示出模式化的音乐认知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压抑。同时也说明,即便面对雅乐,在当时也存在着程式性和直觉性两种反应方式。施父认为曹太子不应该在官方场合发出叹息,反向证明了他在非官方场合似乎可以发出叹息。就此而言,对待雅乐,在当时也未必不可以采取私人的、情感的态度。或者,雅乐并没有因追求合目的的善而彻底丧失了审美。
有论者曾将周代雅乐称为“拖沓平板的庙堂音乐”。这种评价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暂且不论,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与此对立的郑声肯定更能激发人的生命本能,否则也不会让听者“不知倦”,并在那一时代广为流传。但必须注意的是,与音乐所能提振起的崇高精神和理性情怀相比,这种对生命本能的激发毕竟是生物性的,两者的品位和格调并不存在于同一个层级之上。同时,雅乐虽然承载着政治和伦理内涵,其本质是观念性的,但这种观念既然以音乐的方式被表现,它也就必然显现为感性,并因此可以成为人直观和情感把握的对象。受近代认识论的影响,今人一般强调认识过程总是沿着从感性到理性、从现象到观念的路径发展,往往忽视了理性向感性的生成、内容向形式的积淀,或者观念向具体现象的物态呈现。可以认为,正是这种包蕴理性意味的形式,才保证了艺术既是感性的、能够激发情感的,同时也具备意义的深度和精神的高度。
由此反观季札观乐,我们之所以说它是审美批评,固然是因为它理解周乐的切入点是感性的、直观性的,但显然它又借助这种感性实现了对理性精神的洞见,并因这种精神的引领而最终登上审美的高峰。这种精神性的愉悦,既避免了俗乐因诱发人的生物性欲望而出现的浅薄和反道德,同时也避免陷入概念化的僵硬和死板。它具有伦理性,但它是一种被审美精神渗透和灌注的伦理,或者说,是被审美的无目的最终带动的合目的。正是因此,季札观乐,虽然从审美走向了政治、风俗、道德,但并不足以减损它作为审美批评的属性。甚至相反,正是这一系列看似非审美要素的支撑,才使雅乐有了积厚之功,并最终将倾听者送上了“蔑加于此”的审美高峰。
注释
[1][4] 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上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2] 季札“观乐”顺序为:《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小雅》《大雅》《颂》。今本《诗经》排序为:《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雅》《颂》。比较可以看出,被季札所评价的乐歌,仅缺失《郐》和《曹》(“自郐以下,无讥焉。”),《豳》《秦》比《诗经》顺序靠前。按照孔颖达的看法:“郐、曹二国,皆国小政狭,季子不复讥之,以其微细故也。”又:“季札此时遍观周乐,《诗》篇三百,不可歌尽,或每诗歌一篇、两篇以示意耳,未必尽歌之矣。”(参见《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96页,第1101页)
[3] 汪祚民:《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2-83页。
[5]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6] 如《礼记·乐记》云:“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另如《吕氏春秋·本味》:“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7] 黄鸣:《左传与春秋时代的文学》,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4页。
刘成纪: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韩宵宵)